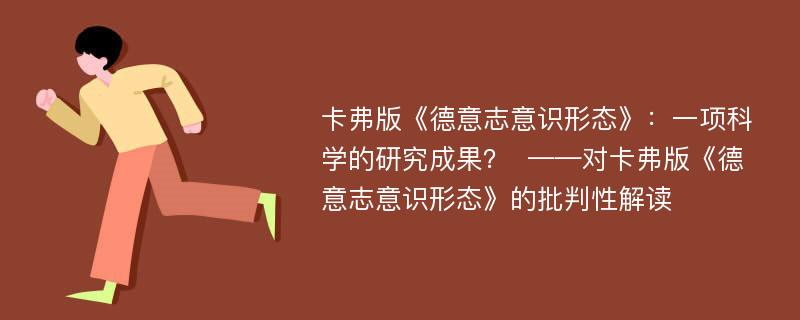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研究·
摘 要:卡弗认为自己版本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一项科学的研究成果。其以时间顺序为编辑原则,崇尚客观中立的、科学的编排方案,最终把《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视作一部季刊文集。然而,时间顺序原则不过是旧原则的再现,仍然不可避免地遭遇一系列困境;纯粹客观中立的科学的编排方案不过是一个无法达成的目标;季刊文集说不过是解构《德意志意识形态》,解构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解构历史唯物主义,建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卡弗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时间顺序原则;纯粹客观中立;编排方案;季刊文集说;马克思主义
特瑞尔·卡弗(Terrell Carver)是英国布里斯托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UK)政治理论教授,也是国际知名的西方“马克思学”学者,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以文献学、结构主义和后现代方法论的方法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著作颇丰。《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是卡弗近年来的一个研究重点。2014年,他出版“语境版”(contextual edition)《形态》(以下简称卡弗版《形态》)。卡弗版《形态》以2004年MEGA2年鉴版(《马克思恩格斯年鉴·2003》)为底稿,标点符号和大写同英语用法一致,但也尽可能地将德语手稿的翻译考虑在内,并用罗马字体和黑体字体分别表示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字迹。作为卡弗以版本的政治史为方法论上的指导原则全面地研究既有诸版《形态》的一个成果,卡弗版《形态》强调彻底贯彻时间先后顺序原则;崇尚纯粹客观中立、科学的编排方案;把《形态》手稿视作一部季刊文集。卡弗版《形态》一经推出即在国内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2017年11月,国际学界期待已久的MEGA2版《形态》终于出版,《形态》中文第二版的编译出版也提上了议程。那么,《形态》中文第二版应当参照哪个版本、遵循什么原则进行编译出版呢?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对既有各种有影响的方案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作出正确的抉择。对卡弗版《形态》的批判研究,由此就具有了中国现实性。
一、卡弗版《形态》的行文架构
卡弗版《形态》在编排结构上采取双栏页排版,在文段安排上强调彻底贯彻时间顺序原则,充分凸显出字、句、段以及文本的发展变化。(1) 在排版结构和文段安排方面,卡弗对于广松涉的《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1篇》给予了高度的肯定性评价,认为这是《形态》手稿阐释史上一大进步,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位编者努力按照这个方式出版整部1845-1846年手稿”。不过,卡弗认为广松版《形态》存有诸多缺陷,如再次建构平滑文本《费尔巴哈》章,基于MEGA1,而不是原稿,主观加上拼写、标点等。参Terrell Carver and Daniel Blank,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Editions of Marx and Engels’s “German ideology Manuscript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4,p.140,pp.109-110.据此,其行文架构如下(2) Terrell Carver and Daniel Blank,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Editions of Marx and Engels’s “German ideology Manuscript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4,pp.143-148,pp.157-158.排版结构中的阿拉伯数字和字母均为了便于后续讨论由笔者所加。关于其翻译,因卡弗版《形态》与MEGA2年鉴版一致,以下关于各部分之间的中译文均参照MEGA2年鉴版的中译本,部分没有出现在该年鉴版中且带有书名号“《》”的翻译均参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版,除此之外,一切翻译根据卡弗的英文原文直接翻译。这大体上同MEGA2年鉴版一致,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卡弗版《形态》收入了圣麦克斯和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部分,没有收入马克思和魏德迈所写的《布鲁诺·鲍威尔及其辩护士》。但是,正如帕格尔博士和胡布曼博士所指出的,陶伯特女士的MEGA2年鉴版如果将圣麦克斯手稿纳入,那么其时间顺序原则的编排将毫无效力,也不符合MEGA编排准则(参见赵玉兰:《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情况分析——访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MEGA工作站格哈尔特·胡布曼博士和乌尔里希·帕格尔博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8年第5期,第7页)。:
(1)马克思的文章《答布鲁诺·鲍威尔》
(2)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写作有关鲍威尔文章的剩余部分
(3)批判《圣麦克斯》
a 压缩前的手稿(“拓展阶段”)
然而,这不过是旧原则的再现,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一系列的困境,卡弗版《形态》的编辑原则是时间先后顺序原则(chronological order),即对所有文段按照写作的时间先后顺序进行排列。其与逻辑编排原则(logical order)相对,甚至未能解决历史上在贯彻此原则所产生的诸多问题,更映射出卡弗自身对《形态》的判断。
(4)马克思、恩格斯共同的有关鲍威尔文章的修改的剩余部分(马克思文本纠正/片断修改和将文章划分为“费尔巴哈”“历史”“鲍威尔”等)
(5)批判《圣布鲁诺》
(伴随着“鲍威尔”文本残篇,这些残篇从有关鲍威尔文章的剩余修改部分拿出来的)
(6)马克思编码的“主手稿”(3) 这部分稿子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历史 草稿和笔记》。(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写作有关鲍威尔的文章的已修改的残篇,“费尔巴哈”“历史”等,没有“鲍威尔”的文本残篇,加上来自“圣麦克斯”的修改的剩余段落)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步,人们在妇幼保健工作方面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相关技术和管理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妇幼保健档案管理属于妇幼保健工作一项主要内容,能够为妇幼保健工作的展开提供重要的信息资源,提高档案信息利用有效性,并为妇幼保健工作提供数据支撑,提高妇幼保健工作质量与规模,促进其发展进步。当前妇幼保健档案管理工作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很难取得理想的管理效果。必须要重视妇幼保健管理水平的提高,对原有妇幼管理工作进行革新,本文就此展开了研究分析。
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学”的典型代表,卡弗因袭该学派传统,在方法论上采取“较为温和的后现代主义方法”(20)卡弗:《政治性写作:后现代视野中的马克思形象》,张秀琴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2、237-239页。——语言学、视域融合等后现代主义方法论。同时,作为MEGA2编委,卡弗的理论研究因卡弗参与编辑马克思恩格斯文本而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文本学倾向。对此,在卡弗看来,苏东剧变等重大政治事件已然使传统的马克思形象难以为继,也将引导我们重新评价马克思,为马克思“做他自己”提供了契机。而这就有必要解构传统马克思的叙事方式,解释和捍卫“多样性的马克思”。这是一个开放的马克思。卡弗对《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研究对马克思文本进行语言语境分析,强调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互动关系,强调对马克思理解的多元性。(21)卡弗:《政治性写作:后现代视野中的马克思形象》,张秀琴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2、237-239页。关于这一点,卡弗在卡弗版《形态》中表示再编辑《形态》手稿的重点是再现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思考(thinking),而不是思想(thought)。这最终并没有提供任何知识性答案,而是作为一个开口,一种思维方式,探究理解的运作机制,并使我们受益。(22) Terrell Carver and Daniel Blank,Marx and Engels’s “German ideology” Mscripts:Present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Feuerbach chapter”,New York:Paave Macmillan,2014,p.4.
b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引言
c 《I.“莱茵年鉴”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哲学》
第2卷:
(9)马克思的《序言》
盆腔炎是临床常见的妇科疾病,主要分为慢性盆腔炎和急性盆腔炎两种。其中慢性盆腔炎主要是由于急性盆腔炎我能治愈或者因为患者体质较差,病程迁延导致,临床表现主要为下腹部坠胀、疼痛和腰骶部疼痛,对于性交后和月经前加剧[3]。对于病程较长的患者来说,盆腔炎还可能导致患者出现不孕、失眠、神经不振和输卵管妊娠的症状,不仅影响患者的身体健康,还会给患者的心理健康造成很大的损伤[4]。
从文段安排上看,卡弗版《形态》再现字、句、段以及文本的发展变化:对于同一文本,再现其不同历史阶段,包括增删修等;对于不同文本,展现其相互关系。这种方法终将呈现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手稿的创作历程,不会产生“最终文形”(versions of last hand)和作为“最终成品”(end product)的“主题卷”(thematic volume)。这种版本将不同于MEGA版:不再像已有的MEGA版那样,将《形态》的整个手稿分为主题卷和附属资料卷进行编辑处理,而完全以写作的时间先后顺序依次排列所有文本片段以及各部分的最终文形,再现马克思恩格斯的创作历程。卡弗认为相比那种根据主观判断编排手稿的做法,这种按照时间顺序编排手稿的做法是一种日记式重构手稿的做法,便于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及其变化过程,尽管其在操作上确实有难度。(5) 张一兵、特瑞尔·卡弗:《〈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否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张一兵对话特瑞尔·卡弗》,《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1期,第7页。
二、时间顺序原则:旧原则的再现及困境
从版式安排来看,卡弗版《形态》采用了双栏页排版,并在字迹上了做出了明显的区分:左手页展现出各种变化、插入等,以突出手稿原貌,右手页展现的是平滑流畅的文本(smooth text),便于读者阅读;为了区分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的笔迹,卡弗用罗马字体(roman typeface)表示恩格斯的笔迹,黑体字(bold typeface)表示马克思的笔迹。这给予了原稿极大的尊重,也将最大限度地限制编者意图,使新版文本的排列顺序与原稿顺序尽量保持高度的一致。更为重要的是,卡弗认为这记录了一种写作对话模式——这种排版拒斥把整个手稿用单一的权威声音和语调的处理方式,展现出作者们的思想变化轨迹。(6)Terrell Carver and Daniel Blank,Marx and Engels’s “German ideology” Manuscripts:Present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Feuerbach chapter”,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4,p.5,p.7.在卡弗看来,这实质上不是学术化的讨论,而是政治批判——对政治身份和政治立场以及欺骗性力量的幻想进行无情的批判。(7)Terrell Carver and Daniel Blank,Marx and Engels’s “German ideology” Manuscripts:Present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Feuerbach chapter”,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4,p.5,p.7.
但是,时间顺序原则并非卡弗首创。在卡弗看来,这一原则以1962年巴纳关于《形态》手稿的新发现为契机开始运用于之后的《形态》诸版本之中。这特别体现在MEGA2年鉴版之中。在后意识形态时代,MEGA2经由苏东巨变绝处逢生之后便以“去意识形态化”“国际化”以及“学术化”为编纂原则。MEGA2年鉴版便在这一原则指导之下的研究成果,其明确宣称以时间先后顺序排列这7份手稿,否定《形态》一书的存在,尤其强调把其中的费尔巴哈章看作一个未完成的、多层次的手稿。但是卡弗认为它试图呈现出费尔巴哈章以及最终文形,这一做法预设了最终文形,体现着后意识形态时代中的一种政治策略。(8) Terrell Carver and Daniel Blank,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Editions of Marx and Engels’s “German ideology Manuscript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4,pp.121-122,p.137.
b 压缩后的手稿(“缩短阶段”;没有剩余段落)
2.4.2 精密度试验 取供试品溶液(S16),连续进样6次,考察色谱峰保留时间的一致性,10个特征峰保留时间RSD小于0.02%,峰面积RSD小于1.10%。同时考察各色谱峰的相似度,用相似度评价软件计算,测得的色谱指纹图谱与其所得的共有模式图的相似度均为0.985,表明仪器稳定,精密度良好。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阳离子交替吸附作用,水中 Ca2+、Mg2+置换出岩土所吸附的 Na+,使得 Ca2+、Mg2+含量减少,Na+含量增加。这也是本区Cl-Na型水形成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卡弗版《形态》在贯彻时间顺序原则时不可避免地遭遇一系列困境,并非解决历史上在贯彻此原则所产生的诸多问题。
(一)关于部分手稿的安排
关于第7部分手稿安排。各个手稿写作的时间先后顺序决定了各个手稿在卡弗版《形态》的位置。但是,通过仔细比较,我们发现第7部分和第8部分、第9部分之间编排有悖于这一原则。第7部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是恩格斯写于1847年2月到4月,而第8部分、第9部分这两篇文章都写于1846年。根据这一原则,第7部分应该排在手稿的最后。但是实际上作者却毫无理由地就将第7部分插在第6部分和第8部分之间。对此,卡弗只是指出第7部分“这一手稿准确的产生历程有待调查”,以“没有理由”(no reason)一笔带过。
关于第1部分手稿安排。第1部分手稿是《驳布鲁诺·鲍威尔》,被置于篇首。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卡弗版《形态》将马克思的一篇反驳文《驳布鲁诺·鲍威尔》作为开篇之作。其理由在于:一方面,《维干德季刊》第三卷上鲍威尔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特点》攻击马克思后,马克思决定必须独自写一篇批判性回复,进行自我辩护;另一方面,这篇文章标有1845年11月20日,在1846年1月22日到24日之间出版于《社会明镜》杂志。(9)Terrell Carver and Daniel Blank,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Editions of Marx and Engels’s “German ideology Manuscript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4,p.144,p.79,p.148,p.80.这一做法及其理由说明与MEGA2先行版高度一致。但是这一理由显然不具有说服力。然而,这一安排却反映了卡弗关于《形态》作为一本书不存在的基本观点:“既不是在1845年春,也不是在1845年10月末11月初,马恩计划写以《形态》为标题的书或其他的著作。受到维干得季刊第三卷出版的诱发,马恩仅仅写一组文章,捍卫他们自己的观点。其中一个是作为‘note’出版;其余的,旨在更加具体,变得越来越长。”(10)Terrell Carver and Daniel Blank,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Editions of Marx and Engels’s “German ideology Manuscript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4,p.144,p.79,p.148,p.80.因此,按照时间先后顺序,《驳布鲁诺·鲍威尔》成为卡弗版《形态》的第一篇文章。换言之,卡弗认为《形态》作为一本书是不存在的。而卡弗的这一做法恰恰与卡弗自身对于《形态》手稿的理解构成了相互印证关系:一方面,基于这种理解,《驳布鲁诺·鲍威尔》理应为开篇之作;另一方面,《驳布鲁诺·鲍威尔》成为卡弗版《形态》开篇之作正使卡弗的这一理解得以证明。
(二)关于各个手稿写作的判定
由于《形态》只是手稿,其本身具有未完成性、不连续性,要判断其各部分手稿的写作时间却极其艰难。根据时间先后顺序原则,各部分手稿初稿、修改稿、誊清稿、刊印稿等手稿的创作历程及其相互关联必须得以体现。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并不打算写一本名为《形态》的书,即使决定对鲍威尔、施蒂纳、“真正的社会主义”等进行批判之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写作提纲。而在写作过程中,它从字、词、句乃至整个文段也是不断地得到调整、修改、删除。所以,且不说卡弗对各个手稿写作时间的判定是否合理,他们的这一行文结构也未能将处于写作各个阶段的手稿准确地以时间顺序体现出来。这尤其体现在《形态》的《费尔巴哈》章手稿的编辑过程中。另外,关于1845—1846年手稿写作结束时间,卡弗也未作深入论证,只是指出,一方面,1846年夏季,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实现了“自我澄清”,也想更直接地投入到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另一方面,1846年12月,马克思决定写作《哲学的贫困》。(11)Terrell Carver and Daniel Blank,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Editions of Marx and Engels’s “German ideology Manuscript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4,p.144,p.79,p.148,p.80.
(三)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对手稿所做的编排
关于《形态》两卷本划分,1845年5月14日,马克思给魏德迈写的信用“第一卷”“第二卷”“那部著作”以及“两卷书”来代称《形态》。(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69-372页。这表明马克思已经对《形态》做了两卷本的划分。然而,尽管卡弗承认了这一点,但是他却认为“仍然不知的事是这是否应用于书卷的顺序或杂志期刊或其他有许多作者编辑的季刊出版”(13)Terrell Carver and Daniel Blank,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Editions of Marx and Engels’s “German ideology Manuscript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4,p.144,p.79,p.148,p.80.。如此一来,他不仅否认《形态》手稿作为一本书的存在,而且还否认《形态》手稿存在写作计划的存在。此外,有研究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手稿定稿时也对手稿做了系统的编排:
第1卷:
977 信息化时间追踪管理模式对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救治速度的影响 沈红健,邢鹏飞,张永鑫,吴 涛,张永巍,柯 骏,刘建民,杨鹏飞,邓本强
一、费尔巴哈;莱比锡宗教会议;二、圣布鲁诺;三、圣麦克斯;莱比锡宗教会议闭幕。
REN Jie, HUANG Hai-dong, WANG Qin, YANG Yu-guang, HUANG Yi, LI Qiang, BAI Chong
(8)“I.费尔巴哈”的三个开头以及“残篇1”“残篇2”(4) 这部分便是马克思恩格斯的《I.费尔巴哈 A.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I.费尔巴哈 1.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哲学》《I.费尔巴哈 导言》《I.费尔巴哈 残篇1》和《I.费尔巴哈 残篇2》五篇稿子。不过这些稿子之间的顺序,卡弗并没有作区分,参见Terrell Carver and Daniel Blank,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Editions of Marx and Engels’s “German ideology Manuscripts”,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4,p.147.
第三,新媒体赋予我们行动与实践的权力。表达本身就是一种行动,这里的行动强调表达与现实的行动相结合[9](P13),强调虚拟与现实的结合与行动。新媒体通过信息赋权使得每个个体都有可能成为自由表达的主体,然后通过交互行为快速地将表达转化为实践,线上活动和线下活动的结合,最大可能地打开了现实行动的空间,推动了传统信息传播中难以达到的实践改革。
“真正的社会主义”;一、《莱茵年鉴》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哲学”;四、卡尔·格律恩。《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1845年达姆施塔特版)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编纂学;五、“荷尔斯泰因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预言。(14)英格·陶伯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的问题和结果》,见林进平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285、285-302页。
(7)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准确的产生阶段必须进一步调查)
综上所述,小剂量阿司匹林治疗特发性胎儿生长受限合并脐动脉血流异常能较好地改善胎儿生长发育,降低血流阻力,提高胎儿血液供给,且不良反应少,安全有效。由于研究对象有限,可能会对结果造成一定程度偏差,会在进一步研究联合用药治疗特发性胎儿生长受限合并脐动脉血流异常中着重完善。
而在手稿写作过程中,写作框架多有变动。根据卡弗的严格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原则,卡弗版《形态》不仅无视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所拟定的体系结构,而且还无视马克思恩格斯这一体系结构安排背后的理论寓意及其价值。
针对时间顺序编排原则,MEGA2 I/5编者格哈尔特·胡布曼博士(Dr.Gerald Hubmann)和乌尔里希·帕格尔博士(Dr.Ulrich Pagel)十分明确加以指责,认为要尽可能复现手稿,制作一篇完整版本并不仅仅要考虑到写作时间顺序,还要考虑到MEGA编辑准则、手稿既有的标题、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手稿所作的页码编号、作者的预先说明以及回顾性说明等所有相关因素。显然,卡弗版《形态》仅仅考虑时间先后顺序这一因素,对诸如手稿编码等其他相关因素不屑一顾。(15) 赵玉兰:《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情况分析——访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MEGA工作站格哈尔特·胡布曼博士和乌尔里希·帕格尔博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8年第5期,第8页。另外一件具有戏剧性的事件是陶伯特在MEGA2年鉴版中着重强调时间顺序的编排原则,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的问题和结果》中对严格按照时间顺序的编排提出质疑(16)英格·陶伯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的问题和结果》,见林进平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285、285-302页。。总之,卡弗版《形态》特别强调时间先后顺序并不是一个明智之举,不过印证了卡弗对《形态》手稿判定。
三、纯粹客观中立、科学的编排方案:一个无法达成的目标
卡弗版《形态》号称严格彻底贯彻时间顺序原则,摈弃一切主观肆意,崇尚纯粹客观中立和科学。从科学角度来看,这确实可避免诸多不必要的主观建构或解构,是学术编排中所追求的一种原则。但是,“编辑即阐释,编者即阐释者”(卡弗语)。卡弗的这一方案不过延续了西方“马克思学”一以贯之的策略——以科学地研究马克思之名建构异于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具体来说,卡弗意在以纯粹客观中立、科学的方案向世人阐明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西方“马克思学”之“解释学转向阶段”的特征——对马克思的任何阐释只是作为一种可能的阐释,并不具有唯一绝对的性质。卡弗与西方“马克思学”在研究原则和实质方面都有高度的一致性。西方“马克思学”素来以学院化的姿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活动和著作思想,强调学术研究的客观中立原则。然而,西方“马克思学”在20世纪的发展始终处于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对话、对抗之中,是一种异质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景观。其表面上是一种深入马克思思想及其文本的马克思研究,而实质上不过在质疑苏联式马克思主义,攻击苏联式社会主义。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东巨变,苏联社会主义不复存在。由于其存在的基质发生变化,加上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发现进入后成熟阶段以及该学派经过数十年的积累已形成大量共识,其在西方学院中迅速边缘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解释学转向阶段”。(17) 张亮:《西方“马克思学”研究方法的历史演替及其当代走向》,《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第31-32页。这一时期学术研究更加专业化、学术化、多样化以及学院化,其典型特征便是旨在强调任何研究主体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建构都具有合理性。这一阶段的西方“马克思学”糅合了后现代主义、解释学等方法论资源。对此,卡弗指出:“伽达默尔和利科的解释学、德里达的解构,以及剑桥的‘情境主义者’,都极大地改变了对文献的理解方式,也同时改变了对作者意图、语言本身的地位和重要性以及书写者本人角色的看法等。对马克思的阐释工作有必要与这种后现代思想时代保持同步。”(18)卡弗:《政治性写作:后现代视野中的马克思形象》,张秀琴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2、237-239页。其表现出“疑古主义、挑战既有定论”“文本编辑崇拜”“自我翻新”以及“‘自由’嫁接”等特征。(19) 张亮:《西方“马克思学”研究方法的历史演替及其当代走向》,《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第32页。换言之,借助这些方法论资源,西方“马克思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换了新装,但实质上却仍在重操旧业。
a 《卡尔·格律恩。“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1845年达姆斯塔德版)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编纂学》
如何判断出写作手稿的时间先后顺序?我们知道,《形态》现存手稿以印张的形式呈现,分别被编码,以双栏形式,其内容不连续,与不同主题相关,此外,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笔迹明显不同。卡弗认为这反映出原始手稿的写作时间。据此,卡弗版《形态》抛除任何理论预设,不再对手稿进行有逻辑地架构,而是恢复马克思、恩格斯在手稿的写作历程,展现整个手稿中字句段篇等各自的变化及其相互关联以及所谓的最终文形。其凸显的是他们的思考(thinking),而不是他们的思想(thought)。
这种让马克思卸去后继者赋予他的形象的举措似乎真的可以让马克思“做他自己”。然而,在反对传统权威马克思的道路上,卡弗强调马克思的多元性,强调研究主体对马克思理解不仅具有相对性,而且还具有合理性。如此一来,任何一个研究主体马克思的阐释都是合理的。按照这一理论逻辑,卡弗作为阐释者一员,可名正言顺地将马克思人道主义化,提出否认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的论断。这同样是合理的,因而也是无可厚非的。由此可见,卡弗的这一尝试未尝不是在主观建构马克思,其所崇尚的客观中立的科学原则未尝不是一种主观原则。更为关键的是,卡弗的这种主观原则实际上把马克思人道主义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卡弗所说的纯粹客观中立的科学的编排方案是一个无法达成的目标。
四、季刊文集说:对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的文献学解构
卡弗版《形态》认为《形态》的著作说及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过是政治建构的产物,从文献学角度得出《形态》手稿是马克思、恩格斯和魏德迈三人合作的季刊文集的结论。但是,这不过以文献学解构之名解构《形态》,解构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解构历史唯物主义,把科学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显然,这仍然是在主观地建构马克思,消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
关于《形态》手稿的季刊文集说,卡弗提出两点:
其一,作为一部历史唯物主义著作的《形态》不过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政治建构的结果。
20世纪20-30年代,《形态》在苏联当局官方领导与支持之下被梁赞诺夫和阿多拉茨基先后出版发表。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两者各有特色和目标。但不可否认的是,两位领导人都想借助出版、阐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此,《形态》在梁赞诺夫和阿多拉茨基领导之下仍然具有共同的特征:用逻辑结构架构手稿。这在阿多拉茨基那里特别明显。在阿多拉茨基看来,《形态》被认为首次系统阐释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种思想一直影响到后来东德1958年版《形态》、1970年代的英语版《形态》等。20世纪60年代以来,既有各版试图以手稿写作的时间顺序呈现出手稿原貌。但从本质上来看,它们并没有改变一直以来构建出一个有最终文形的做法。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之类的简单导言表明研究者主观赋予该手稿以不被作者所意图的意义。
成本管控已从粗放式的管理向精细化管理升华,从静态管理向动态管理转化,从事后核算向事前管控发展,从成控管理部门独撑门面向“三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管理迈进,从传统管理向信息化管理升级。成本管控已成为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中的重要一环,需投资方的项目策划立项、勘察设计、招采供应、合约规划、财务、工程施工管理及营销等各个环节密切配合,才能实现效益、利润的最大化,实现目标成本的不突破,实现项目功能的最优化[1]。成本管控的措施很多,本文主要从5个方面进行阐述分析。
其二,卡弗考察《形态》手稿的形成背景及其特征,得出《形态》尤其费尔巴哈章根本不存在的结论。
卡弗明确宣称:“所谓的《I.费尔巴哈》章实际上并没有写成,因此也不存在。自从1924年所印刷的东西实际上只是不连续残篇的集合,其写于‘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不管怎样,只有这些与费尔巴哈有关的详细部分可能被马克思用作计划批判费尔巴哈章部分的草稿。”(23)Terrell Carver and Daniel Blank,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Editions of Marx and Engels’s “German ideology Manuscript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4,p.81,p.80,p.81.pp.91-92,p.80,pp.55-56.虽然这部分手稿与费尔巴哈有关,且被编码,但是,卡弗认为:(1)编码并不是基于内容的逻辑推理,不足以说明他们用以出版,仅仅反映手稿写作的时间先后顺序,以便于辨识,以免他们将这些手稿弄混,除此之外,别无它意;(2)其直接原因是他们对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态度;(3)1846年初夏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为这部分手稿增加新思想,也没有可添加的新材料,因此,他们放弃该部分的写作。(24)Terrell Carver and Daniel Blank,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Editions of Marx and Engels’s “German ideology Manuscript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4,p.81,p.80,p.81.pp.91-92,p.80,pp.55-56.
卡弗断然否认作为一部著作的《形态》的存在,认为我们熟知为《形态》的东西实际上只是不同批判以一个松散顺序被编排起来的。理由在于:(1)他们没有找到出版商;(2)马克思于1846年2月打算写《哲学的贫困》;(3)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些编码“Ⅰ.费尔巴哈”“Ⅱ.圣布鲁诺”“Ⅲ.圣麦克斯”指代“章节”;(4)马克思自己相关论述也不足以说明《形态》计划就直接等于《形态》作为事实存在。(25)Terrell Carver and Daniel Blank,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Editions of Marx and Engels’s “German ideology Manuscript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4,p.81,p.80,p.81.pp.91-92,p.80,pp.55-56.关于《形态》写作起因,卡弗指出《形态》手稿不过是马克思、恩格斯受到《维干德季刊》第三卷出版的诱发而写的一组文章,以捍卫他们自己的观点;在写作该组文章期间,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其他文章应该与格律恩之类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相关;于是,第二部写作以“真正的社会主义”为标题。(26)Terrell Carver and Daniel Blank,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Editions of Marx and Engels’s “German ideology Manuscript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4,p.81,p.80,p.81.pp.91-92,p.80,pp.55-56.
且不说《形态》计划是否存在,卡弗认为马克思自己相关论述也不足以说明《形态》计划就直接等于《形态》作为事实存在,即卡弗否认作为一部著作的《形态》的存在。对此,卡弗指出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顾性说明更可能导致马克思恩格斯仅仅想要通过写作一系列的文章“发展他们的世界观”,其所提到的“自我澄清”早已可能不是作者1845年春所期待的那样。(27)Terrell Carver and Daniel Blank,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Editions of Marx and Engels’s “German ideology Manuscript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4,p.81,p.80,p.81.pp.91-92,p.80,pp.55-56.
然而,其季刊文集说不仅不是一个新的判定,因为戈劳维娜、英格·陶伯特以及MEGA2 I/5都提出季刊文集样稿说,(28) 戈劳维娜根据其所负责编纂的MEGA2 III/2(马克思恩格斯1846年 5月至1848年 12月之间的往来书信)把《形态》手稿判定为“两卷季刊原稿说”,参见郑文吉:《〈德意志意识形态〉与MEGA文献研究》,赵莉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1-67页。英格·陶伯特作为《形态》手稿资深研究专家根据手稿的特征、题材、篇幅和形式把《形态》手稿视作季刊文集样稿,参见英格·陶伯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的产生史》,见林进平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卷,北京:中央编译局,2014年,第41、51页。MEGA2 I/5在《形态》既有的编译研究的基础上以“最终的稿本”自称,根据《形态》手稿不完整性和不连续性认为其最重要的特征是批判,而不是建构(“制定自己的理论”),因而把其判定为季刊,不过认为作为著作的《形态》和作为章的《费尔巴哈》作为计划是存在的,而在事实上并不存在。参见赵玉兰:《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情况分析——访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MEGA工作站格哈尔特·胡布曼博士和乌尔里希·帕格尔博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8年第4期,第9-12页。而且还以文献学解构的方式拒斥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因此,卡弗版《形态》在文献学式解构《形态》的同时走向解构传统马克思之路。
路面施工时,会对当地的交通产生较大的影响,如果没有及时公布施工信息,外界交通也会对施工产生较大的影响,甚至出现交通事故等。为了防止此类情况的出现,施工单位需要提前公布施工信息,尽可能减少意外事故的出现。在施工现场,会堆放大量的施工材料和大型的机械设备,整体路面的宽度也会缩小,因此必须及时公示施工信息[3]。
卡弗认为,解构后的马克思的更为重要的身份是政治理论家,不是革命家。对此,卡弗指出马克思思想在1842年便由哲学研究转向政治活动,其体现在关注经济问题,体现在他们发表在报纸、杂志上的政论文章。马克思所从事的活动既不是哲学思考,也不是学术写作,而是政治活动,是实践上的考虑。(29)张一兵、特瑞尔·卡弗:《〈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否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张一兵对话特瑞尔·卡弗》,《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1期,第5、4-8、55页。
对课堂教学的情景创设、素材选择、活动组织、结构安排、媒体使用等教学要素的精确把握和经济妙用,使课堂变得更为简洁、清晰、流畅、凝练、深刻。一篇文章,可教的东西很多,我们所教的内容既要反映出客观规定性,又要反映出主观能动性,因为任何作品一经选入课本,就有其特殊的客观规定性,但同时,任何人阅读作品,总是带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一堂课的教学,完全可以选择一个最有特色的方面施教。
桂越边境跨国婚姻家庭中的子女是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处于两国边境交界处,在个人成长、教育与发展过程中受到两国文化的双重影响,在民族认同、政治认同、国家认同、社会认同等方面备受困扰,为解决他们面临的生存发展困境,就需要积极探索跨国婚姻家庭子女的身份认同困境解决策略,积极利用国家力量、社会力量、文化力量,从多个层面入手解决民族认同问题,通过加强两国文化沟通、改善边境环境、解决国籍问题、开展跨国教育合作与民族政治活动等举措解决这些孩子的民族认同困境,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更好地实现个人的成长与发展。
这里显然存在三个需要卡弗进一步厘清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早期马克思,特别是1842年之前的马克思,是否参与政治斗争的问题。这个问题显然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导师,无论研究哲学,还是关注经济政治,马克思终其一生都是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早期,在他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站在青年黑格尔派的立场上比较研究伊壁鸠鲁和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突出自由意志和原子偏斜运动的重要性,继而用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来同老年黑格尔派划清界限,批判当时德国的思想专制制度。《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出版自由、林木盗窃等问题严厉抨击普鲁士政府。之后,马克思确实把研究点转向了具体的经济问题,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理,并写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著作文章。这些成果都是在为无产阶级革命制定科学的理论指导。在这个意义上来讲,马克思终生致力于参与政治斗争活动,不过其政治参与表现为由哲学研究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马克思思想转变的问题。卡弗承认马克思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由哲学转向物质利益的经济政治问题。但是他认为这一转向恰恰表明马克思思想转变的最终完成,此后的研究不过是该研究的继续。但是这种转变并不简单地如卡弗所指出的那样,是在表面上由哲学问题转向物质利益问题,在实际上是更为根本性的方法论的转变——在关注物质利益问题时马克思的方法论由政治理念先行的一般唯物主义转向以现实的社会的历史的物质实践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30)张一兵、特瑞尔·卡弗:《〈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否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张一兵对话特瑞尔·卡弗》,《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1期,第5、4-8、55页。也正是在后者的意义上来说,马克思在《形态》中所发生的革命性意义得以凸显:首次系统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对比之下,卡弗的这种转变说一方面将关注点置于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表层现象,并没有深入这种表层现象背后的内在逻辑演变,继而阉割了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科学的、革命的理论,另一方面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前苏联式马克思思想发展研究很类似。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马克思思想的载体问题。文本是思想的载体。要研究马克思的思想,研究焦点不得不放在马克思遗留的文本上。关于马克思遗留的文本,张一兵教授把它们分为三类——读书摘录以及心得体会类的笔记、未完成的手稿和书信以及已完成的论著和公开发表的文献,认为每类文本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31)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3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2页。但是,卡弗指出真正能体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不是这些著作,而是这些政论文章以及笔记手稿之类的。(32)张一兵、特瑞尔·卡弗:《〈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否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张一兵对话特瑞尔·卡弗》,《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1期,第5、4-8、55页。诚然,卡弗这种过度抬高这些政论文章的价值和意义未尝有点头重脚轻,因为忽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尤其是他们发表的著作,相关研究很容易陷入那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思想阐释,在研讨马克思思想时也几乎是不可能获得完整而科学的认知结果。
如此一来,卡弗视野中的马克思并不是一个实干的革命者,而是一个从事社会批判的理论家。在《21世纪的马克思》中,他明确地把这种马克思称作“新的‘人道主义马克思’”,并认为这一形象下的马克思便得更加易于理解,因为他早期的异化理论能更明确有力地批判资产阶级社会。(33) Terrel Carver,21st Century Marx,2018,https://aeon.co/essays/who-is-marx-now-and-what-can-he-say-to-the-21st-century,2019-08-28.由此,他消解马克思的革命性一面,解构历史唯物主义。
但是,马克思伟大之处正在于他是一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血、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3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03页。这种革命性对于马克思具有首要性,也是贯穿于马克思毕生活动的重要特质。正是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使空想社会主义变为科学社会主义,为人类解放的伟业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器;正是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深刻地剖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理,使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所处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自身的解放条件,从而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总之,卡弗版《形态》以科学自诩,意在凸显一种动态的思考历程,而不是一种静态的思想阐释。表面上看,按时间先后顺序和纯粹客观中立原则编辑《形态》手稿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它们解构了历史唯物主义,解构了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形象,错误地把科学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仍然没有成功地避免主观地建构马克思,把马克思主观建构为“新的‘人道主义马克思’”更是缺乏依据。卡弗版《形态》不过以科学之名行文献学解构之实,以此消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随着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日益国际化、学术化、多样化,尤其《形态》中文第二版提上议程,面对各类研究中可能存在的自觉或者不自觉的主观建构,我们须始终自觉地保持警惕;在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时,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自觉地坚定马克思主义这一阿基米德点。
中图分类号:A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19)05-0001-09
DOI:10.12046/j.issn.1000-5285.2019.05.001
收稿日期:2019-05-25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方‘马克思学’形成和发展、意识形态本质及其当代走向研究”(13&ZD070)系列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向玉竹,女,苗族,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张亮,男,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政府办公大楼智能工程施工进度要得到有效控制,需要在建造初期编制项目进度计划,并根据各工程的相关情况展开合理的时间安排,做好相关的智能设备安装建设工程,最终实现按照施工建设要求完成建设任务的目标[3]。除此之外,在具体的施工建造过程中,应针对具体建设中遇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补救措施,使工程在规定日期内完成。
(责任编辑:林日杖)
标签:卡弗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论文; 时间顺序原则论文; 纯粹客观中立论文; 编排方案论文; 季刊文集说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