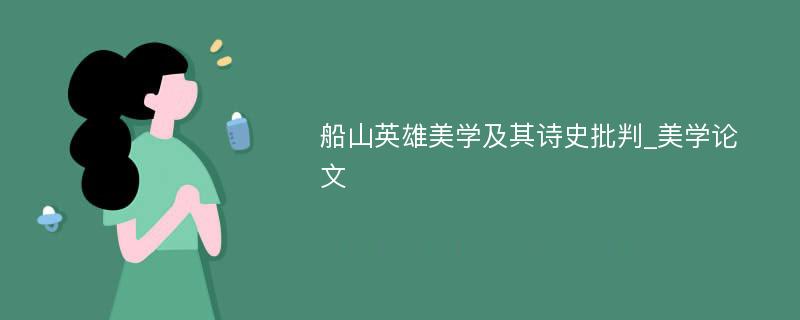
船山的“英雄美学”及其对诗史的苛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史论文,美学论文,其对论文,英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0)05—0128—07
《中国诗史》的作者陆侃如、冯沅君曾说:“我们认为在中国古代哲学家中,只有三个人是真能懂得文学的,一是孔丘、一是朱熹、一是王夫之,他们说话不多,句句中肯。”[1](P46)说王夫之关于文学的言论“句句中肯”,肯定不确切,但大体上人们都承认,王夫之是真能懂得文学的。王夫之不仅把明代的大部分文人墨客,还把我们今天仍然视为大家的杜甫、孟郊、韩愈、白乐天、苏轼等,批得左右不是,让当代学者辗转难安,不惜著文责怪。(注:郭瑞林《千古少有的偏见——王夫之眼中的杜甫其人其诗》以不让于船山的愤激口吻对船山的“偏见”进行了批驳,见《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同时, 又有大量著述高度评价船山的美学思想和他在诗学理论上的创获,谈得最充分的是船山对情景、情理关系的辩证把握,对审美意象的分解,对“兴、观、群、怨”诗学观的创造性诠释,还有船山对于“现量”“取势”“取影”等概念的改造与厘定。在无法否定船山美学与诗学的杰出贡献的同时,研究者似乎有意无意回避了船山对历代诗人的苛刻批评,这种批评不论是用古典的还是现代的审美标准来看都不尽合理,有的甚至有违背常识之嫌。除了某种可以理解的意气使然之外,是什么原因使得船山超越或者说背离了常识的判断呢?事实上,研究者对此的回避不止出于呵护圣贤的下意识策略,也缘于船山思想本身。按照船山的美学理想,船山对于诗史的苛评是可以自圆其说的,而按照其自身的思想逻辑合理地解说他或肯定或否定的历史与审美判断,正是本文的初衷。由此,我们还可以洞察到古典美学中一种并不陌生的中国式的英雄主义理念,这种理念及其所隐含的思维方式延续到现代。
一
整个明代诗歌创作,船山最不屑的是竞陵派领袖钟惺、谭友夏,其中,对钟毫无保留地指斥,对谭保留了同情的理解,说“人自有幸不幸,如友夏者,心志才力所及,亦不过为经生为浪子而已,偶然吟咏,或得慧句,大略于贾岛、陈师道法中依附光影,初亦何敢以易天下,古今初学诗人,如此者亦车载斗量,不足为功罪也,无端被一时经生浪子,挟庸下之姿,妄篡风雅,喜其近己,翕然宗之,因昧其本志而执牛耳,正如更始称尊,冠冕峨然,而心怀忸怩,谅之者亦不能为之恕巳。”[2] 对竟陵派的批判,表明了船山对创作者创作天姿和才能的推崇。在船山看来,竟陵派之不成样子,最直接的原因是他们根本不具备大方之家的才具,强立山头,婢学夫人,装腔作势而已。“诗不以学”而“别有风旨,不可以典册、简牍、训诂之学与焉也。”(《诗绎》)而且,很容易为“名利”所葬送:“弇州以诗求名,友夏以诗求利,受天虽丰,且或夺之,而况其本啬乎!”[3] 竟陵派的失败正是源于“受天”不丰又误入歧途。
依照船山的观点,最宏量大度的诗属于“元声元韵”,即保持了生猛蓬勃之气、未曾分解破裂的生命元声,除了无法避免的时间因素对于生命中原生浑厚的诗性的淘涮剥蚀外,最明显的破坏性因素大约有两端,一端是功利主义的围剿,所谓“名利热中,神不清,气不昌,莫能引心气以入理而快出之”“汉晋以上,惟不以文字为仕进之羔雉,故名随所至,而卓然为一家言。隋唐以诗赋取士,文场之赋无一传者,……燕、许、高、岑、李、杜、储、王所传诗,皆仕宦后所作,阅物多,得景大,取精宏,寄意远,自非局促名场者所及。”[4] 具有破坏性的另一端是创作上的过分“自觉”,即刻意地以某一种程式和技术作为僵硬的指导原则,以至走向反动。船山曾直截了当地指出,有《诗式》而诗亡,有“八大家文”的范本而文丧,他甚至具体说“五言之敝,始于沈约,约偶得声韵之小数,图度予雄,奉为拱璧,而牵附比偶,以成偷弱、汗漫之两病”,以至后来者“强砌古事,全无伦脊”,成为“猥媟亡度之淫词”[5]。在船山看来,声律对于古诗并不是绝对的惟一的,声律的刻意讲求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诗道沦亡的标志,所谓“因小失大”,诗因此成为一种可以堆砌做作出来的技术,而失去了其大本大原,即与日月争光的主体及其情感,即“穷六合、亘万汇”的“如江如海之才”。这也正是“晚节渐于诗律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杜甫总让船山耿耿于怀的原因之一。船山直言屈赋之伟大之“光焰瑰玮”就“不在一宫一羽之间”[6]。与此相似的是,任何美学趣味的推崇,往往导向偏执,譬如“趋新而僻,尚健而野,过清而寒,务纵横而莽”[5], 结果是“亡度”“无伦脊”可言。此种结果的酿成,不仅意味着情感与内在性理的贫枯、俭啬、浮浅、褊躁,也意味着创作者在创作法度和美学把持约束上的能力低下。更等而下之的是,文坛上因为某一种创作径路可资取巧借鉴,某一种风尚可以献宠求荣,导致拥戴宗盟,这同样是诗道文场的异数乃至劫数,即使杜甫推戴庾信“清新”“健笔纵横”也是如此[5]。而唐以后,这种“劫数”简直成了日常功课。
以无法为大法,认为为诗为文的关键不在撮弄字句、起承转合,不在章句韵律之限,这是中国诗学史上被不断重复过的思路,船山并不例外地以一种更加极端的姿态肯定了诗文的天然本性,也因此而多少凸现出某种原始主义的审美取向和难免被指目为“退化”的历史观。确实,船山虽然对“诗”与“史”有理智的分解,对诗文的审美属性有宽容的见识,但是,他的诗学观与经学思想依然是浑然一体的。“风华不由粉黛”“言有余则气不足”,船山对后世“文明”丧失了原生浑厚的诗性而以偏枯干涩的理性取代甚为不满,而韩愈称得上是这种偏枯的理性的宗师,“屈嘉谷以为其稂莠,支离汗漫”,而且才华不足,“夺元声而矜霸气。”[7] 对现实的不耐和思想惯性(注:所谓“思想惯性”是指儒道两家哲学均以“三代”甚至“三代”以上的蒙昧世界作为价值皈依之所,并以此打量现实。另外,任何批判与反思往往需要以对原初事实的澄清作为判断的起点,如张承志所说从树根长出的地方寻找阳光。)轻易导致了船山的清算与归结指向原初浑沌之境,指向天人之际。《夕堂永日绪论序》是理解船山诗学观的入口,研究者往往忽略不计而直接检索《绪论》中合乎现代美学理念的言说,但对船山美学的整体索解却无法绕过这篇序言。在船山心目中,“诗”是礼乐崩解后的补偿物,“世教沦夷,乐崩而降于优俳。乃天机不可式遏,旁出而生学士之心,乐语孤传为诗,诗抑不足以尽乐德之形容,又旁出而为经义。经义虽无音律,而比次成章,才以舒,情以导,亦所谓言之不足而长言之,则固乐语之流也。二者一以心之元声为至。舍固有之心,受陈人之束,则其卑陋不灵,病相若也。韵以之谐,度以之雅,微以之发,远以之致,有宣昭而无罨霭,有淡宕而无犷戾:明乎乐者,可以论诗,可以论经义矣。”从最深远的来源、最普遍的功能、最精微的旨趣立论,船山以一种具有人类学意味的经学立场和视点看待文学,大体而言,这种陈述并不违背历史真实。礼乐的发生即是文明的发生,诗的艺术的因子最初是与宗教、伦理、教育的因子一体同构的,礼乐由神秘的仪式过渡到人为的仪式,诗由一种宗教、历史、游戏的公共抒写进入到人文的、私人化的非集体的抒写,这是一个普遍的过程,一个没有可逆性的过程。船山与历史上大多数思想者一样,并不甘心于诗歌的这种补偿性质而希望企及原初的境界。因此,他对“元气”泄尽的后世诗歌与诗人的藐视就是一种不会因局部观感而改变的基本立场(他常曰某人某诗“去古未远”“依然古道”“是古人心”以示旌表)。以他对诗歌作为统一的意识形态性质的确认,他甚至认为,“自竟陵乘闰位以登坛,奖之使厕于风雅,乃其可读者一二篇而已。其他媟者如青楼哑谜,黠者如市井局话,蹇者如闽夷鸟语,恶者如酒肆拇声,涩陋秽恶,稍有须眉人见欲哕,而竟陵唱之,文士之无行者相与学之,诬上行私,以成亡国之音,而国遂亡矣。竟陵灭裂风雅,登进淫靡之罪,诚为戎首”“推本祸原,为之眦裂。”[8] 这种跨越“文学”的政治指责和意识形态讨伐对船山而言一点也不奇怪,而是“当下自然”的逻辑。
正像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与热情并不仅仅是基于一种社会性的洞察和意愿,同时也是出于对生命及其精神本原的洞察和意愿,船山对历史的清算不止停留在人事、社会的层面,而涉及整体的精神历程,他的美学与诗学正是建立在立足拯救与重建的深刻反思之上,挑剔的打量是全方位的,事关生命的本质,虽然无法挽回精神的分化与流变,但整体的人格唤起和具有涵盖性、普遍性的英雄主体及其情感的缔造,庶几可以振拔诗性的萎靡与文明的虚弱。
二
将“诗”与“经义”置于统一观照之下(注:《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多谈诗,而“外编”多谈经义,时有夹缠。),同时又意识到“经生之理,不关诗理”,一如“浪子之情,无当诗情”[9]。 船山肯定“诗以道情,情之所至,诗无不至”“往复百歧,总为情止”[10],但是,既然“诗”与“经义”同样服从于一种更高的精神指令,即作为统一的意识形态,它们在情感品质上就必须是相同或相似的,这种情感不能是过于私人化和充满偶然性的,而应该是一种集体的甚至囊括天地的情感。诗必须有着普遍意义的能指,主“知”要深入“微词奥义”,主“情”要关乎“万古之性情”[11]。船山对诗史的苛评很大成份就是对其所显示的情感品质及价值取向施予尖锐的批判。
船山对杜甫多所责难,除了杜甫那些被称为“诗史”的篇章让他“终觉于史有余,于诗不足”,而论者干脆以“诗史”誉杜更让他觉得是“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12]几近荒唐外,根本原因是杜甫诗中所显示的情感品质让船山痛心不已,《诗广传》卷一《论北门》一篇长行文字,表达了船山对杜甫诗中卑俗情感的轻蔑,以及对整个诗史上这一类情感流程的检讨:“诗言志,非言意也;诗达情,非达欲也。心之所期为者,志也;念之所觊得者,意也;发乎其不自己者,情也;动焉而不自持者,欲也。意有公,欲有大,大欲通乎志,公意准乎情。但言意,则私而已;但言欲,则小而已。人即无从自贞,意封于私,欲限于小,厌然不敢自暴,犹有愧怍存焉,则奈之何长言嗟叹,以缘饰而文章之乎?意之妄,忮怼为尤,几倖次之。欲之迷,货私为尤,声色次之。货利以为心,不得而忮,忮而怼,长言嗟叹,缘饰之为文章而无怍,而后人理亡也。故曰宫室之美、妻妾之奉、穷乏之得我,恶之甚于死者,失其本心也。由此言之,恤妻子之饥寒,悲居食之俭陋,愤交游之炎凉,呼天责鬼,如衔父母之恤,昌言而无忌,非殚失其本心者,孰忍为此哉!……《诗》之教,导人于清贞而蠲其顽鄙,施及小人而廉隅未刓,其亦效矣。若夫货财之不给,居食之不腆,妻妾之奉不谐,游乞之求未厌,长言之,嗟叹之,缘饰之为文章,自绘其渴于金帛,设于醉饱之情,靦然而不知有讥非者,唯杜甫耳。呜呼!甫之诞于言志也,将以为游乞之津也……韩愈承之,孟郊师之,曹邺传之,而诗遂永亡于天下……”不完整地引述这段文字很容易造成歧解,也很难看到船山缕述诗歌的内在情感如何一步步趋向淫滥龌龊的全过程,但对“情”“意”“志”“欲”“大欲”“公意”的分辨是明确的。杜甫的不堪在于将一些过于物质化与私人化甚至充满女气的情感情绪纳入了诗歌的长言咏叹中,甚至缘饰成章而不以为愧耻,即他某些时候所表达的欲望、情感、意念是一些无法上升到理性与天道的高度,没有普遍意义和合法性,不能使人性获得超拔反而会使人性沉沦的欲望情感。几乎所有对于杜甫的不满都是由此生发出来的:“啼饥号寒,望门求索”、自怜悲苦似“游食客”、“装名理腔壳”、“摆忠孝局面”[13]等。抒写悲苦的情志和宠辱皆惊的遭遇成为杜诗最常见的主题,器量胸怀自难广大。情感与品度往往是连在一起的,恶劣的没有深度的情感伴生于本不杰出的品度,“性正则情深”,“力薄则关情必浅”“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14],性、情、欲的组合与关联既简单又微妙,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诗心与平常心及圣贤之心、诗情与日常情感及社稷生民之情、诗性与理性及天地之性,往往交缠于同一主体,既重叠又相互区别,既排斥又兼容。船山在艰难繁复的分辨中,冲击碰撞,曲折回互,充满理论的紧张与险峻,但保持了基本的立场,打通情感与性理,对情感品质与审美表达作出统一的解释。他认为,汉人辞赋大多成为“怨怼之辞”而无法比拟屈赋,是因为作者“徒寄恨于怀才不试”,“以阨穷为怨尤”[15]“屈子忠贞笃于至性,忧国而忘生,故轮囷絜伟于山川,粲烂比容于日月,而汉人以热中宠禄之心,欲相仿佛,婞怒猖狂,言同诅咒。”[15]可以提出的结论便是:“其情贞者其言恻,其志菀者其言悲,则不期白其怀来,而依慕君父、怨悱合离之意致,自溢出而莫圉”“其情私者,其词必鄙;其气戾者,其言必倍”[16]内在的情感状态、心性状态、“气”的状态,决定着审美表达的品级,“情贞”则“言恻”、“志菀”则“音悲”、“情私”则“词鄙”、“气戾”则“言倍”,一切粗糙的、卑俗的、生硬的、无法登大雅之堂的表达对应着作者内在心性与情感的粗厉与卑俗。这符合并且深化了“言为心声”的古老命题。
值得加以考虑的是,按照现代美学观点,文学情感以及表达的私人性质是文学作为起点与前提的要素之一,在远离史诗时代之后,无法设想某种集体情感(与船山的“大欲”“公意”相仿佛)与理念支配下的写作不是做作和充满意识形态意味的。与此同时,情感之“贞”与“私”,气之“戾”与“昌”,很难作道德评判和优劣取舍,而表达常常在一种并不平衡的心性状态下(即“气”的不同状态的郁结与释放)完成,现代审美甚至以表现变态的、阴郁的情感为当仁不让的使命。这样的理论自然非古典语境下的船山所能响应,他对曹植的鄙薄,就是因为他从曹植的诗中读出情感与气质的病态、偏枯,他无法喜爱曹植的多愁善感、忸怩优柔,“以腐重之辞,写鄙秽之情”[17]风雅因之扫地。他甚至怀疑《七哀诗》“明月照高楼”非植所作,而是“谲冒家传,豪华固有,门多赋客,或代其疱。”[17]
从文字考察情感之“贞”“淫”,由情感检讨时代的精神状态,船山痛心疾首晚明的天塌地陷、中原陆沉由此可以有所归结和解答。船山认为,“精神”、“命脉”、“遭际”、“探讨”“总之”、“大抵”、“不过”一流语词进入晚明“经义”,就是人心朽坏的证明,相应地,“诗”“文”被“俚语咿哟”“里巷淫哇”所充斥,这种现实远非一日之现实,而由来有自。“汉魏以降,无所不淫”,这种“淫”不仅是心性情感的,同样是关于法度形式的。陶渊明诗中有“饥来驱我去”之类句子就是“量不弘而气不胜”,“杜甫不审,鼓其余波”“愁贫怯死,双眉作层峦色像”,白居易“本无浩渺之才,如决池水,旋踵而涸”,苏轼“萎花败叶,随流而漾,胸次局促,乱节狂兴所必然也”。更可怕的是,元稹、白居易放弃“诗教”之任而“将身化作妖冶女子,备述衾裯中丑态”“韩、苏诐淫之词,但以外面浮理浮情诱人乐动之心……惮于自守者,不为其蛊,鲜矣……伊川言佛氏当如淫声美色以远之,韩、苏亦然,无他,唯其佻达引人,夙多狐媚也。”[18]
这种对感性的拒斥,这种苛刻的指责,显然基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高标,基于对经国济世的崇高情感的期望与要求,以一种抽象、圣洁的普遍性取消“文学”表达的独立性与私人性,以至高无上的圣贤境界规范所有的世俗情感。所以,船山不仅不屑妇人、衲子、游客、诗佣之作,对市井之谈、俗医星相、迷惑丧心之语、污目聒耳之秽词亦深耻之(注:船山谓“僧诗如猩猩,女郎诗如鹦鹉,曲学人语,大都不离其气类。”语见《唐诗评选》释僧灵澈诗。)。他需要的是“博大弘通”“淹贯古今”“有得于道要”的“雅正之音”“冲穆之度”,可以“引申经传之微言”,而讨厌诗文中“正是不仁”的“娇涩之音”“忿戾之气”和末路悲戚如贾岛者。
三
不能忍受纯粹诗人气质的曹植,船山对高祖、武帝、魏主曹操、曹丕的创作却是无限心仪,从他们身上船山读出了一种禀于天地的高贵气象和巨人的人格力量。他视高祖《大风歌》为“天授”“绝不入文士映带”[19],汉武帝《秋风辞》为“宋玉以还,惟此刘郎足与悲秋”[19]。无保留地认同曹操,谓之“天文斐蔚”“意抱渊永”“卓荦惊人”,建安七子“臣仆之有余矣,陈思(曹植)气短,尤不堪瞠望阿翁”[19]。又谓“读子桓(曹丕)乐府,即如引人于张乐之野,泠风善月,人世陵嚣之气淘汰俱尽”,《燕歌行》“倾情倾度,倾声倾色,古今无两”“殆天授,非人力”“圣化之通于凡心,不在斯乎?”[19]说曹丕、曹植有“仙凡之隔”[20]。
出现在船山几种诗歌评选中的如上表述有点触目惊心,简单地把这种取向看作船山对君权的膜拜有失肤浅,对船山这样以洞彻天地,贯通古今自任且心智卓越、器宇宏大的思想家来说,帝王气象意味着一种可以化育天下、字养生民的崇高的主体性,一种感天动地、民胞物与的心量与情怀。在古代社会,作为臣民无论蒙昧与否,雄才大略,文情豪迈的君主,都是他们最深刻、最心动的梦想,船山自不例外。
船山生当易代之际,以遗臣自居,渴望光复前朝,并为此不遗余力。他把满清入主中原看作是野蛮对文明的颠覆(有时几乎要看成禽兽抢占了人的家园)而不止是常见的改朝换代,当光复无法付诸行动时,船山将满腔热情注入思想的清理,以期重建人的精神与国家的精神。在他看来,晚明的失败根本就是思想文化上的颓堕所致,“自李贽以佞舌惑天下,袁中郎、焦弱侯不揣而推戴之,于是以信笔扫抹为文字,而诮含吐精微、锻炼高卓者为咬姜呷醋,故万历壬辰以后,文之俗陋,亘古未有”“王伯安厉声吆喝个个心中有仲尼,乃游食髠徒夜敲木板叫街语,骄横卤莽,以鸣其蠢动含灵皆有佛性之说,志荒而气因之躁。”[21]因为志荒气躁,情感失范,文章失度,“色引其目而目蔽于色,声引其耳而耳蔽于声”,外在的诱惑遮蔽了内在的性理,于是“划断天人,失太极浑沦之本性”[21],异端纷纭,形而下猖獗。船山标榜气节惟欠一死,以赴死的精神与意志重新诠释儒家原典,并且把释、道思想也纳入自己的考核中,所谓“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疏洚水之歧流,引万派而归墟,使斯人去昏垫而履平康之坦途”(《正蒙注·序》),以此为毕生的使命。
易代的遭际使船山对时代的精神现象较承平之世的思想家有更敏锐的判断与洞察,也强化了他的“经世”倾向,强化了他关于“天理民彝”的思考,对于可以寄托天下的博大的主体的向往异常迫切,指归帝王的美学选择便成为他整个思想的必不可少的环节。《俟解》中说:“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未有圣贤则不豪杰者也。能兴即谓之豪杰。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拖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志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惟不兴故也。圣人以诗教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将孔子诗教中“兴”的概念引申到人性锻造的高度,表明船山手眼中并没有一种独立于经世之学的诗学或美学,而且它们都共同召唤着“英雄”主体与“英雄”人格,所谓“豪杰”“圣贤”,由此去获得最高的完成。
完整而恰当地体现了船山有关主体与人格诉求的是屈子及其骚赋。船山以自己与屈子“时地相疑,孤心尚相仿佛”(《楚辞通释·序例》)作《九昭》列于《楚辞集释》之末,以正选解人的姿态解说《楚辞》并在篇什上予以调整,不屑王逸注解,对朱子的某些说法也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屈赋中所有浓墨重彩抒写的愤怒、失望、犹疑、徘徊、叹息、悲伤、眷顾,都源于忠贞之性高尚之情,源于一个丰沛充实、精光四溢、充满浩然之气的主体,一种完美健康的人格。屈原以千古独绝之忠,“往复图维于去留之际,非不审于全身之善术”“既达生死之理,则益不昧忠孝之心。”[22]船山反复强调,屈子“情贞”“素怀不昧”,是真正的大丈夫,船山自己亦不屈身降志于现实,不屈身降志于任何可以让信仰、意志妥协迁就的思维模式与生存方式。屈原知道“与天为徒,精光内彻,可以忘物忘己”,但“倏尔一念,不忘君国之情”[22];船山于丹道不陌生,对五行魂魄之说也精熟,但他只认可屈原那种不失自身意志与立场(“己之独立”)的老庄之思、王乔之教,而且认识绝不取代信仰,他也知道“冥飞蠖屈”可以应对现实、身家平安,但“固不能从”[23]。
船山“旷世同情,深山嗣响”[24],指认《离骚》为“词赋之祖,万年不祧。汉人求肖而愈乖,是所谓奔逸绝尘,瞠乎皆后者矣。”[22]后世之所以“求肖而愈乖”,就是因为不具备可以对称的主体与人格,而拥有这种英雄般的主体以及人格,情感将变得纯正,艳诗不艳,闲适不闲,表达也由“必然”进入“自由”,“诗教虽云温厚,然光昭之志,无畏于天,无恤于人,揭日月而行,岂女子小人半含不吐之态乎”“两间之固有者自然之华,因流动生变,而成其绮丽,心目之所及,文情赴之,貌其本荣,如所存而显之,即以华奕照耀,动人无际矣”“神理流于两间,天地供其一目,大无外而细无垠,落笔之先,匠意之始,有不可知者存焉。”[21]当表达成为有关生命的书写或者进而是生命的自我抒写时,表达就变得无可指责了,这已然接近圣人师心原道的神秘主义境界:造化本身就是诗文的极致,伟大的诗文必定是伟大的主体人格及其情感与造化对称的产物,诗人只需以开放的心怀体会感受那生生不息的脉动,载录天地间的浩然之气以及对应于心的苍茫情怀——“元气元声,存乎交禅不息而已。”(《楚辞通释·序例》)
四
充足的才华,发乎性理的纯正情感,类似于圣贤豪杰的伟大主体以及人格,这是船山“英雄美学”的主要构件,也是他认可的诗学理想的基本元素。大体言之,船山的“英雄美学”是由儒学所内含的基本美学思想与船山在末世遭逢中挽救颓堕、期许英雄的精神创发共同构成的。儒学特别是演化为宋明理学的儒学,对主体、人格与情感原本有着苛刻的要求,对文学有非常强烈的工具意识,而船山召唤英雄、期待大器,为主体设置了更高的标准,正是这种要求与标准导致了船山对诗人与诗史的苛评。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苛评是非审美的,正如后世崇拜者所说:船山“胸有千秋,目营四表”,“于荒山檞径之中,穷天人性命之旨”,“考其所评选诗钞,与尼山自卫反鲁、正乐删诗之意,息息相通,迥非唐、宋以来各选家所能企及”,孔子删诗使“天道备,人事浃,遂立千古诗教之极”,而船山《诗广传》“从齐、鲁三家之外开生面焉。又评选汉、魏以迄明之作者,别雅、郑,辨贞、淫,于词人墨客唯阿标榜之外,别开生面,于孔子删诗之旨,往往有冥契也。知此可以读三百篇,知此可以观汉、魏以来之正变,以及无穷。紫不夺朱,郑不乱雅,利口覆邦之祸,庶几不再见于中华乎。”(注:刘人熙序《古诗评选》,《湖南通志》载萧度序《船山古近体诗评选》。)将船山对诗史的甄别上升到可以“兴国覆邦”的高度,这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得不可思议的。如果说是后来者的需要使得孔子删诗成了一个范型了数千年文化的大事件,而无法回避其意义的话,那么,船山在末世的待遇却远没有这样幸运,当他的思想从灰墙土瓦中走出并光大于清季时,社会已正在告别古典时代,新的语境在一步步建立。将船山的诗学继续往非审美的诗教意义上拉扯,不仅不能让它获得肯定,反而会使那些真正值得肯定的具有原创性的思想被遮蔽。事实上,只有当船山的理论触角超越已经发育饱满的儒家诗教而作独立的审美体察时,他的卓越的领悟力和创造性才真正显示出来,而这正是他被专业领域内的研究者看成文论大家的所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撇开船山作为理学家所具有的基本思想和逻辑,而能够对船山美学与诗学的最高旨趣获得充分的理解。恰恰相反,当我们孜孜以求于船山思想中合乎现代美学与诗学理念的理论亮点而缺少对其思维方式与逻辑的整体把握时,我们对船山的表彰往往是“谨毛而失貌”,也无法解释他在理论上的矛盾夹缠,譬如他既对魏晋以降的诗文大家挑剔再四,又并不要或者说自知不能取消他们在诗史上的地位,而且常常不小心让审美判断占据先机。理解船山诗学理想的最终指归,理解船山有意无意标举的“英雄美学”,也许必须要回到他的崇拜者的阐释所提供的非审美的经学立场上去,虽然我们不必像他的崇拜者那样把立论者的理论初衷与实际意义等同起来而视船山为千古圣人。
按照经学的视角,审美的诗常常是感性的奢侈品,是理性的颠覆之具,审美气质的东西只有纳入“兴、观、群、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等有效于家国性命的渠道,才具有建设性,其意义才是充足的。否则,就不足以服务于有关主体、人格、情感、气质、风度的统一缔造,以使生命达于圣境,使国家履踏康庄。思想通达深刻如船山,当然懂得感性的诗对于生命的正面含义(他甚至说过“薄夫欲者之亦薄夫理,薄于以身受天下者之薄于以身任天下”[25]),他同时也懂得诗可以负载某些负面的情感而具有破坏性。实际上,这正是一切感性之具共同的两面性。既不能像迂阔僵化的道学家无视生命的诗性成分与欲求而放言审美的取消,又不能放任情感扩张、诗心狂野到自我倾覆乃至社稷倾覆的程度。在古典语境中,禀承一元有机的生命观及思维方式,我们无法要求船山不将改朝换代、社会崩解与道德沦丧、思想窳败、诗人堕落连在一起考虑,那么,船山折中而高明的选择便是将一种英雄主义的理念和理想纳入古典美学与诗学中,以期英雄主体跨越审美与非审美的鸿沟,书写代表“大欲”“公意”的“诗”,进而像写“诗”一样书写人生、打理社会、重整乾坤、赞化天地。此时,就是天与人归、天人合一之实现了。
五
在审美认知与非审美认知之间的理论分辩中,船山的思想获得了不失宽广的生长空间,他的美学与诗学称得上是理学化了的儒家美学与诗学的最高完成。但是,我们无法从船山自列于《楚辞》之末的《九昭》中读出屈骚似的美感与意味,甚至也无法读出船山所期望的那种主体与人格。看来,最高蹈最经典的美学与诗学并不能直接孕育出最经典的诗文。对一个美好的事物,我们可以将每一个要素分解得清楚,但并不意味可以重构这个事物,或者说重构本无意义,正像船山所意识到的,“文章与物同一理,各有原始,虽美好奇特,而以原始揆之,终觉霸气逼人。如管仲之治国,过为精密,但此与王道背驰,况宋襄之烦扰粧腔者乎”![26]确实,当船山把自己认可的“光昭之志”“亘日月之情”嵌入杂剧《龙舟会》,《龙舟会》就像一出几百年前的“样板戏”,情感枯涩造作(注:船山喜边塞诗、疆场诗,不仅喜其豪气,且沉迷于复仇快感,自己的创作也屡屡表现出种族情绪,且视为庄严神圣。),意味淡薄,正是船山所嘲弄的“不蕴藉而以英雄,屠狗夫耳”,不免“削骨称雄,破喉取响”之病[27]。
热切的社会关怀与紧迫的当局感,并不一定有助于诗性的孕育与理性的澄明,有时甚至相反。船山既禀承了一元的“原道”“载道”观,将“诗”“文”置于统一的意识形态范畴,又以服从服务于当时当世为崇高使命(《四书训义》卷一说“道至平天下而极矣”),其激烈的工具愿望、主题意识就难免成就苍白造作甚至拙劣的表达,“史诗”般的情怀始料不及地衍生出语录式的教案和单调的意识形态符号。
时移世易,20世纪中国是一个较船山所处更加激越沧桑的时代,民族国家的拯救与再造同样召唤着船山标举的英雄主体与情感,毛泽东屡屡说不喜杜诗,说杜“哭哭啼啼”[28],这绝非只是他个人的一时好恶。且不说毛泽东与船山在学术上的渊源关系,从20世纪中国文化的基本走向看,将文学与启蒙、与国民精神的改造、与主体的高扬作划一的规范与要求,就显示了古老的世界观生命观的延续与再生。除此之外,对创作主体及其情感纯洁性的诉求,对高洁绝尘的英雄人格的推崇,对私人性体验与欲求的拒斥,美学上清洁单纯到“洁癖”与对“儿童思维”的嗜好,直到今天某些以“史诗”自任的写作,无不可以从船山的“英雄美学”中找到影子。由此也凸现了古典的“英雄美学”在现代的困境及其可能性。毕竟,文学就是文学,文学又并不止于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