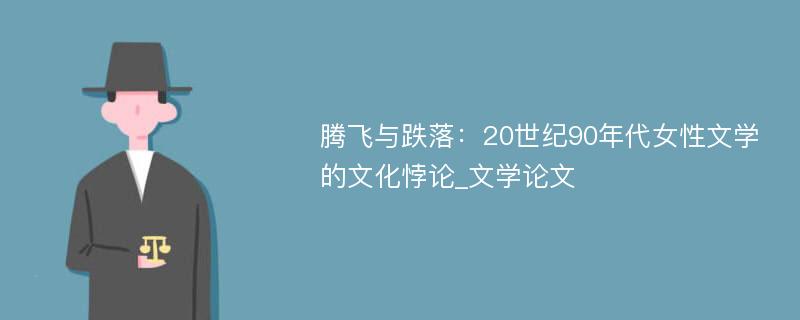
飞升与坠落: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悖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悖论论文,女性论文,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女性文学而言,九十年代似乎意味着一次契机。当不无沉重的历史反思和民族重塑的文化运动随着八十年代的终结而逐渐淡出的时候,女性文学却在这底幕的映衬下凸显出来,不期然间成为一个亮点。这固然是因为理想主义失落之后的年代里,这一领域成为注意力转移的一个依托之地;更重要的是,由于主流话语自身的裂变,原本相对统一的价值标准和理想诉求分解成多种歧异的趋向;就在这布满缝隙和裂痕的文化板块上,女性文学获得了一次类似于飞升的时机:挣脱“宏大叙事”的束缚,而去碰触过去从未接近的崭新的自我领域。
因此,九十年代的女性文学一时之间呈现出一幅繁复、多元的图景。如果说,八十年代最出色的女作家在创作中常常表现出对主流知识分子身份和立场的认同,那么到了九十年代,类似的认同已经起了复杂而微妙的变化。王安忆写《纪实与虚构》《伤心太平洋》的时候,知识分子式的现实关注依旧存在,但已不似“反思”“寻根”时期的俯瞰众生,而是转入对个人家世的追问与回溯,以隐喻的方式建立叙述,表达寄托。她的《叔叔的故事》则将男性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所形成的诸种心态,置于冷静的观照和解析之中,对一度放大的知识者形象进行了一次还原。到了另一位女作家徐坤那里,对经典知识分子话语的解构表现得尤为突出——《先锋》《游行》《白话》……所选择的甚至不是批判与自我批判的方式,而是在调侃和戏谑中消解历史与现实中的诸多神话。
与对精英知识分子立场采取相对复杂化的态度几乎同时出现的,是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的另一个明显特征:对都市文明中女性生存状况与精神状况的体察和表述。八、九十年代以来不断扩张的都市空间,是现代化进程中一处充满变幻的风景,它不仅极大地改写了“乡土中国”的外部形态和内在理念,而且也重新塑造着性别规范和性别秩序。历史在这里仿佛是一次重演,三、四十年代上海的繁华景观以及对它的文学表达,在九十年代的现实和文学中似乎经历了一次“原画复现”,“女性”则成为这一特定时代风气的敏感的测试器。王安忆的《香港的情与爱》《长恨歌》,在有意与无意中复活了四十年代张爱玲的笔触,这些作品把物质化、商品化的都市呈现为一个浮华的文明进程,升降沉浮于其中的女性既是被俘获的对象,又是主动的俘获者;她们执着地演绎着自己的历史——那小写的历史,以女人特有的方式进入的历史。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女性写作表现出一种相当自觉的性别意识。除了王安忆之外,更年轻的女作家如张欣,在近乎通俗文本的“都市系列”中,将“白领女性”的登场、出演以及这出演的尴尬作了浅近而不失精细的描述:方方、池莉、蒋子丹……虽然各自形成了不同的写作方式和文体风格,然而她们的作品都不乏一种更为洞达的眼光,都市中永恒的性别游戏规则常常在这种眼光的审视下露出它的破绽和荒诞。而另一批以“个人化写作”而知名的女作家,如陈染、林白、海男、徐小斌等,则将一些从未表达过的女性的独异体验第一次引入了文学。诸如《一个人的战争》、“黛二系列”、《私人生活》《双鱼星座》……这些作品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们通过自陈自述的方式,复沓着一个女性成长的主题,把那些被长期掩蔽在无名、混沌状态下的、女性成长中的身体感觉和心理流程鲜明地裸露了出来;更为重要的是,她们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反叛主流、固守边缘的性别立场,意味着女作家对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具有了一份更明澈的体认。
九十年代的女性文学在趋于多样的同时也指示着危机,这种危机来自内、外两重原因。九十年代社会体制的变迁,商业文化的涌流,都市化进程的加快,不仅使性别与性别关系空前复杂化,同时它们也在重新设定着一些强硬的边界。相对于那个“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统一的声音,现时代的女性有着更为灵活、更为多样的选择。然而一种主导的倾向也分外清晰,那就是再度确立性别不可更改的本质,再次划分两性间不可逾越的沟壑。诸如“女性解放”之类的话语,因为与旧有的政治体制相连而受到精英知识分子的警惕与排拒,并在一个已经变动了的语境中表现得如同可笑的陈迹;而所谓“女人就是女人”之类的认定,却成为仿佛天然如此、不言自明的概念。九十年代曾经风行一时的“小女人散文”,并没有被理解为对女性的某一种生存样式的抒写和展露,相反,对它的反复炒作潜在地包含着广泛的社会期待,这一现象由此成为重造性别的一个标记。
对“女性”这一概念内在涵义的狭隘化还不仅仅如此。更为突出的,是“性别”被利用为商业策略,女性被界定成一个单纯承载各类欲望的容器。在相对松动的文化环境里,女性原本获得了表达自己,包括表达自我欲望的勇力和自由,然而,这却很快成为商业炒作的一个最显眼的卖点和窥视点。女性写作中对个人隐秘的表露,对身体欲望的陈述……无形当中被置于男性窥视的视域之内,凝固成一个个“欲望的对象”。女作家们的“边缘写作”、“身体写作”在从男权话语的牢笼中突围而出的同时,又被统摄到无处不在的欲望化、商品化的陷阱中,其原初的主观愿望受到严重的扭曲。有研究者敏锐地发现,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出版时,书籍的封面竟被设计为一幅“春宫”——一个裸体的女人,没有头也没有四肢。画面对“女人”意义的指认是显而易见的:“她”既不会思考也不会行动,只是一个“性的人”。相对于过去革命文学中女性对于固有性别秩序的超越,和八十年代文学中女性以“人”的方式参与历史,九十年代无论在现实还是文学中,女性形象都呈现出一道坠落的轨迹。
除了外在因素之外,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的危机还源于其自身的问题。当“个人化写作”、“边缘写作”作为新异之物在女性文学中出现之时,许多批评者曾为女性终于形成了鲜明的性别意识、终于能够大胆地袒露原本属于禁忌的自我体验而感到惊喜,然而此类写作的起点也便成了它们的终点。这一批女作家的写作或隐或显均受到过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影响,然而杜拉斯的唤醒作用更多地被局限在欲望表达的浅层方面,其作品巨大的激情以及掩藏在这激情之下的深邃的绝望,却无法转化为中国女作家所能借鉴的有效资源。在杜拉斯那里,“边缘”立场意味着在边缘处进行激进的反抗,而在中国女作家那里,“边缘”往往成为逃避男权主流社会压力的避难之所。这也是在两类文本中,一种让人感到尖锐的力度,而另一种却显得无力的原因。由于狭隘地理解了女性所拥有的独异体验,对女性自我欲望的表述无以避免地趋于单调、扁平。像赵玫的《高阳公主》之类的作品,本意通过女主人公惊世骇俗的性爱行为而肯定其内心的真实欲求,可是小说中的女性却最终只是一个纯粹的欲望的符号。这种自设的陷阱也许是女性文学更难逃脱的罗网。
九十年代以后的女性文学写作是与女性主义批评共同发展起来的。批评和写作达成了某种共生共存、相互促进的关系。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传入和运用,对更新中国固有的女性意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许多女作家对西蒙·波伏娃、弗吉尼亚·伍尔夫、埃莱娜·西苏……这些西方女性主义先行者的作品和思想相当熟悉。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依循先在的理论进行创作的现象,那些尚未被自身体验所融化、尚未与生活产生入骨入血联系的理论有时候会破坏作品。像陈染的一些小说,就可以明显地找到它们与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一对应之处,创作的概念化由此而生。实际上,女性主义理论并不应该被视为对女性问题的唯一、终极的解决,它不过是提供了通向纷繁复杂的女性体验的可能之门。不如此,女性主义也会变得越来越偏执,越来越狭窄。这同样是产生于女性文学内部的矛盾和问题,它更为隐蔽,同时也需要更冷静、更深入地加以思考。
由此看来,九十年代的女性文学所面临的是一个个深刻的悖论:在知识女性与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之间、在男权社会的边缘人与性别本质主义的规定之间、在对自我体验的表述与消费文化强大的改写力量之间,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中国女作家的现实情境之间,均充满了张力与冲突,对抗与裂隙。而女性文学只有对自己所处的悖论有所感知和反思,才可能突破和超越已经达到的高度。
标签:文学论文; 女性主义论文; 文化论文; 女性文学论文; 性别文化论文; 飞升论文; 九十年代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