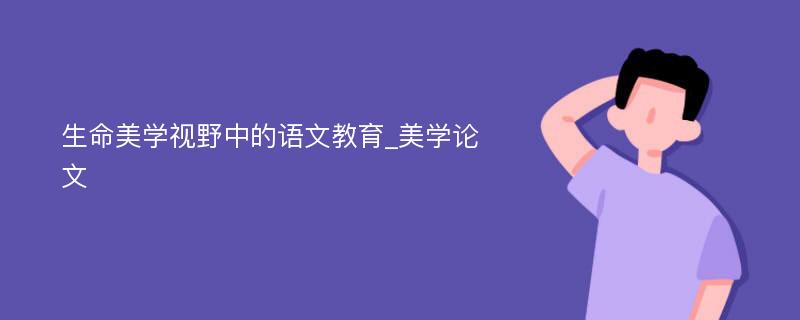
生命美学观照下的语文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语文教育论文,生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潘知常曾敏锐地指出中国当代美学在研究内容上存在的失误,那就是“以对象世界为核心”,“忽略了内在生命活动,忽略了体验,忽略了有限与无限的关系,忽略了作为生命意义的秘密”,审美活动应当是“一种充分自由的生命活动,一种人类最高的生命存在方式”[1],它是一种具体、直接的生命体验,是一种非理性、诗意的生命之思,是对人自身生命价值的一种去蔽。 中国美学研究的失误,也正是当下语文教育的失误。潘知常对于生命美学的概念的厘定,也适用于语文教育。随着现代社会的日益浮躁功利,现今的中学语文教育“工具论”也甚嚣尘上,甚至有“专家”说:“语文教学更高境界的目标还应该是语言文字运用,而不是走向内容与情感。”按这种说法,我们最好像教英语一样教语文。中国人学英语,就是只追求基本运用,语法正确。母语教学的底线是语言文字的教学,但不能止于底线。朱自清说:“我以为中学国文教学的目的只需这样说明:(1)养成读书、思想和表现的习惯或能力;(2)发展思想、涵育情感。”[2]没有情感的推动,我们就学不会什么。机器从来“学”不会任何技能,它只会按照人所设定的程序运转,因为它没有感情。但动物有感情(且不说人),所以任何一只母鸡,总能学会如何保护它的小鸡。 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应该以谋求人类自身的幸福为目的。如果语文“不必走向情感、内容和意义”,那么,人类是为语言而活的吗?世界的存在目的是发展语言?语言是手段,是载体,却不是终极目的,它只是路径。希特勒就是靠他的语言来煽动民众从而一呼百应的。还有他的艺术天才,学美术出身的希特勒亲自设计的军装,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依然是世界上最帅最有型的军服。希特勒说,给我设计最好的军服,让全国的青年,单为了一套军服就愿意参军。事实上的确有很多年轻人就是为了这身军装而投身军旅的。 语言,艺术,都是中性事物,最终造福人类还是祸害人类,取决于使用它们的人的心灵和信仰。片面强调工具性,武断否定或忽略人文性,是本末倒置,是违背人性,是一种“物化”的教育。 1922年,叶圣陶就在《小学国文教授的诸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第一,须认定国文是儿童所需要的学科。”“第二,须认定国文是发展儿童的心灵的学科。……学童所以需要国文,和我们所以教学童以国文,一方面在磨练情思,进于丰妙;他方面又在练习表出情思的方法,不至有把捉不住之苦。”“教授国文不以教授形式为目的,这不过是附带的目的;宜为学童开发心灵,使他们视学习国文如游泳于趣味之海里。”[3]笔者以为,语文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引导生命向善、求真、审美,这才是我们要努力抵达的彼岸。至于语言文字的形式,你可以说它是一条船,也可以说它是一座桥,它是工具,但工具永远不是目的。朱光潜说:“人性本来是多方的,需要也是多方的。真善美三者俱备才可以算是完全的人。”[4]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生命美学与语文教育是有着深厚的学科因缘的。 一、语文教育的本质与本原 在现代语文教育史上,蔡元培是第一个将办什么样的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教什么样的语文、重视语文的什么价值明确联系在一起进行构想和阐述的教育家。他指出“国语国文之形式,其依准文法者属于实利,而依准美词学者,属于美感”[5]。他始终倡导美育,将国文与音乐、美术并列为美育最基本的课程,发挥其“陶养性灵,使之日进于高尚”的功能[6]。 语文教育进入20世纪后始终处于争论之中,语文教育的本质越辩越模糊,人们对“怎么教”的关注趋之若鹜,却忽略了“为什么教”和“教什么”的问题。语文教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笔者以为,教育的本质是培养大写的人、舒展的人、丰富的人、深刻的人、美好的人,引导学生追求无限广阔的精神生活,追求人类永恒的精神价值,而不只是为社会培养准职业者。 潘知常说:“我们的语文教育还有什么用?当然,从表面上看,语文教育肯定有用,因为语文教育在教学生写文章方面,例如写记叙文、写议论文方面肯定是有用的,甚至还可以说,是很有用的。可是毋庸置疑,这些绝对不是人类设立语文教育的本意,也肯定不是语文教育的最高追求。那么,我们的最高追求在哪儿呢?我们给学生提供什么样的营养才对得起人类,也才对得起我们的三尺讲台呢?”“我们的语文教育有再多的理由都不能淹没其中的一个最根本的理由:它必须是给人性以尊严的教育,它也必须是给文学以尊严的教育。”“第一点,我们必须为自己的学生提供最好的精神营养。”“第二点,我们的语文教育必须回归爱的教育。”“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想法,我们的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7]“给人性以尊严的教育,给文学以尊严的教育”,这就是语文教育的本质。 而语文教育的本原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是人性,是生活。这是语文教育能够影响学生生命成长的原因,也是语文教育的源头。“教育”这个词在拉丁文中意为“引出”,即把一个真正的人引导出来、塑造出来。教育的本原是直面人性的深渊,将里面那个“人”引导出来,带领他走向健壮、丰富、智慧和美好。我们只有在承认永恒人性使情感共鸣成为可能的前提下,也只有在承认生活是生命的产物也是语文的源头的前提下,语文教育才有可能真正展开。 宗白华说德国诗人侯德林以下诗句含意极深: 那无边际的“深”, 这最生动的“生”。[8] 这首诗说的就是只有在人性和生活的最深处,才有最壮阔最美丽的风景,才有最鲜活最丰富的人生。宗白华讲到《水仙操》的创作经历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伯牙学琴于成连,三年而成。至于精神寂寞,情之专一,未能得也。成连曰:‘吾之学不能移人之情,吾之师有方子春在东海中。’乃赉粮从之,至蓬莱山,留伯牙曰:‘吾将迎吾师!’划船而去,旬日不返。伯牙心悲,延颈四望,但闻海水汩波,山林窅冥,群鸟悲号。仰天叹曰:‘先生将移我情!’乃援操而作歌云:‘繄洞庭兮流斯护,舟楫逝兮仙不还。移形素兮蓬莱山,歍钦伤宫仙不还。’伯牙遂为天下妙手。”对此,宗白华说:“‘移情’就是移易情感,改造精神,在整个人格的改造基础上才能完成艺术的造就,全凭技巧的学习还是不成的。”[9] 由此看来,语文教育乃至一切文学艺术的本原就是人性和生活。伯牙之琴技未始不精,但一个没什么生活阅历和情感经历的单薄苍白的人,绝难创造出永恒人性能够与之共鸣的艺术作品。经历了孤独凄凉绝望之后,再以因为孤独凄凉绝望而变得敏锐善感的触觉去感受周遭,世界就大不同了。说到底心灵是一面镜子,镜子的质地和光泽,决定它映射出来的那个世界的样子。所以,心灵若变得丰富了,精神若得到改造了,人格若得到升华了,一切才成为可能。 二、文学审美的必然与必需 潘知常说:“一个人可以不爱善,我们说这个人是个坏人;一个人可以不爱真,我们说这个人是个伪君子;但是有史以来却很少见到不爱美的人——尽管他爱的那个美可能根本就不是美。”[10]审美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必需。与世界关系的最高境界是审美,进入审美境界的人生,才是超越的人生。 朱光潜说:“我坚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一定要于饱食暖衣、高官厚禄等等之外,别有较高尚、较纯洁的企求。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11] 文学能够带给我们审美享受,这是一种必然。审美情感能够丰富感觉,激活想象,苏醒智性,完善人格,激发人们对生活、对世界、对自己的重新审视。只有在审美境界中,我们才能挣脱现实世界的限制,我们的人性才有可能真实而完整地呈现出来。因此,审美情感的焕发能够激活人的各种潜能,使人的心灵保持健康活跃。 美的最终根源在于人的自由创造。马克思说:“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2]朱光潜说:“‘生命’是与‘活动’同义的,活动愈自由生命也就愈有意义。人的实用的活动全是有所为而为,是受环境需要限制的;人的美感的活动全是无所为而为,是环境不需要他活动而他自己愿意去活动的。在有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环境需要的奴隶;在无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自己心灵的主宰。这是单就人说,就物说呢,在实用的和科学的世界中,事物都借着和其他事物发生关系而得到意义,到了孤立绝缘时就都没有意义;但是在美感世界中它却能孤立绝缘,却能在本身现出价值。照这样看,我们可以说,美是事物的最有价值的一面,美感的经验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一面。”[13]审美是人的最高生命境界,是人的最为本真的生命灵性,是人的诗意栖居之地,是人之为人的根基,是人类灵魂的家园。审美是生命的至深需要也是最高需要,是生命超越与灵魂升华的见证。审美判断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思维能力,随着媒介的熏陶和生活的引导逐渐走向成熟,最终形成独立的审美意识。审美对现实生活的超越可使人从中获得安慰和寄托,从而形成人们充满兴趣、满怀信心地走向生活的一种动力源。语文教育就是要在自由的生命活动中促成美和审美的生长。 一个人在审美熏陶中所形成的审美情感会储存在他的意识之中,成为主体心灵的一部分,成为一种生命能量,它能够自由自觉地与偏离这种情感的负情感发生碰撞,并把发生在个体感性中的不符合“美”的标准的欲望和情绪通过审美情感的自觉规范与调节,得以洗涤、澄清、陶冶和重塑,使人的心境得到调适,恢复和谐,建立审美的生命视角和审美的生活态度。因此,审美情感的丰富完善是人的精神世界日益丰富的重要标志,有利于促进人心理的健全和人格的完善。 与其他情感相比,审美情感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审美情感具有超越现实功利性的特质。审美情感不是“实用”的,它是非功利的,在审美活动中,审美对象必定与审美主体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从这个意义上说,审美情感是一种提纯了的情感。二是审美情感的发生是自由和自觉的。黑格尔说“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审美情感能够将主体引入摆脱束缚的心灵自由的境界。此外,审美情感的产生是不需要任何外力强制的一种心灵的自觉活动。审美情感的这种自觉自由性往往会造成一种毫无强制的轻松愉快和谐融洽自由自在的气氛和情境,带给审美主体精神上的愉悦与享受。所以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审美需要是人的高层次需要,审美需要的满足是人自我实现的标志。 爱因斯坦在《我的世界观》(此文最初发表时用的标题是“我的信仰”)中说:“照亮我的道路,并不断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14]因此,在语文教育中借助文学的审美来让受教育者得到成长和发展,也是一种必需。 三、学科融合的可能与可为 美之于人不可或缺,而文学,恰是美的载体。美的本质与语文教育情投意合。文学具有美学的价值。语文是美,是艺术的生活,是文化的生命。语文教育就是要在语文(语言、文章、文学)中张扬受教育者的独特个性,激起情感波澜,点燃思想火花,让受教育者置身于生命存在之中去体验世界的活力、丰富和美,鼓励受教育者去创造价值多元的人生。带领学生在广阔的思维空间和自由的生命状态中,多角度、多层面去理解、鉴赏作品,引发对文本的情感美、哲理美、意境美和语言美的认同与赞赏,并产生强烈的阅读欲和创作欲,这样,在长期的熏陶中培养学生的语感和美感,触发学生的灵感,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涵养学生雍容的博学气质和优雅的文化风度。久而久之,学生的语文能力、语文素养和文化品位、健全人格层次得到了提升,也就意味着具有了获取人生幸福生活的能力和素养。 文学的存在之维是生命活动。语文教育是浸润式的,是超越功利的纷扰,带领学生真诚地投入到文字的品读和生命的体验之中,从生命活动的视角和生命美学的视角来阐释文学。审美判断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思维能力,语文教育就是要在个体自由的生命体验中促成美和审美的生长,引导学生处理好人生中“生命与生活的紧张”,使他们意识到自我生命内涵的多面性、丰富性,从而能够深刻地体认生命的可贵,去追求人生的更大价值与意义,终则获得超越的生命:求真、向善、审美。 生活让美学与语文牵手。生命与生活是美的发源,表达与创造是美的结晶;语文学习的土壤是生活,生活有多宽语文的外延就有多大。热爱生活,追求美,才会有美好的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文学形象,就是审美的本体:自然风物,缤纷多彩;人生世相,参差多态。语言文字承载着美的形象,透过审美主体,让自然美和人文美相互融合渗透。美学与语文都以生活为根基,二者相得益彰,所以二者的学科融合是可能的,亦是可为的。语文教育是一种审美的教育,促进个体生命去享受诗意的栖居。所以,语文课堂要重视美学维度,从自然视野、心灵视野、文化视野、艺术视野、人性视野中去发现美、创造美,让情趣变得纯粹而高雅,让生命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近百年来,中国步入了审美流派的多元共生时代。新世纪伊始,美学界更是“百家争鸣”,雄踞美学界近30年的实践派美学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其中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争论最为激烈,成为“后实践美学”的亮点。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实践美学风头正盛之时,潘知常就率先在中国美学界提出“生命美学”的理论构想(《美学何处去》),后来他又连续出版了专著《生命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诗与思的对话——审美活动的本体论内涵及其现代阐释》(上海三联书店)、《生命美学论稿》(郑州大学出版社)、《我爱故我在——生命美学的视界》(江西人民出版社)、《没有美万万不能——美学导论》(人民出版社)等,在这些著述中,潘知常系统地建构了自己的生命美学本体论美学思想体系,所有立论都围绕着“审美是一种最高的生命活动”这一命题展开。 对此,西城这样评价:“他提出的从生命活动入手去考察审美活动,正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美学”,“他更多承传着中国古典美学的话语传统——在逻辑的表象背后,飞动的灵气、诗化的秉性、生命的情调共同构成了他生命美学的‘真味’”,“潘知常的生命美学,为世纪之交的中国美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形态”[15]。 至于生命美学和语文教育之间的关系,潘知常曾经做客“凤凰语文网”,就此话题做过一个系列的讲座。一部分专家和语文教师也逐渐关注到这一课题,涌现了一些思考成果。譬如刘志民的《〈雨中登泰山〉的生命美学观》(《语文教学通讯》1997年第21期),曾磊的《从生命美学来看中学语文写作教学》(《文学界(理论版)》2010年第11期),笔者的《王维的生命美学——王维诗文专题教学设计》(《语文教学通讯》2012年第5A期),等等。 但是这些思考,要么零碎不成体系,要么跟语文教育本身关系不够密切,如何在语文教育中具体实践生命美学,或者说如何用生命美学的理念来践行语文教育,是目前一个尚付阙如的命题,也是一个非常有研究价值的问题。 四、生命课堂的审智与审美 教育的根本出发点是人,不是人力,教育应促进人的身心生长与自我实现,即帮助每个人愉快、从容、动态地活着。教育是为了人的生活,为了使人拥有丰富的内心世界,掌握基本的知识技能,获得深刻的人生智慧,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教育的核心在于使人人化,即使人的生命具有人的尊严、人生的意义,使人像人一样生活,并谋求人生的幸福,使人领悟到生命的内涵,并使人的灵魂觉醒。 人的生命存在是生活的基点,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则是生活的归宿。生活是指人的生命动态展开的过程,梁漱溟先生曾经把生活等同于生命,他说:“生命与生活,在我说实际上是纯然一回事;一为表体,一为表用而已”,“‘生’与‘活’二字,意义相同,生即活,活亦即生。惟‘活’与‘动’则有别。所谓‘生活’者,就是自动的意思”,“生命是什么?就是活的相续”。[16]所以,笔者在语文教育实践中,一直努力在生命美学的观照下,营造“生命课堂”,以生命为核心,以美学为手段,重构学生的心灵世界。 里尔克有这样一首诗: 既未认清痛苦, 也没学会爱, 那在死中携我们而去的东西, 其帷幕还未被揭开。[17] 现在的语文教育对于学生成长的影响,笔者以为就是处于让学生“既未认清痛苦”“也没学会爱”的状态。浮于知识技术层面的语文课堂,既未能启蒙他们的思想,也没能陶冶他们的性情,也就是说,既没有审智的功能,也没有审美的效果。 生命美学观照下的语文课堂,应该既有审智的功能,又有审美的效果。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重“智”重“美”。审智与审美,往往是密不可分的。孙绍振说:“审美就是情感审视,但情感不是孤立的,它表层是感觉,深层次是情感,再深层次代表人的立场、观点,人的智性、修养,人的道德观念、价值准则等。”“感情是审美的核心,它不但和感觉联系在一起,而且和智性有着深刻的联系;智性往往深深地隐藏在情感的深层。”[18] 审智方面,笔者以为语文教育最核心的学科素养就是价值意识。潘光旦说:“价值意识之发达,用之于理智,便知是非真伪的区分;用以待人,便识善恶荣辱的辨别;用以接物,便识利害取舍的途径;甚至艺术家所称的‘赏鉴的能力’,即美丑的辨别力,西文所谓taste,也无非是价值意识的一部分。”[19]能够培养学生价值意识的生命课堂,就是具备审智功能的课堂。 审美方面,笔者以为语文教育最核心的目标追求应该是培养生命充沛、有创造力、有爱的能力和审美能力的人。宗白华说:“中国哲学是就‘生命本身’体悟‘道’的节奏。……道尤表象于‘艺’。灿烂的‘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人类这种最高的精神活动,艺术境界与哲理境界,是诞生于一个最自由最充沛的深心的自我。这充沛的自我,真力弥满,万象在旁,掉臂游行,超脱自在,需要空间,供他活动。”[20] 经过近十年的探索与实践,笔者于2013年出版了专著《语文:生命的,文学的,美学的》(教育科学出版社),引用了自己丰富的课堂案例与教学实践,深入探讨了生命美学与语文教育的关系。该书强调了语文教育的五个审美向度:自然视野中的美、心灵视野中的美、文化视野中的美、艺术视野中的美和人性视野中的美。提出了语文教育的三维目标:感性、理性和知性。语文教育的目标就是要赋予学生以丰富的感性体验、精准的理性认知、美好的知性素养,这是一个以生命为轴心的三维空间。第一维(“丰富的感性体验”)侧重于文本的素材价值,帮助学生从中获取直接的人生感知与情感体验;第二维(“精准的理性认知”)侧重于文本的工具价值,帮助学生从中获取客观知识与基础能力;第三维(“美好的知性素养”)侧重于文本的生命价值,帮助学生从中获取审美情趣、艺术修养和人生智慧。整合了三大维度:文学、美学、哲学;分析了生命的位格:宇宙位格、国际位格、社会位格、家庭位格、全位格;思考了文学的本质:理解VS解决、体察VS批判、感性VS理性、自语VS对话、间离VS重建。 生命美学观照下的语文教育,研究的对象就是语文教育与生命美学的互动与共生。让美进入生命,以审美的眼光认识生命,从生命出发理解文字。譬如在《捕蝶者》的课堂中,我们解读出了一个看重物质美学胜过生命美学的捕蝶者,一个追求声誉、价值与意义却在其中迷失了灵魂的捕蝶者,一个残忍得不动声色的捕蝶者,一个拒绝平庸却与卓越绝缘的捕蝶者,一个获得了胜利却可怜可悲的捕蝶者……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胜利者,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刽子手,他的人生恰是一种人质的人生,他把自己作为人质抵押给了科学(或曰“真”)与“美”,却输了“善”与“爱”。再譬如在《木兰诗》的课堂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全新的木兰:她的活力,她的机智,她的勇气,她的兴奋,她的调皮,刷新了一个时代的视野,如同一道闪电,划破了黑暗的天空。替父从军,固然首出于孝,然观其表现,竟常流露出无比兴奋和无限向往之意!木兰选择替父从军,除了对亲人的呵护与疼爱以外,不能排除她对军旅生活有一种享受冒险、体验刺激的心态。生命力充沛、灵魂活跃的形象富有神秘的美感,诱人探究,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