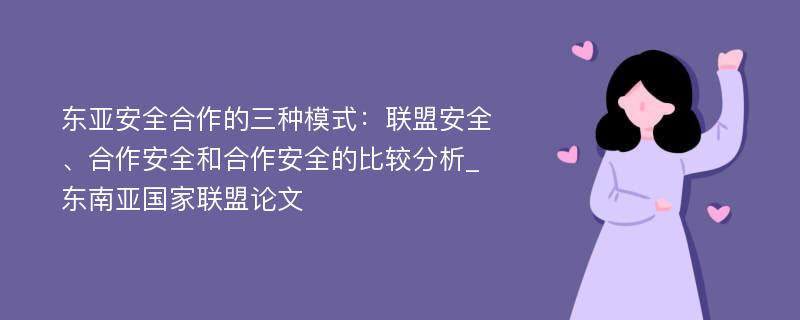
东亚安全合作的三种模式——联盟安全、合作安全及协治安全的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三种论文,治安论文,模式论文,联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6)09—0052—06
东亚安全结构正在发生诸多引人注目的变化:一方面,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另一方面,地区安全的摩擦和冲突更加频繁。前者呈现出全球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后者则凸显出这个地区受到地缘政治影响的历史痕迹。因此,这些变化既是传统安全因素作用的结果,又是新的、非传统安全因素驱动的结果。笔者认为,联盟安全、合作安全和协治安全三种方式是推动东亚地区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
讨论这三种可能模式的意义在于:惟有清楚我们所在地区安全结构的基本特征以及每一种可能模式对中国国家利益意味着什么,我们才能明白应当采用何种安全战略以塑造之。事实上,国际政治中所出现的任何重大事件(例如欧盟兴起以及苏联解体)都不过是该行为体自我塑造与外部力量互动的产物。东亚安全结构的无政府特征使得东亚相当一部分国家透过霍布斯眼睛看世界,反过来,又正是东亚各国这种传统的安全观念和政策造就了东亚的无政府文化。变化的发生既出现在外部也出现在内部,既发生在物质层面也发生在观念层面。也可以说内部与外部的、物质与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正在使东亚安全复合体发生变化。问题还在于,果真如此的话,这种变化是何种程度和性质的?仅仅是力量对比和格局的变化,还是具有革命意义、告别强权政治的变化呢?
一 东亚安全结构分析
按照史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的理解,“安全(security)”也就是国家安全,被他人的武力所威胁,靠自己的军事力量来保卫。① 他将安全概念看做“对免于威胁的追求”,显示“国家和领土完整,反对敌对势力的能力”。② 这种基于物质主义而忽视观念(idea)的对安全的理解,认为获得安全的途径是“自助”而非合作,使其在追求安全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陷入“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巴瑞·布赞和奥利·维夫等人提出,“安全化(securitization)”过程,即一个行为主体适应其他行为主体对一种“真正”威胁内容构成的认知,正塑造着国际体系内的安全互动。行为主体之间和行为主体之内,这两者“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安全认知的共享程度是认识行为主体行为的一个关键。如果人们知道谁能够在涉及什么问题和什么条件下“制造”安全,有时它将可能调整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并因此抑制安全困境。③
在东亚,权力分配和敌意—友善法则两大要素塑造了其独特的地区安全结构。虽然东亚经济方面有东盟+中日韩(“10+3”)合作机制、 博鳌亚洲论坛和东亚展望小组会议,安全合作方面有“东北亚合作对话会议(NEACED)”、东盟地区论坛等合作框架,但东亚仍然具有明显的无政府特征,地区安全的动力仍然是军事、政治因素。东盟成员国之间共享地区利益、共同的价值与行为准则虽可以视其为一个次地区社会,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东亚总体的地区国际体系特征。“在一个地理上多种多样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中,这种安全相互依存的常规模式是一种以地区为基础的集合——称之为安全复合体。”④ 因此,今天的东亚是安全复合体而不是地区社会,也就是不存在有组织的正式地区合作。
社会建构主义并不否认物质力量的作用,但认为它只有在被建构为对于行为体有着特定意义的时候才是重要的。例如,国际关系以物质力量界定的“极”是有意义的,但是它的意义取决于各“极”之间的关系,即是朋友还是敌人,而这种关系是共有观念导致产生的。因此,未来东亚安全模式的形成是因东亚主要力量的观念以及彼此互动塑造而成。哈斯认为,国家对历史的经验以及地区内国家相互利益的影响和作用的认知,不断调整的认知系统以及建立一种“认知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y)”,形成交互认知,从而使国家间相互进行调整和适应,最终制定适合自身乃至整个地区的外交政策。⑤ 东亚主要力量安全观念的变化,首先是国际社会结构变化的结果。这种变化的一个明显迹象即对武力效用的认识方面,各国开始意识到用非军事手段解决安全问题也是可能的。在东亚地区,新安全观念(比如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开始出现在各国外交政策文件中,这本身也是各国调整安全观念及修改政策的结果。在东亚的主要力量即中国、日本、东盟和美国中,大致形成了三种安全观念或模式:第一种是以美、日为代表的安全观念,即“集体防务”思路;第二种是东盟国家的安全观;第三种是中国的新安全观。其中,中国与东盟的安全观念较接近,而东盟与美日之间的安全关系又千丝万缕。这三部分构成了东亚地区安全结构的基本框架。美国虽非东亚国家,但属于东亚力量(其驻军、军事同盟体系、经济力量等)是不容置疑的;东盟虽未形成一个超国家,但一体化的进程使得它越来越能够在安全问题上以一个声音与外界对话。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说,选定地区力量的四“极”及其安全观来分析未来东亚地区安全结构的特征,应当说在强调观念重要性的同时,也承认了物质力量在国际政治生活中不容忽视的作用:主要力量影响着国际或地区安全之命运。
二 美国方式与联盟安全体系
在古典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理论基座上形成了一种传统的地区及国际安全的模式,即集体防务(collective defence),也可称之为联盟安全(allied security)。按照沃尔弗斯的定义,所谓集体防务是指两个以上国家通过“进行防务安排,以防止其国家安全利益遭受被其视为现实的或潜在的主要敌人的某个国家或国家组织的威胁。集体防务的特点是,直接针对其成员国已知的对手,虽然出于外交考虑这个对手可能未点明”。⑥
就安全的相互依存而言,这种联盟体系主导下的地区安全秩序,无论是敏感性还是脆弱性都是不对称的:在其内部,由于提供的安全成本不一,扮演的角色不同,自然也就形成了等级式的、领导与被领导的结构,也形成了在可预期的安全利益中分配的差异;在其外部,凡是联盟之外的国家,要么是非敌非友的关系,要么是敌手关系而被边缘化,虽不一定被宰割,但利益却得不到公平对待甚至受损。霸权稳定论者一直声称,霸权体系与国际秩序稳定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一个强大并且具有霸权实力的行为体有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公益的实现。在其联盟体系内以及一些追随者国内,这种秩序是可以实现的。然而,这种霸权秩序的缺陷在于它不可能成为一个所有国家参与的安全俱乐部。
在东亚,与美国有军事协议的国家毕竟是少数,由于美国军事同盟体系的封闭性,这就决定了在其圈外的国家是多数。如果美国推行的是集体霸权,这一集体只是少数国家,其结果就只会是少数国家损害多数国家的利益。在这种模式中,地区安全自主性被某种强权所“覆盖”,地区出现某种秩序甚至是和平。该模式中,无政府状态通过“霸权领导”消失,但与安全共同体的无政府状态消失不同:它是权力以及等级制抑制作用的结果,它既会因为霸权的消失而再现,也会因为霸权的争夺而出现无休止的战争、冲突。
冷战后,美国试图用“集体防务”来维持其在东亚地区的地位,将在亚太地区的双边军事同盟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多边安全同盟体系。美国具有影响东亚秩序的优势:它的综合力量以及它在国际政治及历史上的地位。除此之外,它还具有地理上的优势,远离东亚,使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对手的打击。地理上的优势还可以使美国趋利避害,对来自地区内的影响可以有选择性。这是东亚国家做不到的,地理上的相互依存性使地区内各国无法回避地区影响。因此,美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地区秩序,却不必担心这种塑造可能带来的任何负面后果,在无形中这会铸就它潜意识中的不负责任而只计利害。对于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小国来说,美国的地理性使其可以放心与之结好或结盟而不必担心威胁,正如史蒂芬·沃尔特所说,威胁性总是与地理性相连的,一个国家可能会担心并不具威胁的邻国,却不担心有威胁的外部大国。⑦
在东亚安全结构中,美国扮演着一种主动的、积极的塑造性角色,这是由其综合国力以及在东亚的历史地位决定的,如果美国不能走出历史怪圈,坚持以霍布斯的目光看世界,那么其军事同盟体系之外的国家都可能成为其联盟战争的指涉对象,这样一来,所产生的“畏惧”将重塑东亚地区结构中的“敌意—友善”法则。而实际上,在这种思维下的战略互动和实践则使得东亚地区“安全困境”加重:一种战争文化将主导东亚地区的命运。而那些美国联盟体系以外的国家既然不被美国联盟所吸纳,只能有两条路可选择:或者保持中立,或者是倒向另一方(如冷战时期情况)。出于被遏制的担心,非联盟体系的国家就必然组成另一种集体组织,虽然不一定是集体防务性质的,但这一组织军事功能的意义必然是较之其他功能更重要的。比如,上海合作组织将由此加快其区域一体化进程,尤其是军事安全功能可能因此完善和强化。
如果说,具有冷战特征的这一东亚秩序是被权力分配和敌—友法则所塑造,那么这种权力分配一方面是美国及同盟体系在东亚结构中的物质力量分配以及中国、俄罗斯在其中占据的位置和角色;而另一方面则是“观念的分配”,美国的冷战思维以及传统的遏制战略最终打造了东亚的无政府文化——这种霍布斯文化自“东亚封贡体系”解体之后就一直存在,但是在冷战之后的许多良好迹象(比如国际社会化趋势)原本可能在东亚至少造就一种“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而敌意—友善法则从另一个角度重塑东亚秩序:中日之间的一系列历史问题非但未被超越,反而日益使两国成为“历史的囚徒”;而美国对朝鲜、越南等国的历史性敌意也可能成为新的情势下国家关系重塑的导因。美国的单边行径又可能使一些新的国家产生“畏惧”以及“敌意”,这样一来,东亚秩序也必然带有下述特征:一是无政府状态。在霍布斯文化结构的东亚,两大国家集团之间的安全困境和军备竞赛被驱动。二是军事—政治安全在国家诸安全领域中占据优先主导权。军工复合体可能再现,生产和军事之间的关系变得密切。三是在这两大体系的竞争中“覆盖”出现了,即地区安全自主性被抑制。四是两大势力之间的竞争溢出区域层面,上升到体系层面,并因此改变全球安全政治结构。五是这两大体系之间可能不会发生直接战争,但是局部性的冲突却因此变得频繁。
美国“集体防务”安排的加强影响了中、美、日等国的双边和多边关系,损害了这些国家的互信基础,阻碍了相互间进行安全合作,并加剧了地区国际安全形势的不确定性。因此,以美国方式(the American Way)整合东亚地区只会加剧地区动荡甚至分裂。
三 东盟方式与合作安全
东盟(ASEAN)提供的多边主义框架推动了东南亚次区域社会化运动,其结果产生了一种集体认同:相互间以“磋商妥协一致通过”原则寻求地区安全的文化结构。东盟的安全模式可以概括为“合作安全体系”。这种合作安全实际上是一种中小国家推动的、通过协调的集体安全,其目的是实现安全共同体。
对东盟来说,任何一个东盟国家都无法单独解决自身的安全问题,任何一种内部的双边合作或与集团外大国的双边合作也不足以解决自身的安全问题。而以集体面目与地区外的其他大国开展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可以在三个层面上缓解东盟的现实和潜在的安全压力:其一,进一步提升东盟国家的整体安全意识,巩固东盟内部的团结和合作。其二,通过开展与地区外大国的多边安全对话,增进与大国之间的互信关系。其三,通过多边安全对话,为各大国提供一个协商和合作的机制,促进它们之间关系的缓和,防止因大国之间安全困境的发展而危及东盟的安全,缓解整个东亚地区的紧张局势,并为建立地区多边安全保障机制创造条件。基于上述考虑,东盟国家将“东盟地区论坛(ARF)”作为开展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重要载体,其目的就是将“东盟方式(the ASEAN way)”变为“东亚方式”, 将东盟这一安全共同体拓展至整个东亚。
那么东盟方式能不能成为整个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一种模式?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提出,通过东盟地区论坛活动,东盟方式可以进一步扩大到整个亚太地区安全问题的处理上来。尽管它有局限,但对促进整个地区的“社会化进程”仍发挥着积极作用。⑧ 但是反对意见认为,即使“东盟模式”在东南亚是成功的,由于东亚地区的情况不同,这一模式运用于整个地区不一定合适。⑨
笔者认为,东盟方式的内在因素制约了它进一步拓展。冷战期间,东亚的安全形势从本质上说都是由大国关系决定的,东亚的稳定是靠大国之间不断变动的均势维系的。冷战后全球形势不断发生变化,东亚安全环境也在变化,但是大国关系至少到目前为止仍然发挥着关键性的影响。东亚地区安全秩序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主要力量的塑造。ARF所依据的理念与其实践实际上存在某种距离。 它虽倡导“合作安全”,但东盟国家在创立ARF的过程中, 潜意识地仍将中国当成限制约束的对象。⑩ 作为ARF的设计者,东盟国家看到了大国间相互竞争与制约的微妙关系,力图在大国竞争的空隙中,利用可以为各个大国接受的特殊地位,从中起缓冲、协调和润滑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小国家的作用,提高自身在亚太地区安全结构的地位,甚至主导地区安全合作进程。比如,东盟力图拉住美国和日本以牵制中国;吸纳越南、缅甸以增强整体实力,抗拒西方压力,也有限制中国影响扩大的考虑。(11) 同时,拉入印度这个区域外势力来抗衡中国。由于地区内大国相互缺乏信任而东盟又不具有威胁性,各大国也乐见东盟在地区安全中发挥主动性的作用。(12) 东盟地区论坛在地区大国关系中起着“润滑剂”的作用,既为中、美、日、俄搭起了一个接触交流的舞台,又通过各国在论坛中的活动搞平衡外交,形成一种成员国间的相互制约构架。(13) 如果东盟国家在安全实践中仍然采取均势的做法,本身就在削弱它的新安全观的影响力和作用,自然也就制约了东盟方式在东亚拓展的可能。
美国的单边(或双边)主义政策也会限制东盟方式的拓展。美国之所以对欧洲选择多边主义而在亚洲选择双边主义,是由于集体认同所致。美国视欧洲为一个需要多边介入的地区,因为它们与欧洲有一种共同体感。因此,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约在冷战结束之后的欧洲安全构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仍是以类似欧洲安全合作组织为基础的多边主义,但在亚太是以美国为首的一系列双边军事同盟在地区安全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9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为对付共同安全挑战而展开的新的地区交流——ARF,美国给予了支持。通过对话和透明度,这些安排能够增进地区安全和相互理解。这些交流是目前存在的双边关系网络的基础”。(14) 美国还认为ARF的一些成员能对美国在东亚的前沿军事部署发挥积极的作用。因此,“美国建设性地参与和支持地区安全对话,积极鼓励东盟和太平洋地区国家为美军提供东道国援助”。美国需要东盟地区论坛,因为这是美国与其他非同盟国家接触的一个有用工具。但是,美国强调多边安全框架不能替代以美国为首的双边安全军事同盟,认为虽然ARF这类多边安全合作有助于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但“它们只是补充而不能替代美国在地区内的双边关系”。只要美国的双边同盟体系存在,美国就会反对这样一个多边的安全机构来管理东亚安全事务。对美国来说,这样一个多边机构是一种制约。
在东亚存在着大国互信困境,大国之间的互信是改变地区安全结构的主要因素,而这又取决于大国之间能否建立某种磋商机制(谈判及共循规则),而这似乎又不是一群中小国家提出的安全对话论坛所能解决的。这正是东盟方式无法扩大为东亚方式的内在制约。
四 中国方式与协治安全
美国无视冷战结束之后东亚地区发生的一些新的变化而试图用霸权模式塑造未来东亚安全秩序,并强化了在东亚的一系列军事条约,这种集体防务的安排对地区安全结构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美国“集体防务”安排的加强影响了中、美、日等国的双边和多边关系,损害了这些国家的互信基础,阻碍了相互间进行安全合作,并加剧了地区国际安全形势的不确定性。出于对美国通过单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谋求霸权利益的担忧,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大国都提出了推动世界多极化的主张。
东盟的安全观念带有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忽略了东亚安全复合体的特征,也忽略了从安全复合体向安全共同体过渡所必要的途径,特别是忽略了敌—友法则和权力分配仍然是塑造地区秩序的主要动力,更忽略了强权对地区结构的特殊作用。大国之间的互信是改变地区安全结构的主要因素,而这又取决于大国之间能否建立磋商机制(谈判及共循规则)。除非这样一个安全机制能让中国、日本、朝鲜和韩国等国觉得有希望解除各自的安全顾虑,并且这种解决方式要较之“自助”战略或联盟战略的风险代价更小。事实上,只有相对稳定的中美关系和大国关系才能促使ARF及东亚其他多边安全合作顺利进行,东亚地区安全合作的进程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大国关系的演变。
如何在地区安全秩序的塑造中既体现国际政治的民主化,又超越均势,并现实可行呢?这就是本文需要讨论的多极安全模式的一种思路,即“协治模式”。这种模式具有混合性,很大程度上它是东亚地区安全政治复杂性、历史性的现实产物。
区域的“协作治理”,即按照多数国家的意愿实现地区秩序与和平的一种进程。这一进程包括了共同体观念、行为体努力维护或推进这种秩序目标的实践以及作为社会的基本机制框架以协调各行为体的互动。但是鉴于地区国际政治的特征,尤其是大国在地区安全政治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因此就形成一个折中或过渡:协作治理及大国协作框架下共同治理的地区安全模式。我们称之为“中国方式(the China Way)”。
协治安全(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ecurity)的第一个维度即“协作”。它与集体安全的相同之处在于,协作以集体行动原则为基础,但在这样一个协作体系中,是由一小群共同协作的大国来防止侵略。其成员不是由于某种正式义务的约束而对侵略做出反应,而更多的是通过在非正式的谈判中共同协作来解决争端和危机。协作即大国更加有效地对地区冲突加以管理,虽然它或许不能消除所有的冲突,但可以通过大国之间的共同携手将冲突的范围和程度降至最低。(15)
协治安全的第二个维度即“治理”。俞可平认为,“治理”被用于政治发展研究,特别是被用来描述后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状况。(16) 詹姆斯·罗西瑙指出,治理就是这样一种规则体系:它依赖主体间重要性的程度不亚于对正式颁布的宪法和宪章的依赖。更准确地说,治理是只有被多数接受(或者至少被它所影响的那些最有权势的人接受)才会生效的规则体系,“治理就是秩序加上意向性”。(17) 奥兰·扬(Oran Young)写道;治理体系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其一是治理的基本机制。宪法为现代主权国家提供了这样的框架,而国际法和多边主义则在当代国际社会充任这一角色。其二是有组织的治理,即“为管理治理体系而创建的物质单位”。(18)
一个和谐的体系要求许多属性,这些属性包括:第一,区域危机可以通过大国之间的双边以及多边协商得到比较满意的解决。第二,区域稳定可以通过其成员的协议来维持。第三,大国之间的冲突可以在一个和谐体系中得以缓解。(19) 也就是说,均势也是可能带来和谐的。协作治理模式的核心点即大国之间的竞争虽不会消除,但大国之间不会再为权力争夺而发生战争。东亚地区的协作治理形成一个通过大国推动的共同治理局面,即东亚安全社会,由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管理地区安全事务。通过大国之间的“协作治理”推动,东亚地区最终发生带有结构性基因的变化——规范、制度性因素制约地区的无政府动力。地区组织、地区意识以及各国的地区政策由此开始塑造着一种新型的地区安全关系结构。
可以称之为中国方式的“协治安全”既有现实主义安全观对地区格局基本判断的一面,又具有社会建构主义安全观相信社会进化的一面。这种协治形式上接近“欧洲一致”或“大国协调”,但在本质上完全不同。之所以不同就在于国际结构的变化:“欧洲一致”是现实主义均势理论的现实政治写照,它的目标虽是和平与秩序,但大国利益却是凌驾于和平之上的,这成为其后两次世界大战的潜在动力。这一差异的意义在于,今天的均势伴随着安全相互依存——这一相互依存虽不必然带来合作,但是却带来了更多的合作机会。也就是说,传统欧洲均势所带来的安全是一种竞争性安全,而今天的均势却可能带来合作性的安全。
一国的安全观念的解读既源于其本身的政策宣示,也源于其安全实践。美国是通过其在东亚地区的一系列双边军事同盟、东盟是通过其安全共同体过程以及东盟地区论坛、中国则是通过上海合作组织而昭示其安全观念内涵的。东盟所提倡的安全观与中国的新安全观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与美国的安全观念有本质的不同。中国与东盟的安全立场相似源于相似的地理环境以及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历史;而不同则源于两个行为主体不同的战略利益、战略身份以及战略背景。这种战略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在塑造地区安全秩序上虽然目标一致,但是路径却完全不同,并且可能造成不同的政治后果。
五 结论
如前所述,东亚大致形成了三种安全观念或模式:第一种是以美、日为代表的安全观念,即“联盟安全”思路;第二种是东盟国家的合作安全观;第三种是中国的新安全观。在第一种美国方式中,地区安全自主性被某种强权所“覆盖”。就现在而言,能够推动这种“霸权”的国家即美国和日本。第二种是由东盟推动的“安全共同体”模式,即以东盟为核心扩大至整个东亚地区的一体化。与集体防务那种基于大国的霸权利益的“美国方式”以及那种基于小国利益“东盟方式”的考虑不同,协治安全既考虑到大国在本地区的特别位置的现实,又考虑到小国的利益需要被保护的一面。通过大国之间的协作治理推动,东亚地区最终发生带有结构性基因的变化,各国之间虽非彼此视为朋友,但是也不再互视为敌人。这种关系模式并非地区安全共同体,但是却可以称之为地区安全社会——从安全复合体演变为安全社会,有了向安全共同体(20) 演化的可能。
[收稿日期:2006—01—30]
[修回日期:2006—07—02]
注释:
① Stephen M.Walt,“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5,No.2,1991,pp.211—239.
② Barry Buzan,“New Patterns of Global Secur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7,No.3,1991,pp.431—451;Stephen L.Spiegel,ed.,At Issue:Politics in the World Arena,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4.
③ 参见[英]巴瑞·布赞、[丹麦]奥利·维夫、[丹麦]迪·怀尔德著,朱宁译:《新安全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66页。
④ 巴瑞·布赞等:《新安全论》,第16页。
⑤ Ernst B.Haas,“Collective learning:Some Theoretical Speculations,”in George W.Breslauer and Philip E.Tetlock,eds.,Learning in U.S.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1,pp.67—97.
⑥ Arnold Wolfers,“Collective Defence versus Collective Security,”in Arnold Wolfers,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62,p.183.
⑦ Stephen Walt,The Origin of Alliances,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pp.1—32.
⑧ Amitav Acharya,“Ideas,Identity,Institution-Building:From the‘ASEAN Way’to the‘Asia-Pacific Way’?”The Pacific Review,Vol.10,No.3,1997,p.343.
⑨ Shaun Narine,“ASEAN and the ARF:The Limits of the‘ASEAN Way’,”Asian Survey,Vol.37,No.10,October 1997,pp.377—378.
⑩ Rosemary Foot,“China in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Organization Processes and Domestic Modes of Thought,”Asian Survey,Vol.38,No.5,May1998,p.439.
(11) Ralf Emmers,Cooperative Security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ASEAN and ARF,New York:Routledge Curzon,2003,Chapter 5.
(12) Jose T.Almonte,“Ensuring Security the‘ASEAN Way ’,”Survival,Vol.39,No.4,Winter 1997/1998,p.81.
(13) 尚前宏、丁奎松:《大东盟及其在亚太的地位》,载《现代国际关系》,1996年第8期,第10页。
(14)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The White House,February 1995,p.28.
(15) 有关coordination与collaboration两个概念的区别,参见[美]阿瑟·斯坦:《协调与合作:无政府世界中的制度》,载[美]大卫·A.鲍德温主编,肖欢容译:《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58页。
(16) 俞可平:《引论:治理与善治》,载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17) [美]詹姆斯·N.罗西瑙:《世界政治中的治理、秩序和变革》,载[美]詹姆斯·N.罗西瑙主编,张胜军、刘小林等译:《没有政府的治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18) Oran Young,“International Governance: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in a Stateless Society,”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4,pp.9—26.
(19) 有关“均势和谐论”请参见Nicholas Khoo And Michael L.R.Smith,“A Concert of Asia?”Policy Review,No.108,http://www.policyreview.org/Aug01/khoo.html。
(20) 这一“安全共同体”思想可参见伊曼纽尔·阿德勒:《和平的条件》,载[英]提莫·邓恩等主编,周丕启译:《八十年危机:1919~1999年的国际关系》,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标签:东南亚国家联盟论文; 东盟共同体论文; 东亚共同体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国际秩序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