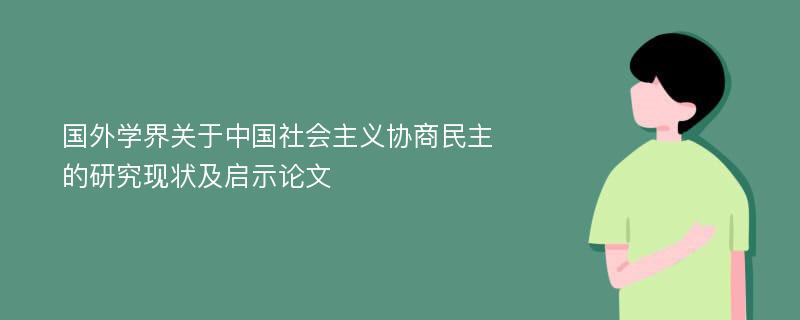
·政治发展研究·
国外学界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研究现状及启示
刘 俊 杰
(江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摘 要: 国外学者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给予了长期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涉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存在与否与存在范围、兴起原因与鲜明特征、实践功能与现实问题、发展路径与未来担当等内容。国外研究既有客观理性的评价、中肯善意的建议以及独到新颖的见解,但也存在西方话语色彩浓厚、整体性研究不足、有些认识不符合中国实际等局限性。基于国外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得出以下基本启示:批判地吸收国外研究成果,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话语体系,国内研究应注重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
关键词: 国外学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国民主政治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成果日益受到国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实践成效与理论成果更是受到国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梳理国外学者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研究成果,对于拓宽理论研究视野、深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研究、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存在与否与存在范围
尽管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已有长期实践,但一些国外学者总是习惯于以西方民主政治的标准来评判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成就,导致其往往作出不切实际的评价。
1.中国是否存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国外大多数学者通常以一种有限的民主概念理解民主化,他们将是否存在西式竞争性选举制度作为判断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民主与否的主要依据。受此影响,一些国外学者否认中国是民主国家,不承认中国存在协商民主。例如,美国学者伊桑·莱布指出,“如果没有竞争性选举,一个国家根本无法称自己为民主国家(至少在政治科学界)。这是一个底线……没有选举层面的政治平等,就没有被视为协商民主核心的公民审议和社会平等。”[1]正是依此标准,他们认为中国不存在协商民主。
与前一种观点不同,有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不应把竞争性选举制度作为协商民主的前提,在他们看来,协商民主已经超越了自由选举民主,而且规范的协商民主即便是在西方国家也是难以实现的,所以,判断中国是否存在协商民主还要看中国的实际情况。而从实际的情况来看,中国是存在协商民主的。澳大利亚迪肯大学何包钢教授指出,西方学界认为“协商民主只能在建立自由选举民主之后才能发展的观点,在方法上存在很大问题”[2]。他主张从中国的文化、历史与现实来理解中国协商民主,通过对中国协商民主实践的考察,他认为中国协商民主是存在的。丹麦学者罗宁·梅达格利亚等通过对中国社交媒体协商的研究认为,“中国的协商民主实践不仅存在,而且以独特的形式运行”[3]。
国外很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分析指出了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功能及其面临的现实问题,他们的观点有些是比较客观的;但有些认识由于受思维方式、研究视野的限制,以及对中国国情和中国协商民主实践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而存在明显的片面性。例如,上文提及的一些学者就认为中国的协商民主实践缺乏公民决策权,这种认识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对中国民主政治运行原则缺乏足够的了解,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对中国协商民主运行的实际情况缺乏客观的认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运行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公共事务协商是民主集中制原则中的民主原则在中国协商民主中实际运用的重要体现,各级党委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对协商事务作出最终决策是民主集中制原则中的集中原则在中国协商民主中实际运用的重要体现。因此,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重要体现,也是解决“议而不决”问题的客观需要。当然,从中国协商民主实践来看,并不是所有的协商事务都由各级党委作出最终决策,在一些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中是存在决策型协商的。所谓决策型协商是指协商成果可以直接成为决策的协商民主形式。在决策型协商中,协商参与者本身也是决策者,如在“湖景社区‘同心议事厅’的协商实践中,协商结果就直接纳入决策,交由社区执行”[22]。
2.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存在的范围
第三,协商列宁主义。英国学者曾锐生将中国协商民主的特征概括为“协商列宁主义”,其主要内涵是:执政为民;持续治理改革,旨在满足公众对民主化的需求;持续努力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以唤起、回应和顺应民意;在经济和财政管理中奉行民族主义,以促进民族主义代替共产主义[16]。当然,他也指出“协商列宁主义”不是一个静态系统,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体系,它要求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不断适应环境的发展变化,以保持执政地位并指导中国的发展。在他看来,“协商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基本结构和执政动态已经形成,即把协商咨询要素纳入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并对各种新挑战作出反应和应对。
尽管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存在协商民主,但他们中的大部分学者依据西方协商民主理论认定中国协商民主只存在于地方层面。这里的地方层面主要是指乡镇以及城乡社区层面,即基层政治领域。这主要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国家层面的协商容易受到政治权力的影响,而依据西方协商民主理论这是不能称之为协商民主的。澳大利亚学者乔纳森·昂格尔等认为,尽管中国缺乏国家层面的协商民主实践,“但在这里可以找到数不胜数涉及普通百姓的充满活力的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的案例”[4]。澳大利亚学者约翰·德雷泽克指出,“如果中国确实具有协商能力,那么它可能在地方一级的参与式创新中发现”[5]。由此可见,他们将目前中国城乡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公民评估会议、民主恳谈会、参与式预算、协商民意测验等均视作地方协商民主实践的重要形式。
不过,也有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协商民主实践不仅存在于地方层面,也存在于国家层面。如韩国学者李允熙等指出,中国的“全国人大每一件法案的起草都采取协商民主的形式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或举办专家座谈会、论证会听取专家对法律草案的意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虽然不是全体公民都能参与的协商民主,但它却是由一批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公民组织和公民直接、平等参与的协商民主”[6]。加拿大学者约埃尔·科恩里奇以2009年中国医疗体制改革为例考察了中国国家层面的政治协商,指出“在最近对中国医疗体制进行改革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推出了各种形式的咨询。为了解决官僚主义的分歧,启动了一个与学者和国际组织磋商的进程。为了收集技术反馈意见,政府还与专业人士进行了另一种精英咨询‘两会’”[7]。
需要指出的是,个别国外学者也把网络协商视为中国协商民主实践的重要领域。美国学者欧瑞利·刘易斯提出,中国“在线协商形式的政治多元化可能被认为是更加互动和自由化的政治秩序的基本条件,这种政治秩序源自更多的公众协商和社会反馈”[8]。罗宁·梅达格利亚等指出,“尽管中国社交网站、新浪微博、微信等应用越来越受欢迎,但在网络讨论方面,传统的在线论坛在中国互联网中仍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讨论公众活动时”[9]。
国外学界对于中国协商民主存在与否与存在范围的认识表现出明显的西方话语倾向,特别是否认中国协商民主存在的观点表现出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事实上,中国的协商民主不仅存在,而且是广泛地存在,它既存在于国家层面也存在于地方、基层层面,既存在于政治层面也存在于社会层面,既存在于现实层面也存在于网络层面。
二、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兴起的原因及其特征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中国缘何兴起是国外学界研究的兴趣点之一。国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兴起的原因,同时指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鲜明特征。
第三,有助于培育协商公民。何包钢通过对中国乡村协商实践的调查发现,“协商已经培育出一种新型的协商公民,因为它改变了村民对平均分配观念的看法,这对解决问题至关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也减少或解决了过度上访的问题。当公民学会妥协,能够进行理性对话和实行自治管理时,他们就会发展和提高协商公民的能力和素质,从而有助于减少和管理社会冲突。”[20]不过,他也认为,“为了培养协商公民,一次性的大规模民主协商投票是不够的,必须定期和非正式地重复。”[20]
(5) 若P(a≥b)≥0.5,P(b≥c)≥0.5;则P(a≥c)≥0.5;当且仅当P(a≥b)=0.5,且P(b≥c)=0.5,则P(a≥c)=0.5
1.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兴起的原因
第一,中国共产党增强执政合法性的需要。不少国外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一系列不可忽视的问题,如干部贪污腐化严重、社会分配不公、群体性事件频发,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受到严重影响。然而,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来源不断下降时,协商程序可以产生合法性”[10]。在他们看来,合法性是重要的政治资源,即使是威权统治也需要积累合法性以缓解社会冲突和降低执政成本,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协商民主实践是增强其执政合法性的现实需要和重要途径。
第二,中国社会实现善治的要求。如上文所述,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国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依靠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越来越难以应对这些问题,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转变治理方式。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创新,“推出了各种协商机构和设计,以应对在深化市场改革和社会转型时期不断增长的治理挑战。”[11]
第三,地方领导人的积极推动。一些国外学者认为当今中国协商民主实践的创新探索主要集中在地方,这方面的创新探索与地方主要领导人的决心和勇气有着很大关系,而这种决心和勇气直接受领导人的动机影响。“地方领导人也有各种动机和动力来推动协商机构的发展。一些官员的目标是达成真正共识,以获得某些政策的合法性、减少社会冲突,甚至是为了赢得个人荣誉。也有一些官员则认为,协商机构是实现民主管理和监督的有效工具。还有一些官员认为协商机构有助于缓解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紧张关系。”[12]178
第四,中国发展民主政治的需要。何包钢认为,中国“试图发展一种将行政秩序与政府、人民相结合的协商机制,以改善干群关系、实现地方政治的良好治理。可以肯定的是,北京已经将协商民主用作温和民主的一种形式”[12]178。在他看来,协商民主对于中国而言是一种温和的可以接受的民主形式,这是因为协商制度不强调竞争性选举,更容易被中国所接受[13]136。
第五,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实践在中国文化和历史上有着明确的根源”[2]。有学者认为中国从古至今就存在协商的传统和文化,中国古代在政治层面有朝议制度,君臣之间围绕国家大事展开讨论;在民间社会层面有书院,儒家学者通过建立公共论坛讨论国家大事。清朝末年清政府为推动宪政改革就建立了咨议局,这是地方性的审议机构。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路线思想使得干部和群众能够围绕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协商对话[14]。
2.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鲜明特征
第一,协商威权主义。一些国外学者指出协商威权主义是中国协商民主的鲜明特征。所谓协商威权主义是指中国的“协商是在一党统治下进行的。国家在发展、动员和推动协商机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3]134。还有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将威权主义领导与协商影响结合起来,产生了明显的威权主义协商现象”[10]。“简而言之,威权协商允许领导人保留权力做出最终决定,而民主协商授权公民或选民作出最终决定。”[15]
第二,协商工具主义。在很多国外学者看来,中国协商民主实践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注重利用各种协商形式解决实际问题,具有明显的工具主义色彩。新加坡学者韩海津指出,“中国政府主要是从工具角度开展协商的”[11]。何包钢等也指出,“今天中国的公众协商侧重于治理的具体问题,往往直接回应冲突”[14]。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扶贫攻坚的主攻方向,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难中之难、坚中之坚。方案围绕扶贫任务,提出了医疗保障扶贫的六大目标。
第一,有助于巩固共产党统治。国外学者普遍认为具有威权主义特征的中国协商民主实践不仅不会削弱威权统治,反而会增强威权统治。美国学者苏珊·奥格登通过案例分析认为“在中国,局部形式协商和咨询的出现似乎巩固了威权国家的权力”[17]。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唐贝贝通过案例分析认为,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中国协商政治的发展及协商机构的建立是为了充分收集民意,更好地推进共产党科学民主决策,其实施效果是有助于增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8]。
三、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实践功能与现实问题
一些国外学者通过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实践功能与现实问题进行了考察分析,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1.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实践功能
国外学界对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兴起原因和基本特征的分析有些是比较符合中国实际的;但受思维方式、研究视野、认知程度的影响,一些国外学者的认识还存在一定局限性,“协商威权主义”“协商列宁主义”等特定表达都是西方政治学语境下基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而生成的概念,具有明显的西方话语特征。
第二,有助于推进中国善治。美国学者谭青山通过考察中国农村协商民主实践提出,“协商民主机制可以缓解治理不当引起的社会动荡,并可以建立以集体决策和公开政治进程为基础的新的合法性。”[19]200何包钢通过对中国社区协商民主实践的考察提出,“定期和频繁的参与性和协商性会议解决了社区问题,避免了公共决策中的重大失误,节省了管理地方事务的金钱、人员和时间,从而减少了人们的上访和投诉数量。在这方面,协商机构可以视为释放中国‘快速机器’压力的‘阀门’”[12]177。曾锐生更是将中国的协商民主实践称之为“中国特色善治”[16]。
⑪Neil M.Richards,Jonathan H.King,“Three Paradoxes of Big Data”,Stanford Law Review Online,66,2013,pp.41 ~46.
隐层可以有一个或多个,隐层中的神经元均采用S型变换函数。三层前馈神经网络能以任意精度完成任何连续函数的映射。
第五,协商过程不规范。在西方,协商民主的核心要素是审议,强调协商主体深思熟虑的协商讨论。在一些国外学者看来,中国的协商实践“所使用的技术具有广泛代表性,但缺乏深思熟虑”[13]141。何包钢认为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不倡导尖锐的批评,协商往往在温和的气氛与柔和的谈话中展开,参与者可能仅仅在表面上取得满意,导致协商过程拒绝积极而富有成效的观点分歧,使协商结果在很多情况下是虚假的一致[12]193。
第一,协商成本高昂。国外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公共协商的发展和实践会产生高昂的成本,包括组织会议、促进学习和制定规则等,这使得政府官员不得不投入大量时间和资金”[21],这种高成本的投入不利于协商民主充分且持续地发展。
第二,公民决策权缺乏。国外有学者认为,公民的决策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而民主政治的实践则是公民发挥民主决策的保障。然而,在中国协商民主实践中公民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参与权而非决策权,决策通常由党和政府作出,“协商会议不过是在早期阶段进行磋商。即使在今天,许多地方的协商实践仍然如此,这就使一些人将其仅仅视为形式主义。”[13]143
就连著名的宝石切割大师阿伯特·拉姆齐(Albert Ramsay)都曾对19世纪末到访印度的经历有以下描述:
新媒体平台中,微博最为典型。因此,本研究将新浪微博作为新媒体的代表,利用Gooseeker数据抓取软件,通过对“取消计划生育”“停止计划生育”“放开二胎”“放开二孩”“单独二胎”“单独二孩”“全面二胎”“全面二孩”等与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紧密相关的关键词进行抓取,得到2009年8月14日到2015年10月28日期间的1 980条微博数据[注]数据采集于2017年3月15日。另外,由于微博数据量极大,关键词搜索只能随机呈现其中一部分,因此1980并非是全部相关的微博量,特此说明。 。去除无效和重复数据后,按转发量进行排序,选取前500条微博作为样本。
能源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基础。由于传统化石能源日益枯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开发新能源、加强可再生能源的综合利用成为解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能源需求增长与能源紧缺之间矛盾的必然选择。2015年7月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在促进智能电网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加强能源互联,促进多种能源优化互补”。
第三,民主代表性不足。国外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协商民主存在代表性不足的问题。他们提出,“在许多中国地方协商会议上,参与者要么是政府官员选择的,要么是自我选择的。因此,这些参与者所具有的代表性是有问题的。此外,他们可能会被视为受官方操纵。如果中国的做法已经变得更加‘民粹主义’,那么可以认为,他们既没有充分的审议,也没有足够的代表性”[13]141。还有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的协商民主存在主体不平等的问题,他们认为“在大多数中国的协商机构和会议上,参与者在理论上享有平等的‘权利’,但通常被迫进入传统和高度不平等的权力关系”[13]140。另外,个人素质与经济实力的差距也会造成协商主体对协商结果影响的不平等。
锁相环是一种自动控制反馈系统,主要由鉴相器、环路滤波器和数控振荡器组成。锁相环通过鉴相器比较外部信号和输出信号的频差,通过数控振荡器的调节,使输出信号与外部信号相位差恒定,频率一致,从而起到跟踪信号频率相位的作用[9-10]。SPLL是基于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在DSP等通用可编程器件上通过软件编程的方式实现的数字锁相技术。SPLL的设计通常采用在模拟环路设计的基础上,利用数字映射变换到数字环路的方法实现。数字映射变换方法主要有双线性变换和后向差分变换。简单的二阶软件锁相环通过双线性变换的线性Z域模型如图1所示。
第四,协商制度不健全。关于这一问题,国外学者主要论及了两个方面:一是协商民主探索“缺乏强有力的激励措施”[12]179,这不仅使得协商主体参与动力不足,缺乏主动投入协商、主动提升协商质量的积极性,而且导致中国协商实践探索陷入了被动的动员式参与境地,造成协商的实效性不足。二是未能建立相应的监督制度,导致“协商缺乏集中且公正的监督体系”[12]193。协商组织、协商主体、协商过程由谁监督、如何监督尚不明确,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协商的实效性。
2.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面临的现实问题
狮子纹饰还具有象征美的艺术价值,威武庄严的狮纹形象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体现了无惧邪恶,勇于进取的精神,是中华儿女对中华文明的自信。狮纹带给人的精神力量有利于提升社会人性的觉悟,改变社会的人的精神现状。
虽然中职学校开设了语文拓展教学这门课程,但是在实际教学中我们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中职生的语文学习基础十分薄弱,对于拓展教学他们需要有太多的功课去做。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他们的口语交际能力比较差,主要表现为在一些人比较多的并且比较陌生的场合,他们与别人交流时就会出现一些结结巴巴、语无伦次、说话无中心、语言不连贯等不良现象。这些不足对于他们以后的工作面试来说,是非常不利的。这种不良现象并不是完全不能改正的,只要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有针对性地多加练习,就可以很好地克服。
四、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路径与未来担当
国外学者从不同方面分析指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路径,并对协商民主未来能否担当起主导中国民主化的重任进行了深入探讨。
1.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路径
使用镉标准液GSB G-62040-90按照岛津原子分光光度仪设定程序建立镉含量与吸光度关系的标准曲线,结果见图1。
第一,增强协商的代表性和平等性。为保证协商的代表性、平等性,有学者针对精英阶层对于协商的过分影响问题提出,中国协商民主实践中的“参与者是通过一定资格限制选定的,从而确保富人(和其他团体)具有不成比例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也许减少富人影响力的唯一方法是设计政治机构,明确授权代表穷人和边缘化群体的利益,例如,代表性的会议为弱势群体保留位置”[23]151。也有国外学者根据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提出“儒家传统也为当代中国提供了一种更可行的替代方案:协商者可以通过儒家式的考试来选择”[23]154。
第二,培育和发展自治团体。有些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的协商民主实践大多由官方主导,民间社会主导的较少。在他们看来,这样不利于中国协商民主发展,因为官方主导的协商实践越多,投入就越大,成本就越高。此外,众多社会问题仅凭官方主导的协商民主实践也是难以应对的。因此,中国“需要培育和发展自治团体”[19]199。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逐步关注“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不过很长一段时期内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的关注是润物细无声的,并没有将航行自由视为中美南海博弈的焦点。美国这一时期的政策重点是将维护“南海航行自由”视为自身的霸权责任,通过敦促相关方以外交谈判方式和平解决南海争端来最大程度地防止地区冲突危及其“南海航行自由”。
第三,加强协商能力建设与系统化建设。有国外学者认为,协商能力建设能够使公民更多地参与现有的政治制度,积累民主活动经验,这是民主建设的重要路径,中国要推动协商民主发展,也应注重从社会能力、组织能力、参与能力等方面加强建设[18]。也有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协商民主发展需注重系统化建设,以提升协商民主的整体效能。“中国的协商政治应该将现有的协商活动扩展至更大规模的体系。作为一个系统,它可以包括一些话语领域和不同的参与者以及非直接的国家控制活动:当一个协商场所被强制掩盖时,另一个场所可以填补以平衡该系统。”[18]
第四,推动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共同发展。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不能仅局限于协商民主形式,要提升协商实效、推动民主发展、降低参与成本,同时还要将协商民主与其他民主形式结合起来,特别是与选举民主结合起来。他们提出,在涉及人数众多的情况下协商主体的产生可以运用票决方式;当协商共识难以达成时,也可以考虑运用票决的方式解决。“直接应用于公共政策选择的协商投票技术作为一种民主协商形式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并且不需要党派竞争,不会威胁到一党制国家统治)”[24]。
2.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未来担当
对于未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能否担当起主导中国民主化的重任,国外学者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协商民主发展有可能为未来中国开辟一条民主新路即协商民主主导的民主化。何包钢认为中国“发展和改进协商机构是一种民主化战略”[12]175。他基于中国地方协商民主实践的调查指出,“协商机构的重复试验能够超越原来的界限,导致更为实质性的结构变化,并为地方民主化铺平道路……协商制度是走向民主的道路,也是中国人发展和改善地方民主的新领域”[12]194。唐贝贝认为:“这种在中国政治体制下的协商转向能否推动中国民主化发生更深刻的变化,取决于更强大的公共领域的不断发展,更有效的政府反应能力以及公民参与能力的提高……总之,随着协商能力建设的发展,协商政治可能会改变中国的政治格局。”[18]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未来中国不可能出现由协商民主主导的民主化。有国外学者指出,中国的“这些磋商和有限的协商过程不可能主导未来中国的民主化。尽管协商论坛让参与者表达自己的想法,有时也与其他人交换意见,但政府仍然保持对讨论范围和内容的控制”[7]。也有国外学者指出,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实践是国家—社会模式的一种新探索,“然而,这不是民主化,而是一种复杂的具有威权主义特征的间接社会治理。”[25]
客观地讲,国外学界关于中国协商民主发展路径的有些认识是具有建设性的,有些建议是中肯善意的;但是有些观点主观性明显,不符合中国实际,我们必须警惕。国外学界关于中国协商民主未来能否担当起主导中国民主化重任的认识分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西方话语特征,同时也体现了国外研究的局部性、片面性。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两种重要形式,“在中国,这两种民主形式不是相互替代、相互否定的,而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26],两种民主形式都是为了保障人民有效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因此,思考中国协商民主的未来担当不能仅着眼于协商民主,还必须将其与中国选举民主、与中国整体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结合起来。
总的来看,国外研究既有较为客观的认识和评价,也有中肯善意的建议和独到而富有启发的见解;但由于受到知识背景、思维方式、政治立场、研究视野的影响,以及中国协商民主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导致国外研究存在西方话语色彩浓厚、整体性研究不足、有些认识不符合中国实际等局限性。通过梳理国外学界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研究可以得出三点基本启示:其一,批判地吸收国外研究成果。对于国外学界的研究成果我们既不应该全盘否定,也不应该不加辨别地全盘接受,应批判地吸收,对于符合中国实际情况、有益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的成果要积极借鉴吸纳。其二,构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话语体系。国外学界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某些方面的研究具有明显的西方话语特征,这就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话语体系、增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话语权的迫切任务。为此,需要“从历史与逻辑、传承与创新、比较与借鉴、解析与建构的多重维度,不断拓展研究进路,加快推进学术创新,自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理论与话语体系,以掌握话语主导权”[27]。同时,“造就一批既有深厚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研究理论基础,又要精通西方协商民主话语体系的学者,为提高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国际对话能力造就人才队伍,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国际对话能力”[28]。其三,国内研究应注重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国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研究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大量使用实证研究方法,与之相比较,国内学界对实证研究还不够重视。国内学界的研究更多的是单纯的理论分析,这种理论分析虽然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但有时在分析协商民主具体问题时会显得宏观空洞,说服力不足。因此,国内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
参考文献:
[1] Ethan J.Leib,“Pragmatism in Designing Popular Deliberative Institu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In Ethan J.Leib,Baogang He,The Search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China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US,2006,p.115.
[2] Baogang He,“Deliberative Culture and Politics:The Persistence of Authoritarian Deliberation in China”,Political Theory ,Vol.42,No.1,2014,pp.59-81.
[3] Rony Medaglia,Demi Zhu,“Public Deliberation on Government-Managed Social Media:A Study on Weibo Users in China”,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Vol.34,No.3,2017,pp.533-544.
[4] Jonathan Unger,Anita Chan,Him Chung,“Deliberative Democracy at China’s Grassroots:Case Studies of a Hidden Phenomenon”,Politics and Society ,Vol.42,No.4,2014,pp.513-535.
[5] John S.Dryzek,“Democratization as Deliberative Capacity Building”,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42,No.11,2009,pp.1379-1402.
[6] 李允熙、杨波:《协商民主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7] Yoel Kornreich,Ilan Vertinsky,Pitman B.Potter,“Consultation and Deliberation in China:The Making of China’s Health-Care Reform”,The China Journal ,Vol.68,2012,pp.176-203.
[8] Orion A.Lewis,“Net Inclusion:New Media’s Impact on Deliberative Politics in China”,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43,No.4,2013,pp.678-708.
[9] Rony Medaglia,Yang Yang,“Online Public Deliberation in China:Evolution of Interaction Patterns and Network Homophily in the Tianya Discussion Forum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Vol.20,No.5,2017,pp.733-753.
[10] Baogang He,Mark E.Warren,“Authoritarian Deliberation in China”,Daedalus ,Vol.146,No.3,2017,pp.155-166.
[11] Heejin Han,“Policy Deliberation as a Goal:The Case of Chinese ENGO Activism”,Journal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19,No.2,2014,pp.173-190.
[12] Baogang He,“Participatory and Deliberative Institutions in China”,in Ethan J.Leib,Baogang He,The Search for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China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US,2006.
[13] Baogang He,“Western Theories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the Chinese Practice of Complex Deliberative Governance”,in Ethan J.Leib,Baogang He,The Search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China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US,2006.
[14] Baogang He,Mark E.Warren,“Authoritarian Deliberation:The Deliberative Turn in Chinese Political Development”,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9,No.2,2011,pp.269-289.
[15] Baogang He,“Reconciling Deliberation and Representation:Chinese Challenges to Deliberative Democracy”,Representation ,Vol.51,No.1,2015,pp.35-50.
[16] Steve Tsang,“Consultative Leninism:China’s New Political Framework”,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8,No.62,2009,pp.865-880.
[17] Suzanne Ogden,“Reviewed Work(s):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by Pierre Landry and The Search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China Edited by Ethan J.Leib,Baogang He”,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7,No.3,2009,p.697.
[18] Beibei Tang,“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China:The Dimensionsof Deliberative Capacity Building”,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19,No.2,2014,pp.115-132.
[19] Qingshan Tan,“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Village Self-government in China”,in Ethan J.Leib,Baogang He,The Search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China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US,2006.
[20] Baogang He,“Deliberative Citizenship and Deliberative Governance:A Case Study of One Deliberative Experimental in China”,Citizenship Studies ,Vol.22,No.3,2018,pp.294-311.
[21] Xie Lei,“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Rural China”,China Information ,Vol.30,No.2,2016,pp.188-208.
[22] 刘俊杰:《城市社区协商民主的现实问题与推进路径——以无锡市城市社区议事会为例》,《黑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23] Daniel A.Bell,“Deliberative Democr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 Comment on Baogang He’s Research”,in Ethan J.Leib,Baogang He,The Search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China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US,2006.
[24] James S.Fishkin,Baogang He,“Alice Siu,Public Consultation Through Deliberationin China:The First Chinese Deliberative Poll”,in Ethan J.Leib,Baogang He,The Search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China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US,2006,p.241.
[25] Jessica C.Teets,“Let Many Civil Societies Bloom:The Rise of 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 ,Vol.213,No.213,2013,pp.19-38.
[26]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
[27] 孙德海、方世南:《论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理论与话语体系建构》,《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9期。
[28] 董树彬、刘秀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从发展优势到话语优势的转变》,《理论探讨》2018年第2期。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2X( 2019) 06-0057-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协同发展研究”(15CKS019)
作者简介: 刘俊杰,1982年生,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巩村磊]
标签:国外学界论文;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论文; 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论文; 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