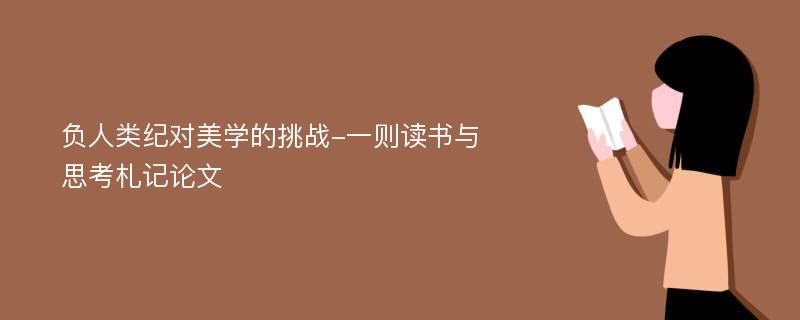
负人类纪对美学的挑战
——一则读书与思考札记
胡继华
摘 要 :20世纪90年代至今,一波接一波的事件表明,瓦雷里、胡塞尔和列维-斯特劳斯所忧患的“精神危机”还在延伸和延续,其结果势必是“人类纪”的自我超越及其向“负人类纪”的转型。斯蒂格勒指出,“人化”过程的每一刻都在发明生命和摧毁生命,技术学的每一个进步都在补偿人性的匮乏和剥夺人性的潜能,器官学一方面将生命延伸到身体之外,另一方面又废黜了某些精致的身体官能,药物学则揭示一切药物都是补药又是毒药。“人类纪”逆转时代,意义因纯粹化更趋稀薄,象征极度贫困,只剩下那些神秘的能指。于是,生理美学、器官美学和社会美学,都必须处理普遍的失调,这就提出了复苏“智性灵魂”,探索人类在技术时代自我拯救的可能。
关键词 :人类纪; 负人类纪; 技术二重性; 美学拯救
一、引 言:“没有未来”
以宇宙宏观尺度观照地球史,人类对地球的地质与生态系统发生决定性影响的时代,被称为“人类纪”(anthropocene)。同时,“人类纪”也是一个描述人与自然对话的范畴,它表明一个人类主导对话的机缘,其中人与自然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中存在着非对称性与非互惠性。
1)通过问卷形式对我国建筑业从业人员及市民进行调查可知,人们对绿色建筑的认知观念存在偏差。部分施工人员认为,绿色建筑的基本要求在于提高建筑周边绿化率,即提高绿化率就是绿色建筑。人们对绿色建筑认识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绿色建筑的发展。
2018年,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将他1983年以来的哲学探索凝练为“负人类纪”(neganthropocene)范畴。[注] 斯蒂格勒曾在图卢兹经营一家咖啡馆,1978年至1983年,因武装抢劫银行,他被判刑5年。在服刑期间,他开始研究哲学,后来在德里达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他曾任法国国立视听中心主任,声学与音乐研究中心主任,巴黎国际哲学学院教导主任,宫片涅科技大学“技术认识、技术组织和技术体系”研究中心主任,现任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文化部负责人、创新与研究学院负责人,兼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他指导过文本、图像和声音的数字领域的多样技术实验,而且在法国中部小镇埃皮纳伊莱弗勒里耶(Épineuil-le-Fleuriel)成立了自己的哲学学校。斯蒂格勒的多卷本著作《技术与时间》已经有三卷译成中文,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其在中国美院的讲演由重庆大学出版社以《人类纪里的艺术》结集出版,部分论文发表于《热风学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他的论文集《负人类纪》由Daniel Ross编辑、翻译、作序,由伦敦开放人文出版社出版。犯罪入狱,铁窗日月,对他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灵魂的转型,也许正如柏拉图所说,研究哲学,就是关切灵魂,一定会导致灵魂的转型。关于这段日子,他用胡塞尔现象学的哲学语言写道:“我被关押在圣米歇尔监狱,这是我贸然行动的后果,这让我悬置我的行为,中止我的行动;此乃监狱的作用。但中止与悬置也是哲学的开端(苏格拉底的守护神也是喝令中止的神),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我反思贸然行动的普遍机缘——同时,我也回忆起一切让我陷入此等处境的一切行动。”(Bernard Stiegler:Neganthropocene , edited,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aniel Ross, London: Open Humanities, 2018, p.15)在他看来,以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技术为前锋引发的一场“自动化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改变了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及其在地球上的生存方式。2015年,在埃皮纳伊莱弗勒里耶夏日哲学研讨班上,斯蒂格勒发表讲演宣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纪元的纪元(l’ époque san époque)。”这么一个没有纪元的纪元,就是预测“后人类纪”将把人类纪带向终结,从而超越前此宇宙史,从根本上改变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开启一场“人与自然”的新对话。斯蒂格勒还暗示,“人类纪”之登峰造极,便得到了所有关于“死亡”“终结”“耗散”“枯竭”的所有悲剧性命题。在这些命题之中,有一个命题就是人类在主导地球的纪元里伤痛至深以至于“无法疗伤”(L’ impansable)。恰好也有一名当代法国作家也用“无法疗伤”作笔名,写了一本题名为《溶解时间》(L ’effondrement du temps )的小说,书中主人公“花神”为“负人类纪”的极端不确定性感到厌倦之余,还有几分听天由命的冷漠:“我们是最后的一代,或者终结之前的最后一代。”[1]15但时间永在流逝,日月星辰周行不殆,可就是一切这么不确定,却确定“没有未来”。
二、人类纪及其转型
1944年,波兰尼(Karl Polanyi)提出我们时代政治和经济正在发生一场“大转型”。这就预测到了“人类纪”登峰造极,势必朝向“负人类纪”转折。斯蒂格勒在其《自动化社会》一书中高度关注随着数字化时代到来而出现的普遍自动化趋势所引发的诸种问题。他的基本论点是:算法自动化导致工资劳动和就业减退,宣告凯恩斯“生产收入再分配”经济模式的终结,而这一模式的基本前提是宏观经济的偿付能力。我们目前所经历的全球变革为人与自然的对话提供了新的选项:
首先是模糊控制器1的设计,根据荷电状态的变化率ΔSOC,以及温度的变化率ΔT来计算析气电压Uq的大小,与锂电池的端电压进行比较,判断何时进行负脉冲去极化处理。以ΔSOC和ΔT作为模糊控制的输入量,Uq为输出量。
但是,如果把热力学第二定律运用于人类文化与精神现象,发挥出一种“熵世界观”的悲观哲学,也就像把生物进化论运用于人类,而推导出“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样,都是郢书燕说,谬以千里。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前提是系统封闭性。也就是说,在一个封闭系统内,能量转化趋向于熵最大值,热量趋向于均衡,秩序趋向于瓦解。然而,生命是一个开放系统,允许生命过程及其演化的地球存在的宇宙,也很可能是一个开放系统。尼采、列维-斯特劳斯以及安德森,也许重复了“熵世界观”的谋划者们同样的严重错误:关闭一个开放系统,终归导致系统稳态,甚至导致系统消逝。布卢姆(Harold F. Blum)在《时间之矢与进化》中对逃避“熵化”展开了开创性探索。他指出,有机体生长体现了微小的局部熵减,伴随着宇宙总熵在更大范围的递增。[12]生物通过从周遭环境摄取自由能量,以自体免疫的方式反抗随着时间而递增的熵流,甚至朝着逆反熵流的方向进化。摄取负熵(neg-entropy),是生物生存的基本前提。[11]48反抗熵流,便是生物生存的本能。薛定谔断言,生命的本质是一种耗散结构,朝向平衡态的进化是所有生命的共同趋势。[13]然而,生命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其耗散能量的过程是一种涨落,一如海上潮涨潮落,一如天上云聚云散。作为开放系统,生命有能力从周围环境中不断摄取负熵,吸纳有效能量,抵抗无坚不摧的熵流,防止自己被耗散告罄,阻止朝向终极平衡态和无序化的进程。所以,生命是一个同熵流抗争的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人类纪”中人与自然对话所导致的大规模创造性毁灭,也许是宇宙间熵潮的涨点,是一阵无序的旋风。相对短暂的人类进化史及技术与环境的关系状态,不足以证明宇宙复杂系统的涨落有序,以长时段的眼光感受人与自然的呼吸则可领悟,不稳定的开放系统比如人类精神及其器官的外化,不仅高度复杂,而且包含着潜在数目巨大的分叉,对宇宙的涨落极度敏感,哪怕是非常微小的涨落也可能震荡和改变整个结构。于是,“人类纪”的登峰造极及其向“负人类纪”逆转,就是从熵学到负熵学的逆转,就是从封闭的熵世界观到开放的负熵世界观的逆转。这种逆转充满了希望,也充满了危机。说它充满希望,因为它提示我们,生活在不确定的涨落宇宙中,不应该固守任何一种浅薄的乐观和盲目的信念。说它充满了危机,因为它告诫我们,反抗熵流,摄取负熵,生命自我持存和自我拯救之途格外艰辛。[14]
*对我们而言,一切都证明政治信仰、信念、信任、希望与意志全面溃败,一种绝望、反动和仇外的势力相应上升,一切都过分率性随意,以至于无法命名那些代人顶罪的人,利用一切机会诉之于恐惧和愚蠢,迄今为止其高潮在2016年11月8日一名真人秀小商贩被选为美国总统,人们渐渐理解一种政体乃是由作秀驱动的过滤泡沫构成,其主体是观众而非公民,它再也不遵循“民主制”的最低要求,而民主制向来被理解为一种代议制度,集体决策的权力寓于“民众”(demos)——所谓的“特朗普纪”(Trumpocene)首先就是一个后民主的无世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集体决策严格说来是不可能的,因为真理失落了其现实效用,多少显得像是一种无关紧要的陈腐标准。
2008年,C. 安德森(Chris Anderson)发表著名论文《理论的终结:数据洪流超越科学方法》(The End of Theory :The Data Deluge Makes the Scientific Method Obsolete ),这篇文章被许多人读作是数字文化革命的宣言、传统知识形态的判决书。安德森断言,以大数据为基础的算法自动化将比科学家更快捷、更有效地证明命题,发展理论,验证理论,发明理论。[2]机器的相关性能力岂是人类所能比拟?理论终结,也就是理论知识的贫困化,或者说理论的“无产阶级化”。按照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分类,科学知识(epistēmē)让位于实践智慧(phrönesis),实践智慧必将由工艺知识(technē)取代。工艺知识的新形态就是人工智能的结晶——人机合体(Robot or Cyborg),它为人类纪自我超越和转向负人类纪提供了典范的样例。
计算思维[1]的英文释义是Computational thinking,顾名思义,即是将计算机的思维用在人的思考里。拓展开来,便是我们用计算机的基础概念、计算方法、语言逻辑等去思考、设计和解决人的问题。
人类在自己意识不到的“人类纪”里,通过主导自己同自然的对话而产生的一切,包括人工智能与人机合体,都是“熵的剧增”或“负熵式分枝”。或者用德里达所援引的柏拉图的话说,一切人类文化发明,就像从古代埃及侵入到古代希腊的“书写”技艺,都是毒药和补药。于是,在一切都不确定而唯一确定的是“没有未来”的生存境遇下,人类必须“以反讽的方式生活”。也就是说,“接受我们自身存在的无根基的一个理由,也就是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中”。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中,就是要学习一种智慧,一种与药物共生的智慧(learn to live pharmacologically)。斯蒂格勒尝试建构一套“精神药物学”(Pharmacology of Spirit),意在让生活值得生活(makes life worth living)。[3]欣然接受药物,不同于病态地迷恋药物,一如伊格尔顿所说,“欣然接受死亡,不同于病态地接受死亡”[4]。而这就是反讽地生活,或者说悲剧性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文化理论就是精神药物学,它将人类生存的困境升华到了悲剧绝对性和反讽本体论的境界。
4.生产水平低。不单是育肥指标,母猪的生产性能(母猪利用率、产仔数、哺乳率)也低于发达国家,养猪技术落后,设施条件差,除发达地区和后来兴建的一些猪场设施较好以外,很多猪场设备老化,结构不合理,无法提供现代猪所需的良好环境,发挥其生长潜能。
以大数据为样例所引领的全球化策略营销和消费主义正在摧毁人类历史上所有的知识形式:理论知识,实践智慧,生活风格,手工技艺,机械复制,等等。人类已经越过工业化浪潮,急速滑向一个超工业社会。斯蒂格勒将这个大转折时代描述为一场世俗的启示录(a secular apocalypse),而“我们的时代【人类纪】正遭受一种巨大的象征苦难”,“【它】将导致欲望的整体性摧毁,也就是将要毁灭力比多经济”。“投机式营销”(a speculative marketing)经天纬地,正在系统地剥夺我们的驱力,人类生存丧失一切关联,而进入海德格尔所谓的彻底的“无所牵挂状态”。这就是斯蒂格勒所谓的“无产阶级化”,他还调遣道宁(Nicolas Donin)的说法,断言“感性的机械转向”将个体的感性生活“永久地交给大众媒体来控制”。[1]101所以,当代人类的“无产阶级化”与媒介/庸众专权(mediocracy)互为表里,彼此强化。感性的机械化转向进一步导致了生命的数字化转向,而将始于三百万年前的“人类进化”过程推至极限。古人类学家A. 勒鲁瓦-古汉(Andre Leroi-Gourhan)将“人化”过程描述为“生命的外置化运动”,即生命以一种同生命异质的方式来发明生命,补益生命。[5]52-53这个过程是技术学、器官学、药物学的进化过程,其成果的累积和速度的加快构成了地球上生命的根本难题。人化过程的每一刻都在发明生命和摧毁生命,技术学的每一个进步都在补偿人性的匮乏和剥夺人性的潜能,器官学一方面将生命延伸到身体之外,另一方面又废黜了某些精致的身体官能,药物学则揭示一切药物都是补药又是毒药。
*2006年9月26日,Facebook全面上市上线,开创了一个时代。这不仅是数字时代(溯源至1958年集成电路,1971年第一台中央处理器CPU),不仅是网络时代(1993年4月万维网全球开放),而且是“社交”数字网络时代,迄今为止其后果被证明是充满悖论的:压倒一切而且在本质上乃是反社交的(尽管且因为其流行性的无情飙升)和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反网络的,因为这种网络基本上就是一种系统的努力,将用户维持在一种以运算控制和逐渐以影像为基础的“接口端”,进而消减同基于链接的因特网的互动。
没有那么多的精神力,就不可能造成那么多的惨祸:要在那么短的期间杀死那么多的人,浪掷那么多的资材,毁灭那么多的城市,无疑必须有很多的知识。可是,精神上的资质也不可或缺。精神和义务,你们难道会令人怀疑吗?[6]
1935年至1936年间,胡塞尔以哲学的语言称之为“欧洲科学的危机”。胡塞尔认为,“普遍的哲学理想及其内在解体的过程”,意味着“一切近代科学的危机”,一种最初潜伏的“欧洲人性本身的危机”,“整个文化生活的整个意义的危机”,“整个实存的危机”。[7]在斯蒂格勒的论域之中,这种精神危机、人性危机、意义世界的危机,就是技术进化的危机。“在当今技术时代,技术的力量具有毁灭整个人类的危险”,而人随着技术干预的加深、人类纪的登峰造极而成为“宇宙秩序及其自我毁灭的力量”。[5]103这种以“自动社会的控制艺术”为极端表达方式的危机,体现为“消费者的无产阶级化、去象征化、去认同化和基于驱力的苦难中囚禁,将所有的独特性都压制到了可计算之中,而这种可计算性将当代世界变成了一个沙漠”。精神的危机便升级为“精神价值的暴跌”。20世纪90年代至今,一波接一波的事件表明,危机还在延伸和延续,其结果势必是人类纪的自我超越及其向负人类纪的转型。
1993年前后,网络技术向全球开放,网络通讯更为快捷,网络阅读与网络书写出现,数字技术已经将超工业社会、将“无产阶级化”引入一个新阶段,“系统愚拙”的时代到来,犬儒主义网上线下翻腾。数码自动装置成功地绕过了亚里士多德的“智性灵魂”,在消费者和投机者之间建立了一套又一套“愚拙系统”[8]。与这套系统的作用匹配的,乃是一种普遍化的麻木状态,一种剧毒的冷漠状态。[9]数字技术也导致一种震惊。面对Gogle、Apple、Facebook、Amazon“天启四骑士”,后启蒙时代的信仰与知识显然荡然无存,而且似乎百无一用。网络忧郁症(net blues),成为技术进化史诗的意境。
2008年的金融危机表征着全球化的资不抵债:踪迹工业霸权,战略营销风行,投机式金融蔚然成为气候,民族-国家衰落。“心灵的无产阶级化,更确切地说,理论化的心智官能,也就是科学、道德、审美和政治慎思的无产阶级化,与20世纪的感知和情感的无产阶级化,与19世纪的工人姿势的无产阶级化结合在一起,既成了这一持续‘危机’的导火线,也成了它的结果。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什么决断也没有作出,我们也没有到达任何转折点……而这一危机的根源处存在的毒性,反而更加强了。”[1]109-110
从1993年至今的20多年里,种种征兆和里程碑事件表明,人类纪不仅不可持续,而且是全球性高速和大规模的毁灭过程。[注] 《负人类纪》的英译者在其长篇《导论》里描述了五种里程碑事件(或者征兆)、两大挑战,论说负人类纪对哲学的挑战:
“人类进化”一剑双刃。我们无法回避这些难题,甚至一定会直落绝境,但人类纪的技术发明不断地复制了这些难题和绝境,同时也表明我们对这些难题和绝境负有不可逃避的责任。当生命和感性被粗暴地交付给机械、数字、虚拟甚至幻象,那些“非-活性的技艺装置”对我们的摆布就毫无商量。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口中那些活力弥满的灵魂就丧失了“翅膀”而堕落尘埃,甚至永远不会再度振翅,重新飞上九天。亚里士多德的那个会爱的“智性灵魂”就丧失了智性而迷失在技艺的迷宫。人类进入了一种“系统的愚拙”,即将到来的白痴化,就是瓦雷里在1919年就忧患的“精神危机”:
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其思想传记《忧郁的热带》中以悲剧笔调描述人类纪的宇宙学历史与前景:“在这个世界开始的时候,人类并不存在,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人类也不会存在……人类的角色并没有使人具有独立于整个衰败过程之外的特殊地位,人类的一切作为,即使都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也并没有能扭转整个宇宙性的衰亡程序,相反的,人类自己似乎成为整个世界事物秩序瓦解过程最强有力的催化剂。”年高德昭的人类学家甚至表示很不喜欢他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他要逃离人类纪,到前人类纪的南美土著民族那里去享受素朴的宇宙秩序,挥洒智性灵魂的诗情画意。他特别注意到现代传播给人类带来的困境:“每一句对话,每一句印出来的文字,都使人与人得以沟通,沟通的结果就是创造出平等的层次。”沟通导致的信息平均化导致了组织的瓦解,秩序的衰落,无序的增长。如果说,人类纪是“熵纪”,是熵大规模增长而将宇宙驱向无序的世纪,那么列维-斯特劳斯的话可谓昏世警钟:“人类学(anthropology)实际上可以改成‘熵类学’(entropology),改成为研究最高层次的解体过程的学问。”[10]安德森的预言同出一辙:大数据如同大洪水,将人类再次带向洪荒,在这么一个洪荒的宇宙,“无产阶级化”臻于峰极,超个体化导致了精神的衰微,知识已经死亡,理论寿终正寝。星球肃杀,万物枯萎,灵魂陨落,熵趋极值——如果这种描述属实,那真的没有未来,没有出路,没有弥赛亚降临的空隙,没有自救的力量,也没有他救的代理。然而,果真如此么?
*2007年岁暮,美国的“次贷危机”如火烧身,将金融活动的腐败性、“投资”活动的极端投机性以及对于自动化高速交易的非理性依赖昭告天下,这场危机导致了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掀动了全球金融危机,其起因大致可以判定,但倡议的解决方案不仅支离破碎,而且难以实施,进一步引起了全球经济萧条(惟有Alphabet、Apple、Facebook、Amazon成为卓然不败的例外),与之相伴的乃是更多破灭和更深危机的持续风险(像希腊那样)。
物极必反,下降之路亦是上升之路。不可持续的“人类纪”,将“无产阶级化”推至巅峰,以创造一切来毁灭一切。而这种当前走向势必会逆转。斯蒂格勒建议,我们应该以“负人类纪”来质疑和挑战“人类纪”。他认为,当安德森提出大数据导致知识的灭绝时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忽略了人类知识系统的开放性。而一个开放系统可能会以生产负熵的方式抵御毁灭一切秩序的熵流。他还认为,列维-斯特劳斯宿命般地认同了“人类纪”的虚无主义,而低估了人类理性引人向善的潜力,以及人类创造“负熵”和重构秩序的能力。这里涉及到“熵”和“负熵”这两个物理学概念,及其所蕴涵的宇宙论和形而上学意义。
*我们已经看到,以Alphabet为前锋的人工智能技术和机器人技术的飞速发展(其典型是2012年Amazon巨资收购Kiva Systems,随后便终止了所有新客户合同),从而导致许多人预言一波正在来临的自动化浪潮,它不仅将导致范围广大地摧毁工作,摧毁作用将不限于制造业,而且还会延伸到许多其他的就业领域,而这助推了“分裂性的”去中介化(优步化),潜在地危及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妥协纲领(它构成了再分配过程的本质,决定了消费主义恒增长宏观微观经济模式,而这个模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当今一直居于统治地位)。
*人们渐渐意识到,19世纪工业化和20世纪超-工业化已经产生了大量毁灭性的后果,在生物界层面上现在都能感觉到这些后果,它们包括但不限于气候变化的危机,人们因此断言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地理学纪元,即人类纪(献身于研究2016年8月29日问题的工作团队推荐我们采用这个命名),在这个纪元里面,人类种系发生的后果将会成为地理学变化的主要推动者,换言之,这个纪元契合于行星及其系统的人类化,但由于其不可持续性,又可能导致最终的解-人类化。
或者,它让我们离开工业资本主义在过去二百年来施加在我们身上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它通过一种网络化的智性政治【noetic politics】让自动设备为“去自动化的”个人和集体能力服务,从而产生负熵的能力的大规模发展),也就是说,让这些自动设备和系统去生产出负熵式的分枝(negentropic bifurcation)。[1]177-178
*2007年6月29日,苹果公司推出其第一代iPhone,开创了电容性多重触摸的“智能电话”时代,输入/输出屏幕无处不在,方便携带,而且永远连线,它有双向界面,让“用户”虚拟地体验到所有外界事件和(以Facebook为媒介)体验到他们自己的生活,同时将他们通过与这些可触屏幕的互动产生的数据传回电子怪物的运算程序。
三、逃离人类纪,驶向负人类纪
*美国灾难的外交政策决断,至少可以溯至1990年老布什发动的“沙漠盾牌和沙漠风暴行动”,“9·11”之后,2003年小布什又发动“伊拉克自由行动”,这些外交决策可能持续展现其影响广泛的后果,经过以Facebook为媒介的“阿拉伯之春”(开始于2010年末)的骚乱与冲突,引发了叙利亚公民叛乱的骚乱与冲突(2011年),这场冲突进一步升级为一场极端残酷的内战,其灾难性品格深刻地激发伊朗和阿联酋创立了所谓的“伊斯兰国”(2013年采纳这个名字),反过来又引发了一长串用枪炮、炸弹和汽车作为致命武器的袭击事件,其中特别著名的包括2015年1月7日《查理周刊》枪击案、2015年11月13日巴黎策应袭击案、2016年7月14日尼斯袭击案,以及所有一切警察、军事和“安保”回应这一波恐怖主义而引发的骚乱和冲突。
熵(entropy)是不能再被转化作功能量的总和测定单位。19世纪20年代一名研究蒸汽机作功原理的年轻法国军官加诺(Sadi Carno)发现,蒸汽机之所以能作功,是因为其系统内部冷热不均衡,系统各部分之间能量集中程度存在着差异。当能量从较高集中程度的区域转化到较低集中程度的区域,能量就转化为功。每一次能量从高集中区域转化到低集中区域,就意味着下一次再作功的能量减少,如河水越过堤坝而流入湖泊,落差减小,作功能量减低。而不能再度作功能量总和的增加,就是熵增。熵增意味着无效能量的增加,指向了系统秩序的瓦解。1868年,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Rudolf Clausius)生造出“熵”这个物理单位,并概括出热力学第二定律:宇宙之熵,即无效能量的总和,总是趋向于最大值。也就是说,随着时间之箭矢射向未来,宇宙之熵趋向于最大值,无效能量总和趋向于最大值,整个宇宙在某一时刻会达到能量分布终极平衡,整个宇宙达到热寂状态,而一切有序都转化为无序状态。[11]31热力学第二定律引起了科学和人文学界的不安、困惑以至于骚乱。如何解释热力学第二定律与热力学第一定律以及与进化论的矛盾?热力学第一定律揭示,能量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宇宙能量守恒。可是,热力学第二定律说,无效能量趋向于最大,宇宙总熵递增,最终可作功的能量等于零。每一次呼吸,每点燃一根烟,河流每一次越过堤坝,都在减少宇宙间的有效能量。进化论断定,生物进化就是进步,就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发展,宇宙演化会神奇地在地球上创造更大的价值和更优美的秩序。可是,热力学第二定律似乎捣毁了进化论的乐观:在进化之链上,越是高级的生物,就会把越多的能量从有效状态转化为无效状态;在进化过程中,愈是新的种类也就愈是复杂,它转化有效能量和生产无效能量的能力也愈是强大。然而,更为让人困惑甚至悲催的是,进化阶梯上越是高级的生物,流通能量的能力越大,给宇宙带来的紊乱和灾异也越是巨大。[11]51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人类就是这么一种高级的生物,它已经“成为整个世界事物秩序瓦解过程最强有力的催化剂”。
或者,它【这一过程】导致超-无产阶级化(hyper-proletarianzation)和普遍化的自动流向控制,造成结构上的“资不抵债”(structural insolvency),以及熵的剧增(vertiginous increase in entropy);
收集、整理瓦斯吹硫、热氮吹硫停工过程耗能工质消耗,如表3所列。热氮吹硫采用氮气、工厂风加热后对克劳斯系统进行吹硫、钝化作业,加氢单元、脱硫单元、酸性水汽提单元正常运行,增加氮气消耗131×104 m3、电耗8.72×104 k W·h、低压蒸汽2183 t,燃料气节约12.56×104 m3,除去低压氮气综合能耗增加2563750 MJ;单次热氮吹硫能耗成本340万元,较常规吹硫增加149万元。
第3步:在软件Matlab 2012b中通过编程求得该预测方法的相对误差,并且与BP神经网络直接预测法的相对误差进行对比分析。
斯蒂格勒回到了技术问题。技术是人类自我创造的力量,也是自我毁灭的力量。技术仿佛是神的恶作剧:让人类在持续的过失之中艰难前行,在享受巨大技术带来的巨大便利之时也时刻遭遇可能灭顶的风险。当人类纪熵趋最大而臻于至极,技术有没有可能为生命、为人类的生存创造生产“负熵”?斯蒂格勒说,热力学第二定律描绘的宇宙热寂前景,人类学的虚无主义倾向,以及生存论哲学的极度悲剧意识,是因为他们没能看到,生命的开放性及其负熵、反熵性质,负熵从熵之中产生出来又迂回返归于熵,于是人与宇宙的对话乃是一场“无尽的对话”。而且,他们还没有理解到,技术生命是扩夸张负熵形式(an amplified and hyperbolic form of negentropy),简言之,技术不只是有机的,而且还是器官的;技术学不仅是机体学(organics),而且是器官学(organology)。[15]57于是,技术就像活的生物,产生出熵值也产出负熵,负熵通过迂曲之路再轮回到熵。在轮回之中,技术加速差异和去差异化(即德里达所说的“延异”),激发欲望又投射欲望,而成为一种无限化的力量。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样例预示的负人类纪里,技术不只是改造了自然,而且创造了自然,不仅延长躯体,而且创造了躯体,不仅增益于生命,而且创造了新的生命。以“代具”(prosthesis)延伸躯体,将器官植入他物,技术人化了自然,自然也向技术生成,其造物是“活的”,丰盈丰沛,繁茂兴盛,具有植物性和动物性。斯蒂格勒就此断言,不同于纯粹的有机存在,人类乃是器官的存在,在两个层面上是熵和负熵的轮回:首先,作为生物,作为有机存在,人类通过剩余而产生有别于进化源头的“细微差异”,这就是薛定谔所说的“负熵即生命之本”;其次,作为技术化过程的操纵者,作为人工技术的存在物,人类既产生种的差异又产生属的差异。于是,人类进化,除了西蒙栋所说的“心理”(psychic)和“集体”(collective)的进化之外,还有“技术”(technical 的进化。与人类精神发展和集体进化相比,人类技术进化的情形远为复杂,它不只是简单的熵增过程,而且是生产负熵、增益生命、延缓甚至阻止宇宙秩序瓦解的过程。
在这一点上,哲学人类学能够支持斯蒂格勒所洞察的技术“延异术”或者熵与负熵轮回的辩证法。技术之发明,源自人类本质的匮乏,其功用乃是襄助生命吸纳负熵,自我更新。人类进化不服从“适者生存”大法,但工具和人类造物服从优选法则。布鲁门伯格指出,技术的功能一如修辞、神话、社会制序,它是人类种系发生学的产物,为人类活动拓展了地平线,延伸了活动空间。技术导致环境变迁,环境变迁产生焦虑,技术反过来成为征服环境和克服焦虑的强大力量。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合于人类,即不适合于技术的创造者,却适合于作为人类创造物的技术。“进化机制产生了有机系统,有机系统设置一种与进化机制相对立的幻影躯体而避开进化机制的压力,由此完成人化。这幻影躯体,乃是人类的文化领域,制序领域,以及神话领域。自然选择的条件再也不起作用,但对于作为物理系统的人类仍然有效,因为他学会了让他的人工造物和人造工具而非他自己服从适应过程……所以,适者生存法则可应用于技术,而非技术的创造者。”[16]人类不服从自然选择,人类的创造物却必须服从自然选择。技术经过人类发明、改造、优选、更新,而不断地趋向于精致。为人使用而得心应手的工具,乃是人类与自然对话之中技术选择的结果,这一过程可谓“器竞天择,工者生存”(Darwinism of Technique)。
于是,斯蒂格勒有理由相信,技术加快了熵增,同时也加快了负熵的生产。技术并没有加速终结的到来,反而在延异世界的末日。比如说,仅就速度而论,数码已经达到一秒钟20万千米,或者光速的三分之二的速度,比神经脉冲大约快了400万倍。在人类纪一场不可持续的情形里,“惟有果断假定器官学的前提,也就是增强负熵,我们才能转变当前发生的技术矢量速度,为自己赢得时间,展开差异化,延异,就此对工业经济的重估将我们介入到这种负熵之中,帮我们从人类纪里摆脱出来”[15]58-59。在这个人类纪向负人类纪转向的特殊时刻,经济学家阿玛提亚·森(Amartya Sen)的“能力”理论和哲学家怀特海的“思辨宇宙学”将指引一条通道,逃离人类纪,驶向负人类纪。
阿玛提亚·森将生命的负熵与自由相关联,进而将自由与能力(capacities)相关联。“个体自由是一种社会介入”,通过介入自由既获得了个体性又获得了集体意义。[17]自由既是发展的手段,又是发展的目的。[17]自由是认识到的必然,而知识乃是能动的表达,故而“能力”便是一种行动能力。以知识丰富能力,以能力驱动行动,以行为创造个体和集体的自由,生命的耗散结构以远离平衡态为取向,而避免了人类纪强制跳跃所导致的熵流虚无主义。出离虚无深渊的道路,便是走出无序而重构秩序的道路。这条道路是尼采、海德格尔的哲学所应许的由“存在”走向“生成”之道。“生成”允诺“未来”,这个未来出自人类纪的负熵。逆反熵流,便是驶向负人类纪的原始动力,一种创造性的力比多经济驱动力。斯蒂格勒以自由与能力的关联为基础,构建一种“普遍的器官学”和“精神药物学”。器官学与药物学,都关注包括人工智能、数码技术之类飞跃发展的人工制品,这些既是“人化”的条件,又是对“人化”的威胁。质言之,器官学和药物学既关注威胁着宇宙秩序的熵,也关注拯救宇宙秩序的负熵。在熵与负熵之间,生命有能力进行选择。生命选择的进向,乃是个体和集体的自由。
激素在临床应用中往往需要长期使用才能达到效果,这样就容易给患者带来一些不良反应。如果把激素与维生素类药合理搭配使用,就会减轻和防止激素的副作用。
本刊审稿费为100元每篇。缴费方式:网上银行汇款、手机银行、支付宝或银行柜台转账至本刊账户,本刊不接收邮局现金汇款;请勿汇至个人账户。
一切“非人状态”(the inhuman)都是对生命负熵、个体—集体自由、人类认知—思维能力以及行动能力的否定。如果从怀特海的“思辨宇宙学”角度看,阿玛提亚·森的自由与能力就不仅涉及到人类自由意志,而且可以被视为生命的负熵潜能。不错,宇宙在整体上趋向于熵最大,系统普遍地趋向于自我封闭,人类总会败落为非人,但是在局部或地方宇宙有反熵流向,系统有开放的可能,人类有超越非人而进化为类神(god-like)存在的自由,即人类自我伸张之后自我拯救的自由。负熵刻画了负人类纪的关怀,这种关怀是一种经济的关怀,一种政治的关怀,一种美学的关怀。经济的关怀指向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政治的关怀指向了文化的丰富、差异与多样性。美学的关怀则指向了生成、自由与未来。三种关怀都牵连着一种药物学知识。在这种精神性的知识建构中,负熵纪引领着负人类纪。而重新估价理性及其外化技术的功能,乃是负人类纪对哲学的挑战之一。负熵与负人类纪蕴含着理性、技术以及一切精神产品的二元性。瓦雷里、尼采、弗洛伊德、胡塞尔、海德格尔、德里达都警示我们关注这种精神的二元性——熵与负熵,毁灭与生成,毒药与补药。对于悲剧时代的古希腊人,这种精神二元性构成了悲剧的绝对性,体现了悲剧与文化之间的血脉关联。[18]更重要的是,精神的二元性,及其绝对悲剧,决定了普罗米修斯、爱比米修斯、赫尔墨斯的命运。[15]63然而,古希腊悲剧时代的诗人和哲人,都没有否定思维及其器官学处境中“负人类”的丰富、差异和多样性,甚至还允诺了一种灵知式救赎的可能。深刻的虚无感,普遍的绝望感,命定的悲剧感,于人类纪登峰造极的熵化趋势无补。丧失了智性灵魂的生命,只能在毁灭一切的熵流面前听天由命。然而,浪漫主义缔造的“新神话”——“理性的神话”,巧妙地将理性与神话、启示真理与自然真理、正统信仰与异教灵知融为一体。“它是自然的不同维度的统一体……因为它构成了‘目的王国’里所有目的不确定的地平线。”在这个地平线之内,理性是一个器官,一个交相引生(concrescence)的器官,一个组织着由“事实”向法则过渡、从潜能到现实转化的器官,一个酝酿生命反熵进化的器官。怀特海的思辨宇宙学给我们的启示在于,“理性强调新意的器官”,在物理自然败落之后,理性让生命复苏在进化的步伐里面,成为历史中自律的创造性因素。[15]63避开人类纪而驶向负人类纪,就是解放理性的自律,激发生命的反熵潜能,从而将人类发明的技术人化和精神化。
四、负人类纪的艺术——一种神秘的表演
启蒙之后,理性专权,神话被收纳于理性之下,“世界不再迷人”(disenchantment),万物祛魅。人类纪向负人类纪逆转,理性功能再度转换,感性经历机械论转向之后,神话再度归来(还有“宗教回归”),“世界魅力重现”(re-enchantment),万物再度附魅。这个附魅过程在相当程度上借助于技术媒介。技术既是媒介,又是信息,因为媒介即信息。因为“技术”可被理解为“一切即将来临的可能性和未来可能性之前景”[5]1。从技术角度看,人类历史无非是技术体系谱系及其过渡所导致的“延异”而已。技术贯穿于人类的种系发生、种族历史,创造了第三物质、第三环境、第三记忆、第三滞存。物质、环境、记忆、滞存的信息化,一种器官学和药物学应运而生。器官学与药物学回应人类纪向负人类纪大逆转所提出的挑战,专题处理数字时代“象征的贫困”。
斯蒂格勒将器官学与市场营销美学联系起来考虑,重点探讨消费文化和媒介境遇导致的符号贫困(苦难)以及意义的纯粹化和枯竭的趋势。美学趣味与艺术风格同西蒙栋所说的超个体化紧密相关。作为反思判断的审美判断,不仅非概念而普遍可传播,而且在技术上也是一种策略性构成物。一种诡异的信念颠倒发生在“达达主义”的离经叛道之中。艺术经过一番人工诡计的改造,一袭灵知主义的神秘也化入了艺术的存在之维。艺术作品不再是一种澄明的存在,其起源变得神秘而且可疑,一如贝伊思(Joseph Beuys)所说的“社会雕塑”。艺术流通也成为全球投机营销发展的一部分,在“网上口碑或口耳相传”的营销技巧与精神主权策略之间存在着某种模态对应关系。艺术流通像非法传销一样成为秘传,关于艺术的认知成为一种神秘化的灵知。“所有这一切都来自可称为社会雕塑的药物学,来自永远受到神秘化威胁的神秘学。一旦神秘化,药物学就成了这种神秘化的材料。”受到神秘化威胁的神秘学,起源于杜尚。日常之物甚至污秽之物进入艺术空间,需要的不是技法,而是精神上的神秘信念。一件作品成为艺术作品的前提,是我们必须相信它,无条件地相信它就是艺术。更具体地说,只要你打心眼相信杜尚的便池是艺术,它就是《泉》这样的杰作。像《泉》这样的作品,因为它造成了感性上的震惊,导致了感性的转变,从而将我们拖入一种神秘,让我们体验某种颇不寻常之物。艺术品的不寻常,就在于它具有一种神秘的表演性(the mysteriously performative),也就是说它蕴含着一种唤醒神秘灵知、唤来创新事件的力量。然而,这种力量并不在于超越性的彼岸,而在于内在性本身的神秘。它在世界之内成为世俗之物,在世俗之内成为寻常之物。[1]44在柏拉图主义的意义上,艺术品是第三实在,是衰弱理念形象的微弱踪迹。在德里达的解构论域中,艺术品是踪迹,是书写,是精神之药、灵知之药,既是补药又是毒药。在一个普遍失去爱的时代,也就是说,在一个人类纪登峰造极而向负人类纪逆转的时代,人类对艺术作品不可能有爱,而只有围观丑闻的欲望,在丑闻的冲击下震惊,进而将欲望投射给被消费的对象。于是,“人类纪”逆转时代,意义因纯粹化更趋稀薄,象征极度贫困,只剩下那些神秘的能指,在熵流涨落的时间里没有目的地漂浮。于是,生理美学、器官美学和社会美学,都必须处理普遍的失调。斯蒂格勒写道:
人类美学的历史包括了一系列连续的失调,这些失调存在于三个构成人类美学力量的大型组织之中:生理组织的美学,人造器官的美学(比如技术、对象、工具、仪器、艺术品),以及由前二者相互协调而成的社会组织。我们必须想象一种普遍的器官学,这门学科专门研究人类美学三大方面的历史,并研究三者相互关联所引发的冲突、创造和潜力。……只有这种谱系式的研究方法才能让我们理解美学的演变,当代的符号贫困(象征苦难)就是美学演变的产物,从中我们应该希望并且肯定,技术和技术科学所带来的无限可能中蕴含着一种新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也同样隐藏在(饱受符号贫困之苦的)情感之中。[19]
我国至今没有一部法律对政府雇员制进行规范,这是其实施的一个重要问题。《公务员法》并不出现政府雇员字眼,全国对其理解不一。这种新的用人制度正在探索,但缺乏法律法规的明文支持,保障不足,实际运行中也存在偏差,其运行并不顺畅。除了个别地方有将政府雇员转为正式人员外,大部分地方的新任领导存有私心,通过任意解除合同达到换人的私人目的。通过法律制度的明确规范势在必行。
普遍器官学与技术的熵/负熵辩证法、药学的补/毒精神二元性紧密相关。援引胡塞尔“时间意识与现象之流”学说,斯蒂格勒提出“第三持存”(tertiary retention)概念,以此来定义人造器官学和精神药物学。通过现象学还原,胡塞尔将持续过程中构成的物体定义为“时间性客体”。时间性客体之流程与对于它的意识之流程相契合。时间之流中刚刚流过的客体,即源初滞存。存留在记忆之中而已经流过的客体,构成第二持存。而保存记忆、留住时间之流中客体踪迹的助记术和广义的人造器官技术(代具技术),乃是第三持存。[20]柏拉图时代从埃及引入希腊的“书写技术”,19世纪的机械复制技术,以及20世纪的记忆工业、数字技术、泛媒体传播技术,都遵循着德里达所称的“增补逻辑”(logic of supplement),强化了精神药物学的二元性——增益记忆和伤害记忆,既是补药又是毒药,既是熵增又是负熵的潜能。书写技术有助于记忆,但它毕竟是记忆的衰退形式,本质上有害于理智的灵魂,甚至歪曲地再现了驻留在回忆之中的美的原型、善的原型和真的原型。“书写符号拥有一种使其背景解体的力量。”[21]背景解体意味着一切非领土化,所有的共同体都变成“非功用的共同体”,所有定向都把人引入迷失方向的时代。
所有第三持存,比如技术、对象、工具、仪器、艺术品、影像,等等,都是药物。一方面这些药物导致个性的消逝和意义的贫困,这就是熵增且趋向于熵最大化,即“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这些药物也可能产生差异关联和意义蔓延,这就是生命反抗熵流,将个体自由设定为宇宙演变的目的。通过技术增补和人工代具,生命吸纳负熵,在整体宇宙的败落之中实现局部的复苏,并奋力去修复被伤残的智性灵魂。惟有智性灵魂才有爱和灵知,以及对美的爱欲迷狂。所以柏拉图将智性灵魂称为“长翅膀”“会飞翔”的灵魂。惟有这样的灵魂才能让人类与药物共生,抑制毒性而放大补性,引领人类从自动化漫无边际的控制之中寻求自我拯救的可能。说到底,在生存论上看,技术毫无地位,只不过是人类的代具,生命的踪迹,没有深度也没有高度,既不超越也不内在。但因为相关于人类的灵魂,它见证了人类源初的记忆、种族记忆、个体记忆被人类纪里的机器取代的悲剧历史。技术一体两面,毒药自带解药,熵流之中涌动着负熵潜能,以技术来拯救技术,进而将智性的灵魂还给饱受象征贫困煎熬的人类,此乃负人类纪对美学的挑战。以负人类纪来拯救人类,这是一场美学的拯救。
【参考文献 】
[1] 斯蒂格勒.人类纪里的艺术[M].陆兴华,许煜,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
[2] ANDERSON C.The end of theory: the data deluge makes the scientific method obsolete[EB/OL].(2008-06-23)[2019-01-23].https:∥www.wired.com/2008/06/pb-theory/.
[3] STIEGLER B. Pharmacology of spirit: and that which makes life worth living[M]∥ELLIOTJ J, ATTRIDGE D. Theory after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294-310.
[4] 伊格尔顿.理论之后[M].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202.
[5] 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M].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6] 瓦雷里.精神危机[M]∥瓦雷里散文选.唐祖论,钱春绮,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223.
[7]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M].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4-25.
[8] STIEGLER B.States of shock: stupidity and knowledge in Twenty-first Century[M]. Cambridge: Policy Press,2015: 45-48.
[9] STIEGLER B. Automatic society, Vol. 1: the future of work[M]. Cambridge: Policy Press, 2016:81-82.
[10]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M].王志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543-544.
[11]里夫金,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M].吕明,袁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2]BLUM H F. Time’s arrow and evolution[M].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94.
[13]SCHRODINGER E.What is life? the physical aspect of living cell[M]∥What is life, with mind and matter and autobiographical sketch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4]普里戈金,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M].曾庆宏,沈小峰,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373.
[15]STIEGLER B.Neganthropocene[M]. Trans. ROSS D. London: Open Humanities, 2018.
[16]布鲁门伯格.神话研究:上册[M].胡继华,译.上海:世纪文景出版集团,2012:186.
[17]SEN A.Development as freedom[M].New York: Alfred A. Knop, 2000:Ⅻ.
[18]布鲁门伯格.神话研究:下册[M].上海:世纪文景出版集团,2014:353.
[19]斯蒂格勒.论符号的贫困、情感的控制和二者造成的耻辱[M]∥热风学术: 第8卷.许煜,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89.
[20]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M].赵和平,印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5-6.
[21]DERRIDA J. Signature, event, context[M]∥Margins of philosoph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2: 375.
A Note on Challenges of Neganthropocene to Traditional Aesthetics
HU Jihua
Abstract : Since the 1990s till up to the present, a series of eve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Western and Eastern alike, imposed on us a kind of impression that ″the spiritual crisis″, which is concerned by many celebrated thinkers such as Paul Valery, Edmund Husserl, Claude Levi-Strauss, etc., could not be released, but rather pushed into the extreme situation, as a result of which anthropocene’s self-transcendence and its transformation into neganthropocene have taken place. About this makeshift and the emergent state it led to, Bernard Stiegler,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thinkers of contemporary France, has proposed his significant observations and philosophical evaluations that he called ″neganthropocene″. Some important ideas of this reflections are concerned with the basic aporia in relation to advanced techno-science which is so complicating and disturbing for immediate thinkers nowadays. According to Stiegler, the most fundamental paradox consists in that every moment of humanization in the history is simultaneously inventing and destroying life, every further step of technology making up a deficiency in humanity while depriving of human potentiality, and organology extending life outside of human body as well as abolishing functions of some refined organs. In one word, techno-science is in nature the pharmacology, which reminds us of the double-edged nature of technique. All inventions are both remedy and poison at the same time. So, in an age of anthropocene’s reversion to its opposite, meaning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rarefied and symbolization is so determinately at the mercy of poverty that there is nothing but some mere signifiers left. Conclusively, physiological, organical, and sociological aesthetics have to deal with universal maladjustment. In order to overcome this crisis, we would attempt to revive ″noetic soul″, by which one could search for possibilities of self-redemption of human beings in the techne-dominating age.
Key words : Anthropocene; neganthropocene; double-edged nature of technique; aesthetic redemption
作者简介 :胡继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院教授,从事比较文学与当代西方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G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94X(2019)02- 0015- 10
[责任编辑 罗 欢 ]
标签:人类纪论文; 负人类纪论文; 技术二重性论文; 美学拯救论文;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