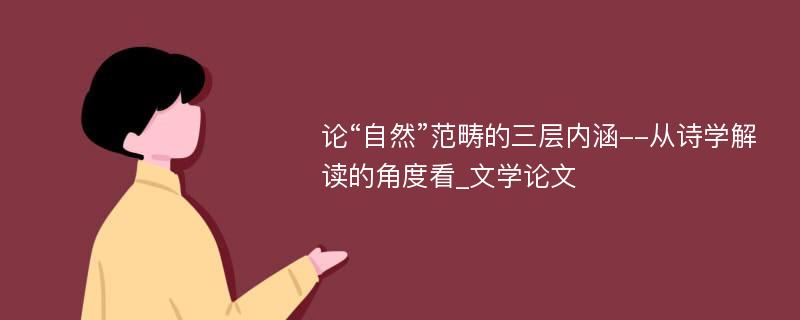
论“自然”范畴的三层内涵——对一种诗学阐释视角的尝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范畴论文,视角论文,内涵论文,自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小引
如何运用具有现代学术品格的合理方法与视角来阐释中国古代诗学范畴的意义与价值,这已是学术界屡屡提起的话题了。有些论者提出要依据中国古代诗学范畴与话语的独特性、复杂性来确立相应的阐释方法与视角,以便使阐释活动能够有效地切近对象本身,这是极有见地的主张。
由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独特性,中国古代诗学范畴、概念以及负载它们的话语形式常常表现出某种不规范、多义项、随机性等特征。这自然会增加阐释活动的难度。但也正是由于中国古代诗学范畴与概念在分类学上远没有西方古代诗学那种内涵与外延的确定性,这反而使它们获得了某种极为深刻、极为丰富的蕴含,对它们往往需要通过十分复杂的解读过程才能比较全面深入地予以把握。
中国古代诗学范畴的这一特点就使得它们所含有的意义与价值往往不能用严格意义上的诗学话语予以规定。换言之,一个诗学范畴常常同时又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或道德范畴。对这种情形绝不能用诸如“一词多义”、“同名异实”等提法来解释,因为在范畴的诗学内涵与哲学的或道德的内涵之间存在着极为紧密的联系而并非彼此无关的。诗学范畴这种内涵上的“溢出”现象也就使它们兼具了哲学范畴、道德范畴的意义与价值。尽管在特定语境中范畴的哲学与道德内涵并不直接呈现,但它们却始终存在并潜在地规定和制约着,甚至可以说是给定着诗学内涵。
这种诗学范畴与哲学和道德范畴交融互渗现象至少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古代,诗学观念并非完全来自于对文学创作与文本特性的归纳与总结,它们中有相当部分乃是来自于哲学和道德观念的“入侵”。这意味着中国古代诗学观念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经常受到某种外部的要求与规范并因此而承担某种额外的任务。对于这样一种很不“单纯”的诗学观念,倘若仅仅从文学创作与文本的角度予以阐释,那是难以对它有全面而准确的理解的。
在这里我们要尝试的阐释视角正是要打破诗学研究与哲学研究、伦理学研究的壁垒,打通诗学发展史与哲学史、思想史在学科分类上的疆界,将古人的诗学观念与他们的哲学观念、人生理想视为相互关联的整体,尽量恢复诗学范畴的多层内涵所构成的复杂结构,并进而梳理出不同内涵之间的逻辑关系。这样或许能够比较准确而全面地揭示出中国古代诗学范畴的独特性与深刻。
作为例证,我们选择了“自然”这一古代诗学的重要范畴。对于我们的阐释思路来说,“自然”是具有代表性的。作为一个诗学范畴,它代表着一种诗歌风格与境界,自六朝之后,这种风格与境界为各派诗学理论所接受,从而成为诗文创作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自然”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重要诗学范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它所包含的道德内涵——它标志着古代文人的一种人生理想与人格境界,一种企盼真诚无伪、任真自得的精神状态的强烈愿望。进而言之,古代文人之所以具有这样的人生追求又是以一种根深蒂固的哲学观念为基础的,这就是对人的个体生命与宇宙大生命之关系的深刻体悟与理解。这样,在“自然”这一范畴之中就统一了诗歌风格、人生理想与哲学观念三个相互关联、层层转换的内涵层次。只有将这三个层次各自的意义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梳理清楚,我们对“自然”范畴才算有了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
二 “自然”作为一种诗的风格与境界
在文学发展史上似乎有这样一条普遍规律——凡是在文学尚未自觉的早期阶段产生的文学作品大多呈现一种“自然”的风格——古希腊的史诗、抒情诗,我国先秦时期的诗歌都是这样。这并非因为早期诗人们自觉地恪守一种崇尚自然的诗学观念,而是因为他们还未能形成任何一种固定的创作模式,只是有感而发、直抒胸臆而已。作为一种明确的诗学范畴,“自然”的产生恰恰标志着文学的发展已经走向成熟与自觉,并且已经出现了某种过于注意形式技巧、创作规则的倾向了。因此,“自然”范畴是作为对诗文创作中过于形式化、程式化、技巧化的反拨而出现的一种诗学观念,它只能是文学发展到十分成熟的阶段的产物。
在中国诗学观念发展史上,“自然”是在六朝时期真正作为一个重要的诗学范畴被提出并受到普遍认可的。如果说西晋时陆机在《文赋》中还在倡导诗的“绮靡”、崇尚文采,依然致力于对文学审美特性的呼唤与建构,那么经过了此后二百年间文学向形式化、技巧化的飞跃性发展之后,到了刘勰、钟嵘、颜之推这里则开始对那种过于讲究用事、声律、辞藻、技巧的创作倾向予以贬抑和消解了。他们将“自然”范畴引入诗文评之中,目的即在于将诗文创作导向一个新的高度,使之突破形式与技巧的束缚而走向真正的成熟。
刘勰提倡“自然”主要是着眼于诗文的发生和创作过程。他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1]。这是讲诗文的发生是自然而然之事并非人们主观意愿所决定。他又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2]。这是说具体到个人的文学创作乃是内在之情与外在之景相触发、相契合而产生的必然结果,并非有意安排、任意为之之事。从两则引文中我们不难看出刘勰用“自然之道”“自然”来解释文学发生与文学创作过程的良苦用心。一方面他把文学的发生看做如同四时更替、万物生长一样是“自然之道”的产物,这就赋予文学以某种合法性与神圣性。这样,文学就不再是人们兴之所至偶一为之的消遣和娱乐,不是可有可无的雕虫小技,而是成了与“天文”、“地文”并立而三的“人文”,是能够“鼓天下”的“道之文”。作为对文学价值的高扬,刘勰的“自然之道”说较之曹丕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说实更有过之。另一方面,刘勰强调创作过程的“自然”,实质上是强调创作过程的“非自觉性”。在他看来,心中有真情实感,偶与外物相触发,则发而为诗,这是一个非自觉的“感物吟志”过程。对这种“非自觉性”的强调实含有针砭时弊的深意,是对齐梁间士族文人玩弄技巧、为文造情不良倾向的否定。
钟嵘亦如刘勰一样,也是针对同样的文学风尚提出自己的观点的。他提倡“自然英旨”,反对用事与雕琢。他提出的“直寻”之说是一种使作品达到“自然”境界的创作方法。“直寻”即是刘勰“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之意,旨在强调心中之情志与眼中之景物直接契合而为诗,反对用事用典、堆砌辞藻而伤诗之真美。
我们应该看到,刘勰、钟嵘等人标举“自然”并非完全否定文采与技巧,他们的目的是要人们将文采技巧与真情实感紧密统一起来,从而使作品整体上呈现一种意蕴或“滋味”。这无疑是对诗文创作更高一层的要求。因此,“自然”的实质是诗文毫无痕迹地呈现真情实感而不使辞藻、技巧成为目的。
唐宋以降,在诗歌创作上那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风格已成为具有普遍性的诗学观念而被推崇了。例如作者尚存争议的《二十四诗品》以“自然”为其中一品,姜白石以“自然高妙”为诗之极致[3],陈白沙论诗应以“自然”为本[4],直到近人王国维论曲之审美特性依然名之曰“自然”[5]。如此种种,不胜枚举。那么,“自然”这一诗学范畴究竟标志着一种怎样的文学价值呢?它对文学创作具有怎样的规范与要求呢?下面我们即以司空图等人的观点为例,试分析“自然”的意义与价值。《二十四诗品·自然》云:
“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真与不夺,强得易贫。幽人空山,过雨采蘋。薄言情悟,悠悠天钧”。
对于这段形象描写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解读。其一,我们可以将它视为对诗人创作过程的描述:一位诗人吟诗时从容不迫、举重若轻。他遣词造句就像信手拈来,丝毫没有苦吟诗人那敛首蹙额的痛苦。诗的意象从他笔下写出就如同花开花落、四时交替那样自然而然。总之,“自然”是指一种不经意的、轻松自如的创作状态。其二,我们又可以将这段描写看做人们在欣赏具有“自然”风格的诗作时所获得的一种审美感受:诗是那样浑然天成,毫无人工斧凿之痕,使人们仿佛置身于大自然之中观赏春花乍开、时序更替,既不劳揣想臆测,亦无须寻绎诗的微言大义,一切都呈现在人们眼前,就如同大自然本身那样真实无妄。这样,“自然”就意味着诗歌文本对于欣赏者而言的一种风格和效应。文中“俱道适往”与“悠悠天钧”二句得之于老庄之学。“道”与“天钧”都是指天地万物默默运作、无为而无不为的规律与特性。用之于此,似可理解为诗人创作不矫情造作而是如自然之道化生万物那样了无痕迹。同样也可以理解为人们在欣赏自然之诗时那种如同面对自然之道无声无息、化育万物而得到的主观体验。前者是遵“道”而为诗,后者是因诗而见“道”,一就作诗者而言,一就读诗者而言。
那么诗的“自然”风格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果然如司空图所描写的那样从容潇洒吗?我们不妨再看看姜白石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又说:
“文以文而工,不以文而妙,然舍文无妙,胜处要自悟”[6]。
白石所言有两层含义,其一,达到“自然高妙”的诗虽看上去平实无华,但其形成的原因却难于言说。其二“自然高妙”的诗境并非文采与技巧所能决定,但倘若离开了文采与技巧也就谈不到这一诗境了。这就是说,“自然”之诗并非真的是信手拈来的不经意之作,它同样离不开“文”——文采与技巧。对此,皎然说得就更清楚了:
“又云:‘不要苦思,苦思则丧自然之质’。此亦不然。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7]。
由此可知“自然”主要是一种诗的风格和境界,也就是作品在欣赏者心理上产生的一种效果。它是一种审美价值,它的实现要取决于诗作本身的特点与欣赏者的主观评价两个方面。至于说到它的形成,即创作过程则并非“俯拾皆是,不取诸邻”那样闲适从容,相反它同样需要文采与技巧,同样需要匠心独运。
从理论上讲,“自然”风格是文采与技巧的产物,同时又是对文采与技巧的征服与超越。言其为文采与技巧的产物,是说倘无高超的创作技巧与文辞的精心修饰,只是随意挥洒,决计写不出达于“自然”之境的佳作;言其为对文采与技巧的征服与超越,是说倘若不能使技巧在文本中深藏不露,使人对其毫无觉察,那同样也不能写出“自然”风格的好诗。只有那种借助文采而使人忘却文采,借助技巧而使人不见技巧的诗作才会给人以自然清新、浑然天成的审美体验。古人所谓“天籁自鸣”、“无法之法”、“不工而工”、“无我之境”等等都是指这种对文采与技巧的征服与超超。这表明,“自然”实为诗文创作的极致与化境,是一种最高意义的审美价值。
除了对文采与技巧的征服与超越之外,“自然”成为一种最高意义上的审美价值还有更深刻的文化心理原因,否则我们就无法回答为什么“自然”之诗能在欣赏者心理上造成愉悦的审美享受而“镂金错彩”式的作品则令人厌烦的问题。这样,我们的追问就不得不超出诗学范围而进入到文化心理层面,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对“自然”这一综合性范畴的第二层内涵进行剖析——在我看来,“自然”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最高的诗文价值,深层原因乃是因为它标示着中国文人的一种人生理想和人格高度。这就是说,作为“自然”的诗学价值内涵之依托的是它的道德价值内涵。古代文人首先是欲做(至少是向往)达于“自然”境界的人,而后才欣赏并创作“自然”境界的诗。在现实生活中,做“自然”境界的人往往只是一种精神追求而难以真正实现,于是创作和欣赏“自然”的诗便具有着某种填补心理匮乏的作用了。既不能使“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获得现实性,那么使心灵在瞬间驻足于诗的境界中也算是略有补偿了。
三 “自然”作为一种人生理想
如果说“自然”作为一种诗的风格是指诗歌作品对“人为”(辞藻、典故、修饰)的征服与超越,那么它作为一种人生理想则是指人对各种“规矩”的超越与征服。以往人们常常有一种观念,以为一提“自然”那必定只是老庄之徒的人生理想,与儒家无涉。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自然”作为一种人生理想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们所普遍向往的,儒家主体人格的最高境界同样也是“自然”状态。由于论及道家清静自然之人生理想的文字已不可胜计,我们在这里专门来看一看儒家士人以“自然”为鹄的的人生理想。
毫无疑问,儒家以天下为己任,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为人生至境。但这只是他们人生理想的一个方面,即当他们扮演某种社会角色时所标举的人格境界。作为生命个体他们同样向往一种超越于重重社会规范之外、任真自得、率性而为、无往而不乐的“自然”状态。在孔子那里,这种人生理想可以从他对曾点与颜回的赞许中表现出来。
对于曾皙“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志向,“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8]对此,宋儒朱熹注云:“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缺,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9]。这段注文除了带有一些理学色彩之外,基本上抓住了曾皙志向的特点。概括朱注之意其旨有二,一是肯定曾皙安于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亦即“安时处顺”、“随遇而安”、“无往不乐”之意。二是称赞曾皙之志是人之主体精神与天地自然同化为一的表现。此二者正是“自然”这一人格境界之主要特征。我们再看孔子对颜回的称赞:
“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10]
对于这段话人们常常认为孔子是在称赞颜回的“安贫乐道”,实际上孔子是肯定颜回不以世俗荣辱之见为念而保持一颗平常自在之心。二程尝云:“颜子之乐,非乐箪瓢、陋巷也,不以贫窭累其心而改其所乐也,故夫子称其贤”[11]。据此可知,颜回本怀有一种平和愉悦之心境,生活上的艰难清贫并不能使其乐有所增减。其本有之平和愉悦心境即是儒者试图通过修身养性而达到的“安时处顺”、“无往不乐”的人格境界,这一境界与老庄清静自然之心态无疑具有相通之处。
孔子对曾皙之志与颜子之乐的肯定以及在《论语》中有关“孔子燕居”的记载为后世儒者在人格修养上树立了一种典范,这便是为宋儒极力推崇的所谓“孔颜之乐”、“圣人气象”,其实质乃是对一种从容闲适、平和愉悦的自然心态的追求。程明道尝言“自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伊川亦言:“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12]。可见濂溪先生教人是以培养其“自然”的人格境界为主旨的。近人陈钟凡先生评濂溪之学云:“及周敦颐崛起湘中,著《太极图说》及《通书》四十篇,以自然为教,主静为宗,虽缘饰《周易》、《中庸》,而归本于道家之旨”[13]。其言濂溪之学“以自然为教,主静为宗”实为中的之论。然以其学为“归本于道家之旨”则不尽然。观濂溪之学虽确受道家影响而成,然其所论无疑是在远绍《论语》与《周易》中固有旨趣,决非全然受之于老庄。盖论者见宋明儒者之学中多有标举“自然”之论,又知其多出入老庄,故而常疑其学为道家而非醇儒,实际上,在最高人格理想上,儒、道原非扞格不入。“自然”作为一种超越名利荣辱之现实价值观的人格境界,正是古代文人安顿个体心灵的共同心理需要之流露。考之史籍,现实中愈是注重名利,那些具有自我意识与独立精神的文人士大夫便愈是向往这种“自然”的人格境界。例如明代中叶,程朱理学日益官方化、教条化,渐渐消蚀了其本有之超越精神、自由精神。而随着科举制度的日益腐朽,在士林中出现一大批满口仁义道德、满腹功名利禄的假道学,在这种情况下,大儒陈白沙高标“自然”、“自得”,提倡“孔颜之乐”,呼吁士人保持独立精神,从而开创一代儒学新风尚。其云:“天下未有不本于自然,而徒以其智而收显名于当年、精光射于来世者也”。又云:“人与天地同体,四时以行,百物以生,若滞在一处,安能为造化之主耶?古之善学者,常令此心在无物处,便运用得转耳。学者以自然为宗,不可不著意理会”[14]。白沙先生以重振儒学真髓为己任,而直言其学“以自然为宗”,可见在他心目中,“自然”并非为老庄之学所专有,亦为儒家最高人生旨趣。
到了阳明后学王艮那里,儒家固有的“自然”思想更被推向极致。其云:“凡涉人为,皆是作伪。原伪字从人从为”。又云:“良知之体,与鸢鱼同一活泼泼地。当思则思,思通则已。……要之自然天则,不着人力安排”[15]。如此,则惟有顺应本身具足之自然心性而行方合乎天理,因为在王心斋看来,“天理”即是自然而然之理,即使为学,亦要以“乐”为原则,不“乐”则有违人心之自然。此种以“自然”为宗之儒学实为对现实之于文人的严酷束缚的强烈抗争,是对于自由自觉之生命状态的热烈向往。
在许多人看来,老庄之学是反对现实规范主张放任自得的,而儒家则要收束心性、守诚居敬。一个是要破除规范,一个是要建立规范,二者判然有别。实质上这是一种误解。老庄那清静自然的人格境界也并非轻易可以获致。否则老子就无须要人们“致虚极、守静笃”了,庄子也不会大讲“心斋”、“坐忘”、“悬解”、“见独”之道了。魏晋六朝之人标榜老庄之学,其实他们那种放浪形骸、任意而为的生活方式并非老庄之真精神。儒家的确讲究修身养性的工夫,主张个体道德自律,但这并非他们的最高人格理想,而只是实现其人格理想的必要手段。在这一点上儒家与老庄之学也很相近——二者都是要通过修持而达于自由,通过自我约束而达到摆脱约束。二者的根本不同乃在于儒家在达到个体人格的最高境界后还要做事——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而老庄之徒在实现个体人格理想之后就无事可做——只顺应自然之化、随时俯仰即可以了。
“自然”作为一种人格境界主要包含两大特征,一是无拘无束的心灵自由状态(在老庄是物我两忘、逍遥自适,在儒家是平和愉悦、从容中道。),二是真诚无伪的处世态度。此两大特征均由人格境界而转换为诗学观念从而影响中国古代诗文创作。以往人们提及诗的自然境界大都以为出于道家旨趣,其实儒家对自然诗境的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并不逊于道家。即如大儒陈白沙为学以自然为宗,其论诗言文同样以自然为最高价值取向。其论诗云:“大抵诗贵平易,洞达自然,含蓄不露,不以用意装缀,藏形伏影,如世间一种商度隐语,使人不可模索为工”[16]。又论文云:“古文字好者,都不见安排之迹,一似信口说出,自然妙也。其间体制非一,然本于自然不安排者便觉好,如柳子厚比韩退之不及,只为太安排也”[17]。其为人为学以自然为准则,其论诗论文也以自然为境界,观其诗作亦确然平实自然、不假安排,全然一片天机生趣,虽不称工,然自有感人心脾处。
总之,中国古代诗学中的“自然”范畴并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文学风格。它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文学风格是因为它象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普遍向往的一种人格理想。他们愿意“自然”地活着,因而才欣赏“自然”的诗文风格。是人生旨趣成为诗学观念之底蕴,是人格价值转化为文学价值。
然而行文至此,我们的追问并没有完结,就是说,“自然”范畴的内涵尚未梳理完毕。人们还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何以将“自然”设定为一种人生理想、人格境界呢?换言之,“自然”成为一种诗文价值范畴更深刻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展开对“自然”这一综合性范畴第三层内涵的探寻了。
四 “自然”范畴的认识论内涵
“自然”范畴的上述两层内涵本质上都属于价值论范围——诗文风格是一种文学的或审美的价值;人生理想是一种道德的或人性的价值。根据一般的哲学史、思想史规律,凡一种价值论观念往往都有一种认识论观念作为依托。“自然”范畴的第三层内涵恰恰就是作为这一综合性范畴之基础的认识论观念。换言之,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之所以以“自然”为人生理想境界,在学理上是以一种认识论观念为逻辑前提的。这种认识论观念可以概括为天道自然论与生命同一论两个部分。
天道自然论是源于一种古老的自然崇拜意识。根据这种意识,凡是存在于世的万事万物均为造化所生,都具有神圣性。据此而形成的自然天道论则认为天地万物都是默默运作的自然之道所化生。这种自然之道无处不有、不可抗拒,离开它便没有天地万物,故而人应该自觉地顺应它。
道家的自然天道论即体现在其对“道”的理解与描述上。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故强字之曰‘道’”[18]。这个“道”既不属于天,亦不归于人,而是包括了天地人间万事万物的形上本原。但它又并非一个类似斯宾诺莎的“实体”、谢林的“绝对同一性”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那样的精神实体,而仅仅是天地万物自生自成的自在本然性而已。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9]。这就是说,天、地、人这世上三种基本存在都以“道”为基本法则,而“道”又以“自然”为法则。这实际上等于说天、地、人这三种实体存在的本然自在性即是“道”,即是宇宙之最高本原。只有这个意义上的“道”,才能够以自身之“无为”而成为人君“无为”之治术的样板。如此看来,“道”只是意味着万物各是其所是,而它则什么都不是,它的意义在于标示了人对天地万物的一种态度——尊重一切自然生成之物;又在于标示了人对社会人生的一种态度——蔑视一切人力所为之物。因此,道家的自然天道论可归结为一句话:万物的合理性在于其自然生成性或本然自在性。
儒家的自然天道思想在孔子那里已有表露。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20]这是对自然天道默默运作、化生万物之特点的认识。后来在《易传》中这种认识得到大大强化与发展,形成了一种生生不息、大化流行的宇宙自然发展观。而作为儒家自然天道思想最集中的体现的则是思孟学派提出的“诚”范畴。“诚”与“自然”具有深刻的内在一致性。
“诚”在孟子那里还主要是指人的一种心理状态和道德品性,即真实无妄之意。但孟子已然将它称之为“天之道”,暗示“诚”不仅仅是人的道德品质,而且还具有某种自然品性(即天地万物所共有之品性)[21]。到了《中庸》,孟子的这样“诚者,天之道”的思想得到弘扬,“诚”与老庄之“道”一样,被赋予了某种本体论意义,成了万事万物存在与运动的自然状态。其云:“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22]。在这里“诚”显然成了万物存在之依据。所谓“诚者自成也”云云,是说万物自然而然地生成即是“诚”。“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说万物都必须自始至终保持“诚”——自然状态,否则事物就失去了存在依据,不成其为事物了。所谓“合外内之道”云云是说人们只要存心养性,使个体人格达到“诚”的高度,那就与天地万物相统一、相契合,从而达到了“参天地之化育”的人生至境了。据此看来“诚”是统一天人的契合点,对天地万物而言,它是固有品性,是万物之所是;对人而言,“诚”是人原有而后失去或被遮蔽之品性,只有通过自我修持,即“求放心”的过程,才能使之重新澄明,而一旦人心恢复“诚”之澄明状态,则人与天地浑然一体,合内外之道,从而达到人生至境。“诚”作为天地万物之自然状态与人性之自然状态,它标示了古人对外在世界的理解,也标示了他们对人自身以及人与万物之关系的理解。这种理解恰恰构成了古人以“自然”为人格理想的认识论基础。
唐宋以后,以“诚”为标志的儒家自然天道观更得到进一步加强。道学的“北宋五子”之首周濂溪即以“诚”为其学说的核心范畴。他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23]。又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24]。这就是说,“诚”是天地万物发生发展之基本特性,亦即天地万物固有之自在本然性。张横渠也说:“天所以长久不已之道,乃所谓诚”[25]。胡五峰说:“天道至诚,故无息;人道主敬,所以求合乎天也”[26]。朱晦庵则云:“诚是自然底实,信是人做底实。故曰:诚者,天之道”[27]。明儒陈白沙也说:“夫天地之大,万物之富,何以为之也?一诚所为也。盖有此诚,斯有此物,则有此物,必有此诚”[28]。统观宋明儒者所论之“诚”实在与老庄所言之“自然”无异,都是人们对天地万物自生自长、生生不息等待征的一种认识论观照,“诚”作为“天之道”实质上即是自然之道,亦即天地万物之自在本然性,只不过儒者们一方面将这种自在本然性理解为天地万物生长化育之依据,另一方面又将它视为人的心性价值、人格价值之本原而已。
中国古代文人(包括道、儒两家及唐宋以后佛禅之学的信奉者们)崇尚以“自然”为旨趣的人生理想、人格境界,这种价值取向是以他们共同遵奉的天道自然观念为认识论基础的。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天道自然观念能够成为古人人生理想的认识论基础呢?则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一因果逻辑链条中,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这就是在古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可以视为中国古代文化深层心理基础的生命崇拜意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生命同一性观念。
老子欲以天地万物的自然法则来规范人世,其立论根据便是天地之道以“自然”“无为”的方式化生万物,万物各依其性而生长寂灭。在老子看来,人世亦应象自然界一样按“自然”形态而存在。他是以宇宙大生命的运作方式来为人世树立榜样,力求使人类放弃尔诈我虞、你争我夺以及种种毫无价值的繁文缛礼,同化于宇宙大生命之流。宇宙生命存在的本然自在性恰恰是令老庄之徒向往的人生至境,而人的生命与宇宙大生命的同一性则是以自然法则作为人世理想的客观依据。总之是人与万物都应在“道”的运作中充分敞开自己的自然生命、一切有害于或无益于生命存在的东西都应彻底抛弃。老子正是将使万物获得生命的那种力量称之为“道”的。其云:“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29]。老子感觉有一种至大至上的力量决定万物的生命存在,但他又从不现身,不自伐其功,他即将这种力量称之为“道”。因此从根本上说,老子的道论是建立在一种生命崇拜和宇宙生命同一性的观念基础之上的,重“道”即是重生命。又因为“自然”恰恰是“道”,也就是“生命”的存在样式,故而老子又提倡“清静自然”的人生境界。
在孔子的“天何言哉”之论中已然透露出对“天”默默运作、化生万物之伟大功能的赞美之情。到了《中庸》更进一步提出通过努力而使人的个体生命同化于天地化生万物之伟业中,使人的生命存在有益于宇宙大生命。其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30]。如前所述,“至诚”是指一种生命存在的自然状态;“性”在此处是指人和万物秉受于天的潜在的生命特性。即所谓“天命之谓性”[31]。“尽其性”则是指使人或万物秉受于天的生命特性(即发展的潜在可能性)得到最充分完成与展现。上述一段话的意思是说,圣人能使自身生命存在达于“至诚”(即自然)状态,故而能使自己秉受于天的诸种生命特性充分实现,因此也能帮助他人达到这一点。人人能使自己秉受于天的生命特性充分实现,则人的生命之流与宇宙大生命合而为一,这样人就必将自觉促进天地万物之生长化育,使万物各按其秉受于天的生命特性充分发展,于是人也就达到了赞助宇宙大生命存在发展的至上境界,从而与天地并立而三。
在儒家早期典籍中,《易传》是最重人的生命与宇宙大生命之同一性的。其云:“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32]。这是讲“道”化生万物,生生不息的功能。《易传》又云:“天地之大德曰生”[33]。将天地化生万物的功能肯定为一种最高价值,这实际上就完成了由认识论向价值论的过渡——人们对天地万物自然生命的认识论观照与对生命的创造者、促动者的崇拜与赞美统一起来了。到了后世儒者那里,这种对生命运作的认识论观照与价值论推崇相统一的思路得到进一步发展,从而使人生理想、人格追求与对宇宙生命的理解紧密联系起来。在这里,我们仅以程明道所言为例以说明之。明道云:“若夫至仁则天地为一身。而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夫人岂有视四肢百体而不爱哉?圣人仁之至也,独能体是心而已”[34]。此即“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之意,乃言人与万物具有生命同一性,故宜爱一切众生,这也就是仁之真义。其所谓“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斯所谓仁也”[35],正说明仁即是生。盖按明道之逻辑,天地之道以生物为本,此人所最宜效法之处。他说:“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元的意思。元者善之长,万物皆有春意,便是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却待他万物自成其性须得”[36]。这即是说,天的伟大处只在其赋予万物以生命,这就是天道之全部内涵。人只有顺此天道而行,厚生而不害生,使万物依其本有之生命特性运作,这才可称为“善”或“仁”。
综上所论,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家们而言,“自然”便是天地万物之本然状态,而生命则是“自然”之价值所在。古人将天地万物都看作宇宙大生命之运作,并认为人的生命亦唯有同化于宇宙生命之流方能充分实现其价值,因此,作为生命充分展现之标志的“自然”状态便成为他们向往不已的人生至境了。
五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之所以欲以天地万物运行的自然法则作为人世法则,欲以“自然”作为人生理想与人格境界,实出于一种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生命崇拜意识与宇宙生命同一性观念。生命之流是最为神圣之物,对它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无论儒道,都充满一种抑制不住的激情。但生命存在常常表现出静与动两种形态,大体说来,道家更看重生命之静的一面,而儒家则更重视生命之动的一面,这就形成了两派学说的明显差异。如果说到对生命的崇拜,则两派并无任何不同之处。
基于对宇宙生命之流的认识论观照与价值论认同,古代思想家开出了以自然的本真性、超越性为特征的人生理想与人格境界并采用各自的方式通过自我修持、自我提升来实现这种理想与境界。这种人生追求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许多一流人物为它倾注了毕生精力。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古人的这种人生追求渐渐浸润到诗学领域,从而形成以古朴真率为特征的“自然”风格,这就形成了“自然”范畴由哲学观念到人生理想,再到诗学范畴的跃升过程。
我们对“自然”范畴的层层追问至少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在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诗学范畴往往会将其根系深深植于深厚的文化观念之中,换言之,某些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会通过层层递转的过程最终呈现为一种诗文风格与境界。这种情形本身对我们诗学研究的方法论即有着重要启示作用,望有心者留意焉。
注释:
[1]《文心雕龙·原道》。
[2]《文心雕龙·明诗》。
[3]《白石道人诗说》,见《历代诗话》,中华书局版第682页。
[4]《批答张廷实诗笺》,见《陈献章集》卷一,中华书局版,第74页。
[5]《宋元戏曲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页。
[6]《白石道人诗说》,见《历代诗话》,中华书局版,第602页。
[7]《诗式》,见《历代诗话》,中华书局版,第31页。
[8]《论语·先进》。
[9]《四书集注·论语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90页。
[10]《论语·雍也》。
[11]朱熹《四书集注·论语集注》,第124页。
[12]朱熹编《伊洛渊源录·濂溪先生》,《丛书集成》本,第3页。
[13]《两宋思想述评》,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14]《陈献章集》,中华书局版,第71页、第192页。
[15]《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
[16]《陈献章集》第74页。
[17]《陈献章集》第163页。
[18]《老子》第二十五章。
[19]《老子》第二十五章。
[20]《论语·阳货》。
[21]参见《孟子·离娄上》。
[22]见朱熹《四书集注·中庸章句》。
[23]《通书·诚上》。
[24]《通书·诚上》。
[25]《张载集》,中华书局版,第20页。
[26]《胡宏集》,中华书局版,第28页。
[27]《朱子性理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第83页。
[28]《陈献章集》第57页。
[29]《老子》第三十四章。
[30]《四书集注·中庸章句》。
[31]《四书集注·中庸章句》。
[32]《周易·系辞上传》。
[33]《周易·系辞下传》。
[34]《河南程氏遗书第十一——第十三》,万有文库本。
[35]《河南程氏遗书第十一——第十三》,万有文库本。
[36]《河南程氏遗书第十一——第十三》,万有文库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