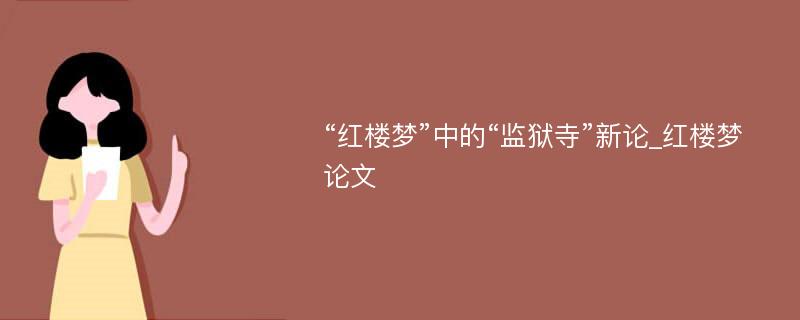
《红楼梦》脂评“狱神庙”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楼梦论文,新论论文,神庙论文,脂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吴世昌和胡辰先生关于“狱神庙”的观点和争论
《红楼梦》前80回的多种脂评本里,多次言及曹雪芹已佚的后40回中有与“狱神庙”相关的情节,共有4回的脂评中提及6次:
一是庚辰本第20回眉批:“茜雪至狱神庙,方呈正文。”二是同上:“余只见有一次誊清时,与‘狱神庙慰宝玉’第五、六稿。被借阅者迷失,叹叹!丁亥夏,畸笏叟。”三是庚辰本第26回眉批:“‘狱神庙’回有茜雪、红玉一大回文字,惜迷失无稿,叹叹!丁亥夏,畸笏叟。”四是甲戌本第27回侧批:“且系本心本意,‘狱神庙’回内(方见)。”五是庚辰本第27回眉批:“此系未见抄没、狱神庙诸事,故有是批。”六是靖本第42回眉批:“应了这话固好,批书人焉能不心伤。‘狱庙’相逢之日,始知‘遇难成详,逢凶化吉’实伏线千里。哀哉伤哉!此后文字不忍卒读。辛卯冬日。”
这些评语表明,在曹雪芹已佚的《红楼梦》后半部分,有关“狱神庙”的情节相当丰富,其中最重要的是在贾府被抄家之后,茜雪、红玉通过各种关系去狱神庙探望宝玉。一些学者据此对“狱神庙”的内容进行了种种推测,并取得了一些相当合理的描述,尤以吴世昌先生的相关著述最有影响,但由于这些推测皆是建立在对“狱神庙”的相关知识背景上,因此,厘清清季监狱制度和狱神信仰的内容便十分重要。因为限于材料来源的原因,吴世昌主要以清代吴语弹词小说《果报录》为依据,剖析清季的监狱制度,而这些材料过于零碎,甚至有该小说作者的误解成分,故引起诸多的纷争,对吴世昌的推测予以否定。其中尤以胡辰载于《红楼梦学刊》1989年第3期“关于‘狱神庙’的性质”一文具有代表性(当然胡辰否定吴说所依据的材料也多依戏曲小说)。
吴说的对狱神庙的性质在《〈红楼梦〉后半部的“狱神庙”》[1]一文中,有如下结论:
(1)清代狱神庙即在监中,在南方一般称为“萧王殿”,当然是因为庙中所供奉的塑像是萧何,俗称“萧王老爷”。殿中“狱神端坐中间”,两旁是“狰狞鬼判”。但也可能是说徐氏所见狱神庙中的囚犯悲惨情况,有如十殿阎罗施刑后的鬼囚一样。
(2)狱神庙里关的犯人大多是死囚,这可以从他的所带的刑具看出来:这些囚犯都是“披枷带锁”,“胡桃大链锁咽喉”,“两足伤痕行不动”。
(3)女犯的监狱在里面,但进去时也要经过萧王殿,然后从殿侧进去。
据上三点吴先生预测“狱神庙”的情节是:既然小红和茜雪是在狱神庙中会见宝玉(凤姐)的,可知在雪芹的后半部原稿中,不但在“荣府事败”(脂评语)之后有许多人被捕入狱,而且宝玉和凤姐竟被判了死刑(或流刑)。小红、茜雪去探监是在临刑之前借“祭狱神”的名义去贿赂狱吏,所以能和宝玉等在狱神庙相见。……又是谁助他们设法越狱呢?当然只有“侠义”、“豪杰”的醉金刚和他的“有胆量的有作为的”“相与结交”之人,例如狱神庙的狱吏、禁子之类。……在宝玉、凤姐都已进了狱神庙的时候,却是她们冒了很大危险入监慰问她们的旧日的主人;又通过市井豪侠和有胆量的狱吏之类,把他们从监中救出。这中间的关键人物是贾宝玉的“义子”贾芸[2]。
胡辰先生据关汉卿《绯衣梦》、明末小说《三刻拍案惊奇》(即陆人龙的《型世言》)中的第19回“血指害无辜,金冠雪枉法”及清代小说《三侠五义》77回相关情节认为,狱神庙的性质是:
(1)狱神庙不是监狱,也不是囚禁死刑的场所。
(2)狱神不单单是狱、吏狱卒与囚犯的祭奉的典狱之神,更重要的是司法官吏供奉的折狱之神。
最后得出有关狱神庙的结论是:“狱神庙是庙,不是狱,它不是关押囚犯的场所。它是安置同案件有关人员(包括证人、首告、涉嫌者等等)的一座庙宇,让“归案备质”的人有一个听候传呼的栖身之处。因此,住在狱神庙中的人与监狱中的案犯待遇很不相同。由于没有定罪,更不会“披枷带锁”,但可能要限制一点自由。可以设想,狱神庙就在监狱附近,与上审衙门相距不远。庙中供奉着狱神,两旁有若干厢房或耳房,以作为“归案备质”人员的住处。由此推测《红楼梦》后半部“狱神庙慰宝玉”的内容:“贾府被抄家,贾赦、贾政、贾珍、贾琏等人入狱,凤姐、宝玉等人暂时羁留在狱神庙。茜雪、红玉和刘姥姥先后到狱神庙慰问探望,并给凤姐和宝玉以重要援助,凤姐把巧姐托付刘姥姥。后来凤姐与宝玉获释,但家产已籍没,无家可归,这才‘树倒猢狲散,”所以,畸笏叟说“此后文字不忍卒读。”
吴说与胡说关于狱神庙性质的对立是显然的,而由此生发的对《红楼梦》后半部相关情节的推测亦大相径庭。事实上,他们对狱神庙的结论与事实皆有出入,加之对清代监狱制度和实际的囚徒禁狱生活的不熟悉,上述的推测和描述多为臆测的结果。为了得出符合事实的结论,有必要厘清古代尤其是明清二朝的监狱制度、狱神信仰和囚徒生活的真实状况。
二 清代监狱制度及其“狱神庙”的性质与功能
先看古代监狱性质。中国古代监狱与现代意义的监狱制度不同,封建社会的监狱主要囚禁未决犯,即当时监狱主要是监禁犯罪嫌疑人之地方,相当于今天各地方公安局所属的拘留所,而与今天的监狱(属司法部门管辖)的性质有异,今天的监狱为已判决的罪犯劳动改造服役的地方(古代判流罪之人,亦相应到流放地驿站、牢城营等处服苦役)。明清二代的监狱亦是如此,《清史稿·刑法志》云:“从前监羁罪犯,并无已决未决之分。其囚禁在狱,大都未决犯为多。既定罪,则笞杖折责释放,徒流军遣即日发配,久禁者斩绞监候而已”。可见,清代久囚监狱之人只有已判决斩监候和绞监候二种犯人而已,而其他皆是未判刑的嫌疑犯。如鲁迅先生的祖父就是因科场通弊案被判“斩监候”而长年囚禁于杭州府司狱司监中[3](十四杭州)。《醒世姻缘传》13、14回中的珍哥因迫害嫡妻计氏使其自杀亦被判“绞监候”而长年在县狱等候年复一年是否执行的通知[4](明清统治者慎刑,对“斩、绞监候”是否于秋天执行特别严谨,故判、斩绞监候的囚徒,往往不会执行死刑而是年复一年的囚于监中)。此外,根据封建社会“有罪推定”的原则,封建监狱往往会将一些重大案件的原告被告乃至相关证人也监禁于班房、牢中,直至案件的最后审定。
清代的监狱分布情况和内部建筑情形大致是清承明制,从地方到中央各级审判层级都设有监狱。从地方监狱看,最基层的县里有县监,其上厅有厅监,州有州监,府有府监。从中央来看,刑部有刑部监狱,另外尚有用于监禁皇室犯罪者的宗人府空房,用于监禁京师所在地旗人和八旗军卒犯罪的军统领衙门监狱等,据台湾学者丁道源统计,清初全国各类监狱“有二千余处之多”[5]。地方监狱一般都设有内监、外监及女监。《清史稿·刑法志》载:“各监有内监,以禁死囚;有外监,以禁徒流以下。妇人别置一室,曰女监。”而刑部监狱则分南北两监,主要拘禁京师、外省死囚及现审重犯。
监狱内部的建筑情况如何,明末清初的葡萄牙籍传教士曾德昭《大中国史》第28章有说明:“他们关押犯人的监狱,比我们宽大,全国的监狱都一个形式,很少差异,所有只要介绍一个,我们就可以得知全貌。它们大都和所属的曼达林(政府长官)的官府和衙门相连接,或者距离不远。监狱临街的一面没有栏杆,但在大门内有一条窄通道,引向第二道门,里面是一座院子,按监狱所能接受罪犯的多少而定,有大有小。然后通往第三道门,那里有看门和卫士的住所,一般是三间。再过去是另一道门,开向一座大四合院,四周是囚犯的房间,朝院子的一面没有墙,但竖有紧密的木柱,它们看来更像栏格,门不是木板做的,而是同样的木格,因此都是开放的;这是关押普通囚犯的牢房。在这一排牢房的尽头有秘密、封闭的牢房,用来关押重大罪犯,他们称之为‘重监’,即重罪牢房,也有如前所述的格栏,其中是关押那些罪大恶极者的封闭牢房,一直被锁起来。”从文中可悉,当时的牢狱有多重大门,牢门之前有狱卒的住房,其后才是一般的囚牢以及重囚牢。
至于与牢狱相关的狱神庙建筑地点和位置,则自宋以来皆建筑在牢狱之中,很少有例外情况。宋方勺《泊宅编》卷中云:“今州县狱皆立皋陶庙,以时祠之……皋陶大理善用刑,故后享之。”另一宋人袁文在《瓮牖闲评》卷2云:“今州县狱皆立皋陶庙,以时祀之。盖皋陶,理官也,州县狱所当祀者。”又如南宋文人洪迈《夷坚志·支乙》卷9“宜黄青蟆”条曰:“宜黄县狱有庙,相传奉事萧相国,不知所起如何也。”可见,在宋朝狱神庙皆建在狱中,所祀狱神既有皋陶,又有萧何。到了明朝,情况也是如此,据天一阁所藏明弘治年间所修《句容县志》卷之2云县衙建筑群内有:“监房十间。狱神祠一间。”狱神庙与监房建筑在一起,外面应有围墙环绕。又如曾德昭《大中国志》第28章亦云:“(明朝)每座监狱内都有一座或两座(狱神)庙。”再如山西洪洞县仍保留的戏剧人物“苏三”原型被监禁的县狱,有一座修于明初的狱神庙,庙甚小,立于墙上,中有三神。居中者为狱神[6]。而清代的狱神庙也是建在狱中,中央监狱的狱神庙为阿公祠,清震钧《天咫偶闻》卷2引濮青居士所著《提牢琐记》曰:“(刑部狱)南则阿公祠。”地方如光绪年间所修的《孝丰县志》载:“县署在城内西北隅……监狱内萧王殿一间。”清人程穆衡《水浒传注略》也云:“青面圣者:狱中皆有萧王堂,祀萧王。其青面神,相传萧王判案。”
狱神庙建于狱中还见可之当时的说部,如《小五义》第69回:“(艾虎)来到监牢狱的门首……往里一走,奔正西。有个虎头门,上头画着个虎头,底下是栅子门,正字叫貔犴门。虽画着虎头,乃是龙生九种之内,其性好守,所以画在监门之上,取其有守性的意思。在貔犴门北边,有个狱神庙,约有半间屋子大小。”这里狱神庙与重囚牢皆在“监牢狱的门首”之内。又如清代光绪初年刊刻的评弹小说《描金凤》17回,金继世随其父准备进县狱探看其结义兄弟徐惠兰时,先是其父“手叩监门”叫道:“开监门,开门来”,进狱后,“四个伙计(狱卒)一起领了金继春到萧王殿,叫金继春在萧王殿等,自己去叫徐惠兰出来。”可见,狱神庙(萧王殿)即在狱中。
那么,狱神庙之功能又是如何呢?
其一,为狱官狱卒和囚徒例祀的地方。狱神则是中国旧时民间信仰的对象之一,为囚徒渴望能主持公道、司法公平的神灵。曾德昭《大中国志》第28章:“(囚徒)这些钱刚付完,还必须再付最后一笔为监狱庙堂及偶象献祭的费用,因为每座监狱都有一座或两座庙,每月阴历初一、十五狱吏都要去献祭,祭品一般有一只鸡、一块猪肉、两条鱼、馒头、果品及其他物品。他们把其中一些祭品用水略煮一下,那只鸡仅煮到可以把它直立在庙前的桌上,其他东西则整齐地放在它的四周,摆一个时辰后,他们就把这些东西拿走,重新烹调鱼和肉,味道鲜美,然后他们举行一次宴会。新囚犯必须捐助和提供这笔费用,那些在这次献祭后入狱,到15天后下次祭祀的人,要提供下次祭祀的费用,而那些经过下次祭祀之后的人,到时则免于交付。”这则材料表明,狱神庙有对狱神的例祀,每月二次在朔望进行,主持者为监狱的狱吏,参与者为看守、囚徒,而祭品的购买费用则由新囚徒提供,最后祭品散福受用为大家共享。这种例祀,某种程度上可说是狱卒压榨囚徒捞取外快的手段之一。清代对狱神的例祀情况亦如此,《提牢琐记》有云:“诸神塑望则祀,履任则祀,报赛日则祀,勾结日则祀,必躬亲,香帛虔洁,宜专厥司,庶几覆盆之中,亦有临质。神道没教,用佐官箴。”这里,祭祀狱神主要包括三种情况,一是塑望的例祀及其赛神日(神的生日)的祭祀;二是狱官履任之日的祭礼,强调对国家和神灵的虔诚;三是处死犯人的勾结日祭祀,以说明神道的公平和不诬。
其二,由于狱神庙为囚徒和狱卒共同信仰的神灵,囚徒希望通过祭祀求拜狱神,能得到其保祐,得到审判官员公正公平的判决;狱卒心理中亦相信狱神在冥冥苍天之中俯临监狱,以维持监狱管理中的秩序和公正。因此,此二类人,若心理存在某种因现实或妄想产生障碍,往往求助狱神,以获得心理的宽慰和缓解。如曾德昭《大中国志》28章云:“这些供奉偶像的庙字,不只供囚犯祭祀,也供其他一般之用,那就是,供囚犯作誓言、抽签,尽管多次出现不幸的结局,因为抽的签允诺他们得到自己和愉快开释,结果却受到官府的刑杖和刑法。”并且,作者举了一个实例:“有一天我在场看见一个可怜的异教徒,虔诚地跪在地上抽签,因为他不识字,他叫另一个人帮他看庙里保存的一本小解书。抽下签,这个可怜的家伙问:‘那么,我抽到甚么?我会在法堂受刑吗?’另一个人翻阅书页,叫道:‘打起精神,一切都好,你抽到一个好签。’”足见,狱神庙之狱神在囚徒心目中具有某种预示功能,是旧日无助的囚徒减轻恐惧的无可奈何的选择。再如,清初小说《赛红丝》第7回,狱卒朱禁子被恶棍皮监生和屠才收买,欲害死无辜秀才宋玉古,他担心公正之神狱神的惩罚,便私下事先求拜狱神的宽恕:“(朱禁子)因有事在心,吃了一肚子酒,磕了四个头,通诚道:‘狱神老爷在上,要害宋秀才性命,皆是皮监生与屠才之过,实与小人无干。小人不过得他几两银子养家活口,望老爷鉴察。’说完头起来,又筛了一大碗烧酒,吃了壮壮胆。”
其三,狱神庙为囚徒亲朋好友探监会见之场所,囚犯接受审问时准备衣着等的临时房间,亦是司狱官员巡察监狱休息之地,也为有钱势的犯人,休息闲游之地。为了便于让带上刑具囚徒与亲朋等人私下谈话,狱卒甚至有意避开,这实际为徇私舞弊留下了空间。如《描金凤》17回狱卒头领金图远:“又关照禁班伙计去外面去叫二桌酒,一桌放在萧王堂让他的兄弟(指探监人金继春和囚徒徐惠兰)饮酒谈心,一桌放在监门跟首,请伙计(狱卒)们喝杯喜酒。”经过这样的安排,狱卒先是让金继春在萧王殿等候,接着从牢中提出徐惠兰,他“哪料弟兄在监牢里萧王堂相见,跟了禁班伙计直往萧王堂而来。”尔后,由于县官要提审徐惠兰,“伙计把刑具、罪衣、罪裙拿在手里,直往里边而来,到萧王殿天井朝里一看,只见徐惠兰一个人坐在那里。”“伙计把他方巾去掉,罪衣、罪裙罩在海青外面,刑具上好,带了金继春直往外走。”这里,被怀疑犯了杀人罪的徐惠兰,由于是秀才身份,虽有杀人犯之嫌疑,但由于未决,故尚能在狱中戴秀才的头巾,而去接受审判时,则必须穿上犯人的囚衣,故在狱神庙中换穿上囚服,戴上刑具上堂见官的。狱神庙有时也是狱官查看牢狱,盘问狱卒监狱管理状况,甚直对狱卒嘱办非法事项、及其暂时休息的场所,晚清西冷野樵的小说《绘芳录》60回,主官狱政的南昌县典史朱丕查看牢房,“这日恰好有一起大盗获住,发下狱来。晚间朱丕亲自去查监。因是一班飞檐走壁的巨盗,嘱咐狱卒,夜间防守须严。”狱卒中有一名禁子名叫窦泗,为人心细如发,办事玲珑,朱丕很喜欢他,“查过了监,到狱神堂少歇,喝退随来众人,单唉窦泗进来。”朱丕如此行事,目的是要通过窦泗,陷害他人。狱神庙,甚至也是囚犯,包括重囚,可以闲游的地方。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第1卷“十四杭州”述及他在杭州陪侍其因科举作弊案而被判“监斩候”而关在杭州府司狱司监牢中的祖父时,有这样一段文字:“当时他的日课,是上午默念《金刚经》若干遍,随后写日记,吃过午饭,到各处去串门,在狱神祠和禁卒等聊天。”可见,狱神庙是牢中囚徒日日可以常去闲游的地方(当然有条件限制,详后)。
其四,狱神庙也是与囚徒有关之人,尤其是其亲朋好友为他乞求狱神保佑之地,他们或许愿心,或作咒罚誓,或倾诉冤情,目的是渴望审决时的公平。当然,这些人要进入狱神庙,或悄悄非法闯入,或赂贿狱卒公然进入。许愿心悄然进入的如《小五义》57回小侠艾虎欲救受冤屈朋友来到牢房劫狱,遇到困难,“正在为难之处,忽然想起一件事来:每遇打官司的,说狱神祠最灵,如今何不哀牢狱神爷去?倘能狱神爷有灵有圣,也许有之。自己仍然扑奔正东,到了貔犴犴门的北边,纵身蹿上去,飘身下来,到了狱神祠。双膝点地,通诚祝告了一番:若得把二位哥哥救出去,重修狱神庙,另塑全身!祷告完毕,又磕了一个头。”诉冤情的如晚清小说无名氏《红风传》11回曹进进监探看荣公子,不料荣公子已被刑而昏死,禁卒便告诉曹英去狱神庙哭冤,以求上天发威使荣公子还生。“禁卒说:‘你不用哭了,我把刑法给他去了。你与他往狱神庙哭去罢”,“(曹英)背着公子来的快,狱神庙不远飓尺中。曹风放下荣公子,双膝跪在地流平,曹风叩头忙告视:狱神老爷在上听,保佑兄弟还阳转,翻盖庙宇报神灵。狱神闻听不怠慢,又把土地叫一声。”上述三例虽是小说家言,但在封建时代的民众信仰和狱政管理中,皆是现实存在的事实。
要推测“狱神庙慰宝玉”的相关情节,尚需了解清季囚徒在牢狱中的日常生活。清代各级监狱的生活住宿条件一般说来异常恶劣,狱卒旧时被归类属倡优隶皂一类的贱民,收入微薄,根本无法维持家庭的生计,囚徒就成为其盘剥敲诈的对象。一方面,囚徒不仅进牢狱就要交各种例钱,而且狱卒时常也以各种借口对之进行讹诈;另一方面,若囚徒富有能满足狱卒的饕餮之心,则狱卒往往不顾王法,想尽办法备办各种设施,使这类囚徒享有种种特权,即使他们犯下各种严重的罪行,依然可在监狱过上与狱外相近的生活。
如“那些关押在封闭监狱(重囚狱)的囚犯,尽管他们不能出去,这只对那些没有钱的而言,若他们有钱赂贿狱吏,就可以随意出去,到他们愿意去的地方停留,他们白天在牢里仍然是自由的,而一到夜晚就被按如下方式收系起来……”[7]交了例钱之后,“普通牢房每天开放,囚犯可以自由地从这间到另一间去,并在后院交谈。”[7]如果说这是明末清初监狱管理的真实现状的话,那么清代中后期的情更是如此,像清末刑部监狱中的赂贿就有多种,其中的“全包”即是“从大门买到监内”,犯人花重金在未入监之前使将从刑部大门外的门役、门茶房一直到大门里的守门头目,提牢厅各提牢主事、书吏甚至狱神庙的正副牢头、刑部堂上各主事等大小官吏全行贿通;犯人“甫至刑部大门,即由大门外的群役趋至囚车将其扶掖下车,……进大门后,大门里的群役也和大门外的一样,都跑到犯人面前殷勤招待,问茶问水,惟恐不周……,到了二门(牢狱大门)、二门外的群役又纷纷相迎,有的向犯人问安,有的向犯人道受惊,仿佛关切得了不得。最后一进狱门,那些值日司狱房的群役,都早已在甬道二旁,垂手立候,大家都抢着过来,把犯人扶在凳子上一坐,献茶致慰,使休息一会,这才扶着他到狱神庙,去见当家的(即牢头)。”[9]再如清人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载:“近日周瑞清等入刑部狱,索费至三千金……周(瑞清)得小室三间,龙止一间,可自携仆作食,且通家人,宾客往来。”又如谭嗣同被捕入狱之后,为了获得较好待遇,立即买通狱卒暗中通知家人胡理臣和罗升,要他们“速往源顺镖局王子斌王爷处,告知我在南所头监,请其设法通融招扶”[9]。可见,在封建统治之下,监狱制度在狱卒的贪婪和金钱的腐蚀下,形如虚设,只要有钱,即使中央监狱的严例规条,也是一纸空文,像谭嗣同这种当时看来异常严重的政治犯,也能通过通融改善生活条件。
三 吴、胡二说的评述与“狱神庙”情节的推测
对明清之际中国古代狱政制度和狱神信仰进行梳理之后,再看吴世昌先生的狱神庙性质的分析,可知:其一,虽然吴世昌只依据《果报录》的描述,得出狱神庙在监狱内部的结论,但这一结论却是正确的,因为狱神庙确为监狱的附属建筑,它是为囚犯、狱卒、狱官等人服务的,所以,必须建筑在牢狱内部。其二,吴说狱神庙是关押死囚的场所,显然错误,他把狱神庙附近的牢房和狱神庙等同起来,狱神庙是祭祀狱神之地,为监狱内的独立建筑物,当然对一些简陋的基层监狱,狱神庙也可和牢房建在同一建筑中。而在清代犯有重罪的嫌疑犯及待决死囚一般囚于重牢之中。其三,关女囚的监狱所在方位,并不能依据是否探监人进监时经过狱神庙,而确定它在牢狱建筑的较里处。这要看各地牢狱建筑的具体情况,以“里外”来描述各监房的方位,无法做到具体确切。其四,至于吴世昌先生对“狱神庙”的情节推测则无法成立,说宝玉和风姐竟被判了死刑(或流刑),小红、茜雪去探监是在临刑之前借“祭狱神”的名义赂贿狱吏所以能和宝玉等在狱神庙相见,可以说是猜臆,因为由前面的介绍可知悉清代监狱一般说来监禁的是未决犯,所以不能说“宝玉和凤姐”被判刑,而对于已判死刑的囚犯执行前先“祭狱神”,这只可能是监斩官、狱官、狱卒和囚犯参与,囚犯的亲戚在这严威的时刻是不可能进入狱神庙的。
至于胡辰先生对狱神庙性质的分析亦大有讹处,第一,是狱神庙并不在监狱之外,而确是在监狱之中。第二,它也不是拘押同案件有关人员包括证人、首告、嫌疑者等等的一座庙宇。由前述可知,在封建时代,犯罪嫌疑人必须囚于监狱当中,而一般的原告、证人、并不需囚禁,只涉及重大案件,才把他们同被告一同分别囚于牢中。第三,胡辰生先推测“贾府被抄家一案,只有贾赦、贾政、贾珍、贾琏等人入狱,而凤姐、宝玉等人只是暂时羁押在狱神庙中”也纯属臆测,并无理据。第四,又言“狱神”更主要是折狱之神则过于武断。狱神庙是囚犯、狱卒和狱官信仰并参与祭祀活动的神灵,至于各级审判官员,则一般不参与其中的活动。当然,审判官员亦可能和一般民众一样信仰狱神能主持司法审判的公正,但在他的司法实践中,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更多的是根据事实和理性,而不是依据所谓神的预示、暗示之类去做判决。
至于《红楼梦》后40回中有关狱神庙的情节,我们据脂评相关的描述,只能推论出,在“贾府被抄”一案中,宝玉和风姐既然在狱神庙和小红、茜雪相见,显然,他们已作为被告、囚禁在监狱当中,且是作为未决犯而被囚禁的。而在监狱中能和小红、茜雪见面,表明小红、茜雪在贾府已抄、没有强大经济能力的情况下,借助朋友之力或动用个人的钱财,贿赂狱官狱卒,获得面见宝玉等人的机会,由于在旧日狱神庙具有作为在押未决犯人和亲朋见面之地的功能,于是在该地见到了旧日的主人。至于要使这个案件的判决有利于贾家或有利于属于次要“犯罪人”的宝玉、熙风,则非得调动大量的金钱且要打通主审官员关系,方可实现。且即使有钱,而完成这一目的必然要依赖于中间人的介绍,在贾府已遭灭顶之灾之时,贾府旧日的权贵亲朋对之避之不及不愿卷入其中,因此,贿赂审判贾府被抄一案的中间人则只能是衙门的差人一类人物,这在封建时代,由司吏、差役、公人、狱卒、门子等通作交通官吏中间人的情况屡见不鲜,倪二可能就是这样一位中介。即在《红楼梦》中,这有可能由茜雪、小红、贾芸等人调动他们能有的金钱,通过倪二(不一定是狱卒),买通了贾府被抄案的主审官员,作出了有利于从犯宝玉、熙凤的判决。由于贾府一案的严重性质,受朝廷关注,故不能对整案作出轻判,且贾芸等人也无如此的经济能力,能彻底满足从门子至各层审判官员多人的贪欲。当然,还有其他种种可能情况,比如皇帝姑念旧恩,对贾府年轻一辈的子弟,放松一马,从而使得宝玉、王熙凤能够脱却牢狱之灾。也有可能是北静安王之类权贵高官,念在与贾府世谊交往的旧情上,对皇帝或主审官员说项,才使得宝玉、熙凤或判轻罪、或被释放,在这样情形下,“狱神庙”情节,则主要是写像小红、茜雪一类的下层民众的美好品德和对宝玉的一片深情,此与深得贾府佑助的贾雨村一类寡恩刻薄之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至于吴世昌先生据脂评预测《红楼梦》后40回中有宝玉、熙凤为倪二劫狱救出的情节,则只能是大胆的想像,有把这一世情小说等同公案传奇了,这与曹雪芹的创造初衷显然不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