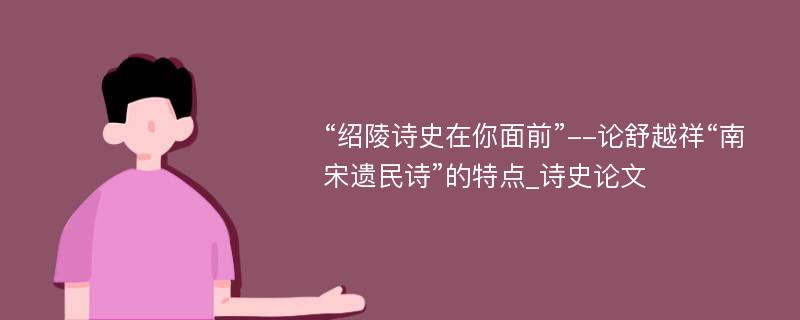
“少陵诗史在眼前”——简论南宋遗民舒岳祥诗歌的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史论文,遗民论文,南宋论文,诗歌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舒岳祥(1219—1298),字舜侯,一字景薛,浙江宁海人,出身于世代读书做官的家庭,自幼受到了很好的文化熏陶。据载,他“童时出语辄惊人,落笔不肯随人后,踔厉风发,士林老宿莫不屈辈行与之交”(注:刘庄孙《舒阆风先生行状》,见《光绪宁海县志》卷二十《艺文内编》)。38岁登文天祥榜进士第,授奉化尉,从此开始了仕宦生涯。宋度宗咸淳末年,以尚气简直,不为贾似道所用,即弃官归故里。后逢鼎革动乱,辄“涉坎险,历蹇难,萍流蓬转,有陶杜所未尝”(注:王应麟为舒岳祥《避地稿》、《篆畦稿》、《蝶轩稿》三书所作序,见《阆风集》卷首)。如宋恭帝德祐二年丙子春夏之间,元兵至庆元、台州一带,舒岳祥始避地蓬转于石林、雁苍等处。十月,元兵扰宁海,入尚义里,屯舒氏宅。舒岳祥《为胡后山提干咏南麓古松》诗末自注:“丙子大兵入尚义里,屯予宅。”次年即宋端宗景炎二年,舒岳祥59岁,他曾赋《自寿》诗以述其当时的蹇难艰辛之状:“阆风老人五十九,白头饥冻荒山走。偶然脱命得生还,闾里相看惊老丑。今朝初度最可怜,五子三孙在眼前;老妻欲作无面饼,问讯鸡娘渠未肯;海水潮小未登鱼,霜后黄柑亦自疏。穷人作事天不与,只有红梅相媚妩。”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己丑,江南农民暴动凡四百余处,舒家亦不免毁于兵火,舒岳祥身无余物,又以71岁高龄流徙各地,过着非常艰难困苦的生活。他甚至“谋生药当田”(注: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二十九,《读阆风题林隐诗追和赠汪秀才》)。谢翱所谓“舒君白头爪尘垢”(注:《晞发集》卷五,《送袁太初归剡原……》),就是对他晚年生计窘迫的真实写照。
舒岳祥作为宋末一位多产而重要的诗人,他对前代诗歌体派风格的推尊本来是并不主于一家的。如他的《诗诀》“欲自柳州参靖节,将邀东野适卢仝”云云,即不难想见其宗旨之所在。然而,舒岳祥晚年所目睹的民族国家的巨大变故和个人所经受的不幸遭遇,实有过于历史上许多困穷诗人,这就不禁使他对杜诗加深了认识,并进而达到了“情有独钟”的地步。他说:
承平三世积,丧乱一朝贫。……平生欲学杜,漂泊始成真。(《九月朔晨起忆故园晚易》)
燕骑纷纷尘暗天,少陵诗史在眼前。……君能于此更著力,唐体派家俱可捐。(《题潘少白诗》)
总的说来,对于杜甫“诗史”的认识,宋人比唐人更为深刻。胡宗愈认为,杜诗之所以被“学士大夫谓之诗史”,就在于其“凡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文天祥也认为:“盖其以咏歌之辞寓纪载之实,而抑扬褒贬之意灿然于其中,虽谓之史可也。”可见,杜甫“诗史”的特质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歌时伤世,幽忧切叹之意,粲然可观”(注:吕大防《杜工部年谱》,《四部丛刊·集部·分门集注杜工部诗》附),使后世读者都能感知到诗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并进而窥见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遭受异族蹂躏的真实情况;二是以写史的笔法写诗,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去记录并评判自己所处的多灾多难时代所发生的种种事件,让后人永远从中记取悲惨的历史教训。
诚然,舒岳祥晚年正是从这两个方面来认识杜诗的真正价值的,并努力把这种思想认识贯彻到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去。因此,我们诵读他的诗作,首先体味到其中充满着“忠愤感激”、“幽忧切叹之意”,与杜甫的“诗史”精神完全相通。如:
杜陵野客酒可赊,只恨青蕊成蹉跎。如今风物尤凄恻,绕丛觅蕊无消息。寒螀相吊野水流,病蝶来偎寒日夕。不见金钱将翠羽,惟有悲风吹蔓棘。……两都风景今何如,泪堕丛边和露滴。(《九日敏求与侄璋九万载酒……》)
忧心悄悄睡未能,开门看月一片冰。窍木相磨作鬼语,冻星入牖如萤青。孤雁哀号向何处,老夫掩耳不欲听。尔从沙场经万里,昔时系书达天子。如今若向上林过,纵有书来谁取视?(《孤雁》)
颓墙宿莽露泥泥,荒田野菊秋菲菲。我止安息?我行安之?噫吁嘻!过殷墟兮渐渐,览周原兮黍离离。……白骨兮成豀,膏肉兮成泥。已焉哉!(《罪言》)
大致说来,舒岳祥的忠愤感激、幽忧切叹之意,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抒发的:一、叹国失君辱。如《杜鹃花》借古蜀王杜宇失国的故事云:“杜陵野老拜杜鹃,念渠蜀王身所变。我今流涕杜鹃花,为是此禽流血溅。嗟哉杜宇何其愚,万事成败皆斯须。一枰黑白翻覆手,揖让放弑皆丘墟。汝初一身今百亿,凝滞结恋胡为乎?尔生不能存社稷,死怨谢豹何区区!至今有子不自保,寄巢生育非良图。”可见,其在叹故国、思故君的同时,又不无作为一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诗人所应有的反思与责备之意。二、叹身历蹇难。其《新历未颁遗民感怆……》云:“故国山河成断绝,孤臣江海自飘零。”又云:“寒气著人身似病,世途多故鬓如银。劫灰今信胡僧说,野磷多应战鬼新。兵甲纵横满天地,衣冠颠倒走风尘。”正是王应麟所谓“晚岁涉坎险,历蹇难,萍流蓬转,有陶杜所未尝”,而“固穷守道,皓皓乎白壁之全”者。三、叹生灵涂炭。如《乱定复过西溪》:“不过西溪三十秋,乱余重到泪双流。黄蒿满地青烟少,日暮驱车不敢留。”又《春雪》:“呜呼!狐狸有屋尔得居,室中居人今在无。或言白骨如白雪,雪亦有仁遮白骨。”读之令人痛心万分。四、叹暴政之虐。其《自归耕篆畦见村妇……》之九云:“妇啼如此苦,吏夺一何豪!尺布不得著,长年空自劳。剥衣聊赎命,覆体不生毛。念欲全家去,乾坤何处逃?”(注:组诗之六云:“阖中寄衣妇,夫婿在辽阳(元置辽阳路,治所在今辽宁辽阳市)。……早愿王师息,我欢还故乡。”其“夫婿”或以随“王师”征日本而至彼地耶?据此,则诸诗所写皆为入元后之事)又《乐神曲》:“污田稻子输官粮,高田豆角初上场。……巫公巫公告尔神,产谷不如多产银。驴载马驮车碌碌,免斫柘条行棰扑。”(注:据诗中“前年军过鸡栅空”句,则此处所写亦为入元后之事)此处所反映的蒙元政权之不仁以及官吏之暴虐,正可与他在《陈仪仲诗序》中所述者互为佐证,而使千载之后的读者犹可知其世:“予亲值乱亡,有先人之莱田在,沦为民伍,遂执里役。晨起开卷,未数行,悍吏操棍曳索,隳突灶奥,败思挠怀,呻吟即事,夜分犹未甘匕饭。城舆绛老,曷日免泥涂之辱耶?”
其实,舒岳祥岂止“幽忧切叹”而已,他更像“少陵歌里哭”(《自次前韵酬马奥诸丈见和》之二)那样,以歌当哭来彻底宣泄自己胸中的悲愤之情。如从“避地身三到,伤时泪数行”(《七月望日避地省坑存思庵留题……》),“安危治乱几番见,到此三年哭断魂”(《解梅嘲》),“寻春曾作太平民,说著花时泪湿巾”(《暮春书怀寄董正翁寺正》),“曾对集英瞻衮冕,孤臣洒泪立东风”(《牡丹》)等诗句中,我们仿佛犹能看到这位故宋遗臣,“自京国倾覆”后,“于极海之涯、穷山之巅,用其素所对偶声韵者变为诗歌,聊以写悲辛、叙危苦耳”(见《跋王榘孙诗》)。当然,无论是幽忧切叹,还是以饱蘸血泪之笔写悲辛,叙危苦,舒岳祥并不止于为一己伤穷悼蹇,更重要的在于以遗臣应有的忠肝义胆去缅怀故君故国,以士大夫应有的本分去关注民族国家的命运,以诗人应有的襟怀去放眼天下苍生,以历尽坎险蹇难者所具有的悲悯之心去同情所有的不幸之人,以遗民的满腔义愤去大胆揭露和斥责蒙元新政权的残暴统治。舒岳祥自谓“平生欲学杜,漂泊始成真”,其真谛应当就在于此。他的诗作与杜甫“诗史”精神相通,其关键也在于此。
然而我们应当明白,舒岳祥所谓的“少陵诗史在眼前”,却是更侧重于从取材如史、笔法如史的方面去高度认同杜甫“诗史”的。因为在他看来,“咸淳无正史,德祐少完人”(《少师丞相国公西石间先生挽歌》之二),如果不加追记申述,何以使这段历史传于后世,以为明鉴?其《次韵正仲秋晚感兴》小序说:“每得正仲秋篇,必先铺叙所见闻,不必左史倚相之读坟典也。盖古事已有传之者,而新闻就泯,或惧无述焉。倘因此而增长之,则咸淳德祐故老所传,犹可一二不没也。”并赋诗句云:“爱尔和诗添记事,愁来时解锦囊看。”说明其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南宋遗民普遍的“以诗存史”的观念是一致的。
显然,在“燕骑纷纷尘暗天”和“寇盗”“旁午”(注:按,当时纷起的农民反元队伍,多有随意烧杀抢掠的行为,故舒氏视为“寇盗”(详见其《出入二岭行》、《归故园》、《宁海县学记》、《蝶轩稿序》等诗文),此当别论)的年代里,浮现在舒岳祥“眼前”的“少陵诗史”,主要当指那些反映当时动乱现实的作品。其《自次前韵酬马奥诸丈见和》之一有句云:“乱离多少事,史笔若为传。”说明他十分清醒地意识到,以“史笔”传写鼎革之际的“乱离”之“事”,让后人了解这段悲惨历史,这无疑是自己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舒岳祥就援引史传的笔法,忠实地记录下了那个动乱时代里所发生的一幕幕悲惨的情景。如其《晓霜成花,日色凄淡,炙背南檐,记所闻见》一开头就叙述说:“十月二十有二日,霜凇成花泥淈淈。黑旗一点飞过村,居民缩头那敢出。又闻鄞骑入连山,搜捕乡兵火庐室。台明隔岭易张皇,纷纷徙家藏谷实。”很明显,诗人无论是对时间、地点的处理,还是对故事情节的安排,都无疑使用了史家的笔法。而《次韵袁伯长寄赠之作》,则又显示了“史笔”叙事的另一特征:“忆昔盗起初……移家入新昌。完璞保贞节,训猷谋善臧,嵚岖远荆棘,瘏痡辟锋芒。五男不挟册,四妇废条桑。长孙病风挛,二孙鹤未昂。三孙始周晬,疡垢浴兰汤。曾孙客中产,敢拟门户当。复有四女孙,包裹针线装。步涉青店溪,伏莽突长枪。性命幸完免,翁媪扶筍将。回首烟焰涨,搜山发窖藏。家林付瓦砾,书籍罹咎殃。赉粮中道绝,万事慨以慷。……又闻来屠剡,玉石恐俱伤。……悲歌寄赠什,歌罢复徊徨。”诗人以亲身的经历和所见所闻,十分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一系列动乱现实,而自己一家人的罹难,则是诗中铺叙的重点。可见其取材有如史家,运用笔法也同样有如史家。而且,为了尽可能增加这类“诗史”的容量,并使其叙事纪实具有一定的情节性,舒岳祥一般都采用了长篇歌行的形式。但它们又不是“传记文学之用韵者”,而是一篇篇在完全遵循诗歌自身艺术规律的前提下创作出来的纪实性诗歌作品。如作者陈述时事时,多夹叙夹议,且时时寓情感于叙述之中。凡此,都可以见出作者的诗心所在。
不过,对于舒岳祥的许多“诗史”来说,它们的纪实功能之所以能得到强化的又一原因,还在于他成功地运用了序言。本来,“序以建言,首引情本”(注:《文心雕龙·诠赋》)。也就是说,按照传统的做法,序言仅仅是用来作为发端,交代创作动机和缘起的。舒岳祥却与前人不同,他运用序言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强化作品的叙事纪实功能,而将交代创作的动机、缘起等退到了次要的位置。如他的《归故园》序是这样写的:“余辟难明越,五迁至版坑棠溪,袁仲素兄弟邀馆其家,已丑六月十六日始就之。明年三月归阆风,寓于凤栖塘田舍。行视篆畦故物,无一存者,惟咸平古松及瑶池无恙耳。作《归故园》二首遗正仲。”其诗之一云:“千家桑梓兵余痛,十世松楸火后悲。瓦砾成滩无鸟雀,荆蒿如杖有狐狸。咸平树在枝柯损,晚易书亡目录遗。半树瑶花微雨里,向谁寂寞泪将垂?”之二云:“辟兵辟寇走他方,六遍移家路转长。百醉与君同出处,五穷随我共行藏。柳花暗度谁家竹,燕子寒归何处梁。最羡刘家好男女,稳抛家事客原尝。”显然,像这样的序言,与其说是为了“引情本”,倒不如说是用来丰富、补充、印证诗作本文所述的内容。要是没有它,诗中所陈述的事实片断就会显得凌乱而无所归属,从而影响到“诗史”所陈时事的完整性,给人以一种模糊和不真实的感觉。
但是,如果从“诗史”的体式方面来看,舒岳祥以序代题形式的广泛运用,则更具有创新的重要意义,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体制短小的诗作本身难于履行叙事纪实职能的问题。今移录其以序代题的二则文字于下:
丙子兵祸,自有宇宙,宁海所未见也。予家二百指,甔石将罄,避地入剡,贷粟而食,解衣偿之,不敢以渊明之主人望于人也。因读渊明《乞食》诗,和韵书怀,呈达善。
七月十五日,竞传有铁骑八百来屠宁海,人惧罹仙居祸,僦船入海,以鸱夷子游。余在龙舒精舍,事定而后闻之,幸免奔窜,深有羡于渔家之乐也,作《渔父》一首。
可见,即使诗作本身体制短小,或抒情成分过多,但由于具有如此长的纪实性诗题发挥着铺垫、补充、印证的作用,诗中所述的诸多事实片断于是得到连贯,所发抒的情感也有了明确的指向,因而整首“诗史”叙事纪实的基本特征也就得到了充分体现。下面,就舒岳祥的一大批“诗史”的题目与诗作本身之关系以及由此体现出的整个作品叙事纪实特征等问题,作进一步的分类举例述说:
其一,以诗题叙事纪实,而让诗本文充分发挥其抒情功能。如他以序代题纪实云:“丙子兵祸,台温为烈。宁海虽经焚掠,然耕者不废。丁丑粗为有秋,但种秫者少以醉人为瑞物。吾亦似陶靖节,时或无酒,雅咏不辍也。八月初九日,连日雷雨,溪路阻绝,山房岑寂。此夕初霁,浊酒新漉,数酌竟,步秋树阴,潭鱼可数;望前峰,老枫数十株,已无色,白鸟飞翻去来,是中有惠崇大年笔。家人遣两力来迎,因倒坐篮舆而归。人或问之,戏答曰:吾日莫途远,故倒行也。记以三绝。”接着的三首绝句,大致都是像“伤今兵乱后,人醉不如枫”(之二),“兴亡谁与吊,聊复快新晴”(之三)之类的抒情性文字。不过,由于诗中所抒发的情感都可以与诗题所陈述的事实互为生发,并从这些事实中一一找到它们之所以被振荡、激发起来的缘由,于是抽象的情感就具有了明确的指向性和具体的可感性,而承担抒情职能的诗本文也就体现出了一定的纪实性。
其二,以诗题为“大事纪”,而让诗本文承担起抒情和摄取典型镜头的职能。如有诗题云:“去年大兵入台,仙居幸免,今冬屠掠无噍类,衣冠妇女相随俱北,闻而伤之,作《俘妇词》。”诗云:“初谓无兵祸,那知酷至斯!相看不敢哭,有死未知期。儿向草间没,夫随剑口离。琵琶犹带怨,况是作俘累!”诗本文在诗题“大事记”的基础上,通过选取“儿向草间没”、“夫随剑口离”两个具体而典型的事例,抒发强烈的慷慨之情,从而使整个作品构成了一幅具有浓郁的情感色彩,能够广泛而典型地反映当时动乱现实的生动画面。
其三,让诗题与诗本文互为补充、生发和印证,但侧重点各有不同。如:“七月望日避地省坑存思庵留题,时章林出白石,可为水晶,有旨差路县官同金玉提举差夫取凿,又宿兵守之。吏卒旁午,指予为上户,求鸡羊酒米油铁,无以应其求,且不堪其屡也,来避于此。予念自丁丑之乱,至此凡三避矣。僧旧屋更新,怅然有感,因赋之。”诗云:“去家无十里,过岭即他乡。避地身三到,伤时泪数行。高檐齐古树,新屋背斜阳。我欲相邻住,青山志未偿。”这里,诗题从纪实方面大大丰富了诗本文的叙事内容,诗本文则主要从抒情方面进一步发抒了诗题中的“怅然”之“感”。又:“过字韵诗,辱诸友联和,方营度枯鄙以酬厚意,偶报北兵自瓯闽回,驱男女牛羊万计,入蛟湖、深畯,出独山,屯尚义,由童公岭以北,三日夜不休,闻之惊心,遂成阁笔。是月十四夜,对月感涕,遂即前韵以纪时事,奉呈诸友。”诗云:“麦倒桑折枝,山外花门过。牛亡主不归,妇去蚕未卧。在者哭空村,吞声谁敢大?盲晖隐空崖,惊尘飞暗堁。川逝痛陵迁,春深悲国破。可惜此良宵,月轮升紫磨。”这里的主要特点是,诗题、诗本文通过分别选择不同的叙事角度,从而使两个部分的内容起到了互为补充的作用。
如果追溯渊源,杜甫的“诗史”已有以序代题的,但非常少见,且文字也比较简单。可是到了舒岳祥,这却成了他创作“诗史”时最为惯用的一种形式,而且文字也大幅度拉长,并十分注意在叙事纪实过程中点明事情所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以及引起本人创作欲望的缘由。因此,如果再加上他创作的其他各种类型的“诗史”,并按其中点明的事情发生的时间先后对所有这些作品依次进行排列,那么便可以构成一幅具有明确编年和事情发生详细地点的长篇历史画卷。这幅画卷起始于宋度宗咸淳末年诗人弃官归里前后对黑暗时政的描绘和批评,终止于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他溘逝前二日所赋《天门杂咏》对自己在饱经世事沧桑后走向人生终极时的感悟(注:详见刘庄孙《舒阆风先生行状》),时间跨度长达二十余年。她可以依照时间递移的先后次序,将一个个具体画面动态般地展现给人们,而其中最为催人泪下的,则是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元兵侵逼和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寇盗蜂午两个时期,东南沿海一带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其害,甚至暴骨原野的几组悲惨镜头。如果说汪元量主要是通过继承并发展杜甫联章组诗的手法来创作他的“诗史”长卷的话,那么,舒岳祥则主要是通过继承并发展杜甫“诗史”以序代题的艺术形式来强化他诗歌作品的叙事功能,从而创作出他那部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宋末元初东南沿海地区动乱现实的“诗史”巨卷的。舒岳祥与汪元量所运用的艺术形式虽然有所不同,但他们“走笔成诗聊纪实”、“少陵诗史在眼前”所表现出的精神实质却是完全相通的。因此,他们所创作出的作品也就成了南宋遗民“诗史”中的两座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