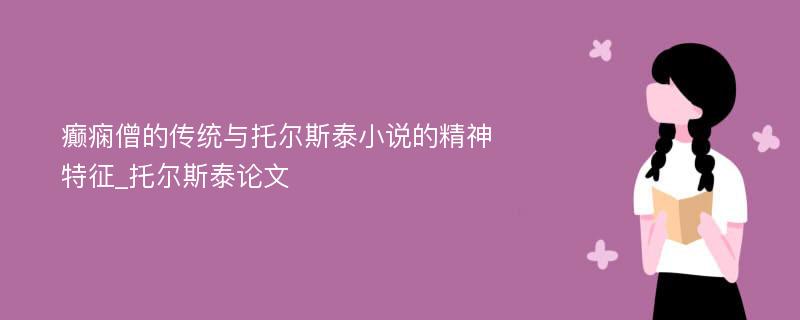
癫僧传统与托尔斯泰小说的精神特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托尔斯泰论文,特质论文,传统论文,精神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梅列日科夫斯基称屠格涅夫是托尔斯泰一生的“敌人”,同时他们也是地球上“唯一的朋友”。说他们“天性上是敌人”,“心灵上是朋友”。[①]生于同一时代的两位现实主义小说大师的艺术个性的差异,是非常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在诸多差异中,二人对“癫僧”的态度最为不同了。
屠格涅夫几乎从来就没有注意过俄国的这种文化现象,他对托尔斯泰表现出来的癫僧习性大惑不解。1857年,屠格涅夫看过《一个地主的早晨》之后说:“我非常喜欢这篇作品的感情真挚和几乎完全不落窠臼的观点,……这一短篇小说给人的道德印象是:只要存在着农奴制,双方就无法接近和理解,哪怕是有十分真诚和无私的接近的愿望——这样的印象,即美好又正确;但与此同时还产生另外一种次要的,第二位的印象,即教育农民,改善农民的生活等决不会有任何效果,这种印象是令人不快的。”[②]其实,好的印象和不好的印象都是出于托尔斯泰的真诚,屠格涅夫不理解这个坏的印象,对托尔斯泰的“老一套”很不以为然。在读过《忏悔录》之后,他仍然不理解,就在他死前的那封信上(1883年6月27日或28日)他还是没有理解托尔斯泰,他以“即将死亡”的份量和资格,以感人肺腑的真诚,对托尔斯泰提出了“最后的请求”:“……我……已处于死亡的边缘。我现在亲自给您写信,为的是想向您表明,我成为您的同时代人是多么高兴,并且向您表示我最后的衷心的请求。我的朋友,回到文学事业上来吧!须知您这种才华只能用在这方面,用在别的地方那就另一回事了。……我的朋友,俄罗斯大地上的伟大的作家——请听取我的请求吧!”[③]
这种临终遗言性的隆重“请求”恰恰表现了两位伟大作家的精神个性上的差异。托尔斯泰永远不能把“心”和“脑”分开,因此他的有些偏执的、不理智的“真诚”令屠格涅夫不快,也使许多“西方型”智者不快。作为受过西方现代文明严格训练的屠格涅夫,不理解托尔斯泰那种癫僧式的教育观念,他不知道,在托尔斯泰那里根本不存在“教育农民”的问题,而是“农民教育我们”的问题,不是改善农民生活的问题,而是“改善我们生活”的问题。是放弃文明,放弃现代文明的所有罪恶观念的问题。屠格涅夫不大理解托尔斯泰批判农奴制不是依托着西欧,而是像列宁说的那样是依托农民,他的好印象和坏印象,都是托尔斯泰感悟到俄罗斯的真实处境之后,急急忙忙不加掩饰地告诉给大家的全部心里话,是一个俄国癫僧式的思想者的精神和肉体的漫游。他是怎么样感悟就怎样说,好坏印象的批评只能让他更加有话直说,更不讲“章法”更加“不得体”。这种散漫的文体风格同屠格涅夫精致的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屠格涅夫总是一方面喜欢,甚至“嫉妒”托尔斯泰的博大无边的文学气度,又极不喜欢造成托尔斯泰浩瀚丰富的精神特质,以及这种精神所产生的“不规范”“不精致”的文体。
托尔斯泰的这种精神特质很大程度上来自俄罗斯的癫僧传统。
从童年有记忆时起,托尔斯泰就知道俄国有一种人叫“癫僧”(po)。托尔斯泰的家庭,宗教气氛极其浓厚。他们家中经常有香客、僧侣、修女和“癫僧”往来,甚至在他们家中歇夜。其中“癫僧”所带来的特殊气氛,构成了托尔斯泰所生长的生活环境的一个重要特征。癫僧式人物在托尔斯泰的生命中起过不小的作用,在通向亚斯纳亚·波良纳的路上,他曾经碰上这样的人[④],巴赫金这样说。这是俄罗斯文化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当时癫僧遍布俄罗斯。
俄罗斯总把一些精神世界格外独特,心灵格外丰富,同现实世界又格外不相融的人物称作癫僧,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巴赫金、肖斯塔科维奇都曾被称为“癫僧”。托尔斯泰非常自觉地把自己和这些癫僧联系起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我们家里有很多这样的半癫的圣徒,家里的人教我对他们特别敬重,为此我深深感谢那些抚养我的人。即使我们当中有些人是不真诚的,或者他们有过意志薄弱和不真诚的时期,可是他们生活的目标,虽然事实上是荒谬的,却非常崇高,因此,我很高兴我从小就不自觉地学着了解他们的目标的崇高”[⑤]。越到晚年,癫僧的形象在托尔斯泰心中越鲜明。“在他的晚年,我们会一再发现这种中世纪的论调的重现(不论是对或错),他这样宣称:重要的并不是一个人的生命的有用与否,而是他的自我否认,与他的灵魂的谦卑[⑥]。在1906年的一则日记里,78岁的托尔斯泰再一次说到癫僧。1910年,82岁的老人,离家出走,离开亚斯纳亚·波良纳,终于成为一个“癫僧”。
托尔斯泰的第一部小说《童年》就单有一章写尼古拉卡对癫僧的印象:“一个五十来岁的人走进屋里来,他脸色苍白,长脸盘,一脸大麻子,留着长长的白发和几绺稀疏的红胡子”,“他穿着一件破布衫,这布衫既像农民的长襟外衣,又像神父的白袍”,“他瞎了一只眼睛,那只眼睛的眼白不住地乱转,给他那本来就很丑陋的面孔增添了更加让人讨厌的神气”,他“走到桌子跟前,向漆布下面吹气,在漆布上面画十字”,“他用一种颤巍巍的悲泣声音说着,感伤地望着沃洛佳,并且用袖口去擦当真掉下来的眼泪”,“他的嗓音粗浊沙哑,动作慌里慌张,语无伦次(他永远不用代词),但是发的重音却那么动听,焦黄的丑脸上有时露出非常坦率的悲哀神色。听他讲话,不能不使人产生一种又是惋惜、又是恐惧、又是悲伤的复杂心情”。[⑦]
托尔斯泰在经常光顾他的家中的许多癫僧中,选出“格里沙”作为“蓝本”,目的是为了突出“这一个”癫僧的外在的“丑陋”“不幸”、“极度”“简朴”极度“原始”,是为了突出癫僧的苦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强调“这一个”给“童年”的强烈刺激,强调“这一个”给“我们”布下的种种疑问:
“他是什么来历?他的父母是谁?是什么迫使他选择了他过的这种流浪生活?谁也不了解这一点。我只知道,他从十五岁起,就成了尽人皆知的苦行者。无论冬夏,他都光着脚行走,朝拜寺院,把小圣像赠给他喜爱的人,说些费解的话,有的人认为这些话是预言。……有人说他是富家的不幸子弟,是个心地纯洁的人,又有人说他不过是个庄稼人,是个懒汉。”[⑧]
癫僧不是食客,不一定是僧侣,不是修道院里的修士。他们没有财产,没有家园,甚至没有真实的名字。三种特征使托尔斯泰一生觉得自己与癫僧在精神上相似:⒈苦行。他们的背兜上只有一点干粮,“无论冬夏都光着脚走路,衣服下面总带着两普特重的铁链,再三拒绝人家提供给他的供给膳宿的舒适生活。”[⑨]他们也许会在哪个地方留下来,但是很快,他们就对安逸的生活、世俗的温暖恐怖起来,于是又会背起瘪瘪的背兜继续苦行。“很难相信这种人只是由于懒惰才采取这一切行动。”从童年起,托尔斯泰的精神苦行就没有停止过。他精神苦行的每一次出发都是对旧有生活的一次全面清洗,对自己生命的一次顽强迫问。⒉信仰单纯。癫僧没有一大套宗教理论,也没有关于信仰的思辩论证。他们是以心灵的方式选择了非常单纯的信仰,并把此作为生命的目标。这种不求理性只赖心灵的特点是托尔斯泰更深的个性。托尔斯泰一生精神上的不断豁然开悟,不是“推理”结果,而是体悟内省的结晶。⒊痴迷,癫僧之所以被称为癫僧,是因为他们同现实世界的格格不入,是他们对现实世界的痴迷的理解,也可以说是疯狂的理解,他们格外的认真和真诚,使他们的言语行为同世俗的正常的世界形成强烈对比。所以在“正常人”眼里,他们都是半癫的怪人。托尔斯泰知道,真理非常简单,但是如果把真理说出来,却是要有和整个世界作对头的勇气,而如果把它实行起来,便要和自我作一生的搏斗了。
托尔斯泰的作品中癫僧式人物不断重复出现。《谢尔盖神父》中忽然一个很有前途的青年人傻癫癫当了神父,忽然,很有圣名的修道者变成了破衣旧衫的流良乞丐,忽然《安娜·卡列尼娜》中卡列宁变成《伊凡·伊里奇之死》中的伊凡·伊里奇,忽然《复活》中的聂赫留道夫抛弃家乡跟一个妓女去西伯利亚流放。
晚年,托尔斯泰构思了短篇小说《梦》,又把两种不同的癫僧的对比当做主题:“一个人梦见他死后受审判,别人把他做过的事放在天平上称。他等着别人拿来他为民众做过的事,慈善事业,他的科学著作,他在家里做的好事。这些都拿来了。可是在天平上没有一点分量。有的还起相反的作用,使天平的一端抬起来,那便是为虚荣而做的事。忽然,别人拿来他已经忘却的东西:他在争论时压抑了自己的懊丧,给小女孩拾起玩具……”“这都是人们不知道,不重视的事。还可以把两个疯僧拿来作比较,一个是公认的疯僧,职业疯僧,而另一个的疯僧行为是不由自主的,谁也不知道。上帝不喜欢前者,只喜欢后者。”[⑩]
从现代观念看,癫僧是愚昧的,从人类进步的角度说,癫僧也可能是最龌龊的。但是,正像列宁在托尔斯泰身上发现了这位宗法制代言人的落后的一面一样,癫僧的文化传统也是构成托尔斯泰精神特征的一大因素。
这些托尔斯泰小说里的癫僧们就是这样同世界、同自我不断搏斗,构成了托尔斯泰创造的艺术形象活动的重要轨迹。那么他们是如何发生这些“忽然”呢?这便是托尔斯泰要告诉我们的谜底。癫僧不断同世界、同自我进行搏斗,构成了托尔斯泰小说人物形象行为的重要轨迹,如何从“常人”到“癫僧”,如何从“公认的癫僧”到“上帝的癫僧”,这成了托尔斯泰小说的一个固定要安排的结构障碍。
托尔斯泰作品中可笑之处就像癫僧的行为一样明显,但是,也许正是这种“可笑”,使他在处理每一个人物、场景、结构、语言、故事(情节)的时候都表现出与众不同,他并非刻意写出“独特”或刻意“反众道而行之”。他仅仅是现实主义地在抒写自己:一个“癫僧”所感悟到的真诚,而恰恰是这种癫僧的真诚,使他的作品永远独特。
由此可鉴,梅列日科夫斯基说屠格涅夫在最后时刻理解了托尔斯泰,似乎不太准确。对屠格涅夫的批评和临终奉劝,以及对西方的类似批评,托尔斯泰显明地表示不以为然。早年他“谢天谢地”“没有听屠格涅夫的话”,“他屡次向我证明,文学家应当只做文学家。这不是我的天性。”(11)晚年他一方面在《什么是艺术》中系统地否定“技巧”、否定“西方的精美”,更加偏执地肯定“上帝的癫僧”的作品是最优秀的作品,另一方面,在创作上更加信游自己的精神探索漫无边际地破坏着各种传统的文体。随在随感随悟,信游自己的笔,平原大河般表现这种俄国独特精神特征。因此,他的小说总是带有一种“置水在平地,东南西北流”的大气度。
注释:
① 《梅列日科夫斯基文选》德文版柏林,209—210页。
② 《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北京,66页。
③ 《托尔斯泰文学书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长沙,215页。
④ 《列夫·托尔斯泰作品全集》,11卷,国家艺术出版社,1930年,莫斯科,9页。
⑤,⑥ 《托尔斯泰传》[英]莫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北京,23页。
⑦ ⑧ ⑨ ⑩ (11)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第1卷,20页、21页、24页。第17卷,297页。第16卷,6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