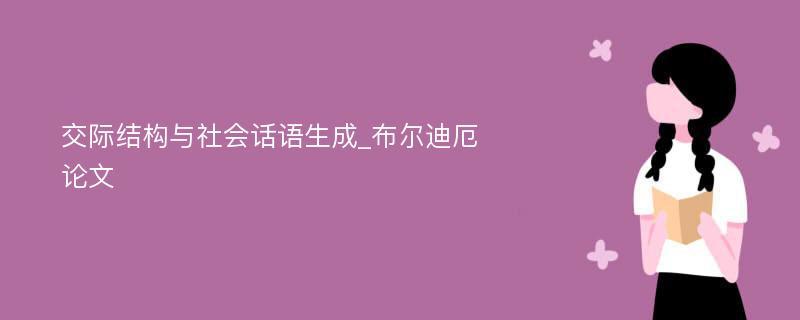
传播结构与社会话语生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论文,结构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22(2009)06-0007-3
传播结构体现的是社会话语生产的能力。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个体或组织,编织传播之网及对传播之网使用和选择的能力不同,他们完全有可能编织他们自己的社会传播网络,也会选择不同的传播之网。因此,只有那些具有较强的编织和使用能力的个人和组织,才会拥有更多的社会信息资源,他们也就能够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才会具有更强的社会话语的生产和掌控能力。所以,传播结构决定传播资本和传播能力,而这种传播结构的编织和使用的能力则主要体现为社会话语的生产。
传播结构首先表现为社会的关系模式。所谓传播结构,是人们在社会传播活动中的各种传播主体之间相对稳定的传播关系模式,以及由这种传播关系模式所决定的社会意义网络的构成。我们定义的这一概念之中,主要包含了三层含义:首先,关于传播主体。这里所指的各种传播主体,既可以是以个体为单位的,也可以是以组织为单位的主体构成。也就是说,传播主体是传播活动的社会行动者,它主要指的是处于社会意义网络中的信息意义的生产者、使用者及所有者。其次,关于传播关系模式,具体指的是在意义的生产、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构成,传播关系和社会关系是相互关联的问题,它们是意义关系在不同层面的具体体现。第三,传播结构主要体现为社会意义的构成。即由传播主体的关系模式所决定,并体现为社会共享的意义网络,其核心是社会话语的生产性特征。传播结构通过社会传播关系模式的构建,生产出社会的话语系统,从而影响传播形态的整合,进一步推动社会整体结构发生变迁。
传播关系模式体现了传播结构的实质。传播关系的本质,就是在传播过程中,传播的意义的生产与消费、交流与互动、编码与解码,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网络得以构建和确认的基本内在机制。所以,传播关系其实就是社会关系在符号象征意义构成层面上的具体体现。由此看来,传播关系的构成模式主要有两个决定因素,即传播的社会意义结构和社会结构关系。有学者就认为:“传播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是纵向的,也可能是横向的。它又是社会关系的体现,传受双方表述的内容和采用的姿态、措辞等,无不反映着各自的社会角色和地位。社会关系是人类传播的一个本质属性,通过传播,人们保持既有的社会关系并建立新的社会关系。”[1]人类传播的真正内涵,无非就是意义的碰撞、交流和构建的过程,在传播的意义构建之中,从而体现出人们对社会关系的确认。所以,传播结构首先就体现为社会的意义的生产,亦即社会的话语生产。
传播在社会结构中的主要功能,是建立影响人们的意识、观念和行为的文化符号系统,使人类达于文明进步的发展水平。在这一过程中,传播结构和社会结构系统互相协调,构筑人们的生活模式和社会关系。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必须处于特定的社会信息系统之中,才能实现与环境、社会相协调。传播结构通过话语生产,从而在社会系统中产生作用。因此,对传播结构探究核心问题,主要是要探究传播结构的社会话语的生产性,这一话语生产性特征则是在传播的动态实践中实现和完成的。
传播话语的生产是社会化的过程,它和社会运行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和谐发展的社会构建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传播活动作为社会协调运作的基本条件,在这一过程中,传播通过话语生产,起着调适社会的作用,这一调适与和谐状态的构建,是在社会现有的结构状态下完成和实现的。所以,依据功能主义的看法,社会话语的生产与社会现有的结构形式密切相关。
社会中的每一个分子都借助于传播以建立日常生活和行为的信息的联系,由联系而产生社会构成主体之间共享的意义,接受共同的意义符号法则,从而产生和谐的社会关系。显然,大众传播已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中重要的因素,对个人、社会、文化都有重要影响。现代化的社会,是一个具有高度应变机能的社会,各种社会利益集团都以一种均衡的状态向特定目标前进或发展,这种发展过程也称为“社会过程”。帕克与柏吉斯对社会过程的定义为“凡属团体生活的变动,均可称为社会过程。”具体而言,人类社会的动态或变迁,统称为社会化的过程。这种动态过程,包括突变、冲突、涵化、顺应、控制、分化等方式,社会过程则包括有五种不同方式:1、自我的内在互动;2、人与人的;3、个人与团体的或团体与个人的;4、团体与团体的;5、结构功能的过程。[2]传播活动在社会化过程中通过话语生产,建构了社会的不同关系模式。我们主要通过对话语生产的分析,重点探究传播结构的功能。
社会话语的生产首先建基于话语理论。在对话语的认识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评为中心),索绪尔、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以语言、文本为中心)以及后现代各种文化理论形成汇流,使话语成为当代文化与传媒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话语理论为当代文化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后现代的视角。葛兰西的“领导权”、福柯的“权力话语”、哈贝马斯的“合法化”、罗兰·巴特的“泛符号化”、鲍德里亚“仿像”等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话语理论,为研究媒介话语提供了理论基础。[3]当然,我们这里主要是在社会意义的构建层面使用“话语”这一概念,也就是说主要探究传播对社会意义的生产和制约。
根据话语理论,从传播的社会结构背景来考察话语生产,我们可以归纳出传播话语生产的三个基本影响因素:1、政治经济因素。传播结构对社会话语生产的影响,首先体现在政治、经济结构因素对传播结构的决定性作用,国家结构、经济结构都构成了传播话语生产的基础。2、社会组织因素。社会组织与话语生产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社会的不同组织、社会的不同阶层、社会不同职业群体等,都对传播结构和社会话语具有建构作用。3、文化制约因素。文化传统和文化符号体系,通过传播结构影响社会话语生产。由此,传播结构与社会话语生产之间表现为一种明确的建构关系。
在传播结构和社会话语的生产关系的探讨中,媒介框架理论作为媒介建构主义理论,对传播结构的话语建构问题,做了很好的解释。框架建构理论就是解释大众传媒如何建构社会现实的一种理论,大众传媒通过建构社会现实,亦即通过以一种可以预报的且形成格局的方式建构现实的镜像,从而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简言之,就是通过特定的、固有方式作为基本的架构,对现实世界进行秩序化和规范化,逻辑化和条理化,使我们能够明确地认识现实,其实在框架建构中就隐含着社会话语的生产。
框架理论源于社会学,在20世纪70到80年代引入到大众传播研究。框架的概念源自贝特森(Bateson),由戈夫曼(Goffman)将这个概念引入文化社会学,后来再被引入到大众传播研究中,成为了定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戈夫曼认为对一个人来说,真实的东西就是他或她对情景的定义。这种定义可分为条和框架。条是指活动的顺序,框架是指用来界定条的组织类型。对于信息传播活动的研究,戈夫曼也是放在框架分析的背景中进行的。不少著名学者,包括戈夫曼(E·Goffman)、吉特林(T·Gitlin)、加姆逊(W·A·Gamson)、恩特曼(R·M·Entman)等,均对框架概念有所阐述。他们所论的传播的“框架建构”,主要指的是传媒通过对有关某一事件、问题、现象的事实、细节、特点等的选择、强调和排除,形成传媒对事件、问题、现象的解释与思考结构,亦即框架(frame),这种框架在凸显某些事实、细节、特点等的同时,将被传媒视为无关紧要的东西排斥在外。[5]
框架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观思想的重要凭据,也就是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那么,框架本身又是如何建构的呢?研究认为,一方面是源自过去的经验,另一方面经常受到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同时,框架也是新闻的中心思想,它具有选择和凸显两个作用,也就是把认为需要的部分挑选出来,在报道中特别处理,以体现意义解释、归因推论、道德评估及处理方式的建议。在对新闻框架的形成因素的研究中,框架是新闻工作人员、消息来源、受众、社会情境之间的互动的结果。
美国传播学者吉特林指出,媒介框架使得超越直接经验之上的世界看起来更为自然,首先,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被描述的世界就是现实中的世界,许多事物都是客观存在的,任何时候,世界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即使在某一特定事物中,也有无限可察的具体细节。所以,媒介框架就是选择、强调和表达的原则,由很多对存在、发生和发展的事物加以解释的细微理论构成。在日常生活中,为了超越、控制、理解并选择恰当的认识和行为,我们建构了现实。媒介框架,很大程度是不可言说和超越认知的,为新闻记者和日益依赖于新闻报道的我们建构了世界。媒介框架是认知、解释和表达的连贯模式,是筛选、强调和排除新闻报道的过程。媒介框架保证记者们能快速、常规地处理大量的信息:对信息进行识别,纳入认知类别,然后进行包装,更有效地呈现给大众。因此,单从组织的角度来考虑,媒介框架是无法回避的,它能实现有组织地管理新闻生产。媒介框架通过整合传播结构,从而进行有效的社会话语生产。
对于传播结构与社会话语生产的关系问题,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分析路径。依据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我们就可以探究以意义构建为核心的传播结构的特质,进而也可探究话语生产的问题。吉登斯通过对“结构”、“系统”、“结构二重性”等核心概念内涵的分析,提出了“结构化理论”[7]。所谓的结构二重性,实际上强调的是结构本身的生产性和能动性的特征。
他首先认为,传统的理论对结构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在功能主义者(其实也是绝大多数社会研究者)的眼里,通常是把“结构”理解为社会关系或社会现象的某种“模式化”。他们经常幼稚地借助可视图像来理解结构,认为结构类似于某种有机体的骨骼系统或曰形态,或是某个建筑物的构架。而另一方面,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概念阐述中,结构的特性并不是在场的某种模式化,而是在场与不在场的相互交织,得从表面的现象中推断出潜在的符码。
因此,吉登斯指出,所谓的结构化理论中的“结构”,“指的是社会再生产过程里反复涉及到的规则与资源;我们说社会系统的制度化特性具有结构性特征,就是指各种关系已经在时空向度上稳定下来。我们可以抽象地把‘结构’概念理解为规则的两种性质,即规范性要素和表意性符码。而资源也具有两种类型: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前者源于对人类行动有活动的协调,后者则出自对物质产品或物质世界各个方面的控制。简而言之,所谓的结构,作为规则与资源,即是人的能动作用的先决条件,也是非预期的后果。这种结构的二重性体现的是什么呢?首先,结构是人们存在和利用的社会基础,这是其作为规则和资源的一面。其次,人们也在利用现有的结构进行着再生产活动。因此,吉登斯更强调的是结构本身的生产性和能动性,同时也强调了结构的实践性的特征,亦即结构的生成性和自我生成性的特征。
依据吉登斯的“社会结构二重性”理论,就传播结构来看,对于社会话语的生产问题,也体现了生产性和再生产的特征。那么,传播结构也就表现为两层模式:社会结构模式和社会话语生产模式。传播结构的实质是意义结构,传播关系的构建就是意义生产关系的构建。围绕意义的话语生产模式,传播结构关系大致有这样的模式构成:首先是传播特征,体现为虚拟的、不可见的、意向性的、预设的基本特征。其次是传播原则,即意义生产的业务流程现实操作层面的问题,具体为社会程式化的过程。其三为传播制度,即管理和控制层面的因素,具有特定的规定性的因素。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传播结构的基本模式,它也在生产和再生产社会话语,构建了社会传播及社会反馈的结构网络,并在其结构关系内部实现资源的互相转换。
传播结构的核心是传播形式决定的传播关系模式。那么,传播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体现形态,显然它是以社会的利益关系作为基础的。在社会的利益关系构建中,传播结构通过话语生产,传播营造了特定的“话语场”,这也就是布尔迪厄所谓的“新闻场”,因此我们还有必要分析布尔迪厄的新闻场域媒介理论。[8]
布尔迪厄针对传统的资本概念,提出“文化资本”的概念,这其实可以作为传播结构研究的基础性认识。在他看来,所谓文化资本,就是借助不同的教育行动如传播式教育、家庭教育、制度化教育等传递的文化物品。这其中他特别提到这些文化产品是在传播中存在的。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式:其一,是具体的形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如文化、教育、修养等的存在形式。其二,是客观的形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如图片、书籍、词典、工具、机器等形式存在。其三,是体制的状态,以一种客观化的形式,如学术资格的形式存在。从社会的传播结构意义上考察,那么,“文化资本”也可以看作是社会的传播结构的生产形式和生产结果。而社会传播结构与“文化资本”的生产性关系,是在布尔迪厄所说的“场域”中发生,正是这一“场域”中的权力角逐,影响传播结构的生成,而传播结构又决定文化资本的特征。
“场域”是布尔迪厄社会理论框架里一个颇为关键的空间性隐喻概念,关于“场域”中不同的权力运作的思考,是布尔迪厄论述社会结构关系的核心。结构性是“场域”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是争夺“合法性”的斗争场所。因此,“权力场域”是最重要的场域,权力场域中的基本冲突因素是对“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权力分配的争夺。[9]因此,“场域”概念的基础因素是多层面的社会关系网络,它始终处于各种力量胶着与角力的紧张状态之中,任何一个特定场域必须与权力场域结合起来考虑。那么,新闻场就是社会权力场域的一种形态构成。
新闻场亦即社会话语生产平台,它容纳并呈现政治、经济、科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等各种话语形式,根据自己的意图与模式给予改造,通过转换、移植、膨化、过滤等方式对这些话语进行再组织。在这个话语生产场中,市场与商业需要构成了生产的巨大动力,消费主义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其运行机制则是由政治、经济及文化等规范结构所决定的。在布尔迪厄看来,虽然世界上大多数传媒声称自己代表正义、公开、公正,传播真理。然而,这一陈述本身被看作是一套话语也许更为切实。布尔迪厄理出了这样一条制约关系的链条:经济场—新闻场—其他文化场。他认为,自身难以自主、牢牢受制于商业逻辑的新闻场直接受到了需求的支配,譬如节目收视率、广告份额等已然成为衡量媒体实力的主要指标,经济资本的数量将直接决定媒体在新闻场中占据象征资本的总数,而媒体一旦掌控了相当的象征资本,则意味着该媒介的符号权力/资本能够在大众文化生产过程中拥有不容小觑的话语号召力量,这是控制市场份额的前提,如此才能更好地吸引广告客户,捞取经济资本。新闻场,作为一个现实的关系网络存在,其内部经济资本与象征资本的共生关联与角逐游戏客观上造就了媒介实力等级。在这里,布尔迪厄分析的第二条基本思路是,新闻报道作为一个社会场域,除了通过收视率的作用和商业逻辑的运作保证了其场域他律性的特质,更重要的在于其本身作为一种场域结构的新闻媒体,一方面会反过来支配其他的社会场域,即以“同构(isomorphism)”的方式对所有其他场域实施控制力,同时也是社会权力场域的同构性再现。换而言之,社会的等级与冲突模式在新闻场中同样得到再生产,甚至可以视作为“社会阶级之间意识形态斗争的委婉形式”。[10]
新闻场域的结构性特征,其实正是我们所说的传播结构,而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角逐,也正体现了传播结构中社会话语生产的权力关系。因此,布尔迪厄认为新闻场域与政治场域最为接近。但是,在这个结构化的传播场域中,存在着深层次的传播结构,正是这个传播结构,决定了新闻场域中话语的生产方式。传播场域的结构化特征,也正是社会话语的意义的生产、理解和交流过程,最终也表现为“公共领域”的建构和公共话语权力的生产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