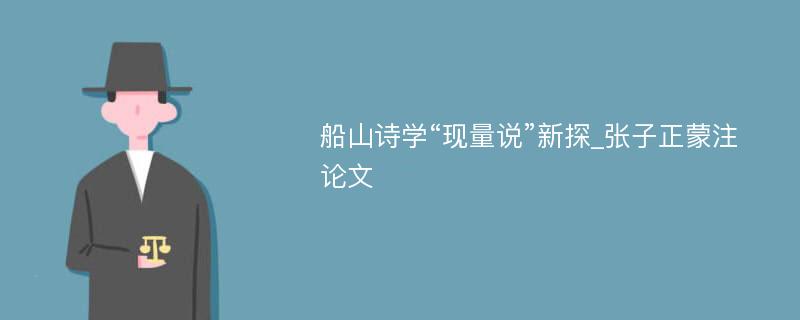
船山诗学“现量说”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量论文,诗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船山对诗歌的创作心理规律亦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他强调诗歌创作应该以“心目相取”、“情景相浃”为审美原则,诗人要善于“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既得物态,又得物理”。船山重视“不忖思度”的“寓目吟成”,反对脱离实际的苦吟和饾饤。为此,船山吸收并改造了相宗的某些理论,用之于诗学研究。关于诗创作的心理机制或心理特征,船山拈出“现量”二字加以说明,如:“禅家有三量,唯现量发光”。(注:《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如此之作,自是《野望》绝佳写景诗,只咏得现量分明,则以之怡神,以之寄怨。无所不可,方是摄兴观群怨于一炉锤,为风雅之合调”(注:《唐诗评选》卷三,杜甫《野望》评语)。但“现量”一词并非船山自己的语言,而是佛学用语。关于船山诗创作心理的美学思想,用船山自己的话来说,可概括为“心目相取”、“即景会心”等。正是鉴于船山在《姜斋诗话》和内部《诗评》中常常借用佛学“现量”这一术语来表达他的“心目相取”、“即景会心”的思想,故而学术界又将船山的诗创作心理学思想表述为“现量说”。有论者最早发现并研究了船山的这一重要理论(注:参见叶朗先生《中国美学史大纲》和肖驰先生《中国诗歌美学》有关章节),在船山诗论研究领域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论、诗学和美学史研究领域功不可设;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阐释上的失误,留下了一些研究的空白,有待再作分析。本文拟就船山“现量说”的美学内涵谈点新的看法。
一、船山对“现量”的误读或借用
“现量”本是印度佛学相宗(或称法相宗、唯识宗、瑜伽宗)宗派教义中的一个术语。相宗义理繁富,研究起来较为困难。船山晚年曾作《相宗络索》,意在贯穿包罗相宗的全部思想,使学者容易了解和摄持。关于《相宗络索》一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有人予以很高的评价,称:
船山先生关学巨匠,博学渊思,高行卓识,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文理密察的方法,独向相宗探求真理,辅之以高度的想象力和系统的组织力,遂将八识、四缘、三境、三量、三性、五受,乃至十二缘起、五位唯识、三种自性,最后转识成智诸种要义,襃集以为本书,使治儒学者对于心理现象、生命现象、认识实践皆能扩大其眼界,丰富其内容,这不能不说是在旧学中的一大进展。虽此书在当时并未曾发生大的影响,但吉羽灵光,终是希有可贵的。因之我们治船山学不可不读此书,治中国学术史也不可不治此书。(注:见王恩祥《相宗络索内容提要》一文,收入《船山全书》第十三册)
众所周知,晚明王学受禅学影响极深,而禅宗动辄呵祖骂佛,不立文字,标为简易。而船山对晚明王学或心学多有不满。在佛学众多宗派中,从义理的博大精深或学理的周密严整的角度来说,首推相宗,乃至可与禅宗形成佛学的二极。但也正因为此,相宗流传不广,几成中绝之学。船山研究相宗,未尝没有从佛学角度正本清源,既显禅宗之浅陋,又助他自己究天人之际之旨(或立通天尽人之志)。再联系晚清欧阳竟无、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等诸位大儒都曾深究佛学义理,谋求儒佛相通之处的事实,更可彰显船山研究相宗的初衷,皆可视为晚期中国封建社会思想家向西学(佛学)谋求真理的一种尝试。对船山与晚清诸儒探究佛理的比较研究,对于中国学术史研究来说,将是一件饶有兴趣和价值的事情,本文主旨不在此,故不做论列,点到为止。
当然,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相宗络索》一书在阐发相宗义理时,也有若干失误,不尽合于相宗的本意。究其原因在于,船山生活的年代,相宗的重要著述大多丧失沦亡,不象今人能遍睹从东邻取回的玄奘、窥基、圆测诸公之作。但即便此书与相宗间有违迕,也绝对不可求全责备于先哲。至于《相宗络索》一书是如何误读误解唯识宗本旨的,这或许对研究佛学很重要,但对我们研究船山的诗学和美学却无关宏旨。因为我们可以并且只需探讨船山视野里的(那怕是误读、误解的)相宗理论。据范文澜先生的意见,“法相宗以阐明‘万法唯识’、‘心外无法’为宗旨,亦名唯识宗。依唯识论所说,以为宇宙万有,都不过是由心识之动摇所现出之影像。内界外界,物质非物质,无一非唯识所变。而所谓能变识,有八种,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眼、耳、鼻、舌、身(触)是感觉器官,是认识的唯一源泉。唯识论称这五种感觉作用为前五识。另外又加一个叫做意识的第六识,这是杂乱无章的感觉,必待心的综合作用加以综合,才能成为知识,这叫做意识。它还说不清楚心外无法(事物)的无理之理,再加上一个叫做末那识的第七识。末那识意为自我本性的显现,站在自我本性后面的那种自我本体,叫做第八识,即阿赖耶识。末那识与阿赖耶识相互为因。阿赖耶识中藏有无量种子,以为一切识是由各自的种子为因,才得生起。一切物的现象,唯识论者说是心上的一种境相,是和心同起的。凡此境相,必自有物的种子为因,才得生起。物和识各有自己的种子, 由这些种子生起各自的果。 ”(注:范文澜《唐代佛教》第34—35页,人民出版社会1979年版)船山当然不接受唯识论的本体论思想,但从认识论和心理学的意义上,船山未尝不认为相宗理论有可取之处,例如所谓“八识论”、“三量论”等。由于我们感兴趣的是船山所阐述的相宗“现量”说,所以我们可径直来看看船山是如何阐述“现量”这一心理现象的。船山在《相宗络索》第六章论“三量”时有一段论述。
“现量”,现者,有现在义,有现成义,有显现真实义。现在,不缘过去作影。现成,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显现真实,乃彼之体性本自如此,显现无疑,不参虚妄。前五于尘境与根合时,即时如实觉知是现在本等色法,不待忖度,更无疑妄,纯是此量。第六唯于定中独头意识细细研究,极略极迥色法,乃真实理,一分现量。又同时意识与前五和合觉了实法,亦是一份现量。第七所执非理,无此量。第八则但末那妄执为量。第八本即如来藏,现量不立,何况比非。故《颂》但言性,不言境量。
“比量”,比者,以种种事,比度种种理。以相似比同,如以牛比兔,同时兽类;或以不相似比异,如以牛有角,比兔无角,遂得确信。此量于理无谬,而本等实相原不待比。此纯以意计分别而生。故唯六识有此。同时意识以前五所知相比,求得其理;散位、独头缘前所领受以证今法,亦多中理,皆属比量。前五不起计较。第七一向执持汙尘,坚信迷着,不起疑情,亦无此量。第八无量,前注己明。
“非量”,情有理无之妄想,执为我所,坚自印持,遂觉有此一量,若可凭可证。第七纯是此量。盖八识相分,乃无始熏习结成根身器界幻影种子,染汙真如,七识执以为量,此千差万错,画地成牢之本也。第六一分散位独头意识,忽起一念。便造成一龟毛兔角之前尘。一分梦中独头意识,一分乱意识,狂思所成,如今又妄想金银美色等,遂成意中现一可攘可窃之规模,及为甚喜甚忧惊怖病患所逼恼,见诸尘境,俱成颠倒。或缘前五根尘留着过去的影子,希冀再遇,能令彼物事倏尔现前,皆是第六一分非量。前五见色闻声等,不于青见黄、于钟作鼓想等,故不具此量。第八无量,准前可知。现量乃圆成实性显现影子,然犹非实性本量。比量是依他起性所成,非量是偏计性妄生。
《瑜伽论》三量外,有至教量,谓值佛出世,及恒住,所说一实至教,闻己生信,即以所闻至教为己识量。此量从根门入,与意识和合而成,亦三量所摄。若因闻至教,觉悟己性真实,与教契合,即现量。若从言句文身思量比度,遮非显是,即属比量。若即着文句起颠倒想,建立非法之法,即属非量。
“三量”是唯识宗所言之人的知识的三种状态或三种标准。船山所论是否完全合于唯识宗的原意,此不论。我们关心的是船山是怎么说的。上述引文中有部分为叶朗或肖驰先生所引用过。叶、肖二氏据此将“现量”释为“当前的直接感知而获得的知识。”(注: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第462 页),称船山所言的审美观照是“感觉器官接触客观景物时的直接感兴”(注: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第463页), 并认为“在王夫之看来,不仅审美认识是‘现量’,创作全过程也就是‘现量’。……这种执拗偏颇的观点,使人觉得他在重蹈王充文论的错误。”(注:肖驰:《中国诗歌美学》第93—94页)粗粗一看,叶、肖二氏所言似乎并没有什么大的失误,但其实他们忽视或回避了船山所言“现量”中所含有的第六识(即意识)与前五识“和合(相互作用)觉了”(把握事物真性实理)的涵义,也就是说忽视、回避了船山所论“现量”中实含有意识与前五识之关系的表达。因此,若只讲到船山“现量”说是对感性知觉经验的研究,则似乎未得要义。前面引文所提及的“现量”的两层含义在《相宗络索》第十八章论“六识五种”时,被船山再次详细阐述,可以见出船山其实是把意识中的两种现象亦归于“现量”,原文不长,兹引如下:
一、“定中独头意识”谓入定时缘至教量,及心地自发光明,见法中言语道断,细微之机及广大无边境界二者为实法中极略极迥之色法,与定中所现灵异实境显现在前。此意识不缘前五与五根五尘而孤起,故谓之独头。此识属性境、现量、善性。
……
三、“明了意识”即“同时意识”五识一起,此即奔赴与之和合,于彼根尘色法生取,分别爱取,既依前五现量实境,故得明了。初念属前五,后念即归第六。其如实明了者属性境、现量;增起分别违顺而当理者属比量;带彼前五所知非理蛮著者属非量、带质境。此识无独影境,三性皆通。
从船山这二段引文来看,船山把心学、禅学所言的“心地自发光明”之类也视为“现量”把“明了意识”或“同时意识”与前五识“和合觉了”、“如实明了”者亦视为“现量”。这两种“现量”一不缘外物,一要依外物,可分别视为唯心论与唯物论的两种直觉,但这两种直觉有一个共同点,即不等同于感知或知觉,而是与第六识相合而生,密切相关。所以,我们说,船山所言的现量(就唯物论意义上讲)乃是一种人的高级心理能力(第六识即意识)参与了的可以洞察事物本质(通过所谓“圆成实性,显现影子”的方式)的直觉能力,而不仅仅是人的五官感觉或知觉。
二、船山论人的五官与人的高级心理的关系
船山在《相宗络索》一书中所论“现量”也许显得有些混乱,不够明确、清晰。但是,如果我们将船山在其他著述论到同一话题时的材料综合起来,与此处对“现量”的论述合并起来看,那么,船山所要表达的真正意思还是相当显豁的。
船山一方面充分认识到五官感觉在人的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对人的感觉器官予以了较高的评价,如“视听之明,可以摄物。”(注:《张子正蒙注》卷四)“目遇之而成色,耳遇之而成声。”(注:《庄子解》卷六)“色、声、味之在天下,天下之故也。色、声、味之显天下,耳、目、口之所察也。”(注:《尚书引义》卷六)“由目辨色,色以五显;由耳审声,声以五殊;由口知味,味以五别。”(注:《张子正蒙注》卷四)船山充分承认人的五官之外的事物的客观实在性,同时又充分注意到人的五官感觉是万事万物得以彰显或显现的主观条件。人的五官“皆心所翕辟之牖”(注:《张子正蒙注》卷四)“耳与声合,目与色合,皆心翕辟之牖也,合故相知。”(注:《张子正蒙注》卷二)即是说人的五官感觉是人的认识得以发生的主观心理和生理前提。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到船山对于人的五官感觉在人类认识万事万物的过程中的基本作用的肯定。
但是,另一方面,船山又清醒地认识到人的五官感觉在认识客观外界万事万物过程中的局限性,这样的论述也比比皆是,如:“人之目力穷于微,……耳目之力穷于小。”(注:《张子正蒙注》卷二)“人所可见者形也,而就形以视之而不得。……人所可闻声也,而循声听之而不得。”(注:《张子正蒙注》卷一)“视之而见,听之而闻,则谓之有;目穷于视,耳穷于听,则谓之无。”(注:《四书训义》卷三)“有视眩而听荧者,则物夺其鉴也。物夺其鉴,而方视而蔽其聪。”(注:《张子正蒙注》卷九)等等。既然五官感觉有这么多局限性,那么,人又是如何达到对世界的认识的呢?为此船山引入了“心”或“神”等概念来说明这个问题。“心”或“神”是人的高级的理性认识能力,兼有先验的道德理性和认知理性的涵义,船山指出:“神者,所以感物之神而类应者也。”(注:《张子正蒙注》卷四)“心者,人道之所自立,动于心而感,人心无不格矣。”(注:《张子正蒙注》卷二)“以目视者浅,以心视者长。”(注:《礼记章句·乐记篇》)有了“心”或“神”的参与,认识活动就可克服和超越五官把握的局限性。
对于“心”与“五官”的关系,船山也有很好的表述,即“一身之要,居要者心也。而心之神明,散寄于五藏,待感于五官。”(注:《古诗评选》卷四。)“以其心贞其耳目,以其耳目生其心。”(注:《尚书引义》卷六)“是故心者即目之内景,耳之内牖,貌之内镜,言之内钥。合其所分,斯以谓合。……盖貌、言、视、听,分以成官,而思为君,会通乎四事以行其典礼。”(注:《诗广传》卷三)既指出了以五官感知启发心神,又强调了以心神引导感性认识。也即是说,人对外物的认识、把握,有赖人的五官感觉与高级的抽象思维或形象思维能力的协同作用。
关于人的认识活动的一般心理过程,船山亦有精彩的见解:
物与目视,目与心谕,而固然者如斯。(注:《尚书引义》卷四)
遥而望之得其象,进而瞩之得其质,凝而睇之然后得其真,密而睽之然后得其情。劳吾往者不一,皆心先注于目,而后目往交于彼。不然,则锦绮之炫煌,施、嫱之冶丽,亦物自物而己自己,未尝不待吾审而遽入吾中者也。(注:《周易外传》卷七)
由于引入了“心”或“神”这个概念,由于有了“心”或“神”的统摄与提升,人的认识因而具有极大的能动性,对此,船山亦多有精辟论述,如:“形则限于其材,故耳目虽灵,而目不能听,耳不能视。且闻见之知,止于己见己闻而穷于所以然之理。神则内周贯于五官,外泛应于万物,不可见闻之理,无不烛焉。……耳目从心,则大而能化。”(注:《尚书引义》卷一。船山亦云:“耳有聪,目有明,心思有睿知,入天下之声色而研其理,人之道也,聪必历于声而始辨,明必择于色而始晰,心出思而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岂蓦然有闻,瞥然有见,心不待思,洞洞辉辉,如萤乍曜之得为生知哉!”(《读四书大全说》卷七)。)“唯心之神,彻于六合,周于百世。所存在此,则犹旷窅之虚,空洞之籁,无所碍而风声达矣。”(注:《四书训义》卷三)“风雷无形而有象,心无象而有觉,故一举念而千里之境事现于俄顷,速于风雷矣。”(注:《张子正蒙注》卷一)
总之,船山认为,人的五官感觉对外界事物的认识有着不可忽视的局限性,只能把握那些看得见、听得到的东西,而对耳目所难以把握的“大象无形”、“大音希声”之类的微妙之物则无能为力;并且在人的生理心理出现异常时,耳目甚至会出现“眩视”和“荧听”,为事物的假象所迷惑。万事万物的“霏微蜿蜒”的“不可见闻之理”是人的耳目所难以把握的,只能诉诸人的高级的心理能力,船山称之为“尽心思以穷神知化”(注:《四书训义》卷三),“有至诚之性在形中而尽之,则知神之妙万物”(注:《张子正蒙注》卷一),“循物丧己者,拘耳目以取声色,……存神,则贯通万理曲尽其过化之用。”(注:《张子正蒙注》卷二;《张子正蒙注》卷九)质言之,船山认为,局限于五官感觉,并不能真正全面真实深刻地把握万事万物;人的认识要真正把握外界事物,必须有人的高级心理能力(“心思”或“神”)的参与。具体地说,人们对外界万事万物的认识,无一不是五官与心思(或心之“神”)协同作用的产物,即便是五官感觉,也有心思、心神的参与(或贯注、统摄、贯通)。即所谓“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觉乃发”;并且,“心”在人的精神活动中占有主导地位。正因为此,船山甚至提出了“诗者象其心”的诗学命题:“视而不可见之色,听而不可闻之声,抟而不可得之象,霏微蜿蜒,漠而灵,虚而实,天之命也,人之神也。命以心通,神以心栖,故《诗》者象其心而已矣。(注:《张子正蒙注》卷一)
以上所引材料遍及船山的许多著作,把这些言论中所表现出来的观点与船山在《相宗络索》中论“现量”的文字加以对照,就可明白为什么船山把第六识(意识)中之两种心理活动也归入“现量”,即前文所征引之“第六唯于定中独头意识细细研究,极略极迥色法,乃真实理,一分是现量。又同时意识与前五和合觉了实法,亦是一分现量”,所论虽不尽合于唯识宗之本义,却有极可取的心理学思想,即“现量”不等于前五识,“现量”亦有第六识的参与(灌注或贯通),是五官和意识的和合、协同作用,只不过这种和合、协同作用不是以逻辑推理或精神病人似的幻觉的方式(即比、非二量),而以直觉思维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已。
三、诗学之“现量”亦称“心目”或“以心目相取”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船山在其诗学著作中论诗美的创造时,喜欢用“心目”这一概念或“心”与“目”连用?原来,“心目”指的就是审美直觉,也就是“现量”。如:
即如迎头四句,大似无端,而安顿之妙,天与之自然。无广目细心者,但赏其幽艳而已。……天壤之景物,作者之心目,如是灵心巧手,磕着即凑,岂即烦其踌蹰哉!(注:《诗广传》卷五)
写景至处,但令与心目不相睽离,则无穷之情,正从此生。(注:《古诗评选》卷五)
“池塘生春草”,“蝴蝶飞南圆”,“明月照积雪”,皆心中目中相与融浃,一出语时,即得珠圆玉润,要亦各视其所怀来而与景相迎者也。(注:《古诗评选》卷五)
语有全不及情,而情自无限者,心目为政,不恃外物故也。“天际识归舟,云间辨江树”,隐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从此写景,乃为活景,故人胸中无丘壑,眼底无性情,虽读尽天下书,不能道一句。(注:《夕堂永日绪论内编》)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自然是登岳阳楼诗。尝没身作杜陵凭轩远望观,则心目中二语居然出现,此亦情中景也。”(注:《古诗评选》卷五)
只于心目相取处得景得句,乃为朝气,乃为神笔,景尽意止,意尽言息,不必强括狂搜,舍有而寻无,在章成章,在句成句。文章之道,音乐之理,尽于斯矣。(注:《姜斋诗话·夕堂永日绪论内编》)
此外,在船山的几部诗学著作中,用了“心目”这一术语或“心”、“目”连用者还有二十余处,为避免读者生厌,兹不一一罗列。笔者以为,船山在《诗话》、《诗评》中频频提到的“以心目相取”、“心目为政”之类决不是“感觉经验”或“感知经验”几个字可以了得,可以说清楚。“心目”即是对诗创作过程中审美直觉规律的揭示,这是船山自己的语言;而“现量”则是船山借用的相宗的语言。“现量”也就是“以心目相取”或“心目为政”。“现量”是心与目的协同作用,只是在协同作用时心与目相合,即意识融化于感性知觉之中而已。它不是单纯的感觉,更不是抽象独立的逻辑思维,也不是感觉与思维的简单相加。有时,船山即便是单独使用“眼”或“目”字,也不能简单地释为相宗所谓前五识的感觉经验,如:“日落云傍开,风来望叶回”,亦固然之景,道出得来曾有,所谓眼前光景者此耳。所云‘眼’者,亦问其何如眼。若俗子肉眼,大不出寻丈,粗欲如牛目,所取之景,亦何堪向人道出?”(注:《古诗评选》卷六)显然,这里的“眼”或“目”不可简单释为五官中的视觉,而应理解为诗人审美人格心理倾向支配下的审美情境注意,仍是诗人的心与目的协同作用。
明乎此,我们则可以重读一遍《夕堂永日隋论内编》中常常为人们所征引的两段著名的论述:
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即极写大景,如“阴晴众壑殊”,“乾坤日夜浮”,亦必不逾此限。非按舆地图便可云“平野入青徐”也,抑登楼所得见者耳。隔垣听演杂剧,可闻其歌,不见其舞;更远则但闻鼓声,而可云所演何出乎?前有齐梁,后有晚唐及宋人,皆欺心以炫巧。有意思的是,作者在讲完“身之所历,目之所见”即讲了“见”“闻”之重要性之后,紧接着就是批评“前有齐梁,后有晚唐及宋人,皆欺心以炫巧”,仍是“目”与“心”连用。这里的“心”当然不是单纯的“见”“闻”,而是诗人的思想感情,故这则材料仍是强调心与目之结合,强调诗人以心目相取的亲身经历的审美经验之重要。这条被人常引用的材料与前面所说的“现量”说仍是一致的。”
“僧敲月下门”,只是妄想揣摩,如说他人梦,纵令形容酷似,何尝毫发关心?知然者,以其沉吟“推”“敲”二字,就他作想也。若即景会心,则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因情,自然灵妙,何劳拟议哉?“长河落日圆”,初无定景;“隔水问樵夫”,初非想得:则禅家所谓“现量”也。
船山在这里批评了单纯的“形似”或单纯的以目相取而不是以心目相取(“纵令形容酷似,何尝毫发关心?”),肯定了“即景会心”“因景因情”的创作态度或创作心理,并明确称这就相当于禅家所谓的“现量”。可见,“现量”除可表述为“以心目相取”及“心目为政”之外,还可表述为“即景会心”、“因景因情”。对此,童庆炳先生有精辟分析。童先生认为,船山的“即景会心”说或“现量”说是中国古典诗学中对艺术直觉的最完整、最明确的表述,并指出:
“即景”就是直观景物,是指诗人对事物外在形态的观照,是感性把握;“会心”,是心领神会,是指诗人对事物的内在意蕴的领悟,是理性的把握。“即景会心”就是在直观景物的一瞬间,景(外在的)生情(内在的),情寓景,实现了形态与意味、形与神、感性与理性的完整的同时的统一。(注:童庆炳:《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第71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明乎此,我们还可以重读一下《诗广传》卷二中经常为人们所征引的一段著名的论述:
天地之际,新故之迹,荣落之观,流止之几,欣厌之色,形于吾心以外者化也,生于吾身以内者心也;而浡然兴矣。“有敦瓜苦,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俯仰之间,几必通也,天化人心之所为绍也。
这段话里所提到了“新故之迹”、“荣落之观”、“欣厌之色”,这些姑且可以说是诗人于俯仰之际以目相取的(笔者之所以暂且称之为“以目相取”,是因为船山其实并不称道或不承认这种简单的“目视”),但是,“流止之几”的“几”,却绝对不是单纯的“目视”可以把握的。船山几乎无数次地提到“几”这个字,如“几者,动之微”。几者,微妙之物也。要把握这种微妙之几,不能单止于事物的表象,而要透过表象直达本质,即通过心与目的协同作用,调动诗人的感知、情感、想象、理解等各种心理功能,才能把握事物间微妙的内在联系。船山在这里所举的《诗经·幽风·东山》中的四句诗亦可说明这个道理。诗中“瓜苦”即苦瓜,乃征人与其妻的结婚纪念物,而今久弃在栗薪之上。因此征人之妻(思妇)于“俯仰之间”见此苦瓜,自然触景生情,不胜思念之悲苦。可见,这里的“俯仰之间,几必通也”,也是“心目相取”、“会景生心”的含义,也即是船山所说的“现量”。但船山在这里没有用“现量”一词,而是称之为“浡然兴矣”。这也说明,“现量”应包含有“兴”的意义,或曰“兴”是“现量”的题中之义。
如前所述,所谓“现量”,是佛学术语,即指那种一触即发、不假思索、通过直觉活动直接穿透事物底蕴的心理能力。在船山诗学中,“现量”亦称“即景会心”,“即景”是诗人面对眼前的客观事物进行审美观照。“会心”指诗人在进行审美观照时同时就把握了事物的内在审美意蕴,也就是船山在《相宗络索》中所说的“同时意识与前五(识)和合觉了实法”,也就是《诗广传》所说的“浡然兴矣”之兴,触物而起情之兴。它是一种无需逻辑推理过程,径直地刹那间地把握对象审美底蕴的心理活动。船山以“现量”喻审美直觉,与严羽以禅喻诗是同一种思路,但比严羽说得更好、更清晰,避免了严羽“妙悟说”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
船山在《夕堂永日绪论外编》称“燕、许、高、岑、李、杜、储、王所传诗,皆仕宦后所作,阅物多,得景大,取精宏,寄意远”,其中的“取精宏,寄意远”,就是说他们的诗歌作品较广阔、深刻地表现了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并寄寓着深远的社会意义。这决非单纯的感知所能把握,而只能依靠一种“心目相取”“即景会心”的比较高级的审美心理功能才得以领悟。这也说明“现量”不等于感知,“现量”实为一种诗性的直觉智慧。
综上所述,“现量”不是简单地等同于感觉、感知,而是“心目相取”、“即景会心”、“几与为通”、“浡然兴矣”,它既综合了钟嵘的“直寻”论,又综合了严羽等人的“妙语”说,具有比单纯的“直寻”或“妙悟”更为丰富的内涵,是作为哲学家、诗论家兼诗人的王船山对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经验(或曰审美心理规律)的一种更为科学的揭示,既坚持了唯物主义认识论,又深刻地把握了古典诗歌创作的特殊审美心理(即审美直觉)的内在规律;同时又摒弃了佛学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因素。因此,“现量说”实为在强调“身历目见”的基础上对钟嵘、严羽等人诗学观念的吸收、改造和超越,在中国诗学史和美学史上带有总结意义。
四、论“现量”——审美直觉的特点
如果说船山在《相宗络索》中所提到的“现量”三义,姑且可称之为船山对现量的定义;但借用到诗学研究中后,不如说是船山对审美直觉心理特征、心理属性的分析描述。易言之,在船山看来,诗人创作过程中的“现量”(或曰“心目相取”、“即景会心”、“几与为通”、“浡然兴矣”)有三个基本特征,即①当下直接性;②瞬间突发性(非逻辑推论性);③真实完整性。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船山对“现量”的解释:
“现量”,“现”者,有“现在”义,有“现成”义,有“显现真实”义。“现在”,不缘过去作影;“现成”,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显现真实”,乃彼之体性本自如此,显现无疑,不参虚妄。(注:《相宗络索·三量》)
船山在这里所说的“现量”的三层含义,虽有细微的区别,但其共同的、中心的意思还是强调“现量”乃是直觉性观照。正因为此,船山才将其借用到诗学研究中来,用来说明诗创作中审美直觉的心理特征。综合船山在《诗话》、《诗评》中的论述,再参之以这里对“现量”的解释描述,我们可以将船山所揭示的审美直觉的心理特征归纳为三点:
其一,所谓“现成”义,即是强调诗人在创作时应当“即景会心”、“因景因情”而作,而不能脱离眼前实景,脱离对当下的审美对象的审美观照。船山所津津乐道的“池塘生春草”、“蝴蝶飞南园”等名句无一不是诗人心目与当前实景相值相取而相融浃的产物。船山在《古诗评选》卷六中评陈后主《望高台》一诗中亦说:“‘日落云傍开,风来望叶回。’亦固然之景,……所谓眼前光景者此耳。”强调的仍是审美观照所直接把握的感性事物的形象。可见,现量或审美直觉的第一个特征即是它的当下直接性。
其二。所谓“现在”义,即是强调诗人的感兴或兴会是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排斥逻辑推论的,因此,诗人在创作时要善于捕捉突如其来的灵感;因为“天籁之发因于俄顷”,灵感到来进,倏忽而起,瞬间即息,无须苦吟,不待忖度。船山所推崇的“长河落日圆”、“隔水憔夫”等正是这种无须拟议、不待忖度的自然灵妙之作。而船山所批评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一类诗句,因为用了比较级副词“逾”“更”,这在船山看来已属“比量”而非“现量”,故而船山对其评价不高。他明确指出:“以追光蹑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是诗家正法眼藏。(注:《古诗评选》卷四。)所谓“追光蹑影之笔”,当然指善于描写一触即发的即兴之景的笔法(当然还不止于此)。此类的论述还甚多,如“天壤之景物,作者之心目,如是灵心巧手,磕着即凑,岂复烦其踌踌哉?”(注:《古诗评选》卷五)“笔授心传之际,殆天巧偶发,岂数觏哉?”(注:《古诗评选》卷四。)“一用兴会,标举成诗,自然情景俱到”。这样创作出来的诗歌,自然是珠圆玉润之作。可见,“现量”或审美直觉的第二个特征是它的瞬间突发性。另,船山对王维诗评价极高,原因之一,也就是欣赏他心灵巧手,善写“寅成”:“辋川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此二者同一风味,故得水乳调和,俱是造未造、化未化之前,因现量而出之。一觅巴鼻,鹞子即过新罗国去矣。”(注:《姜斋诗集·雁字诗·题芦雁句序》)“巴鼻”即根据、由来。觅巴鼻,即船山所批评的拟议、思量、忖度、踌躇、计较和比较等。王维的诗妙就妙在灵心手巧,即兴而作,因现量而出之;而不是那种费尽心思苦吟而得来的。这些都表明现量或审美直觉的瞬间突发性或非逻辑推论性。
其三,所谓“显现真实”义,即强调诗人在创作时要忠实于自己对审美对象的真切完整的审美经验,而不要破坏这种审美经验。正如他在《古诗评选》中所云:“两间之固有者自然之华,因流动生变而成其绮丽。心目之所及,文情赴之,貌其本荣,如存而显之,即以华奕照耀,动人无际矣。古人以此被之吟咏,而神采即绝,后人惊其艳,而不循质以求……何当彼情形而曲加影响?”(注:《古诗评选》卷五)。这段话的含义非常明晰而又深刻,船山强调的是诗人应该通过“心目相取”,把审美对象作为一个完整的审美存在真实完整地加以把握并加以表现,而不能以个人的主观意志妄加判断或曲加影响,割裂美的生动性和完整性。可见,审美直觉或“现量”的第三个特征是它的真实完整性。“显现真实”的另一层含义还有《诗译》中所说的“既得物态”,“又得物理”’或“内极才情,外周物理”。“现量”的这种真实完整性颇近似西方现代学美学所讲的“直观”或格式塔心理美学所讲的对知觉对象完形的把握。
船山之所以重视“即景会心”、“心目相取”、“俯仰之间,几与为通”“浡然兴矣”的“现量”或审美直觉在诗创作中独特的重要作用,除了出于他对审美意象(情景相生相融)的创造规律的深刻认识之外,也是与他的“诗道性情说”的诗学本体论有关。船山认为,诗与其他意识形态(史或学术等)不同,重要原因就是诗创作必须“因现量而出之”,即“兴为枢机”。这与那种以议论、说理、考据、记实、叙事等等为主的历史(史籍)、典册、简牍、训诂文章迥然不同。由此可见出船山论诗的一贯性以及理论上的严密严整性,这也是作为哲学家兼诗人的船山高于一般诗评家的卓越之处。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用船山本人一段精彩之论总结、概括船山“现量”说的全部内涵,即人们常常称引的:“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则自有灵通之句,参化工之妙。”(注:《夕堂永日绪论内编》)“现量”说的提出,不仅是对皎然、贾岛之流苦吟的不以为然,更是对脱离实际生活而一味拟古、掉入古人书袋中的宋人和明人诗风的拨乱反正,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当然,“现量”说也不同于晚明李贽和竟陵派等人的创作路数,它除了比竟陵派强调现实生活的极端重要性之外,又比李贽更重视“心”、“神”、“理”等在创作心理活动中的地位。船山的现量说的诗创作心理研究,是中国古代诗创作心理研究的一个集大成式的深刻总结。如前所述,“现量”说兼综、改造和超越了前人的“应感之会”(陆机)、“直寻”(钟嵘)和“妙语”(严羽)等理论全部合理的美学内涵,成为船山诗学美学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并在中国古典诗学创作论研究史上独树一帜,至今仍显示出独特的魅力和精深的当代学术价值。
来稿日期:99—9—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