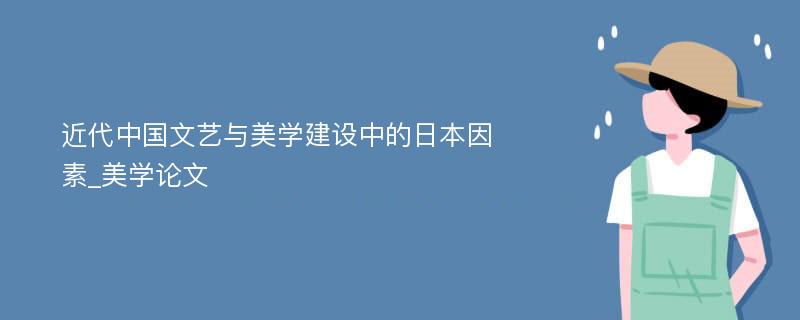
中国现代文艺学、美学学科确立中的日本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日本论文,美学论文,中国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179(2008)04-0149-07
日本近现代文艺学、美学对中国文艺学、美学的影响,具有当初西方对日本的同类影响的几乎全部特征。这种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给予中国美学、文艺学一个学科的名称,更重要的是在基本的范畴、概念、术语及文艺、审美观念和学科体系、方法论等学科构成的奠基性、根本性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种巨大影响成就了20世纪中国文艺学、美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结构性特征,形成了中国文艺学、美学的内在发展理路,表征为中国文艺学、美学现代形态的发生和发展。
一、范畴、概念、术语的输入
综观我们今天文艺学、美学中使用的一套规范的范畴、概念、术语,大部分是从日本移植而来。而日本的现代日语词汇,绝大部分又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在翻译西文书籍时创造出来的。在近代中国,特别是清末民初,伴随着西学东渐的展开,大批反映西学内容的新词语涌入中国。对此国学大师王国维有深入的认识:“近代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之是已。”[1](P111)王国维的“文学”当是就广义而言的文化。
王国维不仅在理论上倡导引进新学语,而且也在文艺实践中切实履行之。以《〈红楼梦〉评论》为例。《〈红楼梦〉评论》中不仅已经出现了“自律”、“他律”等西方文艺学术语,而且通篇运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美学观点和学术话语来评论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作《红楼梦》,第一次破天荒地将“悲剧”作为一种范畴从西方输入中国,用西方现代观念来观照中国古典文学,成为近代中国引进欧西新学语、开风气之先的少有先驱者之一。而诸如“自律”、“他律”、“悲剧”等概念、范畴,王国维又不是直接从西方引进的,而是通过在日本接触到叔本华的哲学美学理论而间接引进中国的。实际上,这种间接引进的方式已经成为王国维及当时许多学者介绍新概念、新术语的基本方式。王国维曾经引进并使用过的文论和美学领域的词汇,还有下面一些:“美学”、“美术”、“艺术”、“纯文学”、“纯粹美术”、“艺术之美”、“自然之美”、“优美”、“宏状”、“高尚”、“感情”、“想象”、“形式”、“抒情”、“叙事”、“欲望”、“游戏”、“消遣”、“发泄”、“解脱”、“能动”、“受动”、“目的”、“手段”、“价值”、“独立之价值”、“天才”、“超人”、“直观”、“顿悟”、“创造”、“现象”、“意志”、“人生主观”、“人生客观”、“自然主义”、“实践理性”等。这些术语,其中当然也有王国维的天才独创,少量或出自对传统美学观念的转化,但主要的则是经由日本从欧美转译,进而用日语书写的。它们作为区别于传统文论和美学的“自治”观念,而重在强调现代“他治”观念的文论话语,流传至今,成为当代美学、文学理论界经常使用的基本术语,也是中国现代文论话语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坛巨擘梁启超,在输入新的文论话语方面,也堪称楷模。梁启超所输入并使用过的文论概念、术语,大致有以下一些:“国民”、“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新文体”、“新小说”、“写实派”、“理想派”、“浪漫派”、“情感”,以及后期的“象征派”、“文学的本质和作用”等。且不论梁启超的文学观、美学观如何,单单就他所引进的这些新的学术语汇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为当代文论家、美学家乃至众多文化人士笔书口传,梁启超的发轫之功便足可与日月同辉了。其他如“新感觉派”、“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派别名称,“真实”、“反应”、“表现”、“再现”、“形象”、“典型”、“个性”、“环境”、“本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优美”、“崇高”、“悲剧”、“喜剧”、“直觉”、“理性”、“内容”、“斗争文学”、“自然生长”、“目的意识”等文论和美学术语,也肇始于此新学语之输入浪潮。据陈慧、黄宏熙主编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世界文学术语大词典》统计,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引进文学术语2018个,其中文论术语533个,光常用的就有126个,其数量之巨着实惊人。
语言不仅仅是工具,同时也是思想本体。语言不光作为文章内容的形式载体和外壳而存在,而且作为文章的精神意蕴的显在表征而存在。现代语言学认为,语言的所有最为纤细的根茎生长在民族历史文化与现实中,一个民族怎样思维,就怎样说话,语言中存留着无数种族文化历史与现实的踪迹,它是种族文化历史与现实的直接呈示。一种语言就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范式。来自或转自日语的新的语词、概念、术语,为中国思想界摆脱“之乎者也”的吟唱模式,确立新的文体,提供了新的符号载体,从而为当时译介日本和西方作品提供了方便。更重要的是,随着新语词而来的日本和西方新的思想传入中国,使中国的文体为之遽变,新文体获得了真正的现代性品格,为当时特别是后来的现代文学写作提供了方便,成为现代文学创作的基本语汇。正如实藤惠秀所指出的:“中国因为流行着广含日本词汇的翻译及掺入日本词汇的新作,所以中国的文章体裁产生了明显的变化。”[2](P291)
这种情况也引起了一些旧人物包括极个别留学生的不满。1915年,留日学生彭文祖就将这些从日语借用过来的词汇讥刺为“盲人瞎马之新名词”,大声疾呼要慎用新名词,否则会导致“亡国灭种”的严重后果。尽管这些反对者是从民族感情出发,或者是基于维护汉语纯洁性的考虑,也有其合情合理的一面。然而,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交合的过程中,外来词汇,包括日语词汇的引入,已经形成了难以驾驭的大趋势。客观地看,近代的那些译著一开始就在为中日文论关系逆转做准备,或者说,在中日文论关系发生逆转之前,它们就从词汇的角度作用、影响于中国文论。究其实质,则在于中国传统学术在理论思维方面存在不足,有必要向西方学习形而上的理论思维方式,以改造中国固有的思维方式。中国现代文艺学、美学之所以能够成就如今这样丰富浩繁、难以计量的词汇之海,正是在一开始就不拒绝、不排斥从多方吸纳养分的结果。
二、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和确立
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方法与观念、理论体系是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美学现代转型的过程,同时也是独有的、新的、科学的方法的寻找和确立的过程。方法论对于美学现代转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论,如《典论·论文》、《文赋》、《文选》、《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等,其文学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一脉相承,往往按照从大到小,由普遍到特殊的顺序,先论大道再论文道。这种思路与现代的“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思路相距甚远。后者具体到文艺研究领域,就是先把文艺研究对象从各种复杂关系中隔离出来,给它一个定义,划定它的边界,再细加解剖,将各种因素拆开,向专门化的空间深入拓展。
时代发展到20世纪初,尽管西方的文艺学已经进入中国文人的视野,但其问题框架和概念还没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光亮依然遥不可及。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方法》还在传统的问题域中思考问题。林琴南的《春觉斋论文》仍然不离“论文十忌”、“用笔八则”、“用字四法”等老一套的文章做法。1925年,马宗霍的《文学概论》出版。由于引入了许多外国学术资源如厨川白村、温彻斯特等的观点,不但在“流派”一章中加入了词曲、小说的派别,使“文学”一词的外延远离传统而更接近现代,而且于全书的纲目划分上,也更接近现代体制。如在“绪论”中讲文学界说、起源、特质、功能;在“本论”中论文学的门类、体裁、流派、法度、内象、外象、材料、精神。从文学本身的界定到特质的分析,再到内外关系的辨析,都是一些现代文论的问题。
然而,现代中国出版的最早的文论却都是从日本引进的。如今可查的第一本以《文学概论》为名的书是1921年由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贸易部出版的,著者为伦达如。实际上全书都是根据日本文论家大田善男的《文学概论》编辑而成。全书两编,上编为“总论”,介绍文学、艺术的基本原理,下编“各论”,分介诗歌、杂文等文体。此书突出特点是推重“纯文学”观念,单从目录即可看出这是一本现代形态的文学理论教材。不过由于多方面原因,此书出版后似乎并未产生多大影响。
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小泉八云、本间久雄和厨川白村。小泉八云是日本籍欧洲人。作为散文家的小泉八云兼具西方人缜密的理论思维和日本人敏锐的感受、细腻的表达,孕育出印象式、鉴赏式的偏重个人感受的批评方式,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感悟评点的批评方式而更科学更理性,与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京派”批评相通。小泉八云运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殊重要的贡献。
本间久雄的《文学概论》和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译文都是先在杂志上发表,然后出版。后者由鲁迅翻译,发表于1924年10月1日到31日的《晨报副刊》,出版于1924年的新潮社。前者由汪馥泉翻译,连载于1924年6月1日到24日的《觉悟》,出版于1925年的上海书店,后由东亚图书馆1930年新版。汪馥泉的译本虽然不属于“名译”,但由于本间久雄的著作本身体系严密,内容翔实,不但出现了重译本、订正本,再版次数甚而累计达六次之多。章锡琛重译本还被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可见该书颇受中国学人重视。事实上,那时国人撰写的同类著作很多都是在摘抄它的内容,乃至例证都一模一样。就研究方法来说,该书也是以现代文艺研究方法为指导的。全书四编,第一编“文学的本质”,分述文学的定义、性质、美的情绪及想象、文学与个性、文学与形式。其中对文学特质的确定来自于对科学和文学界限的划分,采用的是德·昆西(De Quince)区分“知识的文学”与“力的文学”的说法,将文学的特质划定为“通过想象及情感而诉诸读者的想象及情感”。[3](P16)第二编“为社会的现象的文学”,介绍文学的起源、文学与时代、国民性、道德的相互关系。第三编“文学各论”,分述诗、戏曲、小说等各类文学体裁。第四编“文学批评论”,也是采用由普遍到特殊的思维方式,先泛论批评,再分别辨析客观的批评和主观的批评、科学的批评与新裁断的批评。总览全书,明显是按照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结构全篇的。
《苦闷的象征》和厨川白村的另一部深刻影响中国文论界的《文艺思潮论》一起,也为中国确立文艺学、美学的现代科学方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厨川白村写作《文艺思潮论》,其目的就是采用科学方法对西洋文学作系统的、科学的研究。他在序论中说得非常明白:“讲到西洋文艺系统的研究,则其第一步,当先说明近世一切文艺所要求的历史的发展——即奔流于文艺根底的思潮,其源系来自何处,到了今日经过了怎样的变迁;现代文艺的主潮,当加以怎样的历史的解释。关于这几点,我想竭力地加以首尾一贯的综合的说明:这便是本书的目的。”[4](P102)《文艺思潮论》仿照罗斯金(Ruskin)的一代名著《近代画论家》(Modern Painters)所用方法,富于诗情与趣味,且井然有序,论理正确,着重叙述了欧洲的两大思潮的演进、矛盾与交流。
在域外现代文学观念的影响和启发下,中国学人一直将科学的文论的建构,同时也是把运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文艺,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因而寻求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一直伴随着现代文论的始终。五四时期对“科学”的信仰多指向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相应的,对文艺的科学认识即意味着将科学研究的观察、归纳、演绎等原则应用到文学研究上,甚至误以文艺为科学研究的工具和手段。随着观念的日益清晰,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科学与文艺是相异甚至相反的。科学应理解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真正与文艺切近的不是自然科学,而是社会科学。而文艺研究又确实需要一种与传统感悟式或评论式不同的更符合现代学术形式的研究方法。
可喜的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科学思想勃兴的时代,社会科学方法介入原来相对自足封闭的人文科学领域已形成潮流。首先是在西方,以社会学方法研究文学、艺术的尝试逐渐多起来。接着,开国迎西的日本借地利之便率先在东方加以应用。中国的陈北鸥和张希之等马克思主义者凭借敏锐的学术眼光很快捕捉到了日本文艺界这种新的发展动向,将其介绍到中国。1932年,北平立达书局出版陈北鸥的《新文学概论》。该书强调研究文学必须采用社会科学方法,要“应用唯物论的见地确定文学的观念”。张希之的《文学概论》(1933年北平文化学社)对唯物史观的信仰和依赖则更加明显,曾提出以“辩证法唯物论”为文学研究的基本立场,认为文学并非孤立的,应着眼其联系的机构;文学也非固定的,要在历史中理解;文学是“矛盾斗争”的产物,文学的发展阶段相衔接,既有同一性又有特殊性。这种文学研究和认识的方法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30年代之后文论的面貌,也就是马列文论的产生。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对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现代文艺学、美学的发展的确提供了特殊重要的方法论基础。
三、文艺观、审美观的形成
出于中国文论和美学发展的现实需要,晚清文学变革、五四文学革命和其后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三个阶段的现代转换进程,都留下了日本文论和美学的印迹,与日本化后的西方文论思想有不可忽视的联系。在基本的文艺观、审美观的形成过程中,中国总能从日本那里获得启示,找到存在、发展的依据。
1.“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在晚清文学界,特别是梁启超的政治小说盛行的时期,日本政治小说家视小说为文学最上乘的观念,成了晚清小说革命倡导者和践行者建构新的小说观的域外助力,深深影响了晚清的小说理念。明治以前,小说在日本的地位和命运与之在中国古代极为相似,都属于稗官野史之流。进入明治启蒙时期,启蒙思想家们出于开化民智的现实需要,重新审视小说,进而开掘出小说被贵族文学长期遮蔽的社会启蒙功能。1883年8月,《自由新闻》下属的《绘入自由新闻》分三次刊发了《论关于政事的稗史小说的必要性》,论述稗史小说在政治启蒙时代的重要性与必要性。[5](P150)半峰居士在评《佳人奇遇》时甚至明确指出,“盖泰西诸国,稗史院本为文章之最上乘”。[6](P21)随着日本文艺的译介和引进,日本启蒙文艺的这种新的小说观给予20世纪的中国文艺家极大的启示,并使后者最终借助这种全新的外来力量和理念帮助中国的传统文艺走出了轻视和鄙夷小说的误区。
梁启超是最早并且最着力于走出误区的先驱者。1902年,梁启超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专门刊登小说的杂志《新小说》。刊物的起名直接借用了日本1889年和1896年两次创办的同名杂志。刊物的宗旨和贯彻始终的原则,是既要重新评价小说的社会地位和作用,重新认可通俗文艺形式的利用价值,又要在小说的内容上加以革新,与政治密切联系,使原来专供消遣娱乐的旧小说升华为有明确社会目的、政治理想和抱负的新文学。梁启超亲自撰写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是《新小说》创刊号的首篇。在该篇中,梁启超意识到“于日本明治维新之运有大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之后又宣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他深信,“诸文之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7](P3~8)将小说与新民这一时代和政治的文化主体联系起来,赋予小说前所未有的地位和功用。这是中国文学和美学史上首次以现代理论思维模式概括小说的审美特征,并且通过对小说的审美功能和社会功能的高度肯定使小说获得了文学殿堂的正式通行证,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小道”、“稗史”的价值定位,从理论上将小说从文学的边缘推向了中心。
当时在日本文艺的影响之下,不独梁启超,几乎整个小说界观念都为之大变。如陶佑曾在《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中说:“自小说之名词出现,而膨胀东西剧烈之风潮,握揽古今厉害之界限者,惟此小说;影响世界普通之好尚,变迁民族运动之方针者,亦惟此小说。小说,小说,诚文学界中之最上乘者也。”[8](P226)他坚信小说乃文学中最重要的文体,能影响世界之走向。晚清学者这种视小说近乎神灵的思想,虽然从民族文学的发展角度看,可以理解为小说潜在的感人魅力与启蒙时代的精神需求相契合的缘故,但是从国外文学的影响来看,则直接源自日本明治初年的启蒙文艺的新的小说美学观。从小说发展的历史看,它可谓是日本政治小说给予晚清文论最具有文论价值的部分,因为它在人们不经意中改变了中国的某些传统文论和美学观念,动摇了传统文论的秩序,为中国小说的现代变革提供了合法的社会依据,使小说观念的转型与现代化成为可能。
2.“人的文学”。周作人倡导、建构“人的文学”观的内在驱力与基本原则,也主要源于由日本获得的崇尚自然的文化观。初到日本时,周作人下榻于东京的伏见馆。馆主人的妹子赤脚给周作人搬运行李,拿茶水,给了他极大的好感:“我相信日本民间赤脚的风俗总是极好的,出外固然穿上木屐或草履,在室内席上便白足行走,这实在是一种很健全很美的事。我所嫌恶中国恶俗之一是女子的缠足”,“闲适的是日本的下驮”,“凡此皆取其不隐藏,不装饰,只是任其自然,却亦不至于不适用与不美观”。[9](P158~159)这最初印象“很是平常,可是也很深,因为我在这以后五十年来一直没有什么变更或修正。简单的一句话,是在它生活上的爱好天然,与崇尚简素。”[9](P57)正是基于对日本崇尚“自然”、“爱好天然”的文化观的认同和遵循,周作人发展了其著名的“人的文学”的观念:“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是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者,也都应该排斥改正”。[10](P57)在他看来,人性的自由发展,是自然的,是“人的文学”应该着力表现的,因为“个性的表现是自然的”。[11]在《儿童的文学》中,他说:“顺应自然生活各期——生长,成熟,老死,都是真正的生活。”[12](P23)“人的文学”书写的就应是这种顺应自然的生活。他五四前后发挥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等人的文艺理论而写的《平民文学》、《人的文学》、《新文学的要求》、《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等论文,贯穿的基本思想也是这种自然人性论和“白桦派”的人道主义理论,对五四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莫大影响。可见,周作人倡导的“人的文学”观与其所获得的日本经验之间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人的文学”观建构的首要的、基本的问题,是重新界定“人”。“人”是“人的文学”的书写对象,决定着“人的文学”的意义走向。为此,周作人首先将人规定为灵与肉的统一体。他说,“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而是“‘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而这两个要点,换一句话说,“便是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就是说,人既是动物性的,又是社会化的,“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10](P194)人的健康健全的生活,便是灵肉一致的生活。这种观点的原始依据虽然在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等人那里,但对于倾心于日本文学的周作人来说,更为直接的来源,则是在当时影响颇大的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潮论》。在《文艺思潮论》中,厨川白村反对将人的兽性或神性推向极端,认为人的生物性欲求是自然合理的,应予以充分的肯定与满足;与此同时,又不能忽视人的社会性特征,应充分认识到精神的自由发展对于人的意义。如果将周作人的灵肉统一的观点与厨川白村的相关理论进行对照,就不难发现两者论证的过程与结论的一致性。虽然不同地域的人的思想有时会惊人地巧合,但鉴于周作人对于日本文论的极大热情,恐怕直接影响的因素更多一些。
“人的文学”观另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人的文学”如何表现“人”的问题,也就是“人的文学”是人生派的文学还是艺术派的文学的问题。对此,周作人没有简单地将其归入任何一派。他辩证地指出了人生派与艺术派各自的价值和缺陷,认为二者都有自身的合理性又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片面褊狭之处。进而采取中庸调和的态度,说明“人的文学”应当是“人生的艺术派的文学”,就是“著者应当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他对于人生的情思,使读者能得艺术的享乐与人生的解释”。[13](P16~17)这种人生的艺术派,在日本是由二叶亭四迷从俄国文学引进并发扬光大的。在著名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一文中,周作人提到:“他(指二叶亭四迷——作者)因为受了俄国文学的影响,所以他的著作,是‘人生的艺术派’一流。”[14](P285)可见周作人有关“人的文学”属于人生的艺术派的主张与二叶亭四迷不无关系。
在日本文论背景烛照下的“人的文学”观,触及了文学的本质问题,对“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进行了颠覆。“人的文学”和其后的“平民文学”观念一起,借助异域文论的力量,为五四文论最终废除封建的“非人文学”观,成功打通中西文论通道,建立现代化的中国文论作了必要而充分的准备工作。
3.“文艺是苦闷的象征”。文艺是苦闷的象征,这是厨川白村在《苦闷的象征》一书中的核心观念。这一观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着五四时期,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美学观形成之前中国现代作家文艺观的确立。五四时期,泛浪漫主义的整体氛围甚嚣尘上,文艺的主观性、理想性、表现性和情感性、反抗性得到极大张扬,加之五四文学革命的干将留日者居多,对厨川白村的理论较为熟悉。而厨川白村深受柏格森和荣格的精神分析学、尼采的意志哲学、叔本华的悲观哲学、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精神分析学、康德的超功利的美学和克罗奇的表现主义美学的影响,还要极力推崇“新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正好与五四的需求合拍。因而,厨川白村的文艺观成为五四浪漫主义文艺和美学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
那时的许多作家、文艺家,如郭沫若、郁达夫、田汉、许祖正、庐隐等,或多或少都受过厨川白村的理论熏陶。郭沫若在1922年提出:“文艺本是苦闷的象征……个人的苦闷,社会的苦闷,全人类的苦闷,都是血泪的源泉。”“我郭沫若所信奉的文学定义是:‘文学是苦闷的象征’。”[15](P228)后来又进一步强调:“文学是反抗精神的象征,是生命穷促时叫出来的一种革命。”作家“唯其有此精神上的种种苦闷才生出向上的冲动,以此冲动以表现于文艺,而文艺尊严性才得以确立”。[16](P321,326)这些表述与厨川白村的文艺观之间的联系是一目了然的。和郭沫若一样,郁达夫也把艺术家的“苦闷”看成是“象征选择的苦闷”。汲取日本私小说理论的滋养,郁达夫认为,文艺是自我的表现,而自我表现的手段则是“象征”。厨川白村认为“文艺是纯纯然生命的表现”,要“专营一种不杂的创造生活的世界”;郁达夫也主张艺术家应该“选择纯粹的象征”,“因为象征是表现的材料,不纯粹便不能得到纯粹的表现。这一种象征选择的苦闷,就是艺术家的苦闷。”[17](P67)
文艺是苦闷的象征,对此厨川白村的完整表述是:“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文艺表现生命就是表现生命的苦闷。这种生命的苦闷在郭沫若那里由个人的苦闷扩展到社会的苦闷以至全人类的苦闷,文学表现的空间也因此由个人拓展到更为广大的社会、人类。就连视文学为自叙传的郁达夫也在1923年深化了对文学自我表现说的认识,认为文学家“不外乎他们的满腔郁愤,无处发泄;只好把对现实怀着的不满的心思,和对社会感得的热烈的反抗,都描写在纸上”。[18](P134)此时,自我表现已经升华为对社会的表现,对社会现实的表现。文学表现空间的拓展对于五四文学走出狭隘的自我表现界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有助于五四文学的突破与发展,也是文学现代性突围的一个必要阶段。
4.“革命文学”。1928年,沈绮雨在《日本的无产阶级艺术怎样经过它的运动过程》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普罗艺术运动,与日本实有不可分离的关系。”[19](P269)这是基于20世纪前半叶中国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发展的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合理论断。当时,日本文坛被无产阶级文学和现代主义的新感觉派、新兴艺术派等派别分而据之,这些派别又分别从“革命文学”和“文学革命”两个向度展开。而中国正是这两个向度的另一大“演练场”。在日本革命文学的参照系中,中国的革命文学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日本学者辛岛骁说:“到了1928年(民国17年)以后革命文学时代,泛渲在日本文坛的苏俄的文艺理论,差不多次月上海已有翻译,接近到那样。日本左翼评论家的议论,强烈地影响着中国的左翼文学运动。特别是平林初之辅、片上伸、冈泽秀虎、青野季吉、藏原惟人、川口浩等的文章,曾经和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文章并列着,在中国评论家的论说中,像金科玉律地引用过。”[20](P30)中国文坛对日本文学和文论的极度信赖和依赖,对其自觉的借鉴意识,与晚清以来现代性追寻过程中,曾经多方面受惠于日本文学和文论的历史不无关系。参考、借鉴和创化日本文学和文论现代化的途径和方式,已经成为一种文坛时尚,成为中国作家、文论家的一种习惯,一种共识。李初梨从日本一回国就迫不及待地宣称要用“为革命而文学”取代“为文学而革命”,使中国新文艺由五四文学革命转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阶段,扛起了革命文学的大旗。
对于日本福本和夫的“激烈没落论”以及以福本和夫理论为基石的青野季吉的文学论等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包括李初梨在内的革命文学倡导者几乎是照单全收。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没落,也就意味着无产阶级的兴起和小资产阶级的衰落。所以,“中国一般无产大众的激增,与乎中间阶级的贫困化,遂驯致知识阶级的自然生长的革命要求。这是革命文学发生的社会根据。”[21](P58)而文学革命经过有产者和小有产者两个时期,又失去了自身的社会根据,已经没落了。这样,从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中,中国很容易地找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兴起的历史必然性的理论依据。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主将和理论代表,李初梨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中,把文学等同于宣传,“文学为意德沃罗基的一种,所以文学的社会任务,在它的组织能力”。“文学,是生活意志的表现。文学,有它的社会根据——阶级背景。文学,有它的组织机能——一个阶级的武器”。[2](P54,55)李初梨的这一文学观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认同,郭沫若《留声机器的回音》、彭康《革命文艺与大众文艺》、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等,都是这种文学观的回应与深化。
那么,何谓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呢?平林初之辅和青野季吉的回答是,无产阶级文学具有阶级性,必须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服务。这种文学观同时也是中国革命文学论者所认同的文学观。例如郭沫若在《桌子的跳舞》中就坚持无产阶级文学是为无产阶级说话的文学,是包含无产阶级意识的文学。李初梨的表述则更为简洁,更为日本化:“无产阶级文学是:为完成它主体阶级的历史的使命,不是以观照的——表现的态度,而是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斗争的文学。”[21](P59)“阶级意识”、“主体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李初梨革命文学理论的关键词。
梁启超曾说,要用“彼西方美人,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22](P8)中国现代文艺学美学就是中西交合而产生的“宁馨儿”。以留日学生为代表的中国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冲破了数千年来“不肯自己去学人,只愿别人来像我”的心理障碍,“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14](P293)他们借留学之便向异域寻求新质、借取武器,致力于欧美和日本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的译介工作,推动了中国艺术创作的繁荣和文学艺术理论的活跃,促成了中国文艺现代性的确立,带来了审美现代性的演变,新的审美话语的产生,文学文体的新生和新的文学、美学观念的形成。
收稿日期 2007-10-27
标签:美学论文; 文学论文; 文艺学论文; 文艺论文; 艺术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概论论文; 苦闷的象征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读书论文; 梁启超论文; 人文学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