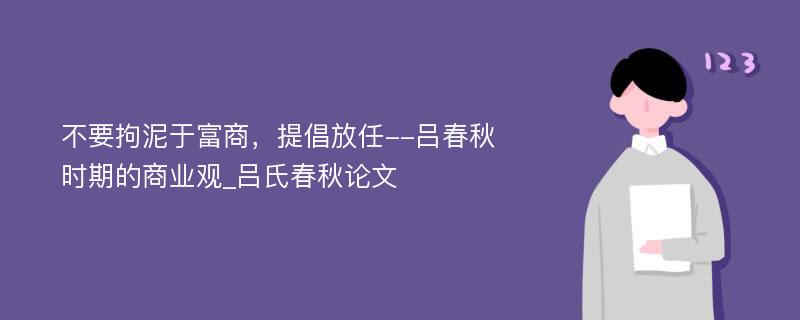
不抑富商大贾,力主自由放任——《吕氏春秋》的商业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放任论文,富商论文,春秋论文,吕氏论文,商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王政八年,是秦相国吕不韦招集其门客编纂而成的。
吕不韦(?—前235),战国末阳翟地区大商人, 《战国策》记载为濮阳人,家累千金,当时秦国正是昭襄王当政,吕不韦以非凡的商业眼光,进行政治投机,千方百计营谋,使在赵国做人质的子楚返回秦国,并最终登上了秦国的王位,即秦庄襄王。他聘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子楚也只执政三年,死后十三岁的太子政为王,即后来的秦始皇。他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当初,吕不韦在邯郸独具慧眼相中的“奇货”,果然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名利双收,这个富甲天下的商人,由经商而从政,由于秦王政年幼,秦国内外的大政方针均出自吕不韦之手。
当时各国显贵有招贤纳士,喜养宾客之风,又多有辩士,著书立说遍传天下。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有食客三千人。这许多门客,人人著述所闻,集论一百六十六篇,约二十余万言,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号为《吕氏春秋》。吕不韦自诩此书“备言天地万物古今之事”,骄矜自负,溢于言表。这部书的观点属“杂家”,汉班固评论它,“兼儒墨,合名法”,容纳了先秦各家学说,对各家矛盾的观点,则采取拼凑调和的方式兼容之。吕不韦主持汇编了全书,并冠其姓氏为书名,书中的一些重要观点,是代表了他的思想的。
秦国僻居西陲, 本来经济文化都落后于东方六国, 但经过秦孝公的商鞅变法,奉行“农战”方针,为稳定和增加农村人口,防止农业劳动力流失,脱离土地去经商,于是在提高粮食价格,增加农民利益的同时,采取了一系的“抑商”政策,如加重商人赋税、劳役,国家独占山泽之利,盐铁专卖,管制粮食贸易等。通过商鞅变法,秦国农业生产发展,财政收入充足,军事力量加强。商鞅死后,秦也一直推行这种重农抑商政策。
吕不韦当政在商鞅变法后一百多年,他是代表商人利益的朝廷新贵,在《吕氏春秋》中,他提倡“重农”而舍弃“抑商”,全书虽然没有对商业的专篇专论,但反映的商业观,却明显地对秦国一贯的抑商思想有所改变。
《吕氏春秋》对农业的重要性十分肯定,《士容论·上农篇》中说:“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力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復,其产復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认为古代圣王引导百姓致力于农业,目的不单纯为增加粮食生产,还为加强教化,使百姓心志淳朴,举止持重,民力专一,使家庭财产不断增加,安居乐业之心稳定,而不轻易离乡背井。如果百姓不尽力农耕,国家就难以为治了。
在突出了农业的重要性之后,《吕氏春秋》中也提到了其他社会分工之必不可少。《上农篇》继续提出:“凡民自七尺以上属三官,农民攻粟,工攻器,贾攻货,时事不共,是谓大凶。”这是说凡百姓成年以后,都分别归属于三种社会分工:农、工、商。农民的职责是生产粮食,工匠的职责是制作器物,商人的职责是经营货物。如果不能按时做好应办的事,就称为大害,显然这三种分工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但分工必须各专其职,尤其“农不敢行贾,不敢为异事,为害于时也”,强调农民不得经商,不得去干其他事,因为这会妨害农时。从必要的社会分工来考虑,已可看出,作为“属诸三官”之一的商业,在《吕氏春秋》中自有其应占的地位,大不同于商鞅对商业的抑制以至于摒斥的态度。
本来,在战国之末,“农本工商末”的概念已经形成,重农抑商已被说成是重本抑末,由“本”“末”之分,其轻重抑扬之意判然可见,但在《吕氏春秋·孝行篇》中却把“孝”字另作解释:“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本莫贵于孝”。在其他地方,如说:“君立已定而舍其众,是得其末而失其本”,这是以“用众”为本,所谓“以众勇”、“以众力”、“以众视”、“以众知”、“以众者,此君人之大宝也”。又如说“薄疑(人名)应卫嗣君以无重税”,“近知本矣”,“薄疑劝卫嗣君以王者富民,故曰无重税也”,《务本》这又是以无重税为本,“本”字在《吕氏春秋》中无确定意义,务本并非必指重农。“本”字既已泛化,往往与“农”无关,与之相对的“末”字自然也与工商业无必然的联系了。因此,可以说在《吕氏春秋》中,“重农抑商”的抑商概念已被打破了,更看不出它是以工商业为所要抑制的末业了。
诚然,《吕氏春秋》中有时对“末”字也不无讥评之词,须予正视。如:“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善),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后稷曰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上农》),这里虽以务耕织的农为本业,但所谓末,却不是统指工商业,不是“工商末”的“末”,而是先秦诸家以技巧为末事的“末”,即包括奢侈品手工业生产和销售的“奇技淫巧”之谓;也包括农民的放弃耕织而去跑买卖,从事“末”利者,这一点倒与商鞅之意并无不合之处。吕不韦毕竟也是个当国者,从治理国家的角度出发,他同样要求稳定,增加农业劳动力,不能容忍舍本,事末,弃农经商之风大长,这样会“为害于时”,指农时,有失“农不敢行贾”的“上农”之旨。尽管如此,《吕氏春秋》中明确的口号是“务本而后末”,本、末只有先后之分,无存废之别,而不提什么“禁”和“抑”了,比商鞅的态度又大大缓和了。总之,商鞅的“重农、抑商、禁末”三者之中,后两者已大为淡化乃至被抹杀,而只剩下了无可改易的重农了。更突出的是务本的“本”字,已主要被偷换成“孝”字,要教秦王政听吕不韦的话,对这位“相父”尽孝道了。
《吕氏春秋》重农而不抑商,他所不抑的商是什么含义呢?从对农民弃农经商的否定来看,他所不加否定,不加抑制的商,应该是富商大贾了,即抑小不抑大,所要扶植、纵容的是包括了周游列国之间的大贩运商,和在国内经营盐铁、酒等大行业的大商人,尤其是后者。如果说商鞅时代抑商矛头主要是指向弃农经商的中小商人,而非国内“富商大贾”,当时这部分人数量还不多,力量也还不大,那么在商鞅死后的一段时间,随着秦国经济的发展,国内大商人极力谋求发展的机会,与抑商政策的矛盾就日益加深了。代表大商人势力的吕不韦正是不满意由商鞅始作俑的、秦国对发展中的大商人在政策上的抑制,谋求放松限制,使他们能得到自由的发展,从而在《吕氏春秋》一书中,自然流露出自己对这部分人的同情支持的观点。
《吕氏春秋》中《月令·仲秋纪》提出:“是月也,易关市,来商旅;入货贿,以便民事,四方来杂,远乡皆至,则财物不匮,上无乏用,百事乃遂”。仲秋八月是农业收获季节,官府在敦促百姓收获、储藏的同时,要免除关市的税收,招徕商贾,带来财货,使其能以所有易所无,给人民带来方便。由于关市免税,“四方”乃至“远乡”的商人蜂拥而至,统治者和百姓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百事可成。相传这是周代就奉行的徕商政策,地处关中的秦国,为拉拢“四方”“远乡”的境外商人来秦,以扩大贸易、市场来换取这些商人对秦国统一大业的支持,也一直采取了免除关税的做法。《吕氏春秋》中为之宣传的“易关市、来商旅”正是秦国的现行政策,因此,在这一点上对外地商人的优惠,并非吕不韦之独到,非为吕不韦不抑商的主要表现。
吕不韦不抑商的主要表现在对国内进行商品的生产和流通的商人提出自由贸易,免除关税的主张上,他要求政府按适当季节,让人们从事商业活动,鼓励商贾贸易。如《仲夏记》提出“仲夏之月,门闾无闭,关市无索”,《仲冬纪》提出“山林薮泽,有能取疏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导之”,无论关市、山泽,都允许自由往来,自由捕猎,自由采摘,自由贸易,不禁止,不征税。足以证明《吕氏春秋》对国内商人也极力主张实行轻税政策。正和商鞅的“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的重征商税政策以及国家独占山林之利,实行盐铁专卖制度等大唱反调。
正因为对国内大商人也主张宽容、优待,所以吕不韦在主持国政时,怂恿年犹未冠的秦王政,做了两年抬高商人身价的大事:一是下令提高专到少数民族地区做牲畜生意的大富商乌氏倮的地位,他同受封的贵族一样,可按时和大臣们一起朝觐皇帝,二是巴蜀地区一位经营朱砂矿的寡妇清,继承祖业,家资巨富,秦王政对她十分礼遇,专门建造了女怀清台,称赞她为贞女。办这两件事虽然打着幼年皇帝的旗号,却正符合吕不韦的思想,而同秦王亲政后的打击、抑制富商大贾政策是决不相容的。
吕不韦出身于大商人,当政后又垄断洛阳重要的工商业,本人就是官僚兼富商大贾的典型,在《吕氏春秋》中不抑私商,不抑富商大贾也就不足为怪了。为了给富商大贾争取经商自由准备舆论,提供理论根据,吕不韦在他所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中大力宣传无为而治的思想,鼓吹自由放任便成了这部书的一大特色。
《吕氏春秋·季春纪·先己篇》中大讲“无为之道曰胜天”,意思是“天无为而化,君能无为而治民,以为胜于天”,“君无为则万民安利”,“无为而不欲,故能胜天顺性”,特别一而再地强调人君无为而治的思想。在其他篇章中,无为思想也续有发挥,《似顺论·别类》说“正则静,静则清明,清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完全是崇尚空虚无为的黄老思想。在《慎大览》中更专辟《贵因篇》,开宗明义地说:“三代所重,莫如因,因则无敌”,“故因则功,专则拙,因者无敌”,“因”就是听其自然,最多是因势利导而已。《吕氏春秋》的“贵因论”也源于黄老思想,后来司马迁“善者因之”的“善因论”与之已有一脉相承之迹。经济放任主义实以“贵因”、“善因”为其哲学思想;由此出发,当然主张经济放任,不抑富商大贾,不阻自由贸易,与商鞅的源于经济干涉主义的抑商政策当然是完全对立的。
《吕氏春秋》不抑商而重商,持重商主张并身兼大商人出身者,往往是高消费的鼓吹者,如:《管子·侈靡篇》就大力宣传以消费促生产、促流通的思想,与儒、墨诸家的崇尚节俭大相径庭,但商人出身的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中却主张节欲以养生,他认为:“昔先圣王之占苑囿,园池也,足以观望劳形而已矣;其为宫室台榭也,足以辟燥湿而已矣;其为舆马衣裘也,足以逸身暖骸而已矣;其为饮食酏醴也,足以适味充虚而已矣;其为声色音乐也,足以安性自娱而已矣。五者,圣王之所以养性也,非好俭而恶费也,节(和适)乎性也”(《重己》)。以养生适性来代替单纯地讲好俭恶费,似欲以婆心苦口来打动人主,比一般地鼓吹俭德更深了一层。
《吕氏春秋》还大力提倡节丧、安死。指出“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奸人闻之,传以相告”,“上虽以严威重罪禁之犹不可止”(《节丧篇》)。吕不韦出身大商人,位居显贵,本人生活自然著侈无度,却大弹其崇俭的高调,其中不能不大有深意。当时秦王政已日渐成人,虽尚不主政,但个人追求享受,穿骊山作为宫之事已见端倪,《史记》记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中谆谆教诲,是在为秦王政考虑,明代方孝孺称《吕氏春秋》一书“诚有足取者,其节丧安死篇,讥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事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罚不如德礼,达爵分职篇皆尽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后秦卒以是数者偾败亡国,非知几之士岂足以为之哉!”他认为吕不韦编此书是在“诋訾时君”。
其实,《吕氏春秋》欲对秦王政施加影响的要点,尚不在节丧安死,而在提倡“无为”、“勿躬”,也就是不要事必亲躬,只垂拱而治,听任他这个相国长期专权下去,在经济上则是提供自由放任,纵容富商大贾,听任吕不韦长期巩固并发展他的商业利益。为此,必须修改商鞅以来的抑商政策,及经济干涉主义的思想,这才是吕不韦花大力气编纂这部巨著的最大目的,绝不止于像方孝孺所说的:“以宾客之书,显其名于后世”而已。当然,在秦国,商鞅思想已根深蒂固,在《吕氏春秋》成书不久,吕不韦即被已亲政的秦王政贬斥至死,而商鞅的抑商政策,经济干涉主义思想在秦国更变本加厉地推行下去,辛勤著书的吕不韦目的并未能达到,但在客观上,商业在统一的国家这种优良的经商条件下,必然得到相当的发展,到汉代初年,晁错也只好无奈地嗟叹:“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贵粟疏》)。可见法律自法律,事实自事实,正如马克思所说:“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总而言之《吕氏春秋》的商业观并不复杂,但能在当时出现也实属难能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