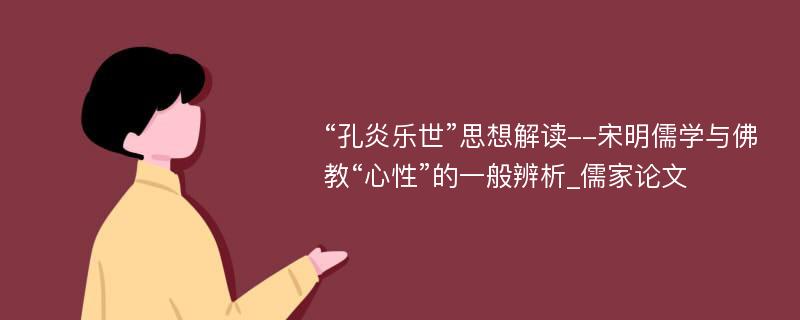
“孔颜乐处”心解——宋明之际一段儒释“心性”通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性论文,颜乐论文,心解论文,宋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人都知道孔子是大圣人,有天大的学问和本事,结果一生颠沛流离,不得其用。他周 游列国,劝说大家来完成尊王攘夷的大一统王业,结果怎么样呢?不但没人听信,在陈蔡还 遭到围困,误会他是阳货,弄得连饭都没得吃。然而,孔子虽然多次处于困厄和险境之中 ,但他的内心总是那样安详和乐观,“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论语·述而篇》)“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同上)。颜回 是孔子最器重的学生,也有很高学问和品德修养,然而一生亦是穷困潦倒,“回也,其庶乎 !屡空。”(《论语·先进篇》)“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论语·雍也篇》)于是“孔颜乐处”就成为一个儒学话题,汉代以来人们不仅把孔子、 颜渊这种“安贫乐道”精神奉为儒家最高的人格精神和道德境界,甚至作为一种“孔颜人格 ”津津乐道与推崇。
然而,到了宋明时代,这个儒学话题发生一些耐人寻味的变化,其不仅为当时佛教禅师们 所熟用,而且在理学家手中也成了用来接引学人的一则“公案”。下面我们就“孔颜乐处” 这个话题,来看看宋明之际儒释两家对于“心性”的体悟以及其中所关涉的义理内容和方法 上启迪。
一、“吾此妙心,实启迪于黄龙,发明于佛印”
《宋元学案》中记载了一则史事,宋代的周敦颐(字濂溪)对来请教的程颐、程颢两兄弟, 常每令其寻孔子、颜渊乐处所乐何事。[1]周子为什么要二程兄弟去寻“孔颜乐处”,难道 作为大理学家的二程尚不知孔子、颜渊所乐何事吗?其实在此之前,周敦颐曾问道于黄龙南 禅师。黄龙南禅师应机说法,就以“孔颜所乐者何事”开示于他:
濂溪初扣黄龙南禅师教外别传之旨,南谕濂,其略曰:“只消向你自家屋里打点,孔子谓 朝闻道,夕死可矣,毕竟以何为道,夕死可耶?颜子不改其乐,所乐者何事?但于此究竟,久 久自然有个契合处。”
濂一日扣问佛印元禅师曰:“毕竟以何为道?”元曰:“满目青山一任看。”濂拟议,元呵 诃笑而已。濂脱然有省。[2](p.552)
以儒家的眼光看来,孔颜圣人的这种“安贫乐道”之“道”自然当是儒学倡导的传统和目 的。周敦颐是宋朝大儒未必不懂其“道”?那么,黄龙禅师为什么还让他去参透这其中的玄 机 呢?说到这个“道”,周敦颐自然想辩个明白,殊不知当他一“拟议”,便落入理念的窠臼 ,无怪佛印元禅师呵呵大笑之。然而这一笑,竟使濂溪豁然有所醒悟,就在“脱然有省” 的一刹那,他悟到了“孔颜乐处”的真谛。所以,当二程兄弟来问道时,他又照样以这个话 题让他们去参悟。
更有意思的是,后来程颐的学生鲜于侁又以这个话题请教程颐:
“颜子在陋巷不改其乐,不知所乐者何事?”先生(指程颐)曰:“寻常道颜子所乐者何?”侁曰:“不过是说所乐者道。”先生曰:“若有道可乐,不是颜子。”[2](p.569)
从濂溪到二程,从程颐到鲜于侁,我们看到理学家每每接引学人总喜欢用“孔颜乐处”这 个话题,但是从程颐的“若有道可乐,不是颜子”这句话可知“孔颜乐处”的真正含义已不 是如一般儒者所理解的伦理道德内涵,或者说汉儒以来所认同的人格理想境界,并非是孔子 、颜渊所体悟的那个境界,甚至还意味着历代儒者探寻“道”的想法和方法本身就是谬误的 。那么,宋代的大儒们究竟从“孔颜乐处”中悟到了什么?
我们来看周敦颐怎么解释,他说,“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 其 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 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3]
这种“至贵至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先看濂溪的主“诚”。一般的人,对儒家的“诚” 看得太简单了,常常仅把这个“诚”字,当作人格品性中的一个美德而已,殊不知这个“诚 ” 字,却蕴含了许多玄机,从而成为理学最重要的一个范畴。周氏在《通书》中,用易学的道 理来阐明这个“诚”字,可以说是得到了精髓。他说:“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 神也;运而未形有无之间,几也。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几微故幽,诚神几曰圣人。”[3]( ](p.495)这里很明确,诚是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是“寂然不动”,是精神作用未 发 动、无污染的清净本原状态。用《中庸》的话来说,那是处于“喜怒哀乐之未发之谓中”的 状态。这样的状态,它与禅宗所讲的“真如本性”、“清静自性”和道家所讲的“道”也 是一致的,与佛教“禅定”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的。如果要说区别,只是一是用于入世, 一是用于出世。虽然“寂然不动”,又不是死寂,因为它可以“感而遂通”。通向哪里去呢 ?通向一切主观和客观的领域,儒家是入世的学说,也就是通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 是“诚者,五常之本,百行之源。”[3](p.483)
这种“寂然不动”的无污染的精神本原状态被称为“天之道”,在日常生活中,使受污染 的精神回归于这种状态,就是“人之道”。只有使精神处于这种无污染的本原状态,才可以 “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乃至达到“参赞天地之化育”,并与“天地合参”的境界。 这就是佛教所说的“一切智”,道家所讲的“无不为”,如果再达到“明则动,动则变,变 则化”的境界,那就是圣人的境界,与佛教的菩萨,道家的真人差不多了。在这个最高层次 上讲,儒释道三家都达到同一境界。只是因人因事的表述不同而自然形成不同的说法而已, 正如周敦颐虽从禅宗悟道,而他的表述则完全是儒家说法一样。
再看濂溪的主“静”。《乐记》上有两句话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 之 欲也。”[4]“静”的第一义是纯净,纯净便自然安静。人性一片纯真、纯善,若无外物渗 扰其间,有什么“欲动”的东西可言。“静”的作用,是把人所浮起来的感情,使其沉静、 安静下来,这才能感发人之善心、仁心、乐心。所以,“乐由中出,故静”[4]。乐由中出 ,即是“乐由性出”,乐由性的自然而感的处所流出,才可以说是静。所以周子说,“无 欲故静”。他在《通书》第二十章回答学习圣人的要领说:“一为要者,无欲也。无欲则静 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后来明代王畿进一步阐述道:“静者,心之本体。濂溪主静 ,以无欲为要。一者,无欲也。则静虚动直。主静之静,实兼动静之义……无欲则虽万感纷 扰而未尝动也。”[5]可见要达到主静的目的,则以无欲为先。所谓欲,便是物欲,而人的 本性之善所以容易消失,便是由于欲的障蔽。濂溪的“主静”,绝不是心如枯井木石般的死 寂 ,而是使心境澄清,不受物欲的扰乱,使其灵秀的本质得以保全。后来宋明理学家讲的“正 心”、“诚意”、“存天理”、“致良知”,说穿了就是讲的人格修养。当人格修炼到人欲 去而天理天机活泼的时候才能感受到那最高境界,才能将生命沉浸于乐与仁得到统一的无限 的 境界。这种由人性“静”、“敬”而得到的快乐与一般所说的快乐,完全属于两种不同的层 次,乃是精神“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大自由、大解放的乐。人在这种境界中,只是把生命在 深处之情向上提,即是向纯净而无丝毫人欲烦扰夹杂的人生境界向上提,层层向上突破,直 至突破到为超快乐的大乐之境[6]。
孔门即在此根源之地定立“乐”的根基。这种“乐”的“至贵至富”与富贵等物欲的东西 不同,见到这种“至贵至富”,对那些荣辱得失、名利爵禄就看得小了,“见其大者而忘其 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 ,故颜子亚圣。”[7]处之一,化而齐者,即是化富贵贫贱如一。孔子、颜渊正是得到这种 “至贵至富”东西,所以不论富贵贫贱皆能“处之一”、“化而齐”。
这种“处之一”、“化而齐”虽然是儒家的所倡导的“诚”“静”境界,但跟老庄的“齐 物”、“无差别”和禅宗的“无分别心”也是一样的,可以称之为一种“超快乐”的“禅 悦境界”,所以,周敦颐由衷地表白说:
吾此妙心,实启迪于黄龙,发明于佛印,然易理廓达,自非东林开遮拂试,无繇表里洞然 。”[2](p.553)
也许周敦颐最初的本意是想极认真地去理解圣人学说,阐扬孔儒之学的原始意义,这是理 学家的根本目的和主要任务。然而当他真正地契悟“孔颜乐处”,实是由于禅宗的启迪。这 种 启迪的意义是重大的,它使宋明理学家对于孔孟学说的阐释更加注重“心性”之学的开发, 由于“心性”的开发,也使他们易于打通儒释道三家的对立。由此可见,这则“公案”在理 学家眼中,意义亦非同一般。周敦颐和二程由此而发明儒学大义,组织道学,宋学的渊源即 发于此。这不得不承认是“禅法烂熟的结果。”[2](p.552)
二、“乐是心之本体,本是活泼,本是脱洒,本无挂碍系缚”
宋以后,随着禅学的浸润民心,儒学以依附佛学为时尚,儒者或攀缘禅师,或口说公案, 或修习禅定。然而对于释家,他们又如何来看儒家阐释的义理呢?明代有一位呆庵普庄禅师 在当时被人誉为“宗门中伟人”。有人曾以“儒释内外之辨”问之,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儒 学的弊病:
教有内外不同,故造理有浅深之异,求之于内,心性是也;求之于外,学解是也。……今 儒学之弊,浮华者固以辞章为事,纯实着亦不过以文义为宗。其实心学则皆罔然也。……夫 了悟之地,非学解所能到,悟则谓之内,解则谓之外,则内教外教所以不同矣。儒者专用力 于外,凡知解所不及者,不复穷究,故不知允执厥中之道,天理流行之处,皆在思虑不起, 物欲净尽之时,践履虽专,终不入圣人之域矣。[8]
普庄认为对于“心性”之学,儒释两家有着内外之别。他批评儒者用“学解”的方法去求 道,注重于“辞章”或“文义”的表面诠释,这样做,是入不了“圣人之域”的。因为靠“ 学 解”之法,是不能穷究“允执厥中之道”、“天理流行之处”的奥妙。普庄所说的境界与佛 家所说的“佛性”、“真如”、“自性”是一致的,其实它正是“思虑不起,物欲净尽”的 一种本原状态。要究尽天理,入“圣人之域”,只有用“心性悟入”之法。
作为王学高弟的王畿(字汝中,别号龙溪),对释儒在开启“心性”的方法论上的争辩看得 更加明白,他说:
师门尝有入悟者三种教法,从识解而得者,谓之解悟,未离言诠。从静中而得者,谓证悟 ,犹有待于境。从人事练习而得者,忘言忘境,触处逢源,愈摇荡愈凝寂,始为彻悟。[9]
如果以这三种“悟入”教法去判别宋明儒对“心性”之学的所达到的境界高低的话,周敦 颐 则是由“静中而得”,从而达到证悟境界。而一般学儒则通过文字言语,用知解去认识“道 ”,最多只是一种解悟而已。而彻悟境界,则非实证实修,不是一般常人能达到圣人之境。 至于那些迂儒、俗儒、腐儒则是在一味曲解孔学,仅得其糟粕而已。[10]
这就是说,禅宗不仅在方法论上对当时的儒学弊病给予纠正,而且指出了“穷究天理”, 入“圣人之域”的不同境界,而这些不同的境界,正来自于主体对“心”体验的不同。值得 注意的是,在王畿那里,由于受禅法影响,他对于“心”的体验有着新的发现和感受。他不 再是从道德伦理的角度,而是从“心”的本体上谈“乐”:
乐是心之本体,本是活泼,本是脱洒,本无挂碍系缚。[11]
人心虚明湛然,其体原是活泼,岂容执得定?唯随时练习,变动周流,或顺或逆,或纵或横 , 随其所为。还它活泼之体,不为诸境所碍,斯为之存。[12]
王畿认为人心本来就是一个自由天使,灵妙活泼,在无限的时空中自在地翱翔,既没有外 在的束缚,又没有内在的拘泥,这是一个何等脱洒,何等快乐的境界!既然如此,那么生而 为 人,就应还他一个活泼之体,还他一个自由快乐,而不应当被外界环境所拘执和系缚。无怪 有个日本人说王畿更似六祖顿悟之见[2](p.762),他的“良知”说也较王阳明更加近于禅:
吾之良知自与万物相为流通而无所凝滞。后之儒者不明一体之义,不能自信其心,反疑良 知涉虚,不足以备万物。先取古人孝悌爱敬五常百行之迹指为典要,揣摩依仿,执之以为应 物之则,而不复知有变动周流之义……[13]
他认为“良知”就是“心之本体”、“天命之性”,这点与王阳明学说相同,但它不是“ 道德本体”,所以他并不主张儒者以伦理纲常来规范人的心体,这就显示出他的学说与传统 儒学教条的冲突。他所主张的是在不受任何制约的前提下阐释“心之本体”的“活泼”、 “脱洒”与“变动周流”,实际上不仅肯定人的生活意欲的合法性,也肯定其个性的复杂性 和丰富性。
泰州学派的罗汝芳(字维德,号近溪)则从“孔颜乐处”中体悟到“心”,即是“生”的自 由:
人问:“孔颜乐处?”罗子曰:“所谓乐者,窃意只是个快活而已。岂快活之外复有所谓乐 哉 ?生意活泼,了无滞碍,即是圣贤之所谓乐,却是圣贤之所谓仁。盖此仁字,其本源根柢于 天地之大德,其脉络分明于品汇之心元,故赤子初生,孩儿弄之,则欣笑不休,乳而育之, 则欢爱无尽。盖人之出世,本由造物之主机,故人之为生,自有天然之乐趣……故只思于孔 、颜乐处,竭力追寻,顾却忘于自己身中讨求着落。”[14]
这里,他把这种“乐”与“仁”提到相同的高度。既然“仁”即是道,孟子说,“仁也者 ,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那么,“乐”也就是道。道是什么?道就是生,它是人生命存 在 的全部价值和意义。由此看出,罗汝芳彻底地悟道了。他对“心”的理解就是“生”[15], “ 生意活泼,了无滞碍”,自有“天然之乐趣”。这种“理解”已经不是从“知解”、“学解 ”得来,它是一种对生命自身的体验和感悟。在他看来,生命本身就是乐,“不追心既往 ,不逆心将来,任它宽宏活泼,真是水流物生,充天机之自然,至于恒久不息而无难也。” [16]所以他认为所谓“孔颜乐处”并不是乐于“君子固穷”之类的道德体验,“圣者之心” 是乐于“生意活泼,了无滞碍”的生命自由的体验。
王畿、罗汝芳之说几乎与禅宗论心无异,他们对心性的体验无疑也是从禅宗那里得到极大 的 启示。这里透露出一个消息,明中叶以后的“心性”之辨,代表了一股时代的趋势,似乎把 人从道德理性的“圣人境界”重拉回到感性世俗的凡人境界,更强调人的自然欲求和日常生 活需要,也更强调一种“率性而为”的自由,用禅宗的话来说就是:
入色界不被色惑,入声界不被声惑,入香界不被香惑,入味界不被味惑,入触界不被触惑 , 所以达六种色、声、香、味触法皆是空相,不能系缚此无依道人。[24]
酒肉而不知戒,犯淫色而不知禁,往往嬉笑怒骂,恣情纵意……究之,极意佯狂,尽是灵 通 慧性;任情极戏,无非活泼禅机。[17]
这就是所谓的“真禅”与“狂禅”。一方面是无缚无依,纵情声色;另一方面有灵通慧性 、活泼禅机等高级精神生活。一方面有色、声、香、触等样样俱全的物质享受;另一方面在 污秽世界保持清净超脱之心,既高雅又万事不亏。明中叶以后的那场声势浩大的市民阶层的 启蒙思想运动,以李贽为代表的一大群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如王阳明、何心隐、汤显祖、 冯梦龙、徐渭和“公安三袁”等几乎无不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而向往着这样一种“心”的解 放与自由。他们在诗歌、小说、戏剧等在各个方面大倡“性灵”,以“情”反“理”,冲击 着“天理”的荒谬,表达着“人欲”的合理。然而这一场启蒙思想的潮流,却是以“发乎情 ,止乎礼义”的“回归”而告终。结局是令人深思的,这些启蒙者的“数奇”的命运也是令 人哀叹不已的(注:数奇,谓命运不好。语出袁宏道《徐文长传》:“先生(指徐渭)数奇不已,遂为狂疾, 狂疾不已,遂为囹圄。”按,不独徐渭命运数奇,李贽亦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罪名被 杀;汤显祖则以不附权贵而被议免官,告老归田,亦从此歇笔。)。
三、“从心所欲不逾矩”
面对这个“心”的解放与自由,如果没有内在心性工夫的人,是很难得到这个“自由”的 。这本身就是一个二律背反的矛盾:既要存“天理”,“人欲”又不能尽灭;既要纵情声色 ,又要保持清净超脱之心。对于这个矛盾,孔子早就说过这样的话:“从心所欲不逾矩。” 可 以看出,孔子并不否定人的正常欲求,对于名利、财富、色声、香味从未有过鄙薄和厌弃。 对于美味食物,孔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乡党篇》)对于财富,他说:“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 不去也。(《论语·里仁篇》)在孔子看来,“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论语·述而篇》)孔子的态度是财富多一点没关系,但在获取财富的途径 上应遵守“道”的规定,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对于仕宦功名,孔子也说过“学 而优则仕”(《子张》)、“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卫灵公》)这是不是说,孔子思想 深处充满着矛盾呢?他一方面大讲“贫而乐”、“忧道不忧贫”、“君子固穷”之类的话 ,另一方面又极重视人物质生活和自然欲求。其实,恰恰在孔子的这些矛盾论述中,我们发 现 了他的真实想法:“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是孔子的智慧,也是真儒的境界。借用佛家的 话,就叫做孔子“中道”观:“从心所欲”,代表着客体满足主体自我纵欲的需要,但如果 “率性而为”,放纵心去追逐物欲的话,人就会堕落为“穷人欲”的“人化物”;所谓“不 逾矩”,这个“矩”就是“仁”,就是“礼”。孔子说“克己复礼谓仁”(《论语·颜渊》 )。“克己”,并不是指人欲一旦与礼义发生冲突,应竭力克制自己的物欲而必须让位于礼 义 ,相反,它意味着人应该在伦理道德的范围内使自身臻于完美完善。所以,“克己”这个概 念意味着修养心性;“复礼”意味着“克己”修身养性所达到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而“ 仁”则指称通过道德的修身所达到的最高的人生境界和生命境界。所以只要“不逾矩”,你 就 可以“从心所欲”,喜怒哀乐、饮食男女、富贵名利都值得人去追求。有了这个“矩”就把 人的情感欲望等物质欲求导向道德情操和伦理规范。
面对着这个“天理”和“人欲”的矛盾,和李贽交情深笃的焦竑(字弱侯,号澹园)看得最 明白。他认为佛经所说,最得孔孟“尽心至命”的精义。下面一段话可以说论到了“根源处 ”:
孟子曰:“尽其心,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天,即清净本然之性耳。人患不能复 性,性不复则心不尽。不尽者,喜怒哀乐未忘之谓也。由喜怒哀乐变心为情。情为主宰,故 心不净。若能于喜怒哀乐之中,随顺皆应,使虽有喜怒哀乐,而其根皆忘。情根内亡,应之 以性,则发必中节,而和理出焉。如是,则有喜非喜,有怒非怒,有哀乐非哀乐,是为尽心 复性,心尽性纯,不谓之天,不可得已。[9](p.261)
何谓“天理”?天理就是人的“清静本然之性”。何谓“人欲”?人欲就是人的喜怒哀乐。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尽心复性”,如何才能达到“有喜非喜,有怒非怒,有哀乐非哀乐” 的境界呢?孔孟子之言往往是“言约旨微”的。焦竑的阐释则是运用了佛教的唯识论和六祖 慧能的“于念而离念”:
意者,七情之根。情之饶,性之离也。故欲涤情归性,必先伐其意。意忘而必固我皆无所 傅,此圣人洗心退藏于密之学也。曰:“圣人无意,则奚以应世?”曰:“圣人应世,非意 也,智也。”“意与智奚辨乎?”曰:“于意而离意,意即智矣。以智而为智,智亦意矣。 染净非他,得丧在我,如反覆手间耳。”[9](p.7)
焦竑是这样来打通儒释之间的对立的:实际上这个“意”就是佛教唯识学上讲的第七染污 知 识,也就是他说的“七情之根”。人的喜怒哀乐皆由此出,所以人心不净。如何使染污意识 转为清净的意识呢?佛教讲“转识成智”,禅宗讲“于念而离念”,就是在念头上下工夫, 一念之转,这个“意”就转为“智”了。这个“智”不是指那些谋略、聪明、伎俩之类的世 间智,它是佛教称的般若智慧。(注:般若,梵语prajna,汉译“智慧”。《智度论》四十三曰:“般若者,秦言智慧。一切 诸智慧中最为第一。”)焦竑说,如果把这个“智”错认为世俗智慧,那么这个 “智”又被染污成“意”,成为第七染识,即是我执法执,而“染”与“净”都由“我”这 个第七识来决定。这个“智”就是清净的意识,即是处于“思虑未起,物欲净尽之时”,也 就是“圣人应世,非意也,智也”的意思。故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难怪焦竑说,这是孔子的顿悟法门,与六祖丝毫无异[20]。处在这样状态,的确不被外界环境所左右 ,“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王弼语)。能作到这点,也就得其佛教之“中道”,跟儒 家讲“允执厥中”、“喜怒哀乐未发之中”的“中庸”之道是一致的。理解了这一点,也就 理解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颜渊的“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境界真义所在, 也就理解“孔颜乐处”的真义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明道”和“智慧”顶点上,佛学 与儒学,正是“撞破乾坤共一家”了。
焦竑的在王学之后无疑是一个具有博大精神的继承者。他对明代的儒学是不满的,他认为 孔圣之学的局限,是因为“言约旨微”,循此以求“尽性至命”之理,并不容易得其要旨。 而汉宋儒家的注疏又只能“玩狎于口耳”,对孔孟思想“精髓”的了解,不但没有帮助,反 而尽得其糟粕:
夫释氏之所疏,孔孟之精也。汉、宋诸儒之所疏,其糟粕也。今疏其糟粕,则俎豆之,疏 其精,则斥之,其亦不通其理矣!”[21]
正因为如此,他大胆以佛教教义注解儒家“心性”之学,他认为佛教所发明的真理与孔孟 相同:“故释氏之典一通,孔子之言立悟,无二理也。”[21]用佛教经典解释孔孟之学,不 仅精要简便,并且通过“学佛而知儒”,实在是最好不过。
从周敦颐、王畿、罗汝芳到焦竑,我们可以看到宋明思想家如何苦心孤诣地为复兴儒学而 努力。尽管象王畿、罗汝芳、焦竑等人与朱熹、王阳明相比,还算不上那个时代的硕儒, 但他们也深深地懂得真正意义上的儒学复兴应该重新回到孔圣之学。然而孔孟之义往往“言 约而旨微”,如何重新阐释孔圣儒学?历史给了佛学这样一个机遇:通过“学佛而知儒”。 如 果没有佛学的加入,尤其是禅学在“体”“用”方面,即本体论和方法论上开掘资源的话 ,宋明时代的思想家在“心性”之学的建树上是不可能达如此辉煌而灿烂的成就,所以,这 一 次回归儒学已经不是原有意义上的回归。也许有人看到,为什么大多理学家又往往入佛而排 佛,其实仔细考察起来,发现他们反对的也仅是佛家那些没有尘世观念的,如“无父无君” 、“不孝无后”等不符合儒家纲常伦理教义的东西,而对于佛典之精华和禅宗的心性工夫则 是全面而深入地吸收,这在思想史上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至于后期佛学的空疏和禅宗的非 理性给儒学发展造成的障阻,这是当另文撰述的问题,在此恕不赘了。
标签:儒家论文; 周敦颐论文; 国学论文; 孔子论文; 禅宗思想论文; 心性论文; 人欲论文; 宋明理学论文; 活泼论文; 佛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