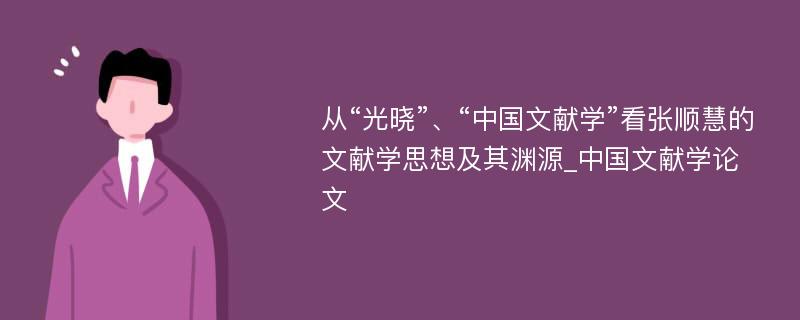
从《广校雠略》和《中国文献学》看张舜徽的文献学思想及其渊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献论文,渊源论文,中国论文,思想论文,广校雠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著名的古典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学识渊博,贯通古今。他在文字学、史学、古典哲学等领域造诣颇深,同时,他在长期的治学生涯中进行了大量古典文献整理工作,为其文献学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因此,从这位典型学者身上我们可以窥见20世纪中国古典文献学理论研究发展的全影。[1]
张舜徽的文献学思想充分体现在其80年代的一部奠基性著作《中国文献学》中。这是一部继40年代的《广校雠略》之后的又一部文献学理论专著。前者是后者的发展,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加以发凡与扩展的。不同之处在于:《广校雠略》的体例,注重史料之引证,而观点往往通过各章节标题注明,许多论断具有启发性,诚为治学经验之结晶;《中国文献学》改变了这种以文言与札记为主的表述手法,较多地以叙述与白话作辅助的方式阐明内容,识见较前者更加广博深邃。另外,体例较为条理有序,并在最后两编增加了对今后的设想。至于对文献学之范围划分,二者是前后相因的。《广校雠略》的文献学范围及其所及内容,囊括已相当广泛,当是继郑樵、章学成之后对校雠学范围的又一次广而大之。80年代,张先生整理旧稿,重新补充归纳,写成《中国文献学》。而此时的文献学,已是以“国学”为底蕴,以“史学”为归宿的一部通人之学,称其为“经、史、子、集无所不包的国学即神州之学”[2]亦不为过。这部文献学著作最终将我国古典文献学的范围推至至极。张先生的“广校雠”思想与现代倡导的“大文献学”观有着如此相似的情愫渊源,正契合了“文献学”本身博大精深的学科特点,也阐释了“文献学”研究及学科构建之艰的合情合理性。’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张舜徽的这两部文献学理论著作来考察其文献学思想,并对这种思想的学术渊源略作阐述。
1 以“校雠”包举无余的文献学——《广校雠略》
张舜徽在《自序》中叙述其治学生涯说,“张舜徽少时读书,酷嗜乾嘉诸儒之学,寝馈其中者有年。其后涉猎子史,兼览宋人经说,……乱中逃串四方,饥寒相捣,温经校史,浏览百家,穷日夜不辍,积之十年,始于群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稍能辨其源流,明其体统。” 所以,《广校雠略》是作者长期治学研究之归纳和发挥。他的撰述思路与目的是,“首证校雠之名,次辨著述之体。”[3]至于“部类分合之际”,“乃效郑氏(郑樵)《通志·校雠略》。”[4]其行文方式酷似郑樵的《通志·校雠略》,读《广校雠略》确有读《通志·校雠略》的感觉。
1.1“广校雠”文献学思想
张舜徽对于从汉代刘向开始,历代相沿持续之校书事业,统称之为校雠事业。他认为,“目录、版本、校勘,皆校雠家事也。但举校雠,自是该之。”[5]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鉴于学界有称目录学之名。作者认为,目录学不能独立为一学科;因为,其一,校雠的最重要作用,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校书成才有目录出现,如果从学术角度看,校雠是学术,目录是成果;其二,从历史角度看,郑樵、章学诚皆不用目录之名,因目录是从校雠而来,用校雠两字,已包含目录在内。[6]
从《广校雠略》的篇目题名及所及内容,可了解其内容范围包括:①著述体例论;②注释流别论;③书籍流布论;④目录体例论;⑤部类分合论;⑥校勘方法论;⑦审定伪书论;⑧搜辑佚书论。可见,其确是总体的文献学研究,犹如现在的文献学研究的范围,已经属“广校雠”文献学。
1.2 文献体式研究
《广校雠略》在文献研究上的贡献,首先是提出了文献体式的研究。[7]他在《著述体例论十篇》中说,著述是一件非常严谨郑重之事,而古代著述都可视为史料,“著述”的标准是研究性著作,即能作到发前人之未发,自成体系。“编述”则是参考前人著作,进行新的体系组织和内容加工;“钞纂”则是汇辑编排史料成书。他指出钞纂的体式是一般的书籍,不可比之著述。
1.3 关于文献分类与著录的见解
《广校雠略》在“部类分合论七篇”展开论述,包括:五经总义;起居注与实录;纪事本末;史抄;时令;谱录宜归类书;小说。
1.4 关于校勘、辑佚的讨论
张舜徽用较大篇幅讨论了校勘、辑佚、辨伪等问题,提出校书方法六篇,如《不可轻于改字》、《取相类之对校》、《据古注以校正文》、《类书及古注不可尽据》,颇有见地。作者还特别提出辑佚一事乃学成之后的事,确是其经验之谈。
2 以“国学”为底蕴、以“史学”为归宿的文献学——《中国文献学》
从《广校雠略》(1945年出版)到《中国文献学》(1982年出版),时隔近40年。此时的张先生已近古稀之年,硕果累累,著作等身,享誉国学大师、史学大家、古典文献学的奠基者。其文献学思想已达登峰造极的学术境界,体系构建亦显高屋建瓴之势。读之,不禁深深叹服于作者的博大精深与真知灼见,油然而生矢志整理古典文献的激情与责任感!此概因已是国学大师、朴学殿军的张先生,国学根底极为丰厚,在《广校雠略》形成的文献学思想的基础上,《中国文献学》体现出的思想更为宏伟壮阔,更具有国学底蕴,这在其前言与绪论中是有所表露的。
该书分十六编六十章,第一编绪论阐述了文献学范围和任务,古代文献的材料和散亡等。其余各编分别叙述了古代文献的著作、编述体例、钞摹、写作的模仿、讹托、类辑等,对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历代校雠学家整理文献的业绩,都作了总结;最后就今后整理文献的主要目的、重大任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认为,过去的校雠学相当于今天的文献学。我们应“继承过去校雠学家们的方法和经验,对那些保留下来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提供方便,节约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方面,做出有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8]显然,“文献学”直接继承了“广校雠”并具有更深广的内涵和外延,它是适应时代需求和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他认为,不独刘氏父子校书密阁,既如郑玄遍注群经,司马迁写成《史记》,“如果从史家的眼光去估计他们的成绩,也不过是替我们整理了一部分文献资料而已。[9]他盛赞梁启超的“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论断。可见,作者与梁启超的观点一致,主要是从“史学”角度以“国学”胸襟考察文献学,构建其内容体系,认为中国文献学就是古代校雠学的延伸和发扬,是文史研究者所必备的辅助知识和技艺,并非一门独立的学科。
张先生的文献学思想非单止于“史学”,更具强烈的“国学”色彩,充分体现出他的“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他在《前言》中指出:“文献学的内容是很丰富的,所以我们整理文献,绝不可局限于校勘、注释几部书就够了,而要担负起的任务,却大有事在。”他又在《绪论》中重申,研究、整理历史文献,“不是我们的落脚点:这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为整理而整理,而是心怀大志,朝着一个宏伟的目标而努力不懈,不仅有大出息,而且可以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他举“司马迁写《史记》”、“马克思写《资本论》”为例,“由于他们有雄伟的气魄,庞大的规模,为了要撰述一部总结性的巨著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最后满怀激情发出号召:“这是我们的绝好榜样。我们要有雄心壮志,朝着前人已经开创的道路前进!……编述为有系统、有剪裁的总结性的、较全面、完整的《中华通史》,使全国人民得从这里面看出悠久而丰富的全部文化,因而油然而生爱国之心。”
因此,有人认为,“张先生对文献学的划分可理解为历史文献学的范畴。”[10]还有人说“其文献学的内容,几乎是国学的翻版。”[11]是“‘文献’名目下的‘国学’。”[12]
3 博观约取,厚积薄发——张先生整理古典文献的丰硕成果
张舜徽这种“会通”的“大文献学”思想(或“广校雠”观),是有其实践基础的。他一生潜心做了大量的历史文献整理工作,共撰写了论著52种,结集为专著25部,约850万字;另主编5部著作。内容涉及经、史、子、集,体现了一位国学大师的风采。关于经学的研究,张氏出版或发表了《两戴礼记札疏》、《毛氏故训传释例》、《郑学丛著》、《小尔雅补释》、《演释名》等论著;关于史学的研究,张出版或发表了《汉书·艺文志通释》、《史学三书评议》、《中国古代史籍举要》、《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中国史论文集》、《清儒学记》、《劳动人民创物志》、《中华人民通史》等论著;关于子学研究,张出版或发表了《周秦道论发微》、《敦煌本说苑残卷校勘记》、《世说新语注释例》、《清人笔记条辨》等论著:关于集学的研究,有《清人文集别录》等论著。他对文字、音韵、训诂、校勘、注释等国学基础,深入研究,无所不精。几乎每一部论著,都是他历经多年的潜心研治、长期积累而成,所著200万字的《说文解字约注》,竟历时50个春秋!80年代初始成的这部《中国文献学》,之所以能成为我国古典文献学的奠基之作,正是作者长期整理和研究古文献,不断梳理、思考、总结、积累的成果—从《广校雠略》到《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再到《中国文献学》。正如他自己所言,“盖著述之业,谈何容易!必须刊落声华,专意书史;先之以十年廿载伏案之功,在益以旁推广揽披检之学,反诸己而有得,然后敢着纸笔。”[13]他这种为文思想无不体现在其诸多文献著作中。
4 博采众家之长,终成自得之学—张舜徽文献学思想渊源
可以说,我国现代文献学的产生与张舜徽的“广校雠思想”和“大文献学”(古典文献学)观不无关系,他对我国整个文献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实具筚路蓝缕之功。但我认为,他这一富有开创性的文献学思想的直接渊源当是郑玄、郑樵与梁启超。
4.1 郑玄、郑樵的文献学思想
张舜徽在《广校雠略 自序》中说其“於汉宋诸儒,独宗二郑”。他对郑玄与郑樵的文献学思想与贡献是推崇备至的,“以为康成经术,渔仲史裁,譬诸灵海乔岳,无以益其崇深”[14]
广校雠文献学创始于东汉郑玄。[15]“经有数家,家有数说,”于是郑玄从文献入手解决学术纷争,遍注群经。其文献学方法包括“一备致多本,择善而从;二注明错简,提出误字;三考辨遗编,审证真伪;四叙次篇目,重新写定;五条理礼书,普加注说;六辨章六艺,阐明体用”。[16]可以说郑玄不仅是经学家,更是开辟文献新路的文献学家。张舜徽深明其意,认为“‘经学’二字,本不足以范围他。”[17]他还说,“我那种打算总结郑玄在校雠学上的成绩的想法,积累了多少年。一直到六十以后,才重温旧业,整理旧稿,区处条理,写成《郑氏校雠学发微》,偿吾夙愿。”[18]
郑玄为张舜徽的文献学思想提供了广泛整理研究古文献的实践体验之源。而张关于文献学的“通学”思想以及由小学入史学的学术路向则是受了郑樵学术生涯的深刻影响。
郑樵是南宋史学家,也是第一个以专著形式系统讨论文献学的,其《通志·校雠略》从理论上阐述了文献工作的各个环节,名之曰“校雠’,但这是个广义的校雠,张舜徽仿其体例做《广校雠略》,进而发展为《中国文献学》。郑樵大力提倡“会通”思想,“会”就是把各种史料、书籍加以搜求、汇集和整理,为修通史做准备;“通”是将各种史料、书籍按时间先后加以整理、编排,寻求源流,理出线索,撰著成通史。他毕生的目的是“集天下之书为一书”,写成一部无所不包的通史。所以他“不应科举,居夹山下刻苦力学三十年,出门访求书籍十年。”[19]并且“进行实地考察,访问田夫野老,用力极勤。”[20]张舜徽对郑玄的精神最为佩服,曾多次提及,也是沿着他的学术路向治学的。
4.2 梁启超的广义史学
张舜徽在《中国文献学》第一页的《前言》中即引用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所说,“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以这句话作为展开全书的立论之点,并说,“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雠学家。所以,校雠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21]所以其文献学思想是与梁的观点一脉相承的,都不承认文献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梁启超多次使用广义的史学,其意义在于强调,清代考证之学都是在古典文献范围内的研究,所以梁用广义的史学—文献学来表述。关于广义史学—考证学一文献学的同义,是梁文献学观点之一。
之二,是“国学—文献的学问”的观点。他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一文中说的两条大路,一为文献的学问,二为德性的学问。指出做这类文献的学问,要达到三个标准:①求真;②求博;③求通。用文献学知识学习传统文化,加强自身修养与德性,是文献学的重要作用。他这一思想影响了人们的认识,提高了文献学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