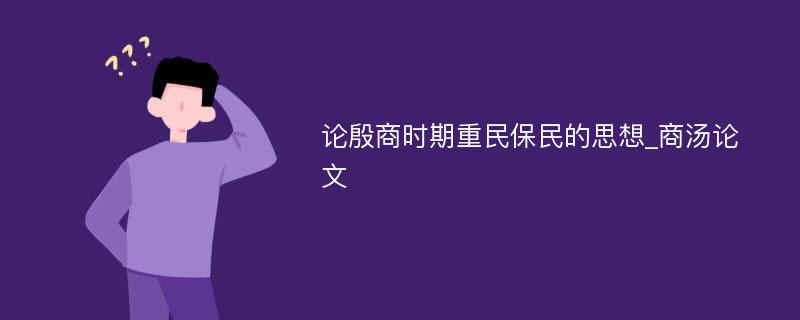
殷商时期重民保民思想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民论文,殷商论文,刍议论文,时期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07-0022-05
“民”作为与统治者相对的阶层,既是任何统治者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又是统治者财用的来源,因此,重民保民并不是封建社会才出现的事情,在奴隶制相当发达的殷商时代也同样存在。事实上,我们不仅能从商代的每一位明王贤臣那里看到重民保民思想的存在,而且他们的思想直接影响并构成了西周初年民本思想的最基本内容。研究殷商时代的重民保民思想,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殷商社会和弄清西周初年民本思想的来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对民众力量的关注往往产生于王朝更迭或政权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一方面因为旧王朝失去民心,在民众的反叛声中行将崩溃;另一方面新兴的反对势力又要依靠民众的力量推翻旧的统治,这时正反两方自然都会感受到民众力量的重要,他们都会主动总结王朝覆灭的原因和提出相应的重民保民主张。殷商时期的重民保民思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我们在《汤誓》中能够清楚地了解商汤伐夏的原因是由于夏王朝统治者夏桀的暴虐。他滥用民力,残害民众。《汤誓》中这样写道:“今而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舎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夏王朝的统治者所犯的罪过正是不保民。商汤说:“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桀的暴虐致使民众无法忍受他的统治,宁愿和他一起灭亡。他的丧失民心的残暴统治成了商汤伐夏的最充分理由。或许我们可以说,夏王朝的统治者尚没有重民保民的意识,但是从商汤的言论中我们却可以十分明确地感受到他对于民众的重视,而事实上,他正是利用重民保民这面旗帜灭掉夏王朝的。
商汤不仅在灭夏的战争中高举保民的旗帜,他还时常告诫臣下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要有功于民,保民为安。《汤诰》的原文已经散佚,但《史记》有这样一句援引文字:“毋不有功于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罚殛女,毋予怨。”大禹、皋陶、后稷都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学习他们勤力办事,有功于民,否则我们同样有丧国的危险。[1 ](殷本纪)
商汤时期的重民保民思想大致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明德慎罚。这是周初统治者给商代圣王们的德政所做的总结。在《多方》中,周公这样回忆道:“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慎厥丽,乃劝。厥民刑,乃劝。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劝。”周公所讲的“德”内容极为广泛,在当时,似乎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可以纳入德的范畴。诸如敬天法祖、怜小民、慎行政、行教化、慎刑罚等等都属于德的内容。周公在这里为了给各诸侯树立一个完美无缺的榜样,或许有拔高商汤的地方,但其基本事实应该是存在的,否则这个榜样也很难取信于大家。这样的语言我们也可以在《逸周书》中看到。如该书载武王言:“我闻古商先哲王成汤克辟上帝,保生商民,克用三德,疑商民弗怀,用辟厥辟。”此话出自周人之口,看来商汤能助上帝保养下民,也成了殷之敌人学习的榜样。(二)“以民为监”。商汤说:“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1](殷本纪)这与后世所说的“以民为监”、 “以水为监”没有什么两样。史传商汤在街巷设置厅堂,以搜集人们的批评和建议[2](桓公问), 足见这位商代的君主的确有一定程度的重民保民意识。(三)有一定的裕民措施。晁错在《论贵粟疏》中说道:“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瘠者,以蓄积多而备先具也。”蒙受数年的旱灾而国民无恙,自然有一定的裕民措施作保障。《孟子·梁惠王下》说,商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孟子的这些话显然是夸大之辞,但我们结合《尚书》看,其中的部分内容还是可信的。商族部落在商汤之时战胜其他部落乃至夏王朝,这是事实,他能取得成功,除了拥有强大的实力支持外,别无他因。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商汤统治下的商族部落是一个富足而有德的部族,正因为这样,众多的小部族才愿意依附于他。(四)从平民中擢拔贤才。这是商汤德治的一个方面,也反映了这位君主对于平民的态度。伊尹被重用时为有莘氏滕臣,地位低微。通过现有的史料我们无法知道商汤时期有多少类似的事情发生,但擢拔伊尹一事影响是巨大的,它至少反映了统治者对于平民人才的关注,并由此提高了统治者对于平民的重视程度。而事实上这种影响的确是存在的,伊陟、巫咸、傅说等大臣的被任用说明商代的统治者在选用人才上确实没有忽略平民这一阶层。
当然,商汤的重民保民思想还带有浓厚的原始气息,甚至与传说中尧舜禹时代的原始民主作风十分相近。这说明商汤时期的重民保民没有上升到制度化乃至理论化的高度,还处于质朴的政治行为阶段。但我们不能由此否认这种思想的存在,而事实上,在早期国家的形成之初,部落的酋长们主要依靠为民众谋求生存之道获得民众拥护,所以从那时起,立志做国君的部落酋长们就已经明确意识到拥护他的人越多,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3]。商汤也不是一个例外。因此, 重民保民思想在商汤时已经产生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二
在商汤重民保民思想的教化下,商代初年形成了重民保民的政治特色,而这种政治遂成为整个商代乃至于后世效法的典范。商汤死后,太甲即位,由于不守“汤法”,权臣伊尹大概发动了一场政变废黜了太甲,并把他囚于“桐宫”,让他悔过自新。如果不是因为他弄明白了商汤之法已经成为不可改弦的圣典,桐宫里的日子恐怕不仅不会结束,杀身之祸也未必不会到来。
可是商代的第二位君主便意欲抛却保民重民政治,所幸有伊尹等一批老臣的坚持,所以才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是变化却成为必然的趋势。所以到了太戊的时候,伊陟叹息:“帝之政其有阙与?”[1 ](殷本纪)看来在这个时候,商汤的德政已经有了极大的变化。在太戊至于盘庚间,我们没有再发现多少有价值的德政信息,正是这种变化的趋势使然。
因为太戊到盘庚间德政的荒废,各种矛盾不断激化,商代政局出现了连续九世的动荡。长期的政治动荡,搞得民不聊生,到了盘庚时期,德治不得不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盘庚迁殷的原因有众多说法,但要缓解各种激化了的矛盾和重振商汤时期的德政恐怕是他最迫切的初衷。从商汤到盘庚,商王朝已经有五次迁都的记录,而“九世之乱”也发生在五次迁都期间,因此迁都与政治上的变故绝对不会没有关系。多次的权争之乱使商汤行德政而创建的基业败损殆尽,所以,盘庚之初“诸侯莫朝”,而且“殷民咨胥皆怨”[1](殷本纪)。 年青的盘庚在没有传统旧势力的支持下,只有再次效法先王迁都的方法来稳固自己的统治。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迁都,贵族当政者当然会不同意,盘庚于是打出了三张王牌:(一)迁都是遵循上帝的旨意。盘庚在讲话中既说迁都是“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又说自己“非敢违卜,用宏兹贲”。[4 ](盘庚)在一个信奉上帝的国度里,搬出上帝来,自然是最有威慑力的。(二)迁都也是先王的旨意。盘庚在说服他的“蓄民”时说,眼下政治上的过失已经使我们的先王对我们很有意见,不随我迁都,先王将降灾惩处我们。在商代,先王如上帝一样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先王既同意我们迁都,历史上的先王又多次迁都,我们又怎么不能迁都呢?(三)迁都又是“恭承民命”的需要。德政的长期破坏,贵族当权者“乱政同位,具乃贝玉”,已经使阶级矛盾到了“不能胥匡以生”的地步,贫苦的百姓在旧的居住地面临着“尽刘”的威胁。“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而且“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我们也应当像先王一样重民保民,用迁都的方法来拯救他们。
尽管盘庚迁殷的动因不全是“恭承民命”,但它却结束了长期的政治动荡,使商汤时期的重民保民思想得以延续和发展开来。盘庚的重民保民主张至少包括以下两个内容。首先,他要求这些贵族们要“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4](盘庚)。其次, 根据官吏重民保民的实际行动决定其升黜。“予其懋简相尔,念敬我众。朕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4](盘庚)《史记·殷本纪》上说, 盘庚迁殷后,“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德政的效力再一次显现,使得商王朝在盘庚时期再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也因为盘庚继承和发展了商汤的重民保民思想,所以后世商代百姓对盘庚时时铭记在心。[1](殷本纪)
由于材料的缺乏,我们无法了解盘庚重民保民思想的更多内容,但他将“念敬我众”与否作为官吏升黜的标准显然是重民保民思想的一大进步。他使这种思想在政治生活中变成了一种制度,从而增强了它的生命力和它对后世的影响力。武丁时期保民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与此不无关系。
三
武丁少年时,长期生活在民间,对民众的疾苦有相当的了解,加上受传统重民保民思想的影响,似乎也进一步认识到了民众对于国家兴亡的重要意义。因此这一时期的重民保民思想又有了新的突破,提出了“敬民”的观点。
《高宗肜日》中有这样一段话:“惟天监下民,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绝命。”尽管天在这里仍有不可撼动的权威,但是民的命运也有了自决。那些“不德之民”甚至可以对天命提出质疑:“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更为可贵的是在本篇中提出了“敬民”的主张。出于民人已有自决的意识,也出于不德之民对天命的质疑,祖己呼吁:“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昵。”如果此篇出自祖庚之时,这应是历史文献中“敬民”一词的最早记载。
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敬民”出现于武丁时期显得过于突兀,不过回顾一下殷代重民保民思想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敬民”思想在此时出现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商代初年商汤便提出“以民为监”的主张,这种主张已经包含了相当程度的重民保民因素;在盘庚时期进而提出使用官吏要看他是否能“念敬我众”、“鞠人谋人之保居”的观点,在这里盘庚的“敬众”和武丁的“敬民”不过是文字上的差异罢了,从“敬众”到“敬民”自然地也不是什么突兀的变化。再之,从商汤到武丁,商代历经了十数次的兴衰治乱,历史已经不止一次地验证了商汤提出的“以民为监”的政治主张的重要意义,事实业已说明德政是通往治世的不二法门。武丁即位,“亮阴”三年,观察国风,思忖历史,我们有理由相信最终要得出一个“敬民”的结论对于他和他的大臣们来说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武丁时期,“天下咸欢”[1](殷本纪),这是商代最为繁荣的时期,成绩的取得是武丁时期“修政行德”的结果,也是其重民保民的结果。
当然,武丁时期对上帝鬼神的崇拜仍是思想上的另一条主流,它在人们的宗教生活中仍占据主导地位。然而现实生活毕竟是人具体操作的,单纯地依靠鬼神显然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卜辞的形式反映了人们对鬼神的崇敬,但卜辞的内容大多数是涉及国计民生的世俗问题。如一期卜辞中大量的“受年”、“受禾”、作田、免馑内容都不同程度显示了商王对于民生问题的关注。
事实上,鬼神崇拜在“天顺民意”或“上天佑民”的观念下与重民保民思想并不冲突。因为在这时,“天”和“人”的利益是相同的。“天人”是协作的关系,“天”地位的提高并不妨碍“人”地位的改善。这正是盘庚、武丁时代卜祭盛行,而重民保民思想却有长足发展的原因。
不过自然的天从来不会按照人的意志运作,它时常“降戾”于民,有时甚至弄得民不聊生。然而,在重民保民的背景下它这样“做”,只会影响它的前程。因此,在武丁时期便出现了人们对它的怀疑,而到武乙时期更发展成为对天公开的挑衅。商王武乙时,“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1](殷本纪)。在崇神的时代, 武乙以射天为戏,似乎是一个壮举。不过仔细回顾商汤以来民人地位的变化,天神沦落到这般地步,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董作宾、张光直、伊藤道治等将商代的祭祀形式以祖甲为界分成新旧派两大系统,旧派卜事多且繁,新派卜事少且简,反映了新派对于人事的重视。[5](P108)这种看法颇有见地,但并不全面。 旧派不仅重卜,且又重民;正因为如此,新派当政时期才出现了对天神的直接挑衅行为,而这时民已经冲破了部分神(尤其是天神)的局限,地位更有所提高了。
事实正是顺着这样的趋势发展的,在商王纣的时候,天神的地位彻底动摇了。商王纣是一位彻头彻尾的暴君,然而他的“暴”正说明了人们对个人能力的自信,只有摆脱了上帝的枷锁,把上帝的所谓惩罚置之脑后时,才有了纣这种肆意违背天命的暴虐。在《尚书》中多处记载商王纣“弗敬上天”、“弃绝天道”、“昏弃厥肆祀弗答”等,人们往往以商纣王一句“我生不有命在天”认定商纣王临死仍迷信上天会保佑他,但我们联系上下文不难看出这是商纣王对祖伊诘问的一个肯定的回答,否则就不会有下文祖伊的反驳。[4 ](西伯戡黎)不仅商纣王“弃绝天道”,商朝的民众似乎也没有把天道放在眼里。“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沉酗于酒,乃罔畏畏”,“今殷民乃攘窃神祇之牺牲,用以容,将食无灾。”[4](微子)把牺牲吃掉,也不怕灾祸降临,只能说明殷民原本就没有把那个上帝放在比自己生命重要多少的地方。
对上帝的蔑视追根求源来自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它是商代民众地位不断提高的必然结果。民在历史的演进和被重被保中逐渐意识到了个人价值的存在,从而在面对上帝和下帝(商王)的威胁时显现出了他们自身的力量。商末“小民方兴”正是民众力量显现的写照。
“小民方兴”不仅撼动了上帝的地位,同时也构成了对下帝权力的威胁,这是商王所不愿看到的,商纣王的暴虐某种意义上说是因为他深深地感到了来自小民力量的威胁。然而在他与小民各自维护自身权益的斗争中,他失败了。他是在小民“天曷不降威”的诅咒声中失败的[4](西伯戡黎),这种声音在夏桀将要灭亡时也时常能够听到。历史为什么这样惊人地相似,因为原因是一样的,他们都失去了“民”的支持。
四
总结和反思殷商时期的重民保民思想,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殷商时期的重民保民思想来源于对夏王朝兴衰的总结。尽管它诞生于神权至上的时代,发展也极为缓慢,但它却没有停止不断发展的脚步。从商汤的“以民为监”开始,到盘庚的以重民保民的实际行动定升黜,再到武丁的“敬民”主张,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重民保民思想发展的轨迹。事实上,正是因为殷商时期重民保民思想的发展才促成了西周初年民本思想的诞生。周公的“明德慎罚”思想、“敬天保民”思想无一不能从殷商时期的重民保民思想中找到其渊源。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周公的德政思想原本就不是他个人和他的集体的创造,他们不过是把殷商时期的同类思想系统化罢了。
第二,“神”和“人”历来被认为是一对矛盾,但是人们创造了神,并不是有意要为自己创造一个对立面的,相反,他们是期望用他们的创造来保护他们,并为他们造福的。所以那些神祗们自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了助民佑民的责任,因此,神和人在质朴的社会阶段并不是一对矛盾,而是一种协作关系。所谓“神—人”矛盾的形成,那是统治者无能人治,靠装神弄鬼稳固和抬高自己地位以后的事情。殷商时期固然有不少帝王靠鬼神御民,但我们同时注意到那些明王们关切更多的是鬼神和人(或民)的协作关系,所以在崇神隆鬼盛行的日子里,并不妨碍重民保民思想的生成和发展。我们发现,盘庚、武丁时期卜辞最多,卜祭最盛,但重民保民思想也最为发展,原因也正在于此。
第三,在重民保民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中,尽管其根本动力来源于下层民众,但推动这种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层力量却并不是这些下层民众,而是那些有识之君和有识之士们。这一点我们不仅不能隐瞒,而且还必须给予充分的肯定。商汤的“视民知治不”思想,盘庚的“念敬我众”观念,以及祖己的“敬民”呼吁,无一不有力地推动了重民保民思想的发展,推动了古代政治文明水平的提高。
然而由于历史发展过分依赖于那些圣君贤臣们,使得重民保民思想的进步往往被人为因素所左右。夏商时代的兴衰消息是统治阶级的最好教材,商王朝的圣君贤臣们正是在这样的兴衰的教育中觉悟出了重民保民的重要意义。但要求统治者接受这种教育的权力并不掌握在下层民众的手里,教育和被教育的权力永远掌握在统治者的手里,他们可以接受这种教育去关注民生,他们同样也可以不这样做。下层民众演绎着历史的兴衰,统治者如果能从中有所觉悟,重民保民思想才有可能出现;相反,我们是无法看到民被重被保的结果的。也就是说,下层民众在重民保民思想的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根本无法显现,这是这种思想在阶级社会里发展的特点。
第四,在奴隶制时代,重民保民的范围是极其有限的,它不可能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最底层人群,所重所保之民至多是在政治生活中有所显现的自耕农及以上的“民”罢了。他们在有关商代的文献中被称作“众”、“众人”、“民”、“万民”、“蓄民”、“憸民”等。“众”或“众人”是商代农业生产和战争主要担当者,是商王朝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群众,要保要重是情理之中的事。至于这些称谓多样的“民”,也都是平民身份[6](P139)。而处于社会最下层的民——奴隶,永远是被奴役和杀戮的对象,他们是商王墓葬里的殉葬品。
第五,一个没有最下层民众参与的重民保民思想,说到底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阶级利益的安全而释放的一种怀柔声音,而无知的民众常极易陶醉于这种温柔的声音中,真的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太平盛世”,这是统治者最希望看到的结果。
正因为没有主体民众的参与,或者说主体无法参与,重民保民思想的发展失去了稳定性和可靠的支撑,它的进步也只能步履蹒跚,随着圣君的出现而出现,随着他的死亡而消退。纵观商代重民保民思想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汤贤而出,汤死而隐;武丁圣贤,也就随着武丁出现,武丁死去,连同他的思想也一并被带走,所以我们从商纣王身上看不到一点受武丁重民保民思想影响的痕迹。而后世的圣君贤臣们也只有在不断的重复总结中迂回发展这种思想,而他们也从来不会想过把这种思想推向民主的结局,这大概是民本乃至于民主思想在我国历史上发展迟缓的最终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