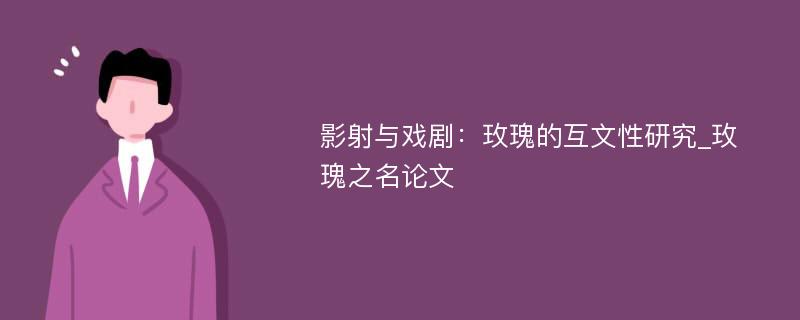
影射与戏拟:《玫瑰之名》中的“互为文本性”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名论文,文本论文,玫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意大利当代杰出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昂贝托·埃科(Umberto Eco 1932--)借以表现自己学术思想的文学侦探小说《玫瑰之名》(The Name of the Rose,1980, 以下简称《玫》)是一部已引起多层次、多方位探讨的奇书,本文拟就此书对其它侦探小说类文本的广泛借鉴做一番探讨,希冀从以“互为文本”(intertextuality, 以下简称“互文性”、“互文”)形式出现的影射(allusion)和戏拟(parody)的运用中窥见后现代主义文学观念对侦探小说这一传统文类(genre)的颠覆和反叛。
由侦探小说向玄学侦探小说的演进
在小说日益变得“多余”的当代,传统侦探小说是西方小说艺术中硕果犹存的“原始”形式。它的叙事结构具有层次分明、情节简练的特点,会为读者带来轻松愉快的阅读享受。
现代意义上的侦探小说始于1841年,这一年侦探小说鼻祖埃德加·爱伦·坡在《莫格街谋杀案》中首次塑造了杜宾这样一个私家侦探。1853年狄更斯在《荒凉山庄》中第一次使用“侦探”(detective)这个词来介绍一位检查官。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侦探小说已成为最受读者喜爱的文类之一。
传统侦探小说突出经典叙事(如神话传说、寓言、民间故事等)的三个基本要素,即顺序、悬念和结局。它把事件按照最容易理解或最吸引读者的顺序排列,设置一个跌宕起伏的悬念,最后的结局是“封闭式”的──读者无一例外地可以预见到正义的一方必定胜利,他所要做的仅仅是去预测取得胜利的具体形式或手段。在这类小说中善与恶是泾渭分明的,最扑朔迷离的奇案最终也会真相大白。一切细节都自有其存在的意义,即使这意义暂时尚不为读者所知晓。侦探小说崇尚理性,试图为读者在一个日益变得非理性的世界上开拓一片乐土。“侦探小说颂扬人类的理性,‘神秘事件’变为逻辑上的缺陷,世界变得容易理解了。”〔1〕因而这类读物通常被视为诱使读者逃避现实的文学。
当我们讨论小说时,“后现代”这个术语具体是指“元小说”(metafiction,又译作“后设小说”),而侦探小说中的“元小说”是“玄学侦探小说”(metaphysical detectivefiction,亦可译作“后设侦探小说”)。这是一种“反侦探小说”(anti-detectivefiction),这一项文类(subgenre)迄今为止已有几十年历史。黑克拉夫特(H.Haycraft)在评述切斯特顿(G.K.Chesterton)的神学侦探小说时首次使用了“metaphysical”这个词。〔2〕考虑到其渊源,笔者认为把它译作“玄学侦探小说”更贴切。
玄学侦探小说是一种借用侦探小说的形式来表现后工业化社会生活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旧瓶装新酒”,侦探小说的公式化情节成为“自我观照性”(self-reflexivity)的载体。它的写作者大都是为人熟知的现当代文坛大师,如阿根廷的博尔赫斯、美国的纳博科夫、品钦、阿斯特、法国的罗布-格里耶、瑞士的迪伦马特和意大利的埃科。
作为历史小说、哲理小说、神学小说和哥特小说的《玫》首先是一部侦探小说,它继承了自坡以来的主流侦探小说传统,符合侦探小说的基本定义:“侦探小说的关注焦点在于具体侦探过程的叙事。”〔3〕它要解决的问题是“究凶”(whodunit)。其次它又是一部玄学侦探小说,一部旨在表现作者理念和学说的自我意识小说。它以通过“互文”体现的影射和戏拟手段揶揄主流侦探小说,无情地颠覆它的常规模式。所谓“自我现照性”由嵌入小说中的含沙射影式的批评表现出来,它不仅是针对传统侦探小说、侦探小说批评的,也是针对广义的现代性话语,尤其是现代主义文学的。《玫》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大量互文正是以此为目的而设置的。
克里斯蒂瓦(J.Kristeva)为“互文”所下的定义是:一种(或数种)符号系统的易位,如小说便是宫廷诗、学术话语等几种不同的符号系统重新排列的结果。〔4〕埃科在这部长达几十万字的小说中不断不加诠释地引用前人的文本,他对经典侦探小说以及与侦探文学有关的所有文献的借鉴实质上是在以文学创作的形式描绘这一文类的演进过程。早在60年代,埃科便表现出对侦探小说叙事的浓厚兴趣。这可以从他对弗莱明(I.Fleming)的詹姆斯·邦德(即007)系列小说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研究〔5〕中窥见一斑。埃科认为侦探小说刻意牵着读者沿着事先确定的小径前行,谨慎地施展叙事才能,以便在适当的时候于适当的场合使读者产生怜悯、恐惧、激动或沮丧的情感。他把侦探小说叙事看作典型的“封闭”式文本,认为一个“封闭”式文本(即仅仅期待读者做出有限的、可预见的反应的文本)与一个“开放”式文本(即一个积极启发、诱导、训诫“典型读者”[model reader])的文本存在着差别。以“封闭”式文本出现的传统侦探小说的“吸引力、能带来的安详感和心理上的满足在于颓然倒在沙发上或火车座位上的读者可以不断一点一滴地获得他(在此之前)已经知晓、而且想再次了解的知识。这就是他买这本书的缘由。”〔6〕
埃科有意在高雅和通俗文学之间构筑一座桥梁,这座桥梁就是“标示”(marker)明显、容易为读者分辨出的“互文性”。“我发现了作家们早就知道(并且一次次告诉我们)的事情:一本书总会提到其它书,每个故事中都会讲述一个已经有人讲过的故事。”〔7〕初次当小说家的埃科对“互文”的工具式应用是在影射和戏拟中解构、重估传统和玄学侦探小说的尝试,也是以“自我观照”对当代文化符号学的图解。读者不仅须分辨其阅读经验中一个个被借鉴的文本,还要大致了解这些文本的文化—历史价值,否则便无法读出此书中的深层意蕴。《玫》中再度讲述的故事既有文学的,亦有历史的。鉴于本文预备将《玫》作为玄学侦探小说予以考察,笔者将只限于讨论文学的、与侦探小说有关的部分互文。
源于古典文学中与侦探行为有关的互文
1.侦探小说问世前,西方文学中最早的侦探行为大概要算希腊神话中俄底浦斯对自己身世的调查。后世以此神话为蓝本创作了许多作品,其中最负盛名的当数索福克勒斯的《俄底浦斯王》。这位西方文学中第一个“认知英雄”(congnitive hero),现代侦探的先驱在剧终时为自己弑父娶母的滔天大罪而痛不欲生,终于放弃王位、刺瞎双目、踏上了自我放逐的不归路。这时剧作家经合唱队之口道出了对狂妄者的劝诫:
“同胞们,第比斯人,瞧瞧吧,这就是了不起的俄底浦斯,
他猜中了斯芬克斯的谜,一度是我们国家里最有权势的人。
城邦中谁人不曾以为之倾倒的目光仰望他的英名?
如今他却陷入了无涯的苦难,面临灭顶之灾:
所以在他今生未已之前,切匆妄言哪个凡夫俗子是幸福的;
待他已永远安息,不再痛苦悲伤时再下结论也还不迟。“〔8〕
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类警诫对观众(读者)有“净化”作用。《玫》亦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后现代主义文学往往以“无结局”(non-solution)收场。虽然威廉和阿德索偶然地破译了墙上的密码、弄清了一系列谋杀事件的来龙去脉,但贯穿于《玫》的侦破工作亦没有结局,没有胜利者──大火吞噬了修道院以及几乎所有没被谋杀的修道士。也不妨说这个结局是死尸狼藉,一切归于灰飞烟灭。仿佛血腥味儿还不够浓,死者还不够多,阿德索又向读者交代威廉死于二十多年后“本世纪中叶”〔9〕的瘟疫。而阿德索本人也在篇首和末尾不止一次地提到:“如同尘世一样,我们垂垂老矣,”〔10〕“一只脚已迈进死亡的门槛。”〔11〕这些关于死亡的宣示预告都是对《俄底浦斯王》中合唱队对死亡进行的反思的反思,告诫世人勿对尘世过眼烟云般的荣辱盛衰过于执着。最后,阿德索对死亡将带来的“极度欢乐”、“无事可做、空旷无物的静寂、荒漠般的神学世界”〔12〕的憧憬,也隐晦曲折地表达了“凡夫俗子”不可能享有幸福的观点。
《玫》的结尾,面对一片混乱中的断墙颓垣,威廉告诉自己的学生:“要接受宇宙间并不存在秩序的想法是不容易的,因为这违背上帝的自由意志和他无所不能的权柄。所以上帝的自由即是我们获罪的缘起,至少是我们因自以为是而获罪的缘起。”〔13〕此话终于点明了《玫》的主题:人类认识世界的努力固然值得称颂,但是天道难违,永远无法企及终极真理。这是对豪尔赫反理智宗教狂热的批判,对威廉本人受逻辑演绎支配的失败的侦破工作的反思,也是对当代人狂妄自大、不可一世地企图“征服”自然(“自然”只是“天道”、“神”或“上帝”的更现代、更科学的同义词)的回答。
2.小说篇首,威廉师徒在赴修道院途中遇到一群修道士,威廉全凭缜密的逻辑推理便断定修道院长的坐骑丢失,并说出它的下落、外貌乃至名字:“它还可能有什么名字?对了,就连那位就要在巴黎当上校长的了不起的布里丹,他在逻辑学范例中提到马时也总是叫它布鲁纳路斯。”〔14〕这一番对走失马匹的推理源于伏尔泰的哲理小说《查第格》(Zadig)中同名主人公对一匹被盗马的下落的推断。〔15〕这是侦探小说问世前西方文学中又一例侦探行为。埃科曾在题为《角、蹄、蹠》〔16〕的文章中分析过查第格的推理,所用的语汇同威廉在小说中所用的相似。
3.在欧美侦探小说发展史上,作者无不为自己笔下的罪犯所采用的杀人方法绞尽脑汁。每一种新颖奇特的手段付诸笔墨后都会引起读者极大的兴致,同时也会使作者们懊恼──他们潜在的可选择方案中又少了一种。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评定侦探小说优劣的标准之一。故德昆西(De Quincey)将谋杀提升为一种艺术,从审美的角度探讨人类的嗜血性。早在1928年,范代恩(S.S.Van Dine)便在《侦探故事写作20条准则》中规定:“谋杀的方法以及侦破的手段都必须是合理的、科学的。”〔17〕
埃科异乎寻常地遵循了这一规则。在后现代文化范畴中,对规则的遵守很可能是以隐匿的方式反叛。在证明所谓上帝按照圣经《启示录》中关于七个喇叭手的预告施行惩罚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后,读者发现七宗凶杀案以四种方式进行。除第一宗阿德尔莫自杀、第四宗塞马里努斯被砸死、第六宗院长阿博被关在暗道里窒息而死之外,第二、三、五、七宗凶案中的受害人均死于毒药(豪尔赫先服毒自杀,后又被烧死),而下毒的方法恰与中国文学中的一个传说呈互文。一心一意要捍卫基督教教义的豪尔赫在禁书的每一页上都涂满了毒汁,书页粘连在一起,谁想翻阅就必须用唾液润湿指头方可揭开。就笔者有限的阅读所及,埃科为豪尔赫设计的方法在以往的欧美侦探小说中尚无人用过,倒见于与《金瓶梅》的成书经过和有关作者身份猜忖的记载。其中一种见于清代《缺名笔记》的说法是:
“金瓶梅为旧说部中四大奇书之一,相传出王世贞手,为报复严氏之督亢图。或谓系唐荆川事。荆川任江右巡抚时,有所周纳,狱成,罹大辟以死。其子百计求报,而不得闻。会荆川解职归,偏阅奇书,渐叹观止。乃急草此书,渍砒于纸以进,盖审知荆川读书时必逐叶用纸粘舌,以次披览也。荆川得书后,览一夜而毕,蓦觉舌木强澁#抵谝印P闹*
被毒……”〔18〕
这类传说共有12个“版本。”这个子报父仇的故事大同小异地“必是好事者所逞的口舌之快。”〔19〕
埃科是否读过这12个“版本”中的某一个:或是听别人转述过?巴特认为互文表明“生存于无限文本之外的不可能性”〔20〕,由此可见文本性的存在前提正是互为文本性,而互为文本性可以是有意识的参照,也可以是无意识地同以往作者思路不约而同所达到的同一境界。
源于传统侦探小说的互文
1.同几乎所有玄学侦探小说一样,《玫》也同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有千丝万缕的瓜葛。
有论者指出,“巴克斯维尔的威廉”定会使读者联想到柯南·道尔脍炙人口的名作《巴克斯维尔魔犬》。〔21〕“犬”隐喻侦探,故这是言之成理的分析。而且英文中“警犬”(sleuth)这个词的派生意义正是“侦探。”
而对威廉的容貌秉性的描述又是对另一个爱尔兰人、大侦探福尔摩斯的影射:“他比常人个儿高,因为瘦削显得更高。他目光犀利,洞察一切;薄薄的鹰钩鼻子更使他表现得机警。”〔22〕同福尔摩斯一样,他也常常沉溺于某种药物带来的幻觉而不能自拔。
在情节建构和叙事技巧方面两位作家的思路似乎很相像。如威廉对院长坐骑所进行的分毫不差的描述会令读者想起福尔摩斯常常在委托人开口陈述案情前便洋洋自得地根据其外貌推断出来人的身份、社会地位、人生经历等等。威廉与他的学生阿德索携手破案,并由阿德索来叙述侦破经过,这个人物自然是华生医生的翻版。埃科甚至在序言中称他为“麦尔克的阿德索或阿德生(Ad-son)。”〔23〕
2.埃科写作这部揶揄侦探小说的“反侦探小说”时自然不会忘记这一文类的鼻祖坡。坡的几篇以杜宾为主人公的小说在侦探小说形成气候之后均被视为范本,如《莫格街谋杀案》中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完全封闭的房间里,这类情节设置已成为经典笔法。《玫》中浪迹天涯、行为不端的修士萨尔瓦多在阿德索眼中活像“一个怪物”──“……额头很低,若是有头发也会同眉毛连为一体,那两道眉毛倒是又粗又浓。小圆眼珠滴溜溜转个不停……那鼻子简直不能唤作鼻子,因为两眼之间只是一根骨头,一隆起马上就又塌下去。”〔24〕这副尊容令人联想起《莫格街谋杀案》中不谙人类语言的毛猿,因为,萨尔瓦多“会说所有的语言,但又什么都不会说”〔25〕
《一封失窃的信》开创了侦探小说的另一程式──一件珍贵物品的失而复得。坡以后的侦探小说史上类似的情节层出不穷,如柯南·道尔的《波西米亚丑闻》便是运用心理演绎方法分析案情的佳作。埃科在《玫》中亦巧妙地运用了这一经典情节。小说中有一部书稿在侦破过程中不翼而飞,其内容直至卷终方为读者窥见一二。拉康认为在《一封失窃的信》中,每一个暂时得到信的人都依次使自己成为下一次行窃的牺牲品。在《玫》中,得到这部禁书的后果却是暴死。威廉认为书存在的目的即是被阅读,由此可见修道士们偷书,不惜出卖肉体甚至谋杀同道以得到书固然是罪过,但将书藏在不见天日的隐密处首先是犯罪。此罪引起彼罪,故读者不妨认为失窃的书本来便一直处于失窃状态。被人藏匿的书与失窃的信虽同为语言符号,意蕴却全然不同。前者所要表现的是权力对知识的支配,这是后现代主义文学所关注的问题之一。后者则只是文学研究中的一种象征或意符,因研究方法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意义。如拉康认为坡的故事将失窃的信作为能指,代表去势(部长因收藏信而被阉割,从而完成了女性化的过程)。〔26〕
有趣的是,《一封失窃的信》以及其它文本被戏拟的过程也就是“失窃”的过程。《玫》不但戏拟了传统侦探小说,也戏拟了侦探小说的读法。读者无须再在阅读中去发现真理,只要识别出那些似曾相识的“标示”便达到了阅读的目的。
3.除坡和柯南·道尔这两位侦探小说大家外,埃科还广泛采纳这一文类的发展史上各流派作家曾用过的各种笔法。密码、无懈可击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封闭的房间、迷宫式建筑、附录于正文之后的修道院平面图等均是30年代侦探小说“黄金时代”里塞耶斯、克里斯蒂等在“究凶”小说中用过的。这类小说中的侦探小说大抵都是单凭过人的智能、靠分析推理破案的波洛(Poirot)式“安乐椅侦探(armchair detective)。《玫》中的侦探不仅善推理,也同样善于行动。由于故事发生在远离人寰、孤零零矗立在荒野上的中世纪修道院中,威廉和阿德索的侦破工作不时需诉诸暴力和性事。这显然是对三四十年代美国“硬汉”小说的调侃。钱德勒等作家笔下的侦探为达到目的往往不择手段,威廉为解开谜团也不惜编造谎言。《玫》中的案情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罪案组成,有些是由侦破活动直接或间接引起的。这种一环套一环的情节设置是模仿“硬汉”小说的。这些侦破活动在结局到来之前始终令读者茫然如堕五里雾中。直到最后一刻作者才解开所有罪案之谜,揭露隐藏于其后的腐败社会现象。诸如此类的借鉴俯拾皆是,不胜枚举。它们都从不同的文本、逻辑角度证明人类的理性始终是可以信赖的,无论时代发生何种变迁。
源于当代玄学侦探小说的互文
《玫》中最机智、给人印象最深的影射和戏拟还是针对玄学侦探小说本身这一后现代主义文类的。与传统侦探小说中几乎所有杰作均具有相似之处的《玫》在此对戏拟进行再度戏拟,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自我观照性”表现得淋漓尽致。研究以互文形式出现的影射和戏拟,读者得以用批评的眼光重新审视一百多年来的侦探小说史。
埃科巧妙“借用”或“复述”的文本主要是博尔赫斯的玄学侦探小说。有研究者已注意到埃科对博尔赫斯及其有关作品的影射。〔27〕埃科自己也承认这些“春秋笔法”是为了向博尔赫斯“还债”〔28〕。
《玫》中的反面人物、视异教哲学为洪水猛兽的“博尔戈斯的豪尔赫”(Jorges de Burgos)是书中最值得研究的人物之一,他的名字是对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影射。博尔赫斯曾任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晚年双目失明。故事发生时,“博尔戈斯的豪尔赫”已失明多年,是修道院图书馆的前任馆长。“一座图书馆再加上一个盲人方可同博尔赫斯势均力敌。”〔29〕有论者曾指出,修道院的图书馆与博尔赫斯在《巴别的图书馆》里描述的那座建筑相似。〔30〕两座图书馆以及其中的迷宫、镜子、布局以及怪诞的内部结构都在宣示世界的不可知性和绝对真理的不可企及。它不仅是“一座巨大的迷宫,是世界迷宫的符号,”〔31〕而且是“检验真理与谬误的试金石”〔32〕。
在博尔赫斯的所有作品中,《玫》与之最相像、互文性最强的当推博氏最负盛名的玄学侦探小说《死亡与指南针》。《玫》中的一连串罪行起初似乎是需验证《启示录》中有关七个天使吹喇叭的预言,因此不妨把《玫》本身也看作类似于《死亡与指南针》式的启示录文本。正如伦罗特对对称菱形的执着美学追求令他走上歧途一样,威廉由于听信虚妄的预言而使侦破工作徒劳无功。黑社会头子夏拉赫设置了一连串迎合伦罗特胃口的怪诞线索,诱使伦罗特来到一座迷宫般的花园。豪尔赫如法炮制,假手他人导演了一系列与经老修道士阿利纳托之口说出的预言相吻合的凶案,并如愿以偿地把威廉引入了迷宫般的图书馆,以便伺机杀死他。
托多罗夫曾指出侦破工作与阅读过程极为相似,将其中的联系精炼地表述为“作者:读者=罪犯:侦探”。〔33〕这两部作品都试图借犯罪-侦破这一侦探小说的俗套说明阅读行为的微妙、艰难。错误的阅读很可能是致命的──伦罗特的错误使他们做出“拉比式阐释,”进而跌入死亡陷阱。如果说伦罗特的阅读主要是抽象、玄奥的,威廉在阅读中面临的危险则是双重的。在具体的阅读行为中,第一次他与已捧在手中的文稿失之交臂,因为他执拗地寻找的是一部希腊文文稿,而这部文稿就订在篇首的阿拉伯文文稿之后。第二次他机智地先戴上手套再去触碰书,从而免受书页上的毒药之害。在抽象的阅读行为(侦破)中他却一败涂地。“是的,他发现了事实,但不是通过一系列演绎推理,而是偶然撞上的。”〔34〕埃科则说,“天真的读者甚至不会意识到这是一部没有做出多少发现的侦探小说,而且那位侦探也失败了。”〔35〕
在传统侦探小说中无所不能的理性在这里显得荒谬可笑。更具反讽意味的是,斗智斗勇的双方都努力要以自己的方式将知识保留下来,结果却以对文化的毁灭而告终。
同埃科天道难违的主题相呼应,每一个人的阅读基本上都是无效的。豪尔赫自欺欺人、一厢情愿地把凶杀同基督的第二次降临联系在一起,在导演了几起凶杀后又不惜自杀去实现《启示录》中的预言。他为威廉设置的“误读”陷阱最后竟使自己堕入其中。皓首穷经的阿利纳托及院长阿博以下的修道士们大都对这一番“天使吹喇叭”的鬼话深信不疑。他们均未读懂圣经,遑论人生这部大书。故威廉说:“我设想了一个错误的模式以解释犯罪者的动机,可这个罪犯居然真的按照这个模式运行了。“〔36〕
在为豪尔赫们设置陷阱的同时,埃科也为自己的“隐含读者”(implied reader)设置了一个陷阱。他多次提及《启示录》和礼拜典仪,误导读者留意发掘个中的玄机,从“情节”中探寻“故事”,从扑朔迷离的神秘事件中寻觅蛛丝马迹。结果读者期望的结局未出现,《玫》自己颠覆了自己鼓励的超然阅读方式。作为侦探的读者败在作为罪犯的作者手下。
《玫》的序言本身则是对博尔赫斯写作迷宫互文式的参照。埃科声称,眼下我们看到的这部小说至少经过四人之手:埃科是根据瓦雷(Vallet)的法文本“意译”为意大利文的,而瓦雷的法文本又源于经马毕伦(Mabillon)校订过的拉丁文本,这个文本出于14世纪末一位名叫阿德索的德国修道士的原稿。这一神秘文本的“渊源”可用下表表示:
序号 作(编译)者 状态文本
成书或出版
时间
1
阿德索原稿拉丁文
14世纪末
2
马毕伦
修订稿
拉丁文
17世纪
3瓦雷 译本(自拉丁文) 法文19世纪
4埃科 译本文译本意大利文 20世纪
这一虚构的、经过多次润饰的文稿正是博尔赫斯为之心醉的那种闪烁其辞、经过多人迻译、编辑、阐释的文本。博尔赫斯曾描述过一部题为《迷宫之神》的不存在的小说,它被一位有借无还的友人拿去了。《玫》的法文本亦遭受了相同的劫难。
有人甚至认为埃科对博尔赫斯作品的影射实质上是对博尔赫斯独特影射方式的“元影射”(meta-allusion)。〔37〕虽然与《玫》发生互文联系的作品很多,埃科却花了很多心血使自己的作品与博尔赫斯的影射方式挂钩。严格地说,影射均应是间接的,可是读者会发现埃科有意无意地要将《玫》与博尔赫斯作品的互文性公诸于众。
综上所述,以侦探小说形式出现的《玫》集传统和玄学侦探小说之大成,将中世纪经院哲学、 异教传说、本体论人生思考、后现代主义文学观等溶为一体。作者就这样将众多的“封闭”文本巧妙地组合构造出具有多种阐释方案的“开放”文本。他充分估计到自己对阐释进行的这一番阐释会引起的反响,务必使“每一种阐释都在其它阐释方案中得到回应”〔38〕。
互文的使用有利有弊。尽管作者本意是要使《玫》成为一部雅俗共赏的书,尽管此书问世后也取得了巨大成功,仍有不少读者无法读至卷终。〔39〕此书中译本亦已付梓多年,似未有十分热烈的反应。令读者望而却步的原因之一便是,他们在令人眼花缭乱的阅读迷宫中找不到有助于理解的“标示”。
在互文式的影射和戏拟中,以现代主义、欧洲中心主义、中产阶级价值观、白人至上、男性至上、异性爱为特征的西方文化得到重新评估,小说的主题得到阐发。一方面作者赞成追求有序、理智的形而上学,另一方面又反对形而上学对永恒终极真理的执着,不承认人生具有某种固定模式,甚至认为智慧即是悲剧、灾难。这同一命题的两个并行不悖的论点是否表明作者的哲学体系是对形而上的折衷?不属于本文讨论范围、却又很值得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崇尚理性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崇尚灵性的柏拉图主义、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是否能在文学乃至人生中和谐一致。
注释:
〔1〕Patrical Waugh.Metaficttion:The Theoty and Practice of selt-Conscious Fi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84,p.82.
〔2〕 Heta Pyrhonen.Murder from an Academic Angle:An l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Detective
Narrative,Columbia,Camden House,1994, p.42.
〔3〕Jacques Barzun,"Detection and the Literary Art,"
in The Detights of Delection,New York,Criteri-on.1961,p.16.
〔4〕 Julia Kristeva,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trans.Margart Waller.New York,Columbia U niversity Press,pp.59—60.
〔5〕〔35〕〔38〕Umberto Eco,The Role of the Reader:Explorations in the Semiotics of Texts,Blooming 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9,pp.144- 172,p.54,p.8.
〔6〕Elizabeth Dipole,"A Novel,which Is a Machine
for Generating Interpretations:Umbeto Eco and
The Name of the Rose," in The Unresolvable
Plot:Reading Contemporary Fiction,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88,pp.177-140.
〔7〕〔29〕 Umberto Eco,Postscript to the Name of the Rose,trans.William Weaver,San Digeo,Calif,New York and Lodon,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3,1984,p.20,pp.27-28.
〔8〕Sophocles,Oedipus theKing,Oedipus at Colonus,Antigone,Vol.1,London,William Heinemann,1916,p.139.
〔9〕〔10〕〔11〕〔12〕〔13〕〔14〕〔22〕〔23〕〔24〕〔25〕〔31〕〔32〕〔35〕Umberto Eco,The Name of the Rose,trans.William Weaver,Lon-don,Mandatin,1994,p.499,p.11,p.501,p.501,pp.492-493,p.24,p.15,p.2,p.46,p.46,p.158, p.130,p.470.
〔15〕Voltaire,Zadig,trans.John Butt,Penguin Books,1964,pp.28-31.
〔16〕Umberto Eco,"Horns Hooves,Insteps:Some Hypotheses on Three Types of Induction",in The Sign of Three:Dupin,Holmes Pierce,ed.Umberto Eco.etc.Bo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pp.11-54.
〔17〕S.S Van Dine "Twenty Rules for Writing Dtec-tive Stories." in The Art of the My stery Story: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ed.Howard Hay- craft,New York.Biblo and Tannen,1976 ,p.191.
〔18〕吴晗《金瓶梅的著者时代及其社会背景》,载姚灵犀编《金瓶梅研究论集》,华夏出版社,香港,1967年,第5页。
〔19〕魏子云《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台北,1981年,第18页。
〔20〕Roland Barthes,The Pleasure of the Text,trans.Richard Miller.New York,Hill and Wang,1975.p.36.
〔21〕〔34〕Brian McHale,Constructing Postmoderni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dge,1992,p.147.p.149.
〔26〕John Muller & William J.Richardson (ed.),The Purloined Poe:Lacan,Derrida and Psychoana-lytic.Baltimore andi London.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8,p.185.
〔27〕〔37〕
〔28〕Leo Corry,"Jorge Borges.author of The Name of the Rose," Poetics Today.13:3 (Fall 1992),pp.419-445.
〔30〕Walter E.Stephens."Ec ( h ) o in Fabula,"Diacritncs.13:2 (1983),p.58.
〔33〕Tzvetan Todorov,The Poetics of Prose, trans.R.Howard,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7,p.87.
〔39〕Theresa Coletti.Naming the Rose:Eco.Medieval Signs and Modern Theory,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8,p.2O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