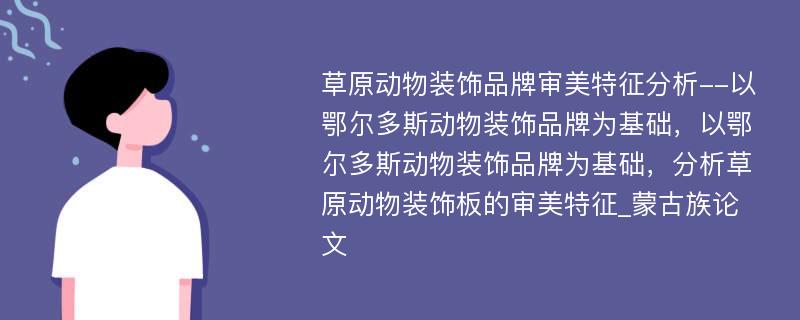
草原动物纹饰牌的审美特征浅析——以鄂尔多斯动物纹饰牌为依据分析其审美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纹饰论文,鄂尔多斯论文,特征论文,动物论文,草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67[2009]1—0088—03
青铜器的出现作为一种生产工具的变革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又以其独有的艺术形式被世界各国学者所关注,同时,也为研究我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上起春秋下至秦汉,延续的时间较长,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各种动物纹,而青铜饰牌又是这种动物纹的集中体现。因此,对鄂尔多斯式动物纹饰牌的研究就更具有典型性。
这里我们以阿鲁柴登、西沟畔、桃红巴拉以及毛庆沟等墓地发现的动物纹饰牌,以及一些国内外学者对鄂尔多斯青铜器的研究为依据,对鄂尔多斯动物纹饰牌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与探索。
根据这里搜集的各种饰牌的造型,可归纳为三类。即:椭圆形饰牌;长方形动物纹饰牌;动物形饰牌。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将动物纹饰牌分成两个层面来进行分析——形式和题材。
一、动物纹饰牌的形式审美特征
(一)对称的审美倾向
这里搜集的动物纹饰牌主要参照《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一书中收录的青铜饰牌样式,有鄂尔多斯地区墓群出土饰牌五十五件,此外零散搜集了四十五件,以及国外戴普列特的《西伯利亚的腰饰牌》,水野清一和江上波夫在《内·长》中收录的器物四十七件。以上的青铜饰牌总共是一百四十七件。
在这些青铜饰牌中,有一类是长方形的,面积很小,饰牌的主要特征是有边框,在边框内有各种动物纹,依据《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中编录可分为十种样式,这里主要通过其中的两种样式来分析。其中一种是群兽纹,一种是双兽纹。
群兽纹是在边框之内同时有很多只同类动物的纹饰,这些动物的排列比较整齐,有的是头和头相对,有的则是头朝着一个方向,有些动物纹额刻画比较仔细,有些刻画比较概念,但是总体特征是十分规范,类似四方连续图案。
第一式:群马纹饰牌,这里一共收集了两件,边框之内一共有三匹马,它们呈上中下并排排列,它们的动势一样,都是站立着并且低着头垂着尾。上下两匹头朝向右侧,中间一匹头朝向左侧。
第二式:群羊纹饰牌,这里收录一件。方框之内,从上到下一次并排着四只角羊,羊呈现蹲状,羊角弯曲,羊头朝天,第一只和第三只头朝向右侧,第二只和第四只头朝向左侧。
第三式:群鹿纹饰牌,这里共五件,只有鹿的前半部,前肢内屈,半蹲,头全部朝右侧,耳朵很大,上两只下两只并排罗列。
第四式:虬龙纹饰牌,这里收集两件,在方框之内上两只下两只并排排列的“S”形龙纹。
双兽纹饰牌是在方框之内,整齐排列的两只同类兽纹饰,大多数头头相对,尾部朝外,也有一些是尾尾相对,头部朝边框的。这些兽纹中有双牛纹、双马纹、双驼纹、双鹿纹、双羊纹等。大多刻画细致,动物特征明显,生动入微。
这些群兽和双兽类饰牌构图都是对称样式,动物个数或双或三或四,显得和平整一、优美自然,正体现了草原的宁静。在形象刻画上,也细致入微,生动形象。整体上给人一种平和自然的静态的美,就像广袤的大草原,自由的放牧生活一样平静。可见,虽然蒙古民族勇猛、强悍、不拘一格,但是同时也有平静、恬静的一面。
这种对称的构图方式,有些类似于中原地区青铜饕餮纹的对称,饕餮是一种狰狞的兽形头像,以鼻梁做中线,两侧作对称排列。中国的思想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有一个中心,在八卦中是太极,在五行中是土;二是处理对立关系运用的是“对立而不相抗”的融合、定位、互补原则;三是有一种容纳万有使之规范的宇宙气魄。① 当然,饕餮纹是对这种思想的最好诠释,但是从鄂尔多斯青铜器上也可隐约看到这样一种思想。
(二)圆形的审美情结
上面我们提到过,根据出土的青铜饰牌纹样,鄂尔多斯式青铜饰牌从外型上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椭圆形、长方形、动物形。椭圆形饰牌一端呈方形,另一端呈圆弧形,有牛纹和马纹以及一些虬龙纹和牧民骑马的场景。牛纹饰牌中,牛是正面的形象,周围有一些凹入的叶状纹,并呈左右对称状排列。牛角向上弯曲,并且组成环状,环上有钩,可见这个是用来衣服的带扣的。牛头下部为方形,上有长方形孔。马纹饰牌中,多是表现马的侧面,是全身像,有表现马散步的,有表现马驰骋的。环的部位多在马头前端。虬龙纹则是整只虬龙盘旋而上,头部在正中,正面,带扣在头的下方。方形饰牌多为双兽和群兽纹,上面已有介绍。动物形饰牌没有固定的形状,是根据动物的造型的不同而变化的。动物形饰牌中,有的是个体动物的,有的是两只动物纠缠厮杀的,有的则是一群动物缠绕在一块的。个体动物形饰牌多形体很小,有马形、虎形、鹿形、豹形、羊形、象形等,有的是正面形象,有的则是侧面形象。两只动物纠缠的饰牌,有的是同类动物,以规则的对称式呈现,有双羊、双鹿、双豹;有的是异类的动物撕咬场景,比如虎咬羊。群兽形饰牌是由两个以上动物组成,形状特殊,表现手法更加夸张。种类有三象、虎鸟纹以及群兽纠结纹。动物咬斗形是鄂尔多斯式动物纹饰牌中比较流行的一种。这种饰牌多数形状相似,包括虎咬羊、虎咬马、鹰虎搏斗、狗咬马、虎吞兽和人物搏斗等多种,在下面的章节中会对这类纹饰做进一步的分析。
在上面的描写中,很容易便会发现,在这些青铜饰牌的造型中,圆形居多,即使不是正圆形也会是弧形,尤其是对动物的刻画中,更多的使用的是流线型,在方形的饰牌中,也只有外型是方形的,内部的动物线条多是弧线形。
这种对圆形的过多的刻画并不是偶然。通过很多资料的分析了解,蒙古语部族对圆形是有着特殊的感情的。
对圆形的偏爱恐怕要追溯到更加遥远的时代。在贝加尔湖畔查干扎巴岩画上,一些画面生动地刻画了蒙古语部族古代萨满教仪式歌舞的某些动作特征。考古学家们指出:其中一些类人形画面,手持圆环,双手搭扶肩或手拉手,是“一种跳舞人形,不过是在跳一种特殊的舞,不是那种动作频繁、激情洋溢的舞,而是一种祭祀的时候的喜庆舞。这种舞合乎较贵,有严格的节拍的。”② 并通过民间调查后,指出“布里亚特人相信,在萨满教祭祀的仪式上,围绕成像太阳形状跳圆圈舞的”③。
蒙古牧民把圆形图案统称为普斯贺,是一个上通天、下通地的长寿符号。圆形一般是太阳和阳性符号,反映了北方民族太阳崇拜的观念和太阳的阳性内涵,有着生命永恒的涵义。
蒙古语部族对圆形的这种偏好一直延续着。在《蒙古秘史》中有记载说“绕蓬松树而舞”,绕树而舞,自然也是围成圆形。据说是铁木真与札木哈二人曾以互赠羊拐骨、互换腰带形式结成“安达”,在结安达之时,绕蓬松茂树而跳舞。该说认为,元朝初期的“踏舞共扶携”等等,都是以树为中心,呈现圆形列队,这些是有着象征意义的,意在暗示人们对“团圆”的期盼,以及团结“安达”而同心同德的心情④。蒙古族的最典型标志——蒙古包就是一个圆形。从蒙古族现代的舞蹈艺术的动作特点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对“圆”的偏好。例如在蒙古族男子群舞《奔腾》中,可以看到很多“抖肩”、“翻腕”、“马步”等蒙古族特有的舞蹈动作,舞蹈演员在跳舞的过程中,手臂、脚步都在走一个“圆”形。这些都是题外话,但是可见,蒙古语部族和圆形的确是有着很深的渊源的。
二、动物纹饰牌的题材审美特征
(一)兽型艺术类比的美学思想
在鄂尔多斯的动物外型的饰牌中,有很多都是动物撕咬的场面,上文也有所提及。这种撕咬场面多数是凶猛的动物用嘴巴撕咬着弱小温顺的动物。如虎咬马、虎咬羊、虎咬牛、虎咬鹿等等,这些画面看起来有些让人心生怜悯,为什么这类图案的青铜饰牌大量存在,似乎这不应该用作装饰纹样来修饰饰牌。事实上,追溯到蒙古语部族的古代,这也是有渊源的。
早在蒙古族英雄时代,就伴随着一种兽型艺术类比的审美思想。这一兽型艺术类比的审美对象范畴自蒙古族古代开始,一直伴随着时代的发展。所谓兽型艺术类比,是指以凶禽猛兽类比人的个性性格的形象的艺术表现方式。它是表现蒙古人情感的一种独特的方式。蒙古族的古代文化中的兽型艺术类比美学思想,与其远古时代的狩猎活动和游牧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同时它也是从古代萨满教神秘观念抽象出来的艺术表达方式。蒙古族萨满教认为“万物皆有灵性”,随之产生了很多模仿动物的原始舞蹈,他们用凶悍的动物图腾作为守护神,也就是祖先崇拜,发展到后来,古代蒙古语部族从多神论向一神论发展,所有的这些,构成了兽型艺术类比的前提。
蒙古族自古以来崇拜凶猛的动物图腾,在历史不断的发展变化中,蒙古人逐渐意识到了自身的本质力量及其能动作用,发展到了英雄时代,这种“人的自然化”转化为一种兽型动物的类比,并且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成为一种审美对象范畴。
在英雄史诗《江格尔》中对洪格尔的形体的描绘:“肩宽七十五丈,臂围八十五丈,其腰围只有三十五尺;十二只雄狮的力量,聚积凝藏在其身上,八千个妖魔的力量,蕴藏在其强健的肌腱中”⑤,体现出一种兽型艺术的类比的审美倾向。
(二)崇尚自然,狂野的审美情趣
在鄂尔多斯动物纹饰牌中,可以看到大批的“搏斗撕咬纹”,这个在上面的章节中已略作描写。动物与动物互相搏斗撕咬,使画面呈现一种互相缠绕的扭曲的动态美,线条的旋转、扭曲刻画出有节奏的曲线,而整体上的构图又不缺乏美感,设计者真可谓是伟大艺术家,他们将这种扭动的曲线安排得天衣无缝,同时又将动物们撕咬搏斗的生动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从这些动物纹的刻画中,显然可以看出一种生动、凶猛的表现特征,同时又伴随着鲜明的游牧文化特点。这种生动、凶猛强化了动物纹的欲动性与力量感,从“力”的角度来表现草原青铜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同时这种力量又赋予了动物纹鲜活的灵魂,强烈的动势与力量自然淡化了其宁静、虚幻的因素,这正是草原青铜器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狂野与崇尚自然。这与草原游牧的社会意识形态有着深刻的同一性。
比较中原的青铜,鄂尔多斯青铜的装饰风格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原的青铜器最具代表性的装饰纹样就是饕餮纹。虽然他们在对称上相似,但是饕餮纹更倾向于一种虚幻、神化的神秘力量,狰狞、冷峻而又恐惧,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王权;而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动物撕咬搏斗场面试图用动感、激烈来表现一种狂野的美。正如李泽厚先生用“狞励之美”来形容中原青铜饕餮艺术,鄂尔多斯青铜纹样审美特征刚好与之相反,是一种狂野的、不拘小节的崇尚自然的美。中原青铜饕餮纹是一种静态的美,鄂尔多斯青铜动物纹则是一种动态的美。
(三)追寻自由与和平的审美风格
在鄂尔多斯动物纹饰牌中,我们会发现双鸟纹饰牌以及鸟形饰牌是腰带饰中数量最多的一种。双鸟纹饰牌在鄂尔多斯墓群中共出土三百二十四件,有铜饰牌和铁饰牌两种,分别出土于三十座墓中,其形状大体呈“反向S”形、“卷云”形和“细腰”形。一面有花纹,另一面有钩带。从侧面看呈扁状,中间有突起。根据器形和花纹图案统一编式,可分五种样式:
第一式五件,由双鸟头反向联结呈“反向S”形,鸟的颈部有装饰,鸟眼、喙、耳均图案化。弯曲处有两个圆孔,背有钮。大小一致,长3.5厘米。
第二式二件,较之一式更为写实。鸟的喙、眼清晰可见,亦呈“反向S”形。弯曲处有孔背有钮。大小一致,长大约4厘米。
第三式十二件,图案为双鸟纹的变体,图案化,呈“S”形,鸟眼、喙、耳隐约可见,眼孔变大,长3.6厘米。
第四式十五件,双鸟头反向联结,完全图案化,都为曲线,长大约3厘米。
第五式二百八十二件,与前式各不相同,鸟完全被图案化,并且只有简单的几条曲线,呈漩涡状,大小不等。整个饰牌呈“卷云”形。长4.6—5.3厘米。
此外,鸟形饰牌也共出土四十二件。有的是单纯一个鸟头,喙很大,大约两厘米。有的是雏鸟状,鸟喙、眼、耳均比较清楚,长大约3厘米。还有的是四个鸟头和为一体,呈上下两排对称分布。长大约3厘米。总体来看,鸟形饰牌都很小巧,造型统一中有变化。
可见,在饰牌的题材上,不仅仅有凶猛禽兽搏斗厮杀的场面,还有像鸟儿这样小巧温柔的图案。因为即使是在野蛮的时代,到处充满着血腥争斗,但是追求和平与自由,却始终是人类所共同追求的目标。强者之间的搏斗、弱者被强者撕咬,这样的场面固然是蒙古族特有的英雄情结和审美特征,但是像鸟儿这样欢快的飞翔,也显示了蒙古语部族的另一种审美意味。
这类饰牌与上述的动物撕咬搏斗饰牌风格相差甚远,一位猛士不太可能佩带这种饰牌,那么就有可能是女性或是小孩佩戴,而女性又是男性所追求的对象,小孩又是男性所保护的对象,也是残酷搏斗之外的温柔之乡。而这种鸟纹青铜器刚好是女性,或是田园牧歌生活的象征,体现蒙古族向往自由与和平的审美情趣。
蒙古语部族崇拜太阳,也崇拜天。在阴山岩画中可见很多太阳纹样的图腾。人们崇拜鸟的神力,因为鸟可以在天空自由翱翔,离天那么的亲近,这是人们所渴望的。鹰的喙很大,眼睛神气无比,它作为鸟的一种更为人们所敬奉。在阴山岩画上可见很多类似鹰头的图腾,还有在当时也有大量的民间传说和歌谣,其中对鹰的描绘更是赞赏有加,是其他民族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对天的崇拜与渴望,所以人们将鸟的图案作为一种图腾,装饰各种青铜饰牌。从出土的鸟纹看,都是造型精美、装饰性突出的饰牌,而且,据考证,出土这些鸟纹饰牌的墓室主人地位也都较高。可见,鸟在这个民族中是神物,人们希望这种能飞得很高很远的神物将他们的虔诚与祈祷带到天上,同时把上天的旨意带回人间。
三、结语
无论是造型还是题材,鄂尔多斯动物纹饰牌的各个审美特征都表现了蒙古语部族游牧的生活特性,以及蒙古民族不受约束、对力与勇无比崇拜的审美模式。
注释:
① 张法.中国艺术:历程与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53.
② 文物考古参考资料.1980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编印,第二期,47.
③④⑤ 满都夫.蒙古族美学史.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112,113,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