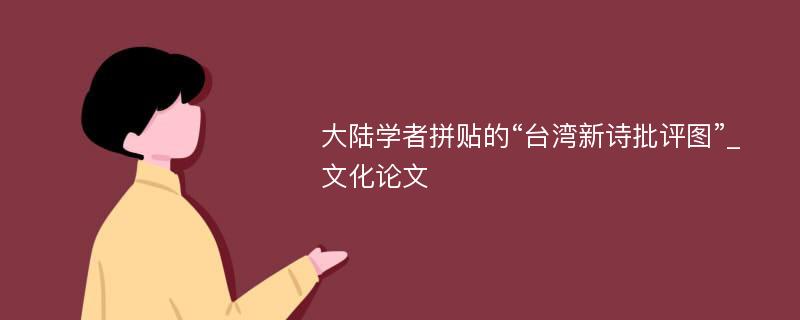
大陆学者拼贴的“台湾新诗理论批评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诗论文,台湾论文,学者论文,批评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争鸣篇:关于“大陆的台湾诗学”的论争(二)
编者按:我刊1995年第1期曾以“关于‘大陆的台湾诗学’的论争”为题,转载《台湾诗学季刊》的争鸣文章,为读者提供海峡两岸诗学交流的信息。1996年3月,《台湾诗学季刊》第14期,又推出“大陆的台湾诗学再检验”专辑,刊登台湾诗评家的10篇文章,对古远清、古继堂、王晋民等人的著作提出批评,随后又在第15期刊出古远清、古继堂等的反批评文章。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正常的现象。其实就是台湾诗评家之间的意见,也并不一致,甚至是互相矛盾的。例如,文治先生在《如果渐成事实》一文中,指责近两年来大陆诗评家评论台湾诗的文章,“通篇只有叫好鼓掌赞美的声音”,“从来不敢或不愿道及台湾诗的缺失”,但在同一期刊登的漫画中,却又讽刺大陆诗评家把台湾诗人“辛辛苦苦炖的肉给狗吃了”。
海峡两岸隔绝40多年,开始文学交流只是近10年的事,而且交流的渠道又很不畅通,因此,通过对话和讨论,将有助于化解彼此的敌意,也有助于创作的繁荣。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期只是选登批评“二古”的文章和“二古”的反批评文章,今后如有新的文章推出,本刊还将继续转载。
台湾海峡宽度大约两百公里,台湾与中国隔绝刚刚超过一百年,同种中复有不同的种族,同文中复有不同的语文,再加上截然相异的政治、经济、社会之制度,越离越远的生活方式、思考模式,台湾新诗与中国新诗的不同,将会如同美国诗与英国诗之殊异。
台湾文化受儒家传统、汉文传统之影响,也受海洋文化、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日本的濡染,基督文明的冲击,南岛语系的刺激,而四百年经济移民与四十年政治移民的个性有别,因此,在台湾的学者深信文化多元之可贵,深信文化、文学有机成长之可能,深信文学艺术突变、多变之可爱,对于发展中的台湾诗史尚未有专著问世,而大陆学者的《台湾文学理论批评史》(古继堂,1993年6月,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古远清,1994年8月,武汉出版社),已相继问世,显见大陆学者之急好与毛躁。
这两本以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为对象的史学著作,企图心极大,搜罗资料之努力也令人敬佩,不过,将资料悉数运用,未加任何择汰,也令人惊讶!如古远清的书封面一列列《文讯月刊》,借用《文讯》简单的书目提要,以求史之评监,未免浮泛、速成。古继堂的书则大量袭用“序”“跋”,不从论文本身去钻研,往往抓不住精髓所在。
此二书以新诗为范畴的章节虽不多,但将相关章节胪列对比,可以看出二书的“拼贴”效果,看出他们拥有(使用)的资料多不多、全不全,二书合观,却看不出台湾新诗理论批评的真面目。
古继堂的书概分六编17章,第五编为“台湾的新诗理论批评”。下分三章,兹列其目如次:
第十三章:台湾新诗理论批评概述
第一节:台湾新诗理论批评的历史演变
第二节:台湾新诗理论批评现状
第十四章:台湾理论家笔下的新诗理论批评
第一节: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批评导向
——台湾现代派诗的克星唐文标
中国诗学体系的创建者李春生
把纯粹的表达工具化为活生生文化化身的关杰明
呼唤中国诗魂复旧的高上秦
认为诗是心灵净化剂的黄永武
为台湾新诗测试坐标的萧萧
第二节:新诗“现代化”的理论追求
——试用神话原型说批评新诗的张汉良
台湾第一部诗论专著的作者李英豪
名理前诗境诗论的提出者古添洪
认为诗是诗人和语言对话的简政珍
后现代派诗的批评家孟樊
第十五章:台湾诗人笔下的新诗理论批评
第一节:崇尚传统和写实诗人的诗歌理论批评
——反对台湾新诗西化的理论主将罩子豪
诗必须有动机开道的陈千武
视生活是诗的源泉的古丁
明朗、健康、中国诗路线的倡导者
文晓村
用剖离法去伪存真的李魁贤
忠实于中国传统诗论的高准
融入自我生命体验的女诗话家涂静怡。
第二节:追求“现代”和“超现实”诗人的诗歌理论批评
——主张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
承的纪弦
主张新诗现代化应落实在乡土之
上的林亨泰
理论观念多变且反覆的余光中
中庸温和的现代派诗评家张默
认为诗人是内在世界造物主的罗
门
诗论主观色彩极强的洛夫
认为寻找语言的关联能力是诗人
能力指数的白萩
台湾女性诗人的知音钟玲
台湾新世代诗人的塑像者林燿德
古继堂的书很单纯化,不论理论家或诗人都概括地区分为“现实”与“现代”的追求,眉目清晰,但各人头上的一句按语,除钟玲、林燿德等人因为有相关书籍出版,极易找到贴切用语,其他按语中可待商榷者实伙,如洛夫“诗论主观色彩极强”(哪家诗论不主观?),张默“中庸温和的现代派诗评家”(谁人不温和?),李魁贤“用剖离法去伪存真”(哪个评者不是在作抽丝剥茧的工作?),这种评述,说了等于没说。覃子豪“反对西化”吗?他一直在介绍法国诗、象征主义、神秘经验;林亨泰“落实乡土”吗?他是笠诗社中跟白萩一样精神前卫,早期现代派的战将;高准“忠实传统”吗?他听忠实的不是性灵、神韵的传统诗歌主流。古继堂书中使用“中国”二字来评论的有四人,没有一个是正确、贴切的,李春生“中国诗学体系的创建者”,李春生在台湾写论,如何去“创建”中国诗学体系?高上秦“呼唤中国诗魂复归”语义有问题,复归何时?五四?唐宋?汉魏?文晓村是“中国诗路线的倡导者”,中国诗路线是指大陆当代诗吗?高准忠实于“中国传统诗论”,就高准与古继堂此书中都未见到他们引用或贴近任何古典诗论,如此评语空疏不切实际。
高上秦主编《龙族诗刊评论专号》,凭一篇序文而成为呼唤诗魂复归的评论家,此誉未免太高吧!李敏勇、陈明台、罗青、渡也,他们都有评论专著、高水准演出,叶维廉、向明、白灵、向阳,他们都有杰出的诗观、卓荦表现,竟朱能有一小节给予绍介评论,挂一而漏万,实不能诿过于资料之不足。黄永武先生为台湾当代最权威的古典诗研究者,其论著亦可为新诗创作者之所借镜,但是实在不能将他当做是新诗理论批评者(凭一篇《诗与传统》?)。尤有甚者,古继堂此书中讨论了二十七家评论家与诗人,至少有四分之一在台湾诗评界是不会被视为评论者来加以鉴识的,玉石不分,淄渑并泛,这是一个评论者最大的忌讳。
古继堂的书称之为“理论批评史”,自应有正确的史实依据,错乱之处却随时可见。如称李英豪为“台湾第一部诗论专著的作者”,当然应该置于张汉良之前。第十四章第一节是“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批评导向”,第二节则是“新诗现代化的理论追求”,此二节实宜对调先后秩序,先有现代化之追求,才有现实主义的导正,否则一开始即介绍“台湾现代派诗的克星唐文标”不就落空了吗?未有现代派,先有克星!第十五章之二节也应依此归回原位,如果不先谈纪弦的横的移植,如何续编覃子豪的反对西化?特别是第十四章与第十五章尤需对调,当然是先有诗人的理论阐述,才可能有理论家的后继批评,世界上不会有理论先创作而行的,除非那是专制国家,意识形态重于一切,大陆学者是否依其经验画相同的葫芦套在台湾诗坛之上,以其唯物意识宰制台湾诗理论之流向,准此或可见其一斑。
再看古远清的《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前者导论,后有附录,全书分为三编:
第一编:光复初期至60年代:从战斗本位向文学本位的转移
第七章:现代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新诗论战
一、群贤并起,论战不断。
二、《天狼星》、《70年代诗选》之争论
三、现代派的崛起:纪弦、林亨泰
四、《蓝星》的制衡:覃子豪、余光中
五、《创世纪》的革新:洛夫、痖弦、张默
第二编:70年代:在论战中蓬勃发展
第九章: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新诗评论
一、笠的诗论:现实经验、赵天仪
二、葡萄园的诗论:文晓村、李春生
第十章:两位有建树的诗论家
一、张汉良
二、萧萧
第三篇:80年代至90年代初:众声喧哗,多元并存
第九章:众声喧哗的新诗论坛
一、罗门
二、张健
三、李魁贤
四、钟玲
五、刘菲
六、旅人
这是有关新诗的篇章目录,古远清与古继堂所犯错误大抵相同,历史秩序颠倒错乱,如罗门、张健、李魁贤三人绝对要放在张汉良、萧萧之前,罗门的诗论最早的两本出版在60年代(《现代人的悲剧精神与现代诗人》,1964年,《心灵访问记》,1969年),以其出道之早,出手之快,置于古远清书中的第一编,与覃子豪、余光中同列,最为恰当。张健的第一本评论,1968年出版;第二本讲义式的书虽迟至1984年出版,但并无一篇可以代表80年代较为新颖(更不必说新潮)的诗论,放在80年代讨论,不见伦类,刘菲、旅人亦可如是观。李魁贤的《台湾诗人作品论》虽在1982年出版,但大部份作品完成于70年代,改置于第二编第九章,与赵天仪同列,所谓“现实经验的艺术功能导向”即李魁贤所撰,放在《笠的诗论》项下讨论他,不是最为切当吗?
80年代,90年代初,最该讨论的是新崛起的更为年轻的诗论评者,如孟樊、林燿德、王浩威、简政珍、游唤,他们写诗也写评,在“新诗坛”荡起涟漪,置之于第三编第九章,代替那些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的诗人,不是更能显示新诗坛之更迭换新?不此之图,竟以张健、刘菲等人代表80年代,甚至90年代,岂不让识者有摸象扪虱之讥!古远清书中第三编之众声喧哗的新诗论坛,除钟玲之外,可说全章是蹈虚、落空了!
人物全然对不上,当然也看不出何谓“众声喧哗”?六人中之五人,在80年代了无新义提出,听不到他们的喧哗,也听不到他们个别的音色。退一万步言,假使以此六人为台湾80年代新诗论评之代表,他们又有什么各自不同,可以喧哗之(新)声?如果有,他们之间又有什么相互之间的纠葛?横向之影响为何?纵向之继承又形成什么样的统系?古远清竟无一语叙及。——因为,张健等人早已不活跃于80年代诗坛,80年代活跃的新诗人没有几个认识刘菲、旅人了!
古远清与古继堂同样喜欢将台湾诗坛二分为“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使之对立、对峙、对抗,难道台湾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诗的主义、诗的集团?再退一万步言,同样是“现实主义”吧!“笠”与“葡萄园”的“现实”之意涵,那又宵壤有别、云泥两判了!古远清如何区隔?
古远清的书在80年代以人为主轴叙说论评状况,患了选人不当的毛病,在70年代则以诗社为主轴划分论评版图,为了他僵硬的“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论点,只选择了两个诗社“笠”与“葡萄园”,遗漏了当时极为繁多而蓬勃的年轻诗社:“龙族”、“主流”、“暴风雨”、“风灯”、“大地”、“草根”、“绿地”、“诗脉”、“神州”、“阳小集”,他们是70年代诗坛注目的焦点,今日诗坛中坚分子都来自这些诗社。这些年轻诗社在70年代就发出了古远清所说的80年代的众声喧哗,70年代的诗坛不注意他们的论评,就不会有80年代的解构现象。所以说,古远清70年代的台湾诗坛论评拼图,只放进了最基本的两小块而已,离成型成式、有模有样,还太遥远!
古远清书中第二编有关新诗部分,除第九章举“笠”与“葡萄园”为现实主义之显例外,第十章又论述两位诗评者张汉良与萧萧,有意以此二人来代表“现实主义”论点之外的另一族群,然而,对照古继堂的书,萧萧则是列在“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批评导向”的章节下,显见单纯地以“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对拳,是相当不智的行为,长期以来,台湾诗坛并未在“为人生而艺术”与“为艺术而艺术”的论争中缠斗不休,二古之作却都以此为划分准则,二分法的论述十分不宜,倒不如采用纪弦老前辈的大植物园主义,让百花开放,万壑争流!
二古之书都故意忽略了以台湾本位为论述主轴的诗评论者,对于台湾诗论来自日据下台湾本土诗人的影响、来自日本诗坛的影响、来自欧美诗论的影响,也鲜少论及。好在,两位古先生都曾先后来台,环岛一游,所见所思,或有修正。对于海洋台湾的诗坛流向,不能再一直以陆块中国的思考方式来拼贴了!不能再以人情的偏颇来涂色了!
(原载《台湾诗学季刊》第1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