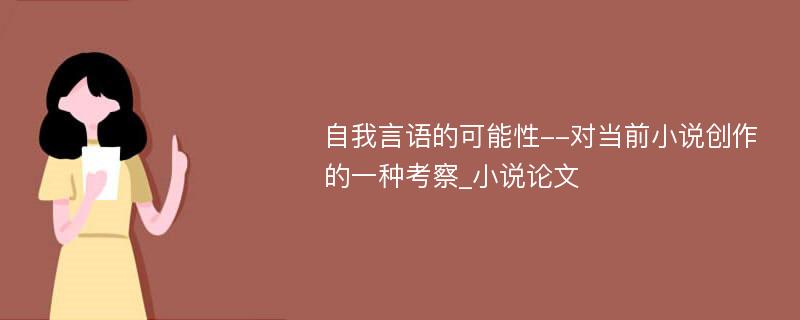
自体言说的可能性——对当前小说创作的一个观察笔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能性论文,自体论文,笔记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篇:目前的状况
汉语言传统是注重伦理学的。中国古典小说,即使是最黄色的,如《肉蒲团》也包含了一个道德说教的外壳,再如《金瓶梅》,也是如此。中国当代男性作家并没有从根本上颠覆这一点,然而尽管如此,男性作家在“道德”方面还是受到了比女性作家严重得多的压力,当代小说家中男性作家在道德上受到的批评较多。但是据我观察,男性作家实在是被他们的性别给拖累了。在道德观念上,男性作家的意识并不象他们的小说本体意识那样前卫,例如新时期以来的先锋作家在文本实验方面迈出的步子很大,对中国大陆读者的审美经验构成了一种真正的敌对,但是读者对他们还是容忍了,并没有怎样敌视他们。而一旦把这种敌对放到道德的领域,情况就不一样了。如张贤亮、王朔、贾平凹、朱文等等,道德习惯的力量要比审美习惯的力量大得多。其实,张贤亮、王朔也好,贾平凹也好,乃至朱文,他们在道德方面的反传统并不象某些人惊呼的那样彻底。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小说,虽然在性题材方面是突破禁区的,但是在性观念上,他却是传统的,甚至是封建的,一方面他描写了身体,另一方面他却在不断地运用自我反思来贬低身体,为身体的欲望而忏悔。王朔的小说在社会观念上是颠覆性的,但是在传统道德方面,王朔的颠覆性却是极为有限的,例如在情爱方面,王朔的小说在表层的痞子腔、游戏味之下依然保持着对浪漫爱情的信念,一位研究者就曾这样概念他的爱情小说显层次和隐层次的矛盾:反“才子”的才子佳人模式;反英雄的英雄美人模式;“凡夫俗女”式“脱俗爱情”。在王朔的词典中,浪漫炽情依然被视为正面词语,它是王朔为他的调侃与游戏留下的最后一个没有被攻破的堡垒。再如,贾平凹的《废都》,这部小说的男主人公庄之蝶在生活上表象地看很迷乱,但是在骨子里这部小说的情爱观念却是很传统的,和庄之蝶发生关系的人,如唐宛儿、阿灿等,都是在对庄之蝶有一种崇拜、一种理解的基础上才献身于他的,这些女性是将庄之蝶作为一个理念,她们在庸常而凡俗的生活中看到了这个理念,就仿佛看到了一种超脱的希望,她们试图通过献身于他而占有他这个理念,从而在精神上自觉超越了原来的自己,贾平凹这样设计人物,是他在观念上将情爱和某种超越追求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缘故。也就是说,在贾平凹的意识中情爱如果不和某种非情爱的东西相连就没有意义。这种观念我们在朱文的小说中也可以看到。朱文的小说引起了极大的争论,例如他的《我爱美元》,许多人认为朱文是一个非道德小说家,其实并非如此,《我爱美元》中出现了“性”,并且性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但是这种“性”在朱文笔下是作为“理想的性”的反面出现的,小说中多次出现了这种“性”的可能。在饭店、在电影院、在歌舞厅,“我”与“父亲”都面对着这种“性”的可能,但是朱文为什么不让这种“性”成功?朱文关心的其实不是这种“性”的可能性与合理性,而是这种“性”的不可能与不合理,他关心的是“性”如何走到了它的反面,如何成为一种障碍。
男性小说家容易受到道德批评——这构成了他们在小说写作方面的性别劣势。郁达夫的《沉沦》一面世,便有人就小说的道德提出疑问,认为这是“不端方”的小说,甚至以此来攻击新文学。而张资平因为在小说中直接触及性爱问题,一直被人们看作是一个三流小说家,他在中国新文学历史上的创造性地位也似乎没有人愿意提了。其实女性作家在情爱道德方面做得比男性作家要“革命”得多。例如丁玲,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在观念上要比《沉沦》“不端方”得多,《沉沦》写的是灵与肉的矛盾,肉的痛苦源于灵的方面,而《莎菲女士的日记》笔墨却是集中于“身体”,以莎菲女士身体的“病”为中心,女主人公对于男性的需要也是以身体为中心,《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存在着将男性作为“上手事物”加以“使用”的迹象,小说中女性的自我中心是明显的,但是《莎菲女士的日记》所激起的道德批评在当时却轻微得多。
新时期以来女性作家在反传统道德方面所采取的立场实际上要比男性作家激烈得多。王安忆的《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小城之恋》、《岗上的世纪》等小说在写性方面可以说是超过了同时期的男性作家的。问题的关键是作者在这里已经不是对那些仅仅为了满足性欲而偷食禁果的芸芸众生采取一种冷观和审视,而是寄予了充分的同情,在人性和社会道德禁忌之间作者的立场明显地站在了人性的一边。《岗上的世纪》中作者实际上已经在要求正视女性作为一个性别从性行为中获得快感的权利,而这一点即使在今天男性作家也很难真正做到,他们大多必须象当年的郁达夫一样为自己的性题材找一个“灵”与“肉”冲突的主题,在我的阅读范围之内我尚不能找到这样一个作家:他毫无心理障碍地强调一个男人从性行为中获得快感的权利。尽管如此,王安忆、张辛欣、铁凝那一代作家等,比起今天的晚生代女性作家以及一批70年代出生的女性作家来还是显得“老派”了。王安忆希望“在新的男女互补的基础上重建人类崭新的文明。”(《神圣祭坛》);张辛欣借女主人公之口说道:“假如有上帝的话,上帝把我造成女人,而社会生活要求我象男人一样,我常常宁肯有意隐去女性的特点,为了生存,为了往前闯。”(《我在哪儿错过了你》);铁凝则希望以一种女性的情爱的力量来感染和改造男性(《无雨之城》)。她们的写作过多地蕴含了社会性的成份,她们把性夸张了,夸大了性的社会意义,另一方面她们也把性缩小了:她们没有将之作为一种个人性的具体的权利来加以坚持,她们的道德观依然是暖昧的,因而实际上她们的呐喊、揭示都是附加的而不是本体的。她们不是把性当作一种身体性关系来写的,而是将之当作一种灵魂性关系来写的,她们依然有一种道德方面的焦虑。
而这一点在陈染、林白、徐坤等那里就不一样了。她们在此一方面的书写具有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意味。她们不再是从女性的灵魂性出发,她们认识到所谓“灵魂”只是历史加之于女性的种种精神禁忌的代名词,她们因而是一群反灵魂的小说家,她们的写作策略是充分地“放纵官能”,让感性发挥力量,让身体自己为自己的存在说话,如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以及宣儿的《随风飘逝》等,从这个意义上可说她们是一些“身体型”作家,而她们的小说也正是因此而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抗拒性和挑战性,她们依据的不是一种黑格尔式的“理性的感性显现”的美学而是一种“身体的感性显现”的美学。如徐坤就说:“男人们受引诱去追求世俗功名,而女人们则只有身体,她们是身体,因而更多地写作。”(《女性写作:断裂与接合》,《作家》1996年第2期)林白也说:“有些病态地喜欢自己的身体, 喜欢遮掩物下凸凹有致的身体,有时候当她一个人的时候她会把内衣全部脱去,在落地穿衣镜里反复欣赏自己的裸体。”(《致命的飞翔》,《回廊之椅》,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个性化文化与身体型作家》(《山花》1997年6月)中也曾经论及这一点。 “这是一种身体的哲学,它确认人的身体的经历的正当性,身体的法则是私人性的、非理性的、欲望化的,它同我们过去所重视的灵魂的法则是对立的,灵魂的法则是禁欲的、理性的、伦理的,过去的哲学基本上都是灵魂哲学所以几乎都在终点上将自己归结为伦理学,而个体性文化时代的哲学是身体的哲学,是对以往一切灵魂哲学传统的一个颠覆,个体性写作的时代作家对自己的身体是肯定的”,“在这部小说中女性不再是作为美和善的化身也就是说不再是作为灵魂存在而是作为一个身体存在进入作家的叙述的,作品中伸张的是女性作为身体的力度因而也是人作为身体的力度”。
徐坤、林白、陈染都身居北京,北京固有的那种姿态性也影响了她们,她们在写作中蕴含了一些表演性的成份,有时候她们故意夸张了自己的身体,将之当成了一种资本、一种象征。而这一点在上海的绵绵和卫慧身上就见不到。绵绵的《啦啦啦》、《一个矫揉造作的晚上》、《九个目标的欲望》、《美丽的羔羊》、《香港情人》、《告诉我通往下一个酒吧的路》等小说,在表现当代中国都市非主流文化状况方面,显然比中国绝大多数作家都要好。酒吧、派对、朋克、大麻、同性恋、爵士乐等构成90年代大都市的非主流文化,而对于这一非主流文化的表现,我们以往的文学界几乎都是隔靴搔痒的。绵绵没有接受过正统的文学训练,这一点在90年代以来的新生作家中很特殊,她的独特的语感不是来自对汉语言传统的阅读与接收,而是来自直接感性,她的语言包裹着直接感性的灵魂,她几乎天生的就是直接感性的表现者。对于写作,绵绵说她不是用大脑而是用身体在写作。卫慧的《艾夏》、《床上的月亮》则将一种身体性激情表现得疯狂而感伤,小说中女主人公对镜自赏,对自己的躯体性存在持一种毫无保留的认同,这种状况在江苏的朱文颖、周洁茹身上也有表现。值得注意的是绵绵、卫慧、朱文颖等都是70年代出生的作家,她们和徐坤、陈染不仅在地域上有南北之别,而且在年龄上有10年的差距,陈染等60年代出生者的那种意识形态意识在她们那里是没有的,加上她们身处南方柔软的本身就身体化的都市之中,因而她们的写作在直接感性方面更为彻底。
下篇:提升的可能
长期以来,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不断遗忘人的身体的历史。在西方身心二分法得以正式确立的关键人物是苏格拉底,他将善看作是最高的道德范畴,他教人要认识自己,而这个自己不是指人的身体而是人的“灵魂”,也就是理智。柏拉图则更进一步,将善不仅看作是道德范畴而且是本体论、认识论的范畴,在他看来我们的感觉以及我们的感官所接触的世界是不真实的,精神理性是崇高的,而感觉物质则是卑下的,幸福不在于物质的满足以及感官的快乐而在于“善”——超脱感官沉思、服从、节欲。在中国早期儒家主要讲“外务”,但是到了《大学》、《中庸》的时代儒学便进入了“内观”,讲如何克服身体(“修身”、“养性”)而达到“正心”,身心二分的思想就定型了。此后身心二分的思路一直是中西哲学、伦理学主导思路。在西方,中世纪哲学自然不必说了,近代哲学也是如此,如迪卡尔,把思与在直接统一了起来,其实是把人当成了精神、思维而不首先是广延实体;在康德那里自我不是身体,而是“灵魂”、“主体”、“能思维的本质”;在东方,中国哲学到董仲舒,再到程朱基本上也是如此,在这一脉哲学家看来“真理”、“善”只是属于心灵的领域,身体离开了心灵就和真理、善无缘。身心一体的原始地安妥于世的“人”死了;传统道德正是以人的身心二分法为前提,割裂人的身心,是以心、理性、灵魂来压抑身、感性、肉体;人的身心二分法发展为神与人的二分法、圣人与民众的二分法、领袖与群众的二分法、群体与个体的二分法,导致前者对后者的奴役。
因而今天的身体型写作对克服人的身心二分是极有意义的。存在就是身体,对于人来说身体性存在是第一位的,任何真正的自我言说必然是以身体性为依据的言说,灵魂的语言已经过多地被“公共信念”玷污和压抑,今天要对压抑性公共信念进行拆解,真正地传达个体性体验在伦理学中的应有的声音,依据唯有一个,那就是我们的身体性存在。身体型写作说明的是感性个体的必然性、合理性,将人拉回别人的感觉而不是神的意志、圣的语录、群体的意愿,坚信善就存在于我们的身体性存在之中。
但是今天的身体型写作也有一种无限躯体化的趋向。因而身体型写作也存在一个提升的问题。身体不仅仅是一个广延物,身体还是对其自身以及所有广延物的意识,我们不能用对物的态度来对待身体:1、 身体为一个物,广延实体——它,2、 身体是对自身之广延的意识——“我”,3、身体不仅是对自体广延的意识, 同时也是对其他一切广延的意识,这个“一切广延”也包括其他“身体性广延”——意识到其他的身体性广延对其自身也有意识——将那个身体性广延意识为一个“他”而不仅仅是“亡”,4、身体是统一了“它”、“我”、 “他”等丰富内涵的范畴,应有一个单独的概念与之匹配——“自体”,5、 自体的意义:意识到自己存在的存在,“自体”是意义价值的源泉,是世界存在的依据,是超越的物理对象,非因果性,非历史性,因为“自体”是因果和历史本身得以实现的依据,因果的因果,历史的历史——“自体”通过来到世界使世界成为世界,一切“世界”只有在自体的参与中才成其为世界,自体赋予世界以意义;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身体具有为世界奠基的价值论基础。
所以身体内在地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下降义,一是提升义。所谓下降义是指纯粹的自我——无规定性的“身体之物”——躯体,主体方面通过躯体来到世界而实现“我”,而一个实现了的“我”才是真实的,在这个方面绝对的善就是对于躯体的自我保全,一切有利于躯体的自我更新与存在的都是善的,在这里单个躯体的生理的感觉(快乐作为躯体运作正常的信号;痛苦作为躯体受阻的信号)构成了善的绝对领域,躯体在此享有一个绝对的实在:“躯体”的唯我论是绝对的。但是身体不仅仅是躯体,它更应该包含一个提升义:自体、“躯体”作为主体意味着就单个主体而言的自为有效性。这里的问题是:躯体如何能使另一个躯体也成立?也即如何处理“我”(Ego)与“非我”(After)之间的关系——“非我”如何获得“我”的地位。只有自体的结构中前提性地包含了“非我”(他者),自体之“我”不仅看到单个自体自身躯体的唯我论,还看到了外在于它的另外的躯体的同样的唯我论:“我”不仅将之感受为一个异己的躯体(它)同时还将之感受为一个异己的但却与我等一的“我”。“我”意识到我始终处于一种在“他”(他为对象的身体)之中即在彼此的那个意识中的境地;质而言之就是,“我”意识到在“非我”的意识中的那个“我”。现在我们可以结论性地说“自体”意义实际上是“在‘非我’的意识中的那个‘我’”。也就是说自体中心的伦理学也坚持“在‘非我’的意识中的那个‘我’”,对于伦理学的有效性,这是一种真正的坚持,它坚持这个概念的“从我原生”性,将这个概念从公共信念中剥离出来,否定了它受到公共信念寄生时的诸种性质(如以人的身体性、集团性否定人的个体性,以人的灵魂性否定人的身体性……),恢复了它的自体意味。
概而言之,我认为当今小说创作存在着一个由躯体化向自体化提升的问题。身体型写作不仅意味着对身体的感性的自由而不仅仅是人的理性的自由作出了新的承诺,同时还意味着把人看作个人的观点:将人提升为“个人”,反对从外在于其自身的含目的性来理解人,而是从无数的“我”是无数的“他”成为主体的前提的意义上来认识人的自体性,是对人的主体性的一个新的认识和保证。
标签:小说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文学论文; 莎菲女士的日记论文; 读书论文; 道德论文; 沉沦论文; 作家论文; 朱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