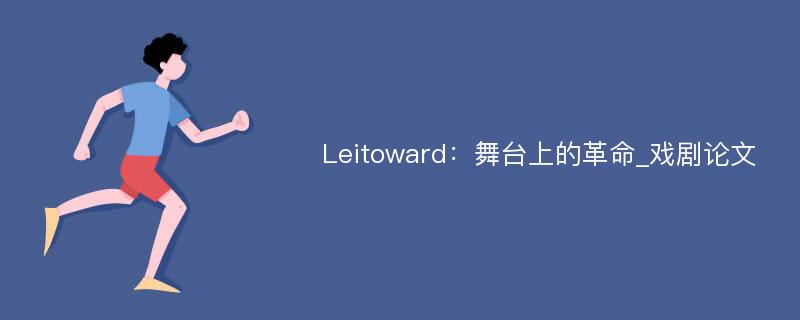
利托沃德:舞台上的革命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革命者论文,沃德论文,舞台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习惯于一种认识:文学形式的优劣取决于表达的个性化程度。果其如此,戏剧这个文学类别怕是难以达到高度的个性化程度的。戏剧的创作过程是集体合作,戏剧的完成形式是台上的集体面对台下的集体。
英国导演利托沃德用自己的创作活动说明戏剧艺术的魅力和杀伤力恰恰来自它的集体创作特点。她依靠理想主义和个人天才开创了艺术创作中的集体主义方式。她粉碎了英国传统舞台的自以为是、商业戏剧的自鸣得意,树立了政治上激进、艺术上大胆的舞台风格,从而证明戏剧艺术的革新首先取决于思想的革命,取决于对旧文化中的旧生产关系的颠覆和批判。她将社会主义信仰贯彻到艺术创作中,首先从体制上对资产阶级剧团进行改造,并以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戏剧创作,创立了一种与导演中心论不同的集体合作模式。
利托沃德出身工人阶级家庭,十七岁获皇家戏剧学院奖学金,但旋即离校。
利托沃德的戏剧生涯从她结识麦克尔开始。麦克尔是出身工人家庭的革命青年,致力于以戏剧形式号召失业工人起来进行阶级斗争。1931年创立了名叫“红色麦克风”的街头剧团。剧团所在地罢工风潮此起彼伏,为配合政治集会和示威游行,剧团采用活报剧的演出形式。有时他们甚至边演边写。演出简洁同时也流于简单,标语口号倾向自然是严重的。但他们坚信他们是在为本阶级的利益说话,所以始终充满信心。有时他们在台上演出,他们的观众则在台下和警察舞拳弄棒。他们的演出难以以专业标准要求,可供他们学习的榜样也只有民间魔术师、歌手和翻跟头的卖艺人。
就在这时,利托沃德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此前,利托沃德对于中产阶级戏剧的趣味深恶痛绝,并只身前往欧洲大陆考察戏剧。她出现时,麦克尔的街头剧团已经看到了莫斯科艺术剧院是怎样以精湛的艺术手法表现深刻的社会内容。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学习人类戏剧文化的经验。他们的导师是克雷、阿庇亚、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瓦柯坦戈夫。1934年剧团更名“行动剧团”,开宗明义地宣布非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不演。
在艺术上,利托沃德采取了与专业剧团不同的舞台表现形式。她首先对团员进行形体训练。他们在这方面的第一个尝试是《约翰.布连:一出带台词的芭蕾》。这场演出融汇了语言、动作和灯光效果,明显受了梅耶诃德的影响。同梅耶诃德一样,利托沃德要求演员像杂技艺人那样灵活,能够创造出舞台感很强的形体动作。同时,这种形体动作并非基于对日常生活的模仿,而是脱胎于大众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如马戏、狂欢节的活动等等。
利托沃德和麦克尔戏剧活动之所以不同凡响,在于他们没有为赢利去重复业已证明有效的模式,而是努力发现新形式,而且是为表达政治纲领的新形式。他们关注社会而且希望通过演戏改造社会。在这个阶段,他们不再因为自己有政治纲领而继续在舞台上摇旗呐喊、在台下捋胳膊挽袖子。他们希望有效地表达思想,同时坚持诗意地表达思想。这时,剧团开始强调技术上的精益求精、演出效果的完美。
1936年剧团演出大型反战剧目《凡尔登的奇迹》,获得巨大成功,众多艺术家要求加盟。利托沃德和麦克尔因势利导,成立了“联合剧院”。不久,西班牙内战爆发,“联合剧院”即上演维加的《羊泉村》和反映这场内战的时事短剧,剧团在众多公共场所举行演出,甚至登门上户为反法西斯阵线募捐。“未来的戏剧不会产生于上流社会的闲适,而必将产生于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激烈冲突”,联合剧院的这一戏剧观,不单单是用文字表达的,而且以团员的行动来实现。
对于利托沃德,组织一个剧团不单是为了戏剧创作,也是为了追求一种生活方式。利托沃德最大的贡献是集体创作模式。这一反导演中心论的方法反映了利托沃德对工业化造成的过于精细的分工的反叛。团员不仅接受声音台词形体训练,同时还学习戏剧文学、舞美设计和舞台技术。一个团员首先是创作者、或者说是创作集体的一员,而不是单纯为某位导演的某种阐释服务的工具,进一步说也不是某一个剧作家的传声筒。1940年联合剧院演出活报剧《最后版》,追溯了1934-1940年间的国际国内大事:三十年代大萧条、英德海军协定、西班牙内战、苏芬战争和慕尼黑协定,最后发出反对战争的呼唤,呼吁各国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不作本国资产阶级的炮灰。整个演出由全体团员根据各自的案头工作集体创作,又由全体团员共同讨论制定舞台方案。
二战硝烟甫定,利托沃德和麦克尔召回原班人马,组建了“戏剧车间”。“车间”依然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建团纲领规定的任务是“创造公正幸福的社会”。戏剧史中的杰作在他们看来无一不是“反映人民的理想和奋斗的”、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戏剧”。戏剧车间就是“艺术家、技术工人和演员组成的团体”,目的是“借助灯光音响的最新技术、借鉴音乐和舞蹈的形式,创造可以和电影媲美的节奏快、造型能力强、灵活多变的戏剧艺术”。剧团同时是一个公社。社员们一起排练、一起生活,工资不多但人人平等、没有大腕明星和小演员,只有分工的不同。凡此种种同专业、商业剧团真是泾渭分明。“戏剧车间”的足迹遍布英伦三岛和西欧。
1957年剧团结束漫游,在伦敦工人阶级聚居区“东斯特拉福”落下了脚。经过多年探索,“戏剧车间”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这就是创作中坚持集体原则,排练中借重即兴表演和小品表演,舞台体现方法杂糅民间传统的歌舞、哑剧、杂耍和小丑表演。
她导演爱尔兰反英剧作家布兰顿.贝汉的《死刑犯》的过程很能说明她的排练方法。《死刑犯》自传色彩很浓,描写爱尔兰一所监狱里各色各样的犯人一天的生活。剧作家本人投身暴力抗英,身陷囹圄,写起监狱生活自然栩栩如生。然而,他笔下的生活不可能为演员所熟知。于是,利托沃德带着演员爬上剧院楼顶。在一个四面都是水泥预制板的狭小空间里,导演要演员围成一个圈,想象自己在放风。演员连续几个小时走圆圈,一直走到厌烦。接下来他们又根据监狱生活排练小品:列队、做操、拍狱卒马屁、夹带香烟。如此日复一日,游戏感逐渐减弱,现实感愈来愈强。读过剧本后演员仍然不知道自己扮演什么角色。等到排练过程进行一半以后,角色才分配下来,而演员这时才发现即兴表演已涉及到剧本的许多细节。同时,演员即兴排练的小品的部分内容也常常被加进原作。结果,演出的真实感大大加强,但自然也常常遭致剧作家的不满。
利托沃德借助即兴表演帮助演员把握剧作内容,但她的成品并不就是高度写实主义的。利托沃德喜欢普通民众光顾的下等歌舞厅,她喜欢那里鲜活放肆、热情奔放的演出气氛。她的演出夹杂了大量的歌谣、舞蹈、插科打诨、以及与观众的直接对话。演出中采用的音乐对观众富有直接感召力,如爵士、摇滚、通俗演唱。她导演的《人质》从头至尾都有歌唱和演奏,以致被称为一出音乐剧。
以上流社会语音为标准的、字正腔圆的台词朗诵是所谓上流社会戏剧的主要形式特点。利托沃德反其道而行之,在台词中大量使用方言土语。更值得注意的是,利托沃德的演出已经难以用“话剧”概念涵盖。她重视语言以外的、非文学的舞台表现方法。在排练莫里哀和本琼森喜剧时,她大胆同时又是合情合理地借用了意大利即兴喜剧的假面具。但最后舞台演出时,她并没有要求演员戴上假面具表演。然而,由于排练时演员因戴上假面具而无法依赖面部细微表情,只能偏重肢体语言,这样登台演出时他们的形体就极具感染力。又如,为了表现一只航行中的船,利托沃德安排两个演员并肩而立,一个上下起伏,一个左右摇摆;一只绿色的航行灯和一盏仓门灯随之颠簸,再配上马达“噗噗”的哼鸣,一只夜航船就出现在舞台上,连观众也体味到了海上航行的眩晕。
在舞台空间的选择上,利托沃德摈弃第四堵墙。《最后版》的演出采用了四面观众的表演区。演出莫里哀剧目由演员当众推动一个直径四米装有一扇门一扇窗的转台。演出《理查二世》和《菲维镇的阿登》时又恢复伊利莎白时代高低两层的表演区。这样的舞台空间显然有助于消除演员和观众的间隔,把剧场变为握手言谈的场所。
利托沃德虽然有种种形式上的探求,但她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她并不以突破某一传统演出形式为最终目标。首先,她是充满是非感和正义感的革命者。无论排练新人新作,还是恢复古典剧目,她首先注意与社会现实是否相关。她的演出,每一次都是对现实的干预。这是她同以剧场为出人头地的战场的“先锋”导演的不同之处,也是她与当代调侃人文主义传统,油腔滑调闪烁其辞的“后现代”导演的不同之处。
对于她,戏剧首先是社会行动,而社会历史和社会关系是可以认识、理解和改变的。所以她演出前的案头工作是认真、仔细、严谨的。一出过去的戏所属的过去的时代、过去的思潮、过去的文学都要认真研究,而且要由参加演出的演员亲自动手研究。研究心得即成为即兴表演的源泉。常常是剧本还没有接触,与剧本有关的研究已经开始,在研究的基础上再开始排练。只有在案头工作和即兴表演已经帮助导演把握了一出戏的精神实质和思想脉络时,剧本的排练才正式开始。
《啊,战争多美好!》是利托沃德的扛鼎之作。最初创意是由BBC一个一战老歌节目触发的。利托沃德决定围绕着这些老歌创作一出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演出。这可以看作是一次主题先行的创作。这主题很明确:揭示战争根源并展现战争丑恶。“戏剧车间”的成员分头研究一战历史,档案、亲历者回忆和史家著作都成为创作素材。演出形式上最重要的决定是参照叫做“快乐公鸡”的歌舞团的表演风格。“快乐公鸡”是活跃在英国海滨城市布莱顿的一支白面丑表演团。一战时他们正是唱着BBC节目中的这些老歌娱乐游客的。利托沃德让交战官兵穿上白面丑戏装,江湖艺人俗艳的装束和战场的刀光剑影就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艺人当众载歌载舞,身后多面巨型荧幕上由幻灯打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景象,这再次形成了动人心魄的对比。有时一场戏结束,幻灯投影还不动声色地加上评论:“11月松姆战役结束。伤亡人数:1,332,000。战利品:0”。射击、投弹、刺杀这些战斗动作都被利托沃德化解成白面丑的舞蹈套数,这就同观众熟悉的舞台战争场面形成了不同寻常的对比。利托沃德采用这些手法旨在达到一种间离效果,以不同寻常的表现方法表现不同以往的战争观:战争丑陋、冷酷、猥琐、猥亵。交战双方都不是英雄,因为他们都不过为各自国家的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战。利托沃德采用这种方法并不是为了强调戏剧的游戏感。她也许意识到,写实手法描写战争容易使观众为战争中的人和事感动,而不一定能够帮助观众对战争根源进行思索。而面对涂了白脸的歌舞演员,观众就不能无视眼前的一切是在表演战争、讲述战争、阐释战争。演出中的一战老歌不少都温情脉脉,观众听在耳朵里不免生出怀旧感伤情绪。他们听得泪眼朦胧时,战场上的血腥搏斗、战场外的肮脏交易自然也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利托沃德是不会容许这种情况在剧场出现的。这样,一首甜蜜忧伤的歌曲“大伙都不愿失去你,但还是希望你继续前进”就被安排在双方士兵残酷肉搏的时候响起。利托沃德通过案头研究认为一战归根到底是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原料和市场进行的一场“商战”,各国士兵不过是被代表帝国主义利益的上层军官驱赶的羊群。所以,利托沃德就把士兵冲锋陷阵表现为放牧的场面,为演员设计了羊的形体动作。
不少中产阶级观众和学者在肯定利托沃德演出的艺术成就时,又指责她对一战的阐述失之偏颇和流于简单化。对于这一看法的最好回答来自世界上无可争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权威A.J.P.泰勒。他在自己1963年出版的一战史专著的扉页上,将书题赠给《啊,战争多美好!》的导演。
利托沃德不断获得艺术上的成功。面对成功,面对剧团遭遇的经济困难,利托沃德开始动摇了。她把《死刑犯》和《人质》这两部爱尔兰抗英题材的演出,转移到商业剧大本营伦敦“西区”演出,引起众多团员争名夺利,而部分团员则批评进军“西区”是受资产阶级招安,有违剧团宗旨。利托沃德不得不告别剧团,她感叹商业剧场夺走了“车间”的人才,消解了“车间”的激情。虽然利托沃德后来曾返回剧团,但热情已难胜旧时。1968年利托沃德终于告别了亲手创立的剧团,1975年进而移居巴黎。
利托沃德的戏剧革命首先针对资产阶级商业戏剧的体制。坚持创作上的集体主义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是创作与商业戏剧迥然不同的新戏剧必须的和根本的一步。这根本的一步决定了她的戏剧革命不是戏剧才人进行的抢人耳目、抢夺地盘的操作,决定了她不同于排坐次等招安的草头王。
利托沃德摈弃典雅周正的客厅话剧,从生机勃勃的大众娱乐中汲取养分,在能够与观众自由交往的空间里,创作一种融形体动作、音乐谣曲、写实表演于一炉的戏剧表演。当年利托沃德除旧步新,一扫商业剧场的无聊猥琐,给剧坛吹进了充满理想的清新气息。今天她的名字早已湮灭,她的手法早已成为导演的惯用手段。但今天不少声名煊赫的导演都曾从她那里获得过启迪,无论是法国蒙努什金“太阳剧团”的社会主义建团模式、还是布鲁克采用的多种手段的整体戏剧,都曾受到过这位戏剧前辈的有益影响。
在今天,在面临全球资本主义化的今天,在为人生的艺术日益蜕变为粉饰太平的演艺的今天,对有志振兴戏剧批判现实主义功用的戏剧工作者,利托沃德应当是一份沉甸甸的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