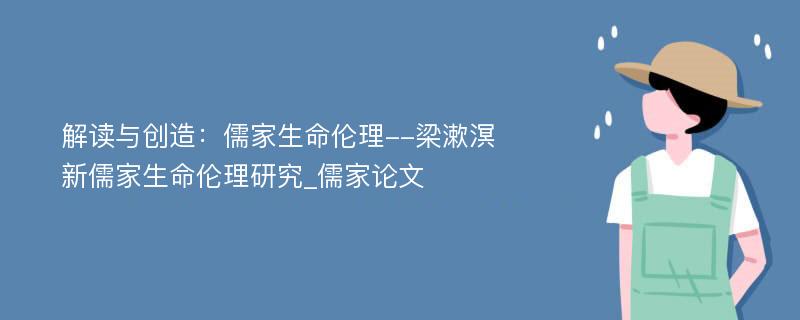
诠释与创造:儒家的人生伦理——梁漱溟新儒学人生伦理思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儒家论文,人生论文,儒学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梁漱溟对儒家伦理“真精神”的发现,可以说是以自己业已形成的解释系统对儒家伦理重新诠释和创造性地发挥。它首先发轫于对儒家形上学的所谓生命体验和悟解。梁漱溟认为宇宙间实没有那绝对的、单的、极端的、不调和的事物;如果有这些东西,也一定是隐而不现的。凡是表现出来的东西都是相对的、双的、中庸、平衡、调和。所谓变化就是由调和到不调和,或由不调和到调和。因此,其思维方式不是实体性的,形成的概念也从不去处理有关实体的具体问题。这在根本上迥异于印度和西方的各种形而上学。
中国的形上学家们据以获得宇宙涨落的感觉和体验是一种非理性的直觉过程。它的概念只能通过“抽象的,虚的意味”加以表达。把宇宙生命描述为一个不停顿的“流”。这种“流”借助相互对抗、相互贯通的二重性力量获得形式和运动。梁漱溟确信孔子就是基于这种原理,系统地讲述人生伦理并为其在社会中实行发展出如礼、乐等各种手段。宇宙的本质和人生的本质是同构的、贯一的。当表现为人生伦理时,就是“仁”,一种和谐的、创造的、乐而忘忧的生活。同充满春意生气的宇宙一样,儒家主张随感而就,“顺着自然的道理、顶活泼顶流畅的去生发”〔1〕。 梁先生就是这样以东西交融的文化视角来发掘或回复孔子人生的“真义”,同时也寄托了他对理想人生的向往。
一、心之路:东、西无碍
早在1918年,梁漱溟开始替孔子“说法”时就明确提出,“欧化实世界化,东方所不能外。然东方亦有其是为世界化,而欧土将弗能外者。”〔2〕由此可见,梁漱溟并不是一个狭隘的东方论者或孔学者。而是企图容受和“拣择”东西之长为我所用,表现了思想家的宽广胸怀及其理论的张力。在他看来,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尤其是儒家伦理精神的张扬,一方面待于旧传统上的新创造;另一方面在世界逐渐一体化的今天,决不可能孤立地进行。儒家伦理要想获得普遍价值和真正意义上的复兴,不能不考虑到其他文化的成就特别是西方现代精神的走向。但是所谓东、西融通只停留在梁漱溟的“心之路上”,仅仅作为一种理论刺激或启示转而成为其旁证或支离的材料。
1.柏格森生命伦理学与佛教唯识宗的契合
柏格森认为,生命的存在不是一种僵死的物理存在,而是一股永恒流动、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流”,是一种永恒的生命创化过程。因此,它流动不居,是一种无穷的“绵延”和“生命冲动”,如同一切存在都是连续表现的动作而无静止的存在一样。也就是说,在柏格森眼里,只有变化着、流动着的倾向和趋势,而生命则是一种最为活跃、最富有变动的一种运动态势。因此,对生命存在的把握,必须抛弃那些既成不变的理性形式和传统教条,用心理的直观去体现生命之流的律动。宇宙万物都是某种神秘的生命之流的派生和显现。但不同的存在状态下,生命的冲动有着不同的形式。
梁漱溟认为生命派之哲学和伦理是西方既往人生态度的反动和转向。从向外逐物到向内求索;从理智计算到直觉体验。“此刻他们西洋人经过了那科学路也转到这边路上来——此刻西洋哲学界的新风气竞是东方彩色。此无论如何不能否认的。”〔3〕
梁漱溟又将其与佛教唯识学作了比较,虽然两者在方法论上有根本的差异,但它们中心概念都是“不断流动的”宇宙和流动的实在,“所得的道理却多密合,这是为两方都研究一个东西——生命、生物——的原故。”〔4〕
如果说柏格森的直觉尚有可疑之处,诸如主观的、情感的,因而也就难免其偏私的一面。那么,唯识宗的“现量”则是纯静观的,将有所为的态度去净而为无私。就是看飞鸟,只见鸟(但不知其为鸟)而不见飞;看幡动,只见幡(但不知其为幡)而不见动。倘能做到,便是头一步现量。次一步现量顺此向前,“不过比前更进一步的无私,更进一步的静观……就是眼前面的人和山河大地都没有了!空无所见!这空无所见就是本体。”〔5〕以此观之,生活就是“相续”。 生物或生活实不以他的“根身”、“正报”为范围,应统包他的“根身”、“器界”、“正报”、“依报”为一整个宇宙。所以“尽宇宙是一生活,只是生活,初无宇宙。”〔6〕面对差不多已成定局的宇宙, 它是由我们前此的自己而成为这样的,故称为“前此的我”,而现在的意欲就是“现在的我”。因此生活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现在的我”对于“前此的我”之一种奋斗努力。“现在的我”是一种生机勃勃的当下向前的活动。
梁漱溟不仅仅是在寻找柏格森与唯识宗的契合点,而是通过这种嫁接获得一种对孔子态度和人生的最佳解释方式,并以此重新建构儒家伦理精神的普遍价值。
2.艰难的复归:梁漱溟与泰州学派
梁漱溟对儒家伦理的认同和归宗并非始于对源头探寻和对正宗经典的解读、了悟,而是采用时间倒推或所谓精神还原的方式。其中泰州学派在其思想嬗变过程中起到了转折性的作用。“我曾经有一个时期致力过佛学,然后转到儒家。当初转入儒家,给我启发最大,使我得门而入的是明儒王心斋先生,他最称颂自然,我便是由此而对儒家的意思有所理会。”〔7〕
泰州学派为王艮王襞父子所创。王艮师事王守仁、但又时时不满师说,以“日用百姓既道”、“淮南格物说”,“安身立本”论等见解在王门后学中自成一派。黄宗羲在剖析王艮的学术宗旨时说:“王门惟心斋盛传其论,从不学不虑之旨,转而称之曰自然,曰乐学。”〔8 〕不学而虑是说“良知”本体是现成的,不存在被货色、名利等欲望蒙蔽的问题。也不必进行“省察克治”之类的道德修养工夫。良知既然现成,那么靠什么去体认呢?“私欲一萌时,良知正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9〕所谓“一觉”是直觉式的思想省司。 泰州学派在人生观或人生态度上“寻孔颜乐处”,即随感而应,以乐为教。此乐非所得于外而深造自得之乐。是一种安和而圆实的人生境界。大体上有三层意思。其一,“人心本是乐”乐就在自己的内心而非他处寻觅。其二,将“乐”这种主观情感提升到本体的高度。其三,认定“乐”的本质是超功利的。“日用间毫厘不察便入于功利而不自知,盖功利陷溺人心久矣。须见得自家一个真乐。”〔10〕与功利相联系的乐是假乐,转瞬即逝,只有对功利的超越方是真乐。这一点是真人生观的核心。
梁漱溟认为只有泰州派传统承了孔子的血脉和把握了真意。从《论语》全书看。孔子以仁为己任,忍受物质生活困顿和“不遇”的艰难“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其并不以为苦、而是抱着乐观、豁达和向上的态度。故自有曲肱饮水之乐,又赞扬颜回有陋巷箪瓢之乐。孔子虽视求富贵去贫贱为每个人对自身利益的正当要求,但这些是以是否符合“义”为前提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同时,倘若与“义”相符,既使“曲肱箪瓢”,“乐亦在其中矣。”梁漱溟认为,这种人生态度是儒家人生伦理的宗旨所在。同时也是体认宇宙生命本体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境界。人如果把重心与乐趣寄托在向外逐物的满足上,只能带来无穷无尽的苦楚和“顿滞”。这也是西方老路在人生上的教训。因此必须超越“有对”而复归于儒家的“仁”。综上可见,梁漱溟通过泰州学派向孔子复归的道路是艰难的。其一,“六经注我”或“我注六经”毕竟不是“本文”。其二,在无现实功利支撑的条件下企图主观超越,到头来终为功利所困,这也是儒家伦理的一个内在难题。其三,中国当时的内忧外患与现代化道路企盼的双重困境,并不是仅仅依靠“精神复归”就能突围的。
3.儒学的现代化出路
完成了东、西嫁接和精神复归,儒学的出路或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也就找到了。梁漱溟论证了真正的儒家伦理精神不仅不同现代化相冲突,而且是现代精神诸如民主、自由、科学等的真正根基。
“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但在“五四”反传统思想家的意思里,现代化几乎等于“西化”。这种误解是有其历史和现实的缘由的。因为处在前现代化的中国要实现的现代化目标,和已达到现代化的西方社会模式具有很多相似性。梁漱溟不否认中国进行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问题在于必须打通一条中国自己的道路。
梁漱溟指出,绕过后世陋儒制作的僵化而冷酷的礼法制度可以发现忘我的、温情的、乐观的、向上的人生。而且人的个性必将在充满生机和秩序的宇宙中充分发挥和施展。因此真正儒家精神足以容受尊重个性、尊重个人人格的民主与自由,而且又可避免西方式的以权利、义务、法律维系的人与人对立关系和计较算帐的心理。
儒家精神缺少科学、但并不意味着排斥科学。梁漱溟坦率地承认,就科学技术而言,中国不是一般地不及西方,而是差距太大。因此,学习科学技术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应有之义。况且它并不是西方民族所独有,而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虽然我们“艺术”的或“玄学”的方法没有直接导出科学的成果,但儒学关注现实生活和经世致用的态度足以使学科技术生根发芽,同时其本身的含容能力和超越精神又可避免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内在冲突。
显然,梁漱溟的结论很难说是儒家精神的本来面目,可能仅仅是他自己的一种理想。正因为如此,梁漱溟对儒家伦理精神的阐释实际上已涵育了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是综合了东西文化之长而对自己文化传统的重新整合。虽然其中充满着牵强和矛盾,但毕竟“巧妙地避免了东方优于西方的偏狭复古见解。他也没有呆板地明白赞成中体西用或旧瓶装新酒的机械拼合。这不能不说是他立论圆融高明的地方。”〔11〕
在某种意义上说,未来儒学能否发展和最终立足,取决于对先进文化特别是科学民主精神的真正容受和接纳。
二、孔子的真精神
孔家伦理和文化的核心是什么?梁漱溟指出,孔子将人生纳入自然流行的宇宙大生命中,其根本主旨是表达一种生活以及如何生活的样法。“吾道一以贯之”并不是知识上的求真态度,而是尽性成德之善。因此,孔子所制定的礼乐、伦常表示的即是日常生活轨道。循着这一最一般的道德规范而生活就是“道中庸”。孔子的人生伦理不是呆板的外在规范,而是基于人的生命本性和内在的精神生活。其根本目标在于成就完善的人格。因此,“道中庸”的生活中又蕴涵着“极高明”的方面。就这个意义上讲,人借以挺立道德人格的实践,是处处只见义理之当然,而非只知现实的功利。所谓义理无非是教人修养以“复其本”,并不是认定一个客观道理,如臣当忠,子当孝之类;并不是一样一样去学着做各种道德善行。只是要人合天理,恢复自己生命自然变化之理。因此,孔子之道,在于充分伸张人的道德可能性和提升人生之境界。而这一切又是顺乎天德的,不是人为立法、掏空活生生的欲望去迎合干瘪的外在规范。
总之,梁漱溟认为孔家的精神在于:人性即天性,人德即天德。这是一种合理的因而也是当今应该发扬的精神。
1.孔子的态度及人生
循着宇宙大化流行的道理,孔子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是一切不认定,唯变所适。《论语》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又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对于其实不如何的而认定其如何,已经铸错了。况且一经认定坚持,在我就失中而倾欹于外了。“平常人都是求一条客观呆定的道理而秉持之,孔子全不这样。”〔12〕机械地规定这个是善那个是恶,这个为是那个为非,不仅抹杀了境遇选择的丰富性而流于一般的形式,更重要的是离开了“本然敏锐”造成“误导”。宋明理学家的失足就在于只认定外面,造成了极端的态度和固执。“天理”成为人们的异在,世所谓“以理杀人”是也。他们把一个道理认成天经地义,顺推下去就成了极端,就不合于中。梁漱溟认为这其中的一道理在于,仿佛事物是圆的,若认定一点,拿理智往下推就成为一条直线,不成圆,结果就是不通。
2.尚情无我的理想人格
由于中国人与宇宙、自然的生命和谐一致,因此,“自我”对外界没有矛盾、没有要求,与物无对,无我而有他。梁漱溟认为孔子就是把握了人类生命最深处,开出无穷无尽可以发挥之前途。他的人格就是不分人我界限,不讲什么权利义务,所谓孝悌礼让之训,处处尚情而无我。“尚情无我”既是梁漱溟对孔子的追寻又是他自己对理想人格的最高概括。
尚情就是履行仁道。儒家之“求仁”,也就是寻求情感上的自慰自安。“直觉敏锐且强的人其要求安,于是旁人就说他是仁人,认真行为为美德,其实他不过顺著自然流行中的法则而已”。〔13〕追求情感上的自安与圆满就是向内心探索,体认或体验人的生命本性与宇宙生命相契合的过程。所以说,“孔家情志安定都为其生活重心在内故也。”〔14〕总之,梁漱溟的“尚情”说强调了道德情感在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中的作用。他认为“情既是道德行为的发出者,又是道德责任的承担者。道德行为主要是出自主体情感意志的自愿、自求,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外在伦理规范的约束。这一点上,显然是对自宋以来,种种偏激之思想、固执之教条的反动。
与“尚情”相应便是“无私”“无我”。这里的“我”不是指与宇宙本体相通的“生命”,而是指基于理智的自我意识、功利观念和“计算之心”。在梁漱溟看来,这些都是同其理想人格相违背或相碍的。理智的计较是出自“私欲”、“有为”、“有对”,它使我们失于中而倚于外。这种“算帐的生活”违背了生命本性,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仁只是生趣盎然,才一算帐则生趣丧矣!即此生趣,是爱人敬人种种类行所油然而发者;生趣丧,情绪恶,则贪诈、暴戾种种劣行由此其兴。”〔15〕人在欲望中只知为我而顾不到对方;反之,人在感情中,往往只见对方而忘记了自己。可见,“有我”的人生与“无我”人生的本质区别和境界的高低不同。但是,当具体的回答如何才能做到“无我”时,梁漱溟的答案却依然类似于宋明理学家“灭人欲”的“无欲”。和其他现代新儒家一样,他一只脚迈向了现代,另一只脚却被“腐儒”的阴魂紧紧地缠住。
这种“尚情无我”的人格理论或模式是集形上学、认知方式和道德践履为一体的。看起来“廓然大公”而圆实有力。这也正是梁漱溟先生一生努力成“仁”的力量源泉和奋斗不已的目标。
3.儒家人生伦理的基本精神
梁漱溟认为儒家人生伦理的基本精神体现于人类生命的终极关怀,又避免了如西方或印度式的宗教“蹈虚”。是在实实在在的生活层面,开发出一条充分宏扬人心向善和自我超越的道路。也就是“吾心卓越乎其身而能为身之主宰”,以生活本身为目的不假外求的生活样法。其基本前提是建立在儒家对人性本善自信之上的。“孔子虽然没有明白说出性善,而荀子又有性恶的话,然从孔子所本的形而上学看去其结果必如是。”〔16〕《易经》上,继之者善,成之者性,百性日用而不知的话,即是对人性的洞察和把握。梁漱溟认为孔子所谓“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其中性相近就是指人性本善和向善的心理。孔或儒家之所以倾力于此,恢复、扩充之,原因在于不使这个“活动自如、日新不已”的本性为习惯所碍、淹滞生机。无论是好的习惯,还是坏的习惯,一有习惯便是一偏。”故一入习惯就是呆定麻疲。而根本把道德摧残了。而况习惯是害人的东西,用习惯只能对付那一种时势局面、新的问题一来就对付不了。”〔17〕可见所谓伦理道德者、只能是那生生不已的生活本身而已。
依据人性本善的道理,如何具体地安顿生活呢!梁漱溟认为,这就是儒家的孝弟之提倡和礼乐之实施。孝弟就是让人作一种富有情感的生活,并从情感发端处下手。人在孩提时最初有情自然是对其父母,和他的兄弟姐妹;这时候的一点情,是长大成人以后“只须培养这一点孝弟的本能,则其对于社会、世界、人类、都不必教他什么规矩,自然没有不好的了。”〔18〕
乐专门作用于情感,并赋于人们情感冲动一个根本变化,形成一种生活的态度。孔子的礼乐所以异于他人之礼乐,“因为他有其特殊的形而上学为之张本,他不但使人富于情感、尤特别使人情感调和得中”。〔19〕《乐记》所说,……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身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就是这个道理。
既然孔子和儒家所追求的是一种同宇宙和谐相契的情感生活,并以其自强不息同生生不已的生命本性相勾通,那么其所贯注的人生精神则是阳刚乾动的。梁漱溟认为,中国人所走的路正是脱离孔子的这个精神而一向总偏阴柔坤静一边、近于老子。“刚之一义也可以统括了孔子全部哲学。”〔20〕所谓“刚”的精神就是里面力气极充实的一种活动。他要求人们奋力地向前动作,而且这种动作是符合生命本性并直接发韧于情感,不是出于欲望的计虑。这不仅是孔子或儒家本来倡导的人生精神同时又是当今中国生灵乃至人类获救的曙光。“只有这样向前的动作可以弥补中国人夙来缺短,解救了中国人现在的痛苦,又避免了西洋的弊害,应付了世界的需要。”〔21〕
三、生命的本质与人生的境界
梁漱溟沿着他所体认的孔子或儒家的理路继续发挥和创造。对其人生伦理思想具有总结性意义的,是晚年所著的《人心与人生》一书。梁漱溟认为,若对人生或人生之伦理认识和把握,必须有其正确的心理学基础,也就是对“人心”的体察。西方近代以来人生哲学的谬疾和人生观的误导,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忽视了对人心的认识或心理学方法偏颇。“心理学之无成就与人类之于自己无认识正为一事”。〔22〕
古代儒家之所以对人类生命有其深切认识者,在于其对人性、人心的洞察和体悟,或者说是以正确的心理学前提为支撑的。但是由于其早熟性、况且又都是通过个体体验的浑然了悟,因而缺乏清析的学理和累加式的进步。尤其随着时代的变化和人类重心问题的转移,人们对生命本性和人生境界认识也应不断翻新。但是儒家立论的基本前提和努力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梁漱溟也是在这个框架中勾划他对生命本质的认识和理想人生的设计。
1.自由与创造
梁漱溟认为,一切生物都离不开个体生存和种的繁衍两大问题,并围绕这两大问题配备所需要的种种手段。这些是随着生物的生命俱来,即所谓本能。作为生物的人,也是莫能有外的,但作为人的生物恰是突破这两大问题的局限,通过对自由的追逐、创造与宇宙大生命通为一体。这才是我们把握生命本性或本质的逻辑起点。人在思想上每有所悟,都是一次翻新;人在志趣上每有所感发,都是一次向上。人类生命就这样新新不已并逐有提升。也就是说,当人类从动物式的本能解放出来后,便豁然开朗、重现一境天地,并与浑全无对的宇宙大生命契合,人类由此获得和开发出无私的感情和廓然的襟怀。这主要表现在对直接或间接来自于生存和繁衍两大问题利害得失的超越。甚少是外面的任何利害得失均不能压倒内在的争取自由和不断创造的生命力。”人必超于利害得失之上来看利害得失,而后乃能正确地处理利害得失。”〔25〕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体现了人类的超越与自我超越。不断超越也就是不断地创造。
总之,“道德之唯于人类见之者,正以争取自由,争取主动,不断地向上奋进之宇宙生命本性,今唯于人类乃有可见。……在一切现在物类——它们既陷于个体图存、种族繁衍两大问题上打转转的刻板生活而不得出——此生命本性早无可见,从而也就没有什么道德不道德可言。”〔26〕
2.本性与道德
人的本性具体表现在情感意志以及行动所恒有的倾向或趋势。梁漱溟认为它是由两个层面构成。其一,是由物到人演进过程中取得的,为人类所共有的自觉能动性,可称之为“人类基本性格”。其二,是其得之于不同时代或不同地方以及不同时又兼不同地的人群生活所感染陶铸的那种性格。也就是具体的差异性,可称之为“人类第二性格”。两个层面虽内在于人类本性当中有机地构成丰富多彩的人性或人生,但其中基本的方面是不能改变的。只能发展向前,更无后退到动物的可能了,所谓恒有的趋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的本性与宇宙的本性接通,生生不已地向前进发。通而不隔是人性的常态,即所谓人性本善的道理。与此相反,人之有恶,无非起于自为局限,有所隔阂不通。“通者言其情同一体,局者谓其情分内外……恶起于局,善本乎通。”〔27〕
梁漱溟认为,既然人类是宇宙本性的唯一代表,那么如何秉持和扩展本性的常态就有个率性不率性的问题,而所谓道德与不道德的问题正是由此而发。人们在社会中总要有能彼此相安共处的一种道路,而后乃成就社会共同生活。此道路取得公认和共信便成为当时当地的礼俗。凡行事合于礼俗,就为其社会所褒奖称之为道德;反之,则认为不道德受到排斥。在这个意义上,伦理道德也就直接表现为礼俗。也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和保证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礼俗同人类的道德本性毕竟又是两个层次不同的东西。礼俗多而不同,道德楷模也是因时因地而异。但人总是人,都必过着社会生活,因而道德本性应是一致的。同时,“一切礼俗制度莫非利弊互见,……早期利多弊少、中期利弊各半,晚期弊多利少。大抵推行尽力之后,总要转入末路,难以维持”。〔28〕因此,道德的源头和归宿只能是基于自觉能动内在本性的自觉自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与其固守礼俗,不如每问于本性。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缺乏本性的根据和独立自主,只能是一种庸俗的道德、而不是“道德之真”。“生命本性就是莫知其所以然的无止境的向上奋进,不断翻新,人在生活中能实践此生命本性便是道德。‘德’者,得也;有得乎道,是谓道德;而‘道’则正指宇宙生命本性而说。”〔29〕古代儒家正是由此开发出一整套践形尽性之学。人身原为本性开豁出道路来,容其充分发挥表露,自由创造,循道而终有所得(德)。
3.人生的艺术化
梁漱溟推测:随着“人对物”转移到“人对人”的时代,也就是人们最需切道德而且道德又充分可能之时。“那时道德生活不是枯燥的生活,恰是优美文雅的生活,将表现为整个社会人生的艺术化。”〔30〕人们超越了个体图存和种族繁衍,但其意识和情感在自我客观化过程中又会产生难以解脱的内存矛盾和烦恼,而且“人心广大深远通乎宇宙,生命力强的人在狭小自私中混来混去是不甘心的,宁于贞洁禁欲,慷慨牺牲、奔赴理想。”〔31〕这便是一切宗教得以产生和维持的内在原因。然而宗教以其否定人生而最终走向自我否定,同时也因科学的发达和经济的繁荣呈现出失势的趋势。因此,以自律的道德生活代替虚幻的来生生活,或者说以“美育代宗教”将成为必然。而依附于宗教的礼乐或艺术活动也将分离为以道德为根据的艺术化人生活动。
梁漱溟认为,自财产私有以来,人的欲望愈见膨胀、逐物于外。它不仅导致自我异化又使人与人之间疏离,失去自然亲和。因此,所谓艺术化的人生,旨在“使人从倾注外物回到自家情感流行上来,规复了生命重心,纳入生活正轨。”〔32〕梁漱溟设想在未来社会中,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有礼俗而无法律,人们的行为是靠道德调节和舆论褒贬。其二,社会尊贤尚智。其三,人在独立自主中过着协作共营的生活,即非以个人为本位而轻集体,亦非以集体为本位而轻个人。是在相互关系中彼此时时顾及和尊重对方。但道德的社会实以道德或艺术化的人生为其开始。人们优美情感、高尚品质的涵养和扶持,在于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上逐渐倾向艺术化。例如,环境布置的清洁美好,或边劳动边歌咏佐以音乐之类。旨在使人集中当下之所从事,自然而然地忘我并超然于物外。精神所聚,勤奋、乐趣自在其中。总之,“其道不在对人说教而宁在其生活的艺术化。唯其社会人生造于此境地,人的自觉性发展乃进于高度深刻中,这便达于人类心理发展之极峰。”〔33〕综上可见,梁漱溟将传统宗法社会的摹本配以准共产主义理想所设计的艺术化人生境界,其本身就是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艺术”。
注释:
〔8〕《明儒学案》卷三十三《泰州学案》。
〔9〕《心斋王先生全集·乐学歌》。
〔10〕《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一、东崖语录》。
〔11〕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第12页。
除以上注释外,其他均引自《梁漱溟全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