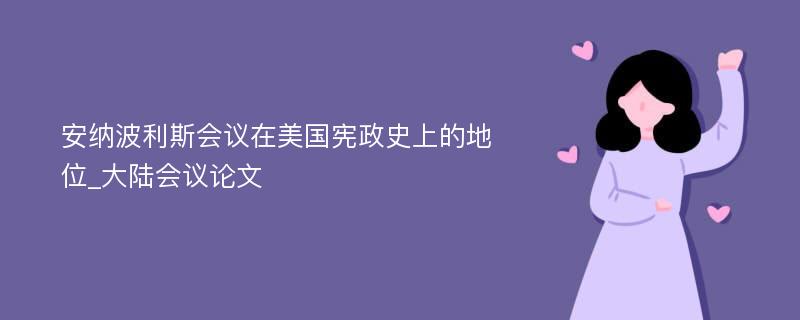
安纳波利斯会议在美国制宪史上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上论文,波利论文,地位论文,在美国论文,会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7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0214(2004)04-0040-10
应弗吉尼亚议会代表的邀请,邦联国会同意召开的安纳波利斯会议于1786年9月11~13日在马里兰邦首府安纳波利斯举行。然而,与会代表所涉及的各邦间存在复杂的利益纷争,另有几个邦代表未能按时出席会议,有的邦甚至拒绝派代表出席会议,致使会议原本要讨论的“赋予邦联国会充分的商业管制权力”的议题无法顺利进行,最终导致安纳波利斯会议在代表们的失望中闭幕。不过,与会代表却借机起草了《安纳波利斯会议报告》,请求邦联国会召开一次全邦联13邦代表参加的会议,讨论赋予邦联政府足够宪法权力以应对联盟紧急事件的问题。由此,安纳波利斯会议成为“1787年制宪会议的先导”(As a forerunner to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of 1787)。[1](vol.2,p4)
美国史学界对于安纳波利斯会议在美国制宪史上地位的评价仅限于上述,有的史学家甚至认为安纳波利斯会议是一次邦联体制改革失败的会议,和以前的邦联改革一样根本没有触动《邦联条例》,[2](p220~421)如马克思·法兰德、戈登·伍德、杰克·雷科夫等,(注:就笔者掌握的资料和互联网搜索的结果来看,中外史学界尚未有关于安纳波利斯会议的专门论述。不过,有关美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著作都提及这次会议,并将它定位于发起费城制宪会议的重要会议,是费城制宪会议召开的决定性事件之一。但是,有的学者提出,如果将美国制宪史置于政治制度的自然发展变化过程中来分析,此次会议并非如此重要,因此提及这次会议多是轻描淡写。关于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参见以下著作:Max Farrand,The Framing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13.pp.8~9;Jack N.Rakove,James
Madiso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Glenview,Ill.,1990.p.41;
Gordon S.Wood,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1776~1787.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9.p.473.)并由此淡化这次会议对后来制定《联邦宪法》的意义。然而,作为一部由立国者们精心设计的、具有历史决定意义的法律文本,《联邦宪法》和《邦联条例》之间的联系是明显的。这种联系不止是时间前后的关联,而是存在制度的变革与延续关系。安纳波利斯会议就是促成邦联体制向联邦体制转变的重要环节。此外,会议报告不仅对未来“全国政府”的权力提出了“宪法性”的要求,而且对如何赋予中央政府宪法权力的程序作了预设。从这个意义上看,安纳波利斯会议对于邦联政府时期“联邦主义者”(the Federalists)所坚持的“国家主义”(Nationalism)(注:杰克逊·特纳·梅因认为,所谓联邦主义者(Federalists)起源于人们对“联邦主义的”(Federal)一词的理解。联邦主义者是指那些支持邦联体制的人。在联邦宪法公布前几年,那些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府的人,开始把这个词汇用到自己身上,其实他们应该被恰当地称为“国家主义者”(Nationalist)。对国家主义者来说,坚持“联邦原则”就是要坚持采取“联邦措施”,这意味着要提高邦联的权威,扩大邦联国会的影响。参见Jackson Turner Main,The Anti-federalists:
Critics of the Constitution,1781-1787.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61,pp.v~iv.
另外,在中文译著中,“ferderalist”通常被为“联邦党人”。笔者认为,在美国两党制正式形成前,在美国社会根本不存在旗帜鲜明的政党,故“federalist”译为“联邦主义者”较为恰当,通常被翻译为《联邦党人文集》的“the Federalist Papers”也宜翻译为《联邦主义者文集》。)原则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
一北美独立后的联盟问题
对共同的利益和安全的追求是不同利益群体形成民族或者建立国家的政治前提,反过来,民族团结的维系和国家的稳定必须以满足人民对利益安全和政治稳定的要求为基础。美国独立战争使13个殖民地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逐渐在《邦联条例》的号召下向实现美利坚合众国的“永久联盟”的政治目标迈进。然而,美国历史学家马克·卡普拉诺夫指出,“《邦联条例》下的政府自始至终是一个革命的产物”[3](p469),始终伴随着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方面的危机。因此,当《安纳波利斯会议报告》在“保全联盟利益”的前提下,提出召开全邦联会议的请求时,一个原本不太合法的动议,却成为邦联国会、各邦议会乃至各邦人民思考的共同内容。
建立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是殖民地人民在美国革命中萌生出来的政治理念。在独立前的150多年里,北美殖民地人民都认为他们是生活在英属北美各个殖民地的居民,他们共同的祖国就是英国。在随后的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中,殖民地人民才逐渐认识到他们自己是美利坚人。[4](p25)到了18世纪70年代,在北美殖民地已经真正形成了一个“现实的美利坚政治共同体”[5](p126)。但是,这样的一个政治共同体却没有一个权威的机构来统一不同殖民地的组织和行动。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指出:“独立以前,美国人既是英国的臣民,又是马萨诸塞、纽约、弗吉尼亚或另外其他殖民地的公民。独立以后,他们就不是英国人了,但是还没有成为美国人,还不存在一个美利坚国家要他们效忠。”[6](p495)
大陆会议是领导北美独立的政治机构,承担着13个殖民地的临时政府职能,其主要职能是组织和协调北美独立的军事行动。独立战争期间,协调殖民地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个棘手问题。大陆会议虽然把各殖民地组织在一起,却没有足够的权威来统一不同的意见。在大陆会议内部,在独立后如何协调各邦之间的关系,是否需要建立一个超乎各邦之上的联邦的问题上,始终存在不同意见和斗争。迫于反英斗争形势的需要,大陆会议最终倾向于建立一个高于各邦的政治机构,以便协调、统一各地的反英斗争行动。1775年6月21日,本杰明·富兰克林向大陆会议提交了一份有关殖民地联合计划的“邦联条款草案”(A draft of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7](vol.1,p238~241)1776年6月,当里查德·亨利·李向大陆会议提议“宣布独立”的时候,也附议:大陆会议应该着手准备一个邦联的计划,交于各殖民地考虑。随后大陆会议成立了以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为首的专门委员会,着手进行关于各殖民地联合的宪法性文件的起草工作。大陆会议宣布独立前,迪金森就坚持“联合的殖民地”(the United Colonies)应该独立,并提议建立一个“强力的全国政府”(a Strong National Government),以取代大不列颠的中央权威。[8](p56)经过近一年的辩论,大陆会议于1777年11月通过了该委员会向大陆会议提交的《邦联条例》的初稿,随后交付各邦议会批准。经过8个邦议会的修改,该法案于1781年3月2日在13个邦正式生效。《邦联条例》第一条规定:“这个邦联的名称应该是‘美利坚合众国’。”[7](vol.1,p248)这样,自托马斯·潘恩在1777年初发表《危机》一文中首次使用“美利坚合众国”以来,这个词汇正式被写入美国的宪法性文件。然而,潘恩所期盼的“美利坚合众国将在世界上和历史上同大不列颠王国一样的壮丽”的理想却没有成为现实。《邦联条例》所确认的“美利坚合众国”只是由13个邦结成的“一个为了共同防御和保护自由以及相互之间的共同福利的巩固的、永久的友谊联盟”,它并不是一个具有主权性质的国家实体。[9](p248)尽管如此,它却表达了各殖民地人民长期向往一个国家归属的理想,部分地满足了殖民地人脱离英国后的民族归属感,得到各殖民地人民的珍爱。“美利坚合众国”的观念也成为维系独立后13个邦团结的重要心理纽带。
但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形成和维系,决不能仅仅依靠情感纽带。美国革命彻底打破了母国与殖民地的隶属关系,割断了殖民地与英国的民族情感。革命也使“美国人几乎一夜之间,成了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最具有经济头脑以及最现代的人民”。根据戈登·伍德的解释,独立战争后,最终能够把各邦人民联系起来的纽带性因素是共同商业和产业利益。[10](p357~362)所以,任何能够维系各邦与人民团结的文件必须恰如其分地体现当时人们的利益要求。
不过,革命过程中依据《邦联条例》建立起来的邦联政府却没有担负起保护各邦共同利益的使命。当初努力使各个老殖民地在一个新的中央权威当局下联合起来时,大陆会议代表根本不是想要建立新的“政府架构”或制定宪法。13个拥有主权的邦都有自己的政府,它们所谋求的不是一个中央政府,而是一个暂时的联盟。用罗得岛邦长库克的话来说,“邦联”不是一个永久性的联盟,而是(有些人认为完全是)作战联盟。尽管如此,《邦联条例》虽然没有创建起一个现代意义的国家,却创建了一种新型的国家体制和新型的高等法律。美国历史学家布尔斯廷评价说,《邦联条例》是从各邦联盟走向联邦国家的重大一步。[6](p508~509)
综观邦联时期的社会情况,一方面,13个邦之间的政治、文化联系日益紧密,要求建立一个行使国家主权的、和谐的政治利益联盟。当时,一些政治领袖已经认识到维护联盟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在制宪会议上分析邦联面临的形势时,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认为,无论从原则和历史来看,联盟应该先于邦而存在,邦政府也是在第一届邦联国会后成立的,“现在我们是一个由同胞兄弟组成的国家,我们必须摒弃地方私利和地区差异”[11](vol.1,p116)。另一个联邦主义者、历史学家戴卫·拉姆齐(David
Ramsay)在南卡罗来纳邦会议上提到13个邦的人民时指出:“作为一个使用共同语言、信仰同一宗教、居住在一个不可分割的国家、被上帝创造的同一个民族,13个邦的人民是一个整体,因此,绝不能允许歧视、损害任何有缺点的、其他邦的兄弟。”[12](p456)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强力有效的中央政府的管理和调控,13个主权邦之间因利益冲突而导致的独立倾向危及联盟的存在。首先,由于各主权邦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邦在没有强大的中央权力当局维持邦际平衡的情况下,联盟面临崩溃的危机。经济利益纷争导致各邦政治上相互不信任,这样的情况在北部商业邦和南部农业邦之间尤为突出。由于《巴黎和约》签订后,美国获得了大量的新土地,如何处置西部土地问题又引起了东部邦与西部邦之间的矛盾和敌视。同时,切萨皮克湾及其相关河道的航行权问题、口岸贸易问题等等,都成为引起相关邦之间相互仇视和冲突的不利因素。其次,战争对经济的破坏、币制不统一造成的通货膨胀以及各邦之间持续的经济摩擦,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经济凋敝,债务危机,阶级分化,导致了阶级对立与仇视情绪严重,各邦都普遍存在人民暴乱的危险。利益纠纷、政派仇视逐渐成为危及“联盟”的严重问题。再者,因为邦联缺乏统一的主权,在与英国、西班牙等国进行贸易时不能协调关税,各邦的对外贸易处处受到限制,难以与欧洲列强达成有效的贸易协定,而邦联却无贸易管制权对此进行管理,致使各邦商人对邦联的存在失去了信心。[13](p1~7)因此,《邦联条例》生效不久,扩大邦联国会权力,赋予其充分的管制商贸权力以协调邦联各邦商贸问题、赋予其解决邦际经济纠纷权力的呼声日益高涨。修订《邦联条例》已成为当务之急。
整个邦联时期,究竟如何改革邦联体制、维护已经建立起来的13个邦的联盟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改革派内部有不同的意见,反对改革的政治势力也存在不同的主张。在随后的邦联改革中,以汉密尔顿等人为代表的激进改革者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加强中央集权,赋予邦联政府以至高无上的权力。[14](p137~141)1782年,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纽约邦议会提议修改《邦联条例》,马萨诸塞附议支持,但是其他邦没有响应。一些革命时代的领袖人物,如华盛顿、杰斐逊、约翰·亚当斯、富兰克林·哈里森(Franklin Harrison)、詹姆斯·威尔逊、戴卫·拉姆齐、塞缪尔·彻斯(Samuel Chase)、约翰·杰伊等,也观察到《邦联条例》的缺陷,就如何修改条例而进行着激烈的辩论。[7](vol.1,p238~268)由于1786年的经济危机而引发一系列社会危机,邦联国会每年从各邦获取的财政收入不及邦联所欠债务利息的三分之一,[15](p14)一些邦因债务问题而导致农民暴动,如谢斯起义。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革《邦联条例》,稳定经济秩序显得更为紧迫。6月27日,约翰·杰伊写信给华盛顿说明他对邦联面临的社会危机的忧虑,“反对公众偏见、挑战现有的秩序、收回邦拥有的不适当的权利,的确不是一件使人兴奋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的行动可能导致些许危机或革命活动,甚至其他我们难以预期的结果”;但如果不采取行动,“我更担心那些本性较好的人,即那些勤劳、循规蹈矩、安于现状、知足常乐的人,也会因此失去对财产的安全感,丧失对统治者的信心、对公众利益的信任以及对正义的期盼,进而把自由的魅力看做是一种虚幻”。[16](vol.3,p63~64)华盛顿在8月1日的回信中赞同杰伊的分析:“就如你看到的一样,对于那些对当前现状不满的、本性较好的人的随时准备革命的情况,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预料、阻止这样的灾难性的偶然事故的发生是明智之举,也是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16](vol.3,p64~65)但是,一些过激的行为(如谢斯起义)引起部分人对民主、自由的恐惧,由此产生了一些过激的改革思想,诸如实行新的暴力专政,建立君主统治等,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已经严重威胁到北美人民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因此,保全联盟实际就是保全革命所获得的独立和自由,保存革命所创建起来的各邦联盟,维护所有北美人民所追求的民族团结。
综观当时一些政治家的信笺和文章,修改《邦联条例》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在改革邦联体制的同时,存在一个如何保全“合众国联盟”(the Union of the United States)的问题。美国学者C.S.托马斯指出:“从革命一直到美国早期的所有问题中,没有比维持殖民地内部联盟以及后来的邦际联盟更为重要的了……围绕联盟问题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长期困扰着联邦主义者。”[17](pⅠⅩ)围绕着如何保全联盟的问题,改革派分化为“反联邦主义者”(Anti-Federalists)和“国家主义者”(Nationalists)。尽管他们主张改革的措施不同,但是都主张一个稳固的“美利坚联盟”。从这个意义上说,《安纳波利斯会议报告》提出的“保全联盟”、“加强联盟共同利益”的思想,团结了不同的改革派别,有效地维护了美利坚民族的团结。另一方面,无论反联邦主义者还是国家主义者,都主张改革现存的邦联体制,建立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因此,安纳波利斯会议代表在确认“邦联面临危机”的前提下,向邦联各邦发出了“加强联盟”的号召,遏止了各邦现存的分裂思想。这样,《安纳波利斯会议报告》就以“保全联盟”的名义团结了不同的爱国力量,也真实反映了各邦人民的共同政治理想。只有如此,政治家们才能在一个“美利坚联盟”的框架下,进行邦联体制改革的制度创新努力。
从某种程度上说,《安纳波利斯会议报告》所发出的“保全联盟利益”的号召,意味着在众多改革邦联体制的方案中“联邦主义”(Federalism)(注:联邦主义,是一种州政府和中央政府分权与共享权利的复合政体,它依赖于三个概念:人民主权、限权政府和双重公民身份。(Stephen L.Schechter,ed.Roots of the Republic:American
Founding Documents Interpreted.Madison:Madison House,1990.pp.267~269.)在安纳波利斯会议报告中,已经明显体现出联邦主义所包含的三重意思:以各州的代表的身份采取措施,加强中央政府;中央政府的权力要加强,但仍然是有限的,并且要符合《宪法》的规定;所有改革、加强联邦措施的权力来源都必经各州人民代表的同意或者授权,同时这里的人民既是州权力的来源,也是这个中央政府的权力之源。)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从美国历史的发展来看,联邦体制就是解决各州之间关系的一种政治体制,它的基本前提是有一个维持各州团结、合作的“全国政府”(General Government),促进全体美利坚联盟的共同事业,维护美利坚人民的共同利益。
二《安纳波利斯会议报告》的意义
在美国革命运动中,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维系13个邦之间联盟的政府,一直是一个困扰革命者的急迫问题,在大陆会议代表中间也存在激烈的争论。1781年依据《邦联条例》建立的邦联政府,是一个各邦之间利益妥协的产物,而且由于《邦联条例》第二条承认“各邦保留自己的主权、自由、独立等一切权利”[18](p740),从而使邦联政府成为权力极其有限的联盟。麦迪逊在《联邦主义者文集》中称之为“一个头脑听从四肢的政治怪物”。因此,自从《邦联条例》制定后,改革的呼声便日益高涨,直到制宪会议制定了《联邦宪法》。
仔细分析制宪会议前的政治辩论,核心是如何加强邦联政府的权利以及如何保护个人财产、协调邦际利益。在邦联体制下,国会没有权力来裁定邦际问题,只能以组织委员会的形式来协调。安纳波利斯会议原本就是解决邦际利益冲突的一次邦代表协调会议。
1785年,未经邦联国会授权,弗吉尼亚和马里兰邦的代表私自就解决两邦间的商业利益纠纷与有关波托马克河(the Potomac River)和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航行权问题签订协议。“无论合法与否,在当时条件下,(这个协议)好像是解决(邦际)问题的有效途径。”[19](p8)它的成功,鼓励了两邦代表准备在第二年举行更大规模的会议。马里兰代表建议,为了解决涉及该地区邦际商业贸易纠纷,召开一个包括特拉华和宾夕法尼亚在内的大范围的协调会议;弗吉尼亚代表提议召开一个包括邦联各邦参加的有关邦际商业贸易政策协调会。这个提议受到许多邦的赞同,各邦很快行动,任命了会议代表。
协调会议原定于1786年9月4日召开。弗吉尼亚代表提出倡议后,先后有9个邦接受邀请,并表示赞同,任命了代表,然而直到9月11日,才共有12名代表到会。会议地点选定在马里兰的安纳波利斯。但举行会议时,仅有弗吉尼亚、纽约、特拉华、新泽西、宾夕法尼亚5个邦的代表出席,另外4个邦也派出了代表,但是他们没有及时出席会议。而且,纽约和宾西法尼亚代表团都只有一名代表参加,不足法定人数。
尽管出席会议的代表不足法定人数,会议还是在9月11日开幕,并选举特拉华邦代表约翰·迪金森为主席,[14](p321)同时会议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起草向与会各邦递交的会议报告。纽约邦代表汉密尔顿是否被推选或者自愿成为会议报告的起草者,现有材料尚难以确定,但他确实在会议上起了重要作用,并成为会议报告的最后起草人。(注:“汉密尔顿是否是会议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汉密尔顿的传记作者布罗德斯·米歇尔认为证据不足(Broadus Mitchell,Alexander Hamilton:A Concise
Biograph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1976.p143),而史学家马克斯·法兰德则认为汉密尔顿是被任命为会议报告的起草者(Max Farrand,The Faming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13,p.9),还有的学者认为汉密尔顿不是会议报告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却担任了会议报告的起草人(William Winslow Crosskey and William Jeffrey,Jr..Politics and the
Constitution in the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322)。)在会议报告初稿中,汉密尔顿一开始就明确指出,除了有代表出席的各邦,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罗得岛和北卡罗来纳也已经任命了代表,但是它们的代表从来没有出席会议。对于邦联政府在管制邦际贸易问题上的无能为力的状况,汉密尔顿极为不满,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试图进一步阐述现存邦联体制的明显缺点。从当时部分代表缺席、代议制有缺陷的实际状况来看,报告如此起草显然是“不明智的”。[14](p323)果然,弗吉尼亚邦长埃德蒙·伦道夫看后表示不满,认为措辞太强烈,容易导致邦联内部的分裂,破坏美利坚的联盟事业。为此,两个强硬人物互不相让,从而使会议报告的拟订陷入僵局。这时,麦迪逊把汉密尔顿拉到一边,悄悄告之伦道夫在弗吉尼亚邦的威望,并建议汉密尔顿先屈从于这位权势邦长,否则会议报告就会失去弗吉尼亚的支持,进而会影响到其他邦对报告的支持。随即,汉密尔顿修改了报告的内容,这样“报告的请求变得温和,以适合那些人的胃口”[20](p143)。
9月14日,汉密尔顿向邦联国会、各邦议会提交会议报告。报告的结论是:“基于上述(对邦联形势的)认识,会议代表们怀着无尚的敬意,请允许他们一致向国会提出如下建议:如果与会代表诸邦达成共识,竭尽全力与其他未指派代表的各邦合作,在明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一聚会费城,考虑合众国面临的形势,做出他们认为必然的进一步规定,赋予邦联政府足以应对联盟紧急事件的必要宪法权力,这是当前增进联盟利益的必要要求。同时,与会代表请求将为这个目的而拟订的报告递交国会,经他们同意后,再经过各邦议会批准,这也同样有效地增进联盟的利益。”[16](p70)报告中最明显的请求是建议国会于1787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在费城召开一个全邦联的会议。这个报告的重要价值在于,它不仅仅是提出建议,而是用很大的篇幅分析建议的合理性,进而论证建议的合法性。
首先,报告着眼于整个邦联的危机和解决办法,而非单纯的会议总结。汉密尔顿是一个律师、纽约银行的创始人、杰出的国会议员,其政治经验使他始终关注各邦具体的经济利益、个人经济权利问题,乃至对《邦联条例》所规定的邦联政府有限的权力表示极大不满。早在《邦联条例》未生效前,汉密尔顿在给朋友的信中就指出,国会应该享有“完全主权”。[14](p137)邦联政府建立后,他又时常抱怨“邦联的致命弱点是国会在商贸、外交和国内问题上毫无权力”。1786年春,纽约邦议会不准备加入第三届邦联国会,汉密尔顿起草了纽约市民请愿书,呼吁立法者“不要对广大邦联民众期盼统一措施的热情充耳不闻,对这些统一措施的无限拖延就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这将给那些审慎的绅士的信心和责任感造成伤害”[20](p140~141)。但是,他的“赋予邦联国会完全主权”的改革计划还是被国会拒绝。尽管如此,汉密尔顿并没有放弃改革的希望。安纳波利斯会议是他实施改革的又一次机会。会议报告由协调邦际商业贸易的会议目的立论,阐明解决这一问题的各邦建议,结果与会各邦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同时,如果不采取措施加强邦联管制邦际商贸的权力,各邦之间的利益冲突便难以协调,因此,各邦联盟实际面临分裂的危险,邦联的利益便难以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召开全邦联会议,思考邦联的形势,提出建立更好的中央政府以应对危机的建议,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由此观之,借一个不成功的商贸协调会,汉密尔顿审慎地阐明邦联危机和改革的迫切性,进而让国会议员、各邦议会、邦政府的官员同意召开费城会议。正因邦联存在严重危机以及改革的持续受挫,汉密尔顿对邦联体制的重重危机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以至于他后来在《联邦主义者文集》第15、16、21、22篇中,深刻指出:目前的邦联政府不足以维系各邦的联盟;现行国家制度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摆脱迫在眉睫的无政府状态。[21](p73~74)随后,他又从邦联的立法原则,邦权的强大,邦联法律缺乏支持的基础,各邦政府不能相互保证、信任,邦联难以管理商业和各邦平等投票权等角度,分析邦联的危机所在,论证推行宪法改革的必要性。
比较《安纳波利斯会议报告》与《联邦主义者文集》中对邦联体制弊病的分析论述,可以发现汉密尔顿思想发展的连续性,这也说明汉密尔顿的联邦主义改革思想在这次会议期间已经初步形成。从安纳波利斯会议的动机来看,这次会议无疑是失败的。但是,从邦联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分析,会议报告却为汉密尔顿等人在安纳波利斯会议上没有能够实现改革抱负寻找了又一次机会,即1787年的费城会议。
其次,汉密尔顿对改革邦联体制程序进行了预先设计。应对邦联危机,必须改变邦联体制,这就必须首先修订现有的《邦联条例》,这几乎是人们的共识。但是,通过修改《邦联条例》进而改革邦联体制的困难在于,修改《邦联条例》需要13个邦议会的一致同意。因此,在报告的结论部分,汉密尔顿不仅向邦联国会和各邦议会明确传递出了改革《邦联条例》的请求,而且为下一步的改革勾勒出了一个合法的程序:召开一个全邦联各邦代表参加的会议,讨论邦联的危机形势,采取赋予联邦政府(the Federal
Government)足以应对联盟危机的宪法权力;赋予邦联的权力是否合法,还需要经过邦联国会代表的同意,再通过各邦立法机构为此召开的代表大会的批准、确认。这样的改革程序,既符合现行的《邦联条例》的规定,也尊重各邦的意愿。很明显,享有最终决定权的是各邦代表大会,而不是现在的各邦议会和邦联国会。在这里,汉密尔顿把修改《邦联条例》的权力主体由原来的“邦联国会”和各邦议会悄然替换为“各邦议会为此召开的人民大会”,这既是为变更国家政体寻求新的合法性,同时也是《独立宣言》所坚持的“人民主权”的革命原则的体现和应用,有利于取得人民的支持。这样,修订《邦联条例》便绕开了“13个邦议会的一致同意”这个巨大障碍,转向了“各邦人民的一致同意”。因为,根据当时人们信奉的“人民主权”理论,“各邦人民的一致同意”是邦政府和邦联政府的惟一基础,这一“人民主权”理论也是建立“联邦主义”国家的基本原则。
不过,报告中提及的“联邦政府(the Federal Government)”实际是个模糊的概念,既可以指现存的“邦联政府”(the Government of Confederacy),也可指通过各邦代表大会采取措施而赋予应对邦联危机宪法权利的新“联邦政府”。结合汉密尔顿的个人政治追求,以及以前提及的建立中央集权政府的改革建议,报告中的联邦政府是一个权力很大的新“联邦政府”。这也就为后来制宪会议上加强邦联政府权利的一系列改革奠定了合法权力基础。考察制宪会议后《联邦宪法》的批准过程,《安纳波利斯会议报告》所设计的“程序”被各邦议会所执行,各邦召开的人民大会成为决定是否批准宪法的最高权力机构。
从邦联弱小、邦权强大的实际情况来看,在安纳波利斯会议不符合法定代表人数的前提下,会议报告的任何改革建议都不具有实施的合法性,也不可能取得各邦议会的支持。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汉密尔顿还是机智地把邦联的危机、改革的急迫性恰当地写进报告。当然,建议的提出也是比较委婉的,是否应该改革、建立怎样的应对危机的体制,应该通过各邦代表参加的费城会议来协商。这正是邦联改革者谋略的体现,也是会议报告文本的历史价值所在。
三“宪政主义”的胜利
“宪政主义”是指强制性权力受到约束这种观念。[22](p5)它既是一种对政体的设计,也是一种法制程序的规范。从《独立宣言》到《联邦宪法》,乃至美国立宪政府的确立,实际上体现着北美人民对美国革命过程中提出的“限权政府”思想的实验和探索。
《独立宣言》提出了“限权政府”等一系列观念。[23](p25)但是,限权政府究竟是怎样的模式,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并没有确切的答案。依据《邦联条例》建立起来的邦联国会具有限权政府的性质,可是现实证明这样的体制难以有效应对13个邦之间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因为如此,从《邦联条例》在大陆会议上的辩论到生效过程中,“新国家主义”(New Nationalism)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思潮,其代表人物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以有效管理邦际争端,把邦联政府的危机看做实施政治改革、促进国家发展的契机。[3](p458~459)在国家主义者提出的改革邦联国会的一系列方案中,限权政府的思想受到一些激进改革思想的挑战。汉密尔顿、鲁弗斯·金等人主张赋予“完全的管制商业贸易的权力”,甚至其他一些权力。这种思想实质就是要无限扩大邦联国会的权力,这样的改革方案无疑有悖于北美人民革命所争取的“民主”与“自由”的初衷。因此,在《联邦宪法》生效前的几年中,如何解决扩大邦联国会的权力与保证各邦主权的独立与自由,不仅是一个困难的程序问题,也是一个不同政治力量不断辩论的、棘手的理论难题。
大多数邦联国会代表也认识到邦联体制的某些弱点,并主持进行了一些改革。仅因“邦联政府管制邦联贸易问题”就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并成立了几个专门委员会,如“门罗委员会”、“大委员会”等,(注:作为弗吉尼亚议会代表,詹姆期·门罗极力主张赋予邦联管理全国商贸的权力。1784年门罗被国会任命为负责这项改革的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也被称为“门罗委员会”。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委员会向国会提交了改革报告,但未被批准。随后,又成立了“大委员会”,进一步协调各邦之间的纠纷,最终也没有取得成效。)着手对邦联政府缺少经济权力的改革。但是,由于各邦惧怕邦联政府权力的扩大而损害邦的权利,因此这些自上而下的改革几乎全部以失败而终。围绕如何改革邦联体制问题,一批国家主义者开始研究邦联体制的弱点,并在不损害各邦自由、独立权利的前提下赋予邦联政府以中央政府的权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以麦迪逊为代表的“宪政主义者”(Constitutionalists)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
詹姆斯·麦迪逊在美国制宪史上的作用举足轻重,因在1787年制宪会议上的突出贡献,被尊称为美国的“宪法之父”。但是,他的宪政思想的发展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其中安纳波利斯会议是他宪政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麦迪逊是影响安纳波利斯会议进程与议题的重要人物之一,甚至会议报告的起草也蕴含了他的策略和智慧。
在制宪会议前,作为一名邦联国会议员,麦迪逊曾以“国家主义者”的身份积极从事邦联的具体财政改革而闻名。[24](p13~71)1786年9月,作为弗吉尼亚邦的代表出席安纳波利斯会议时,麦迪逊年仅35岁,却“是邦联国会和弗吉尼亚邦政坛上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25](p43)。他积极参加公众事务,在弗吉尼亚邦担任多种职务。在作为弗吉尼亚邦议会代表出席邦联国会期间,和其他国家主义者一样,他对于邦联政府的经济危机、乃至体制危机早有深刻的洞察,对密西西比河流域商贸问题、外国势力对边界的威胁等一些重大政治问题,都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但因为国会的权限太小不能有效管理各邦而不得不被搁置。
1785年秋,他积极提出扩大邦联管制商贸权力的议案,支持弗吉尼亚邦派代表出席安纳波利斯会议,讨论邦联国会的贸易管制权问题。但是,他对于安纳波利斯会议的结果并不抱太大的期望。1786年初,在给出使法国的杰斐逊的几封信笺中,麦迪逊就谈到各邦对这次会议的冷淡,以及自己的悲观和忧虑。1786年3月18日,麦迪逊在给杰斐逊的信中说:“实际上,现有政治的弊端都可以归结为经济的弊端,就如所有的道德问题都可以追溯到政治问题一样。”“就目前的形势来看,按照提议即将召开的大会(安纳波利斯会议)是一次拯救性的实验,它的成功依靠每个邦的一致同意;但是,如果这种观点正确,我确信这次会议不应该召开,即使那些提议者抱有良好的目的。虽然,我希望每个邦都同意派代表参加会议,代表们都同意会议计划、并报告各邦,各邦也一致同意对它(《邦联条例》)的修改,但是,我仍然相信这样的事情是不现实的。我时常对这样的成功感到绝望。然而,许多事情需要实验,这也是必要的。即使这不是最好的、可能的权宜之计,也是依靠国会所能够进行的最好实验。”[26](vol.1,p415)从这些语言中,麦迪逊对于改革《邦联条例》的复杂心态跃然纸上:在取得各邦一致同意的前提下,改变邦联体制几乎没有一点可能;但是,不依靠国会或者各邦人民,任何改革也不可能成功;邦联国会是实现改革实验所必须依靠的惟一合法机构;同时,不做局部的实验性改革,就难以采取全面医治邦联体制弊病的措施。
把安纳波利斯会议作为改革邦联体制的一次实验,即使已经预测到会议的失败,麦迪逊还是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实现自己某些改革的抱负。从麦迪逊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在制宪会议以前他一直是一个联邦改良主义者,幻想通过《邦联条例》的修订扩大邦联国会的权力而维护美利坚联盟的利益。在安纳波利斯会议前,他就集中研究历史上的邦联政体的特点,以期借鉴历史经验来完善邦联体制。为此,他通过在法国的杰斐逊收集到大量启蒙政治思想家的著作。通过阅读研究利西亚联邦同盟(Lycian Confederacy)、雅典近海同盟(Amphictyonic Confederacy)和荷兰同盟(Belgic Confederacy)等历史上的邦联政体,写成了读书札记——《关于古代和现代的邦联政府》,得出许多倾向性的结论:没有一个具有总督地位的联盟中心是难以把如此众多的独立的利益团体维系在一起的;(注:在这段话中,麦迪逊特指荷兰同盟(Belgic Confederacy)所设立的邦联总督(States General)享有的保证同盟权威的一切权力。在荷兰同盟中,邦联总督对各省(
Provinces)议会的权力有所限制,但是各省议会也享有一定的权力以牵制邦联总督的特权。如邦联总督制定了统一税率,却由于各省议会的抵制而没有实行。)对奥地利议会的憎恨而使人民避免了由于他们宪法的缺陷而造成的侵害;(各独立省)采取一致行动的艰难在许多方面损害了同盟的根基;通过联盟的许多条款来看,邦联都制定了由统一长官征收的统一税率,遗憾的是这一增益联盟幸福的措施从来没有实施。[27](p47~56)从麦迪逊的研究结论来看,安纳波利斯会议前他始终对邦联政体存有很大的幻想,他的改革希望就是通过修订《邦联条例》而维持邦联的团结,同时也担心任何修订《邦联条例》的措施都会因为各邦的分歧与利益纷争而不能够一致通过。1786年6月底,在他每年的北方旅行途中,得知费城、纽约的士绅们希望安纳波利斯会议能够成为“修改邦联体制的一个全权代表会议”,麦迪逊虽内心无比激动,但他仍然担心即使再温和的改革日程也难以得到民众和邦议会的同意。
1786年9月4日,麦迪逊心事重重地到达安纳波利斯,比实际开会的时间提前一个星期。历史学家G.威尔斯评价说:“他(麦迪逊)知道如何把工作做到结果的前面,但是安纳波利斯会议完全超出了他的组织才能。”[28](p3)的确,到9月11日会议开幕时只有5个邦12名代表的现实,就表明安纳波利斯会议不可能制定什么改革措施。这样的现实使麦迪逊彻底从修改《邦联条例》的憧憬中醒悟,认识到要加强邦联政府的权力,必须制定一部新的邦联宪法。历史地分析,可以说安纳波利斯会议是麦迪逊政治思想发展的转折点。
从9月4日起,麦迪逊就为会议的具体事务做准备,想借会议的商贸改革议题而增加对邦联条例修改的内容。但是,事情的发展却并不像他所预期的那样顺利。首先,代表们并没有如期而至,使他认识到邦联体制的松散,动摇了他对邦联体制的信念;其次,人们普遍心存改革热情与邦联现状难以进行改革的矛盾,使麦迪逊坚定了必须在一个新的宪法框架下建立集权的中央政府的信念。这样的中央政府必须享有邦联国会所没有的权威来限制各邦的独立和散漫。
安纳波利斯会议标志着麦迪逊邦联改革实验的失败,促使麦迪逊开始新的政府体制的探索。历史学家戈登·伍德指出,弗农山庄(Mount Vernon)、安纳波利斯这两次商贸会议都被麦迪逊用来作为变革中央政府的动力。[29](p473)基于对现存邦联体制缺点的认识和强烈的改革抱负,麦迪逊在安纳波利斯会议后,开始了对邦联政府与联邦政府体制的深入研究,积极地为安纳波利斯会议取得的惟一显著成果——1787年的费城会议做准备。安纳波利斯会议后,他深入研究了古代出现的邦联政体的利弊得失和美利坚所急需的加强中央政府权力的联邦体制。这些深思熟虑的理性思考,成为他政治思想的核心。依据自己的政治实践,结合对古代邦联政体的研究,1787年3月麦迪逊撰写了《合众国政治体制的弊病》的草稿,把邦联体制的缺点归结为11个方面:各邦不能履行宪法义务;邦权侵蚀邦联的权威;不遵守国家法律和条约;各邦之间相互侵权;在共同需求的利益面前缺少一致行动;无法消除各邦宪法和法律的相互抵触;邦联政府缺少必要的法律制裁和强制措施;缺少人民修改《邦联条例》的权力;许多邦法律的繁杂、多样性;各邦法律的多变性;各邦法律的不公正性。同时,他思考改革现状的一些措施:当前所急需的是改变政府权力主体,在不同的利益群体和政派之间建立有效的机构,阻止社会上一部分人侵害另一部分人的权利;同时对这个机构进行有效的约束,以防止他们谋取私利、损害社会整体利益。对于共和体制改良的另一个辅助措施是选举程序的改变,从社会上选出那些具有最完美品性的绅士,让他们成为民众的代表,这将成为实现改革目标的恰当手段。[27](p57~65)在这篇文章中,麦迪逊的思想明显地转变为宪政主义思想:权力分配的不平衡导致了邦联的松散,通过改变选举方式,使人民中的精英代表成为权力的主体;通过改革法律体制以加强中央权威并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进而控制因邦权强大而导致的邦联弊端。随后,宪政思想成为麦迪逊起草“弗吉尼亚方案”的理论依据,也成为他在费城会议上为立宪辩护的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以及他在《联邦主义者文集》中为新宪法辩护的重要内容。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麦迪逊宪政理论的核心——《联邦主义者文集》第10篇,被认为是写于安纳波利斯会议后与费城会议前的这段时间。[25](p44)文集中第18、19、20篇的内容是集中论述邦联体制弊端的,麦迪逊所列举的几个欧洲历史上的邦联政体的弊病,也都是《关于古代和现代的邦联政府》中早已提及的内容和结论。从麦迪逊的这些政论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一种不同于邦联体制的全新的宪政模式:党争精神是危害公共管理、社会稳定的重要敌人,政府必须对此加以控制;党争存在的根源是自由,取消党争存在的根源无异于舍本逐末,因此,只能加强政府控制,实质是要扩大政府的权力。麦迪逊认为,党争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利益纷争,即“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现代立法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各种各样、互不相容的利益集团,并把党派精神和党争带入政府的必要的和日常的活动中去”;[29](p46~47)共和政体能够比民主政体管辖更多的公民和更广泛的领土,能够更有效地控制党争;在联邦的范围和适当结构里,共和政体能够医治共和政府最易发生的弊病;人在本性上充满贪婪、褊狭、仇恨和战斗,因此,对人性中的“恶”必须加以控制,“野心必须要用野心来对抗”;政府本身就是人性的耻辱,政府对防御的规定必须与遭遇攻击的威胁相对称,“假如人都是天使,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依靠人民对政府控制时,必须有有效的、辅助性的预防措施”。[29](p290)
此外,安纳波利斯会议后,麦迪逊成为一个积极的宪政主义宣传者和鼓动家。在麦迪逊看来,安纳波利斯会议的惟一结果——建议召开费城会议,就是一个实施政治抱负的机会。他开始和当时有影响的政治人物华盛顿和杰弗逊紧密联系,希望借助他们的威望,迫使国会和各邦议会批准召开一个全邦联的会议,同时着手为即将到来的费城会议做准备。1786年11月8日,麦迪逊在给华盛顿的信中写道:“(最近的集会上)安纳波利斯会议代表们一致同意对邦联体制进行广泛修订的建议,得到了国会代表的认可。为了这个目的,一个体现这个联邦精神的议案正在被审议。”“这个崇高的、肇始于每个邦意愿的目标,是非常明智的。”[30](p50~51)然后,麦迪逊就劝说华盛顿要以自由事业为重,作为弗吉尼亚邦的首席代表出席费城会议。在这个时期的通信中,麦迪逊多次对华盛顿提到“我们的事业”需要像华盛顿这样的领袖人物的支持,如果不能成功,“我们的邦联”就要陷入混乱之中。华盛顿也认识到“危险阴云像是要把整个邦联吞噬”[3](p52),从而决心打破1783年对公众承诺的不参加公共政务的诺言,为了民主、自由的事业出席费城会议。麦迪逊在劝说华盛顿的时候,就认识到费城会议上的斗争必定非常激烈,所以要争取像华盛顿这样的德高望重的领袖人物的支持。这也说明,在他眼里,安纳波利斯会议的决定,不再单纯是一次修订《邦联条例》的普通会议,而是意味着某些能够体现“联邦精神”的重大变革即将来临。
由此可见,安纳波利斯会议后,麦迪逊思想产生了巨大的转变。他不仅从政治哲学中找到摆脱邦联体制危机的理论基础,成为积极的立宪主义者,而且从组织上开始为费城会议做行动准备,进而引导费城会议开成一个具有全新内容的制宪会议。不仅如此,在麦迪逊的宣传鼓动下,一批邦联改革派,如杰伊、华盛顿、鲁弗斯·金(Rufus King)等,走上了立宪主义之路。另一方面,《安纳波利斯会议报告》所体现的修改《邦联条例》的立宪主义程序,无疑为实现联邦权力主体变更,即以邦为主体的邦联政府向以人民为主体的联邦政府过渡,提供了合法的渠道。这意味着宪政主义在政府权力过渡过程中成为指导思想,并依据邦联国会的合法性使宪政程序加以确认。
四结语
1786年在安纳波利斯举行的会议虽然不是一次制宪会议,[6](p509)但是,假如把这次会议置于美国制宪史的过程中来考察,它应该是美国由邦联体制改革走向重新制宪之路的重要转折点。
首先,安纳波利斯会议为制宪做了舆论宣传。安纳波利斯会议从邦联的商业问题入手,揭示了邦联所面临的危机,达成了要求召开对现存的邦联体制进行修正的费城会议的共识。虽然发出制宪号召的仅仅是5个邦的代表,但是通过邦联国会、各邦议会这个合法的权力中枢,向全体邦联人民阐明了为改革《邦联条例》而制宪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787年2月21日,《安纳波利斯会议报告》得到邦联国会的批准。这样,召开“制宪会议”这个原本不具备合法性的会议建议,便成为不争的法律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安纳波利斯会议不仅为制宪会议做了舆论准备,而且使制宪走向了合法的程序道路。
第二,安纳波利斯会议为联邦主义改革造就了政治理论家和“宪政主义”实践者。在解决邦联政府缺少权威这个问题上,存在众多的方案和改良措施,在强调加强邦联国会权力的同时,联邦主义者不仅从理论上找到了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理论依据,而且在实践改革的过程中,始终遵循权力过渡的合法性程序。这是“宪政主义”思想在邦联改革进程中的胜利,也是邦联改革者统一认识,走上联合,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共同指导思想。
要而言之,从历史上美国立宪过程中核心人物思想转变的角度、从邦联体制向联邦体制过渡的进程来分析,安纳波利斯会议不仅是费城制宪会议的发起会议,而且为费城会议定下了主题,从而引导邦联体制改革的不同政治派别都遵循着“符合宪法”的程序进行宪政改革的理论探索。
在写作本文过程中,作者多次得到业师李剑鸣教授的悉心指导,烟台师范学院高春常教授通读全文并提出了宝贵建议。特此致谢。
收稿日期:2003-05-12
标签:大陆会议论文; 美国革命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英属北美殖民地论文; 英国殖民地论文; 殖民地历史论文; 政治论文; 宪法修改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