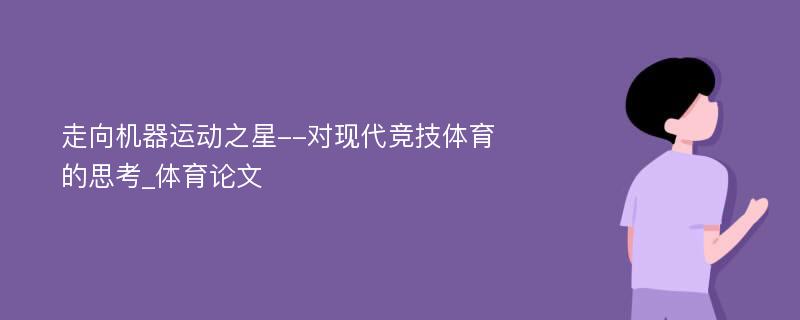
变成机器的体育明星——关于现代竞技运动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育明星论文,机器论文,竞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古希腊人馈赠给人类的庞大遗产中,运动伤害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最具反讽意味的是,为和平而复活的奥运会在历史上却多次成为制裁机构。
教练把成功置于运动员的健康之上。
塞莱斯在赛场遇刺,惊吓过度而隐居不出,她的赞助商竟考虑将她拖上法庭。
运动员“黄金时期”蕴藏在肌肉里的潜能被最有效地榨取。
拳击,穷人的运动,摆脱穷困的阶梯。
[上海临潼宾馆特约刊登]
总经理戴雪江向广大读者致意
现在的运动员,个个浑身伤病,“体育”还能叫“体育”?屡有疑者。
这问题很幼稚,但它本身却是在一种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对另一种价值的怀疑。所以仍不失为一个意义的问题。
近代中国人曾被蔑为“东亚病夫”,那时“体育”引进中国,打上“强种—强国”的印记乃是必然。国人最初想到要锻炼身体显然不是以健康为最终目标的,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而能否达到目的还得划问号。
鲁迅当年其弃医从文的行动即可视为对此提出的有力质疑。他笔下的一群精神麻木、体格健壮的看客围观刽子手杀人,有的竟能吃下蘸着人血的馒头。强壮的躯壳与神智的腐朽,可谓震聋发聩。但“体育救国”曾如此深入人心,难免成为一种偏执,所以“体育”的概念便也僵化,凡在其大名下的事物,都必须有益于人的肉体健康的想法便是。
这想法错就错在把手段和目的混为一谈。从宏观的角度审查,人类从来不曾把强体能当作终极目的。否则以此想法衡量,那么今天的“体育”就是个不伦不类的实足怪物。因为今天不仅是人,许多动物:猪、狗、猫、蟋蟀、青蛙、癞哈蟆比赛都堂而皇之登上许多冠以“体育”之名的专业报刊。
显然,人们不会把“动物的体育”与“人的体育”混淆起来;也非不知“大众体育”与竞技运动的区别以及这种争论主要存在于竞技运动领域。
所以这个疑问要使其变成一个有价值的问题,便应改变提问的方式,即不是用“体育”的概念(这本身就是含糊不清的概念)去套某某事物是否相称,而是就事实本身是什么提出问题。
既然已知人体不过是人类无穷意欲的载体,健康也不是人的终极目的,所以当一些人牺牲健康,忍受着难以想像的伤痛折磨,就有某种强大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或是一种强大的压力或是一种强烈的愿望,它强大到“非搞垮身体不可”。
小斯巴达——童真的失落
有个著名的传说讲,古希腊斯巴达城邦,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小学生带了只狐狸去学校,上课时他把狐狸藏在怀中。狐狸在他的胸膛上又抓又咬,为了不违反课堂纪律,他一动不动。下课后教师和同学发现他已经死了。从此凡勇敢的孩子都被称为“小斯巴达”。不用怀疑这故事的真实性,重要的并不在于传说本身是否真实,而在于它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全民皆兵”的斯巴达城邦鼓励勇敢坚韧的风尚。至少我们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后世常把严酷训练士兵方式称为“斯巴达方式”。
恩格斯说过,在了解人类成就的许多方面,我们常常不得不回到它的源头,优秀的古希腊人那里去。在古希腊人馈赠给人类的庞大遗产中,不妨说运动伤害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从“小斯巴达”说起,则是要强调,在今天的竞技运动的舞台上少年儿童受到运动伤害困扰已成为突出的现象。
古奥运会与战争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正如所有古老文明的早期竞技运动项目几乎无不直接脱胎于战斗技能一样,竞技场上的技能事实上就是战斗的技能,差别仅在于竞技比赛被约定的规则和裁判所限,从而使其形成“点到为止”的特色。
话虽如此,许多史料表明,在古希腊奥林匹克竞技中充斥着的伤亡流血,远比今天的运动场可怕得多。其蛮野程度若用个形象的比喻,就是“斗殴”。有个著名的故事说,某届古奥运会上,一摔角力者被对手死死扼住脖子,他本想认输,但被场外的教练制止。于是他奋力掰住对手的脚趾,最终竟迫使对手认输,而他自己也拼尽最后一口气窒息而亡。
再以古希腊的一项运动混斗——“帕马契亚”(Pammachia)为例。公元前648年第32届奥运会上即列为正式竞赛项目。第83届奥运会时,由该届冠军劳卡洛姆制定出较全面的比赛规则。混斗允许身体任何部位作进攻武器,直至对手丧失抵抗能力或认输为止。揪耳、卡脖子、牙咬,无所顾忌。诗人品达说:“混斗是所有比赛中最危险的项目。受伤致残、流血丧命,简直是家常便饭。”
为规则所限的斗殴虽然不等于战争,但古希腊每隔四年“神圣休战”一次,其间进行的奥运会有明显的“竞技是战争的继续”之色彩。形象地说,前者是“决胜于战场”,而后者则是“决胜于竞技场”。决胜于竞技场自然总比决胜于战场“文明”些。这正是许多西方学者认为“竞技运动”不过是“礼仪化了的战争”的原因。
类似情形在中国也有,不过比起古希腊,中国古人常常更“文明”些。古代兵法云:“攻城为下,攻心为上”。若能“舞台决胜”时,中国人就会觉得连竞技比赛都纯属多余。周武王以大型“干戚舞”震慑蛮夷,使其“口服心服”就是个美妙的例证。炫耀武力的“大型团体操”在中国历代都不乏其例。
这种差别是不同社会中的不同战争形态决定的。在古希腊城邦间的战争中,个人的战斗技能具有极高的价值,因此古希腊“舞台”上都是些单打独斗的好汉,与之相应的宗教观念是古希腊人相信奥林匹克的优胜者必有神佑,所以古希腊出现用拆除城墙的方式欢迎“决胜于舞台”优胜手凯旋故里的事情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过,随着人对自身体能成因认识的加深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浪漫的想像被削弱,祈祷神佑的宗教仪式必然向追求更现实的“强国、强种”手段转化,久而久之“英雄”便不再是从战争中逐渐自然形成,可遇不可求的了。
在古希腊历史上,出现过一个奇妙的现象:战争和竞技能力训练都曾是古希腊贵族垄断的权力,竞技能力的训练不但是贵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运动场是考察判断一个人的出身高贵程度场所。所以在古希腊历史上,许多哲学家、诗人、剧作家都同时又是运动家。难怪有人竟会感叹:希腊的奴隶真是“幸福”,因为他们无权参加战争。
但随着某种历史的必然,古希腊贵族在精神和肉体上双重堕落了,“决胜于运动场”的情形便发生了重大变化。贵族不但从肉搏的战争后撤,也从运动场上逐步后撤,“强种”概念的外延开始扩大到自由民甚至是奴隶。于是在奥运会赛场上就出现了奴隶驾车比赛,马车主人领奖的情形。这时的“强国”的手段“强种”中的“种”便成为可以靠一种强制性的教育体系大量培养出来的预期产品。
“小斯巴达”其实更像古希腊文明走向衰落的证明——人,此时不再有突出的个性,而更像是被贴上标签的社会生物类型。
儿童被调教到至死不吭一声,这和古希腊“英雄时代”有血有肉的众神和英雄喜笑怒骂溢于言表,受伤时也会嚎啕大哭,不以为耻,从不掩饰自己的情感的情形已有本质的不同。
马克思曾说,古希腊社会是人类最正常的儿童时代。这个说法必然不包括“小斯巴达”。因为当儿童甚至能如此有意识地控制(压抑)自己的痛苦反应,它证明的只能是社会对人的控制力量已经大到“类的生存”必须靠牺牲个人的正常情感表达的地步。
显然,空洞的理想本身既不能把所有儿童培养成某种类型的人,许多“小斯巴达”的出现必然是普遍性的社会风尚和带有强制性的教育结果,这包括对儿童肉体的和精神上被风尚所蔑视、抛弃的恐惧。而社会对勇敢精神的称赞则是对这种牺牲的一种补偿。
“小斯巴达”虽然不是死于竞技场,但对了解今天运动场上许多人何以能忍受伤折磨,尤其是对于了解今天的运动场上“小斯巴达”为什么也越来越多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对话还是对抗
顾拜旦在“战争—斗殴—战争……”这个循环的逻辑过程中截取“决胜于运动场(舞台)”的片断,认定它具有“和平功能”,其浪漫性质一目了然。不过这并不妨碍人们接受这个理论,并实践,至于效果则另当别论。
古往今来竞技运动的一大突出特色就在于,竞技运动重要的并不在于它是什么,而在于我们愿意相信它是什么,更准确地说,是形势使人们更容易对它的功能产生哪种倾向性认识。
很多人把“体育运动”称作“世界语”,意思是不论国家和民族,人们很容易借助这特殊的“语言”进行对话。至于对话的内容,可以是和平也可以是“对抗”。
最有反讽意味的是,为和平而复活的奥运会在历史上却多次成为制裁机构,如二次大战后,奥运会连续两届把轴心国运动员排斥在外。假设奥运会这个舞台真能使世界各国青年相互熟悉、消除隔阂,那么排斥轴心国运动员,岂不是正好放弃了奥运会的最重要的功能不用,堵塞这些国家的年轻人走向和平之路?最近的例子则有南斯拉夫运动员被排斥在世界体坛之外,这无疑是个悖论。
在热兵器时代,按理讲更难想像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是古战场的延伸,可事实上,一个柏林奥运会就足以说明,比赛的胜负本不必有现实意义,然而外部条件一旦成熟,它就可以作为某种重大意义的象征,并且显得极具实在性。
50年代至80年代末,美苏两大体育强国的对抗也是如此,它充满了制度和国力较量的延伸的象征意义。在这种较量中,后者有着更严密的组织性、计划性。这种组织和计划性之一就体现在对少年选手的早期培养上。
80年代初至中期,中苏男子体操的激烈竞争一度呈白热化。传媒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譬喻来形容这种态势——“强硬的男子汉对话”。了解这段历史则不难从“对话”前置“硬汉”后激动人心的意味。事实上,参与这种“对话”的也不再限于小男子汉。
竞技运动自身的特性,决定了想像与现实之间不时会出现巨大的鸿沟。顾拜旦希望来“对话”的是世界的青年,而如今青年被越来越多孩子所取代。
1986年12月14日,英国业余体操协会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广告的内容是为很有发展前途的女子体操选手、12岁的埃玛·韦贝尔寻找6千英镑的训练住宿赞助费。三个月时间已经过去,没有哪个人或哪家公司对此作出反应。
大英帝国连6千英镑都拿不出来或不愿意拿吗?
两周后,苏联女子体操队访英,英国体育评论家罗布·休斯在同一家报纸上借机发表评论说:原因在于“体操会损害妇女健康!”——这个结论代表了英国体育界和舆论界的基本看法。
英国体育的最高机构——英国体育理事会,对苏联、东欧国家和美国采用的那种无情的训练年轻女子体操运动员的做法一直深感不安。
罗布·休斯说:“我们在1972年奥运会上,从梳着小辫子的图里舍娃身上最早看到了这种转变。最近,又从奥梅里扬奇克身上得到证实,大胆的翻腾完全挤掉了女性美。人们一贯说的体操运动的本质在于身体的音乐美,今天变成了什么?那些体操运动员完全没了成年女性美,她们在身体上成熟了,而情感十分幼稚。奥梅里扬奇克除了体操一无所知。”
美国儿科专家赖尔·米切利说:“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现象,为世界冠军这个目的而培养孩子。”他所在的波士顿医院一年治疗的病人中,许多是竞技体育的受害者。捷、美、日、瑞典等国的研究人员认为,少女体操选手患脊骨受伤的病率是其他孩子的5倍。
1987年5月3日,英国《邮报》载文说,专家警告少年运动员要冒生长发育受到损伤的风险。最普遍的是骨骼受伤和变形,因为过于发达的肌肉会损伤韧带和妨碍骨骼的生长。
让许多这样的少年儿童担负着“祖国和民族的期望”,换句大白话就是“你看我们的孩子都这么了不起……”;或让他们肩负着“世界和平”的重任,其荒诞性也一目了然。
更有惊人的说法讲,当年苏联、罗马尼亚女子体操水平之所以高,是因为让小女孩子服用不长个的药物。有人解释,“这种评论虽然不是根据事实,却是有见识的猜想。”
罗德妮娜这位三获奥运会双人滑冠军的苏联运动员则现身说法:“优秀运动员过去是精神的楷模,今天他们却成了没有感情的、机械的士兵。”而“一味追求致使体育明星的年龄越来越小。”教练把成功置于运动员的健康之上,“把体育变成了艰难而单调的劳动,强迫那些仍是孩子的运动员参加各种比赛,承受严重的精神折磨和身体伤病。”
这种情形出现显然并不取决于教练,是由更深的社会原因和竞技运动自身的逻辑决定的。苏联体育大厦的崩塌与原来相吻合的意识形态解体密切相关,暴露了这种象征时过则境迁的虚妄性。但少年儿童占领竞技舞台的事实并未因冷战结束而减少,则是由竞技运动自身的特性决定的。
作为“身体语言”,竞技运动在表意上不可能具有唯一性。换言之,就是这种语言具有极大的含糊性,因此我们便看到了一个奇特现象,竞技运动并不就是战争的延伸或意识形态的附庸。然而,它确实又随时可以被臆想为战争的延伸或成为表现任何意识意念的工具。
这样一来,作为可以“艺术地表现”任何一种观念或意念的载体——运动员本人就难免成为一种表意的工具。无运运动员本人怎样想,他们都逃不脱其所处时代的普遍的附会性解释的包围。或者说他们索性没有什么想法,环境让他们怎样思想他们就怎样思想。他们通常因从娃娃起便被纳入强制性的训练生活轨道,几乎丧失了自由表达情感的机会和能力。等到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情感或产生表达它的愿望时,往往也到了被淘汰出场的年龄。
有的运动员想激流勇退而不得,前南斯拉夫网球选手塞莱斯在赛场遇刺,惊吓过度而隐居不出。她的赞助商竟考虑是否要把她拖上法庭,迫使她穿着赞助商产品的广告服装上场继续履行他们之间的合同……今天的少年儿童一旦被选中送上这高速行驶的运动战车,等他们想下来时可能为时已晚。自然他们当中有些幸运儿或由机遇,或由超常天赋,使他们尚未伤病缠身便已挣够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或虽已老迈却因论功封官,归宿明朗亦足欣慰悠然。
运动员之间的任何比赛确实都是一种“对话”,但它的普遍性质决不会以某个人意志为转移。
自古及今,竞技比赛作为运动员个人间、团体间、民族间、国家间“对话”的一种方式,其最典型的面目有以下三种:一是政治或军事“对抗”的继续;二是运动会成为一种大家都承认(至少是表面承认)是和平的一种祈祷仪式或象征,而运动员是和平的“使者”;三是今天人们日益熟悉的情形:作为一种表演性职业,竞技运动已成为一个利润巨大的产业。
竞技运动以何种面目出现,取决于大的时代背景。如果说,古希腊奥运会在早期表现出强烈的“战争的继续”这一特征的话,那么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在汉城奥运会以前的冷战时期,则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对抗的继续”的色彩。不过,从现代竞技运动职业化、俱乐部化的趋势和对“对话者”年龄越来越小的发展态势看,也许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全世界的运动员“对话”的内容已经在金钱上取得了“空前的、划时代的统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古老心理已被更强有力的“世界语”——金钱统一起来。
运动伤害成为醒目的世界性问题,前提有二,一是普遍的职业化;二是比赛的胜负不再有强烈的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兴衰存亡”的象征意义,也就是说一个运动员的成败、健康与否,甚至是死是活更多的是与他自己的收入相关,而不是和他的族类的痛痒“息息相关”。旁观者由于处于“超然”的位置,就容易发现许多早已存在的事物原来竟那么“不可思议”,而什么在支撑着职业运动员忍受着难以想像的伤痛折磨只不过是其中之一。
“英才教育”
现代人用了一个非常精当的术语来称呼今天的名运动员——“明星”,这个词把今天的运动员与古希腊早期奥运会上的优胜者(通常叫“英雄”)准确地区别开来。因为前者存在于高度封闭性空间,而后者存在于高度开放的空间之中。
当年日本有人曾评论,德国网球选手贝克尔接受的是“最彻底的英才教育”。他与网坛四杰博格、伦德尔、麦肯罗、维兰德小时候都喜欢足球。然而,“唯有网球的方式”——从儿童时就强制进行高强度科学的训练培养,才能培养出世界第一流的运动员。
职业运动的逻辑是,运动员仅凭兴趣根本不可能出人头地,只有自幼起就置身于强制性的教育制度下,才有可能成为这个行业的“英才”。结果儿童不是在充满趣味的游戏中而是在严酷的训练和比赛中长大,成年人则经常用伟大的牺牲这类陈词滥调描画它的意义。
网球在说明现代竞技运动这个封闭空间的性质方面,确是个非常好的例子。1995年初,排名世界第一的美国网球选手23岁的桑普拉斯呼吁说,应该改革网球体制,现行的网球排名制度迫使选手为维持自己的排名或积分四处奔波。
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早在10年前,就有许多文章这样描述过网球运动。
“在职业网球场上,因为受伤而不能出席大赛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而且人们已经很难分辨有些运动员的肩部,胳膊,大腿是因为伤肿而显得粗壮,还是本来就粗壮。运动创伤是由于无休止地变换不同质地的场地和比赛过多导致的。没有一个选手能经得起这种长期紧张高强度节奏的考验,或者干脆说就是折磨。
“运动员东奔西跑参加不同洲际的比赛,首先会影响和改变心理状态,继而又在生理上发生反应,生理和心理的不适是发生运动创伤的契机。”
法国老网球运动员达尔蒙说:“我打球的年代,运动员很少受伤……那时一年只有5个月的比赛,其余时间用来训练休息,而现在一年四季都在比赛,即使受了伤,只要还能坚持,就要比赛,没有休息,没有治疗。”
排名制度迫使运动员一年四季都在比赛,希望和成功是建立在关节疼痛的基础上的,冠军称号和巨额奖金伴随身体痛苦一起来临。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巨额奖金刺激着运动员无休止地奔跑,所有的人都置伤病不顾奔波着。
现代网球“系列、巡回大奖赛”是商业化的产物,大奖赛首先为组织者创造了巨额的利润,其次在这个封闭的空间中,运动员除了专心比赛外,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可以不必过问,都会有人替他操办,许多人乐于为这些明星跑前跑后,他们可以从运动员的巨额奖金中获得可观的抽头(分红)。
这个高度封闭的空间是为最有效地榨取(“浓缩”)运动员“黄金时期”蕴藏在肌肉里的潜能而制造的。运动员的痛苦与体育协会的官僚、教练、经纪人、医师都不相干,他们只要找到让运动员出成绩的办法,找到让运动员心甘情愿忍受任何痛苦的支点:“合理”的出场费价码、有足够诱惑力的奖金数额就行了。
金钱和名望的诱惑不但能使运动员承受激烈竞争导致的“自然”伤害,还能使他们坦然或被迫接受来自任何方面馈赠的神奇的“大力丸”或“大理丸”。而不论如何,一切后果则要他们自己承担。
大量的文盲明星在比赛之外唯一要稍加用心去办的事,也许就是练好签名,使人们从签名中还觉得他们有点文化。
80年代中期,国际网联医师顾问团曾严厉抨击青少年参加职业网球赛现象。说这对他们肉体和精神的伤害不可估量。
罗德妮娜也说过:“我反对那些15岁就登上顶峰,而后又无声消失了的冠军。现在是限制重大项目的参赛者年龄的时候了。”
国际网球联合会在舆论高涨时,对自己的章程做出过一些修正,规定年轻的职业网球运动员一年只能参加有限次数的比赛。但很难说这种规定有什么用,因为“英才教育”也非想像的产物,它是商业社会一种销路极好的特殊产品。
进入“英才学校”的儿童本人别无选择,不成才即是废物。而以制造“英才”为产品的工厂显然不能无视效率的原则,运动员什么岁数时容易出成绩,就必须让其在这个成绩里出彩。这也就是国际体操界为何不理睬关于禁止比赛危险动作和对参加比赛运动员的年龄虚报问题眼睁眼闭的原因。确实很难想像“老胳膊老腿”做不出惊险奇绝难动作的体操选手能拉来多少观众,而工厂制造没有市场的产品最终只能关门。
还有更极端的例子。今年元月,新华社报道说,1月31日,一名罗马尼亚体操教练由于在训练中将一名11岁的运动员殴打致死,被判处以8年徒刑。这个教练名叫弗洛林·乔治,今年25岁,任教于布加勒斯特狄纳摩俱乐部体校。1993年11月,乔治对小运动员久拉在平衡木项目训练中的表现不满,将她推倒在地,拳打脚踢,久拉因伤势过重不久死在医院。法庭以杀人罪将其处以8年徒刑,还裁定他向受害家属支付5600美元的“道德赔偿金”。
这里显然有种必然性,就像有人谈到雪橇运动时所说的“没有恐惧,才有速度”。雪橇运动员以每小时110公里的速度掠过,看上去是非常可怕的,在一个长1.2米没有制动装置、没有保护的雪橇里,在1千多米的冰道里滑行,极小的失误都可能导致连人带橇倾覆后斜撞在冰墙上的后果。因此它是冒险而不是运动。
这里又出现了“概念”与事实打架的现象。问题的实质并不于它是不是运动,而在于“有了速度,才会有观众。”比雪橇更典型的还有拳击,几十年来拳击一直是受到最广泛攻击的项目,许多人都断言:拳击,绝非“体育运动”,而且它以打坏人脑为目的,极其不道德。然而拳击运动的市场却丝毫未因舆论攻击而萎缩。为拳击运动辩解的人则强调拳击运动中的死亡事件比起诸如登山运动(每年死数百人)游泳运动(每年30万左右)微不足道。
这辩解显然不通。世上死于登山或游泳的人,绝大多数都是非职业的高山旅游者和普通的嬉水者,而业余爱好与职业显然有本质区别,前者本身就是生活情趣的表现,是一种人生的享受;目的与运动本身是统一的;而职业运动对几乎所有从事它的人来说都谈不上乐趣,目的与手段常常是分离的。所以真正的问题仍应归结于现代竞技运动的性质——为何“愿打愿挨”。
“英雄”与“明星”的区别也类似业余与职业的区别。顾拜旦最初制定奥林匹克宪章时就规定禁止职业化。理由是古奥运会衰败(包括精神)的原因之一就是职业化,诸如贵族雇佣他人代替自己参赛。
顾拜旦无疑是敏锐的,英雄的行为方式不但与自身也与整个社会群体的目的有高度的内在统一性,其行为通常为整个社会评价所肯定;明星则不同,尽管人们也不时称之为英雄,但职业表演性质决定了表演本身与目的分离特性。仍以拳击运动为例,有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穷人的运动”?在美国这项运动对黑人来说是摆脱贫困的阶梯,而对经营者它则是可以带来巨大的利润行当。可以断言,职业运动员即使敷衍了事也能挣大钱时,就一定会“偷懒”。所以今天随处可闻这样的模式语:“要想把××搞上去,就要引进良性竞争机制”。
这里的“良性”显然仅限封闭的空间而言,而它所带来的“进步”往往是以某种重大牺牲为代价。
今天运动场上的英才的技艺肯定高于古希腊,运动伤害的危险程度也肯定轻得多。耐人寻味的却是,现代竞技运动的伤残问题却很扎眼,运动员心理畸形和人格分裂的问题更严重。台上的(或今天的)英雄,在台下(或明天)就很可能是个白痴或魔鬼、恶棍。本·约翰逊如是,泰森如是,辛普森也如是。能力与人格的分裂是“明星时代”的普遍特征。
本文并非要进行道德批判和主张“复古”,而仅想指出,道德是个历史的范畴,人类早已告别童年走向成年,成年并不意味着成熟。在螺旋上升的阶梯中,即使在竞技运动领域,人类所取得的成果也远不像自我吹嘘的那样美妙。黑格尔说:“存在就是合理的”,马克思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进一步说:“既不(应)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而是在于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地也就消失。”
标签:体育论文; 竞技体育论文; 奥运会网球论文; 奥运会体操论文; 网球规则论文; 体育训练论文; 奥运会项目论文; 网球论文; 斯巴达教育论文; 体操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