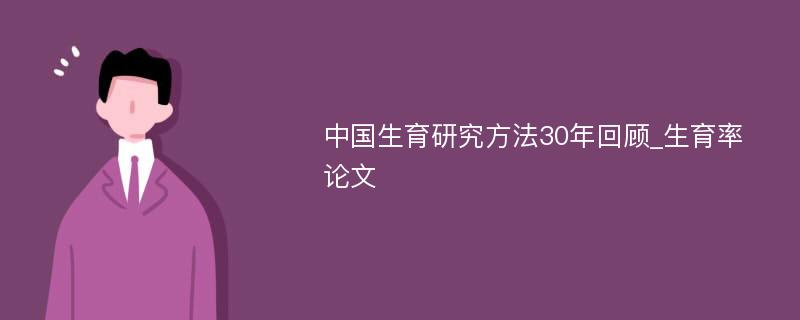
中国生育率研究方法:30年回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育率论文,中国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29X(2009)03-0003-06
生育率转变是当代中国社会最深刻的革命性变化之一。对生育率的关注与研究一直是中国人口研究的主体。可以说,中国的人口研究基本上是围绕生育率变动及其社会经济后果而展开和变化的。对中国生育率的研究,已有一些学者做了回顾和总结。于学军和解振明[1]从生育水平、生育模式、生育率转变及其决定因素、生育率下降后果等方面总结了我国生育率研究的主要结论与观点,并提出在未来应该加强对生育的理论研究、生育水平的估计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评估与调整研究。李竞能[2]总结了中国生育率的理论研究,主要从生育率变动的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包括计划生育)因素,以及生育率变动的人口学模型研究等方面概括了生育率研究的一些理论观点,并指出建立生育率理论体系应该是今后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自1999年以来,陆杰华与一些学者合作,对每年度的中国人口学研究进行回顾与评述;陈卫与一些学者合作对2005和2006年中国人口研究涉及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总结,包括对生育率研究文献的综述。[3-4]这些学者的研究综述帮助我们了解了我国生育率研究的主要成果、观点和变化脉络。然而,在这些无论是几十年、十多年研究还是每年度的研究综述中,它们一般只对生育率研究的主要结论和观点进行了概况,而对生育率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很少总结。实际上,对中国生育率变化的认识、中国生育率转变特征描述及理论解释等,都离不开生育率研究方法的选择、使用和改进。中国的生育率研究方法既有从西方引进的各种生育率指标和模型,也有中国学者为了适应我们自己的需要而改进和创建的方法和模型。本文将回顾和总结在中国生育率研究中所使用的主要方法以及这些方法对我国生育率研究的贡献。本文仅介绍国内学者使用于我国生育率研究的主要方法,分为生育率度量指标和生育率模型两类。
一、生育率度量
生育水平直接决定人口再生产和人口发展趋势、决定人口规模的大小和增长速度,因此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首要任务是降低生育水平、减少出生人口数量。1970年以来,我国生育率出现了迅速下降趋势,到80年代初生育率接近了更替水平。对我国生育率下降的这一过程,1982年人口普查、1982年1‰生育率抽样调查、1988年‰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数据给予了充分的记录与确立。我国生育率研究主要就是从分析这些调查数据开始的,使用各种生育率指标描述生育率变化,确立我国生育率迅速下降的事实,分析我国生育率下降的决定因素。
考察生育率变化可以使用多种指标,例如粗出生率、一般生育率、年龄别生育率、总和生育率、粗再生产率、净再生产率等。[5-6]在具体分析中使用什么指标,取决于我们的研究目的和各种数据的可获得性。在多数文献中,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是最常使用的指标。不过,这些基本的人口学指标在70年代并非为人们所熟知。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人口研究》杂志,使用不少的篇幅介绍和普及人口学基本知识和基本指标,规范化的指标名称和定义得以确立。那时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所做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开创性的工作。实际上,类似的工作至今仍然很有必要。
在度量生育率的各种指标中,粗出生率是最容易获得数据计算的,也是最常用的指标之一。但其主要缺点是受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影响。因为生育只发生于15-49岁的育龄妇女,因此对粗出生率的一个改进就是将分母限制在育龄妇女,这样就得到一般生育率。但是一般生育率仍然受到育龄妇女的年龄结构影响,因此计算年龄别生育率就完全排除了年龄结构影响。但是年龄别生育率又是一组数,1岁一组的话有35个年龄别生育率,5岁一组的话也有7个年龄别生育率,使用起来比较繁琐,因此人口学家巧妙地加总这些年龄别生育率,得到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被定义为一批进人生育年龄的妇女,如果按照当年的年龄别生育率渡过育龄期,她们将生育的平均子女数。这种指标的计算方法以及与此相关的同批人、同期人分析方法是人口学最独特的研究方法之一,也是人口学成为独立学科的标志之一。
根据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的变化,我国的生育率转变被划分为几个阶段:[7-8]1970年前的高生育率阶段、20世纪70年代的下降阶段、80年代的波动阶段和80年代以来的低生育率阶段。后来有的学者还将我国生育率下降过程区分为两次生育率转变:20世纪70年代的第一次转变,生育率由高水平下降到接近更替水平;90年代的第二次转变,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中国实现了低生育水平,并至今保持着稳定的低生育水平。[9-10]
80年代初,在学术界曾经对总和生育率这一指标进行过热烈的讨论。[11-17]由于当时人们对总和生育率的含义、特性没有很好地认识,它被当作当年妇女实际平均生育子女数或终身生育子女数,被用来衡量、评价一个地区计划生育工作成绩的最直接、最贴切的指标,因而产生了总和生育率指标值与实际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相矛盾的现象。一些城市地区计划生育工作开展得越来越好,一孩率越来越高,而总和生育率也在上升。学者们和实际工作者一起探讨了这种现象,对总和生育率和终身生育率的区别和联系、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澄清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这些文献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是人口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必读的文献。
80年代初对总和生育率的争论告诉我们:当生育率变化缓慢、平稳时,总和生育率可以很好地刻画生育水平变化过程;但是当生育率发生急速变化时,总和生育率有时不能很好反映生育水平的真实趋势。通常的表现是“在妇女们推迟生育的年份中,生育率被压低了;而在生育提前的年份中,生育率被提高了”。[18]西方学者在研究90年代欧洲超低生育率时,认为超低的总和生育率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真实的生育水平,生育年龄的不断推迟是形成超低生育率或极低生育率的重要原因。如果排除生育年龄推迟的影响,实际生育水平会有明显提高。美国人口学家Bongaarts and Feeney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明了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TTR′(Tempo Adjusted TFR),通过对总和生育率中由于推迟生育的下降部分做一控制,从而根据时期生育行为更好地估计终身生育水平。郭志刚[19-23]应用中国历年生育数据对TFR′方法进行应用与检验,结果表明该指标作为估计的确比TFR指标更接近于实际队列的终身生育率。90年代中后期我国生育率调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为1.3~1.4,而TFR′指标却达到1.7。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推算的1999年总和生育率为1.23,而TTR′为1.58。郭志刚认为,用以往的生育数据计算TFR和TFR′两个指标,并加以比较,可以提供一些新的信息,帮助我们更好地回顾和认识我国的生育史及计划生育历程。
郭震威[24]在评价总和生育率的缺陷的基础上,讨论了TFR′方法的价值,但同时认为TFR′不伦不类,既不是时期生育指标,又不是终身生育指标,因而是个尴尬的指标。其实正如郭志刚[25]认为,TFR′只是应实际需要而产生的另一种根据时期生育信息对终身生育水平的新估计。统计中凡是不能直接测量的时候,都得采用估计来代替。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它是否比传统TFR更接近于终身生育水平。由于现实中生育模式转变时,除了导致该年生育数量有所变化以外,还会有其他共生现象,如分孩次的平均生育年龄(MAC[,i])也会变化。MAC[,i]实际上是生育模式转变的测量值,可以在理论上建立其变化量与时期生育变化量之间的函数关系。TFR′便是在常规分孩次TFR[,i]的基础上利用MAC[,i]的变化信息来调整,得到去进度效应的分孩次TFR′[,i],然后再汇总为TFR′。经过调整,TFR′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修正TFR距终身生育水平的偏离,因此TFR′更接近于队列终身生育水平。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TFR′来替代TFR原来所承担的终身生育估计的功能,而TFR还可以继续承担描述时期生育水平的功能,TFR′与TFR之差可以作为生育推延对当前生育水平影响的估计。
国内学者针对总和生育率的缺陷,也曾经提出过一些能够更好反映实际生育水平变动的指标。林富德[26]提出采用婚后年数别总和生育率能够比年龄别总和生育率更充分地反映我国生育率转变的真实情景。两个指标的不同表现在:从计算上看,前者是分婚后年数的生育率的总和,后者是分年龄生育率的总和;从含义上看,前者反映已婚妇女的生育水平,后者反映全体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由于中国妇女普遍都结婚,从同一队列讲,总和生育率和总和婚后年数生育率接近相等。当婚姻模式较为稳定时,两者就趋于一致;而婚姻模式发生较大变化,两者就会产生差异。分析表明在80年代之前,总和生育率低于总和年数别生育率;而80年代前期,总和生育率又高于总和年数别生育率。这与70-80年代我国婚姻模式发生的重大变化有关。70年代初婚年龄的不断推迟对总和生育率的下降作出了重要贡献,而80年代的婚姻堆积又导致总和生育率的明显回升。而总和年数别生育率没有表现出总和生育率那样剧烈的变化趋势。
针对总和生育率不能控制孩次结构的缺陷,以及根据我国人口控制特点进行分析的需要,马瀛通等[27-29]提出了年龄别递进生育率和总和递进生育率。它与常规的生育率不同在于分母与分子的对应,即分母是发生分子中的某孩次生育的妇女,排除了与生育该孩次无关的妇女。所以它不是常规生育率那样的“平均率”,而是递进生育的概率。控制了孩次结构的递进生育率有时候与常规生育率相比结果很不相同。比如在发生生育堆积或突击生育一孩的情况下,常规的一孩总和生育率会显著大于1,然后又会明显下降。而一孩总和递进生育率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例如,60年代初由于补偿性生育,我国生育率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水平,一孩、二孩甚至三孩总和生育率都超过1。而70年代一孩总和生育率又降到大大低于1的水平。然而,一孩总和递进生育率始终变化平稳,处于0.95~0.99的水平。又如郭志刚[30]的计算表明,2000年人口普查计算的常规总和生育率很低的原因之一是没有控制孩次结构,因为2000年的总和递进生育率要明显高于常规的总和生育率。同时,按照递进生育率计算的孩次别平均生育年龄也明显高于按照常规生育率计算的孩次别平均生育年龄。需要指出的是,马瀛通等人提出和创建的递进生育模型是一项突破性的研究成果。Feeney也提出了递进生育模型,并应用于中国人口分析之中。[31-33]Feeney的模型突出考虑了孩次递进的间隔因素,但不考虑年龄结构,因而常被称为间隔递进模型;而马瀛通等的模型则突出考虑了年龄递进因素,因此常被称为年龄递进模型。Feeney的模型需要妇女生育史数据才能计算,而马瀛通等的模型可以从人口普查数据计算。也正是马瀛通等的模型具有更强的操作性,郭志刚[34-35]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递进生育预测方法,探讨生育政策调整的人口模拟方法。递进生育预测方法已经被应用于一些生育政策调整的人口后果研究中(例如取消二孩生育间隔和放开单独对人口增长的影响)。这种方法在我国未来生育政策调整研究和决策中,将会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这种方法与常规的生育率预测方法相比要复杂得多,因此一方面需要更多地加以介绍和推广,另一方面应该鼓励开发基于这种人口模拟方法的人口软件,以利于学术界和实际部门的应用。
二、生育率模型
人口学家们使用各种生育率指标度量和估计生育水平、描述和刻画生育率下降过程时,也对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做了大量的、深入的分析。除了定性的理论分析外,也有一些定量的统计模型考察和分析对生育率下降发生影响的各个因素及其贡献。这些定量模型可以分为人口学模型和社会经济模型两类。人口学模型主要关注人口学变量或要素对生育率的影响,一般包括年龄、婚姻、避孕、流产等因素,使用生育率的标准化、生育率的分解以及生育率数学模型来分离这些因素的影响;而社会经济模型则考察社会经济变量对生育率的影响,一般包括个人的、社区的或更高层次的社会经济特征变量,使用多元统计方法分析它们的影响。
生育率的标准化和生育率的分解在方法上是类似的,通过固定(标准化)其中某一个要素来估算其他要素的作用。生育率在不同时间或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可以通过标准化或分解,分析年龄结构、婚姻结构和生育水平各自的影响,考察生育率变化的内在机制。曾毅等[36]利用这种方法对1981-1987年我国及各省出生率回升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出生率回升最主要的原因是初婚年龄提前,其次是年龄结构的影响,最后才是已婚生育率的影响。初婚年龄提前和年龄结构变化导致出生率回升,而已婚生育率则是有明显下降。这项研究对于认识80年代的计划生育工作和人口形势具有重要意义。
总和生育率是年龄标准化生育率,但是它仍然受到婚姻和孩次结构的影响。而总和递进生育率则是将总和生育率又按照婚姻和孩次结构进行了标准化。在上一节的分析表明,在初婚模式变化、对生育进行孩次控制的条件下,总和递进生育率要比总和生育率更能反映真实的生育水平,更利于评估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成效。
在分析生育率影响因素时,一种被广泛使用的模型是Bongaarts生育率中间变量模型。其目的是考察婚姻、避孕、流产、哺乳等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这些因素是在生育过程的各个阶段上对是否生育、生育多少和生育早晚直接产生影响的生物学和行为学因素。其他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是通过这些因素而间接对生育率发生作用的。因此这些因素被称作生育率的直接决定因素或中间变量。通过计算婚姻指数(C[,m])、避孕指数(C[,c])、人工流产指数(C[,a])、产后不育指数(C[,i]),Bongaarts将总和生育率变化表达为这些影响因素及总和自然生育率(一般为13.5~17.0)的函数,进而可以分解这些因素对生育率变化的贡献。这些指数的取值范围都在0~1之间,它们的值越小表明它们对生育率的影响越大。一些学者使用Bongaarts生育率模型对我国生育率转变进行了分析。[37-39]陈卫[40]的研究表明,中国的生育率下降主要发生在70年代,婚姻的作用(初婚年龄推迟)最大。自80年代以来,避孕的作用变为最大。在整个生育率转变过程中,婚姻和避孕的作用占85%,而人工流产的作用占15%。
还有一些生育率模型也被用于生育率变化或人口控制分析中,例如寇尔生育指数和寇尔-特拉塞尔生育模型。[41-44]将所研究人口的婚姻、生育模式与标准已婚生育率模式(1921-1931年Hutterites的年龄别已婚生育率)对比,寇尔生育指数通过分别计算综合生育指数(I[,f])、已婚生育指数(I[,g])、非婚生育指数(I[,h])、已婚比例指数(I[,m])来分析生育率下降中婚姻控制和婚内生育控制的作用。黄荣清等[43]的研究表明,1978-1982年我国综合生育指数与1953-1957年时相比下降了55.1%,已婚生育指数下降了43.0%,已婚比例指数下降了22.1%。可见,70年代大力提倡晚婚为我国生育率下降作出了很大贡献。
寇尔-特拉塞尔生育模型通过实际生育率与自然生育率的对比反映生育控制的程度。该模型基于以下假设:在不存在人为生育控制的条件下,已婚生育率将与自然生育率相一致;否则将随年龄的增长按固定的模式偏离自然生育率。通过这一模型可以计算出所研究人口相对的自然生育率水平(M)和自愿生育控制的程度(m)。M值越大,表明所研究人口的自然生育率越接近标准自然生育率;而m值越大,表明自愿生育控制程度越强。马瀛通等[41]使用寇尔-特拉塞尔生育模型对1962-1981年我国生育率变化进行了拟合分析,1962-1972年生育率变化不大的年份拟合效果较好,而后面年份生育率变化较大,拟合效果略差一些。M值存在波动,但总的看来,由60年代初的0.9降到70年代初的0.8,再降到70年代末的0.7。反映自愿生育控制程度的m值则处于不断上升趋势,由60年代初的0.3左右,缓慢上升到70年代初的0.5,然后迅速上升到80年代初的1.4,反映出生育控制程度大大增强。
上述生育率的人口学模型实际上探讨了生育率变化的内在机制和规律,而生育率变化还取决于外在制约因素,即社会经济环境。社会经济环境是通过生育率变化的内在机制来影响生育率的。对我国生育率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的研究主要使用多元统计模型进行分析。一些西方学者强调中国的生育率下降主要甚至完全是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也有一些西方学者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认为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都对中国生育率下降产生了影响。中国的学者对这一问题更是进行了大量研究,使用许多回归模型考察我国生育率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以及不同层次的影响因素。蒋正华、[45]林富德、[46]彭希哲和黄娟、[47]孙文生和靳光华[48]等从时间序列到横截面数据,使用线性回归,通径分析检验了社会经济发展对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影响。他们得出了基本类似的结论,即中国的生育率下降与社会经济发展有密切的关系。顾宝昌、[49]蒋正华、[50]贾忠科[51]等都使用通径分析模型考察了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因素对我国生育率的地区差异的影响,认为两类因素都有重要的作用。利用1982和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林富德和刘金塘[52]也使用通径分析考察生育率的省际差异,得出结论认为1982年人口控制因素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大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到1990年人口控制因素的作用有明显下降,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有所增强,并超过了前者的作用。为了克服以往研究中诸多自变量的共线性,陈卫[9]使用因子分析和线性回归,利用我国各省1980、1990和2000年的横截面数据考察了“发展-计划生育-生育率”关系,结果表明在过去30年里,计划生育的作用在下降,而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在增强。70年代计划生育的作用是主导,80年代计划生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二者的作用基本达到了平衡,而90年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成为主导。“发展-计划生育-生育率”关系呈献出一种动态平衡。
综上所述,生育率模型,无论是数学模型还是统计模型,对促进我国生育率研究、认识我国生育率转变过程、机制、决定因素等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必将对中国的人口转变理论构建奠定基础。必须注意到,西方的生育率模型,有的是数学抽象,有的是根据西方或其他国家的经验建立的,在应用到我国生育率研究中不一定完全适合。需要根据我们的目的和实际加以应用和解释。一些学者注意到了这些模型的适应性或局限性,提出了改进的模型,是非常有益的探索。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口学的繁荣得益于形式人口学的发展。在人口数据日益丰富、计算机技术迅速发展的条件下,我们有理由期待形式人口学的再度蓬勃发展。
[收稿日期]2008-1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