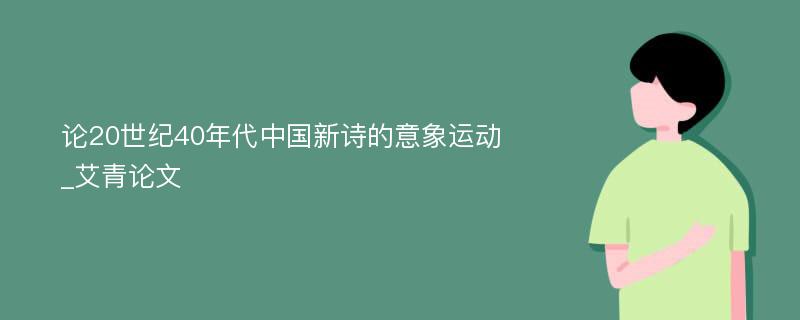
论中国40年代新诗的意象化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诗论文,意象论文,中国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对于意象艺术的重新重视,是借助于英美意象派的介绍。英美意象派诗歌的形成,既受到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影响,又受到中国古典诗歌的启发,但它又不同于法国象征派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它是一种自足的诗歌艺术。在中国古代,最早将意象用于诗歌理论的,是南朝的刘勰。他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曾有“窥意象而运斤”之说,并将其看作“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把它放到艺术构思的首要位置上来看待。此后,历代诗论家对它多有论及。明朝胡应麟在《诗薮》中指出“古诗之妙,专求意象”。何景明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中说:“意象应曰合,意象乖曰离。”古代诗论家一般都认为“意”是指心意,“象”是指物象,意象即“意”与“象”复合而成的“意念之象”。在古代诗人那里,意象是情景交融、寓情于景的一种艺术处理方法。中国古代诗歌一个最重要的传统就是讲究简练与含蓄,而意象的运用,正是使诗歌达到简练与含蓄的重要手段。在西方,真正使“意象”一词被广泛引用的,是在20世纪意象主义诗派的出现之后。意象派创始人庞德在探索用“意象”写诗时,很欣赏中国古典诗词,并从中获取了丰富的营养。他们从中国古典诗词和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中获得启示,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那里获得哲学基础,从而创立了意象主义诗歌流派。他们认为艺术=直觉=意象,艺术家的任务就是通过直觉捕捉生活的意象。根据这种理论,意象的形成是诗人内心的一次精神上的经验,它具有感性和理性两方面的内容。正如庞德说的,意象是“理性和感性的复合体”。意象的使用,使情绪有准确具体的“对应物”,使诗人的主观感受通过感觉印象含蓄地表达出来,以使诗歌摆脱和避免19世纪末浪漫主义对情感的毫无节制的发泄和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的弊病,使诗增强凝炼性和客观性。[①a]由于英美意象诗歌与中国古典诗词的某些相通性,因而很快被中国新诗人所接受。白话新诗的开拓者胡适最早从意象主义那里获得过启示。五四时期的现实主义诗人和浪漫主义诗人也有重意象的,当然它还没有成为其诗歌创作最主要的特征和方法。二三十年代的新月诗派、象征诗派和现代诗派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自觉地以意象作为诗的重要元素和主要抒情手段。进入40年代以后,新诗虽然更注重“普及”,努力探索民族化、大众化的诗歌道路,建立通俗、明快的诗风,但作为诗歌艺术修养较高的诗人(特别是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人)则更侧重于与时代相适应的高层次的艺术追求,他们在创作中特别青睐于既与中国传统诗歌相承接又与西方现代诗歌相沟通的意象艺术,并对之作了进一步的富于创造性的探索。一些论者从对意象的研究中找到了诗歌创作的新角度,并对意象的重要性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艾青在《诗论》中用诗一样的语言表达了对意象的认识。他说:
“诗人的脑子对世界永远发出一种磁力:它不息地把许多事物的意象、想象、象征、联想……集中起来,组织起来。”
“意象是从感觉到感觉的一些蜕化。”
“意象是纯感官的,意象是具体化了的感觉。”
“意象是诗人从感觉向他所采取的材料的拥抱,是诗人使人唤醒感官向题材的迫近。”
九叶诗人对“意象”的探索体现了一种全新的眼光。唐湜说,“在最好最纯净的诗里面,除了无纤尘的意象以外,不应再有别的游离的滓渣”,甚至极而言之,“诗可以没有表面的形象性,但不能没有意象”。表达真情实感,是诗人创造意象的最终目的。在他们的理解中,意象与诗的意义具有完整而不可分性,意象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和增添生动性的修辞手段,“它与诗质的关联不是一种外形的类似,而应该是一种内在精神的感应与契合,一种同感、同情心伸缩支点的合一”。意象对诗常有“廓清或确定诗的意义”的作用。[①b]他们认为意象在诗歌创作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没有经过意象外化的“意志只是一串认识的抽象结论,几个短句即足清晰说明”,没有经过意象外化的“情绪也不外一堆黑热的冲动,几声呐喊即足以宣泄无余”[②b]。由此可见,他们不但对意象高度重视而且对意象的探讨和认识也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对意象从理论到实践的高度重视,是新诗发展的必然趋势。从30年代现代派的成功诗作中,人们看到了意象在新诗中的独特功能,所以意象作为诗歌一种运动形式,已为一般诗人所认可。40年代的民族危机,使文坛普遍生长出一种回归传统的倾向,这种回归,不仅是获取一种民族的自信心,而且是从本民族的文学传统那里获取某种依靠的力量。作为诗人,对意象的青睐,则自觉地达成了与传统的契合,获取了对传统的支持。因为传统诗歌讲究“托物言志”、重主客观统一和诗歌重象征、重含蓄、重精致、重虚和的民族特色,只有在“意象”那里才能找到最切近的原型,最可靠的依托。由于意象是从中国传统诗歌那里发展而来的,又在中国新诗中生根、开花、结果,因而对意象化的重视和强调,能够使40年代诗人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上开拓出新诗发展的新路向。
40年代诗歌的意象化运动,就是把意象当作诗的基本构成成分,或者说,意象是使思想观念或内心情绪具体化到可以被感官感知的一种艺术处理,是诗人含蓄地表现情感的一种重要方式。在他们看来,诗是以语言为符号的主情的审美符号系统,它的主要原件不是语词,而是意象。意象化是整个诗美创造的基础性工作。在一首诗中,意象成分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应当占主导地位。意象成分越充分,诗的成分也就越完满;意象成分也就是诗的成分。即是说,有没有意象,是诗与非诗的根本区别,没有意象,诗就成了直白与说明。诗的创作,就是诗人捕捉意象、创造意象,然后加以有序化组合的过程。或者说,意象是诗人主观情意与客观对象的复合体。一个意象既非单纯的主观感受,又非单纯的客观真理。它是二者在一瞬间突然遇合而成的综合物,它始终伴随着诗人内心精神的体验。所以,意象其实就是诗人感情外化的一种表现形态,它兼有双重身份:主观性与具象性。“意象”在意象派和象征派那里都是重要的诗歌元素,如果诗人对意象体贴入微,将自我化入意象,赋予它以自由生长的生命,则接近意象派;如果诗人挖掘意象潜伏的意旨,进一步追求一个意象意义的形而上理念世界,则与象征派趋同。不过,在40年代,相当多的诗人对西方诗歌的吸纳已进入综合阶段,因此,意象也成为一种综合性很高的艺术手段。如艾青、冯至、卞之琳、何其芳、田间、臧克家,以及七月诗派和《中国新诗》派,都把意象作为诗歌的重要表现方式,甚至把意象的创造贯穿于诗歌创作的全过程。
与朗诵化、民间化、散文化和形象化不同的是,意象化以审美知觉为核心,它偏于象征,富于暗示。意象比较多情感、想象因素,它使诗的结构内部拥挤,脉络精细,诗情浓缩。意象化偏于比兴,长于表现,使诗的感觉变形、跳跃、浓缩,利于抒情而不便于叙事,宜于写心而不适于议论。意象艺术在40年代达到了超越前人的高度,各种倾向的诗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把它引进创作中,从而提高了诗歌的艺术水准。不少诗人为了避免激情的泛滥和诗意的浅露,十分注重诗的意象的营造。卞之琳、冯至、艾青、穆旦、辛笛、何其芳、方敬、绿原等写诗就极注重情感客观化的表现,让激情在情景相契的意象中得到含蓄、委婉的表达。在《中国新诗》诗人群那里,无论哪一种抒情方式都离不开意象,因为他们自觉地“将感情凝结于深沉的意象里”,意象在他们诗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唐湜评价辛笛的《手掌集》时这样写道:“只有在生活经验深入意识的底层,受了潜移默化的风化作用,去芜存精,而以自然的意象或比喻的化装姿态,浮现于意识流中时,浮浅的生活经验才能变成有深厚暗示力的文学经验。”[①c]唐湜评价陈敬容的诗,“即使是深沉的玄想,也总是由带着郁郁色调的意象托出”[②c]。这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创作倾向。就诗人个体而言,40年代新诗的意象艺术,艾青占据第一提琴手的地位,但在面的拓展与丰富上,无论哪种流派、哪种风格的诗人都各有自己的贡献。
总览40年代诗歌,你会发现诗人为了更好地表达思想情感,十分注意诗歌意象的提炼和营造。成熟的意象创造,都是基于诗人对事物外部和内在特征的深刻认识,基于诗人对事物的强烈感受,是“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最愉快的邂逅”[③c]。成熟的意象,“一方面有质的光实,质上的凝定,另一方面又必须有量上的广阔伸展,意义的无限引伸”。例如艾青《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臧克家《春鸟》、辛笛《布谷》、杜运燮《雾》、唐祈《雾》、鲁藜《泥土》、绿原《春雷》、阿垅《纤夫》、臧云远《百灵鸟》、徐迟《江南》、邹荻帆《江》、方敬《尖》、苏金伞《地层下》等诗中的意象,不仅有明丽优美的外在形态,而且更重要的是渗透着诗人强烈的主观感受,融化了诗人深沉的思想意念和饱满的内心情绪。意象在他们诗中,不是空虚的装饰品,而是有意味的物象,它既有鲜明可观的感性形式又有丰富完整的情感蕴含。40年代诗人对意象的提炼,不但注意意象与情感的一致与和谐,而且注重意象的高度简化与抽象,这种意象的简化与抽象不是导向原理与公式,而是获得更本质的理解,是不脱离具体的抽象。如臧克家的《三代》:“孩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葬埋。”仅三句六行,就浓缩了三代人的生活与命运,使“土地”意象的情感内涵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他们对意象的提炼,不仅体现在以尽可能少的语句提供更多的情感与审美信息上,而且体现在对意象内涵的深入挖掘与丰富上。例如艾青的《吹号者》,写的是在一次残酷的战斗中,吹号者“被一颗旋转过他的心胸的子弹打中了”,但是,他的手依然紧紧握着那号角:“在那号角滑溜的铜皮上,/映出了死者的血/和他的惨白的面容;/而太阳,太阳/使那号角射出闪闪的光芒……/听啊,/那号角好象依然在响……”这“号角”意象既是象征为国牺牲的战士的精神不死,它将召唤众人继续战斗,又是“对于‘诗人’的一个暗喻,一个对于‘诗人’的太理想化了的注解”[④c]:即使诗人倒下,他那支“芦笛”仍然吹奏着战斗的歌曲,永远鼓舞着人们为光明、为祖国而战。再如阿垅的《纤夫》中的“纤夫”,可说既是一个特定的纤夫的命运与性格的写照,也是所有的纤夫的命运与性格的写照,还是中华民族的命运与性格的写照。这种意象提炼确能收以简驭繁之功,获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果。它对于提高诗歌的含量、增强诗歌的表现力,具有事半功倍的效力。
40年代诗歌意象在内容上是十分丰富的。这是因为一场民族解放战争把诗人们推向了社会变革的战场,推向了广阔的生活领域,这也同时为诗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生活情感资源和诗歌意象资源。正如唐湜所说,“在诗人,意象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诗人对客观世界的真切的体贴,一种无痕迹的契合;另一方面又是客观世界在诗人心里的凝聚,万物皆备于我”[①d]。如果诗人把在现实人生中所体验出来的印象印证于日常形象,如果诗人的情思与他们在生活中获取的形象发生了某种同构对应关系,就必然产生意象化的诗。冯至说他写作《十四行集》的缘由是:“有此体验,永久在我脑里再现;有此人物,我不断地从他们那里吸取养分;有此自然现象,它们给我许多启示:我为什么不给他们留下一些感谢的纪念呢?”于是“从历史上不朽的精神到无名的村童农妇,从远方的名城到山坡上的飞虫小草,从个人的一小段生活到许多人共同的遭遇”,凡与诗人的生命“发生深切的关连的”,重重地震撼了他的生命,或轻轻地使他的身心颤动的,他都给出他的诗。[②d]因此在他的《十四行集》中总是涌动着富于生命的意象,总是由身边的平凡事物,联想到宇宙人生的哲理。他以“威尼斯”的意象,象征人世“千百个寂寞的集体”,表达他对人们彼此隔膜的感受(《威尼斯》);通过一丛“躲避着一切名称”,“在否定中完成”、“渺小的生活”的小草,称颂了平凡中“伟大的骄傲”(《曲鼠草》)。他的诗以意象化的实写代替哲理化的虚写,内蕴极其丰富。所以朱自清在《新诗杂话》中一再称赞他是“从敏锐的感觉出发,在日常的境界里体味出精微的哲理的诗人”;“冯先生的集子里,生硬的诗行便很少,但更引起我注意的还是他诗里耐人沉思的理,和情景融成一片的理”。杜运燮也是一个善于发现意象、容纳意象的诗人,意象像一个聚光灯一样照亮了他那优秀的诗篇。唐湜在读了杜运燮的《诗四十首》后说,它“给我们的主要印象是意象丰富,分量沉重,有透明的哲理思索,自然又多样,简赅又精博,有意味深长的含蓄,可以作多样的解释,有我们读者自己作独特探索的余地,稳重而矜持的风格里有大胆的肯定,流利的文句里有透明的感悟。意象跳跃着在眼前闪过,像一个个键子叮当地响过去,急速如旋风,有一种重甸甸的力量,又有明朗的内在节奏,像一个有规律的乐谱。有时深厚像老年人的说话,有时轻快从容,又像一枝箭射出去,落下来。”[③d]其实,“意象丰富,分量沉重”,不只是杜运燮诗作的特征,也可说是当时很多诗人诗作的共同特征。
我们从当时诗歌意象的内容来看不外来自于自然,来自于历史文化和来自于现实三个方面。以自然存在物为诗歌意象,表达诗人的情思,是中国诗歌的传统。山水草木,莫不有性情,情感与这些形式遇合,便有意象的产生。40年代诗人无不以自然风物为题,寄托情志,引申哲理。他们善于把抒情氛围置于深沉的雪夜、广袤的旷野、茫茫的草原、绵绵的秋雨等环境中来对诗情进行渲染,通过大自然景象幻变的描绘来暗示现实社会情状。这些自然景物意象不但反射出时代和人民的精神光泽,也透射出诗人的内在情热。从历史文化现象中获取诗歌意象,是40年代诗坛的一种普通现象。一个历史人物,一个历史故事,以及一座古碑、一座神庙、一座古城、一根石柱、一堆灰烬……都会触发诗人的情思,成为他们的抒写对象。这是因为现实生存的艰难,加上民族精神自我确立的需要,迫使诗人在过往的历史文化中寻找现实生活的镜子,从历史文化中获得生活与斗争的信心和启示。当然,更多的还是从直接面对的现实生活中的人类行为里提取诗歌意象,表现生活的本质和人的思想情感。作为一个热爱生活与生命的诗人,他总是尽量将自己对大自然、对历史和现实的感受转换成极富个性和新意的意象。所以自然意象、历史意象、现实意象成了诗人创作的主要内容。而这三方面的内容在诗中又往往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
从40年代诗歌的意象组合形式(类型)来看,则是多姿多彩的。其意象组合的实质,是依从诗人情绪或意念的线索,按照一定的构思,对意象进行有机组接和排列,从而完成诗的整体建构。40年代诗歌意象组合形式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中心意象型。即一首诗中以一个意象为中心,贯穿其他次意象。中心意象是诗的主脉,其他次意象只起补充的作用。例如艾青的《我爱这土地》中的“鸟”,《吹号者》中的“号角”,《火把》中的“火把”,《旷野》中的“旷野”等,就是贯穿全诗的中心意象。这种中心意象本身就是诗的一个有机体,它往往担负起表达主题思想的任务。这些诗中的不少次意象是由中心意象派生出来的,它们不仅是为了表达、丰富中心意象,而且它们本身又有着一定的内涵。如在《我爱这土地》中,诗人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土地,直到死后用羽毛肥沃土地的“鸟”来比拟自己誓为祖国歌唱直到死亡的真挚感情。诗中围绕“鸟”这个中心意象出现的一系列派生意象也都富有自身的内涵:“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暗示祖国的受难、民族的危机;“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和“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暗示着人民对侵略者的愤怒和反抗,“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暗示民族解放战争的必胜信念和希望。所有这些派生意象又都饱含诗人热爱祖国的赤子之情。又如牛汉的《春天》:“没有花吗?/花在积雪的树枝和草根里成长/没有歌吗?歌声微小吗?/声音响在生命内部/没有火吗?/火在冰冻的岩石里/没有热风吗?/热风正在由南向北吹来/不是没有春天,/春天还在冬天里/冬天,还没有溃退。”诗中的中心意象是“春天”,诗人围绕中心意象展开丰富的联想,使之推移向其它意象——花、歌、火、热,其实这些能传神、能发出某种特殊信息的次意象都是为丰富、展现中心意象服务的,脱离了中心意象,它们就失去了意义。二是并置意象型。一首诗中有两个以上的意象,这些意象的关系是并置的。这些并置性意象表面互不相关,实质都是指向意义的同一性,而最终目标是实现“比各部分相加之和的价值”大得多的“整体价值”[①e]。在辛笛的《风景》一诗中先后呈现三组意象:“比邻而居”的茅屋和野间的坟;“绿得丰饶自然”的夏天的土地和“黄得旧褪凄惨”的兵士的新装;“瘦的耕牛和更瘦的人”。这三组相互对照,映衬的意象是一种并列关系,从不同侧面映照出一种病态的“风景”。这些由诗人直觉对于视觉感官的强化而得到的意象,十分生动地传达出了社会生活的病态感。艾青《冬天的池沼》一诗,把“寂寞”的“老人的心”、“枯干”的“老人的眼”、“荒芜”的“老人的发”三个意象并置,然后形成一个“佝偻在阴郁的天幕下的老人”的整体意象,从而衬托出一幅苍凉的图画——冬天的池沼。这些意象的组合是诗人的感觉由点到面、由表层到深层、由实到虚的结果。三是群体意象型。一首诗中,将丰富的、众多的有一定内在联系的意象加以集合,象电影蒙太奇的手法那样进行组接,以表现繁复的生活和情感。40年代诗人大都长于意象群的组合方式。例如,辛笛的诗常常是把一系列能使人产生联想的意象排列在一起以强化读者的印象,加强诗的情感密度,唐湜说他的《门外》一诗中“那种重重叠叠的记忆的意象交织却似秋虫的繁奏”[②e],在穆旦的诗中,富于生命力的活跃的意象总是不断涌现。例如《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控诉》、《赞美》、《春》、《海恋》、《诗八首》等诗,都在诗的形式里凝成了一系列意象,从而呈现出细腻深邃的诗境。难怪唐湜说,“读完了穆旦的诗,一种难得的丰富,丰富到痛苦的印象久久在我心里徘徊。”[③e]这种“丰富到痛苦的印象”正是意象群组合的艺术效力。这种意象群的组合是以诗的情思凝聚点为轴心,将群体意象有序地呈现出来,形成一种整体的网络结构,只有在这整体的网络结构之中,每个意象的意义才能得到确定,诗的整体意义也才能得以显示出来。
从40年代诗歌意象的表现方法来看,比以前更加成熟了。40年代诗歌意象的表现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各个诗人都有所不同,无法一一列出。但从总体上看,主要有三种:一是描述性方法,即诗人带着情感对物与景进行描绘、摹写而产生意象的方法。如陈敬容对《手》的素描:“你,灵动的赋形,不可见的战栗,热的播散,光的把握者:你——伟大的手!”这一描述,就使“手”的意象跃然纸上,有了一种形象的透明感。描述性意象的主观感情是十分强烈的,它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将诗人的主体感情直射对象。如同样写“夜”的诗:杜谷的《夜的花朵》通过对“夜”的描述,隐含着诗人对光明未来抱有的坚定信念;杜运燮的《夜》通过对“树”的描述,渗透着诗人对黑暗的厌憎和对光明的渴求;鲁藜的《风雪的晚上》通过对“雪”的描述,寄托着诗人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斗争的礼赞;牛汉的《落雪的夜》通过对北方“寒冷”的描述,表达诗人自己愿做“一束”为驱走黑夜的寒冷而燃烧的“木炭”。描述性意象在描摹中将比喻、拟人、变形、夸张、通感、反衬等手法兼而用之,使它显得更生动、形象和含蓄。描述性方法是诗歌意象最基本的表现方法,它在其它意象表现方法那里也常常被交叉运用着。二是拟情性方法,即诗人将抽象的、不可见的情感具象化而产生意象的方法。也就是将抽象的情意虚拟为人或物等具体的物象,使之具有更深的寄托。它常常将托物、拟物、比兴等方法综合运用,使诗歌更带拟情意味。例如杜运燮的《山》完全是以拟物的手法写出诗人不满足现状,不断追求、进取的情态:“来自平原,而只好放弃平原;/植根于地球,却又想植根于云汉;/茫茫平原的升华,它幻梦的形象,/大家自豪有他,他却永远不满。……”杜谷的《江》以比喻的手法写出中华民族的希望:“古老的江/喑哑的江/瘦弱的江呵/你不要悲哀/因为春天总归要来。”郑敏的《鹰》以鹰喻志,表达自己一旦看清了现实世界的“不美和不真”,就坚定不移地“舍弃”它;一旦认清了自己前进的方向,就决不停止对它的追求。方敬的《光》以对“光”的意象呈现,礼赞黑暗中的灯光和战斗。艾青的《冬天的池沼》运用典型的拟情手法,把“冬天即将过去,春天还会远吗”的心灵感受融化在寂寞、枯干、荒芜、阴郁的池沼意象之中。拟情性意象的表情作用不象描述性意象那样直接展现,它常常是化虚为实,化情为景,使不可捉摸的情感变得有光有色,有声有形,因而它比描述性意象显得更含蓄更有弹性一些。三是象征性方法,即用象征的方式产生意象的方法。诗人因情绘景秉意造像,将眼前景、心中像与主观情思相渗透、融合、改造、变形,通过丰富的想象力去扩充诗的内涵,从而使诗蕴含丰富的暗示和象征意味。艾青的《树》短小精悍,前四句写树的表层景观:“一棵树,一棵树/彼此孤立地兀立着/风与空气/告诉着它们的距离”;后四句写树的深层景观:“但是在泥土的覆盖下/它们的根伸长着/在看不见的深处/它们把根须纠缠在一起”。这首诗不只写出了树的生存景观,而且写出了当时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实质。“树”是一种象征,诗人用这一手法,象征中华民族是一个表面松散,实则有着巨大的内在凝聚力的民族,它暗示了中华民族必胜、帝国主义侵略者必败的真理。郑敏的《树》通过对“树”的那种寓深沉于宁静的姿态与品格的意象化描写,透示一种深邃的哲理。常任侠《冬天的树》通过对挺拔于冬天的“树”的意象化描述,象征一种理想的秉性,或暗示自己隐秘的内心世界。象征性方法所创造的意象是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统一,意象的表层结构只指向事物外部,意象的深层结构则是心灵与视象的深度融合,是“内在生命”的真正显现。象征性方法和拟情性方法都是一种情感客观化手段,即注意寻找与自己思想情感相契合的“客观对应物”,在思想情感与客观对应物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从而造成诗的弹性与张力。所不同的是,象征性方法是将思想情感与客观对应物融为一体,而拟情性方法是将思想情感与客观对应物构成比附、阐释关系。象征性方法和拟情性方法时有互相交叉的情况,而且它们都要借助描述性方法。以上所举意象的表现形态和方法,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严格区分。诗人在进行意象营造时,往往多种形式和方法综合运用,相互交错,以达到更好的艺术效果。诗人不论使用什么形式和方法,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地营构意象,创造诗的情境,所以意象的营构活动也就是诗的造境活动。
40年代诗歌意象化运动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历史的局限。与二三十年代意象化诗歌相比较,少了些低沉,多了些高昂;少了些阴郁色彩,多了些时代光亮。二三十年代诗歌中大量运用的意象是悲秋、残春、冬夜、孤鸿、衰草、夕阳、垂柳、古道,以及风、花、雪、月,等等,显得低沉忧伤、凄绝哀婉。而40年代诗歌中大量运用的意象则是太阳、黎明、春天、红旗、火把、火焰、军号、战马、大刀、炮弹、鲜血、雷霆、闪电、暴风、骤雨、大海、高山、长城,等等,显得激越高昂,充满着斗争的火药味和进取的精神。这是因为人民的斗争鼓舞了柔弱的诗人,时代的曙色使他们的歌声充满了希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光彩和力度。40年代诗歌意象化与诗歌朗诵化、民间化、散文化、形象化相一致,都注重向大众化、民族化靠扰,所以与二三十年代意象化诗歌相比较,它少了些含蓄朦胧,多了些清新、明朗。胡风曾在1944年给同仁的信中说:“今天的诗确已到了危机,非竭力求新生不可,……不能不求意象的明晰。”[①f]那时绝大多数诗人把象征、现代诸派强调表现瞬间的感受,表现梦幻和下意识的精神状态,把诗写得“异常晦涩暧昧,使人几疑为‘天经’之类”,视为“诗歌的绝路”[②f]。因而他们在诗歌创作中力矫此弊,力求抒情意象明朗、清丽,其大多数诗作并不标示绚丽秀美的形式,更不故作迷离朦胧,借用胡风的话来说,说是“努力用自己的方法向民众突进”[③f]。有些诗人为了诉诸大众,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在诗歌意象营造时,往往跳出来解释或说教,这就使很多诗歌意象完全透明,没有了诗的味道。意象化诗歌一旦失去隐藏与透明之间的把握力,不能使有形的语言渗透无形的语言,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魅力。我们看到相当多的诗人在创作的时候有意地借助意象,然而他又自觉不自觉地用自己透明的话语消解了它,破坏了很多美好的感觉和情趣。过分的透明恰恰是失真和虚伪,空洞无物最透明。40年代意象化诗歌与二三十年代意象化诗歌相比较,还少了些欧化色彩,多了些古典韵味。诗人们更注重从传统诗歌中吸取养分,从古典诗歌的意境创造中获得启迪,他们诗歌中的很多意象都是从古典诗词沿袭过来的(当然有些已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他们诗歌的意象营造方式也更接近于古典诗歌。他们在中国新诗的中西融合的道路上,比以前更侧重于传统的借鉴。这就使40年代的意象化诗歌具有了更加浓厚的民族色彩。总之,较之二三十年代偏于诗歌意象探索的象征、现代诸派,40年代诗人的意象化抒情显得更加成熟、更加中国化了。同时,40年代诗歌的意象化运动,比之其它诗歌运动,更注意诗歌本体建构,它对于中国新诗的表现方式向着更加艺术化的方向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注释:
①a 参见吴晓《意象符号与情感空间》第16~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①b 袁哥嘉:《新诗戏剧化》,《诗创造》1948年第12期。
②b 唐湜:《飞扬的歌·后记》。
①c 唐湜:《辛笛的〈手掌集〉》,引自《新意度集》。
②c 唐湜:《辛笛与敬容》,引自《新意度集》。
③c 艾青:《诗论》。
④c 艾青:《为了胜利——三年来创作的一个报告》,《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
①d 唐湜:《论意象》,1948年《春秋》,引自唐湜《新意度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
②d 冯至:《十四行集·再版序》。
③d 唐湜:《杜运燮的〈诗四十首〉》,《文艺复兴》1947年9月号,引自《新意度集》。
①e 贝尔:《艺术》第155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
②e 唐湜:《辛笛的〈手掌集〉》,引自《新意度集》。
③e 唐湜:《搏求者穆旦》,引自《新意度集》。
①f 《诗垦地》第5辑扉页。
②f 任钧:《新诗话·新诗的歧路》。
③f 胡风:《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