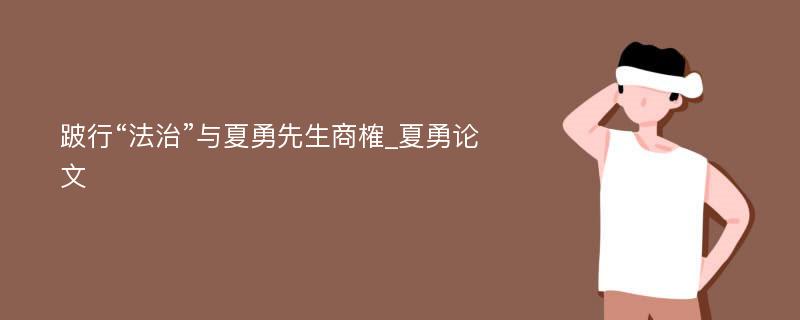
跛了脚的“法治”——与夏勇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治论文,夏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0—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914(2006)02—0003—(07)
夏勇先生是我国当代法学界中十分优秀的学者,也是我的老师;他的文章与为人,都是为我辈所十分钦佩的。但2001年上半年,先生在《读书》第5期所谈到的“法治与公法”问题,看后始终让我有如梗在喉之感。[1] 尔后,在先生所编的《公法》第2卷的“编后小记”中,我再次看到了同样的文字。[2] 如果说我第一次看到夏勇先生这种论述的时候,还仅仅是有一种个人的所谓“不吐不快”之类的感受的话,那么,当我不断地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它就似乎给我增添了一种使命感,觉得有必要将这个问题弄个究竟。
夏勇先生在论述了法治与公法问题后,最后运用领袖式的语气得出了一个结论:“法治既是一个公法问题,也是一个私法问题。但是,归根结底,是一个公法问题。”
果真如斯乎?
一、法治有可能分为“私法意义上的”和“公法意义上的”吗?
夏勇先生在《法治与公法》的开篇便说道:“大体说来,法治可以分为私法意义上的和公法意义上的。”但是,法治真的有可能被分为“私法意义上的”和“公法意义上的”吗?
我们就从夏勇先生所说的“相对说来要容易些”的“私法意义上的法治”说起。夏勇先生说:“私法意义上的法治相对说来要容易些。因为大凡有权威与秩序的地方,无论依习惯法,还是依国家法,私人之间的纠纷‘一断以律’乃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皆是不难做到的。倘若断案的公权者挟私偏袒,便提出了一个公法问题。”[2]
这是在说近现代意义上的私法吗?对私人之间纠纷的处理,“一断以律”也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好,这不是一个诉讼法上的问题吗?一般说来,诉讼上的问题,在近现代以来,不是已经作为一个以司法救济为主导下的“公法”问题了吗①?按照上述逻辑来看,判断公法和私法的标准就成为“断案”是否符合公平和正义了,这样的结论当然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看来,先生在这里还是没有明确到底哪些是“公法意义上的法治”,哪些是“私法意义上的法治”。
而且,就“权威与秩序”的形成来看,不论是法治社会还是人治社会,都可以形成;有时候,甚至人治社会下的典型即专制,更容易建立起权威与秩序——只不过,有这种“权威与秩序的地方”,人们的生活缺乏自由意志罢了。更何况,即使是在一个专制社会,为了维护一种专制下的秩序,“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之说的时候,也总是存在的。因此,不论“断案的公权者”是“取直”也好,还是“挟私”也好,它自然都是一个“公法”问题。
我们再来看夏勇先生所说的“的确难办些”的“公法意义上的法治”。先生说道:“在公法领域讲求法治,自然有两种不同的讲法。一种是着重讲政府要依法办事,老百姓要服从法律,以吏为师。与之相应的是,法律被看作公权者的命令,于是,朕的意志或统治阶级的意志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法律。另一种是着重讲公权者要服从法律,居于法律之下而不是法律之上。与之相应的是,法律被看作体现宇宙大道、自然法则、人类理性或民族精神与传统的公共法则,或者说,是立于公权之上的公理。简言之,前一种法治重在治民,后一种法治重在治官。所谓‘难办些’的法治,正是这后一种。”[2]
但是,这是在说“法治”吗?治民也好,治官也好,皆以“治之”导之,乃“法制”而非“法治”也②。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尝言:“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3](P199) 即所谓“共遵良法”。这就包括了法治的两个方面含义:一是先有良法;二是共同遵守——即法律的服从问题。夏勇先生在这里所谈到的,老百姓“以吏为师”服从法律,是一个法律的服从问题;公权者“居于法律之下”服从法律,也还是一个法律的服从问题。因此,说来说去,还是一个法治的“半边户”,或者说是跛了脚的“法治”。因此,诚如先生自己所言:“如果法治的价值仅仅在于严格地执行法律,而不问法律是怎样制定的,不问执行的是什么样的法律;如果法治的功能仅仅在于维护必要的社会秩序,而不问秩序是怎样构造的,不问维护的是什么样的秩序,那么,我们为什么非要追求法治不可呢?”③
说实在的,如果不管是“良法”或是“恶法”,仅仅强调服从法律,那么,“以刀为治”之“法制”,在短期内或局部,是最为有效的。然而,“以水为治”之“法治”,讲求的法律之自然属性,它以人性为基础,体现的是人类的共同理性,这却又不分是“立于公权之上”还是“立于私权之上”。可见,以先生之说而论,要在法治意义上区别“公法意义上的法治”和“私法意义上的法治”,何其难哉!
事实上,公法(Jus publicum)与私法(Jus privatum)作为一组对称概念,是罗马法学家关于法的基本分类。其目的在于说明,“公法”和“私法”是两个各自独立、互不干涉的法律部门。显然,这种分类建立在法学研究和相关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是一种静态意义的划分。因此,这种划分方法,也仅仅是在法学研究和法律制度层面上,才具有可能性。诚然,近代法在追求实现个人权利和体现自然理性方面,发现了隐藏在公私法分类体系背后的“国家——市民”二元结构的社会背景,但这也仅仅是在“权力——权利”的对抗中发掘了一些法治隐喻,我们实在是不能在“法治”的层面来区分孰为“公法意义上的”,而孰又为“私法意义上的”。
总之,从根本上讲,“法治”(Rule of Law)所表达的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方略,或者描绘了被治理的国家所处的一种状态。它是一个动态意义的概念,其相对应的概念是“人治”。如果法治的这种划分成为可能的话,从逻辑上讲,我们是不是要将“人治”也“大体说来”地划分为“公法意义的人治”和“私法意义上的人治”呢?!况且,即使是我们可以这样“大体上”将法治“一分为二”,然而,这种区分除了满足一下学者的分类嗜好以外,还有其他什么意义吗?
二、“德治”、“治德”与法律的道德性
接下来,夏勇先生从中西方人治与法治之争而论,认为终致德治之失败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历史条件所限,所谓“圣人不在天子位”;二是公法匮乏下的“德治”转化为“治德”。关于第一个原因,涉及所谓贤人政治,并非文章所要讨论的主旨,这里姑且不论。第二个方面的原因,他是这样论述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缺乏一套外在的、可操作的足以规制公共权力的法律体系和司法机制,换言之,是由于天德人道未能通过公法落实在法治上,只能通过教化落实在德治上。讲致善而疏防恶,究公理而匮公法,便难以约束公共权力,难以厘定政府行为的边界,于是,德治也就极易蜕变为‘治德’。一旦‘治德’成为一种国家治理方式,而非私人的修为,统治者就不会治自己的德,而是要去治别人的德;不仅要用法律来管制被统治者的外在行为,而且还要用三纲五常来管制被统治者的内在思想。到头来,便只能由那些缺德者讲德,无仁者讲仁,腐败者讲廉政了。”[2] 在这段论述中,夏勇先生实际上表达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德治之失败,在于公法匮乏,缺乏制约公共权力的法律体系和司法机制。另一种观点是,“讲致善而疏防恶”,于是“德治也就极易蜕变为‘治德’”;而“治德”往往容易导致“治别人的德”,最终也就导致“缺德者讲德”了。对于第一种观点,我大部分地同意;而对于第二种观点,我则与夏勇先生有着根本的分歧。
对第一种观点之所以说“大部分地”同意,是因为从长远来看,仅以德治来约束官吏和教化子民,终究难以获得制度化成就和基础,这是人治思想中的最大弱点。这也是东西方法律传统在“性善论”与“性恶论”之认识论基础上的不同,更是制约中国社会私法发展和私法文化形成的重要原因④。但我还有“小部分地”不同意,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德治之失败在于未行法治,而并非仅为未行“公法之治”;第二,我们不能以人治在总体上的失败而一概地否定其中的合理性因素。中国古代“德”观念比较复杂,主要关注人的自身能力的认识与开发,寻求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和谐与平衡关系。[4] 表现在治国理念中,也有不少合理且有现实价值的东西,如德治之中所包含的“德政”思想。所谓德政,乃以仁义为本,是指行“仁政”,即为王道,与“霸道”相对应。因为霸道乃以实力为本,不讲道义,也称作“虐政”⑤。不管是行仁政还是行虐政,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统治方式都是针对统治者或执政当局所提出来的。孟子说得好:“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5] 因此,行德政、仁政之说,实则也是对统治者的要求,强调治国之道应该以理服人,符合人的本性。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兮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福祸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5]
由是观之,连鸱鸮之国也知“彻彼桑土”,未雨绸缪,为什么我们一方面抱怨道德沦丧、世风日下,而另一方面对于德治之说又畏之如蛇蝎呢?人治社会,或为行仁政,或为行虐政,我们不能因为内心中存有对虐政的灾难性记忆而连仁政之下的积极因素也一抹而去,甚至从根本上去否定道德在社会转型和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有益的社会功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真的成了“恶辱而居不仁”,最后也就“自作孽,不可活”了。难怪一代启蒙先驱黄宗羲在《原法》中云:“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6] 其所谓“法外之意”,便是指道德、习俗、文化、环境等因素。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报道了一起女童落水事件。在该事件中,宁夏回族自治区某市副市长带领一行人马八辆轿车路经一乡村小桥,眼见一名女童落水而无一人下去救助⑥。从法律上讲,他们似乎也没有什么直接责任。因为现行法律语汇中的侵权行为、义务和责任等,都无法将这名12岁小女孩与这批“官员们”联系起来。然而,由这些语汇所构筑起来的“法治”能够平息人们心头的怒火,能够抹去人们内心的悲凉吗?如果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仅仅由这些僵硬的法律语汇所组成的话,那么我们的生活难道还有延续下去的勇气和必要吗?正如舒国滢教授所说,我们在颂扬法治的精神和理念的时候,应当看到它本来的界限。“把一切问题作为法治的问题来对待,甚至过分依赖法治的功能和作用,夸大法治话语的魔力,不是提升了法治的地位,反而可能是损害了法治的品格,销蚀了法治这种‘内在的、默默地起作用的力量’的应有权威和效力。”⑦
说到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人们在谈到德治的时候,经常爱引述孔子的一段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7] 也就据此认为夫子之目的在于使人民“口服心服”,追求一种所谓的“无讼神话”——“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8] 这也几乎成了后进国家、特别是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国家在现代化或西化过程中将责任推卸给历史文化的一个最好的说辞:中庸思想、厌讼心理、权利意识淡薄等等。但是,与我们同一文化区域的比较法学家则告诉我们,“一般说来,诉讼会吞噬时间、金钱、安逸和朋友,对东西方而言,都是一种常识。国民性中的所谓‘好讼’或‘厌讼’倾向之说,恐怕归根结底还是起因于学者的分类癖。”[9](P129) 因此,尽管孔夫子在追求贤人政治中存在一种法制浪漫主义情怀,但实际上,在追求一种大同社会的过程中,东西方未尝又不是一样的呢?!甚至是在今天,我们谁又能够放弃对这种理想状态的美好想象——即使是它仅仅停留在人们的想象之中。
当然,强调道德的社会功能,也无意表明我们要舍法治而求德治。德治与法治,毕竟不是同一层面的概念。本文旨在说明,我们在推行法治的同时,同样要借助道德对社会的磨合和建构作用;特别是对于一个转型时期的社会而言,在法律制度本身存在大量失范现象的时候,道德的社会意义尤其不容忽视;更何况,法律本身、特别是私法,就具有很强的道德性。因此,实际的问题不是我们是否需要讲道德的问题,而问题是我们应当将道德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就涉及到我与夏勇先生存在根本分歧的先生的第二种观点——即由“德治”转化为“治德”到“治他人之德”的问题。
在夏勇先生的第二种观点中,他对“德治”向“治德”问题的转化表现出了明显的担忧,喻之谓“蜕变”。恰恰相反,本人认为,如果“德治”果真能够实现向“治德”问题的转换的话,那么这应该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因为,如果说“以德治国”作为一种治理国家的方略与“以法治国”的提法还存在着一定的需要消弭的冲突的话,那么“以德育人”(即“治德”)的内在含义则与法治国的理念相互和谐一致。
在法律之外,讲求个人(私人)的修身养性,我们很容易理解。事实上,霍姆斯(Holmes)法官早就说过,“尽管我们很多人不以为然,但道德的实践乃是致力于造就善良公民和好人”。[10](P459) 以德育人强调将道德融入法律之中,以便使法律生活与治德育人形成一种互动关系。这一点,在合同法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我国统一《合同法》第6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③ 这里的“诚实信用”条款,就是一个道德性原则,但它却体现在合同订立之前(先契约义务)和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或撤销、以及合同后的附随义务等之中。当然,从对人的行为加以引导方面来说,更为直接的是侵权行为理论。我们姑且不论早期侵权法以自然律、道德解释为基础,即使在现代侵权行为理论中,道德与伦理解释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理论依据⑨。这是因为,法律仅仅只能规范看得见的或能够被证明的行为,而不能规范那些看不见的或无法被证明的行为,更无法去审视人们的内心世界。但是,要促成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和社会的良性发展,又不能只靠那些看得见的或能够被证明的行为规范。它同样需要那些只是凭借“道德良心”的行为,特别是需要将法律规范的外在行为内化为人们内心(潜意识)中的道德律。否则的话,在人类身上浇铸了利益之火的法律,便会将我们的社会变成一个血淋淋的“人肉场”。正因为如此,“在现代化市场经济条件下,诚实信用已成为一切市场参加者所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它要求市场参加者符合于‘诚实商人’的道德标准,在不损害其他竞争者,不损害社会公益和市场道德秩序的前提下,去追求自己的利益。”⑩ 由此,我们的法律才有了它本身的道德性基础;也由此,信用社会才能够逐渐形成。所以说,道德修养绝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它同样可以法律化,同样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遍性基础。
诚然,并不是所有的道德准则都能够被法律化。实际上也并不需要做到这一点。张恒山教授认为,道德包括道德心理、道德行为和道德规则,而法治中谈的道德主要是道德规则。道德规则可以分为四个层面:第一是禁止损害他人;第二是倡导利他;第三是劝导人自我行为完善;第四是引导人自我精神完善。第一个层面是一种底线道德,只是这种底线道德交给了法律,但它仍具有道德性(11)。而按照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1874—1928年)的观点,纳入法律的道德是建立在人本主义仁爱基础上的,这种仁爱学说舍弃了基督教“爱上帝并爱每一个人”的律令,不是为了仁爱本身和人的自由的爱的能力而要求人的福利;相反,它所倡导的仁爱的目的只是为了人类的福利本身。这一点,在古典的或基督教的仁爱学说看来,是一种“价值的倾覆”(12)。因此,从价值论的角度看,需要被法律化的道德只是那些同人与人之间或人类整体的福利相关的部分。只有这种道德的法律化才有必要,也应当以此为限。超越了这种界限,比如将属于个人信仰的部分也加以法律化,就可能走向真理的反面。然而,法律如果失去了自己应当具有的道德性,只是为了人的肉身而存在,也就最终会失去自己。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年)将法律与“正义”、“正确理性”几乎是同等地加以看待。他说:“如果只是对刑罚,只是对惩罚的恐惧,而不是邪恶本身,才使得人们躲避不道德的生活和犯罪的话,那么就没有人可以称之为不公正的人,而且更应视恶人为不谨慎的人;进一步说,我们当中的那些并非由于美德的影响、而是出于一些功利和收益的考虑而成为善者的人,就只不过是胆小鬼,而并非好人。”(13) 也正因如此,查士丁尼(Flavius Anicius Justinianus,485—565年)的那一道德警句才会成为千古不变的法律原则:“为人诚实,不损害别人,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
分。”(14)
另外,在中国古代社会,“治德”也并不意味着“统治者就不会治自己的德,而是要去治别人的德”。恰恰相反的是,在治德问题上一直就存在着“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思想,强调“礼不下庶人”。当然,这其中所包含的“贱民”思想,又另当别论了。
三、法治价值的实现:公私为谋,德法兼备
再往后,夏勇先生从公法和私法两个方面谈到了法治的价值问题。而于此之前,先生在法治工具价值方面的论述,是先生另外一篇关于法治方面论文的一个简述。[11] 这些论述,很难与作者在这里所要论证的结论联系起来。先生认为,法治之发达首先在于公法意义上的法治之发达,私法意义上的法治也有赖于公法之发达,并据此得出本文开篇所谈到的法治归根结底是一个公法问题的结论。他说:“治理之发达,在法治之发达。法治之发达,在公法之发达。这种法治当然首先是公法意义上的法治,而且是着重规制公共权力的法治,着重治官的法治,着重维护受治者的尊严与自由的法治。”[2] 这段话表明,法治的一个重要目标就在于制约公权力,而且法治与公法之间存在着一种成正比或正向关系。无疑,这一点是对的。但是,它不一定就能够得出公法优位的论点。诚如先生所言,“公法意义上的法治”在于解决三个问题:“规制公共权力”、“治官”、“维护受治者的尊严与自由”。前面两个问题,一是公法规制之客体,一是公法规制之主体,它们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我们便可以将“公法意义上的法治”问题简化为两个:制约公共权力之行使;维护受治者的尊严与自由。在这两个问题中,前者是对公权力行使之行为的制约,而后者则是这种法律规制行为的结果延伸;换句话说,前一个问题是一个工具性的问题,而后一个问题则是目的性的问题。
当然,手段与结果、工具与目的在大的方面应当具有一致性。但现实的结果,却并非完全如此。由此,就凸显出公法问题之重要:使手段和工具之指向均与其所要追求的结果和目的协调一致。因为社会契约论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在于:“要寻找一种结合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12](P23) 而由每一个订约者缔约而产生的“共同体”、“城邦”或“国家”,虽然因此也形成了“公共人格”,但毕竟这种公共人格建立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和保障每一个个体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是个体人格得以充分实现的手段而已。个体人格的实现,也就是指作为个体生活的普通老百姓有尊严地自由生活的一种秩序状态,是公法所要维护的所谓“受治者的尊严和自由”。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在分析那句乌尔比安(Ulpianus,170—228年)提出的、后来为查士丁尼所采纳的法律原则时,就曾说道:“给各人属于他的东西”的说法是“荒唐的”,因为我们不能把任何人已经有的东西再“给”他。因此,康德认为如果要明确这句话的含义,它只能是这样:“进入这样一个状态吧,在那儿,每人对他的东西能够得到保证不受他人行为的侵犯。”[13](P48—49) 这种分析,初看起来觉得有些矫情,但仔细想来,也颇有道理。因为在“给”的情形下和后面康德所描述的那种“状态”中,公权力是处在两种不同地位的:前者是一种主动的“施予者”或“主人”的位置;后者状态中,公权力是一种被动的“服从者”或“人民公仆”的地位。这种不同的描述,反映着一个社会的不同的价值取向。
同时,个体的尊严与自由绝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靠点滴的规则和制度运作来实现的;而这些点滴的规则与制度,就是私法规范的范畴。因此,在公法意义上的两个法治问题中,“制约公共权力之行使”是具有实质意义的,而“维护受治者的尊严与自由”是目标指向性的。也就是说,前者才是公法意义上的主要内容,而后者则是前者所要解决的问题之指向,是解决前面问题所希望发生的结果状态——也只有它,才是法治价值所要实现的真正目标。这样,我们便可以从宏观上认为,公法是具有工具性和手段性的,而私法则是具有目的性和结果性的(15)。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事实上已经开始走出目前法治观念的一个误区,即往往从政治哲学角度来理解法治的含义,而较少从人们的社会或日常生活角度去进行探讨(16)。从日常生活角度而言,人类生活由个人而至群体;先家庭,尔后及于社会。虽然由于政治国家的组织形成与强化,致使在现代法律体系中宪法作为顶层的国家根本大法,但从法律观念与制度演进而论,私法乃社会生活之根本大法。因此,有的学者也认为,公法上之主体与客体、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等观念,究其根本,莫不导源于“私权规范的民法思想扩张之、强化之、光大之”。[14](P4) 以此而论,政治哲学上的法治,在推翻专制统治时期具有重要意义,但一旦确立了民主政体,法治问题的重心就应当转移。因为在社会普通生活层面上,人们所关心的是如何获得、利用或转让财产,并且如何有尊严、有人格地生活着。而一部西方法律发达史也告诉我们,“发展得最完善、最引人注目、最为学者所看重并致力于研究和开拓、最有力地推动社会发展、最深入人心、影响人们思维与行为的法律非私法莫属”。[15] 因此,我们今天谈论建构法治国家,已经不是在于提高是否建构法治方面的智识,而是如何去建构的问题;而具体的规则与制度的建构,应当以私法规则的逐步形成与确立为主导(17)。
当然,夏勇先生所言者,意在于强调我国目前法律环境下制约公权即“治官”之重要性,也意在为我国现阶段法治化进程卸下沉重的传统文化包袱。的确,从手段或方法论意义上讲,法治之核心价值就是对公权者形成有效的制约,在于解决有权者依法行使权力的问题。同时,传统儒家文化造成我国法律伦理化倾向,也似乎一直是影响着我国法律现代化进展的重要因素。但是,这毕竟只是“硬币”的一面,它无法就必然地导出“公法优越论”的观点,也不是我们据此而忽视道德对社会的建构作用的理由。因为无论硬币的这一面是国徽也罢,是领袖形象也罢,其用意无外乎是强调这一“货币”的信用和它背后的支撑力。然而,货币的目的在于流通,在于经济生活之基础,在于老百姓日常生活对它的信心指数。岂不闻康熙大帝面对长城尝言“在德不在险”之语?所谓“众志成城”呀!无独有偶。《史记》有载,春秋时期魏武侯也曾志得意满地示山河之险固于人,但吴起则比之以“三苗氏”、夏桀、殷纣等事例,最后说道:“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18) 所以,依法治国,看似涉政体之“国事”,但实则应以“民事”为本;建构法治,虽以法律制度为要,但也应兼顾治德育人。诚所谓公私为谋,德法兼备,方能共襄国事;不然,便是一个跛了脚的“法治”。
收稿日期:2005—11—24
注释:
① 诉讼法的归属问题,即属于私法还是公法的问题,在罗马法学和近现代法学中有着不同的分类。在罗马法学中,诉讼法、特别是民事方面的诉讼,是一个私法问题。但在近现代以来,人们认为诉讼事实上是一种涉及国家与个人关系的规范,已经归为公法问题。参见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编委会编:《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制史》中“私法”词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745页。
② 我们通常所说的“法制”主要是指法律制度,它“距法治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参见卓泽渊:《法的价值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第250页。
③ 其实,先生在他的另一篇谈论法治方面的文章中,也说到过同样的观点。他认为这种绝对工具主义的法治观只是看到了法治的外壳,而无视其精神。参见夏勇:《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第134页。
④ 在最近的一篇讨论“性善论”对我国法治具有消极影响的文章中,作者认为性善论把人视为“义务人”而非“权利人”,进而压抑了现代民法在中国的培育。参见郝铁川:《“性善论”对中国法治的若干消极影响》,载《法学评论》2001年第2期,第20—24页。
⑤ 其实,有的学者还认为,孟子关于行仁政的思想并没有专门从人治立场出发而论,它与人治或法治的理念,都是有可能相容的。这是一种较有见地的看法。但是,本文的论述是在另外一种语境下(或者说是在与法治相对应的意义上)谈论德治问题,不拟在这个层面上进行探讨。参见周天玮:《法治理想国——苏格拉底与孟子的虚拟对话》,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10月第1版,第176—177页。
⑥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在2001年12月1日星期六早8:35—8:50以“当孩子落水的时候”为题进行了报道,报道中也采访了当事人之一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的那位副市长。令人欣慰的是,据后续的相关报道称,那位副市长最终还是受到撤职处分,其他当事人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理。在这一事件,不仅表明道德在社会治理中本身就客观存在,而且反映了人们在内心深处对人类道德良心的普遍认同。
⑦ 参见舒国滢:《法治是什么?》,载《中山大学法律评论》1999年第1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299—230页。饶有趣味的是,舒国滢教授在将此文收录论文集时,将文章题目更名为“法治不是什么?”以愚人拙见,大约也是意在强调法治的局限性。参见舒国滢:《法治不是什么?》,载舒国滢:《在法律的边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171—174页。
⑧ 参见1999年3月15日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这种原则规定同时也出现在其它法律文本之中,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⑨ 在一部收集了侵权行为法现代理论的论文集中,道德论作为一种传统的解释方法,仍然是一种重要学说,而且还根植在其他诸如分配正义论、救济论等之中。特别是,马丁·斯通(Martin Stone)的《侵害与受害的意义》(The Significane of Doing and Suffering)文和朱里斯·克里曼(Jules Coleman)的《侵权行为法和侵权行为理论——关于研究方法的初步思考》(Tort Law and Tort Theory:Preliminary Reflections on Method)文,还对经济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有力的抨击。关于各种理论以及相关论述,See Gerald J. Postema ( Edited),Philosophy and The Law of Torts,U.S.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中文译本,参见[美]格瑞尔德·J.波斯特马主编:《哲学与侵权行为法》,陈敏、云建芳译,易继明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⑩ 参见梁慧星:《民法解释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第305页。郑强博士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曾对《合同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专门研究,并从道德心理、法律规范和客观事实三个层面对该原则加以分析。关于郑强博士的论述,参见郑强:《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研究:帝王条款的法理阐释》,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第14—15页。
(11) 这是张恒山教授于2001年11月29日上午在中共中央党校向学员们讲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专题时提出的观点。在他最近出版的著述中,张恒山教授以三人社会模式为基础,对具体道德规则与行为进行了论述,并认为道德规则转化为法律规则的条件是:“当人们感到某些规则是如此之重要,以至不遵守这些规则,人类社会就无法继续存在,从而产生要求社会组织起来的权力来强迫人们遵守这些规则,这些规则就转化为法律规则。”参见张恒山:《法理要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第98—129页。
(12) 参见[德]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论价值的倾覆》(Vom Umsturz der werte),Leipzig,1919。
(13) 参见[古罗马]西塞罗:《国家篇·法律篇》,沈叔平、苏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8月第1版,第162页。又参见另一中文译本[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第200页。
(14) J.1,1,3.中文译本见[古罗马]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法学阶梯》,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12月第1版,第5页。徐国栋教授将之译为:“诚实生活,毋害他人,分给各人属于他的。”又参见[古罗马]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徐国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11页。
(15) 当然,这种手段与目的关系上的宏观区别,并不排斥二者之间的相互依存的“互惠”特点。特别是一些公法上的权利如选举权,尽管也是以实现民众具体的自由生活为终极目的,但往往在这个过程价值的实现过程中,也体现为本身的目的性。
(16) 就笔者所见,目前我国学者关于法治问题的论述,大多数都是从政治哲学角度来探讨的。笔者在这里也并非想否定这种探讨的价值,只是要说明法治的含义还应当或者说更多地要从人们的日常生活角度来理解。当然,最近贺卫方教授提出“具体法治”的概念,尽管这种提法还不是建立在对老百姓的世俗情感和日常生活的表达上,但这似乎也是一种转化为“具体生活”的很好的开端。参见贺卫方:《具体法治》,法律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17) 诚然,在具体法治的思维中,并不排斥(而是包括)公法领域进行一些“具体法治”式的改革,例如公共事务的具体议事规则,甚至包括议事的场所。人治社会,特别是权力较为集中的国家,一些军国大事往往是在某位领导人家里决定的,招来两三名同僚,在家里进行商议,拟定决议和方案。尽管最后的出台可能还是通过了某一形式,但这一通过形式并不具有实质性讨论和协商的功能民主的外衣而已。因此,诸如这种议事场所的规定,在中国可能都是“具体法治”的一部分。本文这里只是强调,在和平时期的宪政体制下,市民法规范和私人交往行为的形成,应该是更加重要的一种具体法治。
(18)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曰:“善。”
当然,就吴起本人而言,后来相楚成事而亡,则又另当别论。太史公有言:“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参见[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