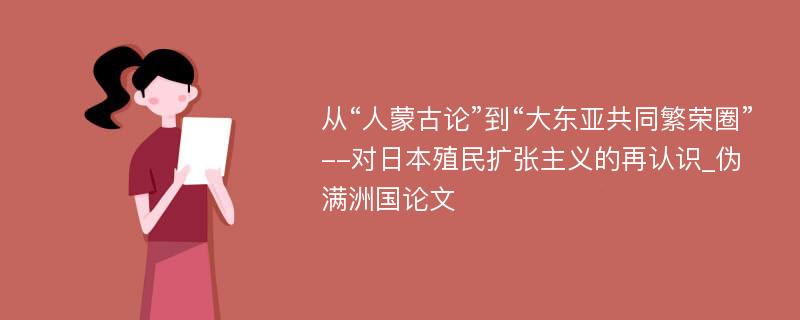
从“满蒙领有论”到“大东亚共荣圈”——对日本殖民扩张主义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扩张主义论文,再认论文,东亚论文,日本论文,共荣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满蒙领有论”和“大东亚共荣圈”,常见于各种史学论著,人们对其并不陌生。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史学界,对“满蒙领有论”的始末及其日本对满洲政策的演变,还缺乏深入的研究,还存在一些诠释上的片面。对“大东亚共荣圈”构想形成的经纬、它的区域范围的演变,也还缺乏系统的论述和探讨。至于日本殖民主义者为了实现这一构想而专门设立的组织——大东亚建议审议会,以及审议会制订的一系列殖民扩张主义方案,据笔者管见所及,更是几乎无人论及。为了进一步认清从“满蒙领有论”到“大东亚共荣圈”这一本世纪日本殖民扩张主义的重要内容及其本质,深化对日本殖民主义、军国主义侵略政策的研究,笔者谨根据自己的学习收获,拙作了此文,以就教于学术前辈和同人。
一
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如笔者以下所述,是“以帝国(日本)为核心,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主干”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占领满洲——中国东北地区,实际上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构想的一个重要前提。因此,对“满蒙领有论”的出笼以及日本对满洲政策的演变的探讨,理应成为本文的切入点。
占有满洲——中国东北地区,是日本“明治大帝的遗业”和殖民扩张主义分子由来已久的梦想。早在1905年,任职于日本参谋本部的小矶国昭(以后担任了日本首相),就在他题为《帝国国防资源》的考察报告中专门列了“支那国产原料”一项,提出“为了进行总体战,必须从中国获取原料和资源”,并认为确保从满洲获得原料和资源,是进行“总体战”的前提。1918年日本颁布的《军需工业动员法》也提出,如不能一举将中国全境纳入日本的“自给自足经济圈”,则应首先“领有满蒙”。但在当时,以东三省为焦点,日本欲将满蒙作为“特殊地区”从中国分离出去,并在那里获得排他性权益的政策和行动,同中国五四运动后高扬的民族主义,发生了尖锐冲突。为了维护在以往的侵略扩张中已经获得的权益,实现其预定的目标,1927年6月1日,日本关东军提出了《关于满蒙问题的意见》,强调为了“日支共存共荣的旨趣”,必须扩展在满蒙的权益。如果张作霖对此不予配合,则应由其他“适任者”取而代之,并因此而在1928年6月策划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
然而,日本关东军试图以此一举解决满蒙问题的图谋不仅没有得逞,反而引起了更强烈的反抗。另一方面,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与对东北地区缺乏支配力的南京国民政府的交涉,又以失败告终。日本的满蒙政策,受到了重大挫折,不得不探寻新的路径。1929年5月,日本关东军情报会议决定,通过武力占领解决满蒙问题。以此为背景,在“皇姑屯事件”余烬未消时出任关东军主任作战参谋的石原莞尔,于1929年7月5日在《作为恢复国运之根本国策的满蒙问题解决策》中,提出了著名的“满蒙领有论”。
据分析,石原莞尔提出“满蒙领有论”,除了为维护日本的“既得权益”外,更出于以下目的:
(一)克服经济危机。“对满蒙的合理开发”,有助于克服爆发于1929年并波及日本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使日本恢复“景气”,触燃眉之急。更重要的是,这种“开发”还能为日本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充分的基础。
(二)形成“自给自足的经济圈”。如前面所述,日本早在1918年颁布的《军需工业动员法》中即提出,若不能将中国全境一举纳入日本“自给自足经济圈”,则应首先“领有满蒙”,然后占领整个中国。石原莞尔的满蒙领有论,实际上就是这种构想的继续。
(三)巩固在朝鲜的殖民统治,防止“赤色传播”。1924年,板垣征四郎曾经在《从军事上认识满蒙》中提出,“一旦俄国人跨越国境,那么占领朝鲜就将是时间问题”,强调为了抵御来自俄国的威胁,巩固在朝鲜的统治,必须占领满蒙。而石原莞尔的“满蒙领有论”,除了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外,还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简而言之,“领有满蒙”具有防止苏联威胁,巩固在朝鲜的殖民统治和形成防止“赤化”隔离带的双重功效。
(四)为日美开战做战略准备。早在1927年,石原莞尔就已预言,日美难免一战。按照他的看法,“支那问题,满蒙问题,不仅是对支问题,而且是对美问题。如果没有战胜美国这个敌人的意识,那么想解决满蒙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注:参阅[日]角田顺编:《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1967年版,另参阅[日]山室信一:《怪兽客迈拉——满洲国的肖像》,中央公论社1993年版,第26-54页。)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日本挑起了九一八事变,并在1932年3月1日扶植建立了由关东军首脑和日本官吏操纵的傀儡国家——满洲国。毫无疑问,满洲国也具有与台湾和朝鲜相似的殖民地性质。然而值得关注的是,虽然“领有满蒙”对日本极其重要,但是日本却没有像在台湾和朝鲜那样,在满洲也建立完全的殖民统治体制即总督制,而是让溥仪当上了元首并进而在1934年让他当上了“皇帝”,其原因究竟何在?
不少学者认为,日本所以这样做,主要是由于占领满洲和占领台湾、朝鲜时的国际形势不同,即外在压力迫使其改变了原来的政策。(注:[日]驹近武:《殖民地帝国日本的文化统合》,岩波书店1996年版,第132页。)但笔者对此类观点存有异议。因为我们不难发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侵略扩张行动所以能一时较顺利地进行,正是由于事变发生时的国际局势和中国的国内局势,对日本比较有利:当时,英美正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无暇东顾,利用国联发出的所谓“警告”对日本根本没有约束力。(事实上,日军不仅没有在受到“警告”后撤出占领区,相反从山海关进入热河,扩大了占领区。日本在1933年3月28日退出国联,则更是无视这种“警告”的反映。)苏联当时正致力于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因专心“内治”而对中日间的冲突发表了“中立和不干涉”声明。另一方面,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为了全力围剿共产党,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采取了不抵抗主义。而拥有25万兵力的东北军一则由于当时11万主力集结在长城以南,余部也散在各处,难以迅速调动,二则由于接到了张学良为避免扩大战火而发出的不抵抗和撤退命令,因此没有迅速进行有力反击。简而言之,事变时的局势并不是阻碍日本“领有满蒙”的关键。按绪方贞子的研究,当时“英国政府甚至认为,由日本政府而不是中国军阀统治满洲,无论是从文明的角度还是从英国利益的角度考虑,都是适当的”。(注:[日]绪方贞子:《满洲事变及其政策的形成过程》,原书房1966年版,第8页。)
也有的学者认为,九一八事变爆发“军部中央得悉关东军的行动后,立即予以支持,并要求增兵中国东北”,但是“内阁决定采取不扩大事态的方针”。(注:赵建民、刘予苇主编:《日本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65页。)但这种解释似与历史事实不符。因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陆军中央鉴于尚未完全建立军部独裁和“总体战”体制,尚未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因此即派遣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前往关东军,让他转达了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不扩大事变”的指令,并提出“应建立以宣统皇帝为首、得到日本支援的政权”。正是在军部上层人士的干预下,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和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等经过磋商,于1931年9月22日,即事变发生后第四天,提出了《解决满蒙问题的政策和方案》,主张“在东北四省及蒙古,建立接受我国(日本)支持、以宣统皇帝溥仪为首脑的支那政权”,放弃了原先的“满蒙领有计划”。(注:见[日]山室信一:《怪兽客迈拉——满洲国的肖像》,第64页。)也就是说,军队内部的意见分歧,是促使日本调整满蒙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1931年12月23日,日本政府发布了《省部协定第一案》,决定“先使满蒙成为从支那本土政府中分离独立出来的政府统辖的地域,然后逐渐引导其成为帝国的保护国”。随着若槻礼次郎内阁的倒台和“币原外交”的结束,上述政策最终成为日本的国策。“满洲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至于日本让溥仪在1934年3月“称帝”,则是为了“使满洲国的国家机构和政治形式,不和日本有显著差别”,使满洲国“一切守国之远途,经邦之长策,均和日本帝国协力同心”。(注:[日]蜡山正道:《帝制满洲国的世界政治意义》,载《改造》1934年4月号。)总之,虽然“满蒙领有论”的放弃和“满洲国”的建立,仅仅是日本殖民主义分子所作的一种策略上的调整,既不意味其收敛了“领有满蒙”的野心,也没有改变“满洲国”的殖民地本质,但它对我们理解为什么日本在几年以后才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却不无意义。
二
随着日本军部独裁和“总体战”体制的形成,以1937年卢沟桥事变为开端,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军国主义者久有的称霸野心,也随着这场战争而急剧膨胀。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了“第二次近卫声明”,提出要“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建立“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构想,开始正式登场。(注:[日]安部博纯:《“大东亚共荣圈”构想的形成》,载《北九州大学政法论集》第16卷第2号,1989年1月。)
1940年初,根据军务局长武滕章的建议,日本政府委托国策研究会着手研究《综合国策十年计划》,以后又转交企画院继续研究并在同年6月制订了这一计划。(注:[日]《大本营陆军部·大东亚战争开战经纬》,载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战史丛书》,韩日新闻社1973年版,第335至338页。)该计划由四个部分构成,即“第一,基本国策;第二,外交及国防;第三,内政事项;第四,日满华事项”。特别在“第一,基本国策”中,该计划明确提出了以下三个目标:“一、布皇道于八紘,通过民族共荣,万邦共和,求得人类福祉的增进和世界新文化的生成发展。此乃肇国之理想,我民族担负之使命。”“我国的最高国策是以帝国为核心,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主干,建设大东亚协同经济圈,以达到国力的综合发展。”“我协同经济圈的范围,是东西伯利亚、内外蒙古、满洲、中国、东南亚细亚诸邦和印度及太平洋。”(注:[日]吉川隆久:《昭和战中期的综合国策机关》,吉川弘文馆1992年版,第148至149页。)不难发现,这里所谓的“协同经济圈”,已经具有了含义特定的“大东亚共荣圈”的雏形。
1940年7月19日,即第二届近卫内阁正式成立前夕,近卫文麿和将就任新一届政府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外务大臣的东条英机、吉田善吾、松冈洋右,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史称“荻窪会谈”,就日本的基本国策达成了共识。7月22日,近卫内阁正式宣告成立。7月26日,内税会议根据《综合国策十年计划》和“获窪会谈”的精神,制定了《基本国策纲要》,针对当时的局势,提出了作为国策基本方针的“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构想,即“皇国之国的根本,是以八紘一宇之肇国大精神为基础,迎接世界和平的确立”,“是建立以皇国为核心,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主干的大东亚新秩序。”同时,根据7月27日政府大本营联络会议提出的《顺应世界形势变化之时局处理纲要》,规定“大东亚”的范围,除了通常人们所理解的日满华以外,还包括“南方”,并提出了“利用形势的变化把握良好的机遇,推进对南方行使武力”的方针。(注:[日]《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65年版,第435至438页。)至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基本形成。同时这一纲要还表明,日本已正式将“南进”政策提上了议事日程,开始了向南进体制的战略转变。
“大东亚共荣圈”作为专用名词的首次出现,是在1940年8月1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会见记者,正式发表《基本国策纲要》时。当时,松冈洋明确宣布,要“确立以日满华为其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注:[日]矢野畅:《“南进”的系谱》,中央公论社1975年版第156页。)此后,“大东亚共荣圈”这一提法,开始陆续出现于各种文件。例如,在同年8月27日的内阁会议上拟定的《小林特派使节携行对荷属印度交涉方针案》,以及在同年10月3日的内阁会议上通过的《日满华经济建设纲要》中,均明确写道,要“确立以日满华为中心、有南洋加入的大东亚共荣圈”(注:[日]《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440页。);“迅速发展以日满华经济的综合增长为基础的大东亚共荣圈”。(注:[日]石川准吉:《国家总动员史·资料编·四》,三铃书房1976年版,第1085页。)
综上所述,无论是“经济协同圈”、“大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还是以后的“大东亚经济圈”、“生存圈”、“生活圈”等,虽然提法各异,但其本质,却是始终不变的,事实上,它们所包含的地域范围的类似,也说明了这一点。
那么,日本军国主义者试图建立的“大东亚共荣圈”,究竟包括那些地域呢?据笔者考察,它所包含的地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国际局势及日本对外关系、外交方针的变化,它的区域范围也发生了一些不甚明显,但却是不可忽略的变化。
按照1940年6月制订的《综合国策十年计划》,“协同经济圈”的范围是东西伯利亚、内外蒙古、满洲、中国、东南亚细亚诸邦和印度及太平洋。这一范围,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初始范围。
1940年7月底至8月上旬,为了给日本正在实施的南进战略出谋划策,实现称霸“大东亚”的野心,小矶国昭撰写了一系列“意见书”,提出了建立“大东亚经济圈”的构想。在他的第一份“意见书”《帝国急需施行的政策》中,小矶写道:“应尽快将远东依存欧美的现状转变为远东自给,果断地进行大东亚经济圈的建设。”“大东亚经济圈的范围是,联合日满华、法属印度支那、泰国、马来亚、缅甸及荷属印度,结成东亚经济联盟,将来吸收菲律宾及大洋洲。”“换言之,本经济圈以东经90度以东、国际日期变更线(约东经180度)以西为范围。”(注:[日]《现代史资料·10·日中战争·3》,三铃书房1964年版,第146页。)同时,小矶国昭还提出建立该经济圈应分阶段实施;以日满华、法属印度支那、泰国、马来亚、缅甸、荷属印度为第一阶段,以其南北周边地区(包括菲律宾)为第二阶段。
1940年8月6日,企画院制订了《南方经济施策纲要》,提出了“为建设国防国家,形成以皇国为中心的经济性大东亚圈”的构想,并就“南方经济施策”的“轻重缓急”作了如下规定:“将施策重点放在法属印度支那、泰国、缅甸、荷属东印度、菲律宾、英属马来亚、波罗州、葡属帝汶等内圈地带,以英属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外圈地带为第二阶段。”(注:[日]《现代史资料·43·国家总动员·1》,三铃书房1964年版,第177至178页。)
在1940年9月6日的“四相”会议中议定,并在9月16日的日本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获得通过的《关于强化日德意轴心的文件》的秘密附件三《处理日德意提携强化之基本要点》,对“大东亚共荣圈”的地域范围,则作了如下规定:“在与德意交涉时,作为建设皇国大东亚新秩序之生存圈应予以考虑的范围,是以日满华为主干,包括原德国委任统治诸岛、法属印度支那及太平洋岛屿,泰国、英属马来亚、波罗州、荷属东印度、缅甸、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不过。在交涉上,我方提示的南洋地域为缅甸以东、荷属东印度新喀里多尼亚以北。另外,可原则上承认将印度置于苏联生存圈内。”(注:[日]《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448页。)
与《综合国策十年计划》中提出的“协同经济圈”、《帝国急需施行的政策》中提出的“大东亚经济圈”,以及《南方经济施策纲要》中提出的“经济性大东亚圈”相比,上述秘密附件中提出的“生存圈”的范围,有几点值得注意的变化:
(一)该秘密附件提出,为了协同德意对英作战,“应努力排除英国在东亚的权益,对英示威,支援英国属领及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因此,“生存圈”包括了属于英邦的广大地域。
(二)南进政策的实施,直接威胁了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根本利益,使日美矛盾急剧尖锐。为了避免过份刺激美国,使日本的预定战略得以顺利推进,秘密附件提出“对美国尽量采取和平手段”。因此,“生存圈”虽然包括亚太广大地域,但却不包括属于美国势力范围的菲律宾。
(三)为了消除南进的后顾之忧,限制苏联的对华援助,秘密附件提出应对苏联“从东西两方面加以牵制并尽力和德意采取相同的立场,尽可能促使其朝对日德意三国的利害关系影响较少的方面发展势力”,因此提出“可原则上承认将印度置于苏联生存圈内”。
与上述秘密附件相呼应,1940年10月3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由企画院起草的《日满华经济建设纲要》。该纲要提出,为了“通过综合一体地推进我国内体制的革新过程和生活圈的扩大形成过程,迅速建成国防国家”,“皇国之基本经济政策是:一、完成国民经济的重新组合;二、形成并强化自存圈;三、扩大形成东亚共荣圈”。特别是第二点,“纲要”明确规定,“通过以皇国之国防和地政学的地位为基础的日、满、华北、蒙疆地区同华南沿岸特定岛屿形成有机的一体化自存圈,即形成政治、文化、经济综合性的强化组合”,“建立包括华中、华南、东南亚和南方各地区的东亚共荣圈”。(注:[日]石川准吉:《国家总动员史·资料编·四》,第1085页。)至此,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构想,得以最终确定。1942年2月23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将“在大东亚战争目前之形势下,应由帝国指导建设新秩序的大东亚地区”,正式确定为“日满华及东经90度至180度之间、南纬10度以北的南北诸地区”。这样,“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也被最终划定。(注:[日]《彬山记录》(下),原书房1976年版,第88页。)
三
随着“大东亚共荣圈”构想的确定和向“南进体制”的转移,1940年9月,日本军队强行侵入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为此,美英荷等国家采取了冻结日本在国外的资产和禁止向日本输出石油的对抗性措施,双方的矛盾急剧尖锐。1941年2月,日本参谋本部着手制订了《南方作战占领区统治纲要》及《关于南洋作战中财政、金融、通货工作的根本理念》,准备进一步具体实施“大东亚共荣圈”构想。但是,由于随后日美谈判的开始,这些文件被束之高阁。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局势的变化,使日本最高统治阶层内部,出现了以外相松冈洋右为首,主张乘虚而入的“先北后南”论,和以陆相东务英机为首,主张等苏联呈败势后再坐收渔人之利的“先南后北”论两种意见的分歧。经过争论,1941年7月2日的“御前会议”通过了《适应世界形势之帝国国策纲要》,否定了“先北后南”论,决定“不管世界形势如何变化,帝国均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为方针”。
与此同时,随着日美谈判实际上的破裂,1941年7月,日军开始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并因此而开始正式走向太平洋战争。同年8月,日军参谋本部将束之高阁的《南方作战占领区统治纲要》重新放上桌面,并以这份文件为蓝本制订了《南方占领区行政实施纲要》。11月12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通过了这份纲要。11月25日,大本营陆军部又制订了《顺应南方作战进程之占领区统治纲要》。另一方面,以《南洋作战中财政、金融、通货工作的根本理念》为蓝本的有关经济政策,也得到了讨论。12月,日本政府制订了《南方经济对策纲要》。(注:[日]岩武照彦:《南方军政论集》,韩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至34页。)
根据上述“纲要”,日本军部首先将作为“协力地区”的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同其它占领区区别开来,决定:一、同原宗主国法国(维西政府)一起,对法属印度支那实行“共同管辖”;二、使泰国作为“独立国家”与日本建立“同盟关系”。三、对其它南方占领区先施行“军政”,并按照1941年11月26日制订的《关于占领区军政之陆海军中央协定》,划定了陆海军各自分管的区域。
以日军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成功为背景,在1942年1月21日举行的帝国议会会议上,已任日本首相的东条英机作了题为《大东亚战争指导要缔》的施政方针演说,明确提出,大东亚战争的目的是“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之大事业,而“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根本方针则是“使大东亚各个国家及民族各得其所,确立以帝国为核心,以道义为基础的共存共容的秩序”。(注:[日]《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576页。)根据这一方针,日本政府决定设立“调查审议有关大东亚建设之重要事项(除军事和外交事项)的大东亚建设审议会”。(注:[日]山本有造:《“大东亚共荣圈”构想及其结构》,载古层哲夫编《近代亚洲的认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4年版,第558页。)
1942年2月1日,日本政府公布了大东亚建设审议会官制。1942年2月7日,大东亚建设审议会正式宣告成立。该审议会由总理大臣任会长并兼任第一部会长,由天皇任命的40名官员和专家任委员(5月25日改为50名,7月1日又改为45名)。审议会还设置了八个部会,分管和审议具体政策咨询问题,提供决策方案。除第一部会外,各部会均由相关的国务大臣任部会长。(注:[日]石川准吉:《国家总动员史·资料编·四》,第1335页。)
1942年11月1日,日本内阁设立了大东亚省,下设总务、满洲事务、中国事务、南方事务四个局。原外务省的满洲事务、中国事务、东亚、南洋等局,以及海外省的北方、南方拓展局均并入大东亚省。大东亚建设审议会也随之划归大东亚省具体领导。(注:[日]百濑孝:《事典·昭和战前期的日本》,吉川弘文馆1990年版,第159、402页。)
大东亚建设审议会拟定了一系列方案,从这些方案中,我们不难洞察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殖民扩张主义本质。
在大东亚建设审议会各部会拟定的方案中,由首相东条英机任部会长的第一部会方案《关于大东亚建设的基本要点》,是提出基本理念的总论。这份文件概要地重复了东条英机在议会所作的施政演说的宗旨,提出“大东亚建设的基本理念源于我国体的本义,即八紘一宇之大义的弘扬和大东亚的显现。为此,要在皇国的指导和统治下,使圈内各国及各民族各得其所,确立以道义为基础的新秩序”。(注:[日]山本有造:《“大东亚共荣圈”构想及其结构》,载古屋哲夫编《近代亚洲的认识》,第561页。)
根据上述总体理念,以文部大臣桥田邦彦为部会长的第二部会方案《关于大东亚建设的文教政策》,和以厚生大臣小泉亲彦为部会长的第三部会方案《顺应大东亚建设的人口及民族政策》,以拟定了以强化“皇道主义”为基本精神、以利用各地历史文化条件为主要手段的“同化政策”。事实上,这一政策是已经在台湾、朝鲜、“满洲国”实施的政策的进一步推广。(注:以下关于大东亚建设审议会各部会拟定的方案,均参阅[日]《国家总动员史·资料编·四》。)
与此同时,以国务大臣(企画院总裁)铃木贞一为部会长的第四部会方案《大东亚经济建设基本方针》,则为以产业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指南”。该方案的要点是:“一、大东亚产业建设的主要目标,是在15年里分两期实现重要国防资源的自给自足。”“二、大东亚的产业分配,以国防和大和民族分配方面的要求为先决条件。”“三、对大东亚地区的资源进行彻底调查,明确大东亚在世界上的地位。”同样,如古川隆久所指出的,“在15年里分两期实现重要国防资源的自给自足”的计划,也是在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背景下,对以《基本国策纲要》为指导的一系列“纲要”,特别是《日满华经济建设纲要》和《国土计划设定纲要》的进一步具体化。(注:[日]吉川隆久:《昭和战中期的综合国策机关》,第163页。)
以工商大臣岸信介为部会长的第五部会方案《大东亚产业(矿业、工业及电力)建设基本方针》,根据将15年计划分为两期的“期间计划”,以“迅速增强顺利进行大东亚战争的战斗力”为目标,规定将钢铁、煤、石油和其他液体燃料、铜、铝、飞机制造、船舶制造。肥料、电力等部门作为建设重点,同时“相应于资源储存状况”,对产业开发地区作了具体划分。
除了上述作为重点加以建设、开发的工矿产业外,“自主的国防经济的确立”另一个物质基础,是以粮食供应为中心的农林水产业。农林大臣井野硕哉为部会长的第六部会方案《关于大东亚的农业、林业、水产业及畜牧业的发展方针》,就是试图奠定这一基础的方案。这一“方针”提出:“皇国必需的主要粮食,将以国防及大和民族配给上的要求为依据。”同时,与工业和矿业开发的地域性划分相对应,这一方针也规定了主要粮食生产的地域性结构。十分明显,这是试图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幌子下,推行老牌殖民主义的“单一经济”政策,是对各国主权的无视和践踏。
以大藏大臣贺屋兴宣为部会长的第七部会方案《大东亚金融、财政及交易基本政策》,提出了关于建立“大东亚金融圈”的构想和方针,即:“皇国和圈内各地区的金融关系,应打破仅以支付能力和资金拥有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旧观念,遵循以皇国为大东亚核心的原则,通过皇国和圈内各地区建立结算关系的新构想来对此加以调整。同时,圈内和圈外的金融联系也以皇国为核心进行一元化统制。”为了建立以这一“基本方针”为指导的“金融新秩序”,该方案提出:“大东亚圈内的金融关系,要以作为指导通货的日元为中心,形成将圈内的各种通货联系起来的日元圈。”需要指出的是,建立“大东亚金融圈”的构想和方针,也不是什么新玩意儿,而是“已经在大陆占领区实现的日元通货圈和日元结算圈的大规模的扩大再生产”。(注:[日]岛崎久弥:《日元的侵略史》,日本经济评论社1989年版,第260页。)
以通信大臣寺岛健为部会长的第八部会方案《大东亚交通基本政策》,是以将大东亚联结起来,以“充实国防力量和强化对广大地区的指导力量,同时确保物资交流,促进产业建设”为指导方针的方案。然而,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就其方针而言,我们均不难发现,这一方案也是对1941年2月14日在内阁会议上通过的《以基本国策纲要为基础的具体问题处理纲要》中的《交通政策纲要》,和1942年5月12日在内阁会议上通过的《计划造船施策大纲》的进一步具体化。
总之,大东亚建设审议会拟定的各项方案,具有顺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局势,试图将1940年7月第二届近卫内部成立阶段提出的"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构想,以及为此而制订的一系列纲领、纲要,修改扩大为“涉及大东亚整个地区的广泛的区域化计划”的性质。
综上所述,从“满蒙领有论”的提出到“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的逐步形成,日本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分子拟定了一系列侵略扩张计划。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计划中,各国、各地区并没有被“等量齐观”。正如由企画院研究会拟定的《大东亚建设的基本纲领》明确指出的,要“修正大东亚战争以前流行的向内地集中的观念”,“在产业振兴方面以日、满、华北为核心……根据国防上的要求及各地原料、动力、运输、劳力等方面的条件,决定产业的分配。通过综合地活用整个大东亚地区的经济力量,求得最高效率的发挥”。即“建设的重点归根结底是日、满、中国。必须在根本上将这一核心体中的骨干产业集中起来,确定稳固的国际态势。南方的建设将以此为前提进行考虑。也就是说,可以将南方称作共荣圈的外围”。(注:[日]企画院研究会;《大东亚建设的基本纲领》,同盟通信社1943年版,第129页。)这一核心和“外围”的规定表明,“大和民族的发展据点”已不仅限于日本本土,而是扩大到日、满、中国,而其他“大东亚地区”,尤其是南方,则是它的“资源圈”。这,无疑再一次赤裸裸地显示了日本殖民扩张主义者特别对中国始终存在的侵略野心,以及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本质。
标签:伪满洲国论文; 殖民扩张论文; 大东亚共荣圈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历史论文; 大日本帝国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工业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