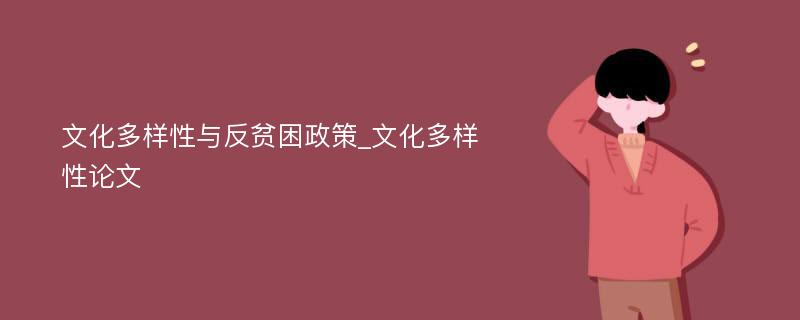
文化多样性与反贫困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样性论文,贫困论文,政策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考察文化与贫困的关系,对文化多样性、经济发展和在囊括各种文化的世界中减轻贫困所面对的挑战予以特别关注①。在过去几十年中,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甚至是经济学家,都已经在国际背景下考察过文化与贫困的关系,产生了非常多样且在近年来水准日益提高的文献(Rao and Walton 2004)。然而,“文化”这一术语对不同学者具有不同的含义,我们面对的部分挑战,就是比照我们对贫困和发展的了解对这些含义进行评估。我们不可能指望在短短几页纸中就完成这方面的所有工作,探讨其所有的复杂性,甚至不能指望忠实地对其进行总结。毋宁说,我们涉及的是小范围但很关键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发现这些问题对有些人特别重要,他们试图在我们所生活的全球化世界中减轻贫困或缓解贫困的消极影响(欲了解更多,请参见Lamont and Small 2008和Small et al.2010)。
关于文化与贫困的关系,有一个普遍而富有争议的信条断定是文化造成了贫困——具体而言,就是个人贫困或者维持贫困状态,是由于他们的文化信仰和态度;社会不能战胜不发达,是因为这些社会的民族或集体的文化(Harrison 1985;Harrison and Huntington 2000)。例如,一些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被认为正是因为缺乏社会凝聚力、缺乏公正倾向或发挥其全部潜力的兴趣,才继续处于不发达的境地。受孟德斯鸠的启发,一些人甚至将气候单独挑选出来,作为造成职业道德差的随机因素,而职业道德差会减缓经济的发展。另外一些人受到现代化理论影响,坚持从与西方的文化接近性方面衡量消除贫困的前景。首先,我们认为,不应当将文化作为社会的信仰、规范、价值观和态度来思考。从这些特质来看,特定社会中的个人之间有着实质性的不同,而且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可以持有相互矛盾的信仰、规范和态度,事实上也是如此。第二,文化条件不仅是规范性的,而且是认知性的,就个人的动机因文化条件形成而论,行动者如何看待自己的周遭环境,可能会与他们看重什么或相信什么同样重要。第三,行为不只是由文化条件塑造,同时也受政治和经济条件的影响,而这又反过来影响个人和集体的发展与贫困的程度。
在本文中,我们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在这个视角中,信仰、规范和价值被理解为只是文化的几个维度中的一维。其他维度包括世界观、框架和行为的脚本(scripts)。这些维度当中,多数与贫困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从这个脉络看,我们建议,重要的不仅仅是研究文化对贫困产生的因果性作用,而且也要研究贫困对文化的作用——缺乏资源如何影响人们感知其社会环境的方式。在我们看来,消除贫困的关键之一,不在于激励贫困者秉承主流的信仰(因为通常来说,主流人士与贫困者通常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而且都持有相互矛盾的信仰),而在于更好地理解和引导异质性。我们建议,为减轻贫困或缓解贫困影响而工作的人们应当更加认真地对待文化,而在过去,很多人一直不太愿意这样做。对穷人世界观的把握,不应当通过考察这种世界观不是什么,而应当通过考察穷人的生活条件如何限制了他们可以利用的选择的范围,同时,考虑到他们的生活情境,考察在他们可以选择的多条路径中,对他们而言,哪一条是最适合的。
为了形成我们讨论的框架,我们按照阿玛蒂亚·森和另外一些人的论点,即有关福祉的研究不仅应当关注物质贫困,而且,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说,还应当关注人们所拥有的获取他们所重视的物品(或实现其功能)的能力(Sen 1985,1999)。在我们看来,这种研究方法的好处是,它使我们摆脱了一种相当狭窄的视角,如果按照这种视角,文化的作用会集中在其与人们的收入、就业或财富的关系之上。而能力概念提出了福祉的主观性这个复杂的问题:能力取决于社会环境,也取决于人们希望得到什么,而这种希望本身又取决于文化环境。在此,我们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但我们可以鉴别出这些环境,对这种环境的输入方面的某种理解,很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文化多样性在不同环境中呈现不同的形式:在有些环境中,它可能与种族差异相关,比如在南非和美国;在另一些环境中,可能与宗教和族群差异有关,比如在尼日利亚。我们的许多实证研究都是以美国为依据的,虽然我们当中的一位也曾经在法国做过研究。在本文的上半部分,我们经常使用美国的例证来框定我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在下半部分,我们将会更概括性地扩展到某种国际背景。为了切实有效地讨论文化多样性,必须先澄清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并将这种理解与他人的理解区分开来。现在首先讨论这一话题。
贫困的文化后果
也许,重新思考前面描述过的简单因果关系模型的最妥当方式,是思考反向的关系,考察经历持续贫困的文化后果。多年来,在这一脉络上最著名的理论是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 1959,1969)的贫困文化(culture of poverty)概念,尽管这种理论有争议。刘易斯论证说,当群体在某个资本主义社会中被从社会和经济上边缘化时,他们会形成应对自身低地位的行为模式,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种贫困文化。他在墨西哥和波多黎各的家庭中观察到的这种行为,其特征是低志向、政治漠然、无助感、无组织性、地方主义和对所谓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轻蔑。刘易斯认为,一旦这样的文化形成,它就会发展出通常会自我长久持续的机制,哪怕是结构性的条件已经改变。这种研究遭到了大量批判,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假定文化具有内在一致性,同时也因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Lamont and Small 2008;Valentine 1968)。
近年来,学者们以更高的理论清晰度和实证力度审视了这一问题。对于贫困的文化后果,也许可以区分为不同的范畴:因个人贫困而造成的文化后果;因街区或社区贫困造成的文化后果。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这些并非只是在不同层次上观察到的同样效果的两种形式。例如,个人贫困既可能在集体贫困的背景下体验到,也可能在集体繁荣的背景下体验到。前一种情况当中的文化后果可能与在后一种情况中不同,在集体富足的背景下,相对被剥夺感可能起到某种作用。
许多人考察过生活在持续贫困或失业状态下对个人的长期性后果。例如,威尔逊(Wilson 1996)认为,持续无业状态尤其会对日常习惯和工作取向产生影响。每天早上在特定的时间醒来,必须参加工作或会议,必须达到工作职责的要求,会形成人们的习性或者说行为倾向,这本身就会促进持续就业。当“工作消失”,个人不再与正式的劳动市场有涉,人们就可能失去这些文化倾向。布尔迪厄(Bourdieu 1965)与雅胡达等人(Jahoda et al.1971)分别在阿尔及利亚人失业范围扩大的过程中和奥地利一次经济萧条期间观察到类似的情况。
还有很多新近的著述重点关注社区层面上的问题。街区贫困的后果,具体来说,居住在贫困者高度集中的街区(无论特定的个人本身是否贫困)的后果,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是美国学术研究中认真考察的一个主题,近年来再次引起美国学术界的关注(Goering and Feins 2003;Valentine 1968;Wilson 1987)。较早的文献对文化做了长篇大论的考察,但并不具有近期著述的理论精确性;最近的学术研究则显示出程度高得多的缜密性,使用了调查数据、人种志的数据,甚至是田野实验,但不幸的是,没有对文化作很多考察。在较早的研究当中,最突出的是汉纳兹(Hannerz 1969)对美国一个无名城市中一个社区的状况的考察,那里高度贫困,人口主要是黑人。汉纳兹发现,该社区既发展出主流的行为形式,也发展出贫民窟特有的行为形式,个人视环境的需要选择一种或另一种。
更新近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街区贫困既可能对个人也可能对整个街区形成文化影响。史密斯(Smith 2007)研究在密歇根求职的非裔美国人后发现,生活在密集的贫困街区,会降低社会网络中的信任程度,致使人们不那么愿意帮助彼此找到工作。有关对街区造成的后果,学者们得出了与汉纳兹一致的结论。安德森(Anderson 1999)对费城黑人城市街区的研究、斯莫尔(Small 2002,2004)对波士顿一处波多黎各人住宅群的研究、哈丁(Harding 2007)对美国有关贫困和非贫困街区的全国性调查数据的利用,都发现街区贫困通常与文化多样性有着联系——就是说,是这样一种情境:其中,有关行为适当的多种信条和脚本在一个背景下同时存在,以至于居民不得不从不同行为模式中作出选择,而这些模式都为社会所接受。
这三项研究指向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安德森进一步将街区中的街道和体面家庭作了区分,间接提到了汉纳兹的研究。但是,通过重点关注不同行动者类型之间而不是不同类型态度之间的差异性,可能还不能完全发挥它原本应使研究取得进展的潜力。斯莫尔对异质性作了鉴别,而且就异质性如何产生提出了一个模型。他指出,同质性群体可能对街区本身(例如,住在这个地方是好是糟)作出相对一致的文化叙述。而且,随着老龄居民为较新或较年轻的同质性群体所替代,可能会形成文化的异质性。哈丁提供了比较性的数据,显示贫困街区可能比非贫困街区更具有文化异质性,至少在有关性行为和男女关系的信条和脚本方面是如此。
扬(Young 2004)最近的一项研究,就个人贫困与街区贫困之间的联系提供了重要的见解。他对处在贫困当中和居住在高度贫困街区的非裔美国男性进行了访谈,话题涉及他们对自身和自己抱负的认识。他发现,那些不怎么离开街区和社交上最孤立的人最有可能相信“美国梦”的信条,即通过努力工作和奉献可以改善自身的处境。而在街区以外(如监狱)度过时日较多,因而与更广大社会有更多接触者,则更有可能相信种族歧视是改善自身状况的严重障碍。
反抗性文化和贫困的复制
在考察了贫困造成的文化后果之后,随之而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些后果是否是本身就会自我延续。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个脉络中的典范性模型是刘易斯的模型。刘易斯不仅认为处在贫困条件下的人们会发展出前面描述过的文化信仰和态度,而且还认为贫困文化一旦形成就会自行延续,以至于人们不大可能改变其行为,即便是最初导致这种行为的社会条件已经发生改变。这种主张可能最有争议性,而且事实也证明它是最得不到支持的主张之一。例如,在美国,许多保守的评论家认为,黑人的失业率较高,是因为黑人不愿工作,或者说他们的文化倾向是反对工作的。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劳动力市场急剧紧缩的情况下,黑人失业率却直线下跌,清楚地说明之前失业的那些工人不是不愿意工作,只不过是找不到工作而已(US Census Bureau 2001,table 593)。
这种主张的理论假设也遭到批评。许多研究者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与个人成功不一致的文化态度和信仰的发展,本身就是对这类社会的经济制度有意或无意的抵制行为。在一种人们最经常引用的模型中,约翰·奥格布(Ogbu 1978;Fordham and Ogbu 1986)论证说,对于社会中贫困的少数族裔的情况,必须在其移民来此社会的背景下理解。一些人是自愿移民的少数族裔和群体,因寻求政治自由或经济机会而自愿迁移到一个社会中来;另外一些人则是非自愿移民的少数族裔,如奴隶和原住民,这些群体是因征服或暴力而成为少数族裔的。奥格布认为,后一种范畴的少数族裔群体可能将他们自己感知为想象中的亲戚(兄弟姐妹),并且对影响自己提升的结构性制约因素(如少数族裔面临的“玻璃天花板”和制度性歧视)保持着敏锐的意识。结果,他们可能发展出对立的文化,即与主流社会的态度和信仰基本上格格不入的一系列态度和信仰,在这种文化中,认同主流信仰,如参与正式经济,或通过标准教育路径取得成功被认为是对虚构的亲缘群体的不忠诚。虽然群体内部通过这种集体文化的形成而得到强化,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其成员的个人职业成功前景却受到了影响。奥格布根据其模型对学校里的未成年人进行了测试,因为人们认为这些学生的未来抱负是最容易感知的。他发现,其所研究的美国城市学校里的许多黑人学生抱怨那些“行为像白人”的学生,并且将那些学习成绩好的黑人学生称为“聪明勤奋的疯子”。这样,文化条件便促进了贫困的复制。
这一模型对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很有吸引力。它提供了一种看待文化的方式,不将受害人的问题归咎于他们自己,反而展示出一种格调高的、全面的观点,以一种直觉上看似乎正确的方式看待各种群体和各个社会在贫困方面的差异。但是,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个模型才得到清楚明确的测试,而测试结果却发现了可以对它提出质疑的理由。安斯沃思-达尼尔和唐尼(Ainsworth-Darnell and Downey 1998)测试了一个全国性的学生群体,考察其对教育、作业、教育成就、学校重要性和教育对名望的作用的态度。他们发现,黑人学生与白人学生的回答并没有什么差异,或者说更倾向于认同获得成功的主流方式,这与那个模型的命题是直接矛盾的(另见Cook and Ludwig 1998)。
然而,人们对这一模型还有更广泛的关注。请注意,在奥格布的模型中,文化既是内在一致的,也是静态的。有人认为,非自愿性移民所持有的那一系列有关成就的信仰和态度并非不连贯,而且一旦确立就不会发生改变。关于文化的两种概念似乎都难以提供支持。例如,许多人写到的城市非裔美国人的文化中表现出的种种不同的信仰组合,这似乎是异质性的、对立的观点,而非一致性居主导地位的模式(Hannerz 1969)。此外,文化是会改变的,这个概念在这种背景下甚少得到思考。然而,正是通过考察文化如何改变和在什么情境中会发生改变,其他形式的变化可能性才会出现。
回到我们所讨论的涉及面更广的议题上来,反抗性文化(oppositional culture)和文化抵制(cultural resistance)的问题指向了又一个难题:将福祉设想为既取决于收入又取决于人们的能力的难题。森和另外一些人已经论证说,在考虑到人们能做什么的情况下,他们做得怎么样,将不仅仅取决于他们所处的特定社会,而且取决于他们的兴趣和嗜好。例如,大多数人会赞同,可以将减少文盲设想为一个目标,但不是实际意义上的主观目标。如果我们正在思考福祉,那么我们关切的并不是是否人人都能受大学教育,而是那些希望受到大学教育的人能否获得这种教育。
当然,这种证据不能得出一个包罗万象的反抗性文化概念,即认为在这种文化中,大多数非自愿移民少数民族的成员会拒绝正常的成功渠道。尽管如此,在抵制性文化的背景下,显然个人可能在文化上与主流社会或者国际标准所假定的预期目标格格不入。如果依据在所有情况下都适用的普遍性,就很难找到答案。然而,一种成功的消除贫困的方法应意识到以下一点:存在因抵制或拒斥通向福祉的主流路径而产生的文化信仰或态度。特别是,虽然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保留传统可能经常被解释为一种反生产力的文化抵制形式,但这种保留也可以维持强有力的群体认同,它起到作为集体赋权和注入活力之基础的作用。反过来,因工业化导致的文化流失可能削弱传统的团结和相互支持网络,并且转而产生新型贫困。经济发展的追求可能在新的伪装下重新制造出原本能得到缓解的一些问题,而与此同时,新的用以巩固成果的空间可能随着少数民族群体和低地位群体遇到新的挑战而出现。有关例子,参见穆尼(Mooney 2009)对迈阿密、蒙特利尔和巴黎天主教社区和海地移民社区的研究。
作为自我效能工具的文化多样性
与主流不同的文化差异,并非总是对主流方式的拒斥。事实上,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差异可以成为取得成功而不是导致失败的工具。文化多样性本身就可以成为发展、自我效能(self-efficacy)的工具,而对于发展,人们已经争论了有些时日。班菲尔德(Banfield)明确地认为,在世界许多地区,文化传统削弱了政治经济发展的可能性。他所称的“不道德的家族主义”(amoral familialism)——一种强烈的保护、受保护意识和群体内部的资源分配方式,其中,人们的优点几乎不起什么作用,对发展是很强大的障碍。另外一些学者就拉美的经济发展和中东的政治发展提出了相似的论点(Harrison 1985;Harrison and Huntington 2000)。
但是,这些论点通常不能令人信服。那种认为文化多样性削弱普遍价值因而有碍于进步的想法,是基于以下有缺陷的假设:集体的政治和经济进步主要倚赖于共识而不是冲突,并倚赖于人们有共同的规范、价值和信仰。当然,人们就诸如尊重生命、公正和经济机会这样的核心概念达成某种一致意见,是很重要的,但这些并不是差异点所在。发达国家在民权、工人权利和经济发展方面的许多最重要的进步来自冲突,这是整个社会沿着正确的历史道路,直接、公开地应对差异的结果。
正如在国家层面认可差异可以导致集体进步一样,在个人之间认可多样性可以被引导为赋权的工具,以改进反贫困的政策。例如,许多权威人士论证说,为了让移民少数群体取得成功,他们必须采纳自己所处的新社会的文化和语言。但是研究者也指出,保持文化特色可以提供重要的优势。在一项关于美国移民使用双语的重要研究中,波茨和绍弗勒(Portes and Schauffler 1994)发现,与那些学习了英语但未保持移民来源地语言的移民子女相比,使用双语的移民子女在数学测试中和其他学习成绩测量中表现更优。另外一些研究者发现,儿童在学校对文化相关材料的反应更积极,而且与仅从一种角度看问题相比,他们也更积极地用多种文化视角、方法看待问题。
作为交流、创新和创造力来源的文化多样性
另一种思考多样性的方式,是考量它对创新和创造力的影响。一些人认为,通过承认和赞扬低收入或低地位少数族裔群体的独特文化遗产,也许可以提高他们的自决程度。虽然缓解贫困需要对收入进行重新分配,要实现权利、制度和其他资源获取途径的平等化,但可能也需要这样的干预:使此类群体在公共领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同时明确肯定他们作为文化和政治体系成员的重要性。公开赞美文化多元主义可以做到这些,但是,通过承认这种群体的存在及其文化特色来促进其自决,很可能更为重要[参见认可马萨诸塞州瓦婆农族马什皮部落(Mashpee Wampanoag)的例子,Badkhen 2007]。这些都无疑会影响到共同的激励抱负能力(Appadurai 2004),影响到维持更强烈的集体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的意识、让其得到发展的能力。
在发展研究领域,最近有学者认为,我们应当赋予本地知识(包括原住民和其他边缘化群体的理解和实践)以更大的重要性(Scott 1999,pp.313-335)。要求广泛的公民参与并作出贡献的政府,往往更具合法性,而且通常来说在动员个体实现集体目标时更有效和更有能力。例如,全印卫生与公众健康研究所(All India Institute for Hygiene and Public Health)开始在加尔各答的索纳加奇人(Sonagachi)中利用性工作者来进行使用安全套的同侪教育(peer education)后,艾滋病病毒的感染率在1999年下降到6%左右,而在其他红灯区这个数字是50%(Rao and Walton 2004,p.8)。在对乌干达和博茨瓦纳的艾滋病病毒感染减控工作的研究中,斯维德勒(Swidler 2009)发现,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只有在将当地社区的意义系统和社会团结动员起来,工作才有成效。即使乌干达的地方政府不像博茨瓦纳的地方政府那样民主,但其显著的宗族结构提供了延伸到当地社区的更有效机制,比由全国性或跨国性的志愿组织运营的机构更为有效。成功的关键,在于利用在具有多样性的当地社区通行的道德秩序的社会形象,并且激发出普通人对各自的朋友、邻居的义务感,以及社会所看重的行为模式。
将祛除耻辱感作为缓解贫困的机制
个人如何理解和应对遭受排斥和耻辱感,是歧视如何影响其心理、生理健康和福祉中的重要因素(Lamont 2009)。这关系到从属群体(subordinate groups)的成员是将其较低地位和随之而来的耻辱感内化,还是对自己的情境作出解释,以便改变地位等级体系和权利结构。
对于有耻辱感的群体的成员,心理学家已经考察了他们用以应对感知到的耻辱感的内部心理机制,例如将群体内的比较置于特殊地位。同样重要的是人们用来定义地位的框架不断变动,包括通过独立于社会经济地位的评估标准来定义(Lamont and Bail 2005)。拉芒(Lamont 2000)以访谈为依据的研究发现,非裔美国人的工人阶层通过将他们的“关爱自我”与白人比较盛气凌人的自我进行对照来区分黑人与白人。就他们来说,在法国的北非移民通过显示出他们在道德基础方面与法国人的不同甚至更加优越来挑战成见。在不同程度上,两国的工人都通过指出中产阶级道德上的失败来将自己定位于中产阶级之上。他们提出了另类的评估标准,这些标准使得他们可以将自己定位于某种等级体系之中。这些文化模板(cultural templates)被广泛地共用。文化抵制可以提供强有力的文化脊梁,承受向上流动遇到的挑战,但文化抵制的出现,可能以相当大的张力为代价(James 1994)。
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有耻辱感群体的成员有获得公民成员身份的其他方式。一种方式是试图接受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态度、信仰和形式;另一种是变得具有双重文化性(bi-cultural)或多元文化性(multicultural),通过“密码转换”(code switching)来采取与不同背景相关的文化形式[Carter2006;DuBois(1903)2005]。严格的文化同化,即走一条传统的路线,可能是通过损失身份和其他重要文化资产的代价而实现。双重文化主义(Biculturalism)长期以来已为向上流动人士成功地利用,但经常性的密码转换可能具有疏离作用(Shoshana 2007)。
较重要的制度和较大规模的政府战略,如平权法案性质的法律或规章,也促进耻辱感的祛除,并允许个人在定义自己的身份时有不同的选择。这种战略的有用性通常取决于情境,并且存在争议或遇到抗争,巴西高等教育中采用平权政策(Silva 2006),2007年法国有关国立人口研究所(Institut national d'études démographiques)在宪法委员会反对的情况下搜集种族和族群统计数字的争议,都属于这种情形。在法国这个例子中,针对少数种族和族群收集人口普查资料的行动受到谴责,因为这可能潜在地神化和强化不平等及差异。
考察中产阶级、政治精英和其他精英的文化实践,对于理解祛除耻辱感策略和把握文化与贫困之间更广泛的关系而言至关重要。文化排斥和社会排斥是所有不平等制度的特征(Bourdieu and Passeron 1990),而且中产阶级将特权传递给后代的策略通常对比较没有特权的群体的选择起到限制作用。比如,在美国,学校预算是由当地税收决定的,中产阶级通过比较好的学校较贵的学费把工人阶层挤出居住区。
精英的冷漠,通常也具有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在一项关于孟加拉国、巴西、海地、菲律宾和南非精英对贫困的感知的研究中,里斯和摩尔(Reis and Moore 2007)指出,尽管来自这些社会各个部门的精英受访者在言谈中显得他们认为贫困是个问题,但他们难以认同关注这些问题非常紧迫或者有着难以抗拒的理由。人们对于以下一点并没有很强烈的意识:容忍贫困继续存在,就是允许浪费某些可贵的人力资源。而且,总的来说,贫困造成的犯罪等传统威胁被认为是相当小的。对于任何引入福利国家、相对普遍地为大部分人口提供广泛的补助这样的想法,仅获得有限的支持(在巴西得到的支持比在孟加拉国多)。围绕积极主动的政策达成一致的领域,是认为促进教育是减贫的最好办法,而减贫则被认为主要是政府的责任。
应对种族、族群或宗教耻辱感的策略是否可以成功地运用来对付贫困的耻辱感,是一个开放可供讨论的问题。从定义上说,低收入群体被剥夺了资源。拥有一种积极的自我概念,可能无法对他们的境况产生真正的影响。尽管如此,承认贫困程度如何受到制度力量和经济力量的影响这一点已经被揭示,目的是让穷人继续努力,改善他们的处境和获得集体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有关印度克拉拉邦的案例,参见Heller 1999)。
成功社会的制度和文化条件
我们的论证暗含这样的意思: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必须将对文化差异的保护、对群体权利的保护包括在内。成功的社会承认个人和群体的权利,采纳的政策公正地对待多种多样的群体,并且让来自不同文化和不同族群的人发出平等的声音来决定自己命运的方向(Kymlicka 1995,2007)。而且情况很可能是,通过普遍的而不是有针对性的方法重新分配资源会阻止耻辱感的发生,并因此不贬低对差异性的尊重,利用一系列制度(如学校、医院和福利)的途径,同时承认他们的独特需要。通过在许多机构中增加群体内部的接触来减少种族间的摩擦(有关学校的情况,见Warikoo 2010),而且确保各群体平等地获得资源。简言之,即最大限度发挥群体和个人的能力(Hall and Lamont 2009)。关于这最后一个方面,康内尔和卡尔特(Cornell and Kalt 2000)已经作过说明,他们的研究显示,采取了“打造国家”的方法(伸张主权,根据当地文化从战略上思考并形成强有力的管治机构)的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地的经济发展状况较好。在加拿大的“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中,欣然接受传统价值和决策方式的共同体[如纽芬兰的米亚普凯克(Miawpukek)部落]通常实现了更好的经济发展。
促进发达国家对贫困的道义关怀
我们针对这一点的讨论,已经确定了文化多样性与反贫困政策之间联系的不同要素。下面,我们将就在多样化的背景中如何促进对贫困的关注进行总结。我们提供五个案例,说明将文化多样性整合到实现这些更广大目标的努力中,并获得成功的情形。
全球范围内混血人口的增长,正在促进关于贫困和文化多样性的国际意识的形成。当北方国家的一些人实际上是根植于南方国家的文化与社会的一部分的时候,要不去考虑南方的贫困问题,只认为这是“别人的”问题,就难得多了。话虽如此,高度的阶级和种族居住隔离经常限制不同类别的人口之间的接触。在这个背景下,文化机构很可能起到某种核心作用,即传播在社会网络中不易散布的信息。传统上,宗教组织在提升关怀贫困的意识方面起到关键作用,但很可能还需要更多努力,特别是考虑到发达工业社会中的“去福利国家化”尚在不断发展之中。
促进对贫困的道德关怀的关键,是确定和说明贫困及与其相关的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许多社会科学家正继续研究如何发现贫困者的有限能力与贫困者和非贫困者都嵌入其中的更广大结构之间的联系。另外一些学者正在思考如何使决策者更加了解他们的研究成果(Carden 2008;Weiss 1980)。还有一些学者更关注如何通过受欢迎的大众传媒使得他们的研究成果更受关注,因为人们对声讨不公正和帝国主义的社会纪录片[如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指导的广受欢迎的影片和阿尔·戈尔(Al Gore)拍摄的全球变暖电影]印象深刻。一种在不同空间、以不同的规模、针对不同的受众同时操作的组合办法,很可能是最成功的。
有些学者(如Rao and Walton 2004)还讨论了集中于政策的解决方案。我们提供一些体现了最佳实践的行动的例子,其机构色彩较淡:
·对“公平贸易”的教学(Fair Trade Schools n.d.)正在英国教育体系中迅速传播开来。它成功地使儿童感受到他人的困境和那些复制不平等的交易条件。在其他工业社会开展相似的训练,会是一种有效的方法,特别是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儿童对于世界的经济外围地区的生活条件只有模糊的概念。
·芝麻街工作室(Sesame Street Workshop)在30多个国家共同制作具本土化特色的《芝麻街》(Sesame Street)版本,帮助促进文化包容和识字率。通过其国际共同制作,这个工作室希望在基层形成社会变革:“随着如今的全球景观由贫困、人权、艾滋病和种族灭绝的紧迫问题所主导,世界上较受欢迎的儿童节目可以作为桥梁将各种文化衔接起来,同时保持社会相关性。”
·“全球性的华盛顿州”(Global State of Washington)倡议是一个由华盛顿州上千个企业、大学、非政府组织和研究机构,加上数百个民间组织所组成的联合体,它们一起工作,动员公民为减缓贫困和增进所有人的权利而努力。他们合力提高每个组织的效能,并且使华盛顿州成为一个重要的可持续发展全球中心。相似的倡议正在洛杉矶成形(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领导)。
·万村(Ten Thousand Villages n.d.)是一家在北美拥有160多个店铺的非盈利企业,帮助来自南方国家的手工艺人分销和售卖表现其独特传统的商品。这个企业与非洲、亚洲和拉美的手工艺人团体合作,确保工人得到自己认为合理的薪酬。诸如此类的努力提供了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历史上处于弱势、被边缘化的群体可以在不放弃其当地传统生活方式的前提下进入全球市场,同时提高生活质量。
·2007年春天,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下,哈佛大学的“跨国研究计划”(Transnational Studies Initiative)赞助了一系列在移民艺术家及其受众之间的公开对话。这些活动探索跨国移民的艺术和文化产品的创作和管理,以马萨诸塞州的拉美、南亚和中国移民为主。每次活动特别呈现一场文化生产者与其受众之间的对话,话题涉及艺术与祖国、认同和归属感之间的关系。讨论集中于不同的文化产品如何被接纳、管理和展示,以及艺术碰撞在输出国和接受国如何为促进公民参与和社会变革作出贡献。教学电影“混合:通过艺术为认同绘图”(Mixing it up:mapping identities through art)即将制作完成。
反贫困政策日益关注贫困,不仅是由于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关于穷人的文化取向的思想,同时也由于低技能移民从文化多样的社会迁移到经济发达社会的情况日益增多。最近的历史和学术研究表明,面对多样化选民群体的政策制定者,有效调动双重文化主义和多重文化主义的方式所带来的益处,比专注于同化所带来的益处更多,而且这对个人和整个社会皆有裨益。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抵抗同质化冲动并鼓励文化共存的社会更有可能降低文化冲突,并从少数族群的迅速成功中获益。加拿大在这方面的成功具有指导意义。
政策制定者应当思考在许多领域如何理解多样性的意义。宗教表达是一种文化表达形式,应当被认可为低收入人群的意义制造来源。近年来,我们可能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宗教基本教义派的复兴,各国有时候通过限制宗教表达来应对,这可能是不利于取得成果的。总的说来,决策者应当寻找途径,让比较贫困、文化上不同或者普遍受到排斥的人群的能动性得到最大发挥(参见Rao and Walton 2004)。对于多样性的考察结果,还应当知会政府中为国家官僚体系配备人员的决策者。面对日益多样化的人口,如果国家机器的成分(包括服务、教育、执法等)继续在全国保持民族或文化的同质性,政府与选民之间的关系可能变得越来越紧张。最后,应当让政府和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处理相互关系时了解到这些考察结果,即特地提醒它们要使其发展工具适应当地的行动背景,同时考虑到目标群体的文化多样性。迫切需要做的是,要避免将不适合和未正确调适的决策制度模式强行置换到新的情境之中(Evans 2004)。
对于在多样化的世界中参与反贫困政策的决策者而言,没有哪一种工具会比信息更为重要。有关文化多样性的各个维度的定性和定量数据采集十分关键。不仅集中关注标准的经济指标,而且关注自我理解和文化实践的人种志案例研究和跨国性调查,在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在集体性数据的收集工作中,各国不只是集中关注本国,而且与其他国家协作,就此而论,我们的决策将可能更好地应对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
注释:
①本文由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报告》(World Report on Cultural Diversity)准备的一份背景文件改编而成。作者希望感谢下列同行,他们的评论以及笔者与他们之间的富有成果的交谈,为这份文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信息:Sara Curran,Jeff Denis,Peter E.Evans,Tamara Kay,Peggy Levitt,Seth Pipkin,Sanjay Pinto,Vijayendra Rao,Jocelyn Viterna,Carol H.Weiss,William Julius Wil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