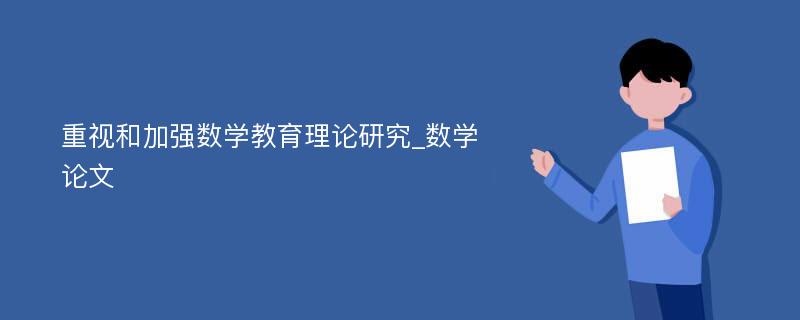
应重视和加强数学教育理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重视论文,数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数学教育学报》在2004年第4期上刊发了谢明初与吴晓红老师撰写的“建立理论体系还是研究现实问题”一文,读后感受颇深,收获很大。但为了厘清某些认识上的模糊性,防止理解上的片面性,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下面就数学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及相关问题谈一些基本认识和看法,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数学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对“数学教育学科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结构体系以及与其它学科的联系”(注:谢明初,吴晓红.建立理论体系还是研究现实问题.数学教育学报,2004.4).的研究(也称数学教育学研究)不同于一般的数学教育理论研究,它属于对数学教育元理论的研究。尽管元理论不能直接解决任何数学教育实践问题,但它从更高的层次上规定了数学教育理论研究的范畴和方法论。即使是在数学教育学创建之初,其研究意义也不仅仅是“引起学术界对这门学科的注意,促使这门学科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注:谢明初,吴晓红.建立理论体系还是研究现实问题.数学教育学报,2004.4),而更主要的是通过规范数学教育研究、健康引领数学教育研究的发展,来提高数学教育研究的自觉性,增强数学教育理论的科学性。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围绕数学教育学科体系的构建,我国先后有一些学者对此作了深入探讨(如:周学海,1986;曹才翰,1989;王仲春,1990;郑毓信,1992;孙宏安,1996),这对指引我国数学教育研究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我认为对此的研究和认识还远远不够,比如,在已出版的林林总总的诸多名为“数学教育学”或“数学教学论”的著作或教材中,结构体系非常混乱,从体系的建构到内容的选择,均表现出了明显的随意性,比如经常可以看到内容“鱼龙混杂”,不在同一层面的内容并举的现象。尽管数学教育学不可能有一个终极的理论体系,但没有一个相对独立和稳定的体系结构,没有一个确定的逻辑起点,没有自己的话语系统,缺乏体现数学教育学科特点的概念、原理与命题,确实不利于数学教育学的建设和发展。
强调数学教育学科体系重要性的必然结果,就是要加强数学教育理论的研究。所谓数学教育理论,就是对数学教育实践活动进行理性思考的产物,是对数学教育现象及其矛盾运动能动反映所形成的具有层次性的、可以指导数学教育实践的观念体系。不可否认,数学教育实践需要数学教育经验和常识,但仅仅停留在经验和常识的层次上是远远不够的,20年的数学教育经验也许只是一年工作的20次重复。没有数学教育经验到数学教育理论的升华,没有感性到理性的跃迁,就不可能获得关于数学教育的规律性的认识,数学教育实践只能在低水平上重复。在数学教育的研究中,我们不能满足于指明相应的事实,即如‘熟能生巧’‘温故知新’,而应对此做出必要的解释。也就是说,数学教育研究不能等同于经验之谈,而应上升到必要的理论高度(注:郑毓信.数学教育研究之合理定位与若干论题.数学教育学报,2003.3)。但人们往往有这样一种错觉:过去数学教育理论研究太多。其实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过多的是经验总结和大教育理论的简单移植应用,理论水平低下是我国数学教育研究的一个明显不足。正如王宪昌教授所指出的:“中国数学教育学研究者群体是在缺乏、很少有或没有理论研究的状况下进行的数学教育学的构建,因为缺乏、较少有或没有理论指导下的数学教育学研究很可能会停留在技艺和经验的层面,很难排除那种以教学经验总结为主的经验型研究的价值趋向。”(注:王宪昌,王文友.关于中国数学教育学研究的问题探析.数学教育学报,2004.1)
然而在当前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出现了一种反本质主义的热潮,即认为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没有什么真理性的本质、规律,即使存在但试图再现也是不可能的,因而应走进田野,关注教育教学的现实性、情境性和问题解决。这种思潮同样影响到了数学教育的研究领域。数学教育研究不是一个揭示客观规律的被动的反映过程,而是包含研究者的内在理解,包括对数学教育内容、目的、方法诸方面的理解及能动的建构过程(注:谢明初,吴晓红.建立理论体系还是研究现实问题.数学教育学报,2004.4)。应该说后现代主义重视研究中对人的生命和价值的关照,重视研究中的情境性和人文性,以及对学术研究中权威话语的批判和解构,都是对我们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的。但应清楚的是,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是基于对现代的反思和批判,它并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明确的理论流派,我们只能以此为工具来审视和批判现实数学教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改进数学教育研究中存在的方法论问题,而不能用一种范式来替代另一种范式,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事实上,数学教育研究仅仅拘泥于现实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是远远不够的,有些问题停留在现实的、具体的实践当中是无法认识清楚的,必须开拓思路,从更高的理论层面去进行思考;而且有些问题的解决,必须借助于哲学批判与理性分析的方法,才能得到根本性的回答与解决。此外,“通过一个具体问题研究所得到的结果只适用于这个特定的情境和条件,并不能将它推广到其它范围”(注:谢明初,吴晓红.建立理论体系还是研究现实问题.数学教育学报,2004.4),所以仅局限于现实问题解决的急功近利的做法,可能使得数学教育研究缺乏对问题的更宽的辐射面,视野过于偏狭,触不到问题的实质与核心,这样就会逐渐弱化理论甚至否定理论的存在,姑且称作是靠近实践的理论研究,也很容易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认识片面性。要真正实现“研究现实问题接近实践也靠近理论”(注:谢明初,吴晓红.建立理论体系还是研究现实问题.数学教育学报,2004.4),不能仅对经验事实作现象描述,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而应采取诸如比较、分析、概括、抽象等手段,揭示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并通过必要的反思与整合,逐渐达到对数学教育的理性认识。就此方面,我认为哈贝马斯的“共识理论”也许值得我们借鉴,即“提倡对教学现象进行多元的解释,并解决教学中出现的实际问题,但是我们也要寻求在更大范围内,特别是研究者与研究者之间、研究范式与研究范式之间的视界融合,通过对话与交流达成共识,从而走向对教学现象的整体理解,为未来的教学及其研究提供具有深度的方向”(注:靳玉乐,于泽元.教学研究范式的后现代转换.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3)。
二、正确认识数学教育理论的实践指导性
首先,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数学教育研究具有不同的层次和水平,既有着眼于数学教育现象的解释性研究,也有着眼于数学教育规律的概括性研究;既有着眼于现实问题解决的问题性研究,也有着眼于理论构建的理论性研究。相应地,所形成的数学教育理论也就有了层次之别。但既然称之为理论,不论是处于何种层次的理论,总是具有一定的抽象性的,因为理论总是追求一般和普遍,而实践更多地体现为特殊和个别,总是和人的感知、经验和习俗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并非所有的数学教育理论都能直接转化为数学教育实践。事实上,数学教育理论主要是对数学教育实践中存在问题的揭露、批判和反思,并为数学教育实践提供概要的、粗略的,甚至是不确定的、不可靠的导引,而不是或不仅仅是为实践主体提供解决问题的某种方案。杜威指出:“教育理论的价值不在于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在解说困难,并暗示应付困难的办法。”然而在数学教育实践领域,许多教师对数学教育理论应用作片面狭隘的操作主义理解,认为数学教育理论应该具有直接可操作性,不能直接操作的数学教育理论就是无用的理论。这种重用轻学、重经验轻理论;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利益,把数学教育研究完全导向实用的目标,强调研究成果的操作性与技术性,自然就使数学教育研究的目标完全依附于数学教育实践的操作目标,从而在价值上模糊了理论目标和实践目标的根本区别。也正是基于这种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和普遍存在的错误认识,所以导致许多数学教师在各种进修或培训中,经常对课例分析和案例研讨重视有加,对理论学习往往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对此我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是深有体会。
其次,也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对“理论脱离实践”就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数学教育理论与实践属于不同的范畴,遵循不同的发展逻辑。数学教育理论一经产生就有相对独立性,特别是形成一定的体系之后,就有它自己的逻辑,按它自己的逻辑发展,而并非简单地从属于实践,这就决定了理论脱离实践的相对合理性。并且理论与实践的脱离是双向的,当人们考察数学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时,往往转换成了对数学教育理论的讨伐和改造,而很少对实践的合理性以及实践者应用理论的态度和行为进行质疑和批判。事实上,数学教育理论要联系实践但不能一味地迎合实践,数学教育实践要以理论为指导而不能将理论拒之门外或束之高阁,也不能拿理论当教条。数学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经常需要适度的张力,这是二者发展的动力,我们不能以理论去框定实践,也不能主张“非理论数学教育实践”。
最后,从理论价值的具体实现来看,要发挥数学教育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往往要经过一系列具体的转变环节,其中最主要的是理论要真正内化为实践者头脑中的观念,切实被实践者所领悟和掌握。真正对数学教育实践产生影响的就是教师自己头脑中掌握的这种“理论”。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种“理论”事实上己不完全等同于书本理论,它是基于教师理论学习和亲身体验自主建构的,其中包含了教师本人通过长期的教育教学反思和体悟形成的“实践性学识”和智慧。书本理论往往是为教师内发的这种“理论”提供概念基础和思维方式,但很难对数学教育实践产生直接而深刻的意义。这也就说明了数学教育理论对实践影响的渐进性和隐蔽性特征。而且由于实践中的情境性和不确定性,这就决定了在数学教育理论应用的过程中,必然需要实践者自觉地反省、发展、分析、评价和改进。所以重要的是,数学教育理论要恰当地内化为教师的观念,真正转化为教师自己的品格,并在实践中对理论自觉地做出选择和评判,这样理论才会产生指导实践、改造实践的力量。
三、有效增强数学教育理论的实践力
如果说以往数学教育理论确实存在内容空乏、功能不实的境况(我曾于几年前做过一次问卷调查(注:李祎,鲁正火.数学教育理论与实践契合困难研究。数学教育学报,2000.3)),那么要改变这种境况,我认为主要应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1.研究范式的合理定位
数学教育学的逻辑起点不是一维而是二维的,一个起点为教育学,它与数学教育学是演绎关系;另一个起点是数学教学,它与数学教育学是归纳关系(注:单墫,喻平.对我国数学教育学研究的反思.数学教育学报,2001.4)。相应地,数学教育研究的范式就可以归纳为两种,一种是把教育学、心理学的理论应用于数学教育中进行演绎式地、解释性地研究,以解决数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另一种是遵循“问题发现—经验总结—理论提升”的研究方法论的问题中心研究范式。然而,在目前数学教育研究中存在着两种极端化的认识和研究倾向:一种是闭门造车,只进行抽象思辨的理论研究。我们认为纯理论研究是必要的,但不应成为数学教育研究的主流,因为这种研究一旦成了主流,会使后来的研究者们理所当然地认同并实践这种研究,最终将导致数学教育研究的单一化模式。二是实证化倾向。主张数学教育研究一切从实验中来到实验中去,过分强调实证,轻视理性反思与哲学层次的研究,使数学教育理论难以上升到较高层次。事实上,数学教育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对它的全方位的理解和把握也就不是一种研究范式可以做得到的,任何一种研究范式都无法单独回答、解释所有的数学教育问题,必须以多元的研究范式去研究复杂的数学教育现象和活动,实现多种研究范式的相互融合、相互补充。重此轻彼的结果,或者是导致理论脱离实际,或者是弱化理论的建设,并最终导致实践的低水平重复。
就这一意义而言,我认为,我们应针对当前数学教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通过研究方法的改进和不同研究范式的互补来重建数学教育理论体系,而不能弱化理论研究和理论体系的建设。但需要注意的是,理论体系的建设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从而也就不应为理论而理论,把本应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异化为追求的目标。但在过去的研究中,数学教育研究范式形成了两极对立的局面:有些学者致力于理论体系的建设,有些学者致力于现实问题的解决。由于两者关系处理不当,最终造成了数学教育学目前这种“上不挨天,下不着地”的状况。这里实际上涉及到一个对数学教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的认识。数学教育学究竟是理论学科还是应用学科,它的功能是对数学教学的基本问题所蕴涵的内在联系或规律进行科学地阐述和预测,还是直接用于数学教学实践,为教学设计对症下药式地开处方,这些问题在数学教育界还未形成共识。但无论如何定位,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数学教育理论必须具有一定的实践品格。把数学教育的研究等同于教育理论的移植加注释,或只做抽象的思辨,一味追求学术理性而缺乏实践关怀,是构建不出真正的数学教育理论体系的。理论体系的研究和建设必须借助于严格的逻辑思辨,但同时更应立足于数学教育实践,很好地归纳、概括来自于实践的第一手资料,否则最终会造成数学教育理论的内容贫乏,徒具空架,虚有其名,使学术界难以认同它的独立存在。尤其是随着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推进,我国的数学教育实践正经历着剧烈的震荡和变革,迫切需要新型数学教育理论体系的建立。所以重要的是通过研究方法的改进和不同研究范式的互补来重建数学教育理论体系,而不能弱化或放弃对理论体系的建设。
2.研究主体的“改良”
首先,教师应成为真正的数学教育研究者。在数学教育领域,研究者与实践者长期处于分离状态,前者的职责是发展理论,后者的职责是发展实践,这种状况直接造成了数学教育理论乏力以及与实践一定程度上的脱节。我们不但要提倡研究者深入数学教学一线,而且重要的是使实践者同时成为研究者。一线教师从事数学教育研究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比如了解学生实际,熟悉数学教材,而且具有丰富的数学教育教学经验。然而,“过去数学教育研究大多是限定在诸如解题、教学方法等方面的一些内容,而没有真正把自己当作一个教育实践者或者说还没有站在一个教育实践者的高度来全面地、系统地看待数学教育和教学”(注:杨骞.也谈对数学教育研究的几点认识.数学通报,2002.2)。近几年所倡导的行动研究是有效解决数学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增强理论实践力的有效途径。因为行动研究强调其参与者即广大中小学教师是研究者,被研究者成为研究主体,是一种将行动过程和研究过程结合起来的研究。这种以教师为主体的行动研究既是实践的,又是理论的;既有教师教育实践对教育理论的批判,又有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的问诊和反思,从而能有效地促进数学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良性循环、转化和发展。
其次,应改变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我国数学课程与教学论专业所培养的硕士与博士生是当前数学教育理论研究的主力军。然而,我国研究生的培养大都是在“象牙塔”式的书斋中进行的,毕业之后仍深居书斋,继续做他们的锦绣文章。研究人员的培养过程塑造了他们“闭门造车”的研究特点,往往对丰富的数学教育实践不闻不问。事实上,从数学教育实践中成长起来的研究者,很明显与书斋中训练的专业研究者有着不同的研究旨趣和研究素养,丰富的教学经验再加上理论的武装,往往促使他们有可能做出创造性的成绩,我国知名数学教育专家顾泠沅教授和罗增儒教授即是明证。这样说,并非绝对地要求数学教育方向研究生的选拔都从一线教师群体中进行,无非是想表明这样一个观点:研究生的培养不能囿于书斋、停留在理论上,而应注意培养的开放性和实践性。
此外,还应努力促进研究者研究文风的改进。就此方面,在文(注:涂荣豹.论数学教育研究的规范性.数学教育学报,2003.4)中有较详细的论述,我不再赘言。这里摘录两位学者对当前数学教育研究不良风气的精辟概括,供大家反思,“千篇一律充满套话的教学经验总结,钻牛角尖繁琐无味的解题研究,大而无当空泛无物的理论作品”(张奠宙),“大同小异的‘经验总结’,名不副实的‘教育实验’,穿靴戴帽的‘教学理论’,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顾泠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