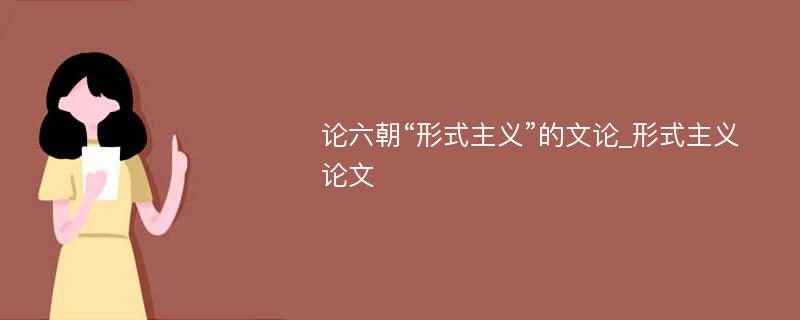
六朝“形式主义”文论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形式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现代人一提到六朝文学,就联想到“形式主义”文风的泛滥,这一点又继承自唐代以后将六朝文风评为“淫靡”文风的传统观念。我们说,在一种确切的意义上,“形式主义”文风盛行于魏晋南北朝并且产生了许多弊害,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对这种文风进行适当的批判清理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作为一个从现代文学观念出发接触古代文学史实的研究者,我们不应该仅仅知道六朝存在“形式主义”这种文风并将它判为文学发展误入歧途的例证,就算尽职尽责了;我们还应该弄清楚什么叫“形式主义”文风和这种文风的盛行对文学发展有什么积极意义。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的研究者应该对形式主义文风从文学发展而非文章发展角度作出反思,澄清“形式主义”文风与文学性的文章和文章的文学性的增强间的关系。而这一工作的最佳着手方式无疑是考察六朝有代表性的“形式主义”文论。本文的任务就是考察“形式主义”文论及其与文学自觉的关系。
事实上,当我们说六朝盛行“形式主义”文风的时候,我们对“形式主义”一词究竟指的什么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因此,我们在这里先结合《文心雕龙》的《情采》篇对文学“形式”的含义作一辨析,以便我们更好地讨论“形式主义”文论。
《情采》篇有一句人们往往不大注意的话:“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辨丽本于情性。”(注:《文心雕龙·情采》。)《情采》篇本来只讨论文章中的两要素即“情”(或“情性”)与“采”(或“文采”)及其关系,但这句话中却透露出了文章中的三要素即“情性”、“言”、“文采”,并认为“言”服务于“情性”,“文采”又服务于“言”。在我们看来,刘勰在这里虽然是以诗歌为典范,但却是面对一切文章类型谈“情采”的,他是在讨论文章诸种基本要素之间的关系。用我们今天的理论说,他提到了文章所具有的“内容”、“形式”、“文采”三个基本要素。他不经意地提到的“言”正好相当于我们现代文论中所讲的“形式”。凡是文章都必然具有表达内容的形式,不论是文学性的文章还是非文学性的文章,没有形式就没有文章。“文章”在很大意义上就是形式,因为文章是一种表达内容的器具,而所谓形式就指用语言构成的器具。如果对传统的“文以载道”作最宽泛的理解,把“道”理解为任何种类的内容,那么文章本质上就是“载道”的器具(“载道之器”)。事实上,包括六朝在内的古代文论在主流上就是这样来理解“文章”和文章之学的。如果“形式”指的就是这种“容纳”某种东西的语言器具的话,指责六朝盛行“形式主义”就是荒唐的,只要有文章存在就有这样的“形式主义”。可见,“形式主义”一词中的“形式”并不是通常所说与内容相对的那种东西,而是文章的另一因素,它就是刘勰所说的“文采”,“形式主义”实为“文采主义”。那么,对我们现代研究者来说,“文采”及“文采主义”意味着什么呢?
简而言之,“文采”就是文章的审美性质,如同“情性”及由“情性”而生的“风力”是文章的艺术性质一样。审美性质与艺术性质是构成文章文学性质(不同于实用性质)的两大基本要素。文学性质既可以指艺术性质,也可以指审美性质。正因为审美性质也是一种基本的文学性质,那些并不抒情言志的散文才属于“文学作品”的范畴,因为它们虽然不是艺术作品,但仍然包含了“文采”,是有文采的文章。所以,文采正是准确意义上的“文学美”。刘勰对文学美有较为明确的认识。《情采》篇说:“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注:《文心雕龙·情采》。)刘勰此处的“文”字可以直接译成“美”字,所谓“形文”即美的形状,所谓“声文”即美的声音,所谓“情文”即美的言辞。虽然刘勰由于过分注重“情”和“采”而忽视中间还有“言”,但他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正如天地间有美的形状、美的声音一样,也必然有美的语言。美的语言或语言的美就是文采,就是文学美,就是文章的审美性质。
但为什么注重文学美的文风被称为“形式主义”呢?了解康德对“美”的研究的人不难明白这一点:美在于外观而不在于实质。康德的讨论很复杂,我们在这里不便详细介绍。我们只需说明,康德认为美是事物外观方面能吸引我们、引起我们愉快或不愉快之类情绪的一种性质,美只是在外观上而不是实质上对我们有价值。事物实质的方面的价值是它的功利性,因此事物外观方面的价值是超功利的(或无功利的),美就是超功利的。由于我们往往把“外观”说成是事物的“形式”,把实质说成是事物的“内容”,因此,美在外观往往又被说成美在“形式”,康德也往往被看作“形式主义”美学的代表。实际上,这里的“形式”与文学理论中常说的“形式”是不同的,后者往往指文章的实质方面。(现代文论中所谓“形式”的含糊性恰恰就在这里,它既可以指文章的实质方面,又可以指文章的外观方面,甚至同时兼指两者。)我们说,文章总有其实质的方面和外观的方面,但只有一部分文章有其外观方面的吸引力即具有美。文学美即文采正属于这部分文章的外观方面的特性,文采即文章美丽的外观。由于把外观说成是“形式”,追求文学美的风气就被冠以文学“形式主义”的称号。其实,“形式主义”的最佳称号应为“唯美主义”或“美观主义”甚至“文采主义”,以表示一种热烈追求文学美(文采,文章的审美性质)的倾向。(一般来说,加“主义”二字往往有绝对追求、极端追求而不顾其余的意思,我们下文“形式主义”仅表示非常重视、强调、提倡文采,而不必有上述意思。)
如果我们是在这样确切的意义上把六朝“形式主义”理解为对文学美的积极追求,如果我们又知道文学美是构成文学之为文学的基本要素之一,那么,当我们考察六朝时期文学的自觉这一重要问题时,我们对一向颇受贬斥的“形式主义”潮流就不得不另眼相看了:难道作为文学中的“唯美主义”出现的“形式主义”文风及其反映形式“形式主义”文论,不正是文章的审美性质和审美性的文章趋向自觉的鲜明表现吗?通观六朝文论,表现形式主义文风的形式主义文论确实占有最为显赫的地位,形式主义文论无疑是六朝人对文论的最大贡献之一。
二
审美性的文章趋向自觉的突出表现是文笔之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注:《文心雕龙·总术》。)按此说法,“文”和“笔”的区分是六朝才出现的(一般认为从晋代开始出现),在刘勰所在的齐梁时代,文笔之分已经是一种流行的习惯用法,即“今之常言”。至于“文”“笔”各自的含义,刘勰也说得很清楚:“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也就是说,文笔之分以是否押韵脚为准,押韵脚的文章叫“文”,不押韵脚的文章叫“笔”;所以,文就是韵文,笔就是无韵文。由此可见,文笔之分是文章体裁样式的区别,是一种与诗笔之分一样的文体区别。
关于这种区别的例证,从清代骈文的拥护者和提倡者阮元父子开始,研究者们从史籍中梳理出了许许多多的材料,非常有说服力。我们在这里选几条有代表性的引述如下。《晋书·蔡谟传》:“文笔议论,有集行于世。”(注:范文澜《文心雕龙·总术》篇注引阮元《文笔对》,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又,《宋书·傅亮传》:“高祖登庸之始,文笔皆是记室参军滕演;北征广固,悉委长史王诞;自此后至于受命,表策文诰,皆亮辞也。”(注:范文澜《文心雕龙·总术》篇注引阮元《文笔对》,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又,《宋书·颜竣传》:“太祖(宋文帝)问(颜)延之:‘卿诸子谁有卿风?’对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注:《宋书·颜竣传》。)又,《宋书·颜延之传》:“元凶(指刘劭)弑立,以(颜延之)为光禄大夫。先是,子竣为世祖(指刘骏)南中郎将谘议参军,及义师入讨,竣参定密谋,兼造书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问曰:‘此笔谁所造?’延之曰:‘竣之笔也。’又问:‘何以知之?’延之曰:‘竣笔体,臣不容不识。’”(注:《宋书·颜延之传》。)从现有材料看,在颜延之父子之前,晋代已大量出现文笔对举连用的情况;不过,明确区分文笔为两种文体的记载却从颜氏父子开始,这说明文笔之分的流行至晚也在刘宋时代。可见,刘勰的话是完全可靠的,刘勰对文笔含义的说明即所谓“无韵为笔”、“有韵为文”也是没有问题的,《文心雕龙》从《明诗》到《书记》二十篇大致以文笔之分来安排,就是很好的证据。
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篇中的一段话往往引起研究者们对“无韵为笔,有韵为文”的确切含义产生怀疑:“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又说:“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能“慧”),笔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而古之文笔,今之文笔,其源又异。”(注:见郁沅、张明高编选《魏晋南北朝文论选》第36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有人据此对仅以有无韵脚区分文笔提出异议,以为文笔之分在含义上永明声律论兴起前后有所不同。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永明以来,所谓有韵,本不指押脚韵而言,文贵情辞声韵,本于梁元……至彦和之分文笔,实以押脚韵与否为断,并无有情采声韵为文之意。”(注: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中华书局,1962年,第215页。)黄侃看出萧绎所谓文笔与刘勰等人所说的文笔含义不同,但他把这解释为文笔观念受永明声律论影响而有了发展的结果。然而,在我们看来,萧绎虽然确实在一种新的意义上谈论文笔及其区分,但他并不是要把“韵”由韵脚之意扩展为“情辞声韵”之意,他实在是响应当时的潮流,在文笔之分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诗笔之分。诗笔之分在当时也不光萧绎一个人谈到。细读萧绎原话,不难同意我们的观点。关于“文”,他说:“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可见文仅指诗赋,文人仅指诗赋作者;再则他说:“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除了同诏策章奏之类相区别的诗歌和部分抒情性辞赋,没有什么文体是“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三则他说:“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这又显然是钟嵘、萧纲等所说的“吟咏情性”的诗歌(和部分抒情赋)。萧绎在这里显然是想努力把艺术性的文体(诗歌为代表)与非艺术性文体(他称为“笔”)区分开来。由于把艺术性的文章与文章的艺术性质同审美性的文章与文章的审美性质混淆起来,没有意识到诗笔之分与文笔之分一样重要,研究者们才误以为萧绎发展了“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的文笔观念。实际上,萧绎虽然运用了“文”“笔”两词,但他用“文”主要指诗歌,用“笔”主要指非艺术性文体,并不证明以有无韵脚区分文笔的“传统观念”已经失效,因为刘勰说得很清楚,文笔之分只是“今之常言”,一种流行的习惯用法,并没有严格的限定。
所以,我们应该明确肯定文笔之分的标准如刘勰所说只是一个有无韵脚的问题。我们觉得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区分文体是一件十分麻烦的事情,标准越复杂越难以进行,标准越简单越便于应用。文章有无韵脚是一目了然的,所以以此为标准区分出文笔两类文体最方便易行,这也是文笔之分能够流行的重要原因。这与诗笔之分齐梁以后逐渐流行一样,从某些外在特征就能很好地辨别出其中的差别,不需要精通声韵之类的专门知识。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把文笔之分看成是六朝文论文休区分方面的一种并不复杂的现象,不必在文笔的实际含义上去多费工夫,而是主要着眼于文笔之分的象征意义。
文笔之分象征着什么呢?刘勰在这里还提及颜延之的“言”、“笔”之分:“颜延之以为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注:《文心雕龙·总术》。)颜延之区分“言”、“笔”两种文章,是以有无文采即是否具有审美性质为标准的,无文采的文章为“言”,有文采的文章为“笔”。颜延之这种以文采即文章的审美性质区分文章体裁类型的努力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它表明审美性的文章观念即“美丽之文”(皇甫谧语)的观念在当时正在趋向自觉。而文笔之分的流行正是它的鲜明标志。从《文心雕龙·总术》篇的语气看,刘勰表面上虽然反驳了颜延之,但他反驳的只是颜延之的例证“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对用有无文采区分文体这一关键点并未提出异议,他显然是赞同颜延之的这一努力的。而且,从刘勰提出“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之后即讲到颜延之“笔之为体,言之文也”,可以看出,刘勰认为文笔之分与言笔之分反映的是同一种努力。所以,文笔之分虽然表面上只是个文章有无韵脚的问题,而实际上是一个有无文采(韵脚为文采的一个要素)即文学美的问题。文笔之分作为一种文论现象,象征着六朝人对审美性的文章之独立于非审美性的实用文章(质木无文的文章)的自觉。它是六朝人自觉追求“美丽之文”在文论中的鲜明体现。
一般说来,由于文采作为美的语言外观通常依附于文章的实用方面,并不具有独立性,因此在同一篇文章中往往实用性质与审美性质并存,文章的实用价值并不排斥它的观赏价值,所以,这样的文章也应该属于有文采的文章即“美丽之文”,而且,所谓有文采的文章多半是这种审美性质与实用性质并存的文章。文章的实质与外观方面的“用途”并不一定互相冲突,文章可以既中看又中用,此即“文质彬彬”的本来含义。所以,与诗笔之分使诗歌这种艺术性体现最充分的文体突出出来有所不同,文笔之分在最深层面即以文采之有无为标准上不会使某一种文体单独凸显出来,它只是消极性地试图把不具文采的文章划出去,只承认有文采的文章为“文”。但是,有文采的文章至少包含两大类型,一是不含实用性质的纯美之文,一是“文质彬彬”的中庸之文。纯粹的美文大概要数以汉大赋为代表的辞赋了,除了少数抒情小赋追求艺术性外,绝大多数辞赋以外观的美丽为它追求的唯一目标。但六朝没有出现赋笔之分,可见文笔之分的“文”包含许多不同文体,并不特指辞赋之类纯美文体,虽然六朝人对辞赋之类纯美文体也有很明确的体认。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以下一点,文笔之分所体现的审美性的文章(“美丽之文”)的自觉虽然很值得注意,但它远不如六朝人对文采的论述和重视中所体现的文章审美性质的自觉显得重要。
形式主义文论到南朝时发展得最充分,我们来看南朝文论家是如何论述文采的。
三
首先我们必须提到刘勰和他的《文心雕龙》。可以肯定地说,六朝文论家中没有一个人比刘勰更全面地重视文学美即文采的了,六朝文论著述中也没有一部比《文心雕龙》更充分地研究和探讨了文学美即文采的了。如果说,钟嵘《诗品》在我们看来之所以至今被目为“文学理论”著作主要是因为它从诗歌角度研讨了文章的艺术性质(即语言的艺术);那么,刘勰的《文心雕龙》在我们看来之所以至今仍可以被看作“文学理论”著作而非仅为文章学著作,主要是因为它在研讨文章的制作和评论诸问题时,突出地研讨和强调了文章的审美性质(即语言的美)。换句话说,《文心雕龙》主要不是因为它对构成文学性的艺术性质一面的贡献,而是因为它对构成文学性的审美性质一面的贡献,从我们今天的“文学”观念出发,我们仍然肯定它是一部不朽的“文学理论”著作。比较一下《文心雕龙》与《诗品》,我们很容易发现,刘勰与钟嵘之重视艺术不一样,他更重视的是美。因此,对我们今天的研究者来说,只有侧重于从美而非艺术的角度去读解《文心雕龙》,才能避免要么抹煞它的文学理论价值,要么牵强附会地证明它对文章艺术性质的贡献。我们下面的研究就是从这个基点出发的。
刘勰的基本倾向是主张“文质彬彬”,也就是主张文章的实用性质与审美性质两相兼顾、配合适当。刘勰希望任何一篇文章既要实用又要美观,不要顾此失彼。要实用就要重视文章的实质方面,因为只有构造出恰当的语言结构才能准确有效地完成传达特定内容的任务,这种适用于特定内容的语言结构就是我们所谓文章的实用性质(即实用要素)。刘勰非常重视文章的实用价值,所以《文心雕龙》也很重视文章的实用方面即实用性质(实用要素)。《情采》篇说:“夫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注:《文心雕龙·情采》。)这里没有提到“采”,只用互文见义的方式提到“情”、“理”与“文”、“辞”。情理与“情性”之类一样,只是内容的代称,文辞在这里也是形式的代称,只不过它只是偏于指不包含文采的“形式”,因而只是文章用于表达内容的实质之用那一面,此即我们所谓“实用性质”。如果“形式”是这样经过限定了的,我们可以同意许多研究者的看法,上述一句话讲了内容与“形式”的协调关系。根据特定内容经营特定的“形式”(语言结构,刘勰称为“体”),这是《文心》的基本思想之一。《情采》篇又说:“夫能设谟(“谟”同“模”,指模范,原型规格)以位理,拟地为置心,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摘藻;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注:《文心雕龙·情采》。)句中所谓用以“位理”的模范,用以“置心”的底子,就是文章的实用性质(实用要素)即上述限定意义下的“形式”。《文心》从《明诗》到《书记》二十篇主要任务就是为了教人学会各体文章的实质构成即实用性质(实用要素)。可见,《文心雕龙》是极为重视文章的实质方面的,《文心》中的“文”字很多地方也是从文章的实用性质(实用要素)方面命名的,虽然都可直译为“文章”。不承认这一点,单纯强调其中对诗赋等文体的重视,是无助于我们了解刘勰写作此书的原意的。
但是,单单注意到上述这点而走向极端,以为《文心》只不过是一部纯实用的文章学著作又是错误的,因为《文心》确实又最集中地代表了六朝人对文学美(文采)的热爱和追求。在《序志》篇中,刘勰解释“文心雕龙”书名的由来说,书名中“文心”指“为文之用心”,而书名中“雕龙”二字是这样来的:“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邹奭之群言雕龙也。”(注:《文心雕龙·序志》。)“雕缛”中的“雕”指雕刻修饰,“缛”指文采丰富。邹奭是战国时齐国学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齐人称他为“雕龙奭”,意指他善于修饰语言,像雕刻龙纹。刘勰的意思是说,之所以书名中有“雕龙”二字,因为文章从来就是要通过文采修饰才能成立,它正是取自邹奭“群言雕龙”的故事。因此,“文心雕龙”一名意为作文的用心所在在于精心雕琢形成文采。所以,就从书名中的“雕龙”二字就已经可以看出刘勰对文章审美性质的重视:没有文采不成其为“文章”。《序志》篇又说:“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注:《文心雕龙·序志》。)这个早年攀采如锦似绣彩云的故事,也表明刘勰心目中的文章与文采密不可分。“文章”一词在《文心》中一般都指包含文采的文辞,如:“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虞夏文章,则有皋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则有赞,王子作歌。”(注:《文心雕龙·正纬》。)在《情采》篇中,刘勰还特别强调“文章”一词与“文采”的关系:“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注:《文心雕龙·情采》。)“文章”一词本指彩色花纹,所以它本身就同文采密切相关。后来单篇著述被称为“文章”,就是因为它们的言辞多含文采。可见,刘勰认为文采是文章的内在不可缺少的组成成分。
刘勰对我们今天所说的美即事物外观的魅力(康德称为事物外观方面能引起我们快感的性质),是有明确深入的体认的。《文心》一开始,在《原道》篇中,他就从天地自然本来就存在美,进而说明文章有美乃是天经地义的事。他在篇中所说的“文”字几乎可以直接译成“美”字。他先谈到“道之文”:“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注:《文心雕龙·原道》。)这就是说,自从开天辟地以来,日月在天上像重叠的璧玉,山河在地上像光彩的锦绣,前者为“丽天之象”,后者为“理地之形”,这种美丽的“形象”(即外观)就是一种“文”,即“道之文”。接下来,刘勰认为“道之文”在万物(他所谓“万品”)中表现为形文和声文两大类。形文即:“龙凤以藻绘呈端,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注:《文心雕龙·原道》。)声文即:“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huáng③。”(注:《文心雕龙·原道》。)我们很容易发现,所谓形文是指可视图像的美,所谓声文是指可听声音的美,而前述日月山川构成的天地之美可以说只是“形文”,只属于视觉方面的美。刘勰用“形文”、“声文”之类“道之文”概括了我们今天所谓“自然美”(虽然“道之文”不限于自然美),即非人工的美。所以,刘勰在这里所说的“文”是有魅力的外观的意思,他所谓“傍及万品,动植皆文”,“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注:《文心雕龙·原道》。),就是证明。由于“外观”一词是一个与“实质”相对的含义很宽的词,它相对于一切感官而言,与仅相对于视觉的“外形”不同,所以,刘勰所谓形文、声文都可以包括进“文”(即美的外观,外观的美)。可见,刘勰认为美是无所不在、遍及整个宇宙的。刘勰这里对事物外观方面的魅力(即美)的体认肯定是同汉大赋及刘宋山水诗所写内容以展现美为主有很大关系的。《文心》专辟《物色》一篇就是为了总结文学中在内容上追求表现纯粹美的那种倾向。“物色”一词,顾名思义指物的色相,主要指春夏秋冬四时自然物的外观,并且还是迷人的外观,即一年四季大自然的美。比如,他描述以刘宋山水诗为代表的文学倾向时说:“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故能瞻言而见貌,即字而知时也。”(注:《文心雕龙·物色》。)所以,刘勰正确地看出山水文学不是以吟咏情性为主,不以艺术为追求目标,而是以图写自然物的漂亮外观为主,追求的是美,“物色”也与用于表现情性的艺术形象(即后人所谓情景交融中的“景”)无关。只要不太极端,刘勰对这种倾向是非常欣赏的。他在《文心》一开始便说文(美)“与天地并生”,充分肯定了美的存在合法性。
在此基础上,刘勰进一步说明文章的美(文采)存在的必然性。根据《易传》,刘勰认为,人与天地相参,因而人在宇宙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为“性灵所钟”,为“五行之秀”、“天地之心”。有了人就有语言,有了语言就有语言的美,刘勰认为这是“自然之道”,即自然而然的过程。为了强调这一点,刘勰在叙说完宇宙中的形文、声文之后说:“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注:《文心雕龙·原道》。)这里的“彩”与“文”是互文见义,都是文采的意思。刘勰的意思是说,蠢笨无识的事物都有浓郁的文采,作为万物之灵有心有识的人怎么能没有文采呢?所以,刘勰说,除了有天文地文即天地自然的美之外还有人文即人类语言的美。刘勰的整体论证很简单,宇宙间的天地万物无一不有漂亮的外观,人的语言也自然有漂亮的外观。仔细阅读《原道》篇,我们会发现其中的“文”字含义非常模糊,它自然可以翻译为“文章”,但很多时候这里的“文章”可以跟“文采”直接等同,往往是美(有魅力的外观)的同义词。刘勰此时好像过分注重文采而忘了“文”或“文章”除了文采即外观之用一面外还有传达内容的实质之用一面。比如,他谈到“人文”时提到《易传》,他特别注重的是其中的《文言》:“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注:《文心雕龙·原道》。)又如,他称孔子删定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木铎起而千里应,度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注:《文心雕龙·原道》。)他所说的文章偏于漂亮的文辞即文采,可以说是昭昭可见的。只有在“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一语出现以至《征圣》、《宗经》篇中,“文”才有从其实质方面即传达儒家政治伦理为内容的语言构成方面而成其为文章的含义。但即使在文以明道这一说法中,文章的美仍然没有被文章的实用性质排斥掉,“明道”也不单是表现道、传达道,而且还是光采道、炳耀道。
《情采》篇一般认为是讲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我们前面说过,“形式”一词既可以指文章用以传达内容的实质方面即实用性质,又可以指与内容关系不大仅供观赏的外观方面即审美性质,而通常我们谈及与内容相对的“形式”时指的往往是前一方面(文章的实用要素);因此,如果这样使用“形式”一词,《情采》篇显然就不是讲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而是内容(“情”)与文采(“采”)的关系。不过,如果,“形式”一词是在“外观”意义上被使用的,如同“形式主义”一名中那样,说《情采》篇谈的是内容与“形式”(美的外观)的关系就是完全正确的。因此,《情采》篇又是《文心》重视文学美的一种典型表现。在《情采》篇中,刘勰提到另一种“形文”、“声文”,它们与“情文”而非“人文”相对。我们已经引述过原文,从中可以看出,形文指五色,声文指五音,二者一为绘画对象一为音乐对象。按今天的看法,形文即绘画中的美,声文即音乐中的美(注意:不是绘画、音乐中的“艺术”),所谓纯粹绘画、纯粹音乐就以它们为对象。刘勰认为与之相应的“情文”,指由仁义礼智信(“五性”)而成的“文”(美)。文学美就是“情文”,所以说“五情发而为辞章”。他由此断定“情文”即文采的存在是必然的,是“神理之数”。考虑到《情采》篇是对各种类型的文章而不只是诗赋等特定文体而言的,刘勰文章必有文采即文章必美的观念就非常明显了。我们不妨引一段为证:“《孝经》垂典,丧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韩非云:‘艳乎辩说’,谓绮丽也。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注:《文心雕龙·情采》。)《孝经》作者、老子、庄子、韩非攻击文采(美)的言论,都被刘勰颠倒过来,成了追求文采(文学美)的见证。
《风骨》篇历来研究者对其争论颇多,对“风骨”究竟何所指不甚明了。我们在此不打算加入这一论争,我们感兴趣的只是篇中下列一段话:“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章之鸣凤也。”(注:《文心雕龙·风骨》。)不论“风骨”确切含义如何,由这段话看来,刘勰认为,文章有文采而缺乏风骨,好像五彩缤纷的野鸡,美是很美却不能远走高飞;有风骨而缺乏文采,好像高飞天上的鹰隼;既有风骨又有文采,好像凤凰既美丽又能高飞。刘勰虽然认为鹰隼高于野鸡,风骨高于文采,但他又认为最好是像凤凰那样,风骨、文采兼而有之。所以,即使在这里,刘勰仍然是肯定文章中审美性质的存在的。
所以,如果说《文心雕龙》的主要目的是指导人们怎样写好文章(掌握诸多“驭文之术”)的话,刘勰是希望让人们写出像凤凰一样既能远走高飞又能赏心悦目的文章,“贵器用而兼文采”是其一贯主张(注:《文心雕龙·程器》。)。他对文章赏心悦目一面的重视贯穿于《文心》全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等篇,主要就是以如何创造文学美(文采)为目的的。在这方面,刘勰研究得比当时任何一个文论家都更全面、深入、细致,涉及声律、用典、对偶、夸张、比喻(比)、寄托(兴),甚至篇章字句等。我们的文学理论往往把它们称为“写作技巧”或“修辞技巧”,这种说法本身并没有错。但这种说法容易让人以为它们只是文学理论中的次要方面,不能让人认识到美的文章恰恰靠它们才能创造出来。不错,它们涉及的是“修辞”问题,但文学美作为文章的漂亮外观本身不就是通过对言辞的修饰润色而产生的吗?美在外观,文学美在文辞的外观,“修辞”不正是创造美的活动本身吗?“修辞”本身应该作为主要的文学活动之一而不只是一种附加活动加以对待。所以,我们认为,同关于文章的艺术性质的学说可以在适当的意义上称为诗学一样,研究文章审美性质(文采)的学说可以在适当的意义上叫做修辞学。声律、用典、夸张等只是修辞学的实践部分,修辞学的本质部分当为对“文采”本身的研究。前述刘勰许多讨论可以说就属于修辞学本质部分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文心雕龙》才可称为文学理论著作而非仅为文章学著作。也是在同样的意义上,从文学观念发展的角度,我们才肯定刘勰的《文心雕龙》体现了“文学”空前未有的自觉。
四
与刘勰《文心雕龙》一样,从重视文学美(文采)的角度体现文学自觉的著名代表,是比刘勰《文心》稍晚一点的萧统《文选》。《文选》的选文标准在唐代以后经常遭到责难,原因是它的形式主义倾向。萧统本人和刘勰一样大体上持文质彬彬的调和论,但在《文选序》中他却显示出了对文章审美性质的极度重视。《文选序》有三个地方表现了萧统关于“文”的观念。其一是在叙述“文”的起源发展时,他和刘勰等人一样,认为“人文”开始于伏羲画八卦、造书契,由此说明了“文”的地位很高。然后他说:“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其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注:《文选序》,见《文选》,李善注本,上海书店,1988年。)说明事物都是“随时变改”的,文章由质淳而趋于文华也是必然的。这表明他完全肯定当时文章追求文采的趋向。第二个表现他的文学观念的地方是在他叙述完各种文体之后所说的话:“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注:《文选序》,见《文选》,李善注本,上海书店,1988年。)萧统提到三十多种文体,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实用性的“经国文体”,但他最后却不说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注:《文选序》,见《文选》,李善注本,上海书店,1988年。),而认为它们可供“入耳之娱”和“悦目之玩”,也就是指它们都适于观赏之“用”。我们说过,美在外观,文学美在文章的外观,所以,美的价值正好是适于观赏,赏心悦目是文采对人的基本“用途”。萧统不去强调文章在经纶事务方面的价值而注重其观赏价值,可见他对文章审美性质的关注。
《文选序》第三个表现萧统文学观念的地方是他对选文标准的说明。他宣称,周公、孔子的经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不能删削剪截,所以不选。老、庄诸子的子书“以立意为本,不以能文为宗”,所以略去。贤人、忠臣、谋士的话很漂亮,但散见于诸多典籍中,过于繁杂,也不入选。至于史书,大体上用来“褒贬是非,纪别同异”,与篇章不同,也不入选。但史书中的赞论序述却另当别论:“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注:《文选序》,见《文选》,李善注本,上海书店,1988年。)最值得注意的是,这虽说的是史书中赞论序述入选的原因,但实际上可以视为《文选》所有文章入选的原因,因此突出表现了萧统对文章的看法。他显然认为文章应该像赞论一样“综辑辞采”,像序述一样“错比文华”,从而都“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沉思”意为精心构造,“翰藻”指文辞美丽。“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意即文章应以文采为中心精心结撰而成。由此可见,他认为文章之所以为文章就在于它有文采,也就是它有令人赏心悦目的外观。这大概就是后人指责他提倡“形式主义”(“淫靡”文风)的主要原因。在我们看来,不管萧统《文选》是否实际体现了他的上述立场,在将“形式主义”作“文采主义”理解的含义上,他在《文选序》中确实表达了颇为极端的形式主义文学观念,这种文学观念从积极方面看来鲜明地体现了当时人对文章审美性质的觉悟。
事实上,追求美的文辞是刘勰、萧统时代人们的普遍观念。连钟嵘在论诗时都主张“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除了要求诗因“吟咏情性”而有动人力量(即艺术性质)之外,还要求诗在语言上华美(即有审美性质)。陶渊明的诗之所以被列入中品,主要就因为“世叹其质直”(注: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甚至有人认为他的诗是村野的“田家语”(钟嵘本人只是稍有保留,认为他的有些诗句不是“田家语”,有点文采)。钟嵘理想的诗是曹植那样除了“骨气奇高”还“词采华茂”的“体被文质”的诗。一个论诗主要从其艺术性质出发,提倡自然真美的文论家,都免不了文采的要求,而不管这种要求是否与他自然真美的艺术要求有无冲突,这就可见文采(文章的美)已经如何地深入人心了。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梁元帝萧绎所说的“文”明明偏于以艺术性质为主的诗歌,却还要在“情灵摇荡”之前加上“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诸语(注:见郁沅、张明高编选《魏晋南北朝文论选》第36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因为它们属于钟嵘所说“丹采”的范围。他们希望诗歌既要有艺术性“吟咏情性”),又要美(“词采华茂”)。
当时文论求美的倾向最显著的标志莫过于永明声律论的兴起和流行了。对于声律论的渊源我们在这里不便多谈。我们只从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沈约那里看看声律论的精神实质所在。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沈约说:“若夫敷衽论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数,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注:《宋书》,卷六十七。)其中“宫羽相变,低昂互节”,“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几句,可以说是声律论的基本纲领。声律论是根据当时人们对汉语声母、韵母尤其是声调的平上去入的认识,对文章声、韵、调方面提出的要求。从沈约的上述言词可以看出,声律论是要使声调的平上(所谓“浮声”)与声调的去入(所谓“切响”)以及声母、韵母彼此之间的搭配错落有致,差异中见和谐,避免阅读起来单调乃至拗口,达到刘勰所谓“玲玲如振玉”、“累累如贯殊”的悦耳动听效果(注:《文心雕龙·声律》。)。可见,声律论无非是一种关于文章声音美的理论,是当时追求美的文章的“修辞学”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因而也是文章审美性质趋向自觉的显著证据。
总之,如同当时以骈体文的形成和盛行为标志文学中出现了形式主义文风、六朝文论尤其是南朝文论中也相应出现了以文采为追求目标的形式主义文论,这是一个确凿有据的历史事实。形式主义文学观念确实是六朝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文学观念,体现这种文学观念的专题、非专题论述在六朝著述中俯拾即是,像著名的文笔之分说和声律论都与之直接相关。所以,研究六朝文论不可能不涉及形式主义文论。但一涉及形式主义文论,研究者又不可能不从自身的立场对它作出理解和评价。就我们的观点而言,形式主义文论并不是一种极端化、绝对化文章的审美性质的理论和主张,而只是以研究和提倡文章的审美性质(文采)为目标的一种文学理论,它表现为当时人们对构成文学性的要素之一的文采的重视和强调,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这是六朝时期文学自觉的鲜明表现。
(附注:本文《文心雕龙》引语多采自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齐鲁书社,199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