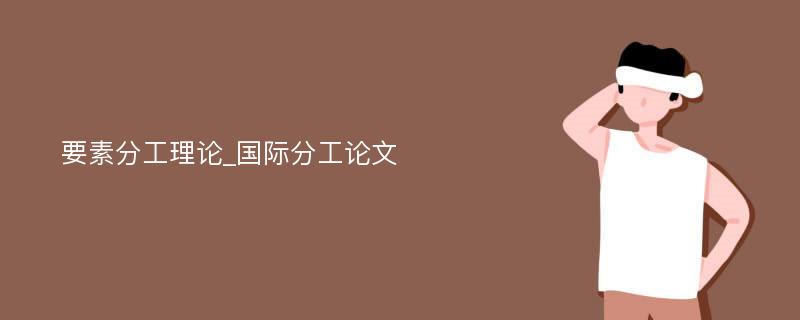
要素分工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要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要素的跨国流动不断增强,国际贸易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突出表现为中间产品贸易迅猛发展。国际贸易商品中传统意义上的“美国制造”、“日本制造”、“中国制造”的产品几乎不存在,大部分贸易参与国不再仅仅出口最终产品或完全由本国生产的产品,转而专注于与其禀赋优势相关的生产过程中的特定环节、工序或零部件,并通过国际贸易实现生产链(价值链)的国际衔接。最终产品的生产通常不再由某一个国家独立完成,“世界制造”(Made in the World)成为当代国际贸易商品的本质特征。对于这些全球化和国际贸易中的新变化,学术界赋予了不同的名称,如价值链切片(Slicing the Value Chain)、地点分散化(Delocalization)、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ing)、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中间品贸易(Intra-mediate Trade)以及片段化生产(Fragmentation)等。尽管上述称呼各不相同,但都旨在描述一个共同现象,那就是国际贸易在实现生产地点和消费地点跨国分离的同时,不断实现着生产过程自身的跨国分离。国际分工不再以“产品”为界限,而是以“要素”为界限了。因为一件最终产品的全部价值已不再完全由一个国家的本土要素所独自创造,而是多国“优势要素”共同创造的结果。从本质上看,这种新的国际分工形式可称为“要素分工”。
“要素分工”的兴起,对国际贸易的基础、国际贸易格局以及国际贸易的利益分配等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甚至无法使用传统意义上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统计量(如原产地、顺差和逆差、贸易条件等)来准确地度量贸易流的真实状况,依托传统理论和传统统计工具所制定的贸易政策和竞争政策不再有效,甚至适得其反。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以全球经济再平衡为由要求人民币币值重估只会对“中国制造”(更确切地说是“中国组装”)的最终产品销售价格产生影响,而不会恢复其他国家相应产品的竞争力。因此,国际贸易理论亟待创新。
国际分工演进与要素分工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当前国际分工的新形式——要素分工,从本质上讲是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的结果。因此,要从根本上理解要素分工,就离不开对分工的理解以及对国际分工演进趋势的把握。
(一)分工与专业化及其演进
分工和专业化是两个须臾不可分离的概念,有分工就有专业化,有专业化就有分工,只不过专业化是针对个人而言的,而分工则是指多个劳动者之间的专业化协作关系。在经济学家那里,分工和专业化是一个古老而又没有太多争议的话题。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富论》开篇就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所表现出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①两百多年前的这一精辟论述,至今仍是经济理论研究的出发点。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分工时,多将分工视为既定事实,偏重于分工的效益、产品和零部件的分工、地域分工、科层组织和市场分工等方面,强调分工和专业化所带来的节约以及对生产力进步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精辟地论述了分工演进的决定问题,认为以劳动工具为代表的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分工的产生和发展,决定了分工的深度和广度。马克思强调职能的分工——“如果说工人的天赋特性是分工赖以生长的基础,那么工场手工业一经建立,就会使生来只适宜从事片面的特殊职能的劳动力发展起来”②,并指出“工具集聚发展了,分工随之发展,并且反过来也一样。正因为这样,机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使分工加剧,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剧也同样引起机械方面的新发明”③。斯密认为“分工受限于市场范围”,而杨格的研究则进一步指出,不但市场规模决定分工程度,反过来市场规模也被分工的演进所制约,同时指出市场规模不仅由人口规模而且由有效购买力所决定,而购买力又由收入所决定,收入由生产力所决定,生产力又依赖于分工水平。④这意味着分工与市场规模之间产生了一个动态良性的循环机制,使得分工水平和市场规模得以不断增加。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家则认为,分工演进是因为存在着分工利益与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这意味着:如果交易效率过低,则每个人不得不选择自给自足,因为交易费用超过了分工和专业化所能带来的好处,以至于每个人只能生产包括中间品在内的多种产品,从而其运作规模小且效率低。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在分工利益与交易费用之间进行适当权衡,可能会导致分工和专业化的出现及其程度提高,即当交易效率超过临界值时,分工和专业化开始出现。随着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交易频率以及由此产生的交易费用随之提高,这又限制了分工进一步发展。接下来又需要交易效率的提高,以促进分工的发展,如此往复,分工不断向前演进。
从分工的技术属性看,生产活动可以被分解为许多最基本的单位,斯蒂格勒将之称为“职能”,而赖宾斯坦则称之为“操作”⑤。因此,所谓专业化就是一个人或者组织减少其生产活动中职能或操作的种类,或者说,将生产活动集中于较少的操作上。分工的演进过程可以被理解为:随着时间的变化,从一组完整的生产活动中分离出去的基本生产操作数量的变化。此外,杨格认为分工的最大特点就是迂回生产方式。因此,如果从迂回生产的角度来刻画分工和专业化的演进过程,就是生产的迂回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就是在生产与消费两点之间绝对地增加物质性中间环节和延长流转路径的过程。按照历史的顺序,分工导致的迂回生产表现为几种不同形态:第一种形态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一般分工,例如人类历史早期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分工;第二种形态就是产品专业化,即以完整的最终产品为对象的专业化,例如斯密所论述的制针业;第三种形态是零部件专业化,例如在汽车工业中,某些企业只生产发动机,甚至只生产发动机的某个零部件;第四种形态为工艺专业化,即专门进行产品或零部件生产的一个工艺过程,比如铸造、电镀等;第五种形态是生产服务的各种职能的专业化,例如专门进行工具及其他工艺装备准备、设备维修、运输等服务。⑥上述各种形态的演进在相当长时间内十分缓慢,但进入工业社会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后三种形态的分工已经具备了要素分工的基本特征,当其跨越国界就成为国际要素分工。生产力水平、市场规模、交易效率、技术变化等,都是决定分工演进和生产迂回程度的关键因素。
(二)从产品分工到要素分工
从空间上看,分工的发展是一个逐渐延伸和扩展的过程,与此相伴随的是市场的统一与扩大,从某一地区扩展到全国,并进而冲破国界发展成国际分工。国际分工演进的历史,就是在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中,随着跨国交易效率的提升,迂回生产过程不断延长,不断向国际市场延伸的历史;就是迂回生产链各个环节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历史;就是迂回生产链各个环节在国际市场中寻找最适生产地点的历史。
我们知道,传统的国际分工是产业部门之间的分工,即工业制成品生产国和初级产品生产国之间的分工以及各国不同工业部门之间的分工,分工的边界是产业。其特点就是各国根据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并根据比较优势逐渐成为迂回生产链某个环节的专业化产品生产者,而迂回生产链条中各环节(指产品)也在这一过程中,根据比较优势被配置到了最适合的生产地点。进入20世纪80年代,信息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利用全球资源的成本降低、远距离多时空经营交易的便捷可行以及商品和要素流动障碍的消减,使得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趋势不断加强,市场范围、市场规模以及世界生产力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迂回生产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为真正的国际迂回生产。此时,价值链上的各个生产活动和各项功能性活动,由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和交易成本的下降,能够在不同国家间实现更加细密的专业化分工,国际分工因此表现为同一产业不同产品之间和同一产品不同工序、不同生产环节、不同增值环节之间的多层次分工。这种分工的界限是生产要素,是价值链上劳动要素密集、资本要素密集、知识要素密集、技术要素密集或其他要素密集性质的各个环节之间的分工。换言之,产品价值链上的不同生产环节或工序按照其要素密集度特征被配置到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和地区,国与国之间的比较优势更多体现在价值链上某一特定环节的优势。原先基于比较成本和要素禀赋的国际产品间分工和贸易进一步让位于基于要素可流动的产品内贸易、垂直专业化贸易和公司内贸易,各国以各自的优势要素参与国际分工从而共同完成最终产品的生产,国际分工形式从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发展。这是国际分工日益细化的必然结果。
当国际分工从产品分工发展到要素分工后,国际分工的细化反过来又会推动要素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产生一个良性的正反馈作用机制。这是因为:其一,分工越是细化,就有越多的生产环节从技术属性上自迂回生产的生产链中独立出来,也就是中间产品生产过程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中间产品的专业化程度也越来越高,中间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要素投入也就越来越专门化,中间产品的要素特征表现得也就越发明显。其二,分工的细化使得要素职能日益专门化,要素异质性日益增强,提高了彼此替代的难度。以劳动要素为例,专业化劳动的出现,加深了劳动要素间的差异,不仅不同层次之间的劳动力要素转移是有障碍的,而且同一层次不同工种之间劳动力要素的转移也是有障碍的,这种障碍(或者说替代的难度)会随着分工的深化愈来愈高。资本要素也是如此,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专用性。在国际分工程度较低时,参与国际迂回生产的中间产品较少,因此国际分工主要表现为以产品为界限的分工,要素专用性并不明显。而一旦国际分工发展到零部件的分工、生产环节和工序的分工时,参与国际分工的中间产品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化、越来越专门化,要素的专用性特征也就越来越显著,从而由该专用性要素所带来的比较优势也就越发明显。因此,从更深意义上看,这种中间产品的分工不仅意味着最终产品的生产是多国要素共同参与的结果,同时还意味着各国赖以参与国际分工的优势要素会在专业化生产过程中得以不断加强,国际分工也就越来越表现为以要素为界限。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要素分工的发展主要表理为两种形式:一是同一产品价值链被分解为若干独立环节而处于不同企业的控制之下;二是尽管这些不同的环节仍然处于同一企业(如跨国公司)的控制之下,但跨国公司却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将价值链的每个环节放到最有利于获得竞争优势的地点。当前全球中间产品贸易的迅猛发展就是上述第一种形式的典型表现,而当前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则是第二种形式的典型表现。当然,上述两种现象并非独立存在的,在大多情形下是一种相互融合、相互依赖、共生发展、合为一体的国际经济现象,即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现象。⑦这种一体化不仅表现为当今贸易和投资在流向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在时间上具有同步性,而且表现为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呈现互补共存、互动发展的格局。
要素分工的实质
当代国际分工从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发展,其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是跨国公司。要素分工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和贸易活动的必然结果,要素分工的实质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整合。
首先,要素分工是跨国公司适应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生产方式变革的产物,是跨国公司所构建的以价值链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形态。企业生产产品的过程就是创造价值的过程,如果我们把产品的生产过程分解为一系列互不相同但又互相关联的经济活动,这一系列环节联结成一条活动成本链,其总和即构成企业的价值链。在工业经济时代,大规模生产方式决定了其组织形式必须是根据垂直整合原则和制度化的社会、技术分工而组构的大型垂直一体化企业⑧,全能型企业也就成为主导发达国家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生产活动日益高度化和复杂化,同一产品价值链上的增值环节变得越来越多,分工越来越细,结构也越来越复杂,全能型企业成为“不能承受之重”;另一方面,模块化生产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生产可分性”不断增强,企业可以利用社会分工将生产的某些阶段交由其他企业来完成。于是价值链开始分解,一些在某个增值环节专业化生产方面具有要素优势(技术更为精湛或成本更为低廉)的企业就会加入进来。如此,一个新的以价值链为基础的分工模式便产生出来。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价值链的分解和整合超越了国界,出现了国际性的劳动分工和生产协作。跨国公司价值链中不同环节的分布,不再局限于一国地理范围,而是以全球市场为依托,实现研究与开发、生产制造、采购与销售、服务等各个环节的全球网络一体化分布和全球优化配置。跨国公司不但要从各国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自然资源、资本)的成本和质量差异中获得好处,而且要通过培育全球范围的协同优势,提升对全球不同市场需求变化的响应和控制能力,全面提高公司竞争优势。
其次,要素分工是跨国公司所经营的“全球生产体系”的产物。在非全球化的环境下,虽然跨国公司的生产因其跨越国界而具有国际性,甚至因其跨越多国而具有世界性,但是由于其散布于世界各国的子公司、分公司所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供应当地市场或返销母国,所以世界各国的生产过程之间并不具有内在的生产关联性,国际分工也主要是发生在最终产品之间,或者说此时主要分工形式还是以产品为界限。当跨国公司进入全球一体化经营阶段时,散布于海外的子公司不再是独立运作或仅与母公司发生简单联系,而是与母公司及其他子公司保持高度一体化联系。跨国公司根据不同区位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将生产活动及其他功能性活动进行更为细密的专业化分工,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可流动的生产要素不断追逐流动性较弱的生产要素。一方面,基于要素的可流动性,跨国公司将可流动的资本、技术以及管理等要素,安排到东道国并与东道国的不可流动优势要素相结合,以优化资源配置;另一方面,跨国公司根据产品生产环节的要素密集度特征将其配置到最具竞争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生产,以降低生产成本。此时,任何子公司或分公司所服务的对象不再是分散、独立的当地市场,而是整个跨国公司网络所“瞄准”的区域市场乃至全球市场。由此,产品生产在世界各国之间经由跨国公司的网络体系建立起有机的内在联系,组成了“全球生产体系”的实体部分。正是由于跨国公司组织的全球生产体系使得国际分工超越了国家和产业边界,而转向企业内部、产品内部,传统的以产品为界限的分工也因此演变为以要素为界限的分工。在跨国公司看来,遍布全球的各分支机构的国别属性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在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中的确切位置。⑨
第三,作为要素分工直观表现的全球中间产品贸易也由跨国公司所“掌控”。当代全球中间产品贸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跨国公司内部的中间产品贸易,二是标准化中间产品的贸易。尽管这两者的产品类型有所不同,但都是在跨国公司的“掌控”之下。跨国公司内部的中间产品贸易主要源于那些产品本身所蕴涵的知识、信息和技术特性使得其在外部市场上进行交易面临着较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此时跨国公司就会通过FDI的形式,设法把所需要的、分散在各国的生产活动联合起来,把国家间、企业间的交易转变为公司内的交易。这一形式实际上就表现为我们上文所指出的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现象。标准化中间产品的贸易不需要跨国的资本流动,即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中间品生产者并不是通过“要素契约”联系在一起,表面上看跨国公司对此无绝对的控制。仔细深究,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之间的这种中间品贸易,也并非通过“商品契约”联系在一起。两者的关系较市场上的一般买卖双方更为密切一些,通过介于商品契约与要素契约之间的所谓的“超市场契约”联系在一起,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安排这样的生产,形成庞大的介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第三种组织”。这种组织形态仍然是由跨国公司所掌控,或者说跨国公司是整个生产环节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一个典型的事实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主要就是融入领导型跨国公司管理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在此过程中,要不断接受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给予的一些规范化的参数指导,按照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要求进行中间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因此,当今全球要素分工环境中出现的“第三种组织”形态,其实正是跨国公司管理全球价值链的表现形式之一。
要素分工的基本特征
国际分工发展到以要素为界限的分工时,表现出了迥然不同于以往的诸多特征。
在要素分工环境中,“世界制造”成为越来越多贸易商品的“原产地”。传统的由单个国家独自完成全部生产过程并出口最终产品的生产模式,正在被全球分工协作的生产模式所替代。产品的生产过程超越了国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迂回化国际生产。产品的生产也不再是个别企业的孤立行为,而是在全球生产网络或体系的基础上,在全球范围进行相互协调和合作的企业网络组织框架内进行的全球化生产行为。现有文献中的很多案例都对此进行了很好的描述,例如Dedrick和Linden在研究苹果iPod播放器的全球价值链分布时指出:一款价值144美元的苹果iPod播放器,其中有价值约73美元的硬盘驱动器(HDD)以及价值23美元的显示器由日本生产,价值13美元的处理器由美国生产,价值4美元的电池由韩国生产,其余价值共29美元的部件由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生产,最后4美元价值由在中国进行加工组装所创造。⑩这种“世界制造”也意味着,任何一个国家或企业所生产的最终产品中自身创造的价值只能占据该产品最终全部价值的一部分。
在要素分工环境中,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和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增强,突破了原有要素禀赋理论分析框架下所“锁定”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的实现形式不再体现于出口产品自身,而体现于出口国所参与的价值创造环节。随着生产分割技术的不断进步,产品生产的迂回程度被不断延长,而每一个生产环节作为价值链上的一个特定环节,都可以由不同国家、不同企业进行专业化生产。传统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垂直分工,不再体现在部门间、产业间甚至产品间,而是表现为劳动密集型工序或零部件生产与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工序或零部件之间的分工,甚至是设计环节与制造环节的分工。比如,产品设计由发达国家进行,产品制造则由发展中国家进行,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加工厂”和“制造车间”。此时,国与国之间的比较优势更多地体现为价值链上某一特定生产环节上的优势,从而导致国与国之间按价值链不同环节进行分工的现象。跨国公司则基于全球竞争战略的考虑,将价值链中的每个环节分别配置到最有利于获得竞争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国际分工也就表现为:一国以优势要素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也以优势要素吸引国外直接投资,从而依据优势要素融入国际价值链的特定生产环节。而一国分工地位的提升,将主要表现为沿着产业链条的攀升或产品工序所处地位的攀升。
在要素分工环境中,分工发展呈现出多维度、不平衡的特性,发展中国家更容易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但也更难向更高的分工层次攀升。要素分工的发展,不仅表现为横向上分离出诸多不同工种,而且在纵向上还分解出许多不同层次。各个国家依据各自的优势要素,在要素分工中选择和发展合适的工种和层次,从而使得国际分工呈现出多维度发展特点。这也使得在产品分工时代被排除在国际分工体系之外的落后国家,在要素分工中可以参与国际分工并从中获利,只要该国在任何产品的某一生产环节或阶段上具有比较优势。而与这种多维度国际分工相伴随的却是劳动分工在国际间的不平衡发展。这是由于国际迂回生产链的延长以及国际分工的细化,对国际间的劳动分工产生了两种方向相反的影响:一方面,处在较低分工层次上的劳动横向差别变得越来越小,资产专用性也逐步弱化为通用性。因此,处于这个层次上的国际分工具有“进入壁垒”低的典型特征,这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分工的主要形式。在国际分工的利益分配方面,参与者仅以简单劳动等初级要素参与国际分配。另一方面,它又使得处于较高层次上的劳动横向差别变得越来越大,劳动要素的异质性和专业化逐步增强,专业化知识在分工中的重要性日益显著。与之相伴的是,越来越多的基本生产要素的职能日益专业化而逐渐成为专用性资产。因此,处于这个分工层次上的“进入壁垒”和“退出壁垒”都比较高。在国际分工的利益分配方面,其参与者不仅以专业化劳动,而且以专业化知识和专用性资产参与国际分配,这也是发达国家控制国际分工体系的主要依托。
在要素分工环境中,国际分工利益不再取决于进口和出口什么,也不再取决于企业产权和产品的产地,而是取决于参与国际分工的要素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参与了什么层次的国际分工。这是因为,最终产品的生产需要使用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生产的中间投入品,在要素全球可流动的情形下,甚至中间产品本身可能都是多国要素共同参与的结果,因此贸易品的生产国和生产企业并非贸易利益的全部归属方,贸易利益所得必须按照参与生产贸易品的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从上述意义上来说,在要素分工快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按要素分配也全球化了,参与国际分工的要素的质量和层次是决定一国分工地位及其获益能力的关键。不仅如此,一国自身所拥有的要素素质还决定了其能够吸纳什么层次的生产要素,进而能够影响其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这是因为,经济活动中各种生产要素之间的组合都有一个最优比例问题,这种最优比例不仅体现在要素的数量组合上,同时也体现在要素的质量配比上。发达国家由于拥有诸如技术、标准、品牌、国际营销网络、市场竞争制度等先进要素,不仅能够利用自身的先进要素占据国际分工价值链的优势片段,还能够依托这些先进要素吸纳全球的先进要素,进一步控制全球价值链,因此撷取了国际分工的大部分利益。而发展中国家普遍拥有的则是专用性较低的一般要素(如廉价劳动力),只能占据国际分工价值链的低端位置,其吸纳全球先进要素的能力要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处于被发达国家先进要素整合的地位,只能获得少量的要素报酬。
在要素分工环境中,国际分工不仅具有互利性,更突出地表现为共生性。要素分工使得每一个国际分工参与国都是价值链上某个或某几个特定生产环节的专业化生产者,贸易的性质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从传统分工模式下为最终产品价值实现而进行的国际交换转变为确保全球生产的正常进行而贸易。因此,以此为内容的经济全球化能否持续,取决于融入到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每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或者说,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产品价值链上的任何一个区段出现不可持续性,必然影响到贸易进而影响到最终产品价值的实现,其他国家也难以获取预期的国际分工利益,进而造成整体意义上的不可持续性。要素分工所带来的上述变化,不仅意味着国与国之间开展分工具有传统意义上的互利性特征,同时还意味着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呈现出分工利益彼此相依的“共生性”特征。
要素分工发展与全球贸易新格局
要素分工的发展,正在使全球贸易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贸易的性质出现根本性变化,传统的国际贸易方式与国际合作方式日益融为一体,并表现为贸易与投资一体化;产品生产过程的国际分散与地区集聚同步发展,生产活动在国际间高度迂回的同时,部分生产环节愈发向具有特定要素优势的地区集聚;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贸易中的重要伙伴,并迅速成为高科技产品的“名义”出口国;要素分工自身的反贸易保护属性,使得降低商品和要素的流动壁垒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主流,贸易保护政策的有效性日趋减弱,保护主义也有了新的形式。
要素分工的发展,推动着当代“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当代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得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生产活动被跨国公司联合起来。随着中间产品特别是难以定价的中间产品的不断增多,跨国公司所联合的生产活动越来越多,跨国公司不断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中间产品生产是由跨国公司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实现的,越来越多的中间产品贸易成为跨国公司的公司内贸易。在这里,贸易和投资都是围绕跨国公司国际生产而进行的,投资是发生在价值链各个生产环节上的投资,是跨国公司寻求要素结合效率的手段而不是服务目标国生产的手段,投资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贸易实现分工收益,是为贸易而投资;国际贸易也不仅是生产的结果,而往往表现为生产的环节,是实现投资行为最终目标的手段,是“为生产而贸易”。在跨国公司的主导下,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活动一体化了。
要素分工的发展,正在使国际生产中的“网络”和“区位”变得愈发重要,生产的国际分散与地区集聚同步发展。Gereffi和Sturgeon都曾指出,在过去的20年间,许多产业的产业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传统的一体化企业发展成为生产网络组织。(11)这意味着,产品价值链全球分解和国际间迂回生产并不是单线条发展,而是形成了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参与要素分工的企业镶嵌于相互依赖的分工网络之中,网络使企业能够摆脱自身组织结构和区位的局限,为全球生产链而生产并参与全球化竞争。网络中的制度安排和交易效率决定了网络的厚度和生产的迂回程度,具有优势要素(如品牌形象、专利、市场网络、研发以及创新能力)且能够控制最终产品市场的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成为了网络的中心,并通过OEM和外包合同控制中间产品和零部件生产者。与此同时,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使得“区位”变得更加重要。首先,跨国公司对片段化生产环节的区位选择依托于各国的要素优势,要素优势决定了一国在网络中的层次,亦即决定了从事何种要素特征的生产环节的生产。其次,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依托于要素流动性,全球生产网络的成长就是流动性相对较强的生产要素对流动性相对较弱的生产要素的追逐,具有低流动性优势要素的区域将更可能成为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片段化生产环节。再次,跨国公司搜索生产区位的过程还将诱发跨国公司主导型产业集聚的发展,一方面,具有专门化生产要素的区域会被众多跨国公司“俘获”,不同跨国公司的类似职能部门和类似生产环节因此而集聚在相同区域;另一方面,集聚本身就是一个地区要素优势的重要来源,产业集聚的正外部性使得企业可以通过置身于集群而获得竞争优势,集群的扩张和增长会使企业更具黏附力,并使集群更像一个整体,有助于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向上攀升。此时,更可能是跨国公司被该地区“俘获”,争相进入该地区以提升自身全球竞争力。
要素分工的发展,通过比较优势的创造效应和激发效应,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带来了重要机遇,也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的结构和技术含量“名义趋同”。在要素分工下,发展中国家不再需要在一个完整商品的生产上拥有比较优势,只要在产品的某一生产环节或阶段具有比较优势,就可以参与国际分工并从中获利,要素分工为落后国家创造了比较优势⑩。而生产要素全球可流动性的增强,会促使本国优势生产要素和国外流入的优势生产要素相结合,多种优势要素协同生产,从而进一步激发本国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在这两种效应的联合作用下,通过吸引跨国公司进驻等方式,全面融入到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中,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产品价值链的梯度转移,成为世界产品的生产地和出口地,充当了跨国公司的“价值增值地”和“出口平台”。由于产品价值链上的不同生产环节和工序往往具有不同的要素密集度特征,对于仅仅在劳动密集型生产阶段和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在其专业化生产的阶段和环节,使用到的进口中间产品完全可能是技术密集型、信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等高级要素密集型产品,从而使得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其专业化生产阶段后的出口产品表现为技术密集型等特征。正如Theodore Moran的研究所指出的,发达国家进口自发展中国家(如中国)的高科技产品,貌似由发展中国家所生产,但实质上其中主要的高附加值部分却产自于发达国家自身。(13)因此,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品”与发达国家的“出口品”进行比较,并得到出口结构和技术含量趋同的结论,不免有夸大其词之嫌。
要素分工的本质是跨国公司整合全球资源,因而其本身就具有反贸易保护的倾向。虽然有学者指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本轮全球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是自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的史上最为严重的经济事件(14),但Chad P.Bown的研究却发现,在此期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虽有所抬头但并不显著,更无法与1929~1933年间大行其道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相比。(15)对此,Kishore Gawande等的研究很有启发意义: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企业游说政府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动力越来越弱了。(16)这是因为,贸易壁垒和生产要素流动壁垒的高低,对要素分工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壁垒越高,国际迂回化生产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也就越高,从而不利于要素分工的发展;反之,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壁垒越低,国际迂回化生产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也就越低,从而有助于要素分工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和要素分工的发展,无论对于发展中国家还是对于发达国家而言,都是机遇和挑战。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如果封闭肯定落后,但被动地参与经济全球化也不一定能够获得发展,关键在于怎样应对。要素分工的发展,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呈现要素优势“互补式”、分工利益“共生性”的国际分工新形式。尤其是在要素可流动的情况下,全球化不仅仅对发达国家有利,对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重要发展机遇(17),甚至对于像中国这样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经济发展形势良好的发展中国家更为有利,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明证(18)。
促进现有优势要素的不断升级和加快对先进生产要素的培育,不仅有利于提升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和地位,而且在生产要素可流动的环境中,还能促进国外更为先进的生产要素向本国集聚。(19)虽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最大的优势是劳动力丰富,并强调以现实的比较优势——丰裕的劳动力为基础参与国际分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永远以廉价劳动力作为参与全球要素分工的基础。相反,我们应该不断提高要素质量,培育高级生产要素,促进比较优势的动态演进,以不断提升中国企业整合各类先进要素进行创新活动和全球化经营的能力,从而不断提高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提高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红利分配中的获益能力。
共同发展、均衡发展的包容性增长模式,是要素分工下实现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道路。具体到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就整体实力而言,中国正在崛起为一个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贸易大国和经济大国,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些困难和问题常常被人为地与中国因素联系在一起,诸如全球贸易失衡、发达国家失业问题、世界石油和能源价格上涨以及环境问题等皆是如此。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要素分工体系,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面临着显著的外部压力。因此,在发展开放型经济进程中接受并继续践行“包容性发展”理念,在经济全球化视野下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倡导“和谐世界”新理念,营造和谐共赢的国际环境,不仅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抓住要素分工发展新机遇,同样也是我国开放型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注释:
①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5页。
②《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0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6页。
④Young Ally,"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The Economic Journal,Vol.38,1928,pp.527~542.
⑤赖宾斯坦:《经济落后与经济成长》,赵凤培译,中华台北台湾银行1970年版,第15页。
⑥盛洪:《分工与交易:一个一般理论及其对中国非专业化问题的应用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1~52页。
⑦张二震、马野青:《贸易投资一体化与国际贸易理论创新》,《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⑧李晓华:《垂直解体和网络范式下的企业成长》,《南开管理评论》2006年第9期。
⑨张二震、马野青、方勇:《贸易投资一体化与中国的战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0页。
⑩Dedrick,J.,K.L.Kraemer and G.Linden,"Who Profits from Innov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 Study of the iPod and Notebook PCs",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19(1),2010,pp.81~116.
(11)Gereffi,G.,"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Apparel Commodity Chai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48(1),1999,pp.37~70; Sturgeon,T.,"Modular Production Networks:A New American Mode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11(3),2002,pp.451~496.
(12)例如,有三个国家分别用1、2、3表示,生产两种产品A和B的单位成本分别为a1、a2、a3以及b1、b2、b3,A与B的相对价格用R0表示。显然,当条件满足a1/b1<a2/b2<R0<a3/b3时,意味着国家1在产品A的生产上具有最大的比较优势,而国家3则在产品B的生产上具有最大的比较优势,此时国际分工的模式即为国家1专业化生产产品A,国家3专业化生产产品B,国家2有可能被排除在国际分工之外。但是,如果国际分工实现了要素分工,比如A产品的生产发生了要素分工,即分为C和D两个部件的生产,为简单起见,假定其他条件均保持不变,则国家3的生产情况不变,此时我们可以将讨论集中在国家1和国家2之间。如果国家1和国家2生产部件C和D的成本分别为c1、c2和d1、d2,不失一般性,则当c1/d1<c2/d2时,意味着国家1在部件C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国家2则在部件D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根据比较优势原理,在要素分工条件下,国家1可专业化生产部件C,国家2可以专业化生产部件D,并因此而获得比较利益。显然,上述情形可以推广到m个国家n种产品的多维情形。
(13)Theodore Moran,"Foreign Manufacturing Multinational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Economy:New Measurements,New Perspectives",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orking Paper,No.11-11,April 2011.
(14)Androw B.Bernard,J.Bradford Jensen,Stephen J.Redding,and Peter K.Schott,"The Margins of U.S.Trad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Papers & Proceedings,99(2),2009,pp.487~493; Eaton Jonathan,Sam Kortum,Brent Neiman,and John Romalls," Trade and the Global Recession",NBER Working Paper,No.16666,January 2011.
(15)Chad P.Bown,"Taking Stock of Antidumping,Safeguards,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1990~2009",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No.5436,2010.
(16)Kishore Gawande,Bernard Hoekman,Yue Cui,"Determinants of Trade Policy Responses to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No.5862,2011.
(17)张幼文:《经济全球化的核心与走向》,《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8年第3期。
(18)张二震:《全球化与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思考》,《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19)张二震、戴翔:《开放利益与国民福利水平互动:以转型为基点》,《改革》2011年第8期。
标签:国际分工论文; 全球价值链论文; 产品价值论文; 产品专业化论文; 组织发展论文; 海外投资论文; 要素市场论文; 产品层次论文; 投资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 比较优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