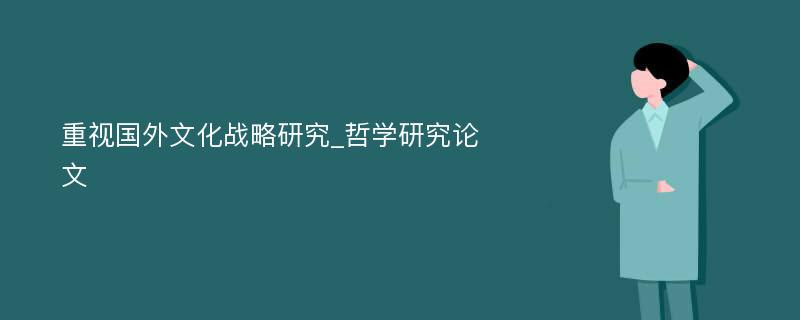
重视国外关于文化战略问题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视论文,国外论文,战略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问题已成为世界普遍重视的“热点”,这不过是集中反映了对人的关注。
●西方理论家把文化战略研究和世界格局变化结合起来,力图为各种文化战略提供理论基础。
●民族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文化,但经济国际化不能消除文化的多样性。民族文化的发展、不同文化的相互作用,将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文化问题现已成为世界上各个思想流派、学术派别普遍关注的课题,进而也成为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鲜明特点。
1983年,在蒙特利尔召开了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这一届大会的主题是“哲学与文化”。会上,东西方各派哲学家虽然观点不同,但在一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因此在闭幕时一致宣称:从整个世界范围看,当代哲学研究的重心正在逐步移向文化问题。近十多年来哲学发展的情况,也已证实了这个论断。
文化问题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受到重视,哲学研究重心的这一重大转移,决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根源。国际格局的改变,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社会主义运动面临挑战,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全球性问题的出现,等等,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把人本身的价值和命运、人类生存和发展问题以十分尖锐的形式突现出来。因此,文化问题研究热潮不过是集中地反映了对人的关注。
早在1970年,荷兰哲学家冯·皮尔森就撰写和出版了一部文化哲学著作,其题目便是《文化战略》。他在书中提出,文化战略就是人类的生存战略。认为研究文化战略的根本目的有两个:一是“防止人类创造出来的缓解人同自然的紧张关系的文化,由于不恰当地应用,转而加剧人同自然的紧张关系,甚至危及人的存在”;二是“防止人创造出来的用以提高人和解放人的文化异化成贬低人和压制人的异己力量”。他提出研究文化战略,也就是要对我们思维和生活方式中正在发生的变化进行研究。
冷战后,西方理论家加强了对文化战略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把这种研究和世界格局、国际形势的变化结合起来,并力图为他们提出的各种文化战略提供理论基础。
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1989年在《国民利益》夏季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该文宣称20世纪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取得了胜利,中苏不得不进行改革和西方文化处于统治地位等现象,不仅标志着冷战结束,更表明将以西方自由民主的普及而作为历史的终结。1993年,他在上述文章的基础上出版了题为《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的著作。1995年,他又写了《信任》一书,提出制度在“历史终结”时呈现趋同的趋势。在制度发生趋同的今天,决定经济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是由文化所构建的社会信任和合作。西方许多学者不赞成福山的论断。如加拿大学者哈格罗夫断定资本主义制度并非历史的终端,但他非常谨慎地拒绝预测未来的社会形式。
在西方提出的种种文化战略理论中,影响最大的当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亨廷顿认为,文化将是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由于文化因素在全球秩序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整个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文明冲突”的历史时期。文明之间的差异是最根本的差异,文明之间的断层是未来的战线。文化的差异加重了经济冲击,“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同时他还认为,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到二十一种主要文明,但存留至今的只有七八种而已。这之中,距西方文明传统最远的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有可能联合起来,向西方的利益、价值和势力挑战。他所谓的“文化冲突”最主要的是指宗教观念和“本土认同”上的差异所引起的冲击。有的学者指出,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表现了美国人不得不面对内外交困和霸权式微的现实。
近年来,西方有些理论家进一步论证,要使西方文化成为“主流文化”,使西方价值观支配国际政治秩序。例如,托夫勒认为,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将不再作为衡量国家实力的主要指标,知识的控制是明日世界争夺权力的焦点。谁家的文化成为主流文化,谁家就是国际权力斗争的赢家。又如,约瑟夫·奈也认为,在当今世界倘若一个国家的文化处于中心地位,别国就会自动地向它靠拢;倘若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支配了国际政治秩序,它就必然在国际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这类观念论的文化史观把全部历史归结为文化史,又把文化史归结为观念史,把文化观念当作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显然是错误的。但上述论调中暴露出的倾向,值得我们注意。
但是,在西方学者和理论家中,观点也不尽一致。一些西方学者深刻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和精神危机。
丹尼尔·贝尔在研究马克斯·韦伯思想时进一步发现,在资本主义精神中存在着相互制约的两种因素,即贪婪攫取的“经济冲动力”和禁欲苦行的“宗教冲动力”。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清教的约束和新教伦理扼制了经济冲动力的任意行事。现代资本主义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已摧毁了清教精神,但“它从未能够成功地发展出一种与变革相适应的新思想体系”。新教伦理曾被用来规定节约和勤俭。但是,“当新教伦理被资产阶级社会抛弃之后,剩下的便只是享乐主义”,“人们将发现道德理想无法革除倔强的物质欲望”。这就造成了一种精神危机,即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
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佩鲁提出一种“新发展观”。他指出,经济的复苏使东方人有机会重新审视传统文明的价值。经济问题往往同社会文化紧紧纠缠在一起,在经济问题的背后往往是严重失衡的非经济问题。经济转型过程不单是经济结构的变动,往往也是人们利益结构的变动,因而必然引起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他还指出:直到最近,西方还坚持认为是它创立了文化,而且就其实质来说,是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文化,这种文化与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办事方式结合在一起。现在,这种文化实质受到了人们的怀疑,其办事方式也受到了非议。这种文化危机要比经济制度失灵更为深刻,其原因就在于人们的思想和感情发生了危机。
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各个部门都是建筑在有效经营基础之上的。在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中,个人必然被当作“物”,而不是人来对待,成为最大限度谋求利润的工具。这对文化发展造成了极大局限性。艾利希·弗罗姆写了《逃避自由》等著作,专门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现代西方社会的整个问题在于物质丰富的另一方面,是精神贫困化的日趋严重。由于滥用本能的冲动,现代西方社会处于混乱迷茫之中。
在苏联解体以前,原苏联哲学家就已十分强调对文化、文明问题的研究。欧亚主义是本世纪20年代就出现的一种关于俄国特殊历史地位的思潮,认为俄罗斯是兼有欧洲和亚洲文化特点的民族。如P·沙维斯基认为俄罗斯文化乃是一种独特的欧亚文明。俄国哲学家H·别尔嘉耶夫也认为,俄罗斯精神矛盾性和复杂性归因于俄国的独特处境,即始终要受到东西方两股世界文化潮流碰撞的影响。这种思潮在苏联解体后又重新兴起。1991年底,《哲学科学》杂志重新发表了原欧亚主义倡导人的系列文章,充分反映了他们企图把欧亚主义作为俄罗斯文化战略和发展模式的理论基础。从周边国家的角度来看,我们不仅要研究俄罗斯和中亚各国的文化思潮,而且还要研究当前日本的文化战略。
自8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杰姆逊作为一位文化理论家,除了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化以外,还着力研究第三世界文化。他指出,现在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可以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则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意识形态受到不断的渗透。因此,第三世界文化如何找到摆脱这种困境的文化战略,是它出路的关键所在。
近年来,美国社会学家、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员约翰·奈斯比特高度评价亚洲的兴起。他在《亚洲大趋势》一书中指出,经济的复苏使东方人有机会重新审视传统文明的价值。亚洲的现代化并不如某些人认为的是亚洲的西方化,而是亚洲式的现代化。亚洲在现代化中保留了自己的传统价值。
现在,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经济也日益国际化。但在世界历史发展的现阶段决不会“取消”国家制度的差别和民族文化的特征。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由于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世界经济联系日趋紧密,促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加强了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但是近几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文化方面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增长,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民族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文化。但是,认为世界各民族必然逐步进入与今天西方相同的“现代”文明是根本错误的;企图把西方文化全盘推行到没有现实基础的东方国家,也是根本不可能的。经济国际化不能消除文化的多样性。独特的区域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不同文化的相互作用将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1991年召开的第二十六届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建立一个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负责起草一份关于文化和发展的国际报告,并得到联合国大会的批准。该报告提出,要探索和阐明文化与发展的某些关键问题,研究文化因素如何决定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看待自己的未来和选择各种不同的发展道路;要“形成一种新的以人为中心、重视文化发展的战略”。
由此可见,加强对国外文化战略问题的研究,探讨文明发展和文明冲突的特点,提出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和文明问题的系统看法,制定一套既能积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又能同外来文明相互作用、积极抗衡的文化战略,已是一项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