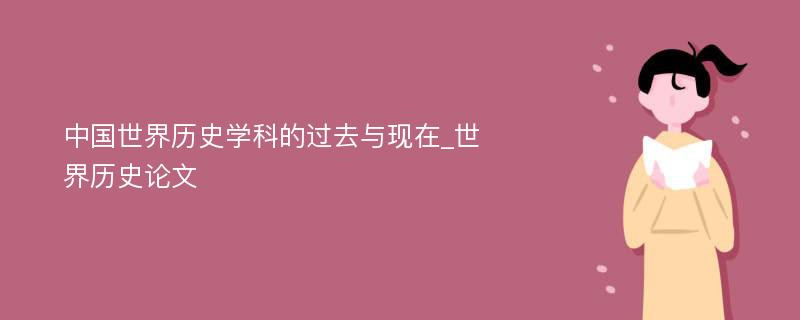
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前世今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史论文,中国论文,前世论文,学科论文,今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郭小凌
世界史研究在中国是一个小学科,以从业人员而论,在一所综合性大学的历史系中,世界史教员大体上占全系教师队伍的四分之一左右。以学科分类而论,世界史为历史学一级学科下属的八个二级学科之一,与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地区与国别史、专门史等处于同一级别。其中,地区与国别史、专门史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世界史学科的部分空间,教员人数与二级学科的几个部门的比例大体一致。但世界史的纵向跨度在三百万年左右,空间范围则在中国之外的五大洲一百九十二个主权国家,再加上约三十个地区,而在高校历史系的基础课程设置与教学时数中,却与两个中国史二级学科相差无几。
这种数量上的“小”在同欧美发达国家高校历史系中外国史教员数量上的“大”的对比中则益发显著。以哈佛大学为例,2010—2011年历史系在职教师四十八人,从事美国史教学与研究的人数占教师总数四分之一(十三人)略强[1],欧、美、日等国家的其他高校大体上都是这种情况[2]。学科从业人数反映了一个学科在国家学科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发展程度等一些质的问题。显而易见,中国世界史学科的规模与它的研究对象及所承载的教学研任务不相匹配。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国策是同时面向内部的改革与面向外部世界的开放,这就迫切需要扩大与加深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外部世界历史的认识。因为不认识外部世界的过去,就不可能认识外部世界的现在,当然也无法更深刻地认识中国自身。然而,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由于规模及人员的局限,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史研究的学人竭心尽力,却仍存在着许多有待填补的缺口,不仅亚非拉美众多国家的历史与文化需要有人做比较深入的探究,即使是一些大国,如美、英、德、法、俄、意、印、加、巴西等国的历史与文化,也有不少细部需要填补。所以无论怎样看,中国的世界史学科都与中国目前的国家地位与发展状况不相适应,这就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史学史问题:为什么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处于如今这种尴尬的位置?
答案中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中国的历史学长期以来一直以中国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史为主。在一所综合性高校历史院系中,中国古代史研究水平的高低往往决定了这个院系的学术声誉。中国古代史学科的这种压轴地位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具有内在的合理性。
历史学是一门颇具难度的专业,因为历史真实,无论是事实的真实还是解释的真实,都不是一块铸好的硬币,拿过来就可以用。每一个历史事实的发现都如同刑侦人员的破案,需要对古代人遗留下来的各种蛛丝马迹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有时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研究。在历史学研究中,越古老的历史,技术难度就越大一些。这主要是因为古代语言绝大部分已经变为死语言,特别是距离近现代更远的古代历史,所遗留下来的文字史料也就越艰涩难懂。比如研究中国古代史,研究者须具备古汉语的知识。研究先秦史,还需要具备甲骨文、金文的释读技能,具备音韵学、训诂学、碑铭学、地理学、年代学、文献学及版本目录学等考据辨伪所必须的本领。这些基本功,尤其是古文字的基本功,乃是先秦中国史学产生以来,经过长期积累总结出来的一整套研究法体系,对学习者来说,绝非短时间即可轻易掌握。仅从语言文字的基本功训练来看,中国古代史研究者在语言方面就需要比中国现代史的研究者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需要更长的培养周期。没有文字学、文献学的功底,没有考据、训诂、音韵的学养,一个学者只能在这个学科的外国打转转儿,进入不了与同行平等对话的殿堂。所以,无论是传统史学技艺的顶峰乾嘉史学,还是近代以来引入了西学史观与方法的中国新史学,都不能离开这套基本功的应用。因此,现代中国史学史中得到公认的大史家,几乎都是此类专业功底极为扎实的学者。正因为登堂入室中国古代史需要越过文字与典籍解读的门槛,所以中国古代史研究一向被视为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正宗。即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和政府的有力引导与推动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产生了一批堪与中国古代史学者媲美的出色史家,也难以取代中国古代史固有的主导地位。
相形之下,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则先天不足,后天又一度失调。所谓先天不足,系指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世界史的史料占有量微乎其微,研究成果几乎乏善可陈。以世界古代史为例,除了印度史领域有一些传统史料,其他领域几乎没有多少第一手史料可资利用,也没有多少具有专业研究水准的成果可资借鉴。而且,20世纪前半叶还谈不上真正的研究。从清末到民国,译介了一些国外世界上古史简编和个别研究性的著作,如清光绪年间的《万国通鉴》,民国期间的《尼罗河与埃及文明》、《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等书籍,从事文学与哲学工作的学者翻译了少量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的作品,如《伊索寓言》、《伊利亚特》、《理想国》之类。此间虽有学者编写过关于西方古代史的书,但多为简单的编译之作。由于缺乏定向研究世界上古史的人才,即使在旧中国的大学之内,也没有真正的世界上古史研究。当时,各大学历史系的主干课程是中国史,世界上古史只是世界通史一门课程的组成部分。当然,有些学者也着手编写初步的世界上古史教材,比如辅仁大学长于先秦史的赵光贤所编《世界古代史》,但深度达不到学科导论的程度。旧中国言必称希腊、罗马的西方史尚且如此,就更不要说埃及学、亚述学、印度学、伊朗学等其他古文明研究了。当然,也不能笼统地说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世界史之贫弱系因史料匮乏,成果稀微。对于古希腊、罗马史而言,中国学者拥有的典籍史料同外国学者相差并不很多,比如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图书馆都收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古希腊、拉丁典籍英希、英拉对照本,即罗埃伯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问题是当时缺少能够使用这些典籍的专业人才。
事实上,世界史研究的难度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学者的进入,其难度丝毫不亚于中国古代史。世界史的一些分支学科,如上古史、中古史的研究难度,甚至要超过中国古代史。因为在世界史研究的基本功中,能够运用现代外语(英语、法语、德语、俄语等)阅读国外刊物和专著,及时掌握学术前沿信息是最起码的专业要求。如果是世界古代史研究者,还应在一定程度上掌握某一时代的死语言,如埃及学家需要掌握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和科普特语,亚述学家需要掌握西亚的楔形文字,印度学要求其研究者能够读解吠陀文献以来的梵文,古典学则要求研究者懂得古希腊文或拉丁文,具有古文献的读释能力。某些特殊的研究方向,如亚述学中的阿卡德史或埃兰史,还要求研究者具有特殊的楔形文识别能力。这当然需要长时间的艰苦训练和潜心钻研的过程。实际上,这些古代死语言本身已经构成了复杂的、独立的学问。以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为例,古希腊语存在众多复杂的语法现象,仅动词就有三百五十多种形态。至于拉丁文,公元前5世纪不同于公元1世纪,公元1世纪又不同于中世纪。而且古希腊和拉丁文文献不仅限于古代典籍,还包括众多出土的铭文。所以,古希腊和罗马史研究者不仅要有拉丁文献学与拉丁文的知识,还应了解并追踪古希腊和罗马的考古进展及其最新成果。由于古希腊和拉丁文及其文献的阅读、识别、诠释均有相当的难度,西方综合性大学普遍设有培养专门人才的古典学系(Department of Classics)或文献学系(Department of Philology),学科的基本内容便是对古代语言和与之相关的古代文献的研究。
对中国研究者而言,掌握这些语言所要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一般较欧美研究者要多一些,因为外国古代的死语言与中国汉语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以古希腊文的学习为例,由于汉语和印欧语属于两个不同的语系,学习现代印欧语言尚且需要众多的学时和课后的记忆及阅读练习,其难度绝不亚于学习古汉语,甚至难过古汉语。学习古希腊文的周期就更长了。所以,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都非常缺乏释读外国古代文字的人才和条件,这是严重制约中国世界古史研究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在这种既缺史料、参考书,又缺能够进入考据层次的研究人员的情况下,即使在海外得到严格专业训练的个别学者,也因客观条件的限制而在国内无用武之地,不得不舍弃专业,专事中国考古和中国史研究,以迎合中国古代史研究一家独大的现实。比如在英国留学埃及考古学的夏鼐、在美国留学西方历史哲学的雷海宗等即是如此。
总之,由于世界史学科严重缺乏支持学科发展所必需的教材、专著、论文、史料集、档案文献等构成的基本参考资料,缺乏专业化的教员,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世界史学科只能是中国史学知识体系中一个无足轻重的配角,甚至构不成一个独立的学科。
当然,中国世界史学科目前与欧、美、日世界史学科在规模方面的差距不能仅用基础薄弱加以解释,19—20世纪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大势其实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西方自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历史学家的主要注意力便开始移向国外。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与文化被移植为欧洲各国的历史与文化的支柱,成为欧洲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基本内容。随着15世纪地理大发现引起的欧洲人向世界各地移民,到19世纪工业化完成之后对亚非拉市场与劳动力的疯狂掠夺与瓜分,使欧美史学家的注意力进一步向外,以适应对外殖民与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需求。这样一来,外国史成为欧洲列强诸国史学的主题,本国史研究反而成为配角。例如,为西方史学专业化进程点下最后一个句号的客观主义史学宗师兰克的代表作,基本都是外国或外民族的历史,其晚年着力最多的也是世界史而非德国史。再如,一度深刻影响西方史学编纂的法国、德国历史哲学家们的视野都是世界历史进程而非国别史、区域史。在世界史对外取向的引导下,自18世纪以来,众多世界史的分支学科均由欧洲学者所创立,譬如梵文、象形文、楔形文、吐火罗文等文字的破译并进而产生的印度学、埃及学、亚述学等难度颇大的新学科。欧洲史学外向型研究的大方向深刻影响了后发的美国与日本史学,确立了今天世界史或外国史研究在欧美日国家史学中无可争议的优势地位。
在欧洲的大扩张时代,中国正处于闭关自守状态,即使是这个时期最聪明的知识分子,也对外部世界所知不甚了了,遑论世界史学科了。当中国闭守的国门被鸦片烟与坚船利炮轰开之后,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志士仁人和知识分子追求的时代主题。虽然在19世纪末叶模仿西方建立起来的新型普通教育与高等教育体系中,世界史是中学以及大学历史系的课程,但这种世界史知识的初步传播并没有进一步导向世界史学科的形成,因为中国人民全力以赴地抵御外敌入侵,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注意力集中于解决国内问题,无暇更多的、深入地顾及外部世界的过去,一般性的世界史认知已能满足时代的需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目标,肇始了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的真正进程。除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停滞,至1997年学科调整之前,中国世界史学科不仅得到确立,而且学科地位显著提高,在许多院校一度达到近乎与中国史平分秋色的地步。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有限度的对外开放(向苏联与东欧开放)的产物。
1952年,中国高等教育模仿苏联的专业设置,将世界史与中国史相分立,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纵向划分成四个段落,由专门的教师分别加以讲授和研究,由此形成了四个互相联系的世界史分支学科,并从组织建制上保证了各分支学科的持续存在与发展,即在各校历史系成立了与中国史各学科相对应的教研室、研究所,组建了相应的教学与科研队伍。学科建制与人员规模同中国史大体相近,从而开始了中国世界学科的蓬勃发展期。经过世界史研究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中国世界史学科不仅编写出了本科生培养所需的基本教材(包括通史与部分国别史),而且还逐步编译了世界史各分支学科的参考资料集,积累了国别史、断代史、专史等专著和译著以及国内外的学术读物。虽然这一时期的世界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等缺陷,吸收国外的成果还有一定局限(这是可以理解的阶段性弱点)性,一手史料的积累还为数不多,但毕竟为进一步的发展打下了较牢固的人员、组织机构与读物基础。显然,世界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与国运、国家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密切与否有着必然的联系。
“十年浩劫”结束之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迅猛发展,中国世界史学科的从业人员焕发出空前的学术研究热情,各领域均取得了质的飞跃性进步,主要表现在学术思想上不再从教条或本本出发,而是从世界史的实际出发展开自己的研究,实现了思想多向度的转变,出现了方向性的全面突破,形成了具体历史观念和解释多样化的局面;研究队伍得到扩大,总体质量显著提高,众多在国内外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人才进入世界史研究领域,使中国的古代至当代世界史的研究不仅进入了以第一手史料为依托的实证研究层面,而且在某些需要古典文献考据的领域,具有了与国外同行平等对话的能力,并赢得了国外学者的敬意。这种学科的飞跃进步可以用当时世界史二级学科的数量加以说明。根据1990年颁布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关于施行《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世界史学科在历史学之下的十四个二级学科中占有三席(世界上古史和中古史、世界近现代史、世界地区史国别史),仅比中国史二级学科少一个(中国史有四个二级学科: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地方史、中国民族史)。学科的数量意味一定的队伍规模、职称配置、经费投入等关乎学科发展的基本条件。所以,改革开放前十八年是中国世界史学科的重大发展时期,这种进步的幅度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开放的深化,现代化程度的提高,走向世界性大国强国的趋势,本应进一步扩大,因为按照常理,越开放越需要了解和认识所要面对的开放对象,越应向国际一般的学科配置靠拢。
然而,在1997年的学科调整当中,世界史学科不仅没有扩充,反而随着中国学科体系二级学科的重点调整,从三个二级学科压缩为一个。中国史二级学科虽然在这次调整中也受到压缩,但中国史与世界史二级学科的数量比却由先前的3∶4变为1∶2。我们无从了解主持这次调整的人们为何作出这样的选择,却知道这一改变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世界史教学与科研人员编制及经费的减少,并导致了今天这样的小学科状态。
1997年学科调整已经过去了十三年,并充分显示出世界史学科调整的正面和负面效果,这就为新的调整提供了理由和条件。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应该伴随中国和平崛起为世界性大国的进程而不断发展,而学科地位的提高应是这种更大发展的重要前提。我们相信,随着当代中国国情的变化以及中国的世界史学人的共同努力,世界史学科在中国历史学中的重要地位很快就会得到学术界与教育管理部门的应有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