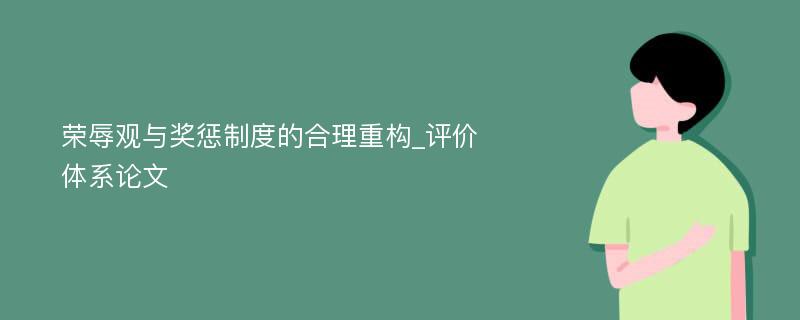
荣辱之辨与赏罚体系的合理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荣辱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道德体系就像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一样正处于弥合“断裂”、重建新机的历史时期。一方面,它需要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无文化现象进行“历史清淤”,并以此为出发点为日益市场化的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提供价值导向;另一方面,它需要在不断反省历史的过程中返本归根地恢复文化的道德涵义,[1]从而使伦理命令不再沦为经济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的工具,而是成为正人心济世事的内在根据。然而,道德体系的复杂性使我们必须对它的构成和机理做仔细的辨析,以便为它的合理重建寻找可靠的基础。本文拟从“荣辱”这一古老的伦理范畴入手对我们的赏罚体系进行初步的检讨,并试图为这种体系的合理重建寻求合理的方式。
一
荣辱是最古老的伦理范畴之一。自从人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并在群体生活的规则下生活,人就有了荣辱感,因为人正是通过荣辱感而享有人在社会化过程中的最初尊严。在一个崇尚气节、崇拜英雄的时代,这种荣辱感更是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个人和人类发展中,荣辱都关乎到人生之大本。从个体意识的成长看,儿童的社会化过程既是儿童学会遵守道德规则的过程,也是培养儿童的荣辱感的过程,道德教育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荣辱感的形成。当儿童没有通过家庭、学校而建立起知荣辱、辨是非的健全心理机制时,他对社会规则的认同将出现严重障碍。美国心理学家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对儿童的道德发展过程所做的实验研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
从历史上看,荣辱问题就像善恶、勇敢、节制等问题一样很早就成了学者讨论的问题。早在赫西俄德的《神谱》中就有“美德、声誉与财富为伍”,“羞耻跟随贫穷,自信伴着富裕”的说法。[2](P10)此后的许多西方大思想家也都或多或少触及这一问题。在中国历史上,“知耻”与“无耻”始终是评判行为好坏的道德标准,寡廉鲜耻被看作道德沦丧、世风衰微的明显标志。《尚书·说命下》中已有“其心愧耻”一词。《礼记》曰:“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孟子·尽心上》有“人不可以无耻”的训导。《左传·昭公五年》有“耻匹夫,不无务,况耻国乎”之语。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之所以特别强调“耻”的重要性,是因为他们深刻地认识到,“知耻”是道德人格的基础,是维护人的自尊的重要条件,因而也是淳化风气的重要条件。
那么,何为荣辱呢?荣辱与荣辱感有何区别呢?它们在人的社会生活,特别是道德生活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的赏罚体系与人的荣辱感之间有什么样的内在关联呢?对这类问题的回答不仅意味着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的出现,而且意味着为我们的社会寻找一个合理的评价体系。
荣辱是荣誉和耻辱的合称,前者是社会舆论或公认权威对个人或集体行为的褒扬,后者是社会对个人或集体行为的贬损。在一个公正合理的评价体系中,社会对个人或集体的褒奖越高,通过荣誉而认定的社会价值就越大,个人或集体从中得到的价值感就越高;反之,公众的指责越激烈,个人或集体的社会价值就越低,个人或集体的耻辱也越大。从道德的意义上讲,当个人对荣誉产生情感上的满足时便产生荣誉感;当个人对耻辱感自惭和痛心时便产生廉耻心。
从词源上看,英文和法文的“荣誉”一词都来源于拉丁文,它既可表示人的行为的内在道德价值,又可表示社会声望,也可表示“头衔”、“勋章”、“奖品”、“称号”、“学位”、“礼仪”、“尊严”和“仰慕”;由于荣誉的授予往往与某种仪式联系在一起,所以又可引申为“盛典”、“荣典”等等。“耻辱”在古英语中写成scamu,古德语则写成scoma,本指“该受指责之事”,后来进一步引申为由于意识到自己或与自己密切相关的人或群体的行为或立场有缺点或不正当而产生的内心痛苦。
在中国,最早将“荣”、“辱”对置起来的当推孟子。他将“仁”视为荣辱的试金石,认为“仁则荣,不仁则辱”(《孟子·公孙丑上》)。后来,荀子对“荣”、“辱”进行了专门探讨。在他看来,“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荣有“义荣”与“势荣”之分,辱有“义辱”与“势辱”之别。“义荣”是因“意志修,德行厚,知虑明”等人格的内在价值而获得的荣誉;“势荣”是因“爵列尊,贡禄厚,形执胜”等外在因素而获得的荣誉。“义辱”是因“流淫污侵,犯分乱理,骄暴贪利”等恶劣行径而招致的耻辱;“势辱”是因受到诬陷、强暴和欺凌而招致的耻辱。直到今天,这一区分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诚如英文honor一词的古义所表现的那样,荣誉代表着社会舆论或公共权威对某个人或集体的行为所赋予的精神价值。它既可以通过奖品、奖金、奖状、奖章来体现,也可以通过勋章、头衔、封号、谥号和称号来体现,还可以通过社会舆论的赞扬来体现。五花八门的竞赛,名目繁多的评比,各式各样的庆典,千奇百怪的封赏,无一不是对荣誉的肯定。这些荣誉或用来肯定人的成就,或用来表彰个人的贡献,或用来称道他(她)的才智,或用来赞扬他(她)的品德,或同时兼具这几种目的。不管荣誉采取哪一种形式,其社会功能主要在于鼓励先进,鞭策后进,凝聚人心。然而,只有当荣誉被用来赞扬人的优秀品德,它才具有道德意义,才可以成为道德荣誉,即荀子所说的“义荣”,除此之外,皆为“势荣”。“势荣”无疑能给人带来成就感,但不能使人获得道德情感上的满足。一个演员得了奥斯卡奖,其荣誉显然不代表道德价值,而一个人因舍己救人而得到的荣誉则来自其行为的道德价值。虽然这两种荣誉都能激起别人的崇敬、羡慕乃至崇拜,但在前一种情况下,人们崇敬的是人的才华,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崇敬的是人的品格。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每发现,人的荣誉与其行为的价值并不一致。有些人的行为很有价值,却没有得到什么荣誉;有些人的行为没有什么价值,反倒得到了很高的荣誉。当一个社会的荣誉与成员的行为价值发生严重背离,这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和评价体系便出现了危机。
与荣誉不同的是,耻辱是人的自我价值感遭到损害或人的自尊受到打击时产生的情感。根据是否诉诸道德原则或道德观念,羞耻感可分为道德羞耻感和自然羞耻感。自然羞耻感是指某个人因生理缺陷或某些方面的无能在遭到嘲笑和轻蔑时而产生的羞耻感。由于这种羞耻感并非由人的过失所造成,因而不具有道德意义。道德羞耻感则是因某个人在意识到自己的过错并由此觉得自己缺乏本应具有的品德时产生的羞耻感,如一个士兵在战斗中表现怯懦而产生的羞耻感。再如,一个窃贼在逃跑时摔断了腿,他留下的残疾可能会使他深感羞耻,这种羞耻不仅是源于生理的缺陷,而且源于人格和道德品质的缺陷,别人的轻蔑和鄙夷会使他感到无地自容,以致见到别人时产懊悔、痛苦和难堪的情绪。
此外,羞耻感还有个人羞耻感与集体羞耻感之分。如果说个人羞耻感产生于个人的自尊和价值受到贬损,那么,集体羞耻感则产生于集体荣誉的受损或集体价值的贬低。一个集体的成员是否把某个人所蒙受的耻辱视为集体的耻辱取决于该集体的团结程度以及该成员在集体生活中的地位。一般说来,一个人的集体观念愈强,他对集体羞耻感的体验愈深,他(她)要求雪耻的愿望则愈强。由于一个集体具有区别于另一个集体(在此,我把国家视为放大的集体)的标志(如原始部落的图腾,现代国家的国旗、国徽等等),当这个标志遭到外人贬损时,该集体成员就会产生集体羞耻感。
斯宾诺莎在谈到羞耻时指出:“羞耻正如怜悯一样,虽不是一种德性,但就其表示一个人因具有羞耻之情,而会产生过高尚生活的愿望而言,亦可说是善的……因此,一个人对于他感到的羞耻,虽在他是一种痛苦,但比起那毫无过高尚生活的愿望的无耻之人,终究是圆满多了。”[3](P215)斯宾诺莎的论断无疑符合这样的事实:推动羞耻之心会使人陷入麻木,激发羞耻之心会使人改过迁善。中国无数的仁人志士之所以不断倡导“教耻为先”,是因为他们懂得“知耻振邦”的道理,忍辱负重、卧薪尝胆莫不是因为“耻”在起作用。马克思甚至说:“耻辱是内向的愤怒。如果整个国家真正感到了耻辱,那它就会像一只蜷伏下来的狮子准备向前扑去。”[4](P407)[5](P120-226)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龚自珍反复强调一个社会要兴民风,厚德泽就必须“养人之廉”,“去人之耻”,要“催助天下廉耻”。
与羞耻相应,荣誉的作用也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既可以激发人的热情,也可以给人以忍耐和毅力;它可以增强人的自尊与自信,也可以激励人努力奋发。只要不是把荣誉转变为虚荣,只要以正当的方式去追求荣誉,那追求荣誉对社会的发展就具有积极的意义。即便是先贤圣哲,即便是性情淡泊的隐士,也并非不顾自己的名誉,至少他们把贤达和淡泊本身视为荣誉。斯宾诺莎甚至说,那些声称不爱荣誉的人也总不会忘记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书的封面上。另一方面,对荣誉受损的担心可以促使人发展自己的某种能力和品质,也可以使人检点和约束那些有可能导致荣誉受损的行为。一个运动员可能为了保护已经获得的荣誉而顽强拼搏,一个军人可能为给自己的勋章增光添彩而舍生忘死,一个“劳动模范”可能为了保持先进而再接再厉,一个胆小如鼠的人可能害怕被说成是怯懦而奋勇争先。(注:汪堂家:“道德情感与道德判断”,载《心灵的秩序》,陈根法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96页。拙作的部分观点和材料是我的立论基础,因此本文不得不予以适当采用。)
二
一个社会的赏罚体系不仅要体现这个社会的正义要求,而且要以制度化的形式体现这个社会的荣辱观。只有当赏罚体系有利于维护社会公正时,这一体系才是合理的,也只有当赏罚体系能够从根本上激发民众的荣辱感时,这一体系才可能实现抑恶扬善、祛邪扶正的目的。从表面上看,赏罚体系,即奖励体系和惩罚体系,是两个互不相属的体系,实质上它们反映了价值认定方面的两个极端情形并在现实生活中共同发展,有时甚至彼此会发生微妙的影响。奖赏体系旨在确认个人或群体对社会的独特贡献,它是对个人或群体的正面价值的认定,并且它们所认定的价值超出社会平均价值;惩罚体系则是对个人或群体对社会造成的损害的确认,并以社会权威的名义将个人或群体的负面价值宣示出来。奖赏和惩罚均应成为一种社会行为而不应成为一种个人行为。当奖赏仅由某个人确定时,奖赏实质上很难实现对个人或群体的独特价值进行客观认定的目的,因此,即便是古代的皇帝在进行大的封赏时也不会忘记要举行某种仪式并诏告天下。当惩罚成为一种个人行为时,它便失去了惩罚的意义,而是演变为一种报复,并且这种报复会因报复者的随心所欲的情绪性反应给社会正义的维护带来损害。因此,一种健全公正的法律制度首先意味着杜绝私刑的发生。当一个社会大量存在私刑现象时,这个社会的法律体系便存在严重的问题,其根源不仅在于民众的无知,而且也在于执法机构的公正性并未得到认可。
合理的赏罚体系有赖于公正的评价体系的建立。赏罚制度的确立不仅使评价成为必要,而且使评价成为基础。就像我们在惩罚罪犯之前首先要确认其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并且要有客观有效的量刑标准一样,我们在奖励某个人或团体之前,也必须对这个人或团体的行为及其影响进行可比性评价。然而,评价需要特定的标准,而不同领域的标准又是不同的。由于职业的千差万别,每一种职业对自身都有不同的要求,制定这些标准虽然是专家们的工作,但这些标准只有成为客观化的公开的东西并为公众所遵从时才有普遍的效力。因此,制定标准既是运用专门知识和智慧的过程,也是集思广益获得公众认可的过程。如果评价标准只是某个人的主观想法或是偶然采用的谋利工具,那么,即便这种标准甚为科学,它也不能发挥评价标准的作用。因此,任何时候,我们都得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标准是在对标准的维护中显示其力量的。
那么,合理的标准如何确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此处所说的评价标准仅仅涉及个人的行为,并且常常涉及与道德相关的行为。与质量论证体系不同的是,行为评价的对象不是一个被动的东西,而是能以各种方式影响评价者,甚至左右评价者的人。在对产品的质量进行鉴定评估时,我们比较容易展开量化的标准,评价者比较容易保持客观的立场,而对行为的评价却要涉及动机和后果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并且容易受评价者的情感好恶和价值观念的影响,被评价者也会常常千方百计地利用这些影响去获得有利于自身的评价,更有甚者,一些被评价者为了争逐某种荣誉或某种利益常常会在评价之前、评价之中或在评价之后通过压制对方、毁损对方来确立自己的相对优势。在我们这个社会中,这类情形(如奖励的评比)非常普遍。因此,要确立公正合理的评价体系,首先就要预防性地考虑到影响评价标准发挥效力的主要因素并附带制定对破坏评价标准的行为进行处罚的相关条款,以维护评价标准的权威地位。
毫无疑问,合理的评价标准必须满足客观性和科学性的要求,制定标准时的任何偏私都有悖于社会公正。同时,评价标准必须是可核查并经得起核查的东西。作为标准的东西必须是公开的东西,因而是可供合理修正并能体现普遍意志的东西。然而,有了好的评价标准并不等于有了公正的评价体系。事实表明,对评价体系的挑战每每来自评价者内部。由于评价者是评价标准的直接运用者,他(她)的主观好恶会对评价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因而当评价者本身不遵守评价规则或不合理地运用规则时,评价的公正性将是有疑问的。在一个社会中,法官、裁判、评审团成员唯有不断置于公众的评判之下才能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换言之,评价者本身只有不断接受评价才能保证评价者在评价时保持不受外界影响。然而,这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事实上,一个评价体系中有人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将使评价体系本身失去信誉,这也是评价体系中的最糟糕的情形。评价者持身严正是保证公正评价的道德要求,只有这样,评价的伦理与伦理评价才会走向统一。
合理的评价体系必须使评价者、评价标准的制定者与评价标准的维护者(监督者、护法者)相互分离、相互制约。评价者之所以要与制定者相分离,是因为两者需要不同的知识与经验,而知识的缺乏和经验的不足都足以导致评价的失误,同时,评价标准的制定者与标准的运用者一旦合而为一,就易导致个人出于自己的偏私而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标准,这样一来,标准的客观有效性就会遭到损害。从评价的实践看,虽然评价标准的制定不能脱离一个社会的具体状况,但它又必须独立于个人的具体经验并且超越于这种经验。在某种意义上,唯有当制定标准时做到为标准而标准,才能保证标准的客观性。
在评价者和评价标准的制定者之外之所以要设立独立的“护法者”,即评价标准的维护者,是因为评价者本身只有接受别人的评价和监督才能从制度上保证评价的公正性,从根本上说,“权力需要权力来制约”的理论依然适用于评价体系的建立过程。此外,评价标准的维护者不仅要纠正评价标准的不恰当运用,而且要对评价标准进行审查。标准只有付诸运用才能成为标准,并且需要在保持相对稳定性的同时随社会的进步而作相应的修订。然而,评价标准的维护者只能对评价标准的修订提出建议,而不能越俎代庖地去改变评价标准本身。在一些社会中,评价体系的混乱首先表现为评价标准的模糊不清,表现为标准的制定和解释过程的主观随意性,表现为评价标准的制定者—评价者一护法者这种具有制衡和稳定机制的三维结构被缩合为“统一体”,通俗地说,一些“裁判员”既成了“运动员”又成了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正因如此,评奖过程常常成为一些人的自我授奖过程,成为通过逐奖而争名夺利的过程。这种通过不规范的评价体系而实现的“名利双收”,又反过来导致了评奖活动的泛滥。与此相应的是漫无节制的罚款以及能给评判者带来间接利益的其他名目繁多的处罚。社会的腐败由此反映出来,而且由此进一步滋长。从这种意义上讲,赏罚体系的危机既是价值失范的表现,也是道德的危机。
三
为了克服赏罚体系的危机,我们需要对赏罚体系进行合理化,而一个社会的赏罚体系的合理化不仅取决于评价体系的合理化,而且取决于这种赏罚体系是否能满足社会正义的要求。然而,事实恰恰如卢梭所说,“当正直的人对一切人都遵守正义的原则,却没有人对他遵守时,正义的法则就只不过造成了坏人的幸福和正直的人的不幸罢了。”[6](P49)因此,赏罚体系必须通过社会的普遍的约定和法制的强制力量来保障。当人的名誉权可以通过完备的法律来维护时,当不当的赏罚可以通过法律本身来纠正时,健全的赏罚体系才有可能实现。
但是,赏罚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增进人的荣辱感的手段,并且只能是这样的手段。纲纪之功贵在运用,赏罚之能旨在荣辱。赏罚得当能使人趋荣恶辱;赏罚不当则使人混淆荣辱,虚骄自恣或弃善从恶。因此,合理的社会不仅要赏罚分明,而且要赏罚有度。一个有功不赏,有过不罚,无功受禄,有罪逍遥的社会必然导致五德不修,价值失范,导致荣辱颠倒,恶欲猖狂。反之,滥用赏罚或赏罚无度也可能使赏罚本身失去价值。事实正如霍尔巴赫所说,“论功行赏,等于火上加油;无功受奖,等于火上泼水;完全不奖,等于让火焰自行熄灭。”[7](P327)有小功而重赏不仅反映了道德本身的无奈,而且易使人夸大功绩,望利而行;有小过而课以严刑则体现了一个社会的道德体系的软弱无力,使人不知德性的力量,而仅怀对严刑峻法的恐惧。究其实,这是社会成员“廉耻丧尽”,失去道德自觉,非有外在力量的刺激和强制才能遵守行为规范的反常现象,也是仁道衰微,礼义颓废的征兆。因此,要淳化社会风气,荡除蝇营蚁附之流,只有赏罚适中,才能使人真正做到孔子所说的“行己有耻”。赏罚在社会生活中所起作用的大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人的廉耻心为基础的。在一个“廉耻风衰,君师道丧”(王夫之《黄书·大正第六》)的社会中,严厉的惩罚虽能起作用于一时,但难以使社会长治久安。如能广泛培养人的道德自觉,使人知耻力行,虽奖一人而仍能扬社会之正气,虽罚一人而仍能抑颓风于流俗。因此,败坏人的廉耻无异于败坏人的灵魂,而败坏人的灵魂无异于铲除正义观念和正义原则得以发挥作用的土壤,在这种情况下,即便靠警察来统治也无济于事。
由于奖励与荣誉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并且可能具有政治、军事、科技、文化、宗教、伦理、教育乃至意识形态的意义,我们在设立重大奖项时必须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可能影响并且尽可能制定详细的、可资操作的明确标准,建立可供检查、可供监督的评奖程序,仔细斟酌能真正激发人的荣誉感并能体现社会普遍意志的奖励方式。
如果听任于实利主义的横行,许多人就会被笼罩在瓜分荣誉并进而瓜分利益的阴影之中,追名就会成为逐利的手段,奖赏就会成为利益的分配,沽名钓誉者就会热衷于蝇营狗苟式的利益计算,工于计算者就会把荣誉变成可供批发和零售的商品。一旦荣誉商品化,在许多领域中就会存在着瓜分荣誉的尖锐斗争,奖赏的滥用则使奖励本身成为馈赠礼品的特殊形式。一旦荣誉商品化,奖励在许多领域中就会逐渐失去那种使人卓然独立、超拔平凡的精神力量,失去那种凝聚人心、催人奋进的内在动力,失去那种涵养人心,敦风厚俗的伦理意义,因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奖励之为奖励的存在理由。我认为,我们在建立合理的奖励体系时必须避免下述情形:
(1)避免将奖励与报酬混为一谈。众所周知,在当今社会里,哪里有劳动组织,哪里就有奖励活动,奖励似乎成了人人可以获得的东西,比如,在所有单位里相当一部分劳动报酬是以奖金的名义来分发的。当人人都可以获得奖金时,奖金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奖金,而是体现劳动者的付出与所得之间相对等价的工资关系,因而起不到增进人的荣誉感的作用。
(2)尽可能避免以奖励的方式促使个人尽义务。义务之所以成为义务就在于它是外在的强制和内心的“应当”,用康德的话说,“义务是一种尊重法则而且必须照此而行的行为。”[8](P369)在合理化的社会结构中,个人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是对人的起码要求。因此,真正合理的做法不是对履行义务的人进行奖励,而是对不履行义务的人进行惩罚。只有当人完成了自己的义务并且对公共生活领域做出了远远超出自己应尽义务的贡献时才应给予奖励。否则,义务非但不会成为义务,相反会成为不尽义务者要求获得额外补偿的讨价还价的手段。
(3)避免评奖活动中的变相交易行为和滥奖行为。在一个法制完备的社会中,评奖活动是在法律的规范下进行的非常严肃的活动,任何个人都无权将某项奖励指定给某人,提名者、评判者和申请者的严格分离以及公众舆论的广泛监督,使得评奖活动既是一种专业活动又是一种透明的公开活动。
然而,不公正的奖励体系还要通过公正的惩罚来消除。惩罚有法律上的惩罚、行政上的惩罚和道德上的惩罚。但这些惩罚的目的不仅在于维护社会正义,而且在于“催助天下之廉耻”(龚自珍语),使人自知自重,自尊自惜。当惩罚能使人知耻止耻时,人就能以羞恶之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当人不以受罚为耻,或对受罚麻木不仁时,惩罚只能起警示他人,让人畏惧的作用,而不能铲除受罚者继续为恶或继续犯错的心理根源。惩罚的有效性取决于它的公正性,滥罚就像滥奖一样,只能破坏大众的廉耻心。只有不公正的惩罚行为本身受到惩罚时,民众才会相信惩罚的道义力量。治罪显然不止是把罪犯关进监狱或强制劳动就万事大吉。如果只是束缚罪犯的身体而不能束缚罪犯的灵魂,如果罪犯不能洗心革面,他很可能在回归社会后继续犯罪,当罪犯越惩越多并且不以犯罪为耻时,监狱足可以成为犯罪的学校,众多罪犯的“共在”既使他们减轻了心理的畏惧,也使他们交流犯罪的经验变得十分方便。因此,不能唤起廉耻心的简单治罪,至多起隔离罪犯的作用,而不能洗刷罪恶的灵魂。只有感化和教化才能固人心人性之大本。
标签:评价体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