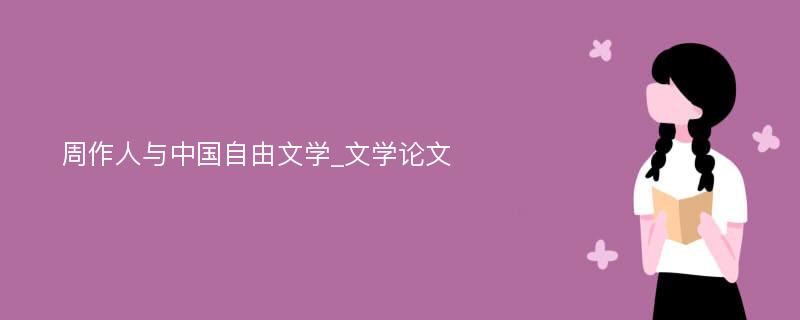
周作人与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中国论文,周作人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人的文学”:自由主义文学的理论基石
“五四”启蒙先驱们一致认定,要改造社会需改造文化,要改造文化需改造旧文化的主要载体——旧文学,无论其吃人的内容还是其僵死的形式都应该改造。改造旧文学是为了重建价值、整合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从文学本体意义上来看待文学自身价值变化的根据和必要性。即使是文化自由主义者胡适,他也总是将思想文艺并称的。比如他提倡文学上的宽容原则,也是把它当作文化宽容的一个适例而非文学本身要求的特例。
周作人亦是十分关心思想文化革命的。他在“五四”时期的大量杂感论文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的同类文章浑然为一个整体。不过,周作人在同中有异。读他此期文章,他显然特别喜欢从伦理道德情感欲望尤其是从性爱这样一个非常私人化的角度具体鞭笞旧文化对人性的戕害。周作人对“性”问题的兴趣,实因他对人的兴趣。他对中国人低下的生命质量、麻木冷漠的生活态度痛心疾首,对受礼教束缚的不自由的中国人尤其是妇女和孩童充满同情。正是在这一点上,周作人显示出了他思想家与艺术家气质兼而有之的特色:不是从制度、物质、典籍文化出发而是从活生生的人的生活状态出发来关怀人、来启蒙。
于是,我们方才可以理解不是别人而是周作人为“五四”新文学贡献了辉煌的“人的文学”理论。在“五四”文学的鼎盛时期,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有了第一篇从人的本体角度看待文学本体的出色文献。尽管“人的文学”理论不仅仅属于周作人,它是周作人对时代感召的回应,对“五四”文坛人学思潮的呼之欲出的理论概括,但毕竟只有周作人概括出来了,而且是“周作人式”的概括。
1918年底和1919年初,周作人发表了《人的文学》、《思想革命》、《新文学的要求》、《平民文学》等文章,把文学革命理论建设大大推进了一步。此前的启蒙者关于文学的理论破得多、立得少。陈独秀的“三大主义”论,李大钊的“宏深的主义、艰深的学理”论,胡适的“言之有物”论、“国语的文学”论等提法都较空洞,缺乏一个明确的“所指”。周作人认为,文学的内容与形式都是重要的。“文学这事务,本合文学与思想两者而成。表理思想的文字不良固然足以阻碍文学的发达。若思想本质不良,徒有文学,也有什么用处呢?”他的看法是:“文学革命上,文学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注:周作人:《思想革命》,《理性与人道》,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下引周文未注明出处者皆出自此书。)当文学改革已初见成效,白话代文言已蔚然成风时,这关键的第二步该如何迈出?周作人指出了一条明确的道路:人的文学。这既是新文化运动深化的必然反映,也是对方兴未艾的新文学初年创作的初步总结。
周作人开门见山地亮起了旗帜:“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非人的文学。”(注: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5卷6号,1918年12月15日。)
“人的文学”是人道主义的文学。“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界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它要求人人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先需要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注: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5卷6号,1918年12月15日。)这是周作人对其“人的文学”的本质概括。他还规定了“人的文学”的基本表现内容:现在的人类生活,“各尽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使人能享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注: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5卷6号,1918年12月15日。)。“人的文学”也是表现凡人生活的文学。包括“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注: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5卷6号,1918年12月15日。)。也就是说,人的文学应该表现理想的应该如此的真正的生活,也应该描绘现实的不得不如此的真实的生活。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有其明确的针对性,即针对封建中国的“非人的文学”包括宋明理学和家庭本位主义文化观念。他认为欧洲从15世纪便发现了“人”,而中国人的个体价值一直被忽略,“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因此须向西方学习,以文艺复兴以来的人道主义为借鉴,去“辟人荒”、“重新发现‘人’”,“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注: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5卷6号,1918年12月15日。)。
“人的文学”的理论依据就是建立在自然人性基础上的人道主义。周作人代表“五四”精英,表达了对人的一种基本理解方式。在他的宣讲中,“人是一种动物”,又是“进化的动物”;因此,人具有“肉”与“灵”的二重性,“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其内面的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注: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5卷6号,1918年12月15日。)。这是从人自身的物质精神关系出发。另一方面,从人与他人的关系出发,强调“人”具有“个人与人类的两重性”,“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在个人与人类的关系上,他强调“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注: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5卷6号,1918年12月15日。)。从这种对人的基本理解出发,周作人在《新文学的要求》中再次概括了“人的文学”的涵义:“一、这文学是人性的,不是兽性的,也不是神性的”;“二、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
重复这几篇研究界同人所熟知的文献的基本表述也许是笨拙的,本文的兴趣在于从中找到周作人对文学史的特异贡献及对后发文学思潮的相关影响。在一个对西方文学史和现代人学理论稍有了解的人看来,周作人贡献给中国文学史的,简直是常识。如果是常识,就谈不上真正的理论贡献。但周作人确实贡献了。没有这种对常识的贡献简直还不行。他就靠这几篇表述过于平实简单的论文确立了他在“五四”文学革命中主要理论家的地位。因为转型期的中国启蒙家,正是用西方的常识或传统去攻打旧中国文化的堡垒的。周作人的理论支点,是自然人性论,这是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对人的基本理解。陈独秀的一段话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以西方常识攻打中国传统的做法。他说:“使今犹在闭关时代,而无西洋独立平等之人权说相较,必无能议孔子之非。”(注: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3号卷2号。)
繁复丰富的中国文化是没有“个人”的文化。孔子虽有“食色,性也”的对自然人性的肯定性前提,但它不是为了发展这天性,而是关心如何限制私欲、克己复礼、修齐治平。儒家的政治原则是社会的安全稳定而不是个人的幸福和利益;“天人合一”取消了人的独立性,修身养性是为了个体之外的更高目的“圣道”,因而个性被泯灭。法家推行愚民政策,根本不尊重平民个人。道家以逃离社会的方式达到“无为”,不想介入社会,因而并不具备个人性,也无积极的自由可言。佛家在抛弃人的自然人性的前提下的“空”“无”,难有生命的欢娱、现世的自由、人格的完整、个性的健朗。中国人被灌输了太过的道德规则和责任义务,但就是没有权利观念、个性观念。周作人从自然人性这一理论基石中肯定了凡人的幸福,否定了偏于兽性或神性的不完整性。在他眼中,非人的文学就是充满兽性与神性的文学。不仅那些宣传封建礼教泯灭人性的文学在他扫荡之列,他也排斥《西游记》、《聊斋志异》、《水浒》、《笑林广记》等,在他看来,这些作品多少具有些神魔性因而少了些人间情怀。承认人的动物性一面,又承认人从动物进化的一面,这就使周作人在介绍西方性学研究及描写性爱的作品时格外理直气壮,也使他为《沉沦》、《蕙的风》和李金发
周作人还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张扬了个体的价值。他所鼓吹的人道主义的准确含义是个人主义、个人本位主义。在人、自然、社会这个三维关系中,中国传统文化倾向于个人服从社会、归返自然,貌似和谐有序,实则死气沉沉。以家庭为人之本位,而国不过是家的放大,因而家庭本位观念强化了家族、国家,削弱了个体。周作人在比较托尔斯泰、梭罗古勃等不同形态的人道主义作家后指出:“他们只承认单位是我,总数是人类:人类的问题的总解决也包含在我之内,我的问题的解决,也便是那个大解决的初步了,这大同小异的人道主义的思想,实在是现代文学的特色。……所以这多面多样的人道主义文学,正是真正的理想的文学。”(注:周作人:《点滴·序》。)强调文学与人的至高无上的个人性,破除家族、种族、国家的偶像,抛弃这些压抑和异化人性的中间物,在人与人类之间联结。周作人在这里显出了与胡适一样的世界主义而非狭隘的民族主义眼光。(注:钱理群:《周作人传》,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11页。)
古代和现代的专制政体和集权主义者从来就是以空洞的国家、乃至人民的概念来压抑个人的。周作人眼里的个人,是独立的有价值的个体,代表了人类,又是社会运作的真正目的。是社会为个人服务而不是个人无条件地献身,个人的贬值也是社会的贬值。
在“五四”时代,周作人的声音并不仅仅是独唱,人道主义、个性主义是启蒙思想家的合奏曲。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都有表述,而胡适、周作人对个人主义的关注更多一些。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也即周作人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胡适强调个人要成器、要负责、社会要改良进步、文化要先行、理性为指导等观点,和周作人的自然人性、正当享乐、个人至上等观点,共同显出他俩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特点。不过,即使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研究颇深的胡适,他谈个人主义仍然是从一般文化角度,他以作家作品为例,也只是他运用于文化领域的一个论证。只有周作人,从文学本体意义上证明了人为文学之中心的现代新文学品格。因此,我们可以说,周作人是文坛上自由主义文学的领唱者。他的“人的文学”理论,虽然没有导致一场单独的自由主义文学运动,但为自由主义文学发展作了坚实的理论铺垫,也给新文学的发展带来了较大影响。与启蒙思想家一般性地从思想内容艺术形式的角度建立新文学相比较,周作人从文学本体价值观角度论述了新文学之“新”在人的觉醒、个性解放。这是周作人对“五四”文坛的独异贡献。
二、“自己的园地”:自由主义文学的个人化实践
如果说“人的文学”理论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奠定了一块坚实的宽泛的基石的话,周作人在1922年起经营“自己的园地”则是自由主义文学的一次富有成效的个人化实践。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过渡,但又是一次明显的转换。其主要区别在于,“人的文学”作为启蒙思想的一部分,仍有着明确的功利性,而“自己的园地”只属于周作人自己。
“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口号提出后,“为人生”派文学逐渐占了上风,随即又出现了与之相对应的“为艺术”的文学。周作人对人生对艺术都有很大的热情,但对这个“为”字却不以为然。1920年1月,在一次演讲中,他明白地说,“为什么而什么”的创作公式是不可取的,“人生派”的毛病在于“容易讲到功利里边去,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成一种坛上的说教”。他提出文学根本不必“为什么”,只是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作者“对于人生的情思”(注: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艺术与生活》,上海群益书社1931年初版。)。他反思自己的两个口号(“人的文学”、“平民文学”)虽然于思想革命有益,但在文学的领域里则显得太功利化。
在文艺的功利问题上,周作人是有反复的。留日期间,受维新思潮和民族功利主义的影响,周作人在评价文艺作品时比较看重其功利价值,他夸大《汤姆叔叔的小屋》对美国种族平等问题的作用就是一例。回国后在故乡的日子里,他既有改造国民灵魂的功利文学观,亦有趣味至上的文艺观。在《童话研究》一文中,他说:“童话者,其能在表见,所希在享受,撄激人心、令起追求以上遂也。是余效益,皆为副支,本末失正,斯昧其义”,“此固人类之同然,而艺术真谛亦在是也。”他概括世界文学的趋势是:“著作之的不依社会嗜好之所在,而以个人艺术之趣味为准。”(注:周作人:《小说与社会》,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5号。)在新文化运动高潮期,他的言论与启蒙之大方向一致,偏向于强调文学对于人生社会的作用一面。然而,到了1922年1月,他在《晨报副镌》上开辟了“自己的园地”,又偏向于强调个人趣味的文学观。从更深的社会哲学思想来说,他在同情下层人民、以“下者”、“弱者”为本、向往社会主义为特征的人道主义与强调“个人本位主义”的个性主义之间作了一次选择。“五四”分化期,李大钊、陈独秀走向社会主义,胡适则坚持着他的自由主义。鲁迅在“彷徨”,他自感是游勇,但毕竟仍是战士,而周作人则到了十字
毕竟,周作人有了选择,“自己的园地”的开辟,就是选择的结果。它的可贵,就在于它是“自己的”,他要在文艺之园中,“依了自己的心的倾向,去种蔷薇地丁,这是尊重个性的正当方法,……倘若用什么大名义,强迫人牺牲了个性去奉同白痴的社会——美其名曰迎合社会心理,——那简直与借了伦常之名强人忠君,借了国家之名强人战争一样的不合理了”(注: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周作人在此已不在乎启蒙不启蒙了,而且预先抵拒了可能来自新文化阵营中的批评。他心目中的艺术,是以个人为主人、以表现情感为主旨的个人活动,强调个性,强调艺术的独创性、表达的私人性,追求“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注:周作人:《自己的园地》。)。
提倡无形的功利,也即反对有形的功利。不论为政治目的还是为启蒙目的,一沾功利就会损害“独立的艺术美”。周作人所指的功利并非泛泛而言,而包含着对当时刚刚兴起的阶级斗争术语侵入文坛的反感。他说:“艺术是人人的需要,没有什么阶级差别等等差异。”(注:周作人:《儿童的书》。)“倘若把社会上一时的阶级斗争硬移到艺术上来,要实行劳农专政,他的结果一定与经济政治上的相反,是一种退化的现象。”(注:周作人:《贵族的与平民的》。)他坚决反对工具论的文学观:“文学既不被人利用去做工具,也不再被干涉,有了这种自由,他的生命就该稳固一点了。”(注:周作人:《文学的未来》。)
“文艺只是自己的表现”,“我想在文艺里理解别人的心情,在文艺里找出自己的心情,得到被理解的愉快”(注: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序》。)。周作人在此期文章中反复谈的是文艺中的个人,无论创作之因还是创作之果,都立意于个体。在一篇正面谈到诗的效用的文章中,他反对俞平伯“好的诗底效用是能深刻地感多数人向善的”定义,提出了三条很有说服力的理由。他认为用社会学的眼光看诗的效用未尝不可,但绝不是唯一的。“我始终承认文学是个人的,但因‘他能叫出人人所要说而苦于说不出的话’,所以我又说即是人类的。然而在他说的时候,只是主观地叫出他自己所要说的话,并不是客观的去体察了大众的心情,意识的替他们做通事,这也是真确的事实”(注:周作人:《诗的效用》。)。他还认为,善不能当作判断艺术价值的标准。这一点是古代文论中不可能有的,在周作人的同时代人中也难见第二人。善是不合理的社会上的一时习惯,文学以表现美为特色,因此仅凭“善”与否判定艺术高下抓不住艺术的真正价值。周作人所批驳的,恰恰是此后几十年人们所信奉的或不得不信奉的奴婢艺术观念。所谓政治标准第一、题材决定论、主题先行、世界观与立场决定论正是以善(有时甚至是伪善)的要求取代了美的要求,取消
“文艺的生命是自由而非平等”(注:周作人:《文艺的统一》。),这是周作人坚定的艺术观。他重视作家的个性,而人们的个性又绝不相同,尊重个性也即尊重创作多元化。因此,他自然要提倡文坛的宽容原则。他认为:“文艺上的统一不应有也不可能。……文学是情绪的作品,而著者所能最迫切感受到者又只有自己的情绪,那么文学以个人自己为本位,正是当然的事。”“因为文艺的生命是自由不是平等,是分离不是合并,所以宽容是文艺发达的必要的条件。”(注:周作人:《文艺的统一》。)
1922年,周作人与另几位知识界名流发表过一个关于信教自由的宣言,与他此期主张文艺自由,在精神上是相通的,都是为了维持个人的思想行为自由。周作人自己从“五四”高潮期启蒙主义文学观念的代言人变成了“五四”后期自由主义文学的鼓吹者。强调趣味,反对功利;强调个性,反对统一;强调宽容,反对压制;强调自由,反对平等是他此期文艺论文的主调。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周作人写出了最具他个性风格的散文,其简约亲切、冲淡平和在现代散文史上独树一帜,别有风韵。“他在拒绝了政治力量后,奇迹般地在自己的专业——散文创作上建立起新的独创的价值标准:美文”(注:陈思和:《关于周作人的传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3期。)。他的理论和创作,是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一次个人化实践。
“人的文学”观念,既可理解为个人的,也可理解为人类的,还可理解为部分人的(如平民文学),因此,在这面旗帜下,平民主义的、为人生的、为个人的、为艺术的,都可以找到发挥的联结点。可以说:“人的文学”理论,只为自由主义文学提供了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和理论的基石,但还有为各派所利用的功利因素,而“自己的园地”则是“自由思想者”周作人的独舞之地。
三、周作人的影响
“自己的园地”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次自觉追求,一次独立发言,但其影响比“人的文学”理论小得多。周作人自己对个人主义在中国的前途也是没有信心的。在1923年为《自己的园地》结集而写的序中,他把这些鼓吹称为无聊的闲谈;1924年,又把“五四”启蒙称作“不讨好的思想革命”(注:周作人:《教训之无用》。)。虽然信心不足,但他并未放弃基本的信念。比如在1925年反帝爱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之时,针对郑伯奇、穆木天等人又倡“国民文学”口号,他警醒道:“提倡国民文学,必须提倡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自觉”(注:周作人:《雨天的书·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在为《语丝》写的发刊词中,他宣称放弃主义,“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他还这样声明:“我不是研究系,不是教育改进社”,“我不是无政府党或所谓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我的意见是根据我个人的特质加上外来的影响而合成。”(注:周作人:《答张岱年先生书》,《京报副刊》,1925年8月21日。)声明不属于任何派,可见他正是一个“自由派”。1927年,在国共斗争紧张之时,一位读者在信中称周作人的言论是唯一近于人的言论,周作人回答说:“‘此刻现在’的中国,已在以人的生命作游戏、作生意,大讲* 在黑暗高压之下,坚持积极进取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很容易碰壁,而一旦碰壁就容易走向消极,容易以古代的名士、隐士自居,求一种消极的自由。周作人正好经历了这样一种蜕变。他在20年代末提出“闭户读书论”、“乱世苟活论”,表面上看,仍然把个体生命价值放在第一位,但已有了以避归隐的旧文人方式来寻个体自由的味道。“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事”,这是屈从于现实的无可奈何。曹聚仁称周作人是自由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混合休,是很有道理的。在周作人逐渐冷下去的时候,胡适还抱着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热心得很。以后周作人的影响很小而胡适的影响仍大,与此态度是相关的。
即使是周作人对左翼文学的批评,表面看来似乎很激烈,很有说服力,但也没有什么影响。1935年,他批评早成气候的左翼文学是出于“狂信”心理的“新宗教”,并说“狂信是不可靠的,刚脱了旧的专断,便会走入新的专断”(注:周作人:《苦茶随笔·长之文学论文集跋》。)。他反“狂信也反“遵命文学”,认为真正的文学正面临着“左右夹攻,更有难以招架之势”。无论是“想他鼓吹纲常名教”,“还是恨他不宣传无产阶级专政”,都是要使文学成为“传道”“载道”的工具。(注:周作人:《苦茶随笔、儿童的故事序》。)“以文艺作政治的手段”,“无论新派旧派,都是一类”(注:周作人:《苦竹杂记·后记》。)。显然,周作人所指的“真正的文学”,即早年鼓吹的无形功利的个人主义文学、自由文学。
周作人在谈及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历程时,他仍然坚持着自由主义的文学标准,强调个人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文学是两种对立力量的起伏,即言志派和载道派。他对明末文学十分欣赏,认为那时的一些知识分子反抗传统,重视个性,获得了文学与思想的自由,他们的文学也有了个性的魅力。(注: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北平人文书店,1932年初版。)
可以说,坚持个性和个性主义文学,是周作人的一贯思想,也显示了他作为自由主义文学理论家的最大特色。但周作人未必是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这既表现在他30年代以退隐求自由的消极方式,更表现在他附敌之后毫不知耻的自打耳光。40年代他对文化、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作了这样的解释:“文人们以为文艺是完全独立自由的,一切可以随个人意志自由发展,这在某一时期也是对的,也会有益,但是,在现今中国还不能不加限制,凡国民均应以国家民族为前提,文人也在其内。”(注:周作人:《药堂杂文·汉文学的前途》。)这与他20年代的调子完全两样。他还说:“我于文集自序中屡次……对于在自己文章中所有道德的或政治的意义很不满,……偶有可取,那么所可取者也当在于思想而不是文章,总之我是不会做所谓文学的。”(注:周作人:《苦口甘口·自序》。)“我写文章的态度,第一,完全不算是文学家,写文章是有所为的,这样,便与当初写《自己的园地》时的意见很有不同了。”(注:周作人:《立春以前·文坛以外》。)这些话,未必是周作人对自己学术思想的真正清算,也带有他的“政治”需要的成分。
但不管怎么说,周作人在20年代的自由主义文学观念,有着相当的影响,对推动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发展也起过一定作用。陈独秀称“大著《人的文学》做得极好”(注:陈独秀:1918年12月14日致周作人书,见周作人《过去的工作·实庵的尺牍》。)。胡适盛赞周作人翻译的《贞操论》的发表”是东方文明史上一件极可贺的事”(注:《新青年》5卷1号,1918年7月15日。),他还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把《人的文学》一文称为“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认为新文学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两个中心思想(活的文学,人的文学)里面”,周的这篇“最平实伟大的宣言”,“他的详细节目,至今还值得细读”。傅斯年也把《人的文学》与胡适、陈独秀的发难文章并称为文学革命的宣言书。罗家伦说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人的文学“都是去满足‘人的生活’的”(注:罗家伦:《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新潮》2卷5号。)。傅、罗与杨振声、俞平伯、康白情等人皆受业于周作人,视周为精神导师,他们组织的新潮社和刊印的《新潮》杂志是“五四”时期极有影响的自由主义色彩极浓的社团和刊物,周作人在老师辈的《新青年》和少字辈的《新潮》之间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周作人在1920年前* 周作人的文化、文学生涯,贯穿了从近代到当代的大半个世纪。而他最显眼的岁月是在30多年的“现代”时期。在这一时期,他的形象有很大变化,即人们通常所概括的从战士到隐士、从文人到汉奸的转变。但在抗战前,他主要是以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形象出现的。作为中国自由主义在文学领域内的最早理论家和实践者、推动者,他的突出贡献是不应抹煞的。
标签:文学论文; 周作人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新青年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自己的园地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读书论文; 陈独秀论文; 胡适论文; 新潮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