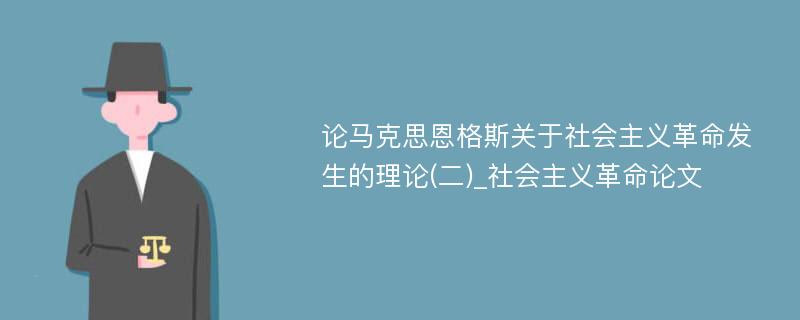
千难起步,万险征途——试论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革命发生论的双要题(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马克思论文,征途论文,试论论文,发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俄国彼得格勒1917年11月7日的起义距离法国巴黎1871年3月18日的起义,有长达近半个世纪的间隔。这一期间,特别是1905年革命风暴时期开始以前的年代中,革命相对沉寂,令人诧异的是,有关社会主义革命的论争仍相对热烈。先还是老话题新议论,主要议的是经历了巴黎公社失败的腥风血雨,经历了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的陶冶洗礼,资本主义文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还有卷土重来的根基吗?如若卷土重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是原先设想的同时发生,共同攻击,同时胜利的老模式,还是稍后设想的相继发生,相继胜利的新模式?或者是德国人开始,法国人继续,英国人完成,角色明确,分工合作,只是德国人与法国人的位置对调的革新型模式?随着岁月的推移,形势的变动,新的兴奋点派生新话题。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和资本主义矛盾的特别尖锐,激发人们思考:哪一种类型的国家最有可能率先实行革命起步,并最有条件夺得革命初期的胜利、巩固胜利、发展胜利、取得全胜。是资本主义高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是其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还是其低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甚至是其殖民地附属国?像俄国这样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封建军事帝国主义国家一旦爆发革命,究竟是最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最先的社会主义革命,它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吗?!这是19世纪20世纪之交和20世纪初期论争的热点,在十月革命前夜和革命告捷最初几年的俄国,这一热点白热化的程度可谓全球之冠。
以老资格、老“权威”自居的普列汉诺夫,一再用训斥性的口吻阐述己见。他在1917年5月20 日《统一报》发表题为《雇佣劳动同资本的斗争》指出:在条件尚未具备时着手组织社会主义是陷于“极其有害的空想”,“所能组织的只是饥饿”,号召如此行动的人,是向无产阶级献媚的人,“不过献媚的人不是人,而是如老黑格尔所说的——只有人的外形。”(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123~124页,三联书店,1980)同年6月20日,他在同一报纸发表《错误的逻辑》一文, 主观断定:“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好将来要用它烤成社会馅饼的那种面粉,因此当它还没有这种面粉时,为了劳动者本身的利益必须让资产阶级参加国家管理。”(同上书,207 页)普列汉诺夫咒骂列宁等着手组织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家是向无产阶级献媚的人,但却没有勇气反躬自问自己卖力为资产阶级争夺国家管理权,是否有向资产阶级献媚的嫌疑。
李可夫的看法与普列汉诺夫的看法雷同。他在1917年4 月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反复说明:俄国是落后的国家,不能先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是否可以指望得到群众的赞助呢?俄国在欧洲是一个最富于小资产阶级性的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不能指望于群众的同情;因此,党如果要站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上,它就会变成宣传小组。社会主义革命应当由西欧发动。”(《列宁文集》,第5卷,107页, 人民出版社, 1954)他大声喊道:“社会主义革命的阳光先从何处射出呢?我以为,根据各种条件,根据常人的水平线,社会主义革命的首创性不属于我们。我们没有力量,没有客观条件以便达到这一点。而在西欧,这个问题大概是和俄国推翻沙皇政体的问题一样地摆着。”(同上)
普列汉诺夫、李可夫等的驳难,其锋芒是指向列宁的。因为列宁在1915年8月间写的《论欧洲联邦口号》、1916年8月间写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已明确地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列宁全集》,第26卷,367 页)“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同上书,第28卷,88页)列宁在第七次代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的总结发言》特别提到:“李可夫同志说,社会主义应从其他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产生。这是不对的。不能说谁来开始和谁来结束。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拙劣的模仿。”“马克思说过,法国开始,德国人完成。可是现在俄国无产阶级的成就比谁都大。”(同上书,第29卷,361页)
针对普列汉诺夫、李可夫等人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前提的怀疑、抹杀,列宁在大会上斩钉截铁地说:“战前在最发达的先进国家中无疑已经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由于战争而更加成熟,并且继续在异常迅速地成熟。”(同上,441页)
“俄国革命不过是战争所必然引起的无产阶级革命中的第一个革命的第一阶段。”(同上,442页)
率先起步的前提业已基本具备,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一点,前提成熟的程度,将直接间接地规定着起步的步幅、节奏、迂回前行的方式方法,同样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这另一点,同时力求十分明确:俄国这样的国家,准备或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列宁说:“俄国无产阶级是在欧洲最落后国家中的一个国家内,在大量小农居民中间进行活动的,因此它不能抢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工人阶级必须支持资产阶级,或者必须把自己的活动局限在小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或者在向人民解释必须立即采取若干实际上已经成熟的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步骤方面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那就是极大的错误,在实际上甚至是完全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同上,442~443页)
这些见解,在列宁写于1917年9月间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 》一书中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他写道:“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不仅因为战争带来的灾难促成了无产阶级的起义(如果社会主义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对于社会主义问题,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抱着学理主义的态度,即根据他们背得烂熟但理解得很差的教条来看待的。他们把社会主义说成是遥远的、情况不明的、渺茫的未来。”“其实,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窗口中出现,在这最新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的每项重大措施中,社会主义已经直接地、实际地显现出来了。”(《列宁全集》,第32卷,218~219页)
列宁大声疾呼:“在整个历史上,特别在战争期间,站在原地不动是不可能的。不是前进,就是后退。在用革命手段争得了共和制和民主制的20世纪的俄国,不走向社会主义,不采取走向的步骤,……就不能前进。”(同上,218页)当年列宁的这一思路, 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流行的一句名言来表述,即:战争引发革命,革命催生社会主义制度。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起步,资本主义制度崩溃问题的论争,列宁在反对普列汉诺夫、李可夫等人的错误论点的同时,也反对布哈林的另一种性质的错误看法。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中有这样一段既有独到见解又是别出心裁的学究气的话:“总的说来,这些制度的稳定性是同国家资本主义组织的高度成正比的。没有这种稳定性,资本主义甚至在历史交给它的这段时期内也活不下去。与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有关的这种稳定性,在生产方面是如此,在社会阶级方面也是如此。然而,只有当一般资本主义关系处于一定的‘成熟’阶段,国民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本身才可能产生。生产力、金融资本主义组织和新资本主义垄断关系的、总体愈发达(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种形式就愈完善……但是,不仅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而且从技术生产的角度来看,在巨大冲突中最稳定的制度,应当是具备帝国主义战争所需要的最发达的技术的制度。这种技术在军事上有决定性的意义……资产阶级社会力量在国家政权(它与资本的经济组织是紧相联系的)中的集中,给工人运动造成了很大的阻力。因此,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是从最弱的、国家资本主义组织最不发达的国民经济制度开始的。”(转引自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59~60页,人民出版社,1958)列宁对这段话的评论,有两处肯定一处否定。列宁指出:布哈林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是从最弱的、国家资本主义组织最不发达的国民经济制度开始的”的说法不对。他强调“是从‘比较弱的’开始的。没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我们是不会成功的。”(同上,60页)至此,读者可以清楚看到: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起步,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观点极为明确:既不可能从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最强的地方开始,也不可能从其发展程度最弱的地方开始,只能从它的发展比较弱的地方开始。
列宁的这一著名的科学论断是以对下列的新实际的精辟分析为依据的:一.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磕磕绊绊地转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愈演愈烈、触目惊心;二.19、20两个世纪在世界大战逼近与革命风暴期将至的错杂微妙的局势中更迭;三.帝国主义列强争霸大战爆发后的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三大对抗性矛盾空前激化、深化,险象环生,顾此失彼;四.矛盾最集中,而从根本上解决矛盾的力量强大的国家,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者不愿意照原来的样子生活下去的局面日趋明朗,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慨。面对这一系列新实际、新态势、新角逐、新抗衡,列宁纵观全局抓大事,见微知著抓动向,致力于回答新课题,回应新挑战,把社会主义革命发生论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读者会记得,本文前面论及社会主义革命发生论时提到,斯大林曾用革命在资本主义文明国家同时发动、同时攻击、以取得同时胜利的公式来表述马克思、恩格斯的见解;而用革命在资本主义文明相对不发达的一国数国首先发动并在这个范围内取得全胜的公式来表述列宁的见解,并认为前一公式适用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不甚明显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后一公式适用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十分明显的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两个公式对于自己的时代来说都是正确的。笔者曾不揣冒昧地说,斯大林的说法有所偏颇。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发生论的数量可观的言论,仅有几次提到同时发动、同时攻击、同时胜利的问题,而且属于40年代的作品,因此,不应以偏概全。公道地讲,斯大林这一偏颇事出有因,欧美一批社会民主党人,把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提及的革命同时发动、同时攻击、同时胜利加以定型、定格,似乎关于社会主义发生论,两位导师只此一说别无他论,诸如:相继发动,相继胜利;一国发动,多国响应,相互配合补充;法国人开始,德国人继续,英国人完成等多种多样的说法都被排斥在他们的视野之外。他们把革命同时发动,同时攻击,同时胜利教条化、僵硬化、普泛化,不问时间地点条件到处套用,造成很大的危害。对此,斯大林倒是清醒地看到了。他指出:被欧美的一些社会民主党教条化、僵硬化、普泛化的同时发动、同时攻击、同时胜利的理论,是编造的无生命力的理论。他说:“这个理论不仅不可采用来作为世界革命发展的方案,因为它和有目共睹的事实抵触。它尤其不可能采用来作为口号,因为它不是发挥而是限制那些由于一定的历史条件而有可能独立突破资本战线的个别国家的主动性;因为它不是推动个别国家积极进攻资本,而是推动个别国家消极等待‘总解决’的时机;因为它不是在个别国家的无产者中间培养坚决革命的精神,而是培养‘万一别人不来援助’这种哈姆莱特式的怀疑心理。”(《斯大林文选》,上卷,305页,人民出版社,1979)
斯大林对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李可夫等人津津乐道的那种“无生命力理论”的严肃批判,可说是对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新论的高度赞扬。在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列强争霸大战战火纷飞,无产阶级革命风暴来势迅猛的历史关节点上,列宁关于战争、和平、革命的理论,特别是关于社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格外激化、被压迫者被剥削者的组织性觉悟性迅速提高的国家,有在国际资本主义链条相对薄弱的环节上率先打开缺口的现实可能性与变可能性为现实的条件。这是历史发展的关节点上促进历史大转折的具有关键意义的创造性的理论思维,曾被誉为时代的良心与智慧。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正是这个创造性的理论思维经过各种中介转化成创造性的革命实践的硕果。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次成功的起步,十月革命科学地继承、创造性地发展了巴黎公社的革命起步的主要成功经验:更加声势浩大地组织无产阶级大军,坚定不移地奔赴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战场去赢得自身解放的权利;初战告捷,政权在手,更加紧握手中枪,把工兵农赤卫队逐步发展为正规军——红军;更加彻底而有序地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具有俄国特色的公社式政权——工兵农苏维埃。同时,认真汲取巴黎公社的教训,想方设法防止重蹈其错误(未及时而坚决地进军凡尔赛,未坚决没收巴黎银行的资产,未坚决彻底地镇压反革命,等等),力求做到公社吃一堑,苏维埃长一智,增长才智以更出色地迈好千难起步。至于如何直面革命千难起步后或早或晚总要摆到人们面前的革命的万险征途,以列宁为核心的布尔什维克中央领导集体,也极为认真地从巴黎公社的哪怕只是一种比较抽象的、原则性的启示中去进行举一反三的思考、学习,诸如:防止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防止公仆蜕化为主人,防止被革命否定的腐朽旧事物改头换面假借新生事物之名而重现等等具有重大原则意义的启示,在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生机勃勃发展的初期,就有意识地通过多方的探索、多次的尝试、多种的举措与决策加以充实,加以具体化。当然这仅仅是开始。就社会主义革命发生论中相关联又相区别的两个层次的问题相比较而言,革命万险征途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比革命千难起步需要解决的问题繁重得多。就拿征途万险中的几大主要危险(如:被武装颠覆,被和平演变,经济长期处于劣势,资产阶级自由化大泛滥,“左”倾顽症一再复发,改革蜕化为改向,贪污腐败、特权死官僚主义病入膏肓,自我糟践自毁长城,等等)来说,没有举国上下、一代又一代坚持不懈而又正确有效的努力奋斗,侈谈化险为夷岂不自己麻痹自己。面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万险征途,确实不要轻率地大讲特讲什么最后胜利。在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千难起步中成绩卓著的第一个国家,经过70多年的努力,由于极其复杂的原因而终于在革命的万险征途中遇险,出现了顷刻瓦解的大灾变、大倒退,给各国献身共产主义崇高事业、关注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有识之士留下一个务必孜孜求索加以解决的特大课题。
“无限风光在险峰”。历经千难万险的磨炼而茁壮成长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将其无限风光光照全球,光照千秋万代。
(全文完)
标签: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俄国革命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列宁论文; 经济论文; 恩格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