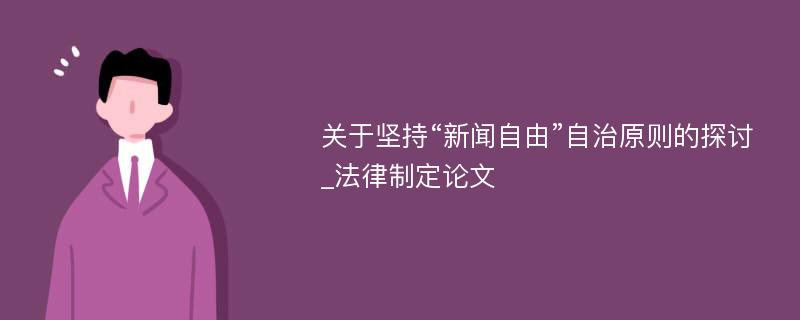
关于坚持“出版自由”自主性原则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主性论文,原则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提要
出版法为出版界翘首久盼。但“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主要分歧集中在“什么人可以办出版单位”问题上,关键的问题在于对出版自由的理解。
出版自由是相对的。任何一个权利主体,在法律上都具有一定作为或不作为的规范。出版法既要保障公民的出版自由又要设定自由的限度,都是以国情为根据的。
出版自由又是发展的。如果仅因为今天的出版法对出版自由的体现尚不完善,就否定制定出版法的必要性,是不明智的。
任何主权国家对出版自由的界定都是自主的,既不能照搬外国的“自由”,也不必硬去“接轨”,必须坚持自主原则,制定一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出版事业蓬勃发展,制定出版法的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建国以来出版管理工作的实践,为制定出版法提供了丰富的、可借鉴的经验。党中央、国务院对制定出版法的工作十分重视,1985年春即责成有关部门成立了出版法起草小组,并于当年写出了出版法草案第一稿,向有关部门和单位征求意见。党的十三大再次强调必须抓紧制定出版法。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对出版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也带来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制定出版法更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1991年出版法草案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1994年10月,经过必要的程序,出版法草案终于由国务院提交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进行了第一次审议。这期间,出版法草案讨论修改不下20稿。
从以上出版法草案起草工作的简要回顾中不难看出,党和国家对出版法的起草工作不可谓不重视,社会各界对出版法不可谓不关注,客观形势对出版法的出台不可谓不需要,有关部门对出版法的起草工作不可谓抓得不紧,但是,为什么出版法终难出台?“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核心的问题是在出版法中如何恰当地对“出版自由”进行表述,作出解释,设定限度。主要分歧又集中在“什么人可以办出版单位”的问题上。关键的问题在于对出版自由的理解。
一、出版自由是相对的
在我国,出版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宪法或其他法律,对出版自由一般都有明文的规定。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为公民行使出版自由权利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出版自由的内涵不断扩展和完善。出版法是出版自由存在的法律形式。制定出版法可以使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出版自由权利进一步具体化、规范化,进一步保障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同时规范出版行政管理,依法制止滥用权利和自由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因此,制定出版法十分必要。
出版自由又有其相对性。在政治上,出版自由这一概念有鲜明的阶级内容。资产阶级曾经用出版自由这个口号,反对封建专制,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进步性和革命性。无产阶级始终高举出版自由的旗帜,在夺取政权之前,为争取自由、平等的民主权利而斗争;在夺取政权之后,用以加强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可见出版自由是阶级的深层次利益的反映。世界上从来没有绝对的自由权,包括从来没有绝对的出版自由。任何一个国家都对出版自由有一定的限制,只是限制的方法不同,范围不同。瑞典的《出版自由法》开宗明义第一条,在规定瑞典国民有权出版任何书面材料,不受任何部门和其他公共机构预先设置的障碍的限制,亦不得因出版物内容而受到指控的同时,规定了法院提出的不在此限,内容妨害公共秩序者除外;把在印刷品中发表违法陈述或以印刷品形式发表非法出版物列为“侵犯出版自由罪”,并规定“如果有理由相信某印刷品由于侵犯出版自由罪而可没收时,该出版物可以在对问题作出决定以前,予以查封”。法国的《出版自由法》在规定“印刷和出版是自由的”同时,也规定,一切日报或定期出版物在出版之前,应向共和国检察院检察官申报出版物名称、出版方式、承印者等内容。并且对新闻及其他途径,规定了煽动罪、妨碍公共事务罪、妨碍个人罪等。这些虽都无可指责,却也说明了出版自由是相对的这个道理。
社会主义法律在确认和维护公民自由权的同时,也都对自由权的行使规定必要的范围和限度。任何一个权利主体,在法律上都具有一定作为或不作为的规范。权利和义务密不可分,一方有权利,他方必有相应的义务,或者互为权利义务。因此,法律上的权利都是相对权利。在我国的出版法中设定限度,包括规定不允许私人办出版单位,并没有什么不光彩的,也不必感到理亏的。
二、出版自由是发展的
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任何国家的任何法律都是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意志的反映,而这种利益和意志的内容,又是由统治阶级的政治生活和物质生活的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依法规定人们在社会中的权利和义务,使一些重要的社会关系具有法律关系的性质,用以贯彻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巩固和发展有利于自己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法是有阶级的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的出版法(如果有的话)对出版自由的界定,也是和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在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赋予它不同的内涵。西方的被认为出版自由的管理体制,由预防制演变为追惩制,也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的。16世纪的英国,出版业实行严格的检查和特许制,直到18世纪以后才有所松动,直接干预减少,但对某些出版物仍然实行检查制度。现在英国的出版管理体制主要是追惩制,并同时保留了预防制中的某些措施。16世纪的法国,出版业也实行检查制度,法国大革命以后,1789年颁布了《人权宣言》,规定了公民的出版自由权利。但拿破仑一世执政后,又恢复了检查制,直到法兰西共和国成立,才逐步实行追惩制。
我国近代第一个具有出版法性质的法律是1906年经清政府批准颁布的《大清印刷物专律》。袁世凯篡权以后,于1914年颁布了《报纸条例》和《出版法》。国民党执政时期曾于1930年颁布并于1937年修正公布了《出版法》。此外还有一些管理出版的特别条例、规则、法令等。这些法令都是当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经济关系的产物,其核心是为维护当时的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广大人民群众何尝享受过真正的出版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彻底废除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法律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就明确规定了人民的出版自由权,给出版自由赋予了新的内涵。40多年来,党和政府为人民群众行使出版自由权创造了各方面的条件。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出版事业蓬勃发展,新建了一大批出版单位,图书出版社已有550多个,杂志8000多种,报纸2000多种,近年来又新发展了300多家音像出版单位,印刷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出版物的流通环节得到很大加强和完善。尤其是贯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双百”方针得以真正落实,支持和鼓励不同学术观点和风格流派的竞争,人民群众可以通过出版物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见,自由表达对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意愿和见解,自由发表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成果。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我国实行的出版自由还不充分、不完善,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我国的出版自由比之资本主义的出版自由具有更大的真实性、广泛性。我们可以相信,随着我国经济改革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我国人民将会享受到更广泛的出版自由。
自由程度还与可控程度密切相关,法制健全,群众的执法意识强,自由程度相对就大。我国由于出版法都还没有出台,出版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还比较薄弱,近年来非法出版活动猖獗,屡禁不止,就是一个证明。因此,目前出版管理的规章比较多,这是不必讳言的。但是,今天的管理是为了明天有更多的自由。今天的出版法也只能从今天的现实出发,实践发展了,可以进行修订,任何法律都是这样的。如果仅仅因为今天的出版法对出版自由的体现还不完善,就否定制定出版法的必要性,是不明智的。
三、坚持出版自由的自主性原则
既然出版自由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既然出版自由是一个国家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反映,那么,毫无疑问,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对出版自由的界定都应该而且必定是自主的。有人认为,出版法中不明确规定允许个人(同人)办出版单位,出版自由就无从谈起,在国际舆论上会造成对我不利的影响,甚至有损国家形象。似乎不允许个人办出版单位的出版法是见不得人的。可谓杞人忧天之见。
首先,出版自由的内涵是很丰富的,个人办出版单位是出版法要规范的一个内容,决不是出版法的全部内容。
其次,我们并不认为允许个人办出版单位天就会塌下来,问题在于当前情况下利弊得失的权衡。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要体现国家的利益。在这一点上,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利益是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维护国家的利益就是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在出版自由问题上的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的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与其他社会制度下的出版自由的本质区别。我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允许个人办出版单位,弊大于利:(一)我国的出版事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事业根本不同,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针,出版单位不宜掌握在私人手里。(二)出版单位是意识形态工作部门,宣传舆论阵地,思想性、政治性很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尖锐的。在这种情况下,出版宣传舆论阵地掌握在谁的手里,至关重要。(三)出版业是一种产业,但它不同于一般产业。出版物是一种商品,但它不同于一般商品,它是有思想内容的特殊商品,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如果允许私人办出版单位,一些人可能把出版作为牟利的工具,不利于从总体上把握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正确方向。只有真正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实际出发,才可能准确把握“出版自由”的度,真正确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法规,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而不能为立法而立法。在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出版社、报刊社一直实行国有制,这是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相适应的。我们在与国外交往中,对此是直言不讳的,外国朋友很了解我国的规定,并表示理解,我们并没有矮人一头的感觉。至于这种体制今后是不是就一成不变,那也不一定。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发展,也许在不太长的今后我国也允许其他经济成分的出版单位存在。
邓小平同志在《我国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中指出:“西方民主那一套我们不能照搬,中国的事情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办。中国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同社会主义法制相辅相成的。”法律属于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我国与别国的经济基础不同,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制度当然也要从我国的经济基础出发。在国际交往日益扩大的今天,很多东西都要和国际接轨,但是,上层建筑领域不是什么都能与国际接轨的。特别是像出版法这样的法律,意识形态的性质很突出,必须坚持自主性原则,我们要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制定出一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