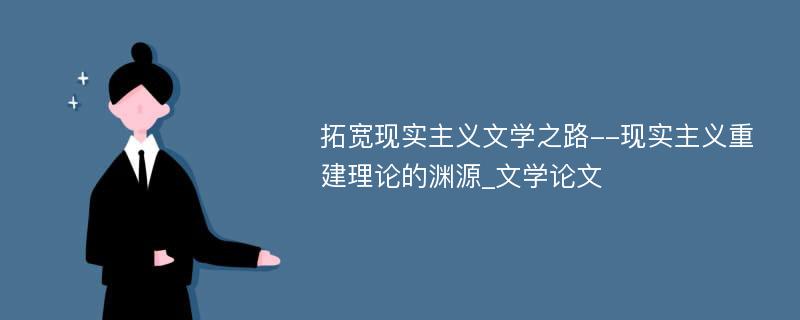
拓宽现实主义文学之路——现实主义重构论之缘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之路论文,缘起论文,重构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本刊和《作家报》联合开展“现实主义重构论。”这样一个问题的讨论,决不是一个商业性的策划。既不是故作惊人之语,当成招徕读者的一种广告式的宣传;也不是有意标新立异,作为聚拢作家的一种组稿手段。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能为当前正在探讨的文学出路问题提供一个新的批评话题。为慎重起见,事先我们曾征求过省内外许多评论家的意见,他们都表示了十分浓厚的兴趣,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次发表的两篇文章,只是作为一种观点提出。下期将刊出的著名学者孔繁今教授的《一个通向文学新世纪不可逾越的话题》一文,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我们欢迎更多的专家、学者、作家参与我们的讨论。
对于中国的文学如何走出低谷,特别是在一个新的世纪到来之际,能否看到振兴的希望之光,这是许多关心文学事业的人期待已久的事。一些有识之士从八十年代后期就开始呼吁,提出一些振兴文学事业的主张,特别是许多文学期刊的编辑,更是忧心忡忡。由于广大读者对文学的热情逐渐冷却,绝大部分文学刊物的订户大大萎缩,他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精神上的失落,生存的危机也在时时地威胁着他们。为了文学的振兴,同时也是为了摆脱自身的困境,先后推出了“新写实”、“新乡土”、“新言情”、“新体验”、“新状态”等一系列精心运筹的文学活动。为了扩大影响,他们还借助媒体大加宣扬,把整个文学界炒得沸沸扬扬。但是,文学圈外的人对这种热闹却置若罔闻,视而不见,与八十年代初的情景形成鲜明的对比。可以说,中国的文坛从来没有象今天这么热闹过,同时,也从来没有象今天这么被世人所冷落。他们的用心可谓良苦,他们的这些策划也确确实实为中国的文学园地开辟了一片片新的风景,但是这种结果却不能不让我们这些同仁心冷。与此同时,一批年轻气盛的青年作家踌躇满志,他们完全置中国的文学传统于不顾,似乎以为采用一种全新的外来艺术一定能够把中国的文学推向一个前无古人的高峰。但由于和者太寡,终于耐不住寂寞,感到实在无法达到理想的彼岸便退却了。近几年来,在众多探索者的努力下,中国的文学虽然“始终在运动中前进着,局部的创新和进展从未间断,可是就整体而言,仍然处于一种被动状态(雷达语)”,一种基本上徘徊不前的境况。那么,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呢?
我们以为近年来文学界在探讨文学发展的问题上有一个误区,即有一种追新逐异的趋势。似乎只有那些贴着五光十色“新”标签的东西才能使我们今天的文学得以发展和振兴。于是一个又一个的文学主张便拼命在“新”字上作文章。那么是否只有这些“新”的东西决定着文学发展的命运呢?我们认为,文学的创新非常重要,可以说没有创新就不可能有发展。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些“新”的文学主张所强调的只是孤立的某一个点某一个面的突破。譬如“新写实”,虽然在对人的生存状态方面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出现了一批有份量的作品,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由于这种文学主张不论是对表现空间的限制上,还是表现这个空间的态度的要求上,都显得过于狭隘。因此,不可能产生出博大、宏阔的作品。而“新体验”则强调作家的亲历性,“新闻小说”则强调作品的时效性,其局限性也就更显而易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新”的文学主张虽然确有其创新之处,但是如果我们的文学按照这样一种状态“发展”下去的话,每一次“新”的文学主张的提出其结果最终只能是使我们的文学走向狭窄的一隅。那么,在探讨这个问题时,能否调整一下思路呢?我们的重构论设想的提出正是基于此。
其实,最初我们并没有打算从现实主义这样一个话题切入的。但是我们看到,新时期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就其主导倾向而言,实际上是现实主义的一次回归和深化,是新时期文学的主要推动力量。不论是最初的伤痕文学,还是紧随其后的反思文学,直到今天的这些贴着各种“新”字标签的“新”字号文学,基本上都是沿着现实主义的轨迹前进的。一些早期的所谓现代派,只不过为了更深入的展示现实,借鉴了意识流的一些表现手法而已。从这类作品的整体来看,仍属现实主义范畴。作为真正的现代派作家,其实只占很小的比例,而且除了少数人还在顽强地固守着自己的阵地外,多数已逐渐向现实主义靠拢。有人把今天文学园地的丰富多彩称为多元化,总感到是一种错觉,因为这种“丰富多彩”(不包括先锋派文学)似乎均与现实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的这种选择完全是从文坛的现实出发的,不是凭空想象的,同时它也是与我们的文学传统及民族的欣赏习惯相一致的。任何脱离实际的主张,所构建的只能是无根基的空中楼阁。但是现实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文化背景的变化,人们审美观念的更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意识形态下,现实主义呈现不同的风貌,仅名称上就有古典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之别。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今天选择一种怎样的现实主义最有利于出好作品、大作品,最有利于推动文学事业的前进。显然,套用一切现成的模式都是不明智的,于是我们便试图重新构建一种同我们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特别是我们的文学现状相适应的现实主义理论,以拓宽文学发展之路。
但是,今天我们倡导重构现实主义决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简单地回归,也不是几种文学主张的简单地归一,而是一种整合和扬弃,一种前进和超越。首先,他不放弃现实主义的最基本的原则,即严格地忠实于现实,艺术地真实地反映现实。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我们提出的重构论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简单说来就是:现实精神+现代理性精神+现代叙述话语。
我们对现实精神的定义是:对现实的人生的深切关注和对人生的现实的理性审视。这是我们重构论的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核心。传统的现实主义(包括古典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偏重对于人生的现实的理性审视,在对现实的人生的关注方面虽然能够关心人的命运(主要指批判现实主义,显然只是物质的,外在的),但是在对现代社会对人的精神世界的痛苦、人的灵魂的扭曲的关怀上远远不如一些现代派作家如卡夫卡、福克纳等人的作品深刻。我们认为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现实主义要走向前进,必须关怀人的精神世界,帮助人寻找精神的家园,使人的灵魂得到抚慰。这是现实主义必须关注的一个现实。同时由于“新写实小说”在关注现实的人生方面也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即对人的生命存在形态的表现,这样便为作家探讨现实的人生又提供了一个新的关注点。凡此种种,我们所理解的现实精神显然具有了一定的现代性,也使得现实精神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
现实主义与现代派文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它充满着很强的理性精神,而后者是非理性的。我们在这里强调现代理性精神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我们文学现实中的理性精神的不断萎缩和淡化,使得我们现实主义文学的这一重要特征逐渐丧失,要求我们必须强化这种精神。二是由于社会的发展,生活内容的丰富和变化,要求我们对现实的理性审视的范围要有所拓展,而且必须要用一种现代的新的观念来审视这个世界。首先,现实精神的内容要求文学要关注人生,也就是说要爱人,要用爱的精神来体察人生,反对所谓“从情感的零度开始写作”。现实主义之所以有着永久的生命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它闪烁着强烈的人道主义光芒。但是由于人们在关注人类现实的生存环境时又引出了一个与人类的终极命运如何相统一的问题,这就给作家的爱心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这是爱的至高境界。因此我们称之为至爱精神。然而当我们面对现实时又会发现,现实生活中仍然不断产生的黑暗和罪恶又要求我们必须对其进行无情的鞭挞和拷问。一位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如果放弃了文学的批判品格,实际上也就放弃了爱,同时也不可能产生出惊世骇俗的作品。世界文学史上哪一部伟大的作品不充满着强烈的批判精神。我们的新时期文学在八十年代前期之所以产生如此强烈的轰动效应,其关键也在于此。遗憾的是我们的作家在作为社会代言人的角色逐渐遭到人们的冷落之后,没有向更深的层次探讨。那么我们今天强调这种精神必须有所超越,不能只是一种社会现象的是非评判,而是要从现实生活的广阔背景上,历史文化的渊源上,以及人的本质上去探求,从而把我们倡导的批判精神提高到一个更高的理性层次。我们主张文学要有理想,但近年来有一种淡化理想的趋势,有些人甚至当成一种时髦,一种真正的“现代”派的标志。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现代派文学虽然普遍带有一种悲观主义的色彩和反社会倾向,但并不都是反理想的,他们在对社会的极端的批判过程中总是寄寓着自己的理想的,我们中国作家推崇的福克纳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近年来文学的激情和理想的丧失,无疑是文学的悲哀。但是我们在重建理想时,应避免在价值取向上绝对化,因为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人在价值观上的差异,而且在许多问题上是不可能分得出高下尊卑的。以上三点(至爱精神、批判精神、理想精神)便构成了我们对现代理性精神的描述。
为了从概念上将我们所倡导的重构论的叙述话语特征突出出来,因此我们在叙述话语前加上了“现代”二字。这就说明了这种重构的现实主义的叙述方式一定具有现代性,明确地要求要与它的反映对象现代社会相适应,要与它的接受对象现代人的欣赏趣味相适应。传统的现实主义那种照相似的写实手法在今天的读者眼里显然已经十分乏味和单调,人们的审美观念的不断更新要求作家必须用一种新的叙述方式来构筑自己的艺术世界。同时现代工业化的社会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物质世界急剧膨胀,人们的精神世界却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传统现实主义的优长在于表现客观世界,当作家的笔触由外向内即由客观世界向主观世界延伸的时候,就显得无能为力了。不论是面对接受对象,还是面对反映对象,在叙述话语上必须有所突破。学习现代派经验无疑是一条捷径,因为现代派是以深刻地成功地表现人的主观世界而著称的。学习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走现实主义“现代”化的路。这些年来许多探索者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一开始是写实手法+意识流或现代派其他技巧,这种组合的办法不免显得有些生硬和拙劣,给人以不伦不类的感觉。于是后来有些作家便加大现代派技巧的比重,直至完全“现代”化。这实际上是走了一条一些早期现代派作家走过的路。譬如乔伊斯就是由现实主义出发走向现代派的,其结果是成为创立现代派艺术的一代宗师。我们重复走这条路,其结果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另一种方式我们是从拉美文学新小说的巨大成功中获得启发的。这是向欧美现代派学习最为成功的一个范例。他们学习的方式与我们的学习方式有着根本的不同,他们是倒过来走的是一条将现代派进行民族化和现实主义化的路。即把非理性的东西理性化,把非现实的东西现实化。在这些作家的笔下,把幻想写得如同生活中的现实,把看来不真实的东西写得十分逼真,把看来不可能的东西写得完全可能。其结果使其带有神奇色彩的民族文化特质更加突出,现实主义的理性特征也得到了强化,使得变革后的拉美文学更加民族化和更加现实主义化。这就是所谓引起“爆炸”的魔幻现实主义。而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掀起的外国文学热,主要考虑学习人家怎么写,很少考虑应该怎样学习人家怎么写。我们的这种学习的方法最后是以牺牲自身为代价的,而拉美文学非但没有失去自身,而是丰富了自身,完成了一次主体性的超越,并由此而瞩目于世界文坛。两种方法,两种结果,不很值得我们深思吗?我们的作家在学习现代派的时候能否从拉美文学的自我超越进程中汲取点什么呢?
任何一种创作方法或理论的建立最终都是靠作家的创作实践来完成的,这是毫无疑义的。因此,我们提出的这种理论肯定是不完善的,也许是非常荒谬的。我们决不是企图为疗治当前的文学弊端提供一剂良药,或是一把打开文学繁荣之门的钥匙,也不想以此来统一和取代其他文学主张的存在。我们最希望的是它能成为大家感兴趣的一个靶子,我们因此能获得一簇簇金色的箭镞,那将是我们最欣慰的。
我们渴望着大家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