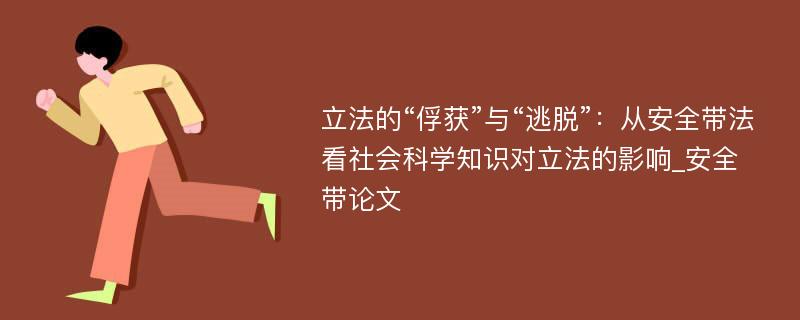
立法的被“俘获”与“逃逸”——从“安全带法”看社会科学知识对立法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安全带论文,科学知识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安全带法”的规范沿革
驾驶汽车时系安全带、骑摩托车要戴头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安全法》)第51条的强制性规定,这些规定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保护驾乘人员安全的措施并被普遍接受。这类强制性立法并非我国独有,而是一种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关于安全带的立法,最早见于1960年代。1964年美国有14个州率先要求机动车辆必须安装安全带,同年总务管理局(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宣布了政府采购车辆的安全标准,其中就包括了安全带的相关规定。依《国家交通与机动车辆安全法》,联邦道路与交通安全委员会在1968年制定的第一个安全标准首要的一条就是:为所有驾驶机动车辆的人员配备安全带(seat belts for all occupants)。[1](P677-725)但强制佩戴安全带的规定在美国出现得却相对比较晚,1984年纽约州才制定了美国第一部安全带法,[2](P315-335)而到了1987年也总共只有31个州制定了类似的法律。[3](P459-470)尽管推广的速度不快,但到目前为止,49个州以及华盛顿都在某种程度上制定了类似的法律。[2]相比之下,新西兰的立法进度显然比美国要快得多,1965年新西兰要求机动车辆必须安装安全带,1972年要求必须佩戴安全带。此外,英国的安全带法制定于1983年。[4](P187-227)而加拿大早在1976年就已经有两个省——安大略和魁北克制定了安全带法,之后其他省份也纷纷跟进,直至1987年,最后一个省份阿尔伯达也制定了类似的法规。[2]
我国安全带立法(与之相同的还有强制摩托车驾驶者戴头盔的规定,由于两者的功能高度类似,下文中将这两种情形统称为安全带法)的立法理由一如既往的不可考,公开出版和可供查找的文献中并没有关于2003和2007年《道路安全法》规定强制系安全带和强制戴头盔的理由。或许,这一规定
不需要解释理由,这是因为,包括本文作者在内的人们几乎都会不假思索地认为:从技术层面来讲,强制系安全带或戴头盔对于个人安全和社会安全是不言自明的。因此即便对此类立法有所质疑,也集中在从道德层面探讨基于个人安全而限制个人自由的正当性上。
二、“安全带法”的被“俘获”——社会科学知识①对“安全带法”的催生
对安全带法能够产生的积极效果,有英国两大集团——伯明翰大学事故研究所和交通与道路研究实验室的研究成果的支持。前者的结论是强制安全带法每年会拯救约1000人并防止或降低数以万计的伤害。后者在1979年的研究结论则被认为是更权威的。该结论认为安全带法会降低40%的死亡风险和60%的严重伤害。[5](P339-364)这两个机构的结论迅速被公众和官方接受并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并且也得到了许多后续研究的支持,尽管在具体的评估数字上可能略有不同,但安全带可以降低伤亡率这一观点却得到了广泛的赞同。
但争议并非不存在。早在1970年,以佩尔茨曼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就认为安全带法非但不会带来什么积极效果反而会造成更恶劣的后果,他们的这一观点和两大集团的研究结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但是后者的观点迅速获得压倒性的优势并形成了广泛共识,而前者的观点则基本上无人关注,更谈不上认同与共识。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耐人寻味的,某种程度上这可能与双方的学术影响力和对公共话语的支配程度有关(并且后者还有可能得到从安全带法中受益的汽车巨头的支持)。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或许在于两大集团的研究结论很大程度上与一般公众对于安全带的直觉反应是相一致的,并且他们的纯“技术”的外表也更容易获得公众的认同。于是,尚需进一步理论论证和实践检验的“系安全带有利于驾乘人员安全”的观点由于形成共识的缘故而在技术层面被认为是科学的。
对于安全带法这样不涉及重大的政治利益的社会规制性的法律,能获得知识层面的科学性证明无疑是至关重要的。由于人们对技术层面的科学性形成了共识,因此尽管在具有强调个人自由传统的西方对于安全带法限制自由的正当性存在一些争论,尽管安全带法带来的安全利益立足于所有人都严格和普遍遵守该法这一前提(这一规范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却被忽略了),但技术层面的共识依然使其具有了公共政策方面的可接受性,因此也就具备了形成立法的民意基础。于是,安全带法不仅在西方国家,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成了立法通例。这是很典型的技术共识“俘获”公共政策的例子。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大集团对安全带法的肯认,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假设、预测以及对现实进行模拟的基础上,无法完全反映真实世界机动车驾驶人的行为。而佩尔茨曼和亚当斯等人对于安全带法的质疑,却在现实世界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印证,并且也引发了更多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
三、“安全带法”对社会科学知识的“逃逸”
(一)真实世界中的“安全带法”
两大集团的研究更多地是在类似于实验室的环境下进行的,佩戴安全带是否会对驾驶人的行为产生影响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得到关注。而佩尔茨曼等人的反对意见也正是由此切入。佩尔茨曼以及之后一系列研究者认为,佩戴安全带会改变驾驶人的驾驶行为,安全带会提高驾驶人对于自身的安全性的预估,由是他们会倾向于驾驶得更冒险(这也间接增加了乘车人的危险性),因此会导致更多的交通事故,而安全带的积极效果也将被驾驶人的这种冒险驾驶行为所部分或者全部抵消(offsetting)。[1]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驾驶者佩戴安全带的行为与致死或严重伤害的交通事故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如果有,这种因果关系的密切程度如何——实在很难直接证实。因为影响到交通事故这一结果的因素有很多,不同的地理、天气乃至人文环境都可能会影响交通事故的数量和严重性,因此很难认定到底关键或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哪个或哪些。并且,驾驶者佩戴安全带之后是否会基于安全感而冒险驾驶所牵涉的完全是当事人的主观心理状态而不是外在行为,从而也就更加难以证实这一因果关系。正是为此,许多学者都回避了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论证这一问题,同时,他们也不像波斯纳与曼昆那样基于标准经济学的进路而得出结论,②他们更多地是从统计学的角度以数字来验证这一假说,从相关性而非因果关系的角度来论证这一理论。
1991年,埃文斯和格拉汉姆收集了美国五十个州的调查数据并进行分析,他们首先观察了安全带的使用率。通过在路边观察的方式,他们发现虽然随执行规则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无一例外的是,在制定了安全带法规之后,各州的安全带使用率都有很明显的提高(平均提高28%)。根据已有的研究表明,佩戴大腿/肩带可以使乘坐人的伤亡率降低40%-50%。由是,如果完全不存在抵消(offset)效果的话,以安全带使用率提高25%-50%计算,那么安全带法的制定应该可以使前座的汽车乘坐人的死亡率下降10%-25%。[6](P61-73)通过对联邦道路交通安全委员会的致命事故报告系统提供的1975至1987年的数据分析,他们发现安全带法使前座的乘坐人(front-seat occupant)的死亡率下降了8%,这一结论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安全带立法行为。可另几项结果却立刻推翻了这一支持。通过对非机动车乘坐人(包括步行者、自行车乘坐人)伤亡数字的分析发现:汽车乘坐人伤亡数字的降低,部分的被非机动车乘坐人伤亡数字的上升抵消了(而这之中骑自行车者的伤亡数字的增加最为惊人,最高的增幅甚至达到了35%)。而对于其中八个州来说,安全带法的效果甚至已经完全被抵消了。由此,他们找到了可以支持佩尔兹曼的证据。[6]
更明显的证据则来自于加巴茨的研究,从1990年到1992年的两年时间里,加巴茨先后发表了四篇关于安全带法的调查报告,除其中一篇调查的是新西兰之外,其他三篇全都是针对美国的调查。在1991年的那篇关于新西兰的调查报告中,他收集了新西兰从1965年(开始强制安装安全带的年份)到1985年的相关数据,并且以伤亡率为因变量建立了一系列最多包括安全带使用率、收入、速度、年龄、酒精、里程数以及时间趋势(time trend)七个自变量的模型,借此他检测了安全带的使用分别对总体的交通伤亡率、机动车伤亡率以及非机动车乘坐人(包括行人、摩托车乘坐人以及自行车乘坐人)的伤亡率的影响。结果,他发现在包括了速度以及时间趋势的模型中,安全带给机动车乘坐人的伤亡率带来的积极效果几乎完全被它带给非机动车乘坐人的消极效果所抵消了,因此安全带对总体的伤亡率带来的积极效果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同样的,在排除了速度这一自变量的死亡人数(率)的模型中,他再次观察到了类似的抵消效果。因此,他得出结论,无论是包括或者不包括速度以及时间趋势这两个自变量的模型最终都支持了不利于安全带法的结果。[7](P310)
被机动车驾驶人的冒险驾驶行为所危害的人群甚至可能还不止于非机动车乘坐人,加巴茨1992年的调查报告表明驾驶人更冒险的驾驶行为非但会造成非机动车乘坐人的更多伤亡,而且也会导致机动车后座乘客的伤亡率的上升。基于从疾病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CDC)通过随机电话抽查得到的安全带使用率③的数据以及从致命事故报告系统(Fatal Accident Reporting System)获得的关于死亡率的数据,他构建了一个类似于佩尔茨曼的模型,但对自变量进行了微调,其总数缩减到了六个:安全带使用率、收入、酒精消费量、速度、城市汽车所占的比重以及里程数。另一个与之前的模型的不同在于,他分别考察了机动车驾驶人、前座以及后座乘坐人的不同伤亡率。而最终的结果显示,制定安全带法均都将在使机动车前座乘坐人变得更安全的同时,大大增加了后座的乘坐人与非机动车乘坐人所必须面对的风险。[8](P157-168)
除了以上提及的这些文章之外,类似的研究还有1994年利沙对挪威的相关研究、[9](P844-857)1995年彼得森等人对装备安全气垫汽车的效果的研究[10](P251-264)以及索贝尔和内斯比特对纳斯卡赛车中安全措施的效果的研究[11]等等。
(二)风险补偿理论及其对安全带法的影响
由佩尔茨曼首先提出并得到随后的一系列学者进一步发展的理论被称为风险补偿理论(risk compensation theory)。这一理论更多地关注真实世界中机动车驾驶人的驾驶行为,认为在真实世界中,由于安全带的影响,驾驶人会更加冒险地驾驶,从而给机动车驾乘人员、非机动车驾乘人员以及步行者带来更大的危险,造成更多的交通事故。他们的理论不仅在逻辑上是可以自洽的,并且也得到了大量的实践证据的支持。赞同这一观点的学者日益增加,在八十年代以后尤其如此。连时下非常流行的教科书如曼昆的《经济学基础》和波斯纳的《法律的经济分析》都采用了这一假说,可见这一理论很大程度上已经取得了通说的地位。
当然,通说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是真理,反对风险补偿理论的文章虽然无法与支持者的文章等量齐观,但也绝不是可以忽略的个例。2003年,科恩和爱因内夫分析了美国所有司法管辖区(jurisdictions)安全带使用率的数据,得出的结论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安全带立法:安全带的使用的确可以降低交通的伤亡率。尽管这一效果远不像联邦道路与交通安全委员宣称的那么明显,但确实没有证据可以支持风险补偿理论的成立。[12](P828-843)更晚近的卡朋特和施特赫尔通过对1991至2005年间美国高中年级年轻人的安全带使用率数据的考察,发现强制使用安全带的法律的确可以大大增加安全带的使用率,并且更高的安全带使用率也导致了更低的交通伤亡率。[13]而森以及迈真的研究也并不完全支持风险补偿理论,[2]类似的研究还有许多。
事实上,由于客观世界的高度复杂性,以及实证研究无法避免的盲人摸象的可能,如果实证研究的结果清一色地支持风险补偿理论,恐怕反而是会更加让人怀疑的。但反对意见的存在同时也让我们无法轻易地断言风险补偿理论就一定是正确的,科学研究毕竟不是民主投票,文章的数量并不能直接证立其正确性。但笔者所要强调的是,无论风险补偿理论是否能够成立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范围内能够成立,已有的大量的实证研究至少证明了因安全带法而导致的更多的不安全是现实存在并且是大量存在的,并不只是学者的猜想和假设。因此,立法者无疑应该充分考虑这一事实。
但立法的现实却再一次印证了并不是正确的事情就一定会得到人们的支持。与风险补偿理论在学界所得到的呼声相反,各国的立法几乎完全不曾受到风险补偿理论的影响,安全带法在八十年代加速扩张开来(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正是风险补偿理论在学界逐渐取得优势的时期),到今天几乎已经是所有国家所共同坚持的法律,全世界的立法者在这个问题上令人惊讶地采取几乎完全一致的立场。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在六七十年代曾经“捕获”了立法的社会科学知识这个时候却似乎对立法失灵了,或者说,知识已经从立法的领域中“逃逸”了出去,为什么会这样?
四、为什么“逃逸”?
正如前文已经提到的,对于安全带法这样不涉及重大的政治利益争夺的社会规制性法律而言,被认为是“正确”(尽管也许事实上未必正确)的知识很容易“俘获”立法,这一点是很容易理解的。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安全带法“逃逸”出风险补偿理论的影响才令人费解。解释事物的逻辑应该是前后一贯的,如果技术性知识在六七十年代可以俘获立法,那么在八九十年代或者当下应该也可以,那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风险补偿理论无法获得立法上的回应呢?
最直接也最便利的解释或许来自法学的保守性:作为规范的法律自身需要稳定,因此它往往滞后于社会生活。尤其是当风险补偿理论本身还存在一定的争议的时候,采取相对保守的策略并不是一种很不能令人理解的选择。这样的解释乍看似乎有理,但却经不起更细致的诘驳:是的,对于风险补偿理论还存在一定的反对声音,但在六七十年代对安全带的效果也并不是没有争议的,两大集团的研究结果并不是唯一的声音,也不能完全证明安全带的积极效果,而当时立法却迅速地被两大集团的研究结论所“俘获”。为什么本应该是保守的立法在那时似乎又不那么保守了呢?
第二种可能的解释是经济学上的路径依赖理论或者说“锁入”理论。根据该理论的解释,不管安全带更安全的观点当初是如何“俘获”立法的(可能是偶然,也可能是人为的设计,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俘获的结果),当安全带法已经成为当然的选择(锁入)时,任何想要改变这一现状的努力(解锁)都将面临巨大的阻力甚至是完全不可能的。很显然,安全带法的现状符合“锁入”理论的特征:不仅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制定了安全带法,并且大多数机动车辆在生产的时候就会预装安全带,更重要的是,社会公众已经完全接受了强制安装和佩戴安全带的规范(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会主动佩戴安全带)。面对这种“锁入”的状况,想要通过立法上的手段来解锁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样的解释在逻辑上是可以成立的,并且似乎也可以得到现实的印证,但问题却出在路径依赖理论本身上,尽管这一理论向我们描述了“锁入”的情形及其后果,但它却不能很好地说明在什么情况下会被“锁入”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又不会,它同样也无法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有些“锁入”的情况可以被解锁而另外一些情况却不能。具体到安全带法而言,为什么在两大集团的研究结论“俘获”立法的时候我们没有被牢牢地“锁入”在没有安全带的情形上?或者为什么当时可以被解锁而之后却不能了?因此,尽管无法直接找出这一解释在逻辑上的漏洞,但显然对这一解释的效力还是需要存疑的。
或许,在六七十年代进行安全带立法时,有来自相对权威的机构论证出该法多么有利于保护人的安全的结论是一个“好消息”,而且符合一般人的心理特点,加上其时参与立法的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对限制人们自由选择的安全带法在学理上的正当性问题,因此当正当性问题通过讨论形成共识从而被解决之时,能带给人们好的期待的立法也就顺理成章了。而风险补偿理论带给人们的则是“坏消息”,对于立法、废法这样需要“有所作为”的行为,基于“坏消息”而启动一个可能备受利益团体反对、且其效果尚未可知的提案并试图通过立法程序,显然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也就是说,人们有行为经济学上所谈到的“现状偏好”的心理,除非能有一个强有力的、好于现状的预期,否则人们就不会愿意改变现状。④因此,规则自身的惯性(法学的保守性)、时代背景以及对立法效果的预期导致了六七十年代的“解锁”和后来的“锁入”,最终的现实结果就是安全带法“逃逸”出了风险补偿理论的影响。
此外,公共选择理论对于解释安全带法的“逃逸”也有一定的说服力:它意味着“逃逸”可能并不完全是自然发生的,而很可能是利益集团作用的结果。很显然,安全带法的存在对于汽车制造商及其利益相关团体是有利的,安全带有助于养成并使公众接受一种“汽车很安全”的印象。因此,基于理性选择的判断,这一利益团体应该会支持安全带法的推广。并且,由于他们很大程度上掌握了更多的媒体资源,因此也就更有可能鼓吹那些有利于安全带法的言论,⑤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风险补偿理论在学界成为了通说但却很少为社会公众所知晓。进一步的,这些利益团体还有可能对立法施加直接的影响,⑥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安全带是否能使道路交通更安全还没有定论的情况下立法就选择了支持安全带立法,也同样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风险补偿理论已成通说,安全带的安全性备受质疑的情况下立法却毫无回应。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的解释很大程度上只适用于欧美国家,对于中国而言,情况可能有着很大的不同。尽管立法时的资料不可考,但可以想见的是,作为非政治性的规制,安全带法很容易作为一种“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获得立法者的认同,这样的认同很可能使得我们在并没有对安全带做更多的研究和考察的时候就制定了安全带法规,知识上的研究在这里很可能从一开始就是缺位的。更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时下法学界的同仁都喜欢引用国外的研究成果,但在风险补偿理论已经成为通说的情况下,依然没有太多人对安全带法这样一种直接影响着数以亿计的人们的生活的法规有任何兴趣。⑦当然,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样的问题太“小”,它不是那种可以被拔高到“宪政”、“法治”的高度的话题,因此它天生就无法得到人们太多的关注,并且我们已有的对安全带的知识看起来也几乎是理所当然、无可质疑的,更多的研究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必要了。这些或许都可以成为理由,但更深入的问题或许在于,法学界对于探索更多社会科学知识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沉醉于规范分析的天堂自得其乐似乎是一种更主流的选择。并且,由于缺乏知识的积淀以及方法上的训练,我们对于探索社会科学知识在事实上也是十分无力的,这多少是一个让人感觉难堪的事实。
五、结论
安全带法体现了立法与社会科学知识的“俘获”和“逃逸”关系,这种关系的原因很复杂,值得进行知识上的探索。或许法学的保守性与不自足性、制度的路径依赖、人们的现状偏好、社会选择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与纠结导致了这一现象的产生。虽然笔者的解释与结论仍难以称得上是具有坚强说服力的、肯定与明确的结论,但笔者所要强调的是,结论如何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注意到安全带法本身可能存在的问题。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点也不是最重要的,笔者更愿意通过对安全带法的对论引出这样一个问题:立法者应该如何处理立法活动与社会科学知识的关系?
很显然,立法,尤其是不涉及政治利益的社会规制性的立法,无可避免地需要引入社会科学知识。但社会科学知识往往是纷繁复杂的,立法上想要加以选择的问题往往可能在社科学术上并没有定论,匆忙的决断很可能是立法被一种片面的观点所“俘获”,从而做出一种错误的或者至少不那么正确的选择,安全带法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由是,要求立法者对相应的知识做更多的了解似乎是一种很自然的选择,但立法者毕竟不可能在所有与立法相关的问题上都是专家,事实上,现实世界中的立法者们在绝大多数立法领域里都很难称其为专家。因此,由于知识缺陷所导致的立法错误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由人所组成的立法机关犯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有可能改正这种错误。在这一点上,安全带法的发展与现状让人深思:立法者不仅有可能为某种片面的知识所“俘获”,并且还可能被永远“锁入”在这种被“俘获”的境地中。换言之,一旦立法者由于知识上的缺陷而做出了错误的选择,那么很可能他们再也没有机会来纠正自己的错误了。因此,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在立法过程中我们究竟要如何才能避免被片面的知识所“俘获”?而一旦被“俘获”,又要如何才可能“逃逸”出来?事实上,“俘获”我们的,可能并不只有安全带法,也许还有卖淫法、吸毒法等等,我们是否有可能,又该如何“逃逸”呢?这确实是立法者和法律学人面对的问题,尽管这类问题的解决非常困难,⑧但至少立法者和法律学人需要承认法律学在这些方面的不自足,并对社会科学知识保持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面对。在此基础上,根据既有的法律规定,尽可能让立法接受社会科学知识的浸润,进而形成科学、合理的规范。
我国既有的法律规定为立法的科学性提供了规范依据,如2000年3月通过的《立法法》第34条、第58条、第68条和第74条分别规定了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在立法时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立法机关在听取意见的时候,固然要发扬民主,听取来自各方的声音,但对于那些政策性色彩不是很浓厚但技术性很强的规则,尤其要听取相关行业专家的意见,以求让立法经历专业知识的洗礼和社会科学知识的验证与指引。
二位作者的分工为:本文的选题、提纲以及主要观点由郭春镇提出,部分文献的收集和整理由郭春镇完成,文章的第四、五部分的初稿主要由郭春镇撰写;本文的部分文献收集与梳理由郭瑰琦完成,文章的第一、二、三部分的初稿主要由郭瑰琦完成。文章的修订稿由双方讨论与协商而成,并由郭春镇负责全文的定稿。
注释:
①或许会有人质疑,系不系安全带对个人安全的影响是个自然科学的问题而非社会科学的问题。对此,我们认为,虽然安全带问题所关联的对身体的伤害程度等涉及自然科学的知识,但本文的分析与论证是基于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而进行的,它们都属于社会科学知识的范畴。
②参见[美]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492-493页;[美]曼昆:《经济学基础》,梁小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页。
③安全带使用率的调查方式是这样的:向被调查者询问安全带使用的频率,并给出了五个备选的选项,总是、几乎总是、有时、很少以及从来不,这些选项将分别被折算成100%、75%、50%、25%和0%。这样的折算当然是有误差的,但应该还是能反映相当一部分的现实。
④特德和马修曾对现状偏好有过深入的研究,认为在现状偏好的情形下,人们会对“早期给以更强烈的关注”。参见William Samuelson and Richard Zeckhauser,Status Quo Bias in Decision Making,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Vol.1(1988),p.7;Ted O' Donoghue and Matthew Rabin,Doing It Now or Later,Am.Econ.Rev.Vol.89(1999),p.106,转引自科林·凯莫勒等:《偏好与理性选择:保守主义人士也能接受的规制——行为经济学与“非对称父爱主义”的案例》,郭春镇译,《北大法律评论》2008年第9卷第1辑,第92页、第103页。
⑤各种媒体上关于安全带测试或者其他的汽车安全性测试的报道屡见不鲜,如以汽车安全性测试为关键词在google上搜索,在0.2秒的时间里就产生了7,430,000个结果。
⑥如欧美的院外游说团体。
⑦在中国期刊网数据库上,尽管以汽车安全带为关键词搜索的论文在1980-2009年的数字为194篇,以交通安全法为关键词的结果为1856个,以安全带法为关键词搜索的结果为49个,但法学类的论文为零。
⑧详细和具有说服力的论述可见成凡:《法学知识的现状偏差——以麻风病作为切入点》,《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6期;成凡:《社会科学“包装”法学——它的社会科学含义》,《北大法律评论》2005年第7卷第1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