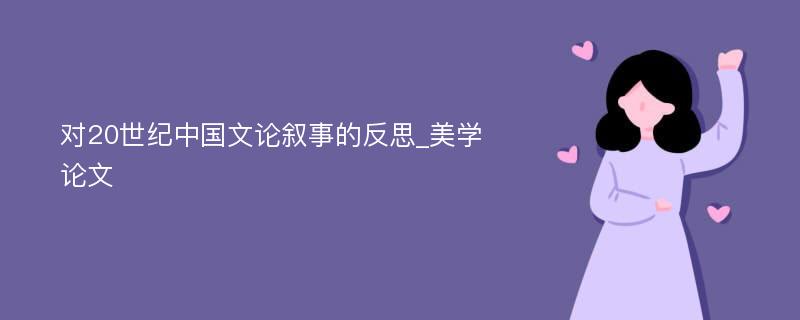
对二十世纪中国文论叙述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世纪末之今日回顾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论历史的“事实本身”不仅可能而且必需。我以为迄今为止的二十世纪中国文论可以概括为彼此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三大叙述:
1.有关文学的“革命叙述”。
2.有关文学的“审美叙述”。
3.有关文学的“解构叙述”。
叙述1和叙述2是以直接对抗论争的样式展开自身的,叙述3 则放弃了这种对抗而别开一路。从时间上看,叙述1和叙述2的冲突大致始于世纪初而终止于80年代末。叙述3开始于80年代末, 迄今虽已音声稀微但未见终结。从性质上看,叙述1 主要受俄苏马列文论影响且暗合中国儒家诗教传统,叙述2主要受西欧自由美学影响且暗合中国的庄禅之学, 叙述3主要受西方解构理论影响且暗合中国的游戏主义。
1 将“革命”和“文学”联系起来思考,并对文学进行“革命表达”,至少可以追溯到梁启超。梁氏的两大口号分别为“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前者见于他的《夏威夷游记》,称“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后者见于《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称“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
梁启超之关注诗与小说,且倡言要对其革命,目的十分明确,即出于“新民”之需。
在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失败后,梁启超认为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蚩蚩之氓”的“蒙昧”,因此,政治变革的前提是“新民”,即“开发民智民德”。而在儒家“诗教”、“乐教”和洋人政治变革成功的经验中,他发现了诗与小说的启蒙教化功能,不过,他以为当今之“诗、词、曲三者皆成为陈设古玩”,而“小说”也只是些供人消遣的“闲书”,因此,只有先行对诗与小说进行“革命”,才能使之担当启蒙教化之重任。
十分显然,在梁启超对诗与文学的思考和表达中确立了一种思维范式,那就是从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思考思想文化革命,又从思想文化革命的角度思考文学艺术革命。这里的逻辑是:文学艺术的革命是为了思想文化革命,思想文化革命是为了社会政治革命。社会政治革命作为终极目标规定着思考思想文化革命和文学艺术革命的基本视域和话语样式。简言之,这三位一体的“革命”规定着有关“文学”的思考与叙述。
“五四”以后,从“文学革命”的表达式到“革命文学”的表达式之转换正是上述逻辑的具体展开。事实上,“文学革命”只是一种初始的、未完成的表达式,因为它将一种隐含的“目的”掩盖着,而且这一目的至少在话语表面是不曾确指的,这种含混性使“文学革命”在“革命”之后完全有可能成为一种“自由文学”。事实上,一些参与“文学革命”的自由知识分子就想这样干。正是为了明确杜绝这种可能,而将“文学革命”的目标引向(社会政治的)“革命”,革命知识分子才将“文学革命”这一结构颠倒过来成了“革命文学”。
这一颠倒看似不经意,实则意义重大,因为“革命文学”这一口号在话语形态和结构上都更直接地显明了革命者思考文学的立场,同时更准确地表达了“革命”对“文学”的限制。
“革命文学”的完整结构是“革命的文学”。“革命的文学”既可以是“偏正结构”,又可以是“所属结构”和“目的结构”。这种关系在一种英文结构中可以更清楚地见出,此结构可写作“The Literature of Revolution”。在此“of”所连结的前后语词间的关系可以是“性质限定性关系”,也可以是“所属限定性关系”和“目的限定性关系”。作为“性质限定性关系”的“偏正结构”,“文学”(Literature)是中心词,“革命的”(of Revolution)是附加的修饰词, 就此而言,“革命文学”论的确是在谈论一种具有革命性质的“文学”理论。而作为“所属限定性关系”的“所属结构”,“革命的”(of Revolution)反而成为事实上的主体和“文学”(literature)的拥有者, 文学 成了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此外,作为“目的限定性关系”的“目的结构”,“of”后面的“革命”(Revolation)则是“文学”的目的。就此而言,“革命文学”与其说在谈“文学”,不如说在谈“革命”,或者说在谈一种被命名为文学方式的“革命”理论。
难怪苏汶笑书呆子胡秋原与左翼文坛争什么有关“文学”之短长,因为对方的真意根本不是谈“文学”而是谈“革命”。苏汶之说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尽然,因为在上述“偏正结构”中,左翼文坛也是着眼于文学的,更何况他们还真诚地相信文学和革命是一回事。当年周扬就如此说道:“革命不但不妨碍文学,而且提高了文学。只有革命的阶级才能推进今后的世界的文学,把文学提高到空前的水准”〔1〕。 更为重要的是,“革命文学”论者认为只有“革命文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因为,“你假使是一个前进的战士,你就一定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百分之百地发挥阶级性、党派性,这样,你不但会接近真理,而且只有你才是真理的唯一的具现者”〔2〕。 “革命的文学”才是“真理的文学”,“具有最高价值的文学”,因此,唯有“革命的文学”才具有存在的合法性。
就此而言,“革命的”对“文学”的限制乃是文学真理性、正义性,至善性乃至艺术性的最终保证。事实上,五四以来的左翼文论之全部努力都在论证将“革命的”加在“文学”前面的合理合法性。因此,唯有“革命的文学”乃是左翼文论的“元叙述”。依此延伸而出的叙述有“进步的文学”、“无产阶级的文学”、“劳苦大众的文学”、“人民的文学”、“社会主义的文学”、“工农兵的文学”以及“革命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等等。与之对应的叙述有“反动的文学”、“落后的文学”、“资产阶级的文学”、“封资修的文学”以及“反动的浪漫主义”、“消极的浪漫主义”等等。
2 将“文学”与“审美”联系起来思考,并对文学进行“审美表述”,至少可以追溯到王国维。王国维与梁启超同时,都处身于大变革时代,但二人的志趣全然不同。梁启超志在维新变法,向往革命;王国维志在学术真理,向往新学。于是,同是思考文学,梁启超取“革命”之一路,故而将文学先行设定为革命的工具;王国维则取“学术”之一路,故而将文学先行设定为独立的学术对象来加以研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的中国文论在主要思路上大抵不出二人之右。
受康德和叔本华影响的王国维是在“美学”的视野中研究文学的。康德美学的核心在于确定审美活动的非功利性和独立性,以及艺术与审美的本质同一性,为此,作为审美活动的艺术被设定为与现实功利无关的独立的情感活动领域,这一领域没有任何外在目的,它自身的游戏就是目的本身,王国维称此为“纯粹美术之目的”,并将这样一种艺术标举为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称之为“纯文学”、“纯美术”。在此一度,他批评中国传统文学的政治功利倾向,“观诗歌方面,则咏史怀古感事赠人之题目,弥满充塞于诗界,而抒情叙事之作,仟佰不能得一,其有美术价值者,仅其写自然之美之一方面耳。甚至戏曲小说之纯文学,亦往往以惩劝为旨,其有纯粹美术上之目的者,也非唯不知贵,且力贬焉”〔3〕。王国维之推崇《红楼梦》就在于它具有纯粹美术之目的。 他认为,具有纯粹美术之目的的文学是“可爱玩而不可利害者”,它具有“神圣之位置与独立之价值”〔4〕。
王国维这一思路显然大异于梁启超,他至少确立了这样一些原则:其一,文学被视为有自身目的而无任何外在目的的活动,因此,不能就文学与政治、伦理等外在关系来思考文学的问题,文学是独立自主的,它有自身的规律及规定。其二,独立自主的文学领域被认为在本质上是审美的,因此,只能借助美学理论思考文学的问题,或者说,只有将文学作为审美活动来叙述才是合法的。
在世纪初的革命时代,王国维这种学术姿态以及非功利的文学主张显然是极其不合“时宜”的,故而常被人骂为反动保守的封建遗老。这一情形带来两种后果,一方面它强化了自王国维以来所接受的康德美学,使更多的人开始在此一路来思考文学艺术的问题;另一方面更进一步使革命者明白了康德美学对革命的危害性,因为康德美学一旦贯彻到底就不仅反对文学载“孔孟之道”,也反对文学载“革命之道”,故而在“文学革命”时期鼓吹反“文以载道”的郭沫若在三十年代初所写的《文学革命之回顾》中说:“古人说‘文以载道’,在文学革命的当时虽曾尽力的加以抨击,其实这个公式倒是一点不错的。道就是时代的社会意识。在封建时代的社会意识是纲常伦教,所以那时的文所载的道便是忠孝节义的讴歌。近世资本制度时代的社会意识是尊重天赋人权,鼓励自由竞争,所以这时候的文便不能不来载这个自由平等的新道。这个道和封建社会的道根本是对立的,所以在这儿便不能不来一个划时期的文艺上的革命”〔5〕。
3 显然,革命文论和审美文论冲突的焦点就在于:文学的目的究竟是革命呢还是审美?在审美文论看来,将文学的目的设定为革命就取消了文学的独立性和自身目的,文学被降格为革命的工具和武器,只有从审美的角度看待文学自身的目的才能保证文学的独立自主性,并将文学作为文学来加以研究。而在革命文论看来,将文学的目的规定为审美就否定了文学的社会性和阶级性,文学被抽象为远离现实或闭于象牙之塔中的东西,这种东西在“革命时代”不仅无助于革命反而对革命有害。更重要的是,在革命文论家看来所谓“文学性”最终不过是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性”和革命时代的“革命性”而已。
其实,“革命”和“审美”都不过是理解文学和设定文学的不同“眼界”。
“革命”的作为一种“眼界”,它体现了革命时代对文学思考的“政治理性限制”,这种限制因启蒙、救亡,反帝反封建等一系列迫在眉睫的现实任务而“显得”是合理合法的。在那个一切为了革命的时代,“革命”意味着真、善、美,意味着拯救、希望与解放,“革命”作为全社会全民的首要至善目标超乎于一切事物自身的目标之上,因此,为了革命目标必须放弃自我目标,文学也不例外。革命文论就深深植根于这一政治理性要求,其合理合法性也来源于此。因此,当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常常能谅解这一时期因革命而对文学的粗暴理解。
问题在于,即使我们如此谅解了这种粗暴就等于我们在学理上消除了这种粗暴吗?我们的谅解只说明我们对这种“粗暴”之发生的原由表示理解,它并不说明我们有理由可以置这种“粗暴”于不顾。就学术而言,重要的是分析这种“粗暴”的非学理性因素以杜绝这种“粗暴”的重演。
如果说“革命文论”所谓的合理合法性源于上述“政治理性限制”,那么,对文学的粗暴也根源于此。这种限制的要害就是要取消文学的独立性而使之成为革命阶级和革命政党的喉舌,其学理证明主要是“文学的阶级性和党性理论”,其理论基础是“经济因素决定论”和“意识形态决定论”。对此,本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多有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要说明文学的超越立场恰恰可以站在各阶级和意识形态之外对此作自由的言述,文学的独立性恰在于它的社会文化批判功能和超意识形态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论说十分复杂,在此不可深究,我只是借此点明文学独立性的问题的确是一个反政治理性限制的问题,它显示的是另一种看待文学的眼光。
这另一种眼光在本世纪的中国主要落实为“审美眼光”。不过,“审美眼光”与西马的“社会文化批判眼光”不同,前者强调文艺超脱社会历史而自由自适的乌托邦性质,后者强调文艺超越社会文化以重新对此作自由的批判的性质。尽管如此,在主张文艺的独立自由方面它们却是一致的。正是在此一度,审美文论与革命文论水火不容。前者强调文艺的自由,后者限制文艺的自由;前者主张文艺的超阶级性和非党派性,后者坚持文艺的阶级性和党派性。事实上,九十年代前的中国现代文论史就是一个“限制和反限制”的历史。革命文论要千方百计将“革命的”(以及“无产阶级的”等)这一限定词加在“文学”头上,只准文学思考在“革命视野”中进行;审美文论则千方百计抵制这一限定,要拆除“革命”对“文学”的限定关系,恢复“文学”这一中心词的独立实存地位,使文学思考在“审美视野”中进行。
察其中国现代文论史,从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到二十年代的“文学革命”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革命文论的主要实绩就是“合理合法”地完成了“革命”对“文学”的限制。“革命的文学”及其派生的文论话语逐步成为中国现代文论中最具合法性的权力话语,这种话语随着政党国家的建立以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不断革命论而起主导作用。虽然,二十年代的“现代评论派”、三十年代的“自由人”、“第三种人”,四十年代的“自由知识分子”以及五十年代的一些“右派”也反抗、抵制这种限制,试图从学术上研究独立自由的文学,但终不成气候,最后以“反革命”、“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等恶名而被批判和清除。至于那些在二、三十年代即生即灭的主义学说也都因其与革命无关或有害而被忽略或淹没。到了七十年代,偌大一个中国只剩下“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以及“两结合”之主义了。
然而,随着“革命时代”的终结,八十年代中国文论的情况发生了“翻转”。亦即革命/审美这种二元对立间的价值砝码发生了位移,“革命文论”的合法性受到了怀疑和挑战,并逐渐失去了合理合法性;反之,“审美文论”的合法性却不断得到肯定并进而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文论样式。
回顾八十年代的这一“翻转”很有意思。这一翻转起始于重新讨论革命文论的合法性理论基础,即“文艺的阶级性和党性原则”问题。严格说来,这种讨论并没有超出二、三十年代“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视野,但为什么在二、三十年代被大多数人肯定的东西在八十年代则被大多数人否定了呢?仔细琢磨起来,八十年代人们放弃“文艺的阶级性和党性原则”并不是因为什么新的学理之提出,而是因为别的因素的介入而使人们重新咀嚼那已被遗忘的学理并开始信赖它。这一因素就是“革命”在“人”身上留下的现实“伤痕”。准确地说是“革命信仰”的危机使“革命”本身的合法性受到怀疑。正是这一现实情境的根本变化为人们提供了重新看待阶级斗争和革命斗争之合法性的眼光,并为“革命”和“文学”的剥离准备了社会条件。八十年代初的“人道主义论”就是这一剥离的最初努力,文学不再被看成是某个“阶级”的文学而是“人”的文学,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的内在隐喻就是坚持这一剥离。从此以后,文学批评话语中那些常常附加在前面的限定词,诸如“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等等,逐渐消失。
值得注意的是,摆脱“革命”的“文学”很快就被纳入“美学视野”。八十年代的“人道主义热”和“美学热”同时发生并非偶然,因为在残酷的革命斗争年代,“人”与“美学”的命运相差无几。强调人道主义和美学的目的就是要使“人”和“美学”彻底摆脱“革命”的限制而获得自由。值得注意的是:八十年代的“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美学”也认为美的本质是自由。实际上,八十年代的人道主义和美学都是一种无所不包的“自由学说”,“审美”乃是“自由”的代名词。如当时颇有影响的美学家高尔泰就一言以蔽之:“美是自由的象征”。
八十年代的“审美文论”骨子里是这种自由学说的一部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八十年代毕竟是中国现代史上空前开放的时代,随着各种新思潮的涌入,八十年代的审美文论具有了一些新的特点。首先它在思想内涵上不仅强化了康德美学的非功利原则以及尼采美学的非理性原则,还广泛接受了存在主义美学的个体自由原则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审美超越理论,但其主流仍是德国的浪漫美学。其次它接受了俄国形式主义和西方新批评等文论有关文学本体论的思想。这些特点使八十年代的审美文论主要在两个维度上展开,其一是审美之维,其二是本体论之维。
“审美之维”进一步强化了自王国维以来将文学等同于审美,或者说从审美角度理解文学本质的思路,而且“审美”的本质被明确表述为“自由”。
“本体论之维”则以新的理论术语,即“文学本体”,重新肯定五四以来有关文学独立性的主张,并将这种主张纳入理论表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学本体”在此被设定为“审美本体”。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审美文论的主要努力就是要证明在“革命的”限制之外有一个独立自由的“审美本体”存在,而真正的文学就是这种本体。八十年代审美文论这种“审美”与“本体论”的双向努力大致以刘晓波的《审美与人的自由》和王岳川的《艺术本体论》告终,其中刘小枫的《诗化哲学》也起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问题在于,在文学艺术中实现的审美自由能够摆脱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吗?伟大的文学艺术真的沉醉于这种幻想的自由了吗?王岳川的《艺术本体论》在表面上似乎是以中立的学术态度清理艺术本体论的种种问题,但对此问题的关注所透露的艺术本体论热情仍然可见“审美文论”的潜在立场,尤其是论说中不断闪烁其词的“审美”和“诗化”等字眼的暗示。因此,就文论自身的逻辑展开而言,我以为《艺术本体论》意味着八十年代审美文论的终结。
4 如果说将文学理解成革命从根本上取消了文学的独立自由和超越之维,而将文学理解成审美就真的抵达了文学的独立本体和自由超越了吗?我不敢肯定。
我在前不久一篇题为《奥斯维辛之后:审美与入诗》(见《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4期)的文章中区分了审美与艺术。 我以为伟大的艺术绝不可归之为审美活动,因为艺术有一个非审美的维度。
艺术与审美混淆的根源主要在于它们表面的相似性,即审美和艺术都有一种对社会历史作自由超越的冲动。然而,艺术和审美的“自由超越”在性质、目的和状态等方面都有根本的不同。审美的自由超越目的在解脱和消遣自适,其状态是物我两忘的怡然自得或自我陶醉,其本质在暂时遗忘人处身其中的现实关系而进入乌有之乡的游心。(伟大的)艺术的自由超越目的在重新介入社会历史,去除俗常之蔽以恢复洞见和更高的人生关怀,其状态是震动、醒悟、恢复记忆以及痛苦之澄明,其本质在重建自我与世界的关系。
1993年“意大利艺术双年展”有一件获奖作品曾强烈震撼过我,并使我直观审美与艺术的区别。这件装置作品由德国艺术家汉斯·哈克创作,名曰“德国厅”。该作品由台阶、大门、门徽、大厅、地板、照片等组成。在台阶边你仰头一望,沉重的方形大门上有一巨大的门徽,这门徽的造型图案是东西德统一后首次发行的德国货币。当你再放平目光,那目光穿过敞开的门洞便直接与另一双目光相遇了,那目光太熟悉了,是希特勒的目光。一幅巨大的横幅黑白照片铺满了整个门厅的正壁,那是希特勒和他的死党们的合影。当你拾级而上,跨过门槛,便踏上了早已四分五裂的地板,门厅里光线阴森,只是门洞外的日光笔直投射在希特勒的目光上,你在这破碎的地板上走来走去,地板发出不和谐的声音,然后你走出去,回过头再对视那双目光,并抬头看看作为门徽的东西德统一后的巨大硬币……
作品沉甸甸地将某种东西给与了我,给了我什么呢?整整一代人的历史、现实与未来,一个时代的真理与谎言,血与泪、幸与不幸……每当我面对各种名目的斗争与争端我都会想起这件作品,想起那阴森的一切,谨记那一切所默默陈述的故事。
与这一作品的遭遇过程就是艺术与审美的冲实过程。审美冲动不断使你执迷留连玩味于大门质地的厚重、黑白照片的精美、门徽制作的工巧、整体布局的智慧而无视所有这一切向你直呈的意义。相反,艺术的冲动却不断中止你的审美欣赏与玩味,将你带到审美形式之外的精神意义面前,在那里你完全被一种洞见之澄明和关怀之痛苦所占据,而此洞见和痛苦的全部根由不是别的,就是你处身其中的历史、现实、未来、真理、谎言、冷漠与关切……
十分显然,这样一件作品也是可以审美的,但只要你以审美的态度去打量它,它的意义就对你隐蔽着。同样显然的是,艺术,尤其是伟大的艺术都是因其意义而存在的,因此,只有当你超越审美的态度,跨过审美距离(当然不是回到日常功利的立场)而直面艺术作品的事实本身时,它才对你说话。也只是在此刻,艺术作品才作为艺术而存在。
八十年代“审美文论”的根本迷失就在于它混淆了审美与艺术的根本界限,将艺术之意义世界混同于审美的空无境界了。为此,审美文论始终没办法理解艺术和现实世界的关系问题,在审美逻辑的终点上,艺术空间只能被设定为与现实历史无关的“诗化乌托邦”。就此而言,审美文论一方面让艺术摆脱了革命的限制而获得自由,另一方面又将“自由”轻抛给审美的天空而不着大地,因此,对艺术的审美思考同样远离了伟大的艺术。
5 八十年代末的审美文论在迅速走向极端之后,就很快因其无限的高蹈而被人们厌倦了,一种新的文论样式正悄悄诞生,那就是“解构文论”。
“解构文论”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难以细究,不过其主要原因还是清楚的,那就是“人文理想主义”的幻灭。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人们曾经历了“革命的人文理想主义”的幻灭,但取而代之的是“自由的人文理想主义”。“自由的人文理想主义”在迅速高涨的同时又迅速地在现实中挫败,这种挫败不仅来自政治方面,也来自突然暴发的商业文化方面。1989年张颐武那篇题为《理想主义的终结》(见《北京文学》1989年第4 期)的文章可以看作这一深刻危机的表征,尽管张文的具体论说不尽如人意。
理想主义的终结在根本上导致了意义虚无和空缺。就文学言述而言,它在根本上抽取了“所指”的实在性而使其还原为纯粹空洞的“能指”。事实上,在过去,无论是文学写作还是批评,“意义”的表达和阐释都是以一个总体上的人文理想主义信仰来保证的。革命的人文理想主义和自由的人文理想主义各自都构造了它们所信赖不移的“过去”(历史)、“现在”(现实)、“未来”(狭义上的“理想”),构造了它们所信赖的“人”和“真理”,而“语词”与“世界”(即上述的历史、现实、未来、人和真理)的对应关系则保证了文学(语词)对世界(历史等)的表达。历史、现实、未来、人与真理作为被设定的“世界”乃是文学能指的“终极所指”或“意义本源”。
人文理想主义的终结与意义本源的消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它具体表现为“历史”、“现实”、“未来”、“人”、“真理”的死亡或解体。失去了“意义本源”的言述再也无法回到传统的“意义言述”上去了。
“说什么”突然变成了一种绝望的困境,所谓八十年代末期的“失语”就是“不知道说什么”的困境。过去,要说的“什么”终究在那里,是伸手可触的;现在,要说的“什么”却突然不翼而飞了,至少我们再也难以自信地说“什么”。“失语”状态的另一表征是,言说者被迫关注“怎么说”的问题,此一关注绝不只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转向,其深刻的背景更在于要说的“什么”不在了,“说什么”或谈论应该说什么已成为事实上的空谈。
“什么”(历史、现实、未来、人与真理——终极所指)的消失在陈晓明的一篇文章中写成了《拆除深度模式》(见《文艺研究》1989年第2期),那“深度”其实就是那要说且一直被说的“什么”。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深度”的拆除并不像西方那样主要是一种理论批判的结果,而更多的是历史现实运作本身的结果。正如陈晓明所说的那样,在中国的理论批评家尚未动手“解构”之前,那“深度”(意义)已经自行解构了。尽管如此,倘若没有西方解构理论的引进,我们当用什么话语来表达这一解构呢?
因此,解构文论产生的另一原因是西方解构理论的大量引介,正是这一理论为中国理论批评家提供了一种理解和表述“意义空缺”之现状的参照系和话语样式。事实上,一旦我们不再相信过去那些文本所指述的“历史”、“现实”、“未来”、“人”与“真理”时,我们面前剩下的就只是一堆空洞的能指了。这种感受乃是中国批评家接受西方解构理论的自身条件。
此外,一批六十年代出生,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写作,后来被称之为“先锋派”的作家似乎天然地站在“人文理想主义”之外而置身于“意义的虚无”之中,他们一开始就对写“什么”不感兴趣,而着迷于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等人的写作方式,他们碰巧玩上了“如何写”的游戏。尽管这些作家对理论上的“解构”还一无所知,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碰巧操作了一种无深度的平面写作,这种写作使当时的批评界手足无措,因为无法对此进行“意义阐释”。这一困境迫使批评界寻找新的理论模式和话语样式,而就在这时解构理论和批评策略的大量引介恰好与批评界的渴求一拍即合。1988年至1990年,陈晓明写了《解构的踪迹:话语、历史与人》一书(出版于1994年),这本书就明确表示了要“通过对解构主义的理解和运用来找到充实当代理论和批评的途径。”〔6〕
6 “解构文论”作为一种文论样式已大异于“革命文论”和“审美文论”。不管革命文论和审美文论的冲突多么激烈,分歧多么大,它们都依存于总体的“人文理想主义”背景,都信赖某个“意义本源”的存在,都认为文学是一种意义表达活动,批评是一种意义阐释活动。它们的分歧仅在于各自设计的“意义本源”不同,这不同的“意义本源”就是那不同的“什么”,因此,它们的论争归根到底是“写什么”的论争(即使论及“如何写”也是为了谈“写什么”),是一种“立场”之争。
“解构文论”对“写什么”的论争不感兴趣,因为那个“什么”不知去向了,所以,它不相信文学是意义的表达或批评是意义的阐释。在它看来,革命文论和审美文论的论争已是过去的事情,在今天毫无根基。
陈晓明曾这样写道:“超越性的信仰一经解除,现实作为立足点也就崩溃了。艺术本文不再是对生活的阐释,不再是超越生活的审美空间……本文就只是一次写作过程,一大串语词的游戏,一大堆生活碎片的拼凑娱乐”〔7〕。程文超也说:“后现代艺术不追求表达某种思想, 因而,它不去追求某种深度。它呈现的,是一个平面,一次游戏。后现代艺术不需要解释,对它,你需要去体验,去陶醉。看莎士比亚,如果你得到美感,你一定伴随着审美判断和更进一步的思考去深挖意蕴,而玩游戏机,如果你得到享受,你只会希望再玩一会儿而充分体验那‘享受’,却不会去思考什么。”〔8〕
在“什么”(终极所指)消失之后,解构文论只谈能指的游戏并只做能指的游戏。《马原的叙事圈套》就在谈马原的能指游戏并与之一起游戏。在这篇文章中,批评不仅揭示作家语言游戏之诡计以显示所写的“什么”之虚无,批评本身也玩这种语言游戏以显示批评的“什么”之虚无,最后剩下的只是玩了一次游戏机的快感。谁要是按惯常“意义阐释”的批评程式去阅读解构批评的文本都注定了要讨苦吃,不信你去读读吴亮这篇《马原的叙事圈套》或陈晓明那篇《暴力游戏:无主体的话语》。
乍一看,近几年的解构文论与批评如万花筒一般使人眼花缭乱,名目繁多,在所谓“后现代批评”、“先锋批评”中都能看到它的影子,而我将它们统称为“解构批评”乃是就其主要旨趣而言。这种旨趣不仅深根于中国现实本身的“人文理想主义”的解体,也依存于西方解构主义的一套话语。
7 无论中国式的解构批评还是西方正宗的解构批评都是“意义虚无时代”的表征。作为这一时代的言述,这种批评为我们理解意义之虚无提供了一条道路。
问题在于,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它将我们引向了那里?
我以为“解构文论”立足其上的“解构时尚”在根本上误解了“意义的虚构性”和“意义存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之间的关联。当这种“时尚”(注意,我称之为“时尚”是因为它并不等于西方解构理论本身)受西方解构理论启发而在语言批判中发现意义的虚构性时,它见到了伟大的真理,走出了人类那个古老的梦幻(将虚构的意义看作天经地义而客观存在的东西)。然而,当这种时尚据此而断言任何意义的存在都不可信而是非法的东西并拒绝重建意义时,它则在说一个可怕的谬论,因为“意义的虚构性”证明的只是“意义原本不存在”,但不能证明“意义不存在”,更不能证明“意义不能或不应存在”。这个道理简单得就像一座房子的存在一样,你可以说这座房子原本不存在或说地球上原本没有房子,但不能说这座已建好并有人居于其中的房子现在不存在,更不能说房子不能或不应存在,因为人之为人就在于他是居住在自己建筑的房子中的存在者。
其实,“意义”就像“房子”,如果一个人硬是相信“房子”天然就是地球上的存在物那是可笑的,但一个人在发现房子原本不存在而只是人自己建筑的东西,又发现自己建筑的房子不过是自囚的牢房之后开始拆掉这囚牢并不准再建新房那就更为可笑了。
西方解构理论的真理性在于它揭示了意义之自然信仰的虚妄,从而使意义的自我怀疑与批判成为可能;此外它还揭示了形而上学所建构的意义世界之非人性并坚决的解构这一世界。然而,解构理论太过迷恋这种解构游戏了,并造成了一种误解,似乎任何重建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僭妄。
不过,问题的复杂性正在于:我们真能偏离形而上学的思路而重建意义的新世界吗?
近来国内有人提倡重建人文精神和道德理想,这无疑反映了人们对意义虚无的反抗和重建意义的要求,但令人担心的是,谁能保证不重蹈形而上学的覆辙呢?
困难在于:我们能因为这种担心而永远忍受意义的虚无而漂泊于荒原吗?
在此我不能深究这些问题,我提示这一背景及其问题旨在显明中国当代文论的基础性危机绝不是“文论学科”内部的问题而是总体文化的危机或意义危机。只要总体文化尚处在一种意义虚无状态,解构文论就还会延续下去,因为在这样一个时代,除了语言游戏你还能做什么呢?
未来文学理论的基点在哪里?
也许只有当我们真正拥有了一种新的意义理论,并切实地重建了一种较为可信的“能指-所指-存在”的关系之后,这一基点才会显现。
注释:
〔1〕〔2〕周扬《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见《三十年代“文艺自由论辩”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47、143页。
〔3〕《王国维遗书·静安文集》第5册,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102页。
〔4〕转引自聂振斌《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
〔5〕转引自包忠文编《现代文学观念发展史》, 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22页。
〔6〕陈晓明《解构的踪迹:话语、历史与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7〕陈晓明《无边的挑战》,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第43页。
〔8〕程文超《意义的诱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第122页。
标签:美学论文; 艺术本体论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艺术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读书论文; 梁启超论文; 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