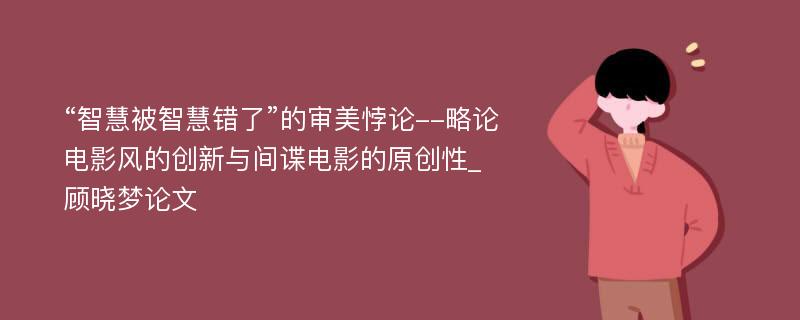
“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美学悖论——简评电影《风声》的创新兼及谍战片的创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聪明反被聪明误论文,简评论文,悖论论文,创意论文,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9年国庆前后风靡全国的《风声》是一部商业性大片,还是一部主旋律影片?是一次成功的文化营销,还是一次失败的电影探索?是一部精彩的谍战传奇,还是一场拙劣的视觉展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风声”过后,尘埃落定,回望银幕,是感慨中的嘘唏,还是欢欣中的忧伤,更是沉重中的思考。对于电影《风声》,当我们用票房价值去衡量时,它无疑是目前国内同类题材的佼佼者;当我们用表演艺术去评价时,它肯定是明星级的演员的真实水平;当我们用制作体制去评说时,它绝对是中国电影市场的有益探索;其实《风声》成功的还给我们留下很多启发,诸如:如何改编小说,如何设置场景,如何运用道具,如何挖掘人物心理,等等,总之它的艺术创新地方太多了,却恰恰忽略了作为艺术的电影应该坚守的美学灵魂和文化关怀:人性——悲剧毁灭时而表现出来的优美而高贵的人性。可以说,《风声》在艺术的创新之时而忘记了审美的基本底线,由此陷入了“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美学悖论怪圈。
那么,这个悖论是如何形成的,又怎样才能解开这个烦难的怪圈呢?
一、主题的悖论:由信仰坚定到信仰消逝
这部场景惊心动魄、情节峰回路转、人物死里逃生的影片究竟要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到了电影的最后才让观众恍然大悟,历经九死一生的吴志国从顾晓梦缝制的旗袍的针脚里读出了她传递的情报,也是最后遗言:
我亲爱的人
我对你们如此无情
只因民族已到存亡之际
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
我的肉体即将陨灭
灵魂却将与你们同在
敌人不会了解
老鬼、老枪不是个人
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
我的躯壳留在人间
灵魂已在风中随信仰而去……
它生动而准确地演绎出了我党的秘密工作者吴志国和顾晓梦体现出的崇尚荣誉和忠诚理想。正如一些网友说的,“惊悚巨制《风声》:最极端的拷问和最强大的信仰。”那么,它拷问的什么呢?拷问的是生命的极限承受力,它信仰的是什么呢?信仰的是正义和道义的力量、真理和真诚的力量。对此导演高群书也说道:“《风声》比以前的革命影片更真实,以前敌人拷打,大家常见老虎凳、辣椒水之类的,说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但钢铁到底是怎么样炼成的这点就比较少展现,他们面临的不仅仅是皮肉之苦,还有生理上心理上的对抗,《风声》剧情的进展要靠这个来推动,以前的影片太过简单化。《风声》也讲信仰的力量,他们在极限状态下靠什么才能撑下来。这里不仅仅是职业的信仰,而是对自己坚守的一种精神的膜拜,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里面的英雄是我们需要仰视的对象。我们现在有时也可能要面对很多的困难,该如何坚守,有很多可以学习。”[1]如果说坚持到底挑战极限的信念,表现出来的、尤其是我方生命的顽强和勇毅,象征着人类生命力放射的耀眼光芒,那么透过这超越普通生命和普遍人性,我们还将能看到些什么呢?那就是一言九鼎和义无反顾的信仰,这是视荣誉比生命更重要的信仰。影片中的吴志国和顾晓梦,他们不论是遭受酷刑折磨,还是人格凌辱,都置生死于度外,坚信正义一定能胜利,对于炼狱中的他们来说,“因为,有信仰就有心灵的寄托之处,它为苦难的生命给予一次温馨的抚慰。因为,有信仰就有希望的出口通道,它为尘世的生命露出一线微茫的光亮。”[2]这不仅给炼狱中的革命者以信心和力量,而且给观众们以希望和欣慰。
然而,影片一方面强化了信仰对于革命者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把神圣信仰的光环罩在了敌人的头顶。特务机关长武田因为其祖父在日俄战争中自杀而使得他的从军道路格外艰难,而他日以继夜、处心积虑地为了破获这个泄密案的目的就是洗清冤屈,当同僚把他视为胆小鬼时他竟然扑向对方,以笔刺喉,从而捍卫了军人荣誉,而他最后被杀,也帮助他实现了武士道精神的信仰。特务处长王田香在所有人都绝望的时刻,他绝不动摇,还执着地相信奇迹即将发生。如果《风声》比一般的谍战片高出一筹的是它渲染了信仰,这个人类精神世界崇高价值标准,这是它的美学立意超越寻常的表现。也许是《永不消失的电波》一类的影片已经表现了革命者的崇高信仰,导演想尝试突破信仰的正面性和崇高性,而将反面人物的精神状态也上升到了信仰的高度,从而使它先前建立的美学高度顿时轰毁。于此影片的主题在它升华之时即是沉沦之日。还有结尾的留言:“我的躯壳留在人间,灵魂已在风中随信仰而去……”影片这最后所谓的点睛之笔,不但没有“点睛”,反而帮了倒忙,它似乎告诉人们的是:躯壳将永远的存在,而灵魂则“不在场”了,因为“信仰已随风飘散”,将导演已经给观众建立的信仰大厦在无奈的沉重和失意的忧伤中彻底摧毁。
二、叙事的悖论:由悬疑丛生到悬疑大白
这是一部悬疑丛生的谍战片。故事讲述了1942年10月10日,在举办庆祝国民政府成立三十周年的盛大仪式上,一名汪伪政府的要员被枪杀,引起了日本方面的高度重视。日军特务课机关长武田怀疑这一系列暗杀行动是北平地区共产党领导人“老枪”策划的,希望抓住这次机会破获他的组织。调查的期限只有五天,被软禁的五个人全部关进了古堡裘庄,他们是汪伪剿匪司令部的收发员顾晓梦、译电组长李宁玉、总司令的副官白小年、军机处长金生火和剿匪大队长吴志国。为了保全自己,每个人都在悉心观察着一同进来的其余四人,都希望尽快把“老鬼”揪出来以便自己能够安全的离开这人间地狱。他们当中谁才是真正的“老鬼”呢?短兵相接明争暗斗之后,谁又能够最终逃出裘庄?五个人逐一被刑讯逼供,最先是白小年受到怀疑,被严刑拷打致死;然后是金生火被怀疑,他受不了这死亡游戏的折磨,在悲愤中开枪自杀;接下来,李宁玉又被怀疑,一次次地被叫到秘密审讯室,在受到武田的身心凌辱后,几乎疯狂。就在审讯李宁玉的同时,吴志国和顾晓梦两人互相攻讦,那么他们哪个就是要抓的“鬼”呢?所有的悬疑就在这抽丝剥茧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地揭开谜底。然而情报还没有送出去,如果送不出去的话,地下组织和它的上级“老枪”就将遭到毁灭性打击。
电影将这种惊心动魄的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命悬一线和扣人心弦的悬疑丛生,在短短的一百二十分钟内演绎得淋漓尽致。影片围绕“谁是老鬼”这个剧中的神秘人物,吸引观众在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中找出哪一个真实的影子般的人物。如剧中的李宁玉和顾晓梦,她们俩是上下级的工作关系,又有患难姐妹情深,两人在裘庄共处一室,生活上互相关照,就是这样朝夕相处的姐妹和同事,谁也不知道对方是敌是友。电影越到最后,越是让观众感到如果“老鬼”在她俩之间,那么她们必然会猜忌、隐瞒、嫁祸,践踏女性特有的善良的姐妹情和温柔的女人心,而这些关系恰恰构成了故事的张力。整出戏就是这样真假难辨、敌我不分,给观众以极大的探秘诱惑和解密快感。
从敌方来讲,坚信泄露情报的“鬼”就在内部,就在走进裘庄的这五个人中,所以日本特务机关长武田和伪军特务处长王田香要不择手段、甚至不惜动用酷刑也要找到这个“鬼”,真有“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走一个”的决心。而我方呢?则要千方百计地设置障碍,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也要把情报送出去,这里有吴志国借唱京剧来联络同志、忍受酷刑来转移敌人视线,有顾晓梦巧安发报机、在旗袍上缝进密码情报、甚至主动暴露自己以死传递信息。最后情报“意外”的成功传递,英雄吴志国九死一生,并手刃仇敌武田,又在咖啡馆里和魔窟裘庄归来的李宁玉述说事情的由来。这样尽管符合苦尽甘来的“大团圆”、好人好报的“菩萨心”和正义永在的“理想性”,但是,严重违背了棋逢对手和将遇良才的智力“游戏规则”,这也是中国谍战片久久不能突破传统的公案戏、传奇剧的原因所在。《风声》里敌方尽管绞尽脑汁,并动用酷刑摧残身体和征服信念,但是依然是机关算尽太聪明,最后的结局是忠心耿耿的伪军特务处长王田香被乱枪打死,尽职尽责的日军特务课机关长武田被刺死;而关进裘庄的五个人尽管处于弱小和被宰割的地位,但是其中三人依靠超人的意志和过人的胆识,甚至借助无名护士送情报这个“飞来”的情节,最后吴志国和李宁玉终于化险为夷。这里如果说《风声》是一出精彩而充满智慧的谍战戏,它就应该将这智力游戏玩到底,而不应该借助正义不败的政治性话题,即《风声》不必用浅显的政治标准代替深奥的智慧水准。换言之,影片既从观众心理学的角度表现了情节的扑朔迷离,这无疑是它的成功之处,又从历史叙事学的角度表现了结局的真相大白,不免陷入光明叙事的窠臼,双重的美学标准使得影片的“谍战”味道受到了无形的冲淡。因此,《风声》从讲悬疑故事的角度上看,这是一个有预谋和结局的“悬疑”,其惊险刺激的审美性感受和想象被表现出来的不惊险和不刺激的政治学叙事彻底消解了,由此再一次陷入了“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美学悖论怪圈。
三、表现的悖论:由视觉愉悦到视觉恐惧
毫无疑问,电影在表现上应该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风声》展示的室外和室内的两个场景都以凝重的色调为主,并配上低沉的重音,给人以恐怖和疑惧的心理压抑,如那突然响起的枪声,那神秘诡谲的行人,更有那多次出现的耸立在海边的危岩上、黑暗中闪着鬼火一样的幽灵的古堡,通往古堡迂回曲折的道路,这一切显得昏暗迷茫,玄机四伏,险象环生,而古堡内部尽管装饰豪华、陈设古典、格调高雅,那凝重的古铜色调、沉闷的压抑气氛,让人心惊肉跳,毛骨悚然。故事还没有开始,影片的艺术表现已经先声夺人,在强烈的视觉快感中给观众造成近乎令人窒息的视觉恐惧,不免让人担心导演在场景、构图和画面的视觉表现上会不会玩过了头。
其实玩过了头的还不止这些。《风声》一个明显的卖点就是对古今中外各种酷刑的展览。“有的谍战片更是大肆渲染酷刑,令观众难以承受其残忍精神折磨,这显然与主流价值观的立意相去甚远。”[3]影片里那阴森森的刑讯室,首先映入观众眼帘的是审讯台,不同的柜子里搁置了药瓶和刀具,房间正中央的床上铺着白色的床单,仿佛刚刚停放过尸体。而里屋的钉子椅和人字凳,则是最让人心惊胆战的“大家伙”了。为了营造恐怖的气氛,编导还在刑房里摆放了骷髅。武田和王田香为了找出真正的“老鬼”,分别对吴志国、李宁玉、顾晓梦、白小年上大刑。最先是白小年座上了“钉子椅”,他在凄厉而绝望的惨叫声中奄奄一息。吴志国则领教了更多的刑具,被打得遍体鳞伤的他先后受到了“电刑”、“针刑”的折磨。如果说在对男性的酷刑中已经让人神经几乎崩溃,而在接下来对女性李宁玉和顾晓梦的摧残更是让人惨不忍睹。在由周迅和李冰冰扮演的女性角色的刑讯中,其场面更涉及到对女性身体甚至性器官的残害,在李冰冰的裸体面前打开的冰冷刑具器械和周迅赤裸的下身那根血糊糊的粗绳子,这让影院里的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感到非常不舒服。
作为视听综合艺术的电影在画面表现上是非常而必须注重视觉效果的,从第五代电影开始,中国电影的画面越来越具有视觉冲击力了,如张艺谋对色彩和构图追求酣畅淋漓的表现力,《红高粱》的红色所蕴含的旺盛的生命活力,《英雄》的特技所传达的视觉奇观。正如著名学者王一川所说的:“影片的外部物质形象应既是物质形象本身,同时又能包含比物质形象远为丰富、含混和深长的深层意味。”[4]即包括电影在内的所有艺术的形象表现,都具有符号的形象本身的能指功能和形象意义的所指功能。作为能指的色彩、光影、构图要有形式美的要素,作为所指的隐喻、联想、象征要有意蕴美的价值,简言之,电影的画面表现不但要给人以快感,而且要给人以美感。当我们用这个影视美学的起码标准衡量《风声》时,失望之情油然而生。不是说影片没有给人愉悦,大牌明星的起用,尤其是当红女明星李冰冰和周迅的靓丽和高雅,首先就给观众以视觉快感;也不是说影片没有给人以美感,那造型独特的古堡、风和日丽的海滨、装饰典雅的房间,还有古朴的家具、华贵的物品和油画般的色彩,不无具有美的视觉效果,而当这一切同一场杀人游戏连在一起的时候,观众先前的视觉美感荡然无存,甚至觉得这些华美显得那样的可恶。尤其令人不快的是,对酷刑场景浓墨重彩的反复渲染和夸张呈现,如白小年那皮开肉绽、表情痛苦的死尸,吴志国受电刑和针刑时用特写镜头强化血肉模糊的局部肌肉和大汗淋漓的面部表情。更令人不忍卒看的是李宁玉和顾晓梦的受刑场面,这里导演借助女性的身体大做文章,不仅要展示她们洁白而柔美的肌肤,更要展现对她们的性虐待,由此而令观众在视觉上产生的难言的羞辱和无比的恐惧。因此,从视觉表现的方面看,《风声》在形式表现美学上的大胆突破创新追求,不但没有产生意外的效果和美好的感受,反而将编导的设想引向了相反,美学建构的同时亦是美学解构的结局。
由此可见,针对上文分析的主题、叙事和表现的三个美学“悖论”,电影《风声》给我们提出了拍摄和认识“谍战片”的三个美学维度,即必须认真思考的三个问题:信仰的终极主题应该昭示什么,悬疑的深层叙事应该展示什么,视觉的艺术表现又应该呈示什么。
首先,信仰的终极主题应该是“爱”的昭示。
纵观我国的这类影片,《国庆十点钟》、《虎穴追踪》、《羊城暗哨》、《林海雪原》、《冰山上的来客》、《秘密图纸》、《黑三角》、《雾都茫茫》、《保密局的枪声》等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它们多半局限于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范畴,只是将主人公大智大勇的计谋和舍生忘死的精神,仅仅表现为对工作的投入和对事业的执着,没有升华为对信念的忠诚和对信仰的追求。实际上,深入虎穴并非是他们人生的别无选择,但是他们一旦选定就意味着:风餐露宿、隐姓埋名、生离死别和遭人误会、割断亲情、随时死亡,这些将如影随形地充斥在他们的所有时空。那么支撑他们的精神动力就应该是为理想而献身的生命信仰,对此,《风声》的确超越了以往的同类电影,但是信仰过后是什么呢?或曰托起信仰的终极主题应该是什么呢?——爱!遗憾是《风声》没有能上升到这样的人性高度,也没有从生命的维度来呼唤、表达和追求“爱”,看完电影给人更多的是“恨”。那么这种“爱”是什么呢?美的生命、尤其是女性生命被无情摧残后的悲悯之爱,善的道义、尤其是良知道义被粗暴践踏后的悲伤之爱,相比之下,影片却津津乐道于无耻之尤的摧残生命和尔虞我诈的践踏道义,仿佛革命者崇高的信仰是来之于对敌人的恨;然而从美学的角度看,信仰的真正来源应该是建立在悲悯之爱和悲伤之爱的基础上。如此,著名美学家潘知常说到:“‘信仰’与‘爱’,就是我们真正值得为之生、为之死、为之难受的所在,生命之树因此而生根、开花、结果。”[5]
其次,悬疑的深层叙事应该是“奇”的展示。
毫无疑问,谍战片表现的领域是很宽广的:政治意义上的敌我关系、道德意义上的好坏关系、法律意义上的善恶关系,甚至情感意义上的恩仇关系,但是它的美学追求不仅是评判其中的是是非非和恩恩怨怨,它应该是达到超越历史和事实本身的人类生命高度:生理承受能力的极限和心理应变能力的极限,尤其是后者;就这个意义而言,谍战片在根本价值上应该体现人类智慧的高度、心灵的深度、知识的密度和想象的宽度,乃至生命的厚度一类的深层叙事。如果用这个标准看,《风声》最多达到了人物生理承受能力的极限,或者说在这个方面挑战了观众的心理承受能力。一部优秀的谍战片应该是一次紧张而精彩的“智力较量”游戏,既表现出剧中人物过人的胆识和机敏,也考验着观众超人的思维和理解。被称为好莱坞“永远的惊悚大师”的希区柯克,他所谓的悬疑必须是电影艺术的“假定性”为前提的,透过剧中角色陷入危机的情节来发展,但是观众却无法得知这些角色与危险是谁造成、或是会再造成什么样的危险可能性,即永远是疑云密布,尽管剧中人已经或即将陷入困境,但是他们却浑然不知,甚至观众也不知道灾难何时发生。《风声》虽然提供了一个极度封闭的空间和有限的时间,然而并没有让进入裘庄的五个人陷入抓“鬼”的智力博弈、精力较量和体力比赛,而是借助巧合和偶然推动情节,让白小年和金生火过早退场了,而吴志国受重刑而“退隐”,而剩下的本来非常有“戏”的两个女性却一个超然物外,一个不幸死去,只得硬性派上一个“护士”传送情报。因此未能体现故事的奇特、奇妙和奇绝。
最后,视觉的艺术表现应该是“美”的呈示。
正是由于《风声》缺少“爱”的信仰的终极主题和“奇”的悬疑的深层叙事,那么,在视觉表现上必然走向猎奇和刺激,以此电影的长处来掩盖这部电影主题的孱弱和叙事的仓促。毋庸置疑,艺术的使命是表现美和讴歌美,那么,又怎样看待影视艺术中的“丑”呢?它们不外是鲜血淋漓的场面、惨不忍睹的细节和少儿不宜的镜头等,难怪当年张艺谋的《红高粱》中剥人皮和野合至今还遭人诟病。而谍战片要编织惊心动魄和险象环生的情节、展示惊险刺激和不忍卒看的场景,甚至刻画性虐待和性侮辱的细节,这些都是在所难免的。但这一切的道德底线是不追求低级的噱头、不夸张生理的本能和不炒作猎奇的卖点,其美学境界是点石成金的化丑为美。这不排除在真实的史实中赵一曼和江竹筠就遭受敌人的性虐待,但是电影《烈火中永生》当徐鹏飞要扒掉江姐的衣服来羞辱她时,导演让她用“你们有母亲吗,你们有姐妹吗”的义正词严从而捍卫了革命者、也是女性的尊严、更是人类的尊严。对此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保罗·里克尔说道:“人类正是利用害怕这一必不可少的手段,才朝着一种不同的有点超越伦理秩序前进,在那里害怕才有可能完全与爱相融合。”[6]的确,艺术是不能回避死亡和鲜血的,反而要竭力再现反生命和反人类的“丑态”,相应的谍战片也应该表现惨不忍睹的场景,判别是否是化丑为美还是以丑为美的关键在于,一是编导的立意,他不能人为地强化丑陋和病态,以此来迎合阴暗的心理;二是编导的表现,他不能夸张地炫耀畸形和离奇,只能用烘云托月、旁敲侧击和蜻蜓点水的方式来表现;最关键是编导要充满着对人类和艺术的爱。
《风声》以它的创新给我们留下了诸多的启发,最有价值的思考意义就是谍战片在展示勾心斗角和尔虞我诈的阴险心理,在展现九死一生和你死我活的残酷争斗,在展露鲜血淋漓和性别虐待的可怕场景等方面,如何保持人性的高贵和守住美学的底线,因为“审美能力包括美感是一个民族文明的基础。有没有美感,有没有审美的能力,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文明是不是健康、是不是有人性的标志。”[7]而体现人性美的背后是人性的大爱。
那就让爱与美的阳光照彻这片幽暗而神秘的世界吧!
标签:顾晓梦论文; 谍战片论文; 电影论文; 风声论文; 时间悖论论文; 视觉文化论文; 李宁玉论文; 吴志国论文; 影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