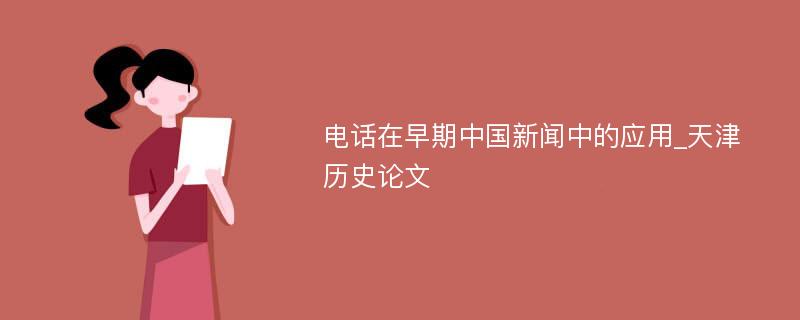
电话在早期中国新闻事业中的应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新闻论文,事业论文,电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传播科技是传播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传播科技的进步不仅决定了传播媒介的更新,促进了传播方式的变革,而且导致了传播观念的进化和高能记者的养成。传播科技每一次突破性的进展,都会大大提高媒介承载、传递信息的能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才提出了著名的“媒介即讯息”的观点。也就是说从长远的角度看,真正有意义的讯息并不是各个时代的媒介所提示给人们的内容,而是媒介本身。换句话说,人类只有在拥有了某种媒介之后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媒介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影响了我们理解和思考的习惯”。因此,对于社会来说,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媒体所传播的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
1876年10月9日,贝尔和助手华生成功地改进了电话,能够很好地实现双向对话。电话真正作为交流工具的功能得以实现。不过电话最初发明时,却被当成一种成人的玩具不被接受和重视。贝尔电话业的合伙人加尔迪纳·格林·哈伯德(Gardner Greene Hubbard)试图以10万美元的价格将电话专利所有权出售给西部联盟电话公司,遭到后者拒绝,西联公司总裁奥顿给出的理由是这个电玩没什么用。英国邮政部同样拒绝购买贝尔在英国的专利权[1]。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此前电报的出现已经深刻影响了人们的传播方式和传播观念,而且这种影响其时仍方兴未艾。就连贝尔本人在电话的第一次专利申请书上也只是写道“电报上的一项改进”,显然他本人也没有特别注意到电话的“交谈”功能。不过1877年7月他在一份计划书里明确地指出“事实上,人得以透过电话来陈述意见,而且基于这个理由,它可以应用到几乎每种从事说话的用途上”[2]。为了向人们展示电话的功用和优势,贝尔做了大量工作。他给自己的电话做了一份广告,称“电话不需要有经验的操作人员,这是一种能够通过说话直接进行的信息交往,不需要第三者干预。信息交往(比通过电报)更加迅速,电报每分钟为15-20个字,而电话则达100-200个字。”[3]“交谈”或“通话”电话的概念逐渐被人们领悟,关于电话的用途的概念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到1877年6月30日,电话进入实用阶段还不到一年,美国已经有230部电话投入使用,7月,上升到700部,到8月底达到1300部,它们主要替代了用于两地间通讯的电报设施[4]。电话正越来越被普及,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它消解了私人线路中熟练报务员的重要性。1880年伦敦《泰晤士报》设立了一条连接到国会的电话线,目的是为了报道深夜议题讨论,并把它纳入隔天日报的版面中[5]。但总体看来,新闻记者对这个装置的使用反应迟缓。数年内,电话对新闻采访并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电报在新闻业中的地位已经得到确立和稳固。不过,到了19世纪80年代,大城市的记者开始以两个梯队进行工作。“现场采访记者”(leg man)收集信息并把它通过电话传送给报馆的“改写加工编辑”(rewrite man)。到1900年代电话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新闻采访报道中,美国的新闻采访和传递活动变得相当依赖电话,甚至超过了电报。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最经典的电话报道新闻的案例,就是《纽约时报》关于泰坦尼克号沉船的报道。《纽约时报》总编辑范安达在码头附近旅馆包了一层楼,并架设了4条直通《纽约时报》本市新闻编辑室的电话线,以最快速度传回现场采访到的消息,在这一轰动世界的突发新闻事件的新闻报道大战中战胜了众多竞争者。
一、电话传入中国
电话于正式发明的第二年即1877年传入中国。是年1月,上海轮船招商局托西人造电话机一部,其电线由金利源栈房通至总局公务厅,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使用电话。此后,电话逐步在上海推广。1882年2月21日,大北电报公司在上海外滩7号正式开设了第一个电话局,设置了一部人工交换机。并在租界内的马路上架设了话线杆。25家客户成为上海首批电话用户。这个电话局是上海,也是中国最早的市内电话局。1900年,丹麦人濮尔生趁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机,在天津私设电话所,称为“电铃公司”。1901年,该公司将电话线从天津伸展到北京,在北京城内私设电话,发展市内用户不到百户,都是使馆、衙署等,并开通了北京和天津之间的长途电话。和电报、自行车、轮船、火车、电影等早期大多数的西洋科技传入中国时一样,电话最初也被尚不了解其工作原理的中国人当作“西洋景”,成为人们围观和谈论的对象,人们对其充满了好奇和新鲜感。15岁的溥仪第一次打电话,不是用来沟通信息,而是捉弄京剧名家杨小楼[6]。直到这种新鲜感逐渐淡化,让位于使用习惯,电话在人际沟通和信息交流中的直接和高效才渐渐被人们所认知和接受。电话在欧美的大规模普及迟至1900年以后,在中国这一进程则要在1920年以后。到20世纪20年代,国内几个重要都市的电话拥有量均陆续破万。上海到1922年电话用户达到2000户,1932年底仅租界内的电话用户即达到3万余户[7]。北京1904年的电话用户仅有100余家,到1911年已达3000余户,1920年后已突破一万余户,最高时15000余户[8]。1920年,南京的市内电话由磁石式改为共电式,城区增扩2000门,下关分局增扩500门,1928年南京成为国民政府首都,政治经济地位提升,电话用户骤增,国民政府交通部又增设新机5000部[9]。天津电话用户1918年已达3000余户,1926年达9000余户[10]。厦门、青岛、长沙、汉口等城市的电话事业、电话拥有量和长途电话事业都有了长足进展。上述重要都市之间,陆续通话。电话数量的增加和电话网的初步形成,开始显现了其在信息交流中的巨大潜力。相比同时期的书信、电报,电话交流不需要任何其他中间环节,只要没有语言障碍便可以采取直接通话,是一种非常便捷的信息传播方式。电话不仅减少了“译码”、“破译”等中间环节,而且变单向传播为双向交流,单位时间交流的信息量呈几何级数地增加。
二、电话在清末民初新闻事业中的初步应用
最先意识到电话的重要价值并率先使用的,大多数是商户和官署。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的一份1909年的《北京电话簿》向我们展示了早期电话用户的分配情况[1]。名单中九成以上的用户是银行、饭馆、药店等商户和京中各署衙或官宦邸宅。但这份电话簿同时向我们透露了另一条信息:京中若干大报亦开始安设电话。笔者统计,出现在名单中的报馆共有11家。笔者又翻阅了津沪2份代表性大报《大公报》和《申报》,发现天津《大公报》自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七日(1906年9月5日)开始在报头下方出现“电话四百五十号,得律风三百二十二”字样;上海《申报》自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初四日(1905年4月8日)在报头下出现“得律风一千五百九十六号”字样。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信息,亦可能意味着电话或被用于采访和传递消息。碍于时间和精力所限,笔者未能找寻到这一时间《申报》、《大公报》使用电话采访或传递消息的蛛丝马迹。不过另一份间接材料却能印证,早在清末,许多报馆已经将电话作为传递消息的重要手段了。宣统二年六月十六日(1910年),直隶总督陈夔龙在给民政部的一份咨文中透露,此前天津出版的《中国报》与“邸钞”、“谕旨”等并列,专门列有“电话”一门[12]。而宣统三年三月十七日(1911年),陈夔龙为天津创设《津话日报》等事致民政部的另一份咨文则显示定于该月二十八日出版的《津话日报》体例共分八门,其中专列“北京要闻及各省电话”一门[13]。这可说是电话用于传递新闻消息的间接例证。《申报》1912年4月2日一则《杭州兵变之谣传》的消息,是笔者所能找到的电话用于探听、采访消息的最早直接记录。该消息称:
昨日(四月一号)本埠忽起谣言,有杭垣数日来军界颇不安靖。下午五句钟,因索饷无著,攻毁某公署之语。但至昨夜十二句钟,本馆并未接访友专电,经由电话询问沪军都督府,亦云并无消息。询之电报局暨旅沪浙江某团体,亦如之。不知谣言之何自来也。
如果将外人在华所办报纸亦纳入研究范围,则这一记录可能还要提前。1911年6月15日,琉球群岛海域发生地震,上海局地有强烈震感。上海英商《北华捷报》馆于地震一分钟后即向电话总局打电话询问有关地震消息[14]。
入民国后,电话在新闻事业中的应用已经比较普遍。在电话普及率较高的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新闻之由长途电话传递者,或不在电报数量之下”[15]。1919年出版的国内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徐宝璜的《新闻学》即列有“电话采集之法”一节,充分肯定了电话在传递消息方面的重要作用。徐宝璜认为:
电话现已成采集新闻之利器,不独访员常可借电话通询以打听消息,或证明各种略示(谣言亦包括在内)之确否,且可借电话以报告重要新闻之略示于编辑,以便其能立时派出其他访员,分途探听。且当访员无暇回社报告新闻时,彼可借电话口授其于脑中所已编就之新闻于社中之阅稿人,由其笔录交于编辑。又编辑亦可用电话通知访员,令其特别探访之事。[16]
徐宝璜将电话视为记者探听消息和确认消息真伪的利器,亦作为外勤记者在特殊情形下向馆内传回消息和报馆编辑指挥外勤记者进行现场采访的工具。“自有电话以来新闻界对于本埠之采访消息,莫不利用电话以传递。编辑或记者只须在其办公室中,各方消息均可传来。既无奔波之劳,复得敏捷之便,时间经济,准确详尽,裨益于新闻事业良匪浅鲜。溯自长途电话创办后,新闻界之传递新闻,咸皆采用长途电话。”[17]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商业大报,都不惜巨资,用长途电话传递重要消息,在时效上以争长短。如上海《新闻报》南京办事处,每晚用长途电话将南京的重要新闻传至上海报馆内。而该报老板汪汉奇怕电话接听有遗漏错误,每晚守候在电话前,亲自接听[18]。电话在新闻事业中的应用,对新闻采访、消息专递和报业广告、发行等经营活动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1)增加了消息传递速度和单位时间的信息传播数量。民初政局动荡、扑朔迷离,消息时常一夕数变,而那时报馆通常在凌晨1时之前即已截稿,一旦排版很难撤稿或换稿,这让报馆十分被动。有的报馆即用电话传递最新的时局动态,来化解这种消息滞后或由此导致消息失真的风险。如天津《益世报》自1920年4月1日起在报纸上辟出“北京电话”一栏,不定期专门登载当天午夜前后北京发生的最新重要信息。5月8日该报第三版一则凌晨1时“北京电话”消息称“靳云鹏母前因赴津做寿,今晚(按:7日)十二钟时忽又携带家属到京,未知何故”。从这则简短的消息可以看出,此前各报必定已经纷纷报道国务总理靳云鹏赴津的消息,而靳忽又回京,可能让许多报馆措手不及。因此《益世报》的这则赶在截稿前发出的电话消息,可以说在时效性上抢得了先机。抗战胜利后,新闻界锐意进取,竞争十分激烈。沪宁、平津等新闻事业和电话事业较发达地区的大报,遇有重大新闻,多舍弃电报,而采用电话传递消息,因为同样时间内电话比电报可传递更多消息。2012年12月,笔者曾就此专门采访天津93岁的老报人张道梁。他称当时平津之间长途通话较方便,报社多用电话报告消息,只有远途才用电报。笔者翻阅1945年底到1946年的天津《益世报》、天津《大公报》,发现北平、保定等天津周边城市的消息几乎全部是由电话传递,概冠以“本报北平电话”、“本报保定电话”等消息头。而上海《申报》1946年10月8日第6版一则题为《新闻是哪里来的?电话铃一响记者们紧张》的特写则称“只要有一天全上海的电话铃声不响,明天你也许就简直会看不到一张报纸。从电报里来的消息,实在少得可怜……各报馆电话设备和事实的需要是差的太远了,但是电话始终还是一切新闻最主要的来源……长途电话当然是更见得重要。有时,刚一个电话报告记录完毕,马上就全报馆动员起来,出版号外。”
一个熟练的话务员,一小时可传递两千到三千字[19],速度是电报的数倍。1946年底南京“制宪国民大会”期间,《申报》南京办事处曾用电话创造每夜传递七八千字的记录20]。1947年3月19日国民党军队“攻克”延安,南京国防部下午四点半才得到西安传来的消息,而《申报》南京办事处即于当天下午6点前将消息通过长途电话传到上海总馆,并通过上海各电台播放出来[21]。许多南京人也是听了上海广播才知道这个消息。这种传播速度倘若放在今天也算十分惊人了。
电话相比书信、电报除了方便、快捷以外,亦有另一个优势:可以有效规避邮电检查。民初因为政局动荡,政府或军阀在特殊时期多实施邮电检查,任意扣押或删减新闻消息。而电话的检查当时在技术上仍有难度,尚难以实施。1926年6月,北洋政府军警会议曾拟颁定电话窃听办法,予以实施,但无后闻。因此报馆在遇到邮电不畅的时候,也多采用电话报告消息,以作为一种补偿手段。如1926年底北伐战争时期,北洋政府对邮电实施了严密的检查手续。刚复刊不久的新记《大公报》即时常采用电话报告京中动态。复刊次日(9月2日),该报第三版出现一条电话消息,报道了北京国立九校教职员为秋季开学问题向政府交涉的办法8条[22]。
(2)电话采访节省了记者采访的时间和经济成本。电话除了能方便消息的传递,亦成为记者采访的利器。相比面对面的实地采访,电话采访可以突破时空限制,节约差旅等采访成本,这在异地采访中尤其体现出优势。名记者邵飘萍则是电话采访的行家里手,他时常用电话旁敲侧击,从政客军阀口中套出重要消息。邵飘萍自称其“每日所得之新闻,殆大半由于电话。以北京各机关距离之远,且官僚每为无事之忙,不知其终日所干何事,访问实为不易。故所赖于电话者甚大。”因此,他认为电话访问“若能用得其宜,则电话自为最经济便捷之一种重要方法”。后来他将自己的电话采访心得和经验陈之于《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中,称“遇不肯接电话之官僚,如有特别必要时,亦可用非常之手段,而此非常手段中半面又有极正当之理由。非常手段者,即谓私宅中人请彼说话,或言某机关请彼说话是也……俟其接谈,则告以‘我乃某某’,并告以‘恐与新闻记者接坐中有人闻之不便,故不得已出此’……”[23]
当然,我们亦不能忽视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受技术等客观条件所限,那时的电话线路常出现拥堵,信号也不清晰。上海《新闻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由老板汪汉奇与南京访员约定,先将新闻翻译为电报字码,然后以电话用英文报道字码,馆中收到字码后再还原为相应汉字24]。申报南京办事处的电讯员遇到紧急情况时,亦采用同样方式向上海总馆的电讯科报告新闻[25]。《申报》、《新闻报》为了垄断沪宁长途新闻电话使用权,几乎将每晚的通话时间全部占据。1927年成舍我在南京创办《民生报》时,请上海友人吴中一代为从上海向南京打长途电话,为了能等到一个空隙,吴中一往往通宵睡在电话局的长凳上[26]。除了线路繁忙、信号不好等问题,电话的安装和使用费用也十分高昂,不是一般报社所能承受的。到了三四十年代,电话才在一些规模和实力较大的报馆中渐次普及开来,但数量也有限。抗战时期在重庆《大公报》兼职的陈纪滢回忆四十年代的情形时仍说“那时偌大的一个《大公报》馆,全馆仅有两具电话,一具在编辑部,一具在经理部”,至于通话质量,“说起话来非到了喊破喉咙的程度,对方听不见;办一桩简单事情都相当吃力……真是‘说话声震屋瓦,对白如同吵架’。”[27]
三、民国新闻界争取新闻通话权益的努力
随着电话在新闻事业中的使用越来越多,许多报馆感到电话费用成为重要的支出成本,纷纷请求政府按照邮政和电报的减费惯例,对报馆使用新闻电话进行减费优待,并要求设立电话专线,专供新闻界使用。1928年9月,以上海日报公会为代表的新闻界向南京政府交通部请愿,要求划一邮资、优待新闻电讯,关于电话要求“长途电话照普通之话费收取两成,并在政治中心之首都与舆论之中心上海间,增设专线”,得到全国新闻界的响应。后新闻界又迭次请愿,迫使南京政府交通部于当年12月制定了《交通部优待新闻事业使用邮电办法》,着手设立沪宁新闻电话专线,并允诺沪宁电话专线建成后,商定新闻界使用电话减费具体办法[28]。但切实的减费办法迟迟没有出台。1932年7月底,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亦曾召集各县党报编辑主任举行联席会议,决议“请省党部分咨文交通部建设厅,援照新闻电报减价比例,减少新闻通话费”29]。1933年交通部又因应新闻界迫切需要,沿沪宁公路另设沪宁直达长途电话线4对,可用作6对。线路完工后,沪宁各报馆可随时通话,无须提前拨打费用更为高昂的加急电话[30]。对于新闻电话减费一项,则因电话铺设成本过巨,成本回收困难,交通当局迟迟没有制定切实的减费办法。
不过一些省份,在省办电话线内给予新闻界切实优待,并制定了详实的新闻界使用电话的优待办法。河南省建设厅应该省新闻记者联合会请求,责令电话局于1933年秋制定了《河南省新闻电信优待条例》[31]。1933年浙江省电话局颁布了《浙江省电话局长途电话新闻通话办法》,规定凡向中宣部或内政部登记之报馆、通讯社及其记者,在向该局请领新闻通话凭证后,即可享受优待。具体办法为:每日下午十时至次日上午六时,为普通新闻电话通话时间,可照正常价目的半价收费;在此时间段以外,欲提前接通者为加急新闻通话,与普通电话相同;手续费及专力费则一律照旧[32]。江苏省也于1934年12月14日颁布了《江苏省长途电话新闻通话简章》,规定报馆或通讯社向该省建设厅长途电话省交换所领取通话凭证后,即可享受优待。凡江苏省内长途电话通话区域内均可享受,具体办法是:每日二十一时至次日上午八时,按照普通顺序接线,照价目表半价收费,单程递送照价目表收取半数,往复递送照价目表收取;上述规定时段以外提前接通者,为加急新闻电话,单程递送照价目表收取四分之三,往返递送照价目表收取一又二分之一;手续费亦只收取价目表规定价格的八分之一[33]。此外,苏浙两省还共同制定了《苏浙两省互通新闻通话办法》,规定每日二十二时至次日六时为新闻通话时间,照价目表半价收费。被叫用户未装有电话者,需要专差传叫,其应收取的专力费按被叫局本省规定收取;手续费在浙江省内收取五分之一,在江苏省境内收取八分之一[34]。
抗战胜利后,新闻界掀起了新一轮争取新闻通话减费的运动,终于迫使交通部在全国范围内制定了具体的减费办法。南京政府交通部于1946年12月16日起开放沪宁间新闻电话,每日下午九时至次日上午七时,按正常价目七折收费[35]。这一规定激发了全国新闻界的跟进,全国各报馆、通讯社代表亦赴交通部请愿,要求与沪宁享受同等待遇。1947年1月交通部同意新闻界“普通新闻电话提前接通”、“沪宁电话七折办法,扩充至全国,并于白天规定两小时为通讯社、晚报使用,同样给折扣优待”的要求。
电话在新闻界的使用,不但节省了报馆的采访、经营成本,而且也使得部分率先采用者,在消息灵敏性和时效性上胜过其他未采用电话者。现仍健在的天津老报人张道梁1946年在天津创办《新生晚报》,为了解决北京政闻消息的采访问题,决定与成舍我《世界晚报》每天中午以长途电话交换上午各自采访的新闻。《新生晚报》受益颇大,节省了一大笔采访费用,而且北京的消息也比天津其他各晚报灵通得多。他认为这是天津其他各晚报都比不上《新生晚报》的重要原因之一[36]。在这里,电话及其开创的可能性,已经成为能关联报馆生存和发达与否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