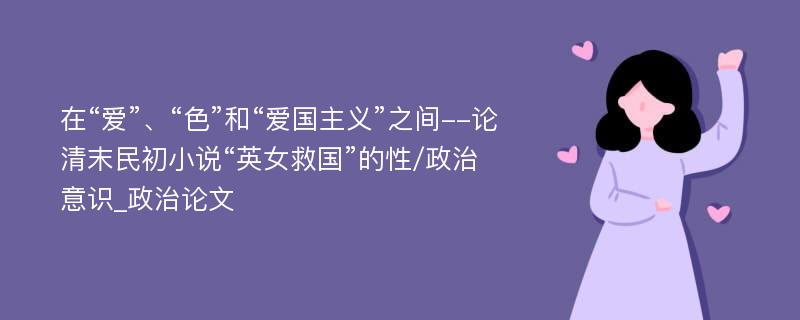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爱国论文,清末论文,意识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7)01-0120-04
“性政治”是凯特·米利特一本著作的书名和主题。凯特把性和政治联系起来是为了强调性并非是隐秘的、个人化的问题,而是与整个社会的各个政治环节紧密相连的①。同样,福柯也坚持“性”和“性经验”都是文化、历史意义上的概念,而不仅仅是自然或生物学上的概念:“我们大家都生活在‘性’社会里,或者说是生活在‘性’之中。……权力突出它,引发它,……为了不让它逃避,……必须控制它,它是一个具有器官价值的用品。”② 的确,性的概念是在性经验机制的不同战略中建立起来的,它是历史政治处境中的性,同时又是与身体分不开的性。在“五四”以前,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一、自由结婚与抑“情”救国
清末民初,西潮东渐带来的一片春光,已对传统中国“父母——媒妁”的权威有了某种实质性的动摇,“自由结婚”在此期的婚姻论中成为最具“新”质的呼声,集中体现了先进人士的性爱理想。
“自由结婚”这一主“情”派的关键词在清末民初被使用的频率已很高。时论自不待说,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女子世界》与《复报》的“唱歌集”、“新唱歌集”都先后刊出过《自由结婚》与《自由结婚纪念歌》,这种方式颇像时下的流行歌曲,传播渠道畅通,辐射面大,往往能收到风靡全国、深入人心的影响效应。而革命派杂志《觉民》对自由婚姻的慷慨高歌——“我今欲发大愿,出大力,振大铎,奋大笔,以独立分居为根据地,以自由结婚为归着点,扫荡社会上种种风云,打破家庭间重重魔障,使全国婚界放一层异彩,为同胞男女辟一片新土……我务将此极名誉、极完全、极灿烂、极庄严之一个至高无上、花团锦簇之婚姻自由权,攫而献之于我同胞四万万自由结婚之主人翁!”③——在今天听来仍具震人心魄的鼓动力量。
看来,单就情爱、婚姻而言,赋予其相应的现代性内容和人性价值,在其时的进步人士中已被首肯。然而,不能忽视的是,情爱、婚姻是不可能剥离于社会政治生活之外而存在的。事实上,清末民初探讨这些问题,往往离不开种族,而其落脚点实为国家思想:“夫人情意不洽则气脉不融,气脉不融则种裔不良,种裔不良则国脉之盛衰系之矣。”④
正是基于上述语境,绝大多数的“英雌救国”小说都赞颂或倡导自由结婚。然而,这种倡导一旦遭遇民族复兴、国家存亡大业,就马上掉转追求方向,一切以后者为英雌的行为指南,于是,抑“情”救国成为英雌人物的标准情感表现和行动追求模式之一。
《自由结婚》在这方面具有寓言和导向意义。该书书名前题“政治小说”,《弁言》称作者写此书欲“使天下后世,知亡国之民,犹有救世之志”。既然如此,为什么小说取名为《自由结婚》呢?其实这是别有寄寓的。少年主人公黄祸与关关因有相同的种族革命情怀而相爱,进而有“缔姻之事”的约定。后关关加入光复党,成为中坚,天天训练军队,准备发动大规模的革命,发誓“一生不愿嫁人,只愿嫁与爱国”(《自由结婚》中“中国”的化名,笔者注)。关关的少女情窦因黄祸的爱国热情而盛开,并随着两人的共同奋斗与日俱增,但个体的男欢女爱究竟不敌民族革命之爱的风起云涌,于是抑“私情”扬“爱国”成为了他们的更高追求。这样,两人起于私性化爱情的“自由结婚”就终结于与中国的“自由结婚”。
如果说,黄祸、关关的男女爱情具有的世俗性,在一定程度上给他们与中国“自由结婚”的宏愿打了一定的折扣的话,那么,小说中对女光复党及其主要人物一飞公主的描写则完全是在彰显革命女性如何与中国“自由结婚”的奇观了。光复党的宗旨是光复“爱国”大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其领袖一飞公主立誓“把此身嫁与我最爱之大爱国祖国,尽心竭力,黾勉为之”(第十五回);并沿此设置了一套奇异而充满悖论的“自由结婚”宣传鼓动策略:号召新来的同志都要在意识上行动上把国家当作自己的丈夫,与其结婚,这样所有人都是“国妻”了;而时下国家被异族盗去,那么女性就理所当然地应“替国守节,替种守节”(第十四回)。在这种宣传中,女性对丈夫——异性的一腔情思被有效地压制并通过爱国的通道转化为复仇的火焰:她们把“亡国之痛当作杀夫之仇,大叫誓灭蛮狗”;“因此光复党中人,尽是女中铁汉,痛心疾首,一副寡妇面孔,日夜只要报仇。”(第十四回)至此,“自由结婚”的隐喻意义方才出现:两性间的自由结婚固然重要,但与国家自由、民族自由相比,前者又算得了什么呢。然前者的坚固的情感凝聚力、两性的相吸相合力却是民族国家的光复所特别看中和借用的,所以,透过“自由结婚”的哈哈镜,作者所要表达的却是“用那寻常儿女的情,做那英雄的事”(第十四回)的精神实质。而这恰是那时代英雄英雌儿女故事的精髓所在,在这一意义上说,《自由结婚》的寓言性是广泛而普遍的。
同样是民族革命的领袖人物,夏震欧(《瓜分惨祸预言记》主人公之一)与一飞公主在抑“情”救国上亦有相似的主张。夏震欧文武兼备,在中国遭“瓜分惨祸”时,她为国浴血奋战,争得了一方净土,成立了兴华邦独立国,获大统领殊荣。言及婚姻,她更是豪气冲天:“这中国就是我夫,如今中国亡了,便是我夫死了。这兴华邦是中国的分子,岂不是我夫的儿子么?我若嫁了人,不免分心,有误抚育保养这孤儿的正事,以故不敢嫁人。”(第十回)后来她果真践了自己的诺言,终身不嫁,专心谋国。
在“救国图存”的伟业中,“自由婚姻”还刚开始就已近名存实亡。如若再加上兴女权的主题,自由性爱的命运又当如何呢?《女娲石》中的花血党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花血党的根据地是秦夫人领导的天香院,这是一个专门暗杀独夫民贼的“英雌”聚居地,也是一个有着浓厚的宗教性质的乌托邦组织。凡入天香院的女子,必须承诺“灭四贼”的宗旨,“灭四贼”是指:灭内贼,即“绝夫妇之爱,割儿女之情”;灭外贼,即忌媚外,重自尊独立;灭上贼,即与民贼独夫,不共戴天;灭下贼,即“务要绝情遏欲,不近浊物雄物”(第七回)。在这里,革命要求与个体情爱、国家利益与生命欲望水火不容:入党的英雌必须冷血无情,视男性、视性爱为天敌,否则她们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别尔嘉耶夫所说的“革命总是指向反抗专制的暴政,但在自己发展的一定时刻它总是建立独裁和暴政,取消一切自由”⑤ 的情景,在中国的民族革命、女权革命开始不久就已露出端倪了。
众所周知,在世界文明史上,欲望与理性的冲突始终存在。但在前现代社会,二者的对立还不能称之为悖论,因为欲望并没有获得合法性。在文艺复兴时期,个人主义的勃兴为欲望的合法性获得开辟了道路。伴随着现代性诉求在人的深层心理的展开,世俗欲望(当然也包括性欲望)逐渐被视为人的天然权利。上面所说的“结婚自由”就是这种观念在中国的反映。但是,个体欲望的被肯定往往是与对更大的群体如党派、群族、国族、国家等的理性认同齐头并进的,于是这种情态导致了现代性知识学内部的欲望与理性悖论的出现。解决的办法也许是同时注重这二者的合法性。但是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现代性进程因为受到具体历史进程——国家存亡的影响,个人主体性的原则不可能也没有得到具体的贯彻和落实,国家功利文学观挤压着个体欲望的自由表达。因此清末民初的小说中,欲望与理性悖论的调适艰难到几乎不存在的地步,难怪阿英会感叹:“两性私生活描写的小说,在此期不为社会所重,甚至出版商人,也不肯印行。”⑥ 既然如此,“自由结婚”的内蕴转向为抑“情”救国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英雄国女”与以“色”救国
在20世纪初,女子的色相或身体被普遍地赋予了政治意义和价值。由是,一类特殊的女性革命者——“英雄国女”出现在“女子救国”小说中。
前面我们已谈到了《女娲石》对于女子本身所要求的禁欲主义革命主张。然而,这只是一面,另一面却是:在民族国家需要的时候,动员女性以姿色献身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解放事业。“国女”与“革命”是《女娲石》的两个关键词,也是作者整个想象秩序的轴心。那么,何谓“国女”?何谓国女的“革命”?
海天独啸子认为社会改革首先涉及到的是妇女:“妇女一变,全国皆变矣。”那么,妇女应怎么变,变成什么样的人呢?海天独啸子提出了方案:“我国今日之国民,方为幼稚时代,则我国今日之国女,亦不得不为诞生之时代。”依他看来,谈“国民”在那时代似乎条件还不成熟,也太笼统,显示不出妇女在社会改革中的重要性,所以在国人的思想、行为演变成为“国民”之前,他设想出一种新型的妇女——“国女”,并强调那时代是呼唤“国女”诞生和养成的时代。对于“国女”的基本素质,海天独啸子有言:“欲求妇女之改革,则不得不输其武侠之思想,增其最新之智识。”武侠思想即尚武精神,最新智识即科学精神。此两点可谓“国女”区别于旧女性的主要标准,也即“国女”之诞生的关键。但仅此两点,“国女”与“国民”的根本区别又何在呢?区别是有的,但作者在理论上似乎“是亦难言”⑦。所以,这“难言”是通过小说这一想象文本表现出来的。小说正文中“国女”出现凡四次:一次指涉“不忌酒色,不惜身体,专要一般国女,喜舍肉身,在花天酒地演说文明因缘”(第九回)的春融党,三次特指主人公金瑶瑟。换言之,虽然《女娲石》描绘了各党各派、形形色色的女性革命者,但被称为“国女”的只有春融党的革命者和金瑶瑟而已。她们与别的女革命党人的根本不同在于:她们自觉地以“色相”救国。
在小说开篇,海天独啸子就发表了“女强于男”的议论,原因是:“男子有一分才干,止造得一分势力。女子有了一分才干,更加以姿色柔术,种种辅助物件,便可得十分势力。”(第一回)也就是说,女性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利用自己的性资源是女性的一大优势,为男性所不可企及。当然,这并非是《女娲石》作者的“独到”见解,当时一些激进的革命派或无政府主义者均持有这样的看法:“……天下之事,又成于女子者多,而成于男子者少。(越之谋吴,日之胜俄,皆暗收功于女子,此等阴谋,本不足贵,然看见女子每能成事。)以女子有坚韧之性,故能耐苦耐劳,恒久不懈也。夫就今世而言,女子思想未尽发达,事权未能掌握,而虚无党和女子助力,其收效已较易,使女子而增其知识,加以学问,将何功不可成耶!故吾尝谓天下事有千百男子为之而不足,一二女子为之而有余者。”⑧ 这段话饰以了委婉修辞,似对女性以“色”为手段的“阴谋”持一定的保留态度,但在称赞女性特质时仍难以掩盖利用女性性别来“成事”的本意。这种观念演化为具体的文学形象则有了“国女”的出现。
春融党是以“色”救国的革命组织。它的革命也就建立在特殊的方式上,它“设有百大妓院三千勾栏,勾引得一般痴狂学生,腐败官场,无不消魂摄魄,乐为之死”(《女娲石》第九回);党员全部是“不忌酒色,不惜身体”的“国女”(《女娲石》第九回)。另外,天山省的中央妇人爱国会曾以“会中绝色少女十人,专嫁与政府中有权势的做妾”(《女娲石》第四回),以此美人计来颠覆“政府”,夺取政权。小说中的这些女性革命者年轻貌美,秀色可餐,她们的全部价值和人生目标就是以美色去引诱男性,并以此来颠覆旧的政府国家。
被誉为“爱种族爱国家为民报仇的女豪杰”(《女娲石》第七回)金瑶瑟则是以“色”救国的“国女”典型,也是《女娲石》的主脑人物和情节结构人物。她以前在海城已做了女子改造会领袖,后又往日本、美洲留学;小小年纪,就占尽了那时代女性所能具有的所有光华:聪慧貌美、通时达情、才情俱佳、自身解放。然而她的人生终极目标是救国,为此,她选择了一条非常的途径:到京城妓院学习歌舞,企图以“姿色娟丽,谈笑风雅,歌喉舞袖”的方式,“在畜生道中,普渡一切亡国奴才”(《女娲石》第二回),把他们鼓舞起来。哪知那些亡国奴麻木痿痹,拉扯不动,失望之际,得日本公使夫人相助,进宫刺杀胡太后,两次未果,逃亡天涯,以“英雄国女”的身份享誉各革命党中。
比海天独啸子走得更远的是张肇桐。在《自由结婚》中,张肇桐塑造了一个更为离奇的“英雄国女”——“妓女大豪杰”(第十三回)如玉。如玉本是良家女,因修道入了清洁堂;后被维新党中人所运动,仿着野蛮宫女之例,自戕其身,成为“生殖无器,好合无从”的“不男不女的美人”(第十三回),于是托迹勾栏,去救那些无知少年。不同于金瑶瑟的失败,如玉有着神奇的感化拯救功能。甘师古乃革命组织自治学社的“公敌”,他庸陋恶劣,专拍马屁,反对进步,阻止革命;不料三日不见,他就摇身一变,成为一个革命者了。而这“速变推进器”就是如玉。如玉如孙悟空一般火眼金睛,一见便知那个是“用得着救”的坏人,顽固如甘师古者,“经他一夜的改造,觉得前后显然是两个人了”(第十三回)。男主人公黄祸听了如玉的故事暗暗称奇:“这真是牺牲一身以救同胞。我爱国也有这种人,不愧为将来爱国独立史的一大特色。”(第十三回)黄祸的议论固然有偏颇处,但它道出了中国男性对风尘女子的美好评价和想象却不假,事实上,这种看法是有深厚的文化渊源的。
中国的妓业发展到晚清,已经历了两千多年。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妓业对男性世界的冲击是巨大的。虽然对此问题有见仁见智之别,但从唐、宋以来,许多士人往往对妓女给予很高的评价却是公认的事实。明代傅山认为:“名妓失路,与名士落魄,赍志没齿无异也。”⑨ 把名士与名妓相提并论。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对名妓马湘兰、薛素素的豪侠勇武极尽赞美之能事,称她们为“翠袖朱家”、“红装季布”。有清一代,特别是晚清,士人崇“侠”风盛,于是“侠骨”与“柔情”共举,所谓“英雄侠骨美人心”。龚自珍将这种侠骨柔情化为一剑一萧的意象,所谓“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己亥杂诗》)。而此后的南社革命者,更是用“剑气箫心”的意象来抒发侠烈情怀。如方荣杲《题红薇感旧记》之“佳人自古说多情,况复箫心剑气横”,周实《哭洗醒诗》有“尘寰从此知音少,剑气箫心谁与抗”的期盼。在这些诗中,“剑气箫心”往往与风尘女子的知性侠勇相联结,显然,“儒侠”多情,引红粉为知己,不仅因为她是自己实现情感欲望的伙伴,还在于她与自己在感悟生命、追求理想方面有同一性。客观地说,清末民初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妓女的“政治身份”和“政治力量”还是有相当的认识的。所以他们笔下的“国女”大都以“色相”为表,而以先进的爱国思想为本,力求对世上龌龊卑劣的男子进行“劝谕改造”,如如玉对客人总是“从半夜到天明”地谈论爱国道理。这种人物设置一方面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士人对妓女某些优良品德极尽赞美的传统和想象;另一方面也是对当时社会现实情形所作的一种艺术表现。“吾闻日俄之役日本许多贵女舍身为妓以作侦探,但知报国不复计一己贞操,此等举动未知中国学士以为如何”。这段话道出了一个民族主义的女性事件,即女性以妓女的身份掩护自己为民族国家而斗争的事实。言说者虽然陈述了事实,但却非常敏感地隐藏了自己的态度。虽然如此,“中国学士”们的态度不还是从对金瑶瑟这些“国女”的塑造中流露出来了吗?
三、舍“情”事“色”与为国牺牲
与革命同志产生了爱情,然而为着爱国理想的召唤,抑“情”而奋斗于“救国”事业的女性是伟大的;没有两性间心心相印的情爱,然而为着爱国理想的召唤,以“色”“献身”于“救国”事业的女性是伟大的;既与革命同志产生了爱情,然而又坚毅地舍弃这两性间心心相印的情爱,为着民族国家的召唤,舍“情”事“色”于“救国”事业的女性更是伟大的。夏雅丽、葛娜属于这更伟大者。
夏雅丽,《孽海花》中光彩照人的革命者。从第九回开始,夏雅丽在《孽海花》中登场,其身份是俄国虚无党党员。她出身豪门,聪慧颖悟,靓丽逼人。至十五、十六、十七回,小说集中描写了夏雅丽的壮举:她从自己的同志加恋人克兰斯那里得知虚无党陷入经济困境,便悄然回国,嫁给了靠枪杀、出卖虚无党员而暴富起来的表哥加克奈夫。不久,她暗杀了加克奈夫,并将其巨额财产转交给她的同党,自己则打入皇室,企图刺杀皇帝,不果而被施以绞刑。
在小说中,作者着力描绘和渲染了夏雅丽的“辱身赴义”(第十七回)的决绝与艰难。对于其表兄加克奈夫的丑陋和凶残,夏雅丽厌恶之至痛恨有加。但是当她得知组织经费奇缺,并且加克奈夫及其父的手上沾满了虚无党员的鲜血时,她竟毅然瞒着恋人克兰斯回国马上嫁给了加克奈夫。其态度的决绝、速度的神速连对她早已垂涎三尺的加克奈夫都惊诧不已。另一方面,夏雅丽做出这一决定而不能对任何人包括她的恋人诉说,其间的艰难委屈自不待言。小说中有两个细节颇能说明这一点:一是克兰斯准备暗杀夏雅丽时,看到她独自对着自己的小影垂泪,并发现照片背后有“斯拉夫苦女子夏雅丽心嫁夫察科威团实行委员克兰斯君小影”的题语,“苦女子”与“心嫁”的叠加所透露的革命与私情的矛盾冲突以及革命信念对私情的强压决不是非当事人所能体悟的。二是夏雅丽准备炸死俄皇前,知道自己必死无疑;所以偷偷潜入克兰斯住所,并把自己的小影留了下来,这小影固然是取出她交给组织的巨款的凭证,但又何尝不是希望组织特别是克兰斯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凭证?
值得深味的是,对于她嫁给加克奈夫,她的男性革命同志是不理解的,以至于她的恋人克兰斯在悲愤之余决定暗杀她。倒是其女友鲁翠坚信她所做的一切是“辱身赴义”,并举例说明这种行为在虚无党中是有先例的。在这里,革命同志中的性别差异得到集中体现。一方面,革命需要女性为革命奉献自己的一切,当然也包括身体,并且革命也正在利用女性,当然也包括女性通过种种手段获取的资源;另一方面却是在革命的名誉下,男性,特别是这些以“色”事敌的革命女性的情爱对象,在“女性名节”与“女性死亡”之间,他们倒宁愿付出自己心爱女性的生命,也不愿她们玷污所谓的“名节”。这样,于不经意间,革命女性已经经历了双重利用与双重赴死。
如果说,在克兰斯对夏雅丽的刺杀中这一心态还没有得到饱满立体的体现的话,那么,《虚无党真相》倒给我们提供了“革命男性视角”对此的真实心态反映。《虚无党真相》中有这么一段故事:在虚无党面临重重困境时,党人为了营救一部分被敌人关押的同志,而让虚无党英雄那普哥罗的未婚妻葛娜做“美饵”——将敌方首领引出。按照生活的通常逻辑,那普哥罗首先应担忧的是未婚妻的生命安危,但是事实却完全相反,无论是葛娜面临被劫的险境还是身处敌人的魔掌中,对于普氏来说,葛娜能否“保全名节”始终是第一位的,这甚至比葛娜能否保住性命还要重要得多:“那普哥罗此时真是锥心泣血,嗳,人孰无情,谁能堪此。他想此事为党中利益,将挚爱的妻子,送到敌人手里,受其折磨凌辱,恁地结梢,还不如直处严刑,倒还光彩些,干净些……”那普哥罗的这种焦虑在小说中一再被强化和表述,而他的朋友也非常理解他的焦虑,于是挺身而出,要求陪伴和保护葛娜:“……那普哥罗所着急的是为她名节,若能保全名节,便是死在敌手,也就万古留名了……”在这里,葛娜的“名节”之所以被如此看重是因为它属于那普哥罗,对那普哥罗来说,葛娜是否贞节是第一位的,哪怕她失去生命,也不能失去操守。这怎不使我们联想到,各个时代女性在遭受异族或敌方入侵时首要的便是保护自身的“清白”。这时,女性的贞操不仅仅属于某个男人,更是她所隶属的民族国家或政党、社群等等集体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当两阵敌对冲突时,争先糟蹋和强奸对方的女人,成为征服、凌辱对方(男人)社群的主要象征和关于社群的具体想象”⑩。在《虚无党真相》中,葛娜则成为敌对双方斗争的“场所”,她是否能够保持身体的“清白”则不仅关系到对那普哥罗的忠贞,更关系到虚无党是征服敌方还是被征服这一关键的“象征”。
清末民初英雌小说的“性政治”情意结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个体生命的人性丰富性,呈现出较为单一的民族国家宏大目标的追求性。而这恰为中国现代小说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革命女性的塑造——提供了最初原型。
注释:
①凯特·米利特著,宋文伟译《性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
②米歇尔·福柯著,佘碧平译《性经验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页。
③陈王:《论婚礼之弊》,《觉民》1904年7月。
④炼石(燕斌):《中国婚俗五大弊说》,《中国新女界杂志》第3期,1907年4月5日。
⑤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著,张百春译:《论人的奴役与自由》,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225页。
⑥阿英:《晚清小说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⑦此段的引言,全见于卧虎浪士《〈女娲石〉序》,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年-1916年)》(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页。
⑧鞠普:《女德篇》,《新世纪》第四十八号,1908年5月23日。
⑨参见李中馥《原李耳载》卷上,转引自吴秀华《明末清初小说戏曲中的女性形象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⑩刘健芝:《恐惧、暴力、国家、女人》,《读书》199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