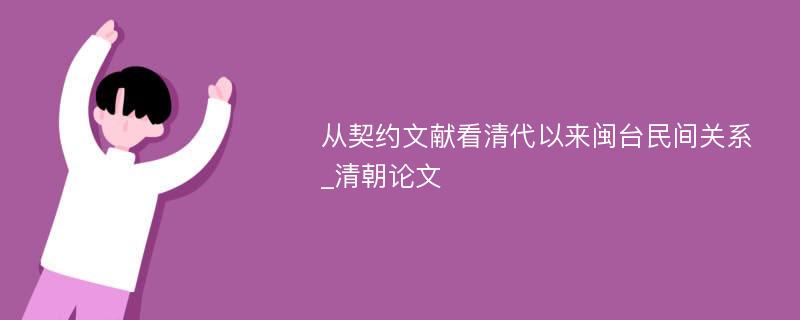
从契约文书看清代以来福建与台湾的民间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福建论文,台湾论文,契约论文,文书论文,民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明清以来大陆人民向台湾迁移的历史,学界论者甚多。但在这众多的论著中,存在着一个缺陷,即人们比较关注大陆人民向台湾迁移的动向,而对大陆人民向台湾迁移后与原祖籍地所继续发生的种种联系,却往往被忽视。十余年来,我们着力从事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从中发现了少量有关闽台民间关系的契约文书。迄今为止,福建地区被发现和搜集的民间契约文书不下万件,但有关闽台民间关系的文书极为罕见,故我们所掌握的此类文书数量虽然不多,但十分珍贵。本文拟就这些契约文书作一初步的论说,同时结合其他相关资料,或可从另一个侧面,对清代以来福建与台湾的民间关系,作一细部的考察。
泉州《陈江陈氏五房五家谱》收录有一纸乾隆年间的认耕字云:
李厝前张绍理认耕字
立字人廿一都李厝前乡张绍理,因陈朝亨有祖坟一首,葬在本乡土名上墓内,坟傍并产园贰坵付理族亲绍统祖父耕种,年收物粒,以为看守坟茔辛劳之资,历有百余年无异。兹族亲绍统欲搬移往台居住,理就与陈宅领耕,依前看守坟茔,毋致损伤祖坟,亦不敢混卸他人等情。如有等情,听闻官究治。今欲有凭,立字为照。
乾隆贰拾年贰月 日 立字人张绍理
知见 丁士美
代书人张日惠(注:引自清末泉州《陈江陈氏五房五家谱》,《契抄》。)
这纸契约讲的是晋江县二十一都张绍统,自祖父辈起为泉州城内陈氏家族看守坟茔耕种园地,“历有百余年无异”。因乾隆二十年欲迁移往台湾居住,把看守坟茔和耕种园地的责任与权利作一清理,并由其族堂亲张绍理予以继承认耕。
永定县洋背乡谢氏家族(现住于相邻的龙岩县)收藏有清末咸丰年间的卖屋间地契一纸如下:
立卖屋间地基迹(址)字人本家侄孙胜美,今因往台缺欠盘费,自情愿将公分阄下屋间地迹(址)一间,坐落祖祠左片第一重横屋,上至花台坎,下至本人屋间为界,内外门坪为界,四址分明,其屋间并无桁桷瓦料,又无门窗户扇,欲行出卖地基屋迹(址),托中送与叔公思秀出首承买。当日三面言议定时价屋间地迹(址)价钱五百文正,其钱即日随字两相交付亲收足讫,无欠分文。委系正行交易,不是货债准折之故。其屋间地迹(址)自卖之日,任凭买人起改造架屋间。其屋间地基一卖千休,永无收赎。此系叔侄甘愿,两无反悔,恐口无凭,立字一纸为照。
咸丰元年辛亥岁四月初十日。
立卖屋间地迹字人胜美
在场母 胡氏
代笔弟 钦美(注:契约复印件现藏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本文所引永定洋背谢氏家族契约文书及《谢氏族谱》手抄本,承龙岩市谢耀承先生提供,特此致谢。)
从以上两纸契约文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清代迁移往台湾的福建人民,贫穷民众占有相当的数量。晋江二十一都的张绍统,实际上就是通常民间所说的“墓佃”,这是一种社会身份地位与经济地位均较为低下的贫民(注:参见陈支平《清代福建的蓄奴制和佃仆制残余》,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而永定县的谢胜美, 为了去台湾谋生,缺乏盘缠,只好把祖分的屋间地基出卖,取得价钱五百文,艰难渡台的贫困处境不难想见。
清代福建民间渡台,交通工具相当落后,大部分是搭乘小型木船,很难抵御台湾海峡的台风与热带风暴,海难事件时有发生。特别是在清代前期,清政府一度施行禁渡政策,福建等内地贫民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冒死犯禁,生命安全更加没有保障,人们都要历尽千辛万苦,才能到达台湾,而许多偷渡者则丧生在渡台途中。乾隆《台湾县志》记载:“内地穷民在台营生者数十万,囊鲜余职,旋归无日。其父母妻子,俯仰乏资,虽急欲赴台就养,但格于例禁,群贿船户,顶冒水手姓名挂验,女眷则用小渔船夜载出口,私上大船抵台。复有渔船乘夜接载,名曰‘灌水’。一经汛口觉查,奸艄照律问遣,固刑当其罪。而杖逐回籍之愚民,室庐抛弃,器物一空矣。更有客头,串同习水积匪,用湿漏小船收藏数百人,挤入舱中,将舱盖封钉,不使上下,乘黑夜出洋,偶遇风涛,尽入鱼腹。比到岸,恐人知觉,遇有沙汕,辄赶骗离船,名曰‘放生’。沙汕断头距岸尚远,行至深处,全身陷入泥淖中,名曰‘种芋’。或潮流适涨,随波漂溺,名曰‘饵鱼’。在奸艄唯利是嗜,何有天良。在穷民迫于饥寒,罔顾行险,相率陷阱,言之痛心。”(注:乾隆《台湾县志》卷二,《山水·海道》。)台湾学者黄湘玲曾披露一纸客家人的《渡台带路切结书》,这是相当难得的原始记录,兹转引如下:
立请约人彭瑞澜,今因合家男妇老幼共九人往台湾,路途不属(熟),前来请到亲罗亚亮亲带至台湾。当日三面言定,大船银并小船钱总铺插花在内,共花边银叁拾壹员正,至大船中一足付完。其路途食用并答小船盘费,系澜自己之事。此系二家甘愿,不得加减。口恐无凭,立请约,付火召批明,九人内幼子三人。
见请代笔兄瑞清
嘉庆九年正月二十五日(注:转引自黄湘玲《客家〈渡台带路切结书〉》,《汉声》杂志第24辑,第84页。)
这纸契约引起众多研究大陆与台湾移民史的学者们的重视与引述。而从我们所接触的福建契约文书中,也有一纸关于福建人民搭船渡台而被飓风吹至浙江回家无门,只好向船主举借高利贷的文书,兹抄引如下:
立生借字人本家侄孙曾成,情因往台地,六月初四往台犯风不顺,开船往在浙江温州府洞头山上,上山无奈,问到船主借伙食银共银一十大员正。今因无从所出,情愿将到祖父遗下水田一处,坐落土名大坪上福坛角公王门首禾田六千把大田坵,上至聚应田为界,下至溪把为界,左至路为界,右至槐盆为界,四至分明。欲行出当前来叔侄商议,问到叔祖太天,送叔公身边生借过银头一十一员七钱二分正。即日随字两相交付足。其银每月每元加四行利,不得少欠分文。如若少欠,即将所当之田任凭银主过手管业耕作,有生银人父子兄弟不敢异言生端资事等情。此系二人甘愿,口恐无凭,立字为照。
同治二年癸亥岁九月初二日。
立生借银字人侄孙 曾成
在场 叔 立生
兄 得海(注:契约复印件藏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
这纸借契中的举借人谢曾成,也是永定县客家人,同治二年(1863年)六月初四搭叔辈的船前往台湾,却被大风吹至浙江温州,虽然保住性命,但流落异乡,衣食无着,只好向船主叔辈举借银一十大员,并以祖籍地的田产作为抵押。债主虽为叔侄关系,但并未能顾及族亲关系,而是趁危盘剥,收取暴利“每月每元加四”的增息。在清代福建民间的一般借款关系中,较为流行的行息是加二左右,超过加三行息的借款,就是名副其实的高利贷(注:参见陈支平:《清代福建乡村借贷关系举证分析》,载傅衣凌、杨国桢主编:《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又《清代福州郊区的乡村借贷》,载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从这纸契约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当时福建人民移居台湾的艰辛历程。
福建各地人民迁移台湾之后,往往与祖籍地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当某一姓氏家族刚迁入台湾的前几代子孙中,他们大多与祖籍地保持着密切的血缘关系,或是经常返乡祭祖扫墓,或是落叶归根,希望把自己的骸骨归葬故乡,魂安宗祠。如永定县下洋洋背谢氏家族,从清代中期起便陆续有人赴台谋生,据谢耀承先生的回忆:“五十年前,我还是儿童时代,每年春节过后,就跟着父母上山去祭墓。二百多年来我房上祖大都迁往台湾,留在故土的只剩我一家了,因此全房族的远祖近祖坟墓都由我家来祭扫。这些坟墓有在台湾逝世后骨骸运回安葬的;有骨骸被水冲掉了就只好用银牌代葬的;有的儿子去台,母亲在家死后骨骸都未捡敛的。踏遍周围几十座山头,走完邻近十多个村庄,二十多门墓地祭下来已是临近清明,最后才祭祖父的坟墓,扫墓活动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注:谢耀承:《两箱谱契维系两岸亲情》,载《客家纵横》总第14期,“闽台客家关系学术研讨论会论文专辑”,1997年出版。)在现存的《谢氏族谱》手抄本中,曾详细地记录着这些迁台族人落叶归根的情景。族谱载该族始祖谢四九郎自元代末年卜居于永定县洋背乡,传至第十五代,约在清代中期乾隆年间,开始有族人迁往台湾,“十五世祖谥永捷公,字香公,妈郑氏。……时遇福(康安)中堂奉旨平台湾时,乃同福中堂迁来台湾府彰化县武东堡,地号小新庄建立居住。”(注:台湾《谢氏大族谱》,永捷公派下,谢富鼎:《族谱序》。)又有“十五世正京公卒于台湾诸罗县而终。 ”(注: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永定洋背《谢氏族谱》不分卷,手抄本,《世系》。)从此至第二十四世,该家族迁台者共有42户。许多族人在台身亡后,子孙便把骨骸送回永定安葬:
十七世约理公,生下二男,长曰元凤公,身往吧城,身故无骸寄回无嗣。次男武凤身往淡水。身故骸骨寄回与父母……连葬。
十八世祖字初凤,号鸣淡公,身往台湾身故。因长男庭应公往台地要收骨骸,无奈被水漂流,以致无骸带回,后附银牌与杨婆夫妻合葬。
十七世祖字燕秀,讳攀琳,谥柔良,号琳洋公。……嘉庆八年癸亥岁十二月十九日在淡水艋舺永珍店正寝。……于乙丑年(嘉庆十年)二月十二日香火带回,请僧发开阴魂入灵祀奉,周年登座,于丙寅年(嘉庆十二年)七月收骨骸寄回。
十七世祖字耀秀,讳攀瑄,谥良朴,号瑄洋公。……于嘉庆十九年甲戌五月初七日午时在淡水艋舺永珍店正寝。……丁丑年(嘉庆二十二年)八月收骸寄回。
十八世祖字秉衡,……不幸于嘉庆十一年丙寅岁七月廿二日未时在艋舺店中身故。……于丁丑年八月收骸寄回。
十八世祖字秉庚公,……不幸于嘉庆十八年癸酉岁十二月十三日卯时身故在淡水艋舺店中身故,……于丁丑年八月收骸寄回。
十八世祖字科瑞公,原命生于癸巳年(乾隆三十八年),卒而台湾淡水艋舺搭寮坑,葬后骸骨寄回,葬在例坑。
十六世祖字长藩,乳俊魁,讳泰辉,谥庆隆公。原命生于雍正十三年乙卯岁 月 日 时,享寿六十六岁。于嘉庆庚申年月日时在艋舺店中正寝。……收骸寄回,葬在倒坑带豆窠。……(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永定洋背《谢氏族谱》不分卷,手抄本,《世系》。)
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当时福建人民迁居台湾后对于故土的眷念之情与落叶归根的乡族情怀。我们曾见有一纸泉州县晋江县的卖山契约,就是为了安葬在台族人骨骸而购买山场的文书:
立尽卖契人口崇社曾天拾,有已分产山一所,坐落西坑村,小地名牛栏坑,内有风水一穴。今因族亲其福、其祥求葬伊父在台骨骸,前来求买。拾等念谊批送宅剪做砂水成坟葬亲。即日收过时价银十二员,其银仝中交讫,其山听银主管掌为业,有留杉松杂木,回护风水。其山界前重圳,后至祖墓下,左至龚宅田,右至砂水外仑,配产米乙升。界限四至明白,不敢异言生端并需索酒礼等情,亦并无内外交挂不明等情,如有不明,不干银主之事,拾等抵当。二比甘愿,各无反悔,恐口无凭。立尽卖契字一纸付热为照。
道光十六年月日立尽卖契字人 曾天拾
在见人 叔尔施、尔球
代笔 弟天分(注:原件藏泉州市闽台关系博物馆。)
清代福建民间各姓氏家族的早期迁台,不仅有相当一部分的族人希望能够安葬故土,落叶归根,而且在事实上,许多人迁台往往是把它当作一种谋生的手段,并非一开始都具有定居于台湾的设想。他们或是来来往往,或是把在台湾的劳动所得携回家乡,置产购业、娶妻生儿;或是汇款捐款回家,仰养俯育、拜祭先茔;也有的因在台湾发展不顺,继续寻求家乡的接济等等(注:可参见庄为玑、王连茂:《从族谱资料看闽台关系》,载《泉州文史》第8期,1983年12月出版。)。 因此我们在民间的契约文书中,可以看到一些关于迁台后继续与家乡发生经济联系的记载。如上述永定县洋背乡的谢氏家族第十七世谢成美,便因在台染病,以老家的房产作为抵押,借款治病,该胎借银字记云:
立胎借银字人谢成美,今因命运不□,染病在床,身边并无半文,少药调治,生借无门,无奈情愿将内地祖家棋盘屋右畔第三间,原系先年与璋秀叔承买之屋。兹乏银使用,欲行出当,托中叔维秀到堂兄林选身边当过胎借番银贰元正。□银面约每年每元行利加三。至若病好,与人伸劳,在此头利一足算还。倘若台地不能交还,俟候回唐之日头利一足清还,不得少欠,余有少欠利□之日,随即□屋时直□□□□□,堂兄林选管业。当日三面言定,叔侄之情,救济之银,房亲叔侄人等不得异言滋事生端。此乃仁义相交,不得反悔,巩口无凭,立借银字一纸付兄执照。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十六日立借字人 谢成美
在场代笔 叔维秀正(注:复印件藏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
这纸借银契字中所反映的谢成美在台染病的困境是比较凄惨的。但就整体情景而言,由于清代的台湾有着优良的自然环境,人口数量比较适中,随着台湾地区的不断开发,许多渡台的贫民往往有着比福建祖家更好一些的经济收益。这种较好的经济收益,是吸引大量内地贫民冒着生命危险纷纷渡台的最基本的因素。于是,许多本无恒产恒心的贫民,逐渐在台湾各地定居下来,开垦殖业,繁衍生息,形成许多新的村落和家族。但是这些外植的家族,并没有数典忘祖,而是与福建的家族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如大陆族人在修纂族谱时,始终没有忘记把他们徙居台湾的子孙载入族谱,说明他们从来都把这些外迁者视为本家族的成员。而迁居台湾的族人,也尽力为祖籍的家族组织建设捐钱捐物,奉献了外迁族人追根溯源的心愿。现存于南靖县的刘氏、赖氏“祭祖业田碑”便是这种心愿的实物见证:
(一)
嘉义刘氏祭祖业田碑
赏思木有本,水有源,而能不忘源本有鲜囗。我珊图住台之人实繁,有徙于嘉义县翻龙路共建祠宇名曰世德堂宗祠,均保祖分十摧,与唐之高山大宗如一辙焉。嘉庆年间裔孙盛兴、天庆等闻唐大宗祭费未饶,奚将世德堂余租银寄回二百元,充在叙伦堂,置祠田焉。道光癸未天庆率孙奠邦、侄利贞深池回视坟祠,增买祭租共银三百余。丙申春奠邦、玄乞等复带银三百余再买祠田。二十余年间台之公银三至共以千,非不忘源本安能若是哉。宜勒石以美其事,并镌所置田段税额,以垂不朽云。
一段在大宗楼后,税八石。
一段在大枋洋,税十三石。
一段在大宗后过林,税三石四斗。
一段在西牛潭高土敢,税十石。
一段在吾宅头,税四石四斗。
裔孙奠邦
道光十六年四月立
玄乞
(二)
上淡水潭底赖氏祭祖业田碑
赏思水有源木有本,所谓追远者,此之谓矣。兹我朴厚祖三,四房裔孙,移在台上淡水内港潭底庄,念祖宗祭祖悠远,处置祖田数段以修丞尝,虑恐子孙贤愚不一,恐有盗卖祖田买业者切在惠顾决勿与他交接。念我裔孙在台有山河阻隔之远,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爰立后记以传知焉,庶乎我祖之蒸尝得以悠久无疆矣。遂将田段计列于左。
祠堂前左右赖家所置之田俱是蒸田
道光贰拾陆年又五月三四
房裔孙首事宁瑞、天关历
代派生等
同书(注:转引自林嘉书:《南靖与台湾》,香港华星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第200~201页。)
以上南靖刘氏、赖氏家族,是族人迁台后回祖籍添置祭祖田业,而著名的台湾板桥林家,祖籍在漳州府龙溪县,则在台湾购置义田,每年把租谷所入寄回大陆祖籍地,建立义庄,赡济族人。其首倡者是道光年间的林平侯,所谓“平侯既富,念故乡族人贫苦,仿范仲淹义庄之法,置良田数百甲为教养资”。祖籍的义庄建在龙溪白石保过井村(今龙海县角美镇),据义庄碑记刊载:“在淡水海山堡水田四十三甲八分四百二毫(每甲合十一亩三分多)。充为原籍本族义田,年收佃租,除完供耗谷外,年实收谷一千六百石,按年寄回内地龙溪县白石保吉上村、潭头村,赡给同宗族人贫乏之用。延请族诚实公正两人,经理其事。”林平侯去世后,其子林国华、孙林维源、曾孙林尔嘉继续经营义庄,使义庄的财产有所发展,一直到抗战期间,两岸交往不便,义庄的赡赈才告停止,先后维持了一百余年(注:参见欧阳宸:《林氏义庄及林平侯一家》,载《龙海文史资料》第二辑。)。当然,台湾移民与大陆福建祖籍地的关系是多方面的,也是相当复杂的,特别是在闽台地区家族势力比较强盛的社会环境里,这种关系,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关系,带有家族牵制的色彩是在所难免的。我们曾见到两纸有关开店生意的契约,就可隐约看到这种微妙的联系:
(一)
立甘愿退份人李胜继,有同二弟李胜义三弟李光弼四弟李光俭随父来台,遗置瓦店乙座,坐落鹿港北头福德祠后,开张什货米铺,近因生意微末,亦有胎借他人银项,亦有被人拖欠数目,所入不供所出,恐坐食山崩,互相推诿,爰是商议,请族长公亲佥议,面订胜义光弼光俭备银壹拾大圆,付胜继别图利路,将胜继应份此店之额,及胎借银项拖欠数目,一尽义等取讨清还,及后来长失,与胜继无干,然按份算抵,继受此拾圆之银,有亏於义等,故又将内地家厝巷边,抽出公置嘉固叔小房屋乙间,配连在鹿港店抵还欠他人银项,当堂交义等掌管,永为己业。此系佥议甘愿,各无抑勒反悔。至于日后子侄亦不得异言生端,恐口无凭,立收银甘愿送份字乙纸,付三位胞弟执照。
即日同族长公亲收过胜义光弼光俭佛银壹拾大圆足讫。批明,再照。
族长 李光邦 (花押)
李大前 (花押)
李阔全 (花押)
李亲迎 (花押)
公亲 徐惠老 (花押)
道光十九年三月 日立甘愿退份字人 李胜继(注:引自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编《明清福建经济契约文书选辑》,人民出版社, 1997年5月出版,第790页。)
(二)
立依允公议和好字人本家侄钦美、母胡氏,情因先年秉德兄弟在于台地开有义聚打铁店一间,因欠公项,不能开张,将店中碛地器皿家伙一并在内,卖与鸣瑞,当日三面言断银五十余元,当时簿内记明,即将此银对与铁匠首鸣瑞交缴公项清欠,不涉秉德兄弟之事。以后鸣瑞改号“万隆”开张,有天送、林选叔侄改号“金荣”开张,二店号各管各业。因丁巳上春有钦美往台,适逢天送叔开“金荣”生理茂盛回家,有钦美听外人唆讼糊说上年先父秉德存有银天送叔手内,即回信与伊母取讨。但此银叔侄明知当年鸣瑞已缴公项清楚,不涉天送叔之事。现因胡氏偏听伊子之信,要讨此银,叔侄不忍,前来劝说,天送叔办出银五员五角正,重八兑,置酒和好。自和好之后,钦美母子不敢生言滋事等情。此系二比甘愿,不得反悔。恐口无凭,立依允公议字为照。
咸丰丁巳年十二月十五日。
立依允公议字人侄 男 钦美
妇 胡氏
在场叔侄镜 招 松应
柱 龙 槐益
林 生 福扬
代笔余瑞(注:复印件藏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
在上引的第一纸契约中,李胜继与兄弟合开什货米铺,从合伙到退股,以至于返回大陆福建“按份算抵”老家的房屋等,都需经过族长公亲们“佥议”。在本文所引的许多契约文书中,无论是在台湾、在大陆祖家,或被漂落到浙江温州,其签订契约合约文书的双方,也大多是有家族乡亲这一层关系的。这种情景,不能不说是清代闽台民间移民过程中维系联系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第二纸契约中,谢秉德与谢天送兄弟二人合开“义聚”打铁店,“因欠公项不能开张”,尽卖给铁匠首鸣德。谢秉德故亡后,其弟谢天送继续在台开设“金荣”号,“生理茂盛”,积蓄了一些钱财回永定祖家。谢秉德之子谢钦美遂怀疑其叔干吞其父的银两。虽经族亲证实并无其事,但最后仍需“办出银五员五角”。可见这种两岸族亲之间的联系,往往干扰和侵蚀了民间的纯经济行为。因此,我们既要看到清代闽台民间关系中良性互动的一面,同时,对于这种斩不断理反乱的复杂关系,无疑也应予以足够的认识。而这一点,也正是以往研究者所忽视的一面。
清末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政府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国之后,大陆与台湾的政治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闽台两地的民间交往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两地在血缘、地缘上的天然优势,并不是由于政治上的割裂而能够完全断绝的。如民间修撰族谱等,台湾的许多姓氏始终与福建祖籍宗族保持着较多的联系(注:参见陈支平:《闽台族谱修纂的互动》,载《炎黄纵横》1998年第5期。)。经济商业的民间往来, 虽受到诸多限制,但也未能中断。我们见到一纸民国二十年(1931年)的渔船交易契约文书,便是一个例证:
立杜尽断根卖发动机新式渔船字台湾基隆市鼻仔头叶狮,有承大日本帝国商民中部几次郎委任狮为全权代表,将一百马力新式发动机电渔船二艘,因日本不景气,托中引就卖断尽根与大中华民国侨商潘育汉先生,日金一万五千圆正。于本年五月三十日仝中见在台湾基隆市鼻仔头狮行,双方妥订契约,经各遵照契约进行本年六月廿八日收足日金一万五千圆正。狮将一百马力发动机新式电渔船贰艘由台湾基隆市驶入厦门港内,交与潘育汉君接收掌管为其所有物。保此发动机渔船贰艘系狮全权发卖,并无交加他人内历不明等情,如有是情,狮自当出头支档。亦无典挂他人财帛,不干买主之事。理会将发动机渔船国籍证书、原有牌照即日双方在大日本帝国领事官公署签字证明卖尽,潘育汉君尽行归割,听其改换船名,永远营业。此系两愿,各无抑勒,口恐无凭,今欲有凭,合立发动机渔船贰艘卖尽断根字一纸付执为照。
一批缴交日金一万五千圆完足。
一批缴手抄台北总督府电船国籍证书贰纸。
一批契约书一本附契。
一批原有船牌照二纸附契。
大中华民国二十年七月 日。
立卖尽断根契约 叶狮
为中人 杨振坤 王振桂
在见人 花井义房
收金人卖主 叶狮(注:原件藏泉州市闽台关系博物馆。)
有关日据时期大陆福建等地与台湾的民间关系与经济往来,论者甚多。我们在此举出这张契约文书,意在从最原始的资料来进一步证实闽台两地关系的不可截然分开。不但如此,即使是1949年以后海峡两岸进入完全隔绝的年代,民间的经济活动也不能完全断绝。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1949~1987年)大陆货走私市场的形成,具有经济和政治的双重背景;经济上,基于国府迁台早期物资的缺乏,大陆和台湾历史上不曾分割的经济、血缘关系,以及两岸地理的接近,生活习性之相同,皆有利于大陆货物在台的销售。因而政治上,当台湾当局祭出反共大旗,对大陆货物颁行管制(抵制)政策后,大陆货物并未因此在台湾市场绝迹,反由正当陈售转入地下交易,走私货仍不断源源流入。”(注:林美伶:《政治力与经济力的竞争:戒严时期大陆货走私和台湾地区问题之研究(1949~1987)》,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经济史组编:《财政与近代历史论文集》上册,1999年6月出版。 )高压戒严及战争气氛笼罩之下的两岸贸易依然如此活跃,则在一般较为平和的时期内,闽台两地的民间关系将得到不断的发展,这是可以想见的。本文所列举的这些罕为人引的契约文书,虽然不能全面地分析清代以来闽台两地民间关系的整体概貌,但由此可以了解到两岸关系的发展虽然有起伏,有良性互动,有负面影响,但其整体趋势,却不是其他种种因素所能割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