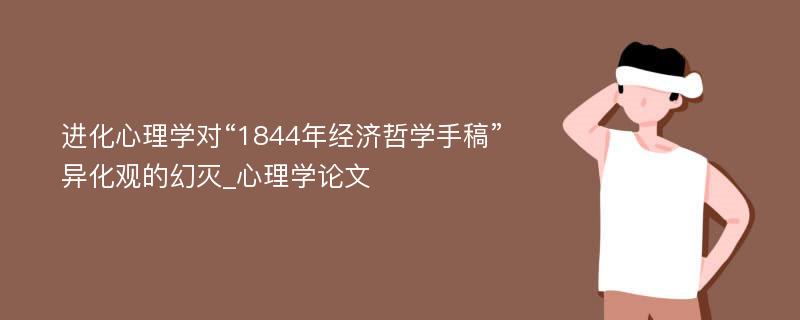
演化心理学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异化”观的“祛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手稿论文,心理学论文,经济学论文,哲学论文,祛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3)06-0054-10
一、引论
改革开放之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日渐成为汉语学界读解的重点,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从总体上看,目前国内的研究者大多在义理上高度重视《手稿》的哲学原创意义,而不再像更早期的研究者那样,将其视为马克思“不成熟”时期的作品,或吝于对其中蕴含的人本主义思想的褒扬。但平心而论,国内的《手稿》研究质量依然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比如,大多数现有《手稿》的研究并没有很好地完成为马克思原著中的晦涩性进行“祛魅”①(英文“disenchantment”,德文“Entzauberung”)的任务,即使用较为明晰的当代学术语言,将青年马克思的晦涩哲学语言予以重述。又比如,研究者往往预设《手稿》中的那些核心关键词(如“异化”、“对象化活动”、“感性活动”、“类本质”等)之含义的自明性,并在元语言的层面上不加辨析地使用这些含义待解的术语,并由此导致解释中的自我循环。另外,也并没有很多研究者意识到采用如下解释策略的必要性:适当引入当代社会科学中那些歧义更少的解释性范畴,来替换掉那些歧义更多的哲学范畴,而不是南辕北辙地从其他晦涩的哲学流派(如存在主义或现象学)那里引入更多、更含糊的哲学范畴,来将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读者或许会说,《手稿》自身浓郁的人本主义色彩,本来就具有和西方当代人本主义哲学思潮之间明显的“家族相似”关系,而带有较强自然科学色彩的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则应当和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成熟期作品有着更强的可对话性。但这番言论至少忽略了两个问题。第一,青年马克思本人在《手稿》里就曾明确反对这种将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相互对立的看法:“自然科学终归会将自己化归为关于人的科学,正如关于人的科学终归会将自己化归为自然科学一样。最终只会有一门科学。”②第二,如果说对人性的探究是《手稿》的重要主题的话,那么这个主题也是那种自然科学化的社科研究的主题,而其典型代表就是在今日的英语世界方兴未艾的“演化心理学”研究。在笔者看来。如果我们能够引入演化心理学的资源来对《手稿》中的思想加以澄清的话,《手稿》中的一些核心概念,如本文所关心的“异化”概念,就能够得到比较成功的“祛魅”。
在正式引入演化心理学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英语哲学界对于《手稿》的“异化”观的一些尚未被国内学界注意到的看法。
二、亟待“祛魅”的“异化”论
“异化”这个词在《手稿》中的德文写法是“entfremdung”,英文翻译则一般是“alienation”或“estrangement”。英国伦理学家沃尔夫(Jonathan Wolff)在为英语世界颇为权威的“斯坦福网上哲学百科全书”撰写“马克思”这一词条时,是这么刻画《手稿》中的这一关键概念的:
《手稿》中最为人所知的部分,即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描述。在此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存的劳工会因四种类型的异化劳动而受苦:第一是劳工和其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即劳工所创造者旋即就被剥夺于劳工。其二乃是劳工和其生产活动(即劳作)之间的异化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劳作被体验为一种受虐。其三则是劳工和其类本质之间的异化关系,这指的是人类并未按照其真实的人类力量来生产,而是以某种盲目的方式来生产。最后是人和其他人之间的异化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交换关系取代了对于共同需求之满足。这四个异化范畴在某些程度上是相互重叠的,但考虑到马克思在这些著述中的方法论雄心,这一点也是不足为奇的。他实质上想做的事情是,将黑格尔的范畴演绎施用于经济学,即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诸范畴(如工资、租金、交换、利润等)最终都可以是从一种对于“异化”概念的分析中衍生出来的。……然而,马克思在《手稿》中最终做成的,仅仅是将这四个异化范畴彼此之间的推演关系呈现出来。……而且,关于异化之本性为何,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文本理解空间恐怕也是太大了。比如,关于何为“非异化”状态,我们只能够从“异化”的反面去理解。③沃尔夫对于异化的四重内涵的分析和国内马哲学者的分析是大同小异的,但和国内学者不同的是,他立即指出,马克思对这四重异化劳动的刻画在逻辑上可能有彼此重叠之处,而且这些刻画和《手稿》的国民经济学批判之间的理论推演关系也是不明确的。最后,沃尔夫对“异化”概念确切的语义学内涵也表示不太确定。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的德国古典哲学专家伍德(Allen Wood)在《卡尔·马克思》2004年新版中直言不讳地写道:
诚然前人已耗费大量笔墨,以图从《手稿》的片言只语中重构出马克思的所谓“异化理论”。但在笔者看来,这恐怕都是在做无用功。甚至有很强的理由去促使我们怀疑,是否存在着这么一种“异化理论”值得后人去予以澄清。就马克思归到“异化”概念名下的诸种不同的现象而言,它们之间的共通点,仅仅在于它们都牵涉到了某种非自然的分离状态或是敌对关系。但这些相似处,并不足以使得我们断言它们之间有着实质性的联系,或它们都因某个共通的原因而起。很难相信,“异化”(也就是非自然的分离或敌对状态)指称了某种关于人类或社会之机能失调状态的自然类(natural kind),而更难让人相信的是,“异化”所指涉的概念或本质在人类劳作活动中的出现,竟然能够解释马克思归于“异化”概念的各种分离或敌对现象。④伍德对于马克思的“异化学说”是否存在的怀疑思路,其实就是英国哲学家莱尔(Gilbert Ryle)对于“范畴错误”(category mistake)的批判的翻版。所谓“范畴错误”,就是指把不应当归为一类的事项归为一类,并错上加错地认为这个类是一个“自然类”(即一个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事物类)。具体到对于《手稿》“异化”观的问题上,伍德的批评实质上说的即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四类“异化”现象或许只具有表面上的相似性(这就好比蝙蝠翼膜和鸟翅之间的表面相似性)。因此,我们并不能指望一种系统化的“异化理论”能够给出针对这些现象的正确诊断书。
笔者认为,伍德先生提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即一种以“异化”概念为基础的理论是否能够满足后世的研究者赋予它的大量期望:对分工机制根源的探究、完成对私有制的批判、奠定共产主义学说的基础,等等。在这里,我们无疑看到了一条鸿沟:一方面,“异化”概念自身的表达是隐喻式的,甚至是美文学式的;而另一方面,一种希冀中的“异化理论”所试图解释的那些社会现象却似乎应当由那些更为“冷酷”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把捉。换言之,“异化”概念自身的含混性似乎使得我们的确有理由怀疑这条鸿沟是否真的能够被填平——至于马克思在其成熟期对“异化”概念的冷落,似乎也为这种怀疑提供了权威性的旁证。
而笔者本人对于伍德之质疑的应答则是:“异化”概念在《手稿》原始文本中的这种含糊性固然是存在的,但却完全有希望通过某种“祛魅化”重构予以克服。因此,《手稿》的“异化”论依然值得我们投入精力和热情予以某种“再发现”。本文则将致力于引入演化心理学的思想资源来完成这种“再发现”。
三、为何要引入演化心理学?
演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渐渐成熟起来的一个新兴交叉学科,不过其渊源可以上溯到达尔文时代。在1871年和1872年,达尔文分别出版了作为其名著《物种起源》之衍生篇的《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⑤以及《人和动物的情绪》⑥。在这两部著作中,达尔文尝试性地研究了人类行为特征以及心理特征在动物中的起源,并由此流露出了将人类的行为研究纳入整个演化论体系的学术雄心。在20世纪,达尔文勾勒的这幅蓝图得到了后继者们更为细致的描绘。在60年代,英国学者汉密尔顿(William Donald Hamilton)对动物的利他主义行为和亲属选择行为的遗传学基础进行了数理化刻画,引起了很大轰动。在其工作的激励下,美国生物学家威尔逊(Edward Osborne Wilson)在1975年出版了其划时代巨著《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⑦,试图对林林总总的动物社会性行为——从养育幼兽到侵略性行为——都给出一种生物学或者遗传学的解释。他的工作又进一步启发心理学工作者将演化论思想和发展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尤其是认知心理学的固有成果结合在一起,并由此催发了现代意义上的演化心理学的诞生。最早将演化心理学的基本思想原则阐述清楚的大部头文献,一般认为是1992年问世的论文集《适应性的心灵》⑧,编辑者有美国心理学家考斯米德(Leda Cosmides)和美国人类学家托比(John Tooby)等。⑨
在考斯米德和托比合写的论文《演化心理学的概念基础》⑩中,现代演化心理学的基本论点被归结如下:
1.人类的大脑可以视为一台经过自然选择机制而演化生成的信息处理机器,其任务是从外部环境中抽取信息。
2.人类所有的外部行为(从照顾老幼到猎鹿驱虎),都是由这样的一部内部信息处理机器所产生的。因此,对于人类行为的了解,就必须牵涉到对于人脑信息处理程序的了解。
3.从演化论角度看,诸种人脑的信息处理程序(如处理“知”、“情”、“意”的程序)都可以被视为“适应器”(adaptations)。这也就是说,这些程序之所以被演化出来,就是因为它们所催生的行为能够使得智人(Homo sapiens)在漫长的采集—狩猎时代进行成功的生存和繁衍。
4.上面所说的这些程序,或许是以相互独立的模块的形式而被组合在一起的,而不是一套通用问题求解策略的种种领域特殊化。这是因为,一种采取模块化策略的心理程序演化策略,能够更高地提高人脑处理外部信息的效率。
5.由于演化过程所消耗的时间量是漫长的,因此,在采集—狩猎时代定型的智人的心理程序是无法应对快速率的文化更新的。这也就是说,这些程序之所以被演化出来,本来主要是为了应付原始的生存环境,而未必适应日新月异的工业或后工业社会的环境。
6.对于人脑信息处理程序的演化论解释,能够帮助我们解释与之相关的各种重要人类文化现象(如音乐、语言、原始艺术、原始宗教等)的产生。对于熟悉马恩经典文献诠释传统的读者来说,演化心理学的上述论点或许显得过于“离经叛道”。具体而言,对于人的存在的二维性——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强调一向被识别为马克思主义人性观的核心论点,而演化论用一种统一的演化论模型来涵盖人类种种心理特征的理论尝试,就似乎等于抹杀了人的社会属性,或抹杀了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的文化发展对于人类固有本性的修正作用。另外,《手稿》也曾明确指出,“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人的机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得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它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11)。这也就是说,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人类的丰富精神活动是不能够还原为单纯的生殖目的的,而演化心理学却似乎正是给出了这种错误的还原。
但在笔者看来,上述这些担忧未必成立。首先,演化心理学固然试图寻找人类心理活动的生物学根据,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试图将个别的历史现象都还原为生物学或者遗传学分析。举个例子来说,演化心理学家并不特别关心为何中国南方人喜欢听评弹、陕北人爱听秦腔,他们更关心的是,为何对于音乐的某种抽象的心理学偏好会成为一个跨文化和跨阶级的人类学现象。很显然,对于此类问题的研究,在逻辑上并没有排斥对于塑成具体偏好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研究,相反,二者完全可以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并行不悖且相互印证。
其次,演化心理学固然承认,很多人类的心理性状之所以被自然选择所偏好,就是因为其能够提高个体的繁殖度,但是这并不等于要抹杀人类相对于其他动物而言的某种特殊性(比如语言能力、社交能力等),相反,演化心理学家恰恰有信心在自己的理论框架中安顿这些特殊性(参见演化心理学基本论点之六)。
再次,演化心理学家所言及的自然选择机制,其实只是以“盲目的钟表匠”的方式而悄然起效的,因此,“提高繁殖度”这一选择目的本身往往未被个体所意识到。而在个体可以意识到的层面上,很多非繁殖的生活目的,甚至某种关于“自由意志”的主观感受,其实都有机会得到涌现。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论点其实和上文所引用的《手稿》对于异化劳动的批判并未构成抵触:在那里,马克思只是批评了异化劳动使得人类的纯生物学机能(吃、喝、生殖)脱离了其社交机能,而成为劳动者有意识追求的唯一目的(并由此压抑了劳动者对自由选择的正常感受),但这并不能够使得我们就此做出对下述断言的有效否定:在一个无法为一般人类个体所意识到的层面上,以“繁殖度提高”为隐蔽指向的自然选择机制,依然构成了智人这个物种几乎所有关键心理特征得以出现的根本动力机制。
最后,马克思本人的确更为关心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具体的历史条件对于人类行为的塑造作用,但这不意味着任何对于具有跨文化稳定性的人性结构的研究肯定就不在他的视野之内。毋宁说,至少就《手稿》对于种种负面的“异化”现象的分析而言,这些分析实际上已经预设了有某种积极的“非异化”状态(即马克思所言及的“人的类本质”)的存在,甚至“类本质”这个提法本身,也暗示了某种跨文化的稳定人性结构的存在。
笔者之所以选中演化心理学(而不是心理学中的其他分支,或是像经济学、社会学那样的其他社科“显学”)成为重述《手稿》之“异化”观的新话语框架,是因为还牵涉到如下考虑:由于《手稿》对于人性(或“类本质”)异化机制的研究已然预设了一种对于“人性”的正面观点,因此,一种旨在为《手稿》祛魅化的解释性理论也必须以“人性”为问题域。诚然,对于“人性”的讨论在传统上一直是哲学家(特别是近代欧洲哲学家)的拿手好戏,但大多数的哲学人性论由于科学明晰性的匮乏,恐怕很难完成同为哲学理论的“异化”论祛魅之重任。这就逼得我们将目光从人本主义哲学转向已为自然科学方法所浸淫的社科领域。但具体哪一门社会科学适合执行这里所说的“祛魅”任务呢?不难想见,对于人性的专题化研究并非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济学只关心和经济活动相关的那部分抽象的人类行为,而不是完整的人性),也非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学关心的是具有人性的大量社会人聚合在一起后所产生的集体行为,而非人性本身),也不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人类学更关心的是人类的生物学体质和外部文化行为的演变,而不是某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人性”),甚至也不是心理学诸传统分支所研究的对象(发展心理学、人格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心理学传统分支,仅仅是对“人性”某个面相的抽象化研究,而未试图对所有这些分支加以整合)。相比较而言,目前我们还很难找到任何一个别的社会科学分支,能够像演化心理学那样,整合遗传学、动物行为学、发展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对智人的人性架构作出一种既具有领域广阔性、又不失科学严格性的描述。因此,就目前全球的社会科学发展态势来看,演化心理学很可能就是我们目前的“祛魅化工作”所能够依赖的话语平台。
四、对《手稿》之人性观的演化心理学解读
前面已论及,要厘清《手稿》之“异化”观,就不得不先牵涉到其人性观,因为“异化”之实质实为人性或人之本质的异化。在《手稿》中与该话题密切相关的关键词还有两个:一个是“对象化”,另一个是“感性”。前者强调的是在人类劳动中内部意识活动和外部自然环境设定之间深刻的因果关联,后者强调的是这种因果关联的直接性。换言之,马克思将“感性的”和“对象性的”这两个标签赋予人的类本质结构,就等于承认了人类在某种先天的意义上就直接是自然环境自身演变的产物。《手稿》中的下面这段评论集中表达了这层意思: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即自己的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说一个东西是对象性的、自然的、感性的,这是说,在这个东西之外有对象、自然界、感觉;或者说,它本身对于第三者说来是对象、自然界、感觉,这都是同一个意思。饥饿是自然的需要;因而为了使自己得到满足、得到需要、得到温饱,他需要自身之外的自然界、自身之外的对象。饥饿是我的身体对某一对象的公认的需要,这个对象存在于我的身体之外、是我的身体为了充实自己,表现自己的本质所不可缺少的。太阳是植物的对象,是植物所不可缺少的、确证它的生命的对象,正像植物是太阳的对象,是太阳的唤醒生命的力量的表现,是太阳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表现一样。(12)这无疑是让演化心理学家感到十分振奋的一段评论,因为它至少蕴含了五个在标准演化心理学体系中都能够得到确认的分论点:
(甲)人类的基本认知能力(以及各种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和心理欲望)均是自然界的产物,甚至人自身也是“自然存在物”。这一论点当然是符合某种最宽泛的演化论框架的。
(乙)人类的生理需求结构和心理欲望结构并不是由个体的自主意识所控制的,相反,是某种自然界配置的规定。演化心理学家自然也乐于承认这一点,并会补充说:这些心理配置是通过自然选择机制而慢慢形成,并通过遗传的方式而代代相传。
(丙)在对象性活动中人类主体得以确证其本质性力量——或说得再清楚一点,内部意识活动的精神产物(如某个三段论推理)的确证性,必须通过这些精神产物的行为结果在外部环境中的成功程度(如某个三段论推理帮助我消除饥饿的程度)而得到担保。站在演化心理学的立场上看,该说法似乎就暗合了后者将人类的心理配置视为环境适应器的论点,因为作为“环境适应期”的心理机制自身的本质机能,当然需要通过“它是否真的能适应环境”这一外部校准来加以担保。
(丁)马克思在《手稿》中反复指出,对象性活动具有“感性”的特征。站在演化心理学的立场上看,这指的即是大量感知模块登记外部输入信息时的高效性和即时性(而这也肯定是长期自然选择的产物)。
(戊)作为对于上述四点的补充,《手稿》在引文中所说的“对象化活动”,并不像有些学者所理解的那样,指的是胡塞尔式的意向投射活动,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何引文提到植物和阳光之间也有这种“对象化活动”(难道植物也能够成为意识主体吗)?从演化心理学的立场去解读,这只可能是指一种生物体自身固有的信息编码方式,比如,绿色植物的遗传编码自身就决定了其必须经历光合作用才能够存活,就像人类的遗传编码形式就决定了其存活离不开对于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一样。由此看来,一种普泛的演化论解释是完全可以把马克思对于植物的“对象化活动”和人的“对象化活动”的讨论纳入同一个理论框架的:因为人类的心智结构对于外部环境的适应也好,植物绿叶之生化结构对于阳光的适应也好,虽然复杂程度彼此迥异,却在根本上都是自然选择之盲目力量的最终结果。
除了引文中所提到的“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个长长的表语之外,马克思还特别强调人性本质架构中的另一个维度——社会维度:
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即从事一种我只是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直接交往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都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因此,我从自身所做出的东西,是我从自身为社会做出的,并且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存在物。(13)乍一看,上述引文似乎对笔者引入的演化心理学解释框架颇为不利,因为马克思笔下的“社会性”往往带有一种超越于动物王国的意蕴(请参看他在《手稿》别处所说的:“动物只是按造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14))。然而,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在演化心理学或(作为其前身的)社会生物学的框架中指出人类的社会习性的某种特异性,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使用某种准自然科学的手段来探究这种特异性。相反,关于《手稿》对于“社会性”的这种言谈,演化心理学家恰恰有大量的备选科学假设可以加以解释。比如,谈到人类之社会性得以彰显的最关键环节——语言——的出现时,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去驱使演化心理学家们去否定智人的语言能力和其相关的自然选择机制之间的因果关系,或去否定语言能力对智人在采集—狩猎时代的繁殖适应性所产生之助益。演化心理学平克和布鲁恩如是说:
人类在其一生中需要海量之信息。正是因为这种信息获取的速率远超生物演化的速度,因此,它就能够在人类在其生活中遭遇到各种不可预期的突发事件时提供无价之助益。这样一来,和那些仅仅依靠漫长演化所积累的策略来防御自身、抵制威胁的物种相比,人类也便获得了一种决定性的竞争优势。以语言的方式获取关于世界的知识,还能够带来另外的一个好处,即通过对于由大量他人之世代积累所构成的大量技能的利用,人们在获取知识前,就不必再重复前辈辛苦求索的过程,不必再经历那些或许会带来危险的试错过程。此外,当你身处于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协作的群体之中的时候,群体中其他成员的内部状态,就是你在世界中所最需获取的知识。这样一来,对于那些确有很多东西要表达,且彼此之间亦相亲相熟的生物来说,对于知识和内部状态的交流就会带来很大的裨益。(15)
由上文的讨论来看,《手稿》对于人性的本质规定的三个环节——对象性、感性和社会性——都可以在一个普泛的演化心理学框架中得到崭新的解读。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种解读将如何帮助我们理解《手稿》的“异化”观。
五、演化心理学视野中的异化劳动
前文已经提到,马克思在《手稿》里提到了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劳动产品对劳工的异化、劳动活动对劳工的异化、人之类本质对劳工的异化,以及发生在劳工之间的人与人关系的异化。
先来看第一重异化:“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6)青年马克思认为,这是一个引发他对于异化劳动之所有讨论的“经验事实”。
今天的经济学家或许会为马克思所说的这一点“事实性”表示困惑。这是因为,只有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商品囤积才会导致商品售价的下降,而供不应求的商品,即使绝对产量很大,依然可以维持比较理想的价位,而由此产生的销售利润中的一部分也很可能会反馈给劳工。不过,在笔者看来,青年马克思对于第一重异化的描述未必就一定要被解读为对于某些经济学现象的概括——它也可以被视为对于某种人类学现象的概括。
这一点集中体现于他对机器在劳动中作用的讨论。从表面上看来,机器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并在单位时间内增加了产品产量,然而——
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一部分工人成为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带来了愚钝和痴呆。(17)这段话千万不能够被解读为浪漫主义者对于一切现代科技的负面情绪发泄,因为马克思在《手稿》别的地方恰恰肯定了,科技的大规模运用“为人的解放做了准备”(18)。毋宁说,马克思在此想表达的意思是,根据资本增值之抽象需要而被组织起来的、并充分利用机器的生产方式,本身是对人类本性的某种戕害。
我们现在完全可以从演化心理学的角度对这个论点提供补充性说明。我们知道,现代化工业化生产形式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高度分工——劳动者长时间地被固定在一个工作岗位上,机械重复着同样性质的劳作。这其实是我们智人在采集—狩猎时代演化而来的大脑所未曾遭遇过的新境遇,因为采集—狩猎时代的生产活动具有与之完全不同的质的规定性。具体而言,当时的分工仅仅是以性别分工或者年龄分工的形式存在的,经济活动从生产到消费的整个链条也都可以通过直观而被劳动者所把握到。另外,那时的个体亦有比较充分的机会在不同的采集任务和不同的捕猎任务之间加以自由选择,由此磨砺自身全面的心智能力。但不幸的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被束缚在流水线上并被强迫分工的广大劳工阶层,则被剥夺了行使这种原始心智禀赋的权利,而这种剥夺则很可能会导致大脑在神经层面上的不适应(如杏仁核的恐惧产生机制的启动),并使得诸多其他负面心理情绪得以展现。这就导出了异化劳动的下一个规定——劳动活动对劳工的异化:
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9)站在演化心理学的角度去解读,这重异化无疑说的就是在工业化生产条件下,未跟得上社会演化速率的“原始”心理机制所产生的种种机能失调或不适应症。
前面所说的两重异化都具有“现象描述”的特征,而热衷于进行本质性概括的马克思显然不可能止步于此。这就导出了他笔下的异化劳动的第三重规定:
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自身相异化。(20)马克思的大致意思是说,在非异化条件下,人之类存在的塑成乃是劳动的指向和目的,而在异化条件下,人的类存在竟然反过来沦为了劳动的手段,成为了抽象的资本运作中可以计量和控制的一个环节。站在演化心理学的立场上看,这指的就是工业社会的信息处理模式和采集—狩猎时代所塑成的大脑的固有信息处理模式(即马克思所说的“类本质”)之间的冲突。前面已提及,按照大多数演化心理学家的意见,智人的大脑已经预装了大量应对原始环境下生存任务的问题求解策略,而原始智人的每一次捕猎成功都在强化这些策略在个体大脑中的神经回路的建构强度,并在间接的意义上增加了和这些策略相关的神经结构被自然选择所长期偏好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智人的较为稳定的生理—心理机制(即类本质)的塑成,自然就可以视为智人和其自然环境之间的长期斗争(即劳动)的某种自然(而非刻意为之的)衍生物。而在工业化条件下,资本运作的信息流程则以一种对远快于生物学演化的速度出现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并迅速强迫大量的从采集—狩猎时代慢慢演化而来的劳动者的大脑(当然也包括资本家自身的大脑)服从这一新的信息处理方式。在这种崭新的生产条件下,个体劳动者对于“成功”的定义被彻底颠覆——“成功”不再被定义为“猎取一只野猪”之类的可被人类感官直接把握的结果,而是被定义为对于抽象的符号化货币的获取。生产规模的惊人扩大化,则在另一方面又使得整个生产的真正目的对个体劳动者而言变得毫无意义。这样一来,原本对猎物敏感的神经回路,现在被“训练”得只对货币敏感;原本关心于整个生产活动之成败的个体信息加工过程,现在被“训练”得只对个体的肉体生存有兴趣;原本成为生产活动之自然衍生物的智人的心智结构,现在则成为了工业产生有目的、有计划地加以改造和利用的对象。
人类大脑的强大可塑性,固然允许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其固有的信息处理方式加以一定程度的改造,但从演化心理学的角度看,这种“后天”对“先天”的“矫正”过程却不可能永远毫无节制地进行下去。不难想见,一旦这种“训练”逾越边界而过于挑战劳工内心深处的“野蛮人积习”,那么,其反叛的怒火就迟早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爆发出来。
对于工业社会的经济统治秩序的最集中反叛形式,当然就是无产阶级发动的阶级斗争。但在青年马克思看来,在异化劳动的现实中,使得阶级斗争得以可能的社会心理学基础(如劳工之间惺惺相惜的阶级意识)却或许是稀缺的。这就引出了异化劳动的第四重规定:
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同自己的劳动,自己的劳动产品和自身的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人同他人,同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21)这也就是说,就像异化社会使得人的类本质成为劳动的手段而非目的一样,它也能够使得劳动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成为劳动的手段而非目的。
站在演化心理学的立场上看,马克思的上述评论,指的就是工业生产所塑造的新人际关系和智人的大脑所长期适应的亲缘网络之间的严酷张力。前文已经谈及了,智人大脑已经在采集—狩猎时代演化出以语言能力为代表的社交能力的环境压力,以便在残酷的生存资源争夺战中获取(针对敌对部落的)信息资源的优势以及(对本部落而言的)集体凝聚性。也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下,原始神话、原始艺术、原始宗教都慢慢应运而生了。不过,这样的环境参数在典型的工业化生产的条件下已经被大大改变。在新的环境条件下,一个工人既不需要知道(也往往很难知道)整个生产流程的全部信息,亦不需要知道和他在同一个车间工作的工友的内部心理状态,因为这些信息和他是否能够获取工资没有直接关系。他真正需要知道的,是他是否能够像一个零件一样满足流水线生产的需求,以及和他配合的其他工友能否同样好地实现同一工业流程所赋予他们的功能角色。除此之外,一切都是“不正经的闲谈”。
但正如前文所已经指出的,渴望“闲谈”的“野蛮人积习”毕竟已经有着远比工业文明自身漫长得多的历史,即使这些积习被车间内的正规工艺流程暂时压抑住了,也迟早会在别的地方找到发泄口。现代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就恰恰表明,普通现代人的社交圈的构成方式,像极了采集—狩猎时代原始人的社交圈(22)——这或许就是对于工业异化所造成的心理失衡的某种廉价的补偿。当然,充满革命精神的青年马克思是不可能满足于这种局部修补的平衡方案的,因为它们至多只能暂时缓解异化之病痛,而无法成为治愈异化病根之药方。在《手稿》中,他就此给出的最终药方乃是共产主义。
六、演化心理学视野中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在《手稿》中是如此描述“共产主义”的:
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说来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的社会的形式。(23)他在此说得清楚,共产主义主要是作为一个历史发展的环节和原则出现的,因此并非是能够被独立切割开来予以辨识的对象。马克思在别处补充道:
无神论、共产主义绝不是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的消逝、舍弃和丧失,即绝不是人的采取对象形式的本质力量的消逝、舍弃和丧失,绝不是返回到非自然的、不发达的简单状态去的贫困。恰恰相反,它们倒是人的本质的或作为某种现实东西的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对人来说的真正的实现。(24)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了,共产主义指的就是一种指向人之类本质之实现的“实现活动”(但不是一种既定的实现状态)。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实现”不是把已经逝去的东西重新找回来(因为我们其实从来没有彻底失去过我们的类本质),而是将工业文明暂时遮蔽的类本质从“潜能”状态转化到“现实”状态。
站在演化心理学的立场去解读,马克思在此表达的意思,不妨可以被理解为对这样一个社会改造工程的提议:我们应当对于后工业时代的生产和生活流程进行重新设计,以便就此重新构造出一个能够使之适应智人原始心理架构的、友好的新环境界面(但同时却在界面的“后台操作”中尽力保留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换言之,“共产主义”应当被视为对用以治疗“工业文明心理机能失调症”的所有措施的总称。很显然,考虑到这种治疗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我们并不能够指望现代工业文明负载在人类心理结构之上的负荷能够得到一种一劳永逸的释放——相反,这种“减负”过程必定是渐进性的和动态式的。所以,我们也不可能从认识论角度找到一个标准,以便将异化社会和非异化社会之间的界限厘定得清清楚楚。从这个角度看,人类社会扬弃异化的历程,或许会和异化历程本身长相伴随,而任何拔苗助长的跃进反倒可能会事与愿违。
就此,笔者已用演化心理学的解释框架,尝试着对《手稿》之“异化”论的各个面相做出了一种或许还显得十分粗糙的新诠释。最后需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历史不长的新社会科学分支,演化心理学自身也并非没有遭遇过学界的批评,因此,本文的很多具体结论也的确有待更为深入的学术探讨的检验。不过,至少就本文开首所规定的“祛魅化”任务而言,经过这种崭新解释的《手稿》的“异化”论,至少应当能够比其原始形态更容易被哲学圈外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所理解,并激起他们对于《手稿》更多的理论兴趣。同时,亦希望拙文能够为更多的对于马恩经典的跨学科研究工作,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注释:
①“祛魅”这个提法是笔者采自于韦伯,原意指现代化和世俗化的社会进程使得中世纪社会赋予某些事物的神秘化色彩消退。在本文中,这个词泛指对于任何难解事物的明晰化重构。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译文根据英文本稍有调整。英文版版本信息:Karl Marx: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944,translated by Martin Millgan,Prometheus Books,New York,1988.
③网址: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marx/#2.3。
④Allen W.Wood:Karl Marx,Second Edition,Routledge,New York,2004,p.4.
⑤[英]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叶笃庄、杨习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⑥[英]达尔文:《人类和动物的情绪》,周邦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⑦[美]威尔逊:《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毛盛贤等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⑧Jerome Barkow,Lead Cosmides and John Tooby(eds.):The Adapted Mind: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the Generation of Cultu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 and New York,1992.
⑨对于急需了解演化心理学基本观点的读者来说,美国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演化心理学权威布斯(David Buss)主编的《演化心理学手册》亦不失为一部详实而可靠的指南书。至于该领域内值得推荐的中文书籍,则有熊哲伟翻译的巴斯的《进化心理学》,朱新秤的《进化心理学》和张雷的同名著作等。
⑩Tooby,J.and L.Cosmides,2005,"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in The Handbook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D.Buss(ed.),Hoboken,NJ:Wiley,pp.5-67.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1页。
(12)(13)(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4—325、301—302、274页。
(15)Steven Pinker and Paul Bloom:Natural Language and Natural Selection,in Jerome Barkow,Leda Cosmides and John Tooby(eds.):The Adapted Mind: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the Generation of Cultu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 and New York,1992,p.460.
(16)(17)(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7、270、307页。
(19)(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0、274页。
(21)(23)(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4—275、311、331页。
(22)现代人的社交圈一般由150个成员构成,其中有5个核心成员、包含前者的12—15人情感圈、包含前二者的35人情感圈(与狩猎采集营地共宿者的数量大致相同)、包含前三者的150人圈(与采集—狩猎时代的整个家族人口成员不相上下)。(请参见Robin Dunbar、Louise Barrett、John Lycett:《进化心理学:从猿到人的心灵演化之路》,第110—111页,万美婷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1)
标签:心理学论文; 人性论文; 演化心理学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人性观论文; 经济学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心理学发展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马克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