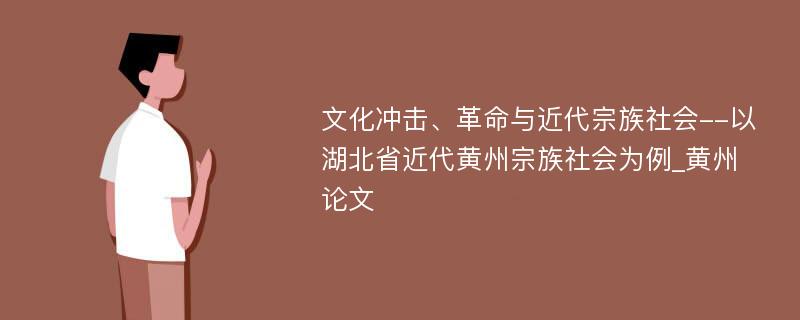
文化冲击、革命与近代宗族社会——以近代湖北黄州宗族社会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宗族论文,近代论文,社会论文,湖北论文,为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以近代黄州宗族社会为个案,考察文化冲击、革命与近代宗族社会关系。作者认为清末以来西方文化冲击使近代宗族社会传统士绅领导阶层出现断层,新文化运动及马克思主义传播又使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从思想上完成对宗族制度的批判,成为农村社会革命的领导者。农村社会革命实现对宗族制度的物质批判,而它又是清末以来文化冲击的发展。
关键词 黄州;宗族社会;文化冲击;革命;社会变迁
以男性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是传统农村社会的普遍社会组织,它是血缘宗法文化传统在唐宋以后地主经济与小农经济矛盾对抗下的产物。近代以后,随着外来文化的深入传播与中国现代化努力的不断加强,宗族面临着与血缘宗法文化迥然不同的外来文化冲击,并遭受以新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农村社会革命洗涤。那么,文化冲击如何作用于近代宗族社会?文化冲击与近代农村社会革命关系如何?文化冲击、革命又与近代宗族社会变迁关系如何?本文以近代黄州宗族社会为例,探讨文化冲击、革命与近代宗族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以说明近代宗族社会变迁的若干特点。
一、文化冲击与近代宗族社会的抗拒及变迁
近代宗族社会首先面对西方宗教文化冲击。大约在19世纪60年代,西方传教士开始以武汉、九江等沿江口岸城市为中心向黄州宗族社会渗透,黄州地区以沿江口岸城市为中心形成两大传教区:以九江为中心,形成以黄梅、广济、蕲州等地为范围的传教区;以武汉为中心,形成以麻城、黄冈、黄安、蕲水等地为范围的传教区。传教士以城镇或集镇教堂为据点,深入宗族社会传教布道,企图以西方宗教文化驯服宗族农民。
但西方宗教文化并没有真正深入宗族社会内部。尽管教堂常常以物质手段吸引农民,如黄梅县“因为下乡经常闹水灾,有很多灾民过九江讨饭,九江大教堂就利用这个机会,煮粥饭施给灾民,趁机劝他们入教”[①],但收效甚微,即使个别因此而皈依西方宗教的农民,也会因无法在宗族立足而搬入城镇或集镇依附教堂。黄州的西方宗教信徒并不多,而且大部分信徒聚集在宗族社会边缘——城镇或集镇。广济县天主教在其发展高峰也仅有教徒400余人,大部分集中在东南与西南部的城镇及集镇[②]。西方宗教传教活动大多局限在城镇与集镇地区,黄梅县基督教“孔垅教会,每作一次礼拜,有二、三十人参加,大部分是集镇上的人。孔垅东街有三百多户,入教的占二十户左右。”[③]
西方宗教文化未能深入近代宗族社会,乃是宗族文化与西方宗族文化激烈对抗的结果。宗族文化以近祖崇拜为核心,以众多的祖先祭祀活动为其特征,“有家祭,有祠堂之祭,有茔墓之祭。”[④]这种祖先祭祀文化奉始迁祖或先祖为宗族的保护神,祭祀活动上升为“以神尊之”的宗教活动[⑤]。以始迁祖、先祖及高、曾、祖、考为祭祀对象的近祖崇拜甚至发展到“非祖不祀”[⑥],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而西方宗教以上帝为惟一真神,反对偶像崇拜与祖先崇拜,劝人依靠上帝而得救,这就直接与近祖崇拜发生信仰冲突,招致宗族传统士绅与农民的顽强抵抗。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正当西方传教士极力突破宗族篱笆时,黄州发生武穴教案、麻城教案、蕲州教案等10起规模较大的教案[⑦]。教案冲突的文化背景即是近祖崇拜的宗族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对抗。1888年11月27日的蓝杰教案更直接是因为近祖崇拜与上帝崇拜的信仰文化冲突所造成,“蓝姓户族以蓝世叨不务正业,弃祖宗而信教,不许其入谱,教士从中干涉,引起民教争执。”[⑧]因此,尽管清朝统治者对西方宗教传播采取放任态度,“内地已有三、四教,复加一教亦无碍”[⑨],但西方宗教传播始终遭到宗族文化的抗拒,并没有融为宗族社会的另一教,更没有带来近代宗族社会的变迁。
另一种近代文化传播方式——新式学堂教育则深刻影响近代宗族社会。学堂教育本来是传统宗族社会士子士人走向王权系统的桥梁。晚清以后,出现大量以学习西方科学文化为主的新式学堂,吸纳大批宗族社会士子士人。特别是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新式学堂成为宗族社会士子士人的唯一出路。湖北在新式学堂教育方面尤得风气之先,黄州各地的府、县、州学也较早采用新式教育,并大量创办各种新式学堂,其学堂数与学生数均居湖北前茅。这些新式小学堂或先或后、或多或少地开展过新式教育。黄冈吴贡三在学堂中讲授经学、史学、地理、时务等课,以新式教育启迪殷子衡等人[⑩]。而黄州高一层次的中学堂则比较系统地开展新学教育,张知本主持的广济文普通中学堂开设经学、国文、修身、英文、博物、格致、历史、地理等课,基本上以新学教育为主。近代西方科学文化通过新式学堂已经在宗族社会士子士人阶层中广泛传播。
宗族社会士子士人之所以能够顺利接受新式教育,其原因是在于他们长期受儒家正统文化的薰陶,与宗族农民不同,他们具有一定的儒家理性精神与经世思想,这种理性精神与国家意识在民族危机与西方文明刺激下能够与西方文化相沟通,较快接受西方文化观念。士子士人接受新式教育,开始世界观与思维方式的转变,脱离家——族——国的观察世界模式而代之以世界眼光观察中国,批判尊卑长幼的伦理型文化而代之以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政治思想。黄冈熊十力读到新学中的格致启蒙课本及《天演论》,感到眼界大开,如梦方醒,深深佩服“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思想[11]。甚至有不少黄州籍青年学子在由旧式的士子士人转向近代知识分子过程中,成为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革命者,据贺觉非编著的《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介绍,参加组织领导辛亥武昌首义的黄州籍革命志士大多系新式学堂的毕业生、肄业生或学生,较著名的有詹大悲、宛思演、查光佛、田桐、居正、方震、梅宝玑、李西屏、万鸿喈、李长庚、屈子厚、张振武等人。
宗族社会士子士人转化为近代知识分子,他们再也不可能发生士子士人→科举仕进→士绅转变而重新回到宗族社会,大多数为早期现代化事业所吸纳而留居近代文明气息浓厚的城市或市镇,不愿意回到旧式伦理控制的宗族社会,并较少与宗族发生联系。《湖北县政概况·黄冈》(1934年)说:“黄冈在科举时代,人材颇盛,晚近从事于军政界者,多侨居外埠。”广济县刘显户,明清两代有在籍文庠生光泽、珍公、玉汉等25人,清末至民国时期受过新式教育的刘贤基等5人则均在外地落户,较少与刘显户往来[12]。传统士子士人是宗族社会的重要组织力量,士子士人的转变与流失使宗族社会传统士绅领导阶层出现断层,并且引发宗族组织领导力量及宗族社会关系的变化。
虽然传统士绅对宗族社会的控制持续到大革命前,但由于士子士人的流失,宗族统治权正逐步向恶霸地主手中转移,形成大革命前豪绅恶霸统治宗族社会的局面。而恶霸地主对自己经济利益的关注远远超过对宗族集体的关心,“各垸自满清以后,从无世家大户捐产”[13],公产不仅停止增长,而且逐渐为宗族统治者所蚕食。伴随组织经济基础的削弱,宗族组织凝集族众的能力不断减弱,宗族统治越来越依靠强权与暴力。
由于近代知识分子与宗族社会的天然联系,近代思想文化主流也通过近代知识分子媒体而深入宗族社会,“呜呼,自欧风东渐,妇竟言平等”[14],新的思想文化观念冲击宗族血缘伦理观念与血缘伦理关系,宗族内部统一的“尊尊”血缘伦理关系逐步削弱,而房(分、支)、亲房、家庭内部的“亲亲”关系逐渐膨胀,宗族内部关系由于统治力量变化与观念变化而向无序化方向发展。
尽管以新式教育为方式的文化传播带来宗族社会的若干变化,但这种文化冲击并不可能导致宗族社会的根本变迁。近代宗族社会的农业生产力与商品经济关系并未充分发展,农村生产与生活仍然需要血缘互助关系,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仍然需要宗族制度加以保护,近代文化冲击必然遭到宗族组织力量的顽强抵抗而不可能发生很大作用。事实上,文化冲击所带来的文化观念变化往往发生在与近代文明有较多接触的“才智之士”家庭,“自欧风东渐,物竞天择之说倡,一般才智之士处心积虑,惟求满足个人欲望,鲜有济人利物为念”[15],其所带来的社会关系变化也仅仅是局部与有限的变化。只是在大革命时期,以革命方式传播的新文化才在宗族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新文化哺育的革命知识分子与农村社会革命的发动
辛亥革命后,中国现代化事业严重受挫。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从中西社会文化对比角度寻找阻碍中国现代化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文化原因,发动新文化运动,对封建礼教与传统家庭——宗族制度展开激烈批判。陈独秀指出中国“以家族为本位”与西方“以个人为本位”的根本对立[16],吴虞则指出宗族制度为专制主义的“根据”[17]。“五四”运动前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先进知识分子又以唯物史观批判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文化。李大钊认为家庭——宗族制度是两千年来中国社会的“基础构造”,他将中国社会结构解释为农业经济(经济基础)——宗族制度(基本社会组织)——专制主义,宗族制度居于核心地位,专制主义与一切旧思想、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则是宗族制度的上层建筑,认为只有消灭宗族制度才能彻底推翻专制统治与消灭旧礼教,主张进行消灭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与宗族制度的社会革命[18]。
新文化与“五四”运动所掀起的新文化狂飙巨澜深刻影响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如果说清末由士子士人转化而来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着对家庭——宗族制度某种藕断丝连的情怀,那么在新文化哺育下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则从理性上完成对家庭——宗族制度的彻底否定,对宗族制度与宗族文化展开彻底批判。武汉青年知识分子所办的《新空气》载文批判“孝”为“野蛮时代一些狡狯大家拿种种手段压制人的社会性充分发展的结果”[19],国民党的《新湖北》提出:“打破一切不自然的恶习惯、恶风俗、恶制度及崇拜偶像之思想,破除现行婚姻家族制度及种种迷信”[20],宗族制度与宗族文化成为进步舆论所共弃的社会现象与文化现象。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所孕育的思想批判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必将演化为对宗族社会的经济制度与文化制度的物质批判。
由于宗族社会有比较发达的初级教育网络,大多数小地主、富农、甚至一些中农家庭子弟均有接受教育的机会,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穷而鄙”的读书人。民国以后,城市新式教育有所发展,吸纳了宗族社会大批“穷而鄙”的读书人。但黑暗军阀统治使早期现代化严重受挫,社会事业日趋萧条,大量中小知识分子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悲剧,特别是“穷而鄙”的读书人更面临着生活出路问题。他们在为个人的出路深深苦闷的同时,对国家民族命运与社会问题十分敏感,正如董必武所说:“穷而鄙的读书人,才是真能立志改造世界的人,救中国的人。”[21]经过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洗礼,大量“穷而鄙”的读书人迅速转化为革命知识分子,进步青年学生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如在武汉读书的黄安籍青年学生王健、王秀松、戴克敏、戴季伦、雷绍潜、董觉生、汪奠川,麻城籍蔡济璜、王幼安、刘文蔚、桂步蟾及罗田籍肖方均经董必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从事农民运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知识分子是黄州农村社会革命的主要发动者与领导者。黄梅县38位大革命与土地革命领导人中,早期发动者有大学及专科学历5人,高中及初中1人,小学6人;县级领导人有大学及专科学历7人,高中及初中6人,小学8人;区级领导人有大学及专科学历1人,小学4人[22]。黄麻起义时期的中共黄安县委与麻城县委基本上由中小知识分子党员所组成,《麻城县委报告》(1929年5月)说:麻城“县委会全系知识分子,如区书记均为知识分子”[23]。
革命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发动与领导农村社会革命,其家庭背景及其士子士人前身的身份地位提供了重要条件。革命知识分子在城市生活中只能算作“穷而鄙”的读书人,但其小地主、富农家庭在宗族社会中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毛泽东曾经说过:“农村中略分为三种阶级,即大、中地主阶级,小地主、富农的中间阶级,中农、贫农阶级。富农往往与小地主利害联在一起。富农土地在土地总额中占少数,但与小地主土地合计,则数量颇大”,小地主与富农在宗族社会往往能够左右中农、贫农阶级,贫农“往往接受中间阶级的意见,不敢积极行动”[24]。而近代知识分子前身——士子士人阶层又在宗族社会具有特殊的地位,受到一般农民的普遍信奉与尊崇。
革命知识分子正是利用其家庭的影响力与其前身的号召力,以宗族的“一员”深入宗族社会内部发动农村社会革命。他们首先举办平民学校以启发农民觉悟。早在大革命前,黄梅县革命知识分子“组织一个少年黄梅学会,升起‘到民间去’的大旗”[25],在开展反帝反封的平民教育基础上,革命知识分子进一步在宗族内部凝集革命力量。1924年10月,黄梅县程鹤林与同族程建勋、程兰田等13人秘密组织黄梅县蒋家咀农民研究会,形成初步革命组织。在黄安县,毕业于武汉大学附中的曹学楷以义学形式在自己家乡自办一所小学,农民子弟免费进学读书,晚上开办农民夜校,开展反帝反封教育,培养一大批革命骨干,并在此基础上于1926年8月组建七里坪区第一个农民协会。革命知识分子在宗族内部完成革命发动工作后,又以此为中心向外发展,如麻城青年学生王树声回乡发动宗族农民,并以王家祠堂为中心,通过同学、朋友关系向外发展,终于在1926年9月15日组建石槽冲农民协会,形成较大的革命力量[26]。
革命知识分子“家为地主富农的多,贫雇农少”[27],他们往往通过家庭革命来倡导农村社会革命,极大鼓舞长期处在地主阶级及其族权重压下的农民投身革命。他们“当众宣布把自家的土地全部交还给农民,宣布从此再也不收租收息,并且拿出钱粮向佃户退押,还当众烧了地契租契。”[28]黄安紫云区吴焕先(麻城蚕业学校学生)实行家庭革命,“所有赊欠帐项,一律作废;除留四斗丘田外,其余田地契约也烧毁了,焕先父亲气得吐血”[29],农民深受鼓舞,在吴焕先领导下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斗争。麻城王树声回乡后宣布不收稞,“我家的稞子你莫送”[30],农民迅速发动起来,形成强大革命洪流。
历史的发展往往具有讽刺意味。在传统社会,小地主、富农及士子士人是宗族制度的社会基础,在维护宗族组织中起着支柱作用;而在近代社会,由于近代文化冲击所带来的思想观念巨变,小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革命知识分子却成为宗族社会经济制度与文化制度的领头掘墓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近代农村社会革命乃是近代文化冲击的一种革命性反应。
三、革命与近代宗族社会
近代农村社会革命以近代新文化为思想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反对农村社会旧的经济制度与文化制度,因而它必然遭到宗族社会血缘宗法文化传统、地主统治阶级及其族权系统的抵抗。1926年的《湖北农民》载文说:“我们农民,现在都渐渐明白了,晓得团结团体、组织农民协会,来解除痛苦”,“谁知我们刚刚开步向前走,就被两个青面獠牙的恶鬼扯住了脚!是哪两个恶鬼呢?一个就是‘家族观念’,一个就是‘地方观念’”,“因为‘家族观念’,就是叫我们只晓得有族人,不但族人做得对要帮助,就是做得不对也要帮助”[31]宗族观念与宗族关系成为地主阶级抵抗农村社会革命的有力工具。
在不同的地区,宗族观念与宗族关系对农村社会革命的阻碍又有不同的表现。在豪绅恶霸势力强大、血缘宗族关系较弱的地区,农民易于打破宗族观念而形成革命力量。黄安、麻城东北部山区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由于抵抗交界山区“匪患”与白莲教势力需要,当地豪绅与以团练起家的恶霸相勾结,形成以乡勇武装为后盾、以区会为压迫农民工具的豪绅恶霸势力。他们广占土地,大量宗族农民沦为他们的佃户。黄安七里有“大地主占田达一千亩至一千五百亩者”[32]。麻城王福店丁家畈共有108户,其中近百户是大地主丁焕章的佃户[33]。豪绅恶霸充当区长、会首,掌握乡勇武装,以强权与暴力压迫剥削农民,“欺压百姓很厉害”[34]。而这一地区由于山区地理环境影响人口聚居规模,很难形成较大规模的宗族聚居,血缘宗簇关系并不十分发达,农民特别强烈感受到豪绅恶霸势力的压榨。当革命知识分子“迭向农民演说”,“农民闻之,甚为觉悟,纷纷要求加入农协会,不三日成立四个乡农民协会,总共会员有五百余人。”[35]因而黄麻地区能够很快地形成革命高潮,并以黄麻地区为中心形成鄂豫革命根据地。
在黄州的丘陵河谷平原地区,大量人口集合形成大规模以地缘与血缘关系相结合的宗族村垸,豪绅恶霸与中间阶级、一般农民在宗族内部结合紧密,形成强大的宗族组织关系。豪绅恶霸势力利用宗族关系抵抗农村社会革命,他们组织假农协,或直接利用宗族力量对抗农民协会。在蕲水县,当革命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夏葆中组织栗寺坳区农民协会时,当地高姓恶霸利用宗族势力将夏葆中活埋于姚家坪,结果引起高、夏两姓宗族械斗,高姓农民迟迟未能发动[36]。在黄冈县,“仓埠萧耀南族属,恃有大批枪支,大肆反动,县府、党部要求派兵镇压”[37],西乡“在昔多巨绅显宦,例多挟厚资,凭藉政权,族大人众,压迫乡邻,无所不至。……日前锦屏山第六区,曾有劣绅程庆余,勾结反动分子,及其族众数千人,捣毁区农协。”[38]在麻城、黄安河谷平原与丘陵地区,一些豪绅恶霸也利用宗族关系抵抗农协,麻城“殷家垸土豪商首元、商思见、商南生……伙同商宏焕、商福成等数百人,到处捣毁党部农协,抢劫党员家。”[39]
甚至在土地革命高潮时期,豪绅恶霸仍然利用宗族关系挟制农民反抗革命。一些豪绅恶霸利用族姓矛盾煽动宗族民团进攻苏区村垸,广济六村董、孙、苏三姓民团1930年6月进攻黄梅、广济边界苏区的张姓村垸,湖嘴上民团进攻苏区李贞垸与杨门村垸,革命与反革命的对抗又表现出宗族械斗的特点。一些宗族统治者还利用血缘宗族关系煽惑苏区村垸农民背叛革命,“广济反动土劣运用封建族姓关系,煽惑群众一夜反水,虽经过迅速反击,压下了反动气焰,但情况仍然紧张。”[40]宗族观念与宗族关系成为革命深入发展的严重障碍。
但是,尽管豪绅恶霸利用宗族关系阻碍革命,近代农村社会革命毕竟有其内部原始动力,农民有强烈的减轻租额、反抗租佃剥削的要求,农村社会革命正是在农民这种要求基础上发生与发展,形成排天巨浪,冲击着宗族社会的社会结构、宗族制度乃至宗族文化。
首先,革命冲垮宗族社会结构与族权系统,建立新的农村社会组织模式。在农民革命冲击之下,大部分地区的豪绅恶霸或被枪决、或逃亡、或低头认罪,麻城县豪绅李舜卿等一批大士豪劣绅被革命政权所枪决,一些小土豪劣绅则为农民协会所斗争,豪绅恶霸威风扫地,族权系统顷刻土崩瓦解。黄梅县妇女冲进昔日族权象征的祠堂,接着又成立了乡村苏维埃,宗族组织为基层苏维埃所取代。其次,革命传播新文化与冲击传统宗族文化。广济县干仕垸革命知识分子带头将家中的祖宗牌位、司命菩萨丢进阴沟,浠水县“凡一切城隍庙、南岳庙、东岳庙、三官殿、溪潭坳岳王庙的泥木菩萨是一律打碎,扫地出门。”[41]男尊女卑的观念也受到冲击,妇女在大革命中挣脱宗族制度与宗族文化强加给她们的枷锁,浠水“1927年上半年全县要求婚姻自由、包括寡妇再嫁的案件,共达260多起,都得到了处理,新风蔚起,人心大快。”[42]
虽然大革命与土地革命先后失败,黄州农村社会又恢复旧的宗族统治,但革命已经造成一个新的社会态势,祠堂与血缘宗法伦理已被革命冲刷去其神圣性与尊严,革命中残存下来的传统士绅开始自动走下历史舞台。革命后的蕲州“乡区绅耆,尤多隐居自好之士,日趋于消极,缺乏培植社会观念”;浠水县“以前土劣,自民十六年以后,所受打击甚深,现尚各自敛迹,不敢与闻地方事件”;麻城县士绅“自民十六年以后,被匪共之压迫,四乡士绅,多逃避武汉,现虽逐渐归来,但老成者,因环境关系,多抱消极主义,对于地方事务不愿负责。”[43]广济下朱祥户,原来“户事由慕臣主持,因慕臣大父系前清举人,生父系恩赐进士,兄弟多,房头大,家产丰,本人又是秀才,真是一言九鼎,人莫敢违。至民十六年后,人心不古,统治力渐渐消沉。”[44]宗族组织已经丧失其“敬宗收族”的组织精神而演化为依靠强权与暴力的社会团体,宗族社会趋于严重无序与衰败之中。正是由于近代文化的不断冲击与革命,加剧近代宗族社会的崩溃。到1949年,革命终于在广大农村打倒地主阶级及宗族制度,结束千百年来农村社会血缘宗法统治。
但是,文化冲击与革命并不可能代替社会经济力量而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并不可能真正完成社会转型。文化冲击与革命不可能取消农业手工劳动方式与自然经济的存在,农村社会生产与生活仍然需要家庭以外的血缘与地缘合作关系,家庭——血缘群体关系仍然为农村社会的基础关系,一切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组织必然受其制约。只有在农村经济发生根本性转变基础上,农村社会才能最终完成由传统血缘宗族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注释:
① ③ 新版《黄梅县志》,宗教。
② 新版《广济县志》,宗教。
④ 民国《湖北通志》卷21引《蕲州志》。
⑤ 光绪《黄安县志》,风俗。
⑥ 黄梅《高氏宗谱》,序。
⑦ 参阅《湖北通志》,新政;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 湖北,1860—191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1。
⑧ 据教务档:湖北教务,1—7辑,转引自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 湖北,1860—1916》。
⑨ 曾国藩:《教务纪略》例言。
⑩ 贺觉非编著:《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
11 熊十力:《十力语要》,湖北十力丛书印本(1947年),卷3,第63页。
12 广济《刘氏显户宗谱》,世系。
13 广济《塍塘湖张孟一户概况》。
14 广济《刊水张氏宗谱》,宗兄复初先生传暨嫂氏胡孺人行述。
15 广济《刊水张氏宗谱》,张蒲洲先生暨哲嗣瑞先生合传。
16 陈独秀:《东西方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载《新青年》第1卷第4号。
17 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见《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8 李大钊:《从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的原因》,见《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19 《新空气》第1卷第2号。
20 《新湖北出版宣言》,载《新湖北》第1卷第1期。
21 转引自刘仲衡《在董老哺育下的“人社”》,载《武汉文史资料》第15辑。
22 据新版《黄梅县志》,人物志。
23 转引自谭克绳、江抗美《论革命知识分子在创建鄂豫皖苏区中的历史作用》,载《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6期。
24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25 李子芬:《湖北黄梅县一年来社会运动的报告》,载《中国青年》第89期,1925年8月22日。
26 30 33 34 见《麻城革命史料调查》,麻城市档案馆档案1—325号卷。
27 29 周业成:《回忆黄麻起义》,载《湖北文史资料》第1辑。
28 肖永正:《从麻城起义到西入川陕》,载《天津文史资料》第6辑。
31 学武:《鬼扯住了我们的脚》,载《湖北农民》第9期,1926年12月7日。
32 见《红安七里区革命史料简编》,麻城市档案馆档案1—343号卷。
35 《麻城土豪破坏农民协会》,载《湖北农民》第11期,1926年12月27日。
36 41 42 邓谷:《大革命时期的浠水》,载《湖北文史资料》第21辑。
37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3日。
38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3日。
39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5日。
40 中共黄梅县委书记老杨致毕竟成信,载《广济县党史资料汇编》。
43 《湖北省政概况》(1934年),蕲春,浠水,麻城。
44 广济《朱姓户族概况》。
标签:黄州论文; 文化冲击论文; 汉口民国日报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社会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黄冈论文; 家庭观念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麻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