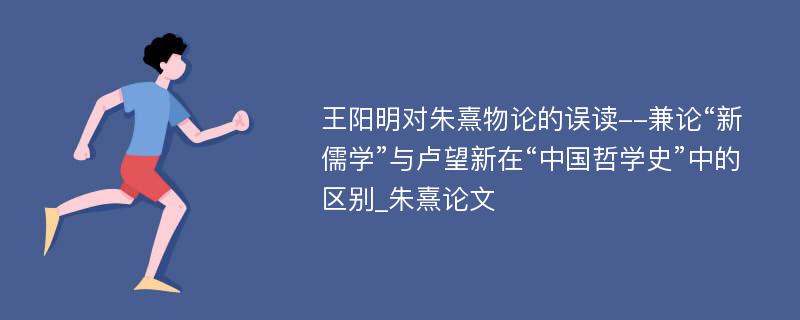
王阳明对朱熹格物论的误读——兼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对朱熹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分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朱熹论文,哲学史论文,误读论文,理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4)09-0020-06 朱熹学术与陆九渊存在着差异,把朱熹学术界定为“理学”,并与陆九渊“心学”对立起来,可以追溯到王阳明对于朱熹格致论的误读。王阳明不仅把陆九渊的学术界定为“心学”,而且认为,朱熹的格物论是“析心与理而为二”,以为在朱熹那里,“理”与“心”是对立的。民国时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识别出王阳明的误读,但并没有予以纠正,而是进一步把朱熹学术界定为与陆王“心学”相对立的“理学”,并成为学术界流行的解读朱熹学术的基本模式。 一、对陆九渊“心学”的界定 对于朱陆的差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指出:“若以一二语以表示此二派差异之所在,则可谓朱子一派之学为理学,而象山一派之学则心学也。王阳明序《象山全集》曰:‘圣人之学,心学也。’此心学之一名,实可表示出象山一派之所以与朱子不同也。”①显然,冯友兰是依据王阳明之说,把陆九渊的学术界定为“心学”,并进一步把朱熹学术界定为“理学”,以解说朱陆的差异。 王阳明《象山文集·序》之所以称“圣人之学,心学也”,是由于在他看来,尧、舜、禹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即“十六字心传”相授受,“此心学之源也”;“孔孟之学,惟务求仁,盖精一之传也”;孔子要门人“求诸其心”,孟子讲“仁,人心也。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②在此基础上,王阳明进一步认为,陆九渊“接孟子之传”,“其学之必求诸心”,所以,“陆氏之学,孟氏之学也”③。与此同时,王阳明特别强调圣人的“心学”与“析心与理而为二”是截然对立的,所谓“析心与理而为二,而精一之学亡”。 显然,王阳明《象山文集·序》是把陆九渊的学术界定为“心学”,而把朱熹学术排除在“心学”之外。但早在王阳明之前,朱熹《中庸章句·序》在论述尧、舜、禹至孔、孟的道统之传在于“十六字心传”,还在《中庸章句》中明确指出:“此篇(《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④ 朱熹虽然没有明确把圣人的道统之学称为“心学”,但是,他的再传弟子真德秀撰《心经》并附赞曰:“舜禹授受,十有六言,万世心学。”何基在解说朱熹诗句“大哉精一传,万世立人纪”时认为,此诗句“明列圣相传心学之妙,惟在一敬”⑤。显然是把朱熹《中庸章句·序》所谓尧、舜、禹至孔、孟的道统之学称为“心学”。 朱熹门人黄榦撰《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⑥,进一步把朱熹列入了自尧、舜、禹至孔、孟的以“十六字心传”为核心的道统,而把陆九渊排除在外。朱熹门人陈埴甚至明确指出:“格物致知,研穷义理,心学也。”⑦直接称朱熹的学术为“心学”。 可见,无论是朱熹还是阳明都认为,尧、舜、禹至孔、孟所相授受的是“十六字心传”。朱熹称之为“心法”,其后学称之为“心学”,阳明也称之为“心学”;黄榦把朱熹纳入传授心法的道统,而把陆九渊排除在这一道统之外。相反,王阳明则把陆九渊归属于“心学”,而把朱熹排除在外。 王阳明读过朱熹《中庸章句》。朱熹《中庸章句》在注“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时指出:“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⑧王阳明在《紫阳书院集序》中则指出:“君子之学,惟求得其心。虽至于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孟氏所谓‘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学者,学此者也;审问者,问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辩者,辩此者也;笃行者,行此者也。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故心外无学。”⑨他甚至还说:“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⑩显然,王阳明是接受朱熹所谓“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 既然王阳明讲“圣人之学,心学也”与朱熹《中庸章句·序》相一致,同时又接受朱熹《中庸章句》所谓“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并由此发展出“心外无事,心外无理”的“心学”,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像朱熹门人那样把朱熹归于“心学”呢?这是由于在王阳明看来,朱熹的学术是“析心与理而为二”,因而被排除在圣人“心学”之外。 二、“析心与理而为二” 朱熹为《大学》作“格物致知补传”,讲“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11)。对此,王阳明说:“朱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即物穷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而为二矣。”(12)事实上,王阳明对于朱熹格物论的这一解读,纯属误读。 朱熹《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讲“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朱熹《大学或问》对“天下之物”作了具体说明,把“天下之物”分为:“心之为物”、“身之所具”、“身之所接”以及“外而至于人”、“远而至于物”。关于“心之为物”,朱熹说:“其体则有仁义礼智之性,其用则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情。”(13)所以,朱熹的格物,既指向外部事物,又指向人的内在的心,包括人的性、情。与此同时,朱熹《大学章句》一开头注“明明德”曰:“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14)对此,《大学或问》解释说:“惟人之生乃得其气之正且通者,而其性为最贵,故其方寸之间,虚灵洞彻,万理咸备,盖其所以异于禽兽者正在于此,而其所以可为尧舜而能参天地以赞化育者,亦不外焉。”(15)《朱子语类》载朱熹说:“明德是自家心中具许多道理在这里。”(16)又说:“能存得自家个虚灵不昧之心,足以具众理,可以应万事,便是明得自家明德了。”(17)显然,朱熹《大学章句》所谓“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实际上就是讲“心具众理”。由此可见,朱熹“格物致知补传”讲“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即物而穷其理”,是既讲事事物物有理,又讲“心具众理”。 朱熹较多地讲“心具众理”。他的《孟子集注》说:“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朱熹还说:“心虽是一物,却虚,故能包含万理”(18);“心之全体湛然虚明,万理具足”(19);“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20)。朱熹还赞同门人李孝述所言:“心惟虚灵,所以方寸之内体无不包,用无不通,能具众理而应万事”(21);“心具众理,心虽昏蔽而所具之理未尝不在”(22)。朱熹既讲“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又讲“心具众理”,因此并不是“析‘心’与‘理’而为二”,朱熹《大学章句》讲“心具众理”,那么,为什么不直接探究其“心”而要通过“格物”以穷天下万物之理呢?《大学章句》注“明明德”,不仅讲人之心“具众理”,而且还接着说:“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23)《朱子语类》载朱熹说:“明德是自家心中具许多道理在这里。本是个明底物事,初无暗昧,人得之则为德。如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从自家心里出来,触着那物,便是那个物出来,何尝不明。缘为物欲所蔽,故其明易昏。如镜本明,被外物点污,则不明了。”(24)在朱熹看来,人之心“具众理”,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而不明。既然为不明,又如何明?所以,必须通过“即物穷理”,“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25)。朱熹《大学或问》则说:“至于一日脱然而贯通焉,则于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义理精微之所极,而吾之聪明睿智,亦皆有以极其心之本体而无不尽矣。”(26)由此可见,在朱熹那里,格物致知的过程,即是明白心中之理的过程,而不是“析‘心’与‘理’而为二”。 在朱熹看来,格物致知之所以能够使心“豁然贯通”,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是因为“物我一理”。据《二程遗书》载,问:“观物察己,还因见物反求诸身否?”程颐曰:“不必如此说。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合内外之道也。”(27)对此,朱熹作了具体说明。据《朱子语类》载:问:“格物须合内外始得?”朱熹曰:“他内外未尝不合。自家知得物之理如此,则因其理之自然而应之,便见合内外之理。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兽,皆有理。草木春生秋杀,好生恶死;仲夏斩阳木,仲冬斩阴木,皆是顺阴阳道理……自家知得万物均气同体,‘见生不忍见死,闻声不忍食肉’,非其时不伐一木,不杀一兽,‘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此便是合内外之理。”(28)朱熹还认为,只要通过格物,“今日明日积累既多,则胸中自然贯通。如此,则心即理,理即心,动容周旋,无不中理矣”(29)。 朱熹在讲“即物而穷其理”的同时,特别强调格物致知并不是“不求诸心,而求诸迹,不求之内,而求之外”,指出:“人之所以为学,心与理而已矣。心虽主乎一身,而其体之虚明,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物,而其用之微妙,实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内外精粗而论也。然或不知此心之灵,而无以存之,则昏昧杂扰而无以穷众理之妙;不知众理之妙,而无以穷之,则偏狭固滞而无以尽此心之全。此其理势之相须,盖亦有必然者。”(30)显然,朱熹既承认“心具众理”,又承认万物之理的存在,而且还特别强调万物之理统一于心。 对于朱熹所谓“人之所以为学,心与理而已矣”,王阳明说:“心即性,性即理,下一‘与’字,恐未免为二。此在学者善观。”他还说,“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邪?晦庵谓:‘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间,而未免已启学者心理为二之弊。”(31)在王阳明看来,只有心的存在,才有物理的存在,“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32),朱熹以为心之外有理的存在,就是“析‘心’与‘理’而为二”。 但在事实上,朱熹虽然承认心之外有理的存在,但又认为“心具众理”,万物之理统一于心,尤其是,朱熹还明确讲“心与理一”。他说:“心与理一,不是理在前面为一物。理便在心之中。”(33)“仁者心与理一,心纯是这道理。”(34)并以此与释家相区分,指出:“儒、释之异,正为吾以心与理为一,而彼以心与理为二耳。”(35)又说:“吾以心与理为一,彼以心与理为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其所见处不同。彼见得心空而无理,此见得心虽空而万物咸备也。”(36)因此,在朱熹那里,“心”与“理”并不是对立的,不能认为朱熹是“析‘心’与‘理’而为二”。 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观点 1934年出版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是“当时水平最高的一部中国哲学史”(37),其中“于朱子之学多所发明”(38),并特别强调,在朱熹那里,“理”与“心”是完全不同的,“心亦是实际的有,亦系‘形而下’者。若理则只潜存,故为‘形而上’者”(39)。 对于王阳明说朱熹是“析心与理而为二”,冯友兰指出:“朱子以为人人具一太极,物物具一太极。太极即众理之全体;故吾人之心,亦‘具众理而应万事’。故即物穷理,亦即穷吾心中之理,穷吾性中之理耳。故谓朱子析心与理为二,实未尽确当。”(40)显然,冯友兰已经识别出王阳明对于朱熹在“理”与“心”的关系上的误读。但冯友兰明确认为,在朱熹那里,“理”与“心”是完全不同的,因而又认可了王阳明所谓朱熹“析心与理而为二”的说法。他说:“惟依朱子之系统,则理若不与气合,则即无心,心虽无而理自常存。虽事实上无无气之理,然逻辑上实可有无心之理也。若就此点谓朱子析心与理为二,固亦未尝不可。”(41) 尤为重要的是,冯友兰还以朱熹讲“理”与“心”的不同阐述朱熹与陆王的对立。他说:“朱子言‘性即理’。象山言‘心即理’。此一言虽只一字之不同,而实代表二人哲学之重要的差异。盖朱子以心乃理与气合而生之具体物,与抽象之理,完全不在同一世界之内。心中之理,即所谓性;心中虽有理而心非理。故依朱子之系统,实只能言‘性即理’,不能言‘心即理’也。象山言‘心即理’,并反对朱子所说心性之区别。”又说,“依朱子之系统,只能言‘性即理’,不能言‘心即理’。依朱子之系统,只能言有孝之理,故有孝亲之心;有忠之理,故有忠君之心。不能言有孝亲之心,故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依朱子之系统,理之离心而独存,虽无此事实,而却有此可能。依阳明之系统,则在事实上与逻辑上,无心即无理。此点实理学与心学之根本不同也。”(42) 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这些观点,张岱年于1937年完成的《中国哲学大纲》予以赞同,并且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不仅把朱熹与陆王的学说分别称为唯理论与唯心论,而且还特别强调朱熹唯理论在根本上不同于张载的唯气论,对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1993年,张岱年在《我与中国20世纪》中指出:“近几十年来,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大多认为宋明理学分为两大学派,即程朱学派与陆王学派。我在此书(《中国哲学大纲》)中首次提出:自宋至清的哲学思想,可以说有三个主要潮流,一是唯理论,即程朱之学;二是唯心论,即陆王之学;三是唯气论,即张载、王廷相、王夫之以及颜元、戴震的学说。这一论点到近年已为多数哲学史家所承认了。”(43) 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以朱熹讲“理”与“心”的不同阐述朱熹与陆王的对立,学术界也有不同意见。贺麟于1938年的一篇论文中说道:“七八年前,当我作《朱子黑格尔太极说比较》一文时,我即指出朱子之太极有两义:(一)太极指总天地万物之理言;(二)太极指心与理一之全体或灵明境界言。所谓心与理一之全,亦即理气合一之全(但心既与理为一,则心即理,理即心,心已非普通形下之气,理已非抽象静止之理矣)。”(44)在这里,贺麟不仅继续强调朱熹的“心与理一”,而且明确认为,朱熹讲“心与理一”,即“心即理,理即心”。 1945年,张东荪发表《朱子的形而上学》,明确认为,朱熹既讲“性即理”又讲“心即理”,同时又认为,在朱熹的学术思想中,“性即理”与“心即理”是相互联系的。该文还引朱熹所言“心与理一,不是理在前面为一物,理便在心之中”,指出:“心之所以能具理,只是由于性使然。须知性即理也。由理造成的性则当然可使心能与理打通……故明心即是尽性;尽性即是穷理;穷理即是理之自己完成。说心、说性、说理乃完全是一回事。因而有‘心即理’与‘性即理’之言”(45)。 1948年,钱穆发表《朱子心学略》,开宗明义便说:“程朱主性即理,陆王主心即理,学者遂称程朱为理学,陆王为心学,此特大较言之尔。朱子未尝外心而言理,亦未尝外心而言性,其《文集》、《语类》,言心者极多,并极精邃,有极近陆王者,有可以矫陆王之偏失者。不通朱子之心学,则无以明朱学之大全,亦无以见朱陆异同之真际。”(46)既大致同意冯友兰从理学与心学对立的角度阐述朱子学,又不满意于此,而强调要从研究朱熹“心学”入手,特别研究朱熹学术思想中关于“心”与“理”的关系问题。于是,钱穆通过大量引述朱子所言,以证明朱子不外心言理,不外心言性,而且还引朱熹所说“心与理一,不是理在前面为一物。理便在心之中”,认为朱熹“明言心即理处尚多”(47)。该文最后得出结论:“我常说,一部中国中古时期的思想史,直从隋唐天台禅宗,下迄明代末年,竟可说是一部心理学史,个个问题都着眼在人的心理学上。只有朱子,把人心分析得最细,认识得最真。一切言心学的精彩处,朱子都有;一切言心学的流弊,朱子都免。识心之深,殆无超朱子之右者。今日再四推阐,不得不承认朱子乃当时心理学界一位大师。”(48) 朱熹《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讲“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即物而穷其理”,王阳明由此推断朱熹“析心与理为二”,是由于他不了解朱熹的“天下之物”包括“心之为物”,而且朱熹也讲“心具众理”,“心与理一”。就文本而言,我们很难找到朱熹把“理”与“心”对立起来的言论,王阳明认为朱熹“析心与理为二”,这仅仅是一个需要证明的推断。与此相反,朱熹讲“心具众理”、“心与理一”,却是不争的事实。就推断而言,王阳明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通过剪裁朱熹的思想,仅仅以有利于自己的证据作为前提,因而这一推断需要作进一步的完善和论证。就结论而言,王阳明推断朱熹“析心与理为二”,明显与朱熹讲“心具众理”,“心与理一”相矛盾,因而属于误读。 事实上,朱熹的“理”,既是“形而上”的理,又是“形而下”的万物之中的理。就“形而上”的理而言,理与“形而下”的心是不同的,这一不同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不同。就“形而下”而言,理与心是相互联系的。王阳明推断朱熹“析心与理为二”,以为心与理是同一的,显然是就“形而下”而言,但在这一层面上,朱熹只是讲“心具众理”、“心与理一”,而没有“析心与理为二”。所以,尽管可以因为朱熹讲“形而上”的理,而称之为“理学”,但不可以这一“形而上”的理与“形而下”的心形成对立,并进一步认为有“理学”与“心学”的对立。 问题是,王阳明对于朱熹格物论的这一误读,实际上成为冯友兰把朱熹学术界定为“理学”并与陆王“心学”对立起来的理论源头,一直为学术界所接受。因此,重新根据朱熹的文本,而不是根据前人对于朱熹的误读,全面而深入地分析朱熹的学术思想,显得尤为重要。 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938-939页。 ②王阳明:《象山文集·序》,载《王阳明全集》上册卷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45页。 ③王阳明:《象山文集·序》,载《王阳明全集》上册卷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45页。 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7页。 ⑤何基:《何北山先生遗集》卷3《解释朱子斋居感兴诗二十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0页。 ⑥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63《勉斋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23页。 ⑦陈埴:《木钟集》卷8《礼记》,文渊阁四库全书。 ⑧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页。 ⑨王阳明:《紫阳书院集序》,载《王阳明全集》卷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39页。 ⑩王阳明:《传习录中》,载《王阳明全集》卷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9页。 (1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7页。 (12)王阳明:《传习录中》,载《王阳明全集》卷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4-45页。 (13)朱熹:《四书或问·大学或问》,载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27页。 (1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页。 (15)朱熹:《四书或问·大学或问》,载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07页。 (16)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4,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3页。 (17)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4,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5页。 (18)黎靖德:《朱子语类》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8页。 (19)黎靖德:《朱子语类》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4页。 (20)黎靖德:《朱子语类》卷9,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55页。 (21)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续集》卷10《答李孝述继善问目》,载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805页。 (22)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续集》卷10《答李孝述继善问目》,载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817页。 (2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页。 (24)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4,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3页。 (2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页。 (26)朱熹:《四书或问·大学或问》,载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28页。 (27)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18,载《二程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93页。 (28)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5,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96页。 (29)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8,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08页。 (30)朱熹:《四书或问·大学或问》,载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28页。 (31)王阳明:《传习录中》,载《王阳明全集》卷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2页。 (32)王阳明:《传习录中》,载《王阳明全集》卷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5页。 (33)黎靖德:《朱子语类》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5页。 (34)黎靖德:《朱子语类》卷37,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85页。 (35)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6《答郑子上》,载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689页。 (36)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6《答郑子上》,载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691页。 (37)张岱年:《近百年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文史知识》1999年第3期。 (38)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载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3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927页。 (40)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955页。 (4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955页。 (4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956页。 (43)张岱年:《我与中国20世纪》,载《张岱年全集》第8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11页。 (44)贺麟:《与张荫麟先生辩太极说之转变》,《新动向》1938年第1卷第4期。 (45)张东荪:《朱子的形而上学》,《中大学报》1945年第3卷第1-2合期。 (46)钱穆:《朱子心学略》,《学原》1948年第2卷第6期。 (47)钱穆:《朱子心学略》,《学原》1948年第2卷第6期。 (48)钱穆:《朱子心学略》,《学原》1948年第2卷第6期。标签:朱熹论文; 王阳明论文; 心学论文; 儒家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心即理论文; 冯友兰论文; 理学论文; 哲学史论文; 宋明理学论文; 读书论文; 朱子全书论文; 陆九渊论文; 朱子语类论文; 国学论文; 中华书局论文; 哲学家论文;
